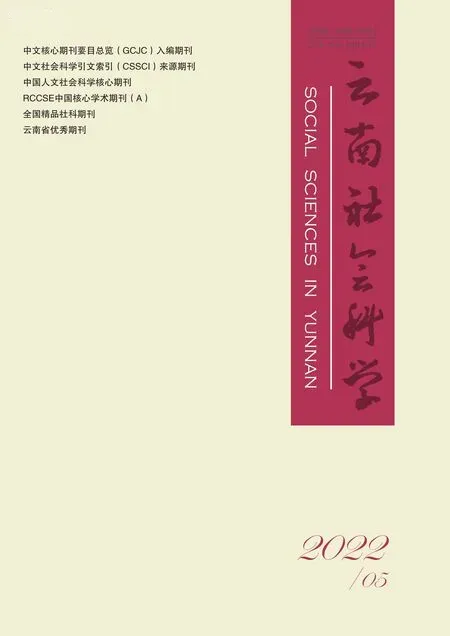濾鏡修辭下的“鄉(xiāng)土發(fā)現(xiàn)”:從視覺預(yù)設(shè)、互動界面到空間收編
劉漢波
濾鏡(filter)原本是指攝影技術(shù)中的濾光鏡,包含UV 鏡、柔光鏡、漸變灰鏡、偏振鏡、減光鏡、星光鏡等可組裝的附加鏡片,旨在改善照片的美觀程度或產(chǎn)生特殊的效果①宋協(xié)祝、白研華:《圖文處理及制版》,北京:印刷工業(yè)出版社,2008 年,第43 頁。,是拍攝前置于鏡頭前端或底部以改變相機光學(xué)成像效果的實體鏡片。隨著應(yīng)用層面的下沉和技術(shù)語境的變更,濾鏡不再是攝影設(shè)計從業(yè)人員或愛好者的專屬配件,而是備受網(wǎng)民青睞的視覺釋義工具。它既是眾多圖像處理軟件的特殊算法和內(nèi)部程序,讓用戶以極低的時間成本為圖像模擬各種物理成像效果;又是當(dāng)今備受青少年網(wǎng)民關(guān)注的、具有高度儀式化的互動慣例(interactional routine),通過容顏重塑、風(fēng)格切換、掛件添加等功能,讓用戶的社交媒體身份(social media identity)符合大眾審美的規(guī)范標(biāo)準(zhǔn),并帶來切實的社交效益。②Jeremy Hunsinger,The Social Media Handbook,New York: Routledge,2013,pp.59-75.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和智能算法組成的媒介生態(tài)下,國內(nèi)大部分社交軟件的圖像上傳環(huán)節(jié)均配備濾鏡功能。濾鏡紛至沓來,一些攝影、圖像類APP 甚至主打濾鏡品牌,聯(lián)合攝影師和“攝影網(wǎng)紅”開發(fā)濾鏡販賣。它們的消費群體以青年網(wǎng)民為主,16—35 歲的用戶占比達77.2%,其中一二線城市用戶占62.8%。③艾瑞咨詢:《2020 年中國美顏拍攝類APP 用戶營銷價值洞察報告》,北京:艾瑞咨詢研究院,2021 年,第7 頁。可以說,“濾鏡社交”成為了城市青年網(wǎng)民的互動常態(tài)。
與此同時,濾鏡圖像所觸達的場景也漸趨多元。經(jīng)歷了“景點種草”“網(wǎng)紅打卡”“云旅游”等一系列風(fēng)潮后,濾鏡實現(xiàn)了“空間轉(zhuǎn)向”——主題化、風(fēng)格化、場景化的濾鏡不僅可以“美顏”,還可以“美景”,尤其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背景下,互聯(lián)網(wǎng)不斷聚焦鄉(xiāng)村場景,讓景觀也逐漸成為濾鏡處理的重要對象。單是在抖音平臺,截至2021 年10 月,旅游內(nèi)容創(chuàng)作人已達10.5 萬人,鄉(xiāng)村旅游視頻累計播放量達1.84 萬億次,旅游打卡次數(shù)13.7 億次,鄉(xiāng)村旅游題材視頻創(chuàng)作同比增長338%。①Fastdata 極數(shù):《2021 年旅游助力中國鄉(xiāng)村振興研究報告》,天津:虎鯨數(shù)據(jù)科技,2021 年,第41 頁。然而,一系列“翻車”現(xiàn)象也不斷引發(fā)公眾輿論:小紅書的“濾鏡景點”被指責(zé)“濾鏡欺騙”②中國青年網(wǎng):《火爆的“濾鏡景點”,背后竟有這些業(yè)務(wù)》,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296325046731322&w fr=spider&for=pc。,被眾多“網(wǎng)紅”套上“文藝風(fēng)濾鏡”的網(wǎng)紅野餐受到非議③澎湃新聞:《被網(wǎng)紅審美綁架的中國野餐》,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92683?isComm=true。,就連進軍“網(wǎng)紅界”的野餐和露營也開始貼上“精致審美”的標(biāo)簽④澎湃新聞:《年輕人正流行“野奢”旅行:風(fēng)格露營+精致審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80684。。這場由濾鏡充當(dāng)重要技術(shù)媒介的“鄉(xiāng)土發(fā)現(xiàn)”不僅是新媒介語境下城市青年引流鄉(xiāng)村場景的行為,更涉及圖像修辭機制、視覺話語權(quán)和空間闡釋權(quán)的問題。城市青年在審美潮流、青年亞文化和文娛資本的聯(lián)動助推下如何對鄉(xiāng)村場景進行編碼,鄉(xiāng)村場景又如何由“可見物”轉(zhuǎn)變?yōu)椤翱烧f物”⑤[法]雅克·朗西埃:《圖像的命運》,張新木等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 年,第9 頁。,并反過來吸引城市青年投入“圖像功能”,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
一、從暗房到明室:由“一切從簡”的濾鏡發(fā)展史說起
濾鏡從實體到虛擬的詞義轉(zhuǎn)換,可以追溯到Photoshop 軟件的誕生。1987 年,在美國密歇根大學(xué)攻讀博士學(xué)位的托馬斯·諾爾(Thomas Knoll)編寫了一個名為“Display”的程序,用于在黑白顯示器上顯示灰階圖像。因其兄約翰·諾爾(John Knoll)的影視特效公司需要,他優(yōu)化了該程序,增加了色彩調(diào)整、圖像校正、羽化等功能,并改名為“Photoshop”。這款能夠在后期改變圖像顯示形態(tài)的軟件受到Adobe公司的青睞,公司買下發(fā)行權(quán)后,于1990 年推出了Photoshop 的1.0 版本。之所以說Photoshop 的誕生開啟了圖像處理的“濾鏡紀(jì)元”,是因為它極大地降低了圖像后期修整的人力成本、物質(zhì)成本和時間成本——在膠片時代,暗房里的沖印師固然也可以通過鋼針擦刮、紗布遮罩、相紙傾斜、二次曝光等物理手段改變照片的亮度、細(xì)節(jié)、透視和內(nèi)容,但需要特定的人(沖印師)、固定的場合(暗房)和大量的時間,三者缺一不可。Photoshop 是膠片后期和數(shù)碼后期的分水嶺,它改變了攝影過程中人的時空感知,也縮窄了技術(shù)路徑與審美意圖之間的距離,讓具體化的自我經(jīng)驗在個人全權(quán)把握的圖像修整中實現(xiàn)主體的遷延(Deferral)⑥[美]艾米利亞·瓊斯:《自我與圖像》,劉凡等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13 年,第73 頁。,下放了“凝視”的技術(shù)使用權(quán)力,為人們提供了一套簡化的、用于“表征自我”的圖像服務(wù)。饒有意味的是,也正是1990 年,柯達推出了數(shù)碼相機DSC-100,開啟了人類數(shù)碼攝影的元年。在此前百年人類的攝影實踐中,攝影的前期和后期是涇渭分明的——不管是拍與被拍,前期都需要“自我”的參與;而沖印和修整這類后期程序,則普遍需要經(jīng)由“他者”代勞。Photoshop 的出現(xiàn)和數(shù)碼攝影的開啟重合在一起,讓身體操持相機而“凝視”外部世界的動作與“自我”懷揣審美意圖而加工視覺信息的欲望高度結(jié)合在一起。
然而,Photoshop 的面世只是勾勒了濾鏡這種圖像技術(shù)的雛形,因為此時它面臨著一個家用數(shù)碼攝影拋來的難題:如何更便捷地處理大量數(shù)碼相機拍攝的無損格式數(shù)碼底片(RAW 圖像文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Adobe 公司于1993 年發(fā)布了第一代Adobe Camera RAW(下文簡稱ACR),這款內(nèi)嵌于Photoshop 的插件除了能夠調(diào)整明暗、顏色、透視等基本圖像選項外,還能保存xmp 格式的圖像預(yù)設(shè),隨存隨取,以便批量地處理大量數(shù)碼照片。正是ACR 的圖像預(yù)設(shè)功能,卸下了人類以數(shù)碼方式開啟視覺表意通道后的“表征的負(fù)重”,也無意中確定了濾鏡的本體內(nèi)涵——視覺預(yù)設(shè)(Preset)。隨著數(shù)碼相機的型號越來越豐富,數(shù)碼后期的日常需求越來越大,簡化的界面、快捷的操作、批量的預(yù)設(shè)這三大ACR 核心服務(wù)愈發(fā)重要,以致于Adobe 公司將其功能單獨移植出來,開發(fā)成獨立的軟件。2006 年9 月,Adobe公司發(fā)布了后期工具Lightroom 的Beta 4 版本,這個脫胎于ARC 的獨立軟件在正式發(fā)售后改名為“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Lightroom 意為“明室”,與膠片時代的暗房遙相呼應(yīng),主要面向數(shù)碼攝影、圖形設(shè)計、批量處理的用戶,支持各種相機的RAW 圖像,用于數(shù)碼相片的瀏覽、編輯、整理、打印等。2010 年前后Lightroom 發(fā)展到2.0 版本,適逢4G 技術(shù)和自媒體興起,視覺預(yù)設(shè)也因社交媒體的圖像展示需求而演化出更為簡單便捷的“菜單式”預(yù)設(shè)形態(tài),即以風(fēng)格或功能命名的預(yù)設(shè)組。它們包括日系膠片、復(fù)古膠片、數(shù)碼負(fù)片、自然色等風(fēng)格類型,功能上涵蓋風(fēng)光、人像、婚禮、街景、美食等應(yīng)用場景。時至今日,Lightroom 宣傳其預(yù)設(shè)功能的時候依然打著“一鍵切換風(fēng)格”(Add style in a single click)的口號。
而正式讓Adobe 公司開創(chuàng)的視覺預(yù)設(shè)從詞義上轉(zhuǎn)變?yōu)闉V鏡的,當(dāng)屬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后大量涌現(xiàn)的美圖類APP。在國外,名為Instagram 的圖片社交軟件于2010 年上市,并透過不斷研發(fā)的濾鏡組開啟了圖像社交的先河,其中一系列提供歐洲風(fēng)情色彩影調(diào)的濾鏡更一直推廣至今,被網(wǎng)民稱為“INS風(fēng)”濾鏡。創(chuàng)始人斯特羅姆(Kevin Systrom)曾直言Instagram 的目標(biāo)是“為了讓手機攝影變得更快速、美觀和有趣。我們從經(jīng)驗中了解到,在手機上拍照并不能帶來我們想要的結(jié)果,所以我們創(chuàng)造了濾鏡,以獲得更藝術(shù)化的體驗”①指北:《“濾鏡”們可能等不到春天了》,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532295。。而在國內(nèi),自2008 年“美圖秀秀”的前身“美圖大師”上線后,濾鏡的功能便從光影調(diào)性、色彩調(diào)整、形狀裁剪、遮罩添加等基本功能延伸到美白、祛斑、面部重塑、瘦身、涂鴉、貼紙等“感官工序”。其“美圖配方,一鍵出片”的宣傳語和Instagram 的理念不謀而合,均指簡單快捷地套用圖像風(fēng)格預(yù)設(shè)。現(xiàn)如今,Snapseed、Snapchat、VSCO、黃油相機、MIX、潑辣等專攻濾鏡的美圖類APP 儼然建成了端口矩陣,日常生活中的攝影攝像行為,由“按照已經(jīng)規(guī)定的方式來生產(chǎn)具有象征性的平面”②[巴]威廉·弗盧塞爾:《攝影的哲學(xué)思考》,毛衛(wèi)東等譯,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shù)出版社,2017 年,第25 頁。,轉(zhuǎn)變?yōu)殡S時隨地在公共語域共享私人經(jīng)驗的媒介內(nèi)容,人們對物理空間的認(rèn)知權(quán)力進一步交付于數(shù)碼化的圖像捕捉。在這種社交網(wǎng)絡(luò)語境下,濾鏡與“特效”“美顏”等功能不斷交織乃至混同③王瑩、張建:《濾鏡特征的歸類分析與大眾美圖再設(shè)計賦能研究》,《工業(yè)工程設(shè)計》 2021 年第3 期。,并在整體上呈現(xiàn)出三種類型:第一,容顏濾鏡,以膚色調(diào)節(jié)、膚質(zhì)優(yōu)化、五官建模和肢體重塑為主;第二,風(fēng)格濾鏡或調(diào)色濾鏡,不在圖像中添加或刪減像素,旨在更改圖像的曝光參數(shù)、明暗影調(diào)、色彩模式來實現(xiàn)畫面基調(diào)的風(fēng)格化;第三,掛件濾鏡,主要是通過“貼紙”功能為圖像添加徽標(biāo)、矢量圖、藝術(shù)字等,以達到某種裝飾效果,尤其是短視頻興起后,外掛花字和實時跟蹤五官位置的裝飾掛件備受歡迎。不管濾鏡功能如何延伸、細(xì)化,其發(fā)展態(tài)勢都是一致的——“一切從簡”,讓圖像修整變得更簡便,讓用戶自我敘事的邊界不斷拓展,讓人們可以在任何時間、從任何地方、對任何圖像進行風(fēng)格套用和視覺編輯。
近年,中國的新媒體經(jīng)歷了2016 年的“直播元年”、2018 年的“短視頻元年”、2019 年的“智能算法元年”和2021 年的“元宇宙元年”,泛視頻成為流量高地,視覺化社交開展了一場由城至鄉(xiāng)的下沉游徙,不僅招攬了一大批鄉(xiāng)鎮(zhèn)用戶,還圍繞鄉(xiāng)村場景催生出新的視覺素材。隨著諸多“短視頻+鄉(xiāng)村振興”成功范例不斷推廣,加上后疫情時代以“云旅游”為代表的“非接觸式”服務(wù)的興起,“鄉(xiāng)土中國”進入了自媒體視覺生產(chǎn)的視野,鄉(xiāng)村場景也開始被濾鏡所表述。這意味著,國內(nèi)濾鏡使用范圍的變化促使了濾鏡功能的泛化與轉(zhuǎn)型:從圖像形式上看,濾鏡由靜態(tài)照片普及到動態(tài)視頻;從作用對象上看,濾鏡不再局限于人像題材的容顏美圖,而進一步擴大到場景風(fēng)格的切換;從空間表征上看,促使濾鏡進一步開發(fā)和應(yīng)用的不僅有城市中那些呈現(xiàn)“中產(chǎn)趣味”的表征物,還有越來越受關(guān)注的鄉(xiāng)村場景。
二、情境編碼:互動界面中的“鄉(xiāng)土發(fā)現(xiàn)”
濾鏡由靜態(tài)到動態(tài)、由容顏到場景、由城市到鄉(xiāng)村的功能轉(zhuǎn)型,主要依賴其孵化的圖像。那些經(jīng)過濾鏡加工后流動于社交網(wǎng)絡(luò)的圖像,與圖書插圖、影院電影、紀(jì)錄片、紀(jì)實攝影等圖像作品不同,它們自誕生起便是一種用來操作的互動界面。在視覺文化的研究視域內(nèi),“界面”(Interface)以互動性(Interactivity)作為基本運作邏輯,反映著兩種介質(zhì)之間的活動進程和交流形式①[法]保羅·維利里奧:《消失的美學(xué)》,楊凱麟譯,鄭州: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8 年,第7 頁。,具有超文本(Hypertext)屬性。在界面的交互過程中,圖像是語言符號(verbal sign),濾鏡是呈現(xiàn)符號序列的媒介(medium),拍攝者是文本操作者(operator)②Espen J.Aarseth,Cybertext: Perspective on Ergodic Literatur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21.,三者的相互作用確定了整個視覺系統(tǒng)的輸出和表現(xiàn),使得濾鏡社交越來越常態(tài)化,讓可供“種草”的景點越來越垂直細(xì)分,針對不同場景的濾鏡資源也日益豐富。這種界面互動性直接催生了濾鏡消費化。近年,大量國內(nèi)外美圖類APP 陸續(xù)開辟了濾鏡商店專區(qū),旨在讓部分熱度和產(chǎn)出率較高的用戶將自己作品中的預(yù)設(shè)上傳并販賣,由此進一步促進并維持濾鏡社交的互動性。作為一款較早嘗試濾鏡交易的社交類攝影APP,美國的VSCO 可以說是濾鏡交易的弄潮兒。該APP 開發(fā)團隊在2015 年前后不斷通過專業(yè)攝影師制作的濾鏡組下放濾鏡的使用權(quán),讓幾美元一個的預(yù)設(shè)進入到更多用戶的應(yīng)用界面。在Lightroom 開啟移動端后,Instagram 上很快便掀起了販賣濾鏡的熱潮,不少攝影博主和“探店網(wǎng)紅”都開通了專屬濾鏡鏈接,將色系和影調(diào)符合自身運營調(diào)性的視覺預(yù)設(shè)方案放在首頁的購買鏈接上。而在國內(nèi),包括美圖秀秀、輕顏、MIX、潑辣、黃油相機等也在近年陸續(xù)推出了濾鏡商店,用戶可以在智能終端和濾鏡開發(fā)者互動,并通過付費、開通會員、積累積分等方式兌換或購買濾鏡。2022 年2 月10日,潑辣APP 官方更是宣布將包括圖像局部調(diào)整工具、圖層工具、智能識別工具、效率工具在內(nèi)的所有圖像功能免費開放,唯獨保留付費濾鏡這一消費項目。可見,濾鏡因其可交易性、可流通性、可挪用性,決定了它本身就具備極強的附加值,以致于它所修飾過的圖像不僅能夠增強人際傳播的效能,還可以帶來實質(zhì)性的經(jīng)濟收益,甚至開辟出新的市場。
濾鏡消費化激活了濾鏡社交的市場需求,從而使濾鏡孵化的圖像通過超鏈接的方式進一步指涉更多現(xiàn)實的事物。當(dāng)觀眾接收到圖像信息后,同款濾鏡可供下載并批量使用,“網(wǎng)紅景點”可提供坐標(biāo)定位和出行指南,就連出鏡的物品也能在彈窗的排版中插入購買鏈接。濾鏡孵化的圖像憑借這種“物鏈接”功能,攜同著“國內(nèi)游”“周邊游”“小眾景點”“秘境探索”等社交媒體標(biāo)簽頻繁地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內(nèi)。有報告顯示,2021 年國慶期間,“小眾景點”的搜索量同比增長超10 倍。③巨量算數(shù):《域見中國·2021 年文旅行業(yè)專題報告》,北京:巨量引擎城市研究院,2021 年,第7 頁。由邊緣小眾的鄉(xiāng)村場景組成的“網(wǎng)紅景點”越來越成為青年網(wǎng)民日程表里的“主流”打卡目標(biāo),它們無疑是文旅資本通過智能算法塑造的“網(wǎng)紅打卡地”,但同時也是人們賴以兌現(xiàn)某種審美默契和視覺需求而認(rèn)可的“濾鏡景點”。因為,這些景點本質(zhì)上是可以增強人際互動和社交效能的情境編碼,它們就像所有技術(shù)性的影像一樣,既包括發(fā)布者的審美觀念和傳播意圖,也涵蓋傳播后的人際期待,甚至可以利用其輸出的圖像文本創(chuàng)造所謂的品位、潮流和時尚,召喚更多的觀看者主動加入圖像生產(chǎn)的隊列,認(rèn)同這種圖像生產(chǎn)規(guī)則和隨之而來的審美趨勢,以實現(xiàn)現(xiàn)實闡釋權(quán)的二次分配。
然而,這種現(xiàn)實闡釋權(quán)的二次分配并不總是“公平”的,甚至常常引發(fā)爭議。2021 年初,“國內(nèi)唯一粉紅沙灘”屢次霸榜微博熱搜、小紅書推薦和抖音熱榜,圖像文本中指述著唯美浪漫的粉紅色最終被證實是豬肝色的紅土地砂石灘涂,在無人機視角、高能見度天氣和特定濾鏡的加持下,這個距離昆明60公里、位于云南澄江撫仙湖畔的“網(wǎng)紅打卡點”很快便因為設(shè)施殘缺、秩序混亂為人詬病而再次出現(xiàn)在熱搜中。無獨有偶,鄭州新密伏羲山云上牧場憑借大量“少女登天梯仰望天空”的圖像產(chǎn)品而備受關(guān)注,但“天梯”最終難免淪為網(wǎng)民討伐的對象,因為那些唯美的“打卡照”只有在特定取景角度和后期濾鏡的配合下才得以呈現(xiàn)。福建漳州魚骨沙洲、海南三亞清水灣的藍色小屋、廣東汕尾風(fēng)車島等透過濾鏡呈現(xiàn)的“世外桃源”,無一例外地成為“僅供參考”的濾鏡景點。盡管如此,瞄準(zhǔn)鄉(xiāng)村場景這個流量密碼的“獵手”們依然深諳“濾鏡景點”這股潮流,依靠那些由濾鏡培養(yǎng)的審美旨趣不斷驅(qū)動網(wǎng)民對“網(wǎng)紅打卡地”進行“種草”和“奔現(xiàn)”。濾鏡商業(yè)化極大地增強了濾鏡的觸達率和使用率,更增強了濾鏡指涉現(xiàn)實事物的可行性。濾鏡社交通過互動性降低了圖像風(fēng)格化生產(chǎn)的成本,提高了圖像傳播的觸達率,并讓眾多被遮蔽的鄉(xiāng)村場景“破圈”而出,隨同流量轉(zhuǎn)化為網(wǎng)民的鄉(xiāng)野愿景和探索經(jīng)歷。這場熱鬧的“鄉(xiāng)土發(fā)現(xiàn)”是一個隱蔽的歷史腳注,它見證了濾鏡超越了簡單的視覺預(yù)設(shè),成為了一個互動界面,被它觸發(fā)的圖像一旦進入社交媒體場域,便成為圖像作者與讀者之間聯(lián)動的媒介,并時刻與其他信息實體發(fā)生互動并相互作用,形成信息反饋循環(huán)。作者/發(fā)布者面對鄉(xiāng)村場景的時候寄存了自我客體化的審美訴求,并根據(jù)具身性的話語實踐引導(dǎo)更多的閱讀者進行互動;而讀圖者/觀看者往往對這些小眾的鄉(xiāng)村場景一無所知,更遑論審美體驗,但在濾鏡重建的現(xiàn)實邊界和濾鏡風(fēng)格引導(dǎo)的色彩美學(xué)的幫助下,在自我想象中體驗作者的拍攝經(jīng)歷,釋讀作者拍攝時的空間感受,甚至沉浸于濾鏡“升格”后的光影格調(diào)和色彩暗示。從小眾景點的發(fā)掘到“網(wǎng)紅野餐”“網(wǎng)紅露營地”的流行,人們并非需要真正融入大自然,而是希望尋找郊野一樣的“背景板”去展示在城鄉(xiāng)之間來回切換的身體在場性,去陳列城市美學(xué)的消費品,在陌生化的山野景觀中演繹城市記憶,在享受其帶來的空間使用快感的同時,抵御“落伍”而導(dǎo)致的社交焦慮。一如桑塔格在《論攝影》中所強調(diào)的那樣,攝影主要是一種社會儀式,一種防御焦慮的方法,一種權(quán)力工具。①[美]蘇珊·桑塔格:《論攝影》,黃燦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年,第17 頁。因此,與其說在這種情境下人們是在閱圖和賞圖,不如說是在互動和遍歷。
三、空間收編:濾鏡修辭下的因果重置
濾鏡本身是一種數(shù)碼化的視覺預(yù)設(shè),濾鏡孵化的圖像在經(jīng)歷了網(wǎng)絡(luò)社交的多次迭代后,升級為一種極具互動性的操作界面,“圖像的傳播”這個行為本身則成為了提供社交內(nèi)容、增強社交關(guān)系、拓展社交空間的“視覺閑聊”(visual chitchat)。②Mikko Villi,"Visual chitchat: The use of camera phones in visu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Culture,2012 No.3.在這種特殊的言語實踐中,濾鏡的使用充當(dāng)著一種修辭(Rhetoric)行為。修辭理論家佐藤信夫指出,修辭從根本上說是賦予語言以審美效果和說服功效的雙重技術(shù)體系,并在人類語言媒介形式不斷拓展的背景下,延伸出“發(fā)現(xiàn)性認(rèn)識的造型功能”③[日]佐藤信夫:《修辭感覺》,肖書文譯,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2 年,第25 頁。。換言之,作為一種跨媒介的語言活動,修辭體現(xiàn)了審美的激發(fā)力、思辨的說服力和認(rèn)知的創(chuàng)造力這三個功能。這也意味著濾鏡能夠借助修辭的功能來調(diào)整注意焦點、改變理解方式和創(chuàng)造認(rèn)知基礎(chǔ)。結(jié)合現(xiàn)階段的媒介實踐來分析,濾鏡修辭大體上通過“奇異性—物質(zhì)性—指引性”的邏輯執(zhí)行其功能。
濾鏡的使用作為一種視覺修辭,首先通過奇異性(Singularity)來觸發(fā)感官關(guān)聯(lián)這一功能,用以激發(fā)讀者的審美活力。用圖像分享私人經(jīng)驗實質(zhì)上是一種視覺人際交流(visu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需要讀者的反饋。當(dāng)人們用社交媒體對鄉(xiāng)村場景進行圖像表征的時候,如何確保它們在信息洪流中脫穎而出,引起更多社交互動,成為了社交效用的重要驗收標(biāo)準(zhǔn)。而采用“經(jīng)驗代言物”作為維持讀者奇異性的感覺通道,從國外著名旅游景點中“借用”異域化的視覺體驗,則早已成為國內(nèi)社交網(wǎng)絡(luò)的默契。近年,國內(nèi)出現(xiàn)了大量“小字輩”的鄉(xiāng)村場景。截至2021 年,中國至少有63 個“小圣托里尼”,62 個城市擁有“小京都”,61 個城市擁有“小鐮倉”,59 個城市擁有“小奈良”,而“杭州小曼谷”“寧波小濟州島”“西安小鐮倉”“大連小瑞士”等景點更是層出不窮。④人民網(wǎng):《網(wǎng)紅景點“濾鏡營銷”頻“翻車”如何不讓“仙境”變“陷阱”》http://ent.people.com.cn/n1/2021/1016/c1012-32255591.html。這些貼上異域景觀標(biāo)簽的鄉(xiāng)村場景反過來又不斷催生新的市場需求,推動著濾鏡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大量以外國著名旅游地及相關(guān)元素命名的濾鏡也悉數(shù)在大量美圖APP 里上架:

表 以異域景觀關(guān)聯(lián)的濾鏡產(chǎn)品一覽(截至2022 年4 月)
這種通過異域景觀命名濾鏡的“視覺借喻”受到追捧,有其內(nèi)在的社會背景。在2020 年疫情暴發(fā)之前,旅游是國內(nèi)社交媒體矩陣中非常重要的垂直內(nèi)容類型,逐漸完備的線上旅游產(chǎn)品銷售平臺不斷下沉市場,使地縣級城市游客也能高效、便捷地獲得境外游的服務(wù)。2013—2018 年間,中國出境游人數(shù)由原來的1 億增長至1.5 億,最高年增幅達14.7%。①艾媒咨詢:《中國在線旅游度假行業(yè)研究報告》,第10 頁。上游資源供應(yīng)、中游產(chǎn)品組合分銷、下游推廣營銷的旅游產(chǎn)業(yè)生態(tài)讓大量不同線級城市的市民走出國門,同時不斷刷新著國外著名旅游景點圖像在社交媒體的發(fā)布頻次,增加了網(wǎng)民在各類社交平臺接收國外景觀的視覺經(jīng)驗,也強化了人們對異域景觀的視覺認(rèn)同。那些以異域景觀命名的濾鏡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福柯談?wù)撔蜗笊a(chǎn)時提到的“相似物”:它經(jīng)由隱蔽的、可塑造的再現(xiàn)機制賦予人和物在場性,并在“物的秩序”建立的過程中,通過摹仿、融合、類比、共鳴等手段生發(fā)出各種特定的相似物,這些相似物以某種“知識形態(tài)”把世界聚攏起來。②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22.不難看出,“小字輩”景點的“小”,是“平替”,是“備胎”,更是城市審美趣味被冠以潮流之名縫合異域空間想象和遍歷意圖的欲望指代。
在這樣的條件下,濾鏡修辭觸發(fā)了第二個功能——視覺說服。濾鏡通過連接“經(jīng)驗中介物”讓圖像保持奇異性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便于網(wǎng)民理解國內(nèi)鄉(xiāng)村場景的物質(zhì)性(materiality),傳達能被真實化理解的闡釋③參見吳瓊:《視覺文化的奇觀》,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131 頁。。為了確保在社交媒體傳播的圖像產(chǎn)生最大化的社交效能,濾鏡執(zhí)行著非常直接的說服邏輯,在“它像什么”這種奇異性指征的基礎(chǔ)上增添“它加濾鏡后可以是什么”的物質(zhì)觀感,讓那些從物理空間的形狀、尺寸、材質(zhì)等方面與被關(guān)聯(lián)的異域景觀差距甚大的鄉(xiāng)村場景獲得后期裁剪、影調(diào)重塑、色彩調(diào)節(jié)等視覺修飾,不斷在社交媒體中形成國內(nèi)鄉(xiāng)村場景與異域景觀的審美體驗高度同源的觀看習(xí)慣。這種視覺說服的后果是讓濾鏡充當(dāng)讀圖者觀看過程中對相關(guān)物理事實(physical fact)的認(rèn)知引導(dǎo),使包括拍攝者、發(fā)布者、觀圖者、評論者在內(nèi)的視覺內(nèi)容參與者在圖像社交中,圍繞圖像及其所指的對象達成可以相互作用的共識(interactional consensus)④Jenni Niemel?-Nyrhinen,Janne Sepp?nen,"Visual communion: The photographic image as phatic communication",New Media&Society,2020,No.6.。
這個時候,濾鏡修辭便開始發(fā)揮第三個功能——憑借圖像的指示性來改變認(rèn)知。“指示性”(indexicality)原本是符號學(xué)的概念,在21 世紀(jì)后多次進入攝影批評理論的視野。符號學(xué)家皮爾斯在分析符號屬性時候指出,一個符號或再現(xiàn)之所以能夠指涉其對象,并不是因為它與對象有多么相似和類同,也不是因為它與這個對象偶然擁有的普遍特質(zhì)相關(guān),而是因為它與特定對象存在著(空間)動力性的關(guān)系,與將它視為符號的人的感官和記憶相關(guān)。⑤彭佳:《指示性重臨:從影像的“曾在”到數(shù)字的“此在”》,《文藝?yán)碚撗芯俊?020 年第6 期。濾鏡修辭恰好在視覺感官的接收環(huán)節(jié)建立起物理空間與事物認(rèn)知的空間因果關(guān)系,讓被生產(chǎn)的圖像能夠呈現(xiàn)出一種視覺經(jīng)驗上格外接近它所代表的對象的存在感,而非簡單的圖案相似或質(zhì)感接近。這份存在感一方面使鄉(xiāng)村場景的視覺經(jīng)驗越來越適應(yīng)以城市審美趣味為主的話語調(diào)性,維持了這些圖像在社交媒體品位中的“正常序列”,模擬出貼合異域景觀的“高級感”和“精致感”;另一方面,它又指引著“鄉(xiāng)土發(fā)現(xiàn)”的求索路徑,指引著視覺內(nèi)容參與者借助濾鏡不斷共享濾鏡修辭的成果,并透過美圖類APP 的濾鏡市場進行發(fā)布和售賣,讓越來越多的人都擁有對物理空間的“改寫權(quán)力”——修復(fù)那些與自我審美期待不一致的成像元素,更改那些與“高級感”“精致感”格格不入的光影、色位、質(zhì)感和層次。如此一來,濾鏡改變了人們透過圖像了解外部世界的認(rèn)知習(xí)慣。
基于感官關(guān)聯(lián)的奇異性、視覺說服的物質(zhì)性和認(rèn)知重塑的指引性,濾鏡修辭最終對鄉(xiāng)村場景實行了空間收編。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中,“空間”的概念超脫了物質(zhì)環(huán)境的解釋,轉(zhuǎn)而進入關(guān)系、權(quán)力、表征和生產(chǎn)等維度。它是“共存的信息秩序”,既包含被建構(gòu)的、被生產(chǎn)的社會空間,又包括感知的、想象的、被表現(xiàn)的精神空間。①[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20 頁。換言之,空間是將社會存在的物質(zhì)現(xiàn)實凝縮為價值關(guān)系、權(quán)力關(guān)系、層級關(guān)系等多方面關(guān)系的場所,是可以將“真實”抽象為“模具”或“設(shè)計”的表征系統(tǒng)。濾鏡修辭收編鄉(xiāng)村場景,正是將鄉(xiāng)村場景抽象為“濾鏡模具”和“概念設(shè)計”的結(jié)果,也是社會關(guān)系中審美主導(dǎo)權(quán)占優(yōu)的一方將鄉(xiāng)村場景納入價值評價體系并生產(chǎn)為“社會事實”的體現(xiàn)。這場空間收編觸發(fā)了圖像與事實之間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重置:在以往,當(dāng)人們面對國內(nèi)的鄉(xiāng)村場景時,攝影是一種對于事實的具身性證明,用以保留既定的觀察視角所得出的時間存證和空間捕捉,即便存在后期的圖像修整,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模擬視覺事實的偶然可能性,最終服務(wù)于事實必然性的審美需要。而在濾鏡修辭流行于社交媒體后,國內(nèi)鄉(xiāng)村場景與國外異域景觀的關(guān)聯(lián)通過特定光線、角度、鏡頭透視的相似偶然性,表達為用戶審美期待和價值預(yù)設(shè)的必然性。濾鏡修辭生產(chǎn)的圖像巧妙地在真實和虛構(gòu)之間謀得審美意圖的傾斜和認(rèn)知法則的寬宥,一邊將圖像中被攝對象的真實性懸置為“可視的可能存在性”(actual visible possibility),一邊把包括異域景觀要素在內(nèi)的諸種濾鏡風(fēng)格所帶來的審美愉悅和身份認(rèn)同默認(rèn)為圖像社交的基要規(guī)則,形成某種“強相關(guān)的先在視覺確定性”(strong suggestion of a possible former visible possibility)。②[法]保羅·勞克瑟:《視覺藝術(shù)的現(xiàn)象學(xué)》,李牧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 年,第57 頁。這時候,人們一旦進入社交網(wǎng)絡(luò)的語境,圖像所指述的主體是否真實仿佛并不重要,概念繁多的濾鏡是否改變、挪移、遮蔽事物原有狀態(tài)也不重要,只有被視覺修辭過濾后獲得網(wǎng)絡(luò)社交話語“復(fù)魅”的圖像才重要,因為被圖像捕捉的現(xiàn)實對象與被濾鏡“升格”后的感官體驗共同構(gòu)成了人們認(rèn)知的“現(xiàn)實”。基于此,為了維持這種存在于整個后工業(yè)化互聯(lián)網(wǎng)生態(tài)中的“便捷審美”和“風(fēng)格生產(chǎn)”,從市場資本到自媒體用戶都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更多有產(chǎn)出意義的人物、場景、信息和事件,來確保有新的、可捕捉的現(xiàn)實對象,來維系這種“復(fù)魅的現(xiàn)實”所帶來的感官體驗和身份認(rèn)同。
四、結(jié)語:施魅的誘惑
誠然,濾鏡修辭能夠帶來如此強大的“狀物自由”,既通過“美顏”讓大眾審美判斷中的邊緣形體覓得網(wǎng)絡(luò)社交的一席之地,又使邊緣偏僻的鄉(xiāng)村場景密集地呈現(xiàn)在公共視野內(nèi),甚至在后疫情時代推進了一股“文旅下鄉(xiāng)”潮流,是有其內(nèi)在的發(fā)生條件的。首先,大量操持智能手機的用戶產(chǎn)生了新的視覺趣味,摒棄了還原事實和展示傳統(tǒng)主題的必要性,“傾向于展示觀感大氣、視覺完美的圖像,它情感舒張卻感染得不為人知,似是蜻蜓點水但又引人注目”③Lev Manovich,Instagram and contemporary image,California: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7,p.85.。其次,相對而言,國內(nèi)鄉(xiāng)村場景的地貌形態(tài)與人們?nèi)粘I钋榫掣叨戎睾希a(chǎn)生了某種“審美怠倦”。此外,部分審美滯后或用力過猛的地方宣傳無法觸動以城市用戶為主的網(wǎng)民群體,甚至產(chǎn)生負(fù)面情緒。這些現(xiàn)實為濾鏡修辭促使空間收編的重要契機,它們客觀上使得這場“鄉(xiāng)土發(fā)現(xiàn)”悄無聲息,卻又聲勢浩大。“悄無聲息”是指濾鏡修辭并不會在表面上對整個社會行為秩序帶來急促而明顯的巨變,“聲勢浩大”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個體受到了它的實質(zhì)性影響。這種基于圖像象征指述體系的空間收編實質(zhì)上構(gòu)成了一種“施魅的擬真”(Enchanted Simulation)。在這個過程中,施魅是透過濾鏡修辭使某個現(xiàn)實客體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產(chǎn)生出一種讓人驚訝和信服的效果,而那些被濾鏡孵化的圖像則通過可以批量制造的復(fù)體(double)來勾勒出圖像生產(chǎn)主體不可遏制的欲望。①Jean Baudrillard,Seduction,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1990,p.62.被濾鏡技術(shù)施魅的個體表面上繼續(xù)參與到圖像生產(chǎn)的循環(huán)過程當(dāng)中,實際上卻撒播著“空間資本”和視覺話語的誘惑(Seduction),實現(xiàn)把“空間資本”轉(zhuǎn)化為“象征資本”的權(quán)力遷移。“象征資本”(Symbolic Capital)是“有形的‘經(jīng)濟資本’被轉(zhuǎn)換和被偽裝的形式”,它“體現(xiàn)了行動者在社會空間里攜帶和積累的、被否認(rèn)和掩飾的各種特權(quán)與資本,它發(fā)生效果的根源是經(jīng)濟力量決定的等級秩序。……由于象征資本的合法化效果,社會空間就像被施行了魔法,社會成員在魔法作用下形成共同‘信仰’,認(rèn)同自身在等級社會中所屬的差異性身份的天然合理性,并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社會結(jié)構(gòu)”②汪民安:《文化研究關(guān)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448 頁。。而這,便是從“都市小資”到“小鎮(zhèn)青年”都“接受誘惑”并迷醉于通過濾鏡向他者施魅的內(nèi)在機理——濾鏡修辭通過奇異性、物質(zhì)性和指引性建構(gòu)著一系列建構(gòu)于城市青年網(wǎng)民觀看世界的標(biāo)準(zhǔn)和秩序,又反過來指引越來越多的社交網(wǎng)絡(luò)用戶執(zhí)行這套標(biāo)準(zhǔn)和秩序,引導(dǎo)和塑造他們的社交愿景,將濾鏡修辭描摹的“真實感”當(dāng)作可觸摸事物的超驗在場(hyper-presence),最終讓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深信凝視的主體可以“抓住現(xiàn)實”和“闡釋事物”。
如此一來,圖像指涉的對象并不是價值觀的落腳點,圖像如何實現(xiàn)指涉的途徑反而成了重要的錨點。空間被視為獵物并轉(zhuǎn)化為流量,濾鏡順著城鄉(xiāng)群體之間曖昧的審美線索編織起圍獵的牢籠。人們真正接受到的不單是鄉(xiāng)村場景被濾鏡施魅后的“真實”,更是施魅這個動作本身,以及“讓施魅的意圖得以實現(xiàn)”這種視覺話術(shù)的反饋效果和身份效用。換言之,“濾鏡可以孵化圖像”不是最根本的現(xiàn)實,“濾鏡修辭能修改認(rèn)知方式”才是。這種慣習(xí)讓過去因為媒體技術(shù)欠發(fā)達而無法自我表述的鄉(xiāng)村場景面臨另一重失語,由“因信息落后無法言說”變成“因信息不對等而不得不言說”:一個鄉(xiāng)村場景但凡要通過社交媒體公之于眾,都必須接受濾鏡的過濾,接受濾鏡修辭的“視覺施魅”和“語言誘惑”,曲折地、花巧地、別無選擇地用城市美學(xué)經(jīng)驗來留下自身存在的依據(jù),甚至無條件地順應(yīng)新的觀看趨勢和視覺范式以徹底融入圖像社交的媒介生態(tài)。這種失語并不是沉默,而是被圖像社交的喧嘩和濾鏡修辭的騷動剝奪了沉默這個選項。很多“鄉(xiāng)土發(fā)現(xiàn)”,不過是審美話語權(quán)占優(yōu)群體進行“施魅的誘惑”的收編實踐,是強勢地利用濾鏡算法合成的“觀念參照物(reference)”來收籠大眾視線(regard)的“攝影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