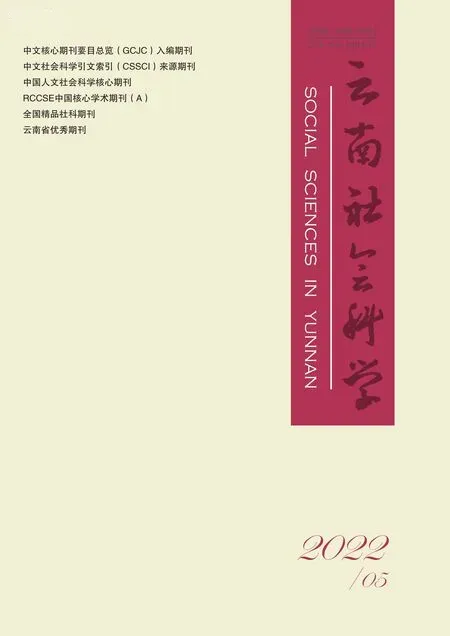基層行政的秩序困境及其超越
董偉瑋
公共行政是國家治理最為直接和常規的方式,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代表著國家,因而對于民眾而言國家就是科層體系。①[美]查爾斯·葛德塞爾:《為官僚制正名:一場公共行政的辯論》,張怡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198 頁。更具體來說,社會公眾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往往是基層行政,它是指發生在行政組織基層的國家意志執行活動。②董偉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層行政基礎》,《理論探討》2020 年第2 期。由于基層行政處在國家與社會的交界面,因此它在反映國家治理的縱向層級關系的同時,又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表征和縮影。所以,基層行政處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銜接點上,各個行動主體在這個場域中進行互動,這意味著若干個體面對面在場時彼此會產生交互影響。③[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馮鋼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12 頁。在互動中,國家具象化為基層行政組織甚至是組織成員,行政組織也不再是封閉和神秘的,基層行政人員和社會公眾也不再是抽象的群體標簽。
一、基層行政互動中的行動與秩序之問
對一般的社會成員而言,日常生活是最切身相關的現實。因此,對基層行政的描述和理解必須還原到日常生活中去,國家、組織和個人的行動意義凝結在日常生活情境之中,并在其中進一步實現意義的再生產。聚焦于情境的分析并未回避結構性議題,它反而使得國家層面和組織層面的政策如何展現在此時此刻變得清晰可見。①E.Hj?rne,K.Juhila and C.V.Nijnatten,"Negotiating Dilemmas in the Practices of Street-Level Welfare Wor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Vol.19,No.3,2010,pp.303-309.因此,面向日常生活本身,基層行政主要通過一線行政人員與公眾的互動,才得以展現出其國家與社會交界面的屬性。前者在理論上也被稱為街頭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這是一個中性概念,體現出其工作界面的特征與行使職權的屬性,而并不強調其是否具有某種編制的法律身份和是否納入干部管理的政治身份;②蘇曦凌、黃婷:《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界面:行動語境中的基層概念及其理解》,《行政論壇》2022 年第2 期。后者則被稱為當事人(client),體現出其在互動情境中的在場特性。一線行政人員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聯系方式在互動中得到觀察和理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科層體系的運行過程得以具體地顯現。
基層行政互動是具體的,因而可以看到不同的行動主體展現出各自的行動邏輯,他們都是自主的行動者,有著各自的需要與訴求。一線行政人員也不會是機械化的執行者,互動過程中屢見不鮮的基層政策變通執行問題③景躍進、張小勁、余遜達:《理解中國政治:關鍵詞的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182—188 頁。就是明證。基層行政過程和結果同上級決策和計劃的期望常常存在落差,引起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多方不滿,這在表面上是國家治理的難題,在實質上則反映了科層制組織的內在特征,是組織成員的行動策略和常規選擇。
對此,國內外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開展了廣泛研究,提出了很多著名的理論解釋,如自上而下的政策執行偏差④[美]珍妮特·登哈特、羅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第3 版),丁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78—79 頁。、委托代理理論⑤[澳]歐文·E.休斯:《公共管理導論》(第4 版),張成福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10 頁。、公共選擇理論⑥[英]丹尼斯·C.繆勒:《公共選擇理論》(第3 版),韓旭、楊春學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396—398 頁。、行政發包制⑦周黎安:《行政發包制》,《社會》2014 年第6 期。、運動型治理⑧周雪光:《運動型治理機制: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再思考》,《開放時代》2012 年第9 期。等。細思之下不難發現,上述解釋無論是從宏觀視角還是從微觀視角切入,其底色都是結構功能主義的,都是在一種客觀主義的秩序框架中解釋組織行為,⑨G.Burrell and G.Morgan,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London: Heinemann,1979,p.26.政策所代表的上級權威和制度安排實際上體現為一種宏觀秩序訴求,給出的問題解決方案都可以歸納為控制官僚。⑩韓志明:《街頭官僚的行動邏輯與責任控制》,《公共管理學報》2008 年第1 期。這里面既存有對宏觀秩序的先天合理預設,如平等、公正、法治、權利、統一、效率等,同時又蘊藏著官僚行為違背這一宏觀秩序應加以負面評價的立場。
然而結構功能主義解釋的最大問題就在于,宏觀秩序的合理性并非不證自明,其具體含義是模糊的;同時這個宏觀秩序內部其實也存在矛盾,加之上級的政策來自各個系統,相互之間難免存在沖突,其背后的價值也難以完全融貫,如平等和公正?洋龍:《平等與公平、正義、公正之比較》,《文史哲》2004 年第4 期。、統一和效率?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第12—14 頁。就都蘊含著深刻的價值沖突。政策沖突和價值沖突雖然在戰略層面上解決不了,卻會轉移到基層行政,矛盾也隨之轉嫁給一線行政人員。基層行政本來就缺乏相應的資源和能力處理這種矛盾,為了避免基層執行偏廢其一,上級就需要不斷強調宏觀秩序的方方面面,這就成了行政實踐中的“面面俱到”,進而演變為“既要……又要……還要……也要……”的復雜要求,這進一步使一線行政人員手足無措、疲于應付。因此,對宏觀秩序的合理性預設是有漏洞的,而它是否值得追求在互動情境中面臨著具體判斷。也就是說,宏觀秩序要求在互動情境中即便不至于完全失效,但在重要性排序上也會發生調整,畢竟“什么都要”總是困難的,對一線行政人員而言,解決眼前的問題更具有實際意義。
與此相對,一些理論轉換視角反映基層行政的實際困難,分析基層行政自身所蘊含的邏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街頭官僚理論,其他理論也包括集權的簡約治理?黃宗智:《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開放時代》2008 年第2 期。、自主性擴張?顏昌武:《剛性約束與自主性擴張——鄉鎮政府編外用工的一個解釋性框架》,《中國行政管理》2019 年第4 期。,正視基層自主決策的意義,并在舉措上提出面向基層簡政放權、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這實際上采取了一種社會建構主義立場,承認存在著一種基層行政的情境秩序,一線行政人員作為理性行動者會采取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行事,他們追求安全順利地完成手頭工作,同時盡量獲得贊許、規避問責,因此他們謀求對情境的掌控。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情境秩序有很大的迷惑性:它雖然也維持了某種穩定,但無法完全以宏觀秩序為導向,一線行政人員處置手頭工作的常規策略無論是按規定行事還是“打擦邊球”——包括“和稀泥”、威脅、支配、妥協等,都是在基層行政情境中的“正常”選擇。“正常”在宏觀秩序的論域內并不一定正當,但在情境中卻伴隨著一線行政人員“正當化”的努力。依靠這種行動維系的情境秩序與宏觀秩序之間僅僅是貌合神離而已,但社會建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承認其合理性,認為這是一線行政人員面臨現實困難的必然選擇。
結構功能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在審視基層行政問題方面的區別雖然在具體理論中有不同體現,但本質上還是圍繞著一線行政人員行動與秩序之間的關系問題。只不過,前者更看重國家和公眾預設的宏觀秩序,后者則承認情境秩序對一線行政人員而言具有現實意義上的優先性。良好的秩序意味著穩定,穩定的基礎在于規范得以正常發揮作用,即便存在不穩定的因素也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 年,第353 頁。雖然宏觀秩序和情境秩序都可以觀察到某種穩定,但相似的穩定現象卻有著不同的本質。基于縱貫國家、組織和一線行政人員以及橫連國家與社會的復合視角,基層行政充分反映了行動者對秩序的理解及其在秩序實現過程中的具體選擇,它本身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在行動與秩序的關系中可以得到分析,優化路徑則需要在處理好行動與秩序關系的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在承認行動者自主的前提下,分析行動者動機的內容和外化是在研究行動問題;而考察這些自主行動者的相互聯系方式就是在回應秩序問題。②J.C.Alexander,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1):Positivism,Presuppositions,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70.具體到基層行政中,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對實現理想的宏觀秩序發揮了什么作用?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行動和秩序的實然層面入手。
二、情境秩序與宏觀秩序的落差:基層行政的秩序困境
秉持結構功能主義立場的研究成果從不同側面還原了一線行政人員實際行動與宏觀秩序要求之間存在的差距,偏重于從宏觀意義上解析基層行政,將情境中個體超出政策要求和制度規定的策略都視為越軌行為。如此一來事情似乎簡單了,即便按照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所說,基層行政存在一種情境秩序,那只要把情境秩序拉回到宏觀秩序的軌道上即可。但一線行政人員所處的情境是特殊的,探尋這個情境的特征,才能深刻理解基層行政同時蘊含的結構性、制度性和行動性要素,也才知道情境秩序和宏觀秩序的落差是基層行政的困境,而不只是能夠簡單求解的問題。
(一)一線行政人員所處的“壓力—自主—應付”情境
基層行政面臨著很多難題,一線行政人員作為理性行動者,他們的工作在訴求多樣、資源不足、目標模糊和規則不確定等不利境況下面臨著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具有相應的結構和制度基礎,但凝結到具體情境中時,其復雜性、稀缺性和即時性更為突出,表現出一定的風險性。③L.Gabriela and P.Roberto,"Street-level Bureaucracy Research and Social Inequality",In Peter Hupe edS.Research Handbook on Street-level Bureaucracy,Northampton,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9,p.89.規避風險是一種正常的心理傾向,這其中可以運用多種策略和工具。與常規認知中“自上而下”的政策實施過程正好相反,一線行政人員往往傾向于脫離上級的直接監管,而慣于在日常工作中運用自由裁量權(包括積極使用和一線棄權)以使總體目標和正式規則能在具體情境中得到解釋。這種解釋基于一線行政人員對情境的判斷,而非完全依據制度規定和上級指示,所要達到的效果是維持情境秩序,因為這才意味著一線行政人員的日常生活得到了維系,他們以處理不確定性的應付策略為基本行動模式。④董偉瑋:《建立一種街頭官僚的政治理論:主題演進、概念愿景與理論整合》,《云南社會科學》2018 年第6 期。無論資源和能力如何,一線行政人員還是傾向于加強對情境的掌控,進而實現對工作流程的全面控制。這種“壓力—自主—應付”情境具有結構性和制度性兩種要素加以支撐。
結構意味著制約行動的外在條件總和,它與自主性相對。從本質上講,結構不是一種實在,盡管一直有試圖將其實體化的理論主張,但它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對社會關系進行模式化理解的傾向。因此結構往往在表征一種結構化的過程,它意味著將社會系統的時間和空間“束集”在一起。①[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社會分析中的行動、結構與矛盾》,郭忠華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 年,第71 頁。而互動使結構變得具體,凝結在基層行政互動情境中的結構性要素融合了互動參與者對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的理解和判斷。政治結構決定了基層行政互動回應性的基本導向,國家性質和政體價值對行政體系的基本要求是基層行政的旗號,無論在基層行政互動中的落實程度如何,一線行政人員在公開場合傾向于宣稱接受政體價值。社會結構影響了一線行政人員對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層次和群體之別的認識,確定了各自參與基層行政互動的初始地位,當事人會因其社會角色被一線行政人員劃分為三六九等、歸入不同類別。
制度性要素在固化與合理化結構性要素的意義上支撐一線行政人員在情境中的策略選擇。制度是規范社會互動的規范體系,而在常人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看來,制度的規范作用在于它能使行動在特定場景中得到解釋。②J.Heritage,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Oxford:Polity Press,1984,p.210.特別是在基層行政中,制度是在組織層面上為人所感知的規則體系,它以倡導、許可或禁止的方式規范或調節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即便與宏觀秩序聯系密切,但只有與情境相關并影響互動過程的規則才會被一線行政人員援引,這是制度在基層行政互動情境中發揮作用的方式。制度作為解釋資源是其作為規范體系的直觀表現和實踐結果。一線行政人員的選擇性解釋又影響著互動情境中的結構性要素:當基層行政互動發生時,一線行政人員既在結構上成為國家和組織的具體代表,又在制度上因熟知組織規范而具有知識和信息優勢,因而他們雖然面對結構壓力和制度規范,但又獲得了自主空間,并能在具體互動中生成相應的應付策略與行動。
(二)一線行政人員的行動邏輯及其內蘊的秩序落差
國家、地方、社區和公民都希望一線行政人員能成為自己的代理人。③S.Maynard-Moody and M.Musheno,"State Agent or Citizen Agent: Two Narratives of Discretion",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2,No.2,2000,pp.329-358.一線行政人員的行動目的與國家、公眾和組織的目的之間可能存在沖突,這除了他們作為理性人會考慮自身利益的原因之外,還因為這些目的之間以及目的體系內部也存在矛盾。由于面臨科層體系的權力指揮和績效評估,一線行政人員會依據命令指向和評估指標分配注意力,轉移工作焦點。他們的策略選擇實際上既迎合國家和組織,又應對當事人和社會公眾,基層行政的情境秩序是按照一線行政人員的“劇本”設計的,其直接目的不是為了完成組織目標或服務當事人,而是讓當事人服從一線行政人員工作程序以順利完成手頭工作。④M.Lipsky,Street-Level Bureaucracy: 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10,p.83.情境秩序表面得到了維持,然而是以有利于一線行政人員的形式得以維持的。由于基層行政互動情境是結構、制度和他人行動疊加生成的公共場景,所以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具體決策超出了情境限制,會通過特定機制產生宏觀影響。
第一,結構賦予的身份是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初始條件,一線行政人員在互動過程中采取一系列策略鞏固優勢。在階級社會中,掌權者相比于社會公眾在整體上更具結構性的身份優勢。具體到基層行政互動中,這有利于一線行政人員對互動的初步掌控。這種結構性優勢來源于社會資源的差異化配置,在這個意義上,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傾向于固化既有結構。
第二,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受到制度制約,制度同時也為一線行政人員行動提供了解釋資源。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受到制度制約的直接表現就在于對行動進行合理化要依賴制度。一線行政人員在基層行政互動中面向當事人會宣示法律和政策等制度性規定來合理化自己的行動,但這種制度化傾向包含著明顯的實用態度,制度在互動情境中不一定規范了一線行政人員行動,而是成了一線行政人員所援引的行動解釋。在這個意義上,制度只是一線行政人員維護情境秩序的工具,他們對制度本身并不必然持有一種敬畏和堅守的態度。
第三,基于結構性和制度性要素對情境的塑造,對一線行政人員而言最合理的行動選擇,就是自覺維護情境秩序同時謀求對其進行主導。但由于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在客觀上可能有悖于正式制度,因此情境秩序與更廣泛的宏觀秩序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線性的。一線行政人員所掌控的情境秩序要鞏固原有的結構優勢和制度優勢,最終保證一線行政人員在情境中對當事人的控制和支配。行動與秩序之間的關系似乎同時游走在積極和消極的兩個方向上,但一線行政人員優先考慮情境秩序,并對當前情境秩序的前景不提供任何規范性承諾,也就是說它是否合于宏觀秩序的要求并不在自覺考慮的范圍之內。
互動層面的情境秩序乃是宏觀秩序的經驗基礎。公眾對宏觀秩序的體認、描述和評價源自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情境秩序的積累。公眾在基層行政中體驗到的情境秩序會轉化為他們對宏觀秩序的評價,而這個由一線行政人員所主導的情境秩序雖然看起來井井有條,卻充滿了對宏觀秩序的忽視和懸置:國家會要求一線行政人員重視自己工作的政治意義,但上級越要求落實政策、制度和政體價值,一線行政人員就越會把形式上的穩定看得更重,因為情境秩序是直觀的、公開的,宏觀秩序是抽象的、潛在的,國家越從實質上控制一線行政人員實現宏觀秩序,一線行政人員就越在形式上加緊控制情境秩序。形式上越來越有秩序的基層行政互動,卻在實質上與國家治理的初衷漸行漸遠,互動秩序與情境秩序出現了反向共變,這就成了難以化解的困境。
三、通過控制一線行政人員以突破秩序困境的失效
在維護情境秩序的過程中,無論一線行政人員是否自覺,他們的行動都影響了宏觀秩序,可能政策目標因此難以完全實現,當事人也會因此對國家治理產生負面評價。對此,國家和組織不會坐視不理,社會公眾也不會漠不關心。然而,外部的要求卻始終難以保障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完全以宏觀秩序為導向,當這種宏觀秩序要求成為維持情境秩序的束縛時,自主行動就會被認為具有消極意義。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消極方面源于基層行政所具有的內在矛盾:當事人需求和基層行政供給之間的矛盾、基層行政回應性和一般行政標準化之間的矛盾、工具理性行動目的導向和價值理性行動規范導向之間的矛盾,總結起來就是一線行政人員自主和控制一線行政人員之間的矛盾。
(一)控制路徑:規范一線行政人員行動以符合宏觀秩序要求
面對秩序困境,控制路徑是繞不過去的解決方案,“管理體制的規則是控制”①[美]拉爾夫·赫梅爾:《官僚經驗:后現代主義的挑戰》,韓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52 頁。,這是現代管理體制的最常規選擇。但控制一線行政人員還面臨他們希望擺脫控制的挑戰。②[美]理查德·博克斯:《公共行政中的社會批判理論》,戴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第115 頁。普羅塔斯(Jeffrey Prottas)在街頭官僚理論創立初期就曾指出:“街頭官僚是獨立的,因為他們有權力并且能夠阻撓原本就有缺陷的組織界定他們責任和觀察他們行為的企圖,而這些正是有效控制的先決條件。最終,可供組織利用的促使他們服從的正式工具只能發揮有限的力量和效用。”③J.M.Prottas,People-Processing: The Street-Level Bureaucrat in Public Service Bureaucracies,MA: Lexington Books,1979,p.162.控制一線行政人員并沒有消除資源配置不均這個問題根源,反而使一線行政人員在日常工作中感覺到壓力和束縛,進而產生動機將控制進行轉移和轉換。對一線行政人員而言,控制當事人是轉嫁或規避控制的最直接選擇。
控制路徑的極端要求是取消自由裁量空間,消滅自主行動,使一線行政人員成為完美執行者。我們可以通過反證法設想一個理想場景,來檢驗控制路徑是否真正有效。在理論上,計算機決策可以做到嚴格且精準地實施法律和政策,程序也可以完全標準化。但由于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的不同,其中還是會出現紕漏,這就需要解釋。這時候,原本的一線行政人員角色可能由技術專家甚至計算機程序、手機應用、人工智能來充當,這時的常用解釋就變成電腦故障、手機卡頓、系統崩潰、網絡不好、缺少權限等。作為“人”的一線行政人員雖然受到了控制,但經由“物化(reification)”產生的程序卻自有一套技術運作邏輯,它擁有各種技術理由擺脫或轉移控制。因此,計算機決策取代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看似打造了完美執行者,但它使基層行政無須再對行動做出任何超越于技術之外的解釋,原本基于法律和政策的制度性解釋統統沒有必要,因為制度已經被化約為計算機程序,基于技術的解釋從后臺走向前臺。在喪失行動自主性的前提下,物化的“一線行政人員”當然也就失去了責任,無須再對宏觀秩序負責。悖論就此出現:基層行政需要完美執行者是為了宏觀秩序的順利實現,而完美執行者本身無須對宏觀秩序負責,因為宏觀秩序未能實現絕不可能歸咎于完美執行者。因此,控制路徑消滅不了自由裁量權,被取代的只是作為“人”的一線行政人員,自由裁量權轉移到技術領域,宏觀秩序并不能隨著技術對基層行政的支配而一勞永逸地得以實現,遑論隨之被消滅的還有基層行政互動中的人情和溫度。因此,基層行政以完美執行者為基礎在理論上是不切實際的。
(二)控制路徑失效的客觀表現:一線行政人員日常生活的功能性悖反
參與基層行政互動是一線行政人員的日常工作,也是其日常生活的基本內容。“只要日常生活的常規不被打斷而能夠持續存在,它們就被理解為沒有問題的。”①P.Berger and T.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Double and Company,1969,p.24.如此一來,一線行政人員對日常生活就缺乏批判的動力和反思的條件。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視角,日常生活本是一種自在的對象化,是實現社會再生產的個體再生產要素集合,概言之就是“個人”的再生產。然而日常生活需要“革命”,通過揚棄自在化和異化以實現類的人道化,這種自為的對象化是維系日常生活的規范和規則的起源。②[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3、53、61 頁。因此,對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來說,對日常生活進行“超越”是其日常生活自身所蘊含的要求,否則就不會在超越自在化和異化的意義上產生公共性。這說明,真正的“革命”或“超越”是內在的,外在于日常生活的力量強加給日常生活的功能并不一定能實現。
對公眾而言,一線行政人員毫無疑問是代表國家的行動者;對國家而言,一線行政人員也在傳遞社情民意方面被寄予厚望,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公眾的聲音。但需要注意的是,一線行政人員還代表著自己,而這在日常生活中更具優先性。從現象上看,一線行政人員的自覺行動自發地聚合為國家行動;然而從本質上看,本是自發聚合產生的國家行動在公眾看來卻是自覺的,而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自覺行動又無法徹底消除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自發性。一線行政人員自覺行動充當了國家自發行動,同時消解了國家自覺行動,這是超越自在對象化走向自為對象化失敗,是通過控制使日常生活實現宏觀的治理功能和社會功能的失敗。
國家和公眾都希望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發揮理想的治理功能和社會功能,希望對日常生活進行滲透并促使一線行政人員產生超越其日常工作的動機,使日常工作與治理目標和社會愿景緊密契合。悖反之處就在于,在日常與超越之間,由于一線行政人員在情境中的自主行動,國家意志的貫徹在表面上強大有力,卻始終面臨著巨大的無力風險,因為伴隨著基層行政的組織化程度提升,官僚化趨勢也會蔓延。組織化是日常生活功能化的基本實現途徑,它將日常生活整合到客觀的社會生產和主觀的社會期望之中,一線行政人員的日常工作也不例外。官僚化是日常生活功能化的外在表現,是日常生活中一線行政人員抗拒組織控制的自主行動。與其說官僚化是組織化的必然結果,倒不如說它是一線行政人員的主動選擇。因此,日常生活中的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很難按照一種統一的頂層設計圖景進行運作,控制會隨著應付策略的累積而不斷內卷。
(三)控制路徑失效的主觀原因:基層行政個體行動的目的性局限
在基層行政的互動中,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直接目的是不受威脅地順利完成手頭工作,當然這一直接目的背后可能有不同的深層目的的支撐。然而無論深層目的的具體內容如何,一線行政人員行動都帶有結果論色彩,更有日常生活層面的實用性意蘊,目的導向①韋伯所劃分的四種行動作為理想類型擁有巨大的學術價值,但舒茨的行動定義表明不可能“無目的地行動”,因此基于目的的理性行動是日常生活中最頻繁和最強大的事實。參見J.C.Alexander,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3):The Classical Attempt at Synthesis,Max Weber,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25-30,pp.55-57.是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基本特征。
目的導向并不意味著先驗的消極性,它賦予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實現個體目的同時還承載了基層行政的治理功能和社會功能。正是在目的導向之下,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客觀上成了國家治理正常運轉的終端環節。這種積極作用可以在化解一統體制和有效治理矛盾的意義上恰當定位高層與基層的理想互補關系:高層決策可以無差別地平等對待所有人,而基層行政則可以考慮在差異基礎上公平對待個別人。在這個意義上,基層行政是國家治理處理差異性需求的基本途徑。作為一種正常的心理傾向,人們希望被平等對待,但更希望別人能格外善待自己。一線行政人員行動在維護情境秩序的同時,又在兼顧當事人特殊性的意義上保障宏觀秩序的韌性。
然而,由于一線行政人員在情境秩序和宏觀秩序中優先選擇前者,這就更多暴露出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消極方面。一線行政人員缺乏更加善待當事人的合法合理動機,制度賦予的空間也很狹小。基層行政互動作為當事人體驗宏觀秩序的經驗來源,它限定了宏觀秩序的體驗上限,最好的情況也就是政策和制度能夠原樣貫徹,甚至公眾會認為達不到也可以接受,“第二等的公平”也算滿意。②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31 頁。當事人所能體驗到的秩序即便在理想情況下也是經過篩選的,一線行政人員在日常工作中將具體的當事人異化為情境的附屬物,而當事人本應該同一線行政人員一樣都是情境的主體,在差異基礎上公平對待每個人的美好期望就此落空,公眾渴望這種差異化對待,最終卻會察覺,能得到無差別對待就已經是“滿意解”了。
四、超越基層行政秩序困境的可行路徑
秩序困境的存在和控制路徑的無效,說明改善一線行政人員行動面臨著嚴峻挑戰。情境秩序實際上是基層行政與宏觀秩序之間的媒介,國家、組織和公眾對宏觀秩序的期望無法繞過情境秩序。解決問題的思路需要從控制個體行動轉向對基層行政秩序困境的整體超越。
(一)樹立兼容基層行政功能差異的治理理念
基層行政是一種國家治理過程,也是一線行政人員的日常工作過程。如果只強調前者而忽略后者,那么秩序困境就永遠不可能突破;相反,如果片面強調后者而忽略前者,那么國家治理的價值屬性與合法性基礎就會被消解,科層制的反功能(dysfunction)就會更多地暴露出來。治理理念需要實現平衡,就必須兼顧基層行政的功能差異,在國家治理和一線行政人員的共同事業層面重新定位基層行政。
公共行政本身當然是一項值得付出和奉獻的事業,它需要公共服務動機、奉獻精神、專業知識,對基層行政而言更需要溝通的親和力、隨機應變能力和良好的身心素質,一線行政人員被認為理應具有上述特質,成為一名合格的基層公共服務工作者。公共行政對社會而言是國家治理的工具和方式,但不能否認它對個人而言也是一項日常工作。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的歷史唯物主義道理與人們直接經驗相符,這正是日常生活優先性的理論和實踐依據。因此,當一線行政人員被要求應該發揮國家治理的工具性作用、將公共行政當作高尚事業之時,必須牢記他們不可能成為理性官僚制所構想的非人格化存在,也不是人形的計算機,國家治理實踐不是給國家機器配上一個流水線工人那么簡單,并不存在完美的執行者。對一線行政人員而言首要的和最真實的現實是日常生活現實,是他們的日常工作,對一線行政人員的管理只有把工作轉化為事業,國家治理的意圖才能更加合理有效地涉入日常生活。
所以,欲使一線行政人員轉變理念,把自己的工作作為與國家和社會緊密相關的高尚事業,必須首先從國家和社會的層面轉變治理理念,需要使一線行政人員、上級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公眾真正理解基層行政功能的發揮是建立在一線行政人員的日常工作基礎之上的,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一線行政人員為什么要掌控情境秩序,就會使情境秩序與宏觀秩序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政策不會自動執行,因而政策有沒有可執行性實際上是政策質量的重要指標,那么上級政策制定者在決策時考慮下級的執行特點也是決策過程的一部分。上級政策制定者在決策時應該把自己置身于基層行政情境中,反思自己會采取何種行動策略;雖然不能放松對一線行政人員的要求,但提出“既要……又要……還要……也要……”時也應該考慮他們需要上級政策制定者做什么。否則,在機關工作多年卻不知道基層行政如何運作,這種決策產生的政策質量是存疑的。基層形式主義往往出自對上級官僚主義的應付,要讓一線行政人員從思想上把公共行政當作事業而不僅僅是工作,那就要給予他們相應的空間,徹底整治文山會海和痕跡管理等繁文縟節,規范來自不同系統、持有不同口徑的考核檢查;激勵體系也應該以正面激勵為導向,崇尚實干和擔當而不是抓住細小過失不放。個人、組織、國家和社會多方需求在基層行政情境中得以兼容,情境秩序與宏觀秩序才可能得到兼顧。
(二)構建面向基層行政授權賦能的組織體系
僅僅減負還不夠,基層行政更需要授權賦能,而這背后其實是資源的重新分配。在制度設計上,基層行政在授權和賦能方面受到很大制約,但正如一統體制和有效治理之間的永恒矛盾那樣:上級可以把權能收得很緊,然而治理無效的結果又難以承受;如果把權能下放,監督成本過高,政策目標的達成又比較困難。這種情況下,無論采取行政發包還是其他策略,看似是在“統”的基礎上進行了下放,盡量確保了政策實施不走樣,然而這種方式給了基層行政自主權的同時,也對違背宏觀秩序的行為加以背書。行政發包是一種以宏觀秩序為導向的結果論行為模式,這期間基層行政一些越軌手段因其最終有利于結果實現而被正當化,特別是在組織體系內部得到了上級的首肯或默許。在此意義上,常見的行政發包制雖然在授權賦能,但并非真正面向基層行政,還是著眼于上級政策實施。同理,機關干部下沉或者所謂扁平化管理,也是著眼于上級政策實施,即便它可以制度化,但其可持續性卻存疑,因為這既打破了上級和基層的原有工作安排,又在某種程度上以運動式治理取代了常規治理,造成了行政資源向基層聚集的假象。權力主體還是上級,能力也是暫時補充基層隨時可以回收,等勢頭一過,基層還是權能不足。下沉更像是一種權宜之計,這只是一種基于上級意志的暫時轉移。
真正面向基層行政授權賦能是以授權為基礎的賦能,而不是臨時從上面調派人力或調撥資源,不以授權為基礎的賦能不可持續,最終仍存在自覺維護情境秩序的同時又自發破壞宏觀秩序的可能。所以,要從行政組織上下級之間的權力體系和權限設置出發,明確將相應權力以法律和政策等形式制度化固定到基層。既然“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那就要在減少“線”的羈絆的同時把解決實際問題的“針”真正做大做強。基層簡約治理的歷史傳統實際上主要存在于行政領域,現代基層治理的實踐又使得多元共治以及政府與社會合作的愿景成為一種潮流。但這一古一今的經驗和愿景都忽視了公共行政在當代的基礎性,為避免國家治理碎片化的局面和治理效能偏離公共價值,基層行政作為現代理性科層體系的基礎性作用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面向基層行政授權賦能,應以建設真正有權的基層行政為目的,而不是事事等批示、時時少資源,能夠在制度框架內明確基層行政的權限,在縱向治理體系中除了關注央地關系之外,還要改變基層的不完全行政現狀,這樣才能使基層行政從缺乏晉升渠道、編制資源、財政資源的結構性劣勢中解脫出來,而不只是淪為官員晉升的“經驗副本”、編制資源的“貧瘠礦床”、財政資源的“過路財神”。
(三)優化實現基層行政責任均衡的問責機制
權責匹配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邏輯。為基層行政授權賦能,問責也要跟上,然而目前基層行政的情況是權力不足也仍然有來自方方面面的問責。問責越多,避責的需求也越強烈,這會導致一線行政人員即便有權也不愿行使,出現所謂的一線棄權——畢竟如果出現過失想適用容錯的規定是非常嚴格的。
一線行政人員需要問責,但在現代行政責任體系中,只強調了下對上負責而忽視了上對下負責。這種上對下負責不是僅僅在下級出問題后承擔連帶的領導和監督責任,而是對下級的工作和生活承擔某種職責和義務。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理應受到制約、監督和問責,在各種理所應當的背后,上級是否有轉嫁責任的心理也值得警惕——畢竟大家都是理性人,在行動邏輯方面的差異并沒有職級之間的區別那么大。
這并非是降低對一線行政人員的要求,而是面向日常生活現實的務實。毫無疑問,基層行政要求一線行政人員負有更多和更大的責任,但公共行政既然具有公共性,那么它就并不僅僅指向一線行政人員,還指向上級、組織和國家,甚至是社會公眾。行政責任的均衡就在于,基層行政從應然上應該讓情境秩序和宏觀秩序銜接一致,那么上級、組織和國家以及社會公眾何嘗不對情境秩序負有責任。在科層體系內部,自下而上的負責當然是基礎性的,但自上而下的責任也是領導力的體現和保證。要求一線行政人員擔當作為,更應要求以上率下,由上級承擔起更大更全面的責任,由國家對宏觀秩序的實現方式進行統籌考慮。基層行政出了問題,在問責一線行政人員的同時,更要問責上級的實際決策者。即便將改善一線行政人員行動視為改進基層行政的關鍵方面,上級、組織和國家在這其中也責無旁貸。超越秩序落差不是因為一線行政人員擁有“原罪”,這是整個科層體系以及受其影響的政治力量和社會成員都要參與的共同事業。
綜上所述,基層行政的情境秩序實際上因互動而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它與宏觀秩序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線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既體現出對穩定即是秩序這一方式的總體繼承,更彰顯出對其進行系統改造的意愿。本文以社會建構主義解釋為本,吸收結構功能主義的合理方面,嘗試從基層行政互動和一線行政人員行動的角度回應這一問題,對治理主體行動表現出何種秩序、應該表現出何種秩序以及怎樣促使他們表現出這種秩序的動機進行了分析。這既是對國家縱向治理體系的一個自下而上的研究,更有一種從宏觀視野拓展街頭官僚理論的思考。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只有上下貫通,才能上下同欲,進而在國家治理中實現上下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