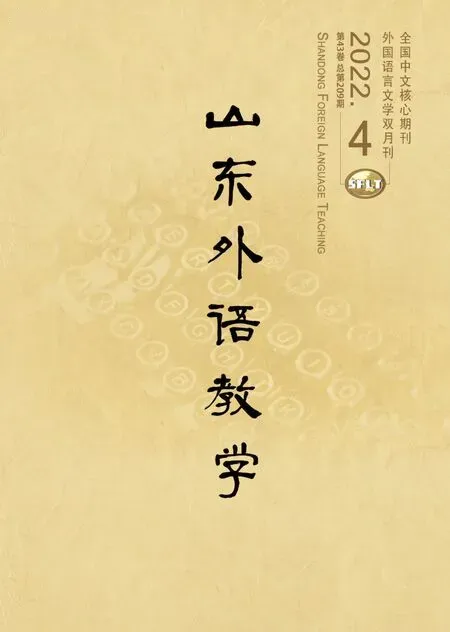《院長》中學院共同體的倫理危機
王菊麗
(魯東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0)
1.引言
C.P.斯諾(1905-1980)是戰后英國文學回歸現實主義傳統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系列小說集《陌生人與兄弟們》(StrangersandBrothers, 1940-1970)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戰后英國社會生活,奠定了在文學史地位。斯諾一生中親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帶給西方社會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摧殘,深諳“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際關系和人對社會的關系日益成為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里沖突的焦點”(瞿世鏡,1998:81)。由此他對現代性及其對社會秩序和心靈秩序的影響展開深度思考。在現代性從工業社會發展到20世紀的“風險社會”帶來的諸多風險當中,倫理危機是受到普遍關注的人類生存困境之一,其中同現代性與生俱來的“個人自我中心或個人主義的道德價值觀”(萬俊人,2002:135)被認為是倫理危機產生的思想根源。
斯諾在《陌生人與兄弟們》中致力于“講述社會中的人”(people-in-society)(Karl, 1963:25),“表現各種群體生活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個體與所在群體的對抗和交鋒” (Ramanathan, 1978:54),其中的學院派小說代表作《院長》(TheMasters, 1951)就是“對群體以及組成群體的成員所進行的最明確的探討”,回答了“群體到底由什么構成,是什么能夠使群體成為整體”(Ramanathan, 1978:54)等問題,其實就是斯諾對學院共同體倫理生活的思考。《院長》對學院公共生活中的倫理危機、倫理選擇失范以及倫理身份錯位等問題進行表現,隱含著作家對構建有意義的學院共同體生活秩序的期待。
2.學院共同體的倫理困境及其文學表達
“就共同體形成的基礎而言,共同體從不單純意味著‘共同的生活’,而且意味著在共同的生活中已經形成一種特定的倫理關系和共同的價值取向”(王露璐,2014:77)。有群體生活的地方,就會有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的發生,共同體成員只有彼此合意,形成社會整合力,才能使共同體得以延續下去并變得越來越美好。學院共同體作為高等教育機構首先是一個制度化、組織化的公共領域,它以文化精英為其成員的符號化形象,以傳授和創造知識、開展科學研究、傳遞文明文化為己任,以無功利之心、追求真理為公共精神。因此,學院共同體有其特定倫理意義上的公共生活指導原則。其次,學院共同體還可以體現為特定心靈秩序的存在。根據社會學家鮑曼的觀點,共同體首先“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共同體’給人的感覺總是不錯的,……它所傳遞出的所有含義都預示著快樂”,共同體生活是“我們能夠互相依靠對方”的地方(2003:2,3);這里沒有困境中的嘲笑、幸災樂鍋,而是充滿同情、原諒,沒有記恨,人們互相幫助,是一個“可以信任、他人的所言所行我們又可以依賴的友善的、心地善良的人群”(2003:4)。這種基于個體美好心靈的共同體倫理可以作為分析學院共同體人際關系的參照。學者們以什么樣的內在品質建構共同體生活,這其中包含著他們的倫理選擇。再次,倫理選擇決定了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它對個體的身份認同也會產生影響。由于“共同體是個體認識自我的基礎;沒有共同體,自我就被掏空了內容和意義”,而且“個體與自我的關系是通過他與共同體的關系進行調節”(Taggart, 2009:170),像在大學這樣組織化和專業性都很強、公共性質非常明確的領域,學者們的存在感、歸屬感、成就感甚至安全感和生存能力都是通過這個共同體實現,他們的倫理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自我認知。
作為戰后社會轉型時期的作家,斯諾在其作品中表現了英國“戰后大眾社會背景下的社會變遷以及‘善的生活’(the good life)和‘善的人’(the good person)之間如何相互影響”(De La Mothe, 1992:150),對社會秩序重建過程中的倫理道德生活予以關注。“從整體上看,《陌生人與兄弟們》主要關注的是正派的人置身矛盾和沖突之中時的道德問題”(Karl, 1963:5),對異化關系的焦慮逐漸凝結成了斯諾對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系和有意義的共同體生活的強烈愿望。他結合自己在政府機構、高等院校、律師事務所以及科學實驗室等領域的工作經歷,將自己的文學觀念融入了對個體與社會、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自我緊張關系的探索之中,“在致力于現實主義小說的回歸中努力表達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社會與個體以共棲共生的方式相互交融”(Ramanathan, 1978:16)。
根據羅森(Janice Rossen)的觀點,“學院派小說幾乎毫不例外地將競爭作為情節基礎,展示這個職業圈內的人想要獲取更大成就的野心,對職業競爭進行戲劇化表現”(1993:4)。小說《院長》以權力的競爭展開敘事,“成為學院派小說中表現學院競爭、勾心斗角和內訌的領先者”(Fullerty, 2008:245),被認為是“有史以來寫得最為出色的學院派小說”(Halperin,1983, 轉引自肖瓦爾特,2012:4)。《院長》以權力競爭主題表現了學院共同體生活的失守以及斯諾對重建學院共同體倫理生活的愿望。
3.公共權力的私人化與公共倫理的傾覆
《院長》是“斯諾對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揭示得最充分的一部小說”(Karl, 1963:68)。劍橋某學院原來的院長弗農·羅伊斯因為病重將不久于人世,新院長的兩個候選人杰戈與克勞佛德在各自團隊支持下把競選過程變成了“一場滿懷敵意的對抗”(斯諾,2007:26)①,在競選的幾個月時間里,整個學院都被與競選有關的各種力量所控制,導致“學院比任何時候都亂”(203),打碎了傳統觀念對大學是一個“溫暖舒適如子宮一樣的地方”(3)、“一個安定、溫暖舒適、與世隔絕的地方”的想象(肖瓦爾特,2012:4),所有人都因被卷入其中而倍感壓抑和焦慮,這樣的氣氛與鮑曼等學者對共同體生活的描繪大相徑庭。
《院長》中權力對倫理關系的顛覆首先體現在參加院長競選的兩位候選人身上。院長競選在學院生活中是一個公共事件,杰戈和克勞佛德作為候選人本該從公共責任的角度、以“規范合理性”和“公平正義優先”的公共理性對待這件事(梅景輝,2015:76)。然而在杰戈那里,院長作為公共權力的服務和管理職能從未被提及,“當上院長在他說來是一個標志……選他做院長說明人們尊重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甚至比他們還強。……野心迷住了他的心竅”(344)。杰戈非常欣賞“權力的戲劇性效果”,因為“他是一個野心家。他干的不論是哪一行,他都不甘居人后;他渴望掌權,如果權力能使他與眾不同,他就要占有權力。他講究穿戴、講究排場,他要有頭銜,要顯赫一時。如果聽到人家叫他一聲院長,他該多么高興呀;他渴望能在一次學院會議上宣布開始執行一項正式條例:‘我,保爾·杰戈,本學院院長……’;他向往住在堂皇的院長住宅里,跟其他學院院長比美”(6)。“院長”權力的符號意義被杰戈的個人欲望和野心所放大,成了他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體驗掌控和支配他人的快感、享受較好的物質生活待遇、滿足虛榮心的手段。受這種想法驅動,杰戈在競選過程中的不擇手段就可見一斑,選舉過程的公正性也肯定無法得到保證。杰戈眼里的院長之職“與其說是公共權力,毋寧說是私人權力(more individual than communal)”(Karl, 1963:69),公共權力被私人化了。與此同時,公共倫理中的利他性原則也被利己主義動機所稀釋,共同體生活中公共性優先的倫理被顛覆。關于院長這個職位的倫理價值,斯諾在小說中通過敘述者埃利奧特之口說:“一位院長應該是大公無私,關心別人;寬宏大度而且有幾分浪漫的想象力……寬宏、豁達,更能關心別人”(103)。對比之下,院長的公共權力被杰戈的欲望和野心私人化,體現了他對待公共生活的利己主義倫理觀,同時也說明被權力欲望所控制的學院生活公共倫理受到破壞。小說對另一位競爭者克勞佛德所著筆墨雖然不多,但在有限的篇幅中也可以看出他和杰戈一樣垂涎院長這個職位,對競選活動也表現出相近的態度和價值取向。
公共倫理的破壞也體現在兩個候選人身后的支持者對待權力的態度上。在杰戈的競選團隊中,布朗、克里斯塔爾、南丁格爾等人都有著個人企圖,盡管他們都知道自己的學術成就和影響不足以有參選院長的資格。“他們對自己的‘辦事’能力十分自信。他們心照不宣,各種統治權術無一不曉。……學院里發生的大事沒有一樣不是得到他們的支持的。……他們毫不懷疑自己從事的各種活動是起作用的。”(31)克里斯塔爾很享受能夠操控競選過程、甚至左右競選結果的權力之感,覺得自己“在這個小小的學院王國里也算是數得著的實權人物。……親眼看到了自己對杰戈所發生的影響,那是十分重要的。”(65)最后,在了解到杰戈和克勞佛德之間勢均力敵,克里斯塔爾把自己這關鍵一票轉而投給了克勞佛德,使其最終在競選中勝出,由此感受到了極大的滿足,全然不顧這樣做有悖學者的文化品格和公共生活規范。而南丁格爾支持杰戈參選僅僅是希望他在當選之后能運用手中的權力幫助自己實現做導師的愿望,被杰戈拒絕之后他將自己這一票也轉而投給對他并無好感的克勞佛德,期待以此換來后者能在他申請成為皇家學會會員時給予特殊關照。布朗雖然從始至終站在杰戈一方,其初始目的不外是能夠體驗在競選團隊中坐鎮指揮的領導者之感。小說從頭到尾把院長競選這個公共事件演繹成了滿足權力欲望和私人利益的契機,學院共同體原本具有利他性和公正性的公共倫理完全被功利主義態度和利己主義的邏輯遮蔽。
4.倫理行為失范與人際關系的異化
作為表現學院內部競爭的經典之作,《院長》展現了一個充滿對抗、傾軋的學院生活,顛覆了人們對“由社會地位較高或才能出類拔萃、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組成”的象牙塔式學院生活的想象和認知(Ramanathan,1978:55),也揭露了共同體本該以信任、共享、互助、友愛等倫理品質維護的人際關系被異化的狀況。從表面上看,人際關系的異化與院長競選事件相關。然而從深層看,在利己主義對利他主義優先性的原則下,人們的各種選擇都對倫理行為形成挑戰,進而對人際關系產生影響。
杰戈與克勞佛德之間關系的異化主要表現為在欲望和野心的驅動下由平衡走向敵對的態勢。競選使兩人由原來平等的同事關系變成了競爭對手,并在爭奪權力的廝殺中成了幾乎要置對方于死地的勁敵;所采取的行動也喪失了共同體公共生活該有的協作機制,被進攻和防御機制所取代。在《院長》中斯諾的代言人埃利奧特看來,“學院選舉跟政界領導階層的一些活動十分相像,簡直令人吃驚。后來我有幸觀察人與人之間更大規模的爭斗,不禁使我想到此時此刻發生的事情”(330)。隨著競選過程在私下串通、密謀策劃、游說拉票、引導評議員投票等不符合正義、公平原則的行為中展開,杰戈和克勞佛德與他們各自的支持者將“嚴肅的選舉由此演變成一場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的鬧劇”(黃福武,2007:4),學院共同體變成了權力政治角斗的戰場。小說結尾處,當克勞佛德以一票的優勢勝出,杰戈在不得不面臨敗選的局面時感到將要蒙受奇恥大辱,這種傷痛反復地折磨著他。由于缺乏公共理性,杰戈不能客觀地面對敗選的事實,敗選對他來說意味著自己反而將要成為克勞佛德掌控和支配的對象。由于“個人利益占據了理性的高地”(Karl,1963:71),公共理性讓位給了個人野心和主觀感受,公共行為準則完全被個人行為準則所取代,人際關系的失衡就一定會發生,公共生活的秩序也因此走向解體。
隨著杰戈與克勞佛德之間圍繞權力展開較量,他們周圍的同事也通過選擇自己的支持者分成了水火不容的兩派,造成學院共同體內在整體性和穩定性遭到破壞。“學院生活中的學者們樂于強化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自己是屬于這個或者那個圈子的,而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根本無法涉足這些圈子,學者們也往往在這個領域里為權勢地位展開競爭。”(Rossen, 1993:4)在《院長》中,人際關系的異化還可以從支持克勞佛德的溫斯洛身上得到印證。身居總務長要職的溫斯洛“性情粗暴,說話魯莽,跟學院里大多數同事關系都不太好。院長很久以前跟他爭吵過……他跟杰戈是水火不容的。克里斯塔爾不喜歡他,也毫不原諒他”(18)。溫斯洛雖然沒有什么學術成就,但他能夠讓“全學院的人卻都感到他是一位重要人物”(18),對他來說,個人的感受更重要,別人怎么看他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他在乎的只有自己的“權力感”,而這一切與一個正派、體面學者的修為大相徑庭。
南丁格爾是《院長》中唯我至上價值觀導致劣質人際關系的另一典型。他希望在根本不具備資格的情況下當上導師并成為皇家學會的成員,因此他先是選擇站在杰戈一邊,在遭到拒絕后,他做出的反應是“開始惡毒攻擊杰戈和他‘那一派’”(155),到處散布關于杰戈和他妻子的謠言。當他以同樣的個人目的轉而決定投票給克勞佛德時,后者拒絕用不正當手段幫他實現,他就充滿了怨恨。南丁格爾在投票這件事上的顛來倒去以及在選擇時表現出的痛苦、懷疑、嫉恨,都與他的個人利益沒有得到實現有關,因此從一開始就成為埃利奧特最反感的人。“學院里只有這個人(南丁格爾)我最不喜歡,而他也同樣不喜歡我。為什么我們彼此不喜歡呢,我想并沒有什么別的理由;只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念、我們的思想毫無共同之處,不過,盡管別人的思想跟我的也沒有共同之處,但是我卻熱愛他們。我不喜歡他正像我喜歡別人一樣,都是一種特殊感情,不太好解釋。如果不是在學院里,那我們是會互相躲著的”(45)。在南丁格爾的行為選擇中包含著工具理性而不是價值理性,體現的是實用價值對生命價值的消解。這是典型的現代人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的最大特征就是感性欲望的張揚”(李佑新,2006:2)。它瓦解了大學自誕生之日建立起來的超越價值,極端個人主義倫理摧毀了本該以和諧、穩定、互信、親密等為特征的學院共同體人際關系。
5.公共人的陷落與倫理身份的錯位
《院長》對學院共同體中個體與群體生活關系的刻畫蘊含著對學者們倫理身份的反思。“倫理身份是評價道德行為的前提。在現實中,倫理要求身份與道德行為相符合,即身份與行為在道德規范上相一致”(聶珍釗,2014:265)。由于共同體視閾中的個體身份是由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構成的,有意義的共同體需要兩者之間維持平衡,滿足共同體生活對個體的道德要求。“斯諾發現,對個體的探討一定同時意味著對社會中的人的考量……只有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得到審視,對人的理解才能合乎情理”(De La Mothe,1992:160)。斯諾的觀點源自一個哲學命題,即“人生來是社會的動物,社會總是以各種共同體的形式存在,因而,人又是共同體的動物”(胡群英,2013:12)。共同體生活中人的完整自我要求公共自我對于私人自我具有優先性,健全的人格是通過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間的有機互動達到平衡來實現的。個體的行為和選擇符合構建共同體生活所必須的倫理道德,是個體實現與共同體之間共生關系的重要途徑。然而,對個人性的絕對化強調無異于使群體生活成為個人權利至上主導,公共性優先的社會規范就會被排斥,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紐帶也就無法建立起來,健全、完整的自我自然也就無從談起。因此,“在這個以無歸屬感和關系疏離為關鍵詞的時代,我們本能地提醒自己,尋求一個完整或全面的私人經驗與公共經驗之間平衡的自我認同實際上是20世紀晚期留給我們的唯一一個英雄主義壯舉”(De La Mothe, 1992:4)。
在《院長》中,倫理身份的錯位首先表現在私人自我被置于較公共自我更為優先的地位。參與院長競選活動的大多數人都表現出自我中心主義傾向,他們追求自我滿足的私人經驗與按照規定原則和程序推選新院長的公共經驗發生混淆。在競選活動過程中,兩個小集團的成員都采用各種手段左右評議員的投票,形成個人意志對公共意志的干預,公共自我以公共理性參與的競選活動就變成了私人自我實現個人欲望的場所。《院長》中倫理身份的錯位還表現在學者身上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淡化。“大學教師,一個知識分子群體,較之以往具有了雙重職責:傳授知識和創新知識。同時,要治愈人的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隔離感”(陳嘉,2011:10)。在大學這個特殊的公共領域,學者們還兼有“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以理性代言人的角色批判社會,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公共知識分子責任(劉亞敏,2006:37)。作為社會價值信念的守望者,他們在持守公共道德、維護社會正義等方面對公共生活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其他人。然而《院長》中的杰戈、南丁格爾們卻表現出公共責任和公共精神缺失等特性,根本無法提供社會期待中的終極意義生產和大學精神的彰顯。因此,《院長》實際上描繪了一幅公共知識分子缺場的學院生活圖景。
6.結語
西方戰后進入風險社會以后,由現代性引發的倫理危機是現代社會結構轉變、即個體化社會形成所帶來的必然后果。“隨著個體化過程的發展,工業社會中的集體意義正在枯竭。個人從工業社會的秩序中被釋放到全球風險社會中,不得不在倫理生活中面對各種各樣的風險與危機”(李義天、邵華,2013:77)。倫理危機對個體認同、人際關系以及個體價值取向都產生影響。西方大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與現代化歷史進程同步發展,個體化社會結構以及世俗化、商業化等社會特征都對大學的內涵、功能特別是對大學原有的倫理秩序和超越性價值產生影響。斯諾以政府官員、科學家和文學家等多重身份和廣為人知的“兩種文化”思想,在文學生涯中對社會多個公共領域的倫理問題進行關注。他不僅結合戰后科技發展對文化的影響,展開“對科學倫理道德的深刻思考”,體現科學人文主義思想(姜慧玲,2022:86);還在其學院派小說中借助權力競爭的敘述揭示由現代性導致的共同體倫理危機及其對學院公共生活運行機制的影響,探討突破個體化社會的局限、建立基于倫理關系的共同體生活秩序。
“學院派小說的主要敘事結構之一就是對一個封閉世界的斷裂及其向秩序和常態的逐漸復原所做的關注”(Connor, 1996:69)。《院長》以競爭和沖突為主題表現了學院公共生活的倫理失范,而作為一個有著廣闊社會視野的作家,斯諾在《院長》中其實也“形象地傳達了整個國家的總體狀況”(Connor, 1996:70)。學院生活題材寄托著斯諾從共同體維度對社會生活的表現,包含著斯諾對共同體生活中被欲望異化了的人與他人、人與自我和人與共同體之間關系及其倫理向度的深度剖析。在戰后原子化的社會中,即使如大學校園這樣與外部社會相對隔離的世界,個體也如支離破碎的碎片化存在。彼此之間緊密相鄰卻缺乏深度交融,反而由于一些個人主義價值取向和利己化的倫理準則,片面追求自我滿足的信仰而不是使公共秩序得到延續的行為規范,導致維護共同體生活的倫理意識難以形成。
作為一部具有人文情懷的學院派小說,《院長》表達了彌合斷裂的文化傳統、修補疏離的人際關系、重塑塌陷的知識分子身份、恢復學院文化秩序的共同體倫理思想。正如小說中院長職位之爭的勝出者克勞佛德所說:“我認為我們應當為自己樹立一個高標準的禮貌、行為準則。我要提醒諸位,任何親密友好相處的社會,都應該制定規章制度,這是很重要的。”(280)這不外乎是在表達,具有倫理意義的品行才是實現美好共同生活的途徑。
注釋:
① 引文出自C. P. 斯諾:《院長》,張健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以下出自該著引文僅標明頁碼,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