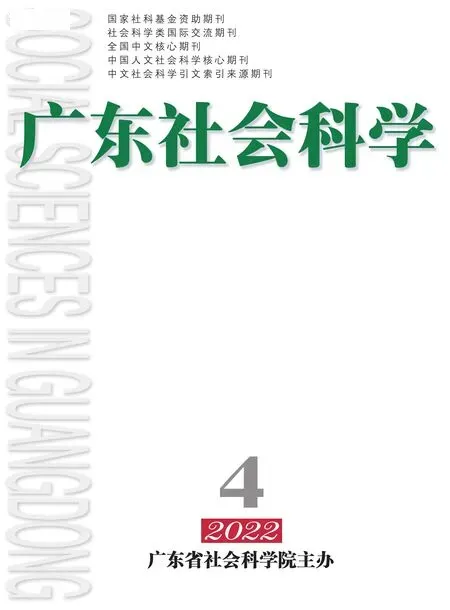社會不平等中的“組織”因素:當代中國組織分層研究的特征與挑戰*
朱 妍 王修曉
引言:組織因素對社會分層的影響
現代社會呈現高度組織化特征,工作組織已成為人們獲取穩定收入、福利保障、社會地位的基礎。這種由“組織”產生的分層,極大地影響了當今世界的社會分層格局。“組織分層”這一領域涵蓋了“組織”和“分層”兩個核心概念。這里的“組織”指正式組織(formal organization),也就是有著明確目標和運行模式、穩定的組織架構,以及通過勞動分工和權力等級來實現某種功能的社會性系統。如公司、學校、政府等,都是正式組織的典型形態。相比之下,興趣小組、網絡社群、同鄉會等就屬于非正式組織(informal organization),結構相對松散,目標較為模糊,資源獲取和分配能力也比較弱。“分層”則是指各種回報、獎賞與生活機遇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平衡分配。“組織分層”的核心就是正式組織通過在勞動力市場中的雇傭實踐(hiring practices)所造成的資源不平衡分配后果。①James N.Baron,“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tratific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0,no.1(August 1984),pp.37-69.
在當代中國的制度和文化情境下,組織特征對于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既包括以單位制為主要特征的傳統組織機制,也涵蓋了市場化改革以來涌現的新型組織形態影響,兩種類型相互關聯,共同形塑了當代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結構。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有不少海外中國研究者對指令性計劃時期的單位體制投入了大量的興趣,他們注意到新中國的工作場所和組織方式與眾不同,認為單位體制的運作是經濟分配與社會管理的微觀展現,單位類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福利與社會地位。②Gail E.Henderson and Myron S.Cohen,The Chinese Hospital:A Socialist Work Uni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E.M.Bjorklund,“The Danwei:Socio-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Work Units in China’s Urban Society,”Economic Geography,vol.62,no.1(January 1986),pp.19-29;Marc J.Blecher and Gordon White,Micr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 Technical Unit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Palgrave Macmillan,1979,pp.9-31.無論是傳統單位制的延續,還是市場轉型背景下組織形態與功能的變革,都激發著研究者不斷探究“組織”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產出了大量重要成果。
本文將首先對1990年代以來有關中國組織分層的重要文獻進行分類綜述,聚焦于兩個維度,一是組織間社會分層,體現在城鎮居民由于受雇于不同類型的單位組織而產生的生活機遇分化,二是組織內社會分層,體現在不同類型的單位組織強化或弱化某些變量的分層作用。在操作化層面,第一個維度體現為單位組織特征的凈效應,第二個維度則體現為單位組織特征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分類綜述之后,本文將基于既有文獻來分析中國組織分層的制度成因,即制度慣性與再分配權力的延續,以及制度變遷和對外部沖擊的回應。
最后,作者指出,目前有關中國組織分層的研究在對于組織本身的分析上仍存在欠缺,大多數研究對于勞動力市場上的雇主機構如何招募、遴選、培養員工,如何匹配職位和分配資源,如何影響生活機遇分化的社會與制度過程的關注仍嚴重不足,由此使得中國的組織分層研究常常只是作為轉型社會分層研究的一條支脈,在議題設置、方法選擇和理論發展上都受到一定的局限。作者提出,要將“組織”帶回“組織分層”研究,借鑒和對話組織研究的前沿成果,在更普遍意義上做出理論突破。
一、組織間不平等的表現形式:“集團”因素導致的社會分化
對于改革后城鎮居民的生活機遇出現分化,研究者認為,單位類型、行業特征等“集團”層次的因素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同樣個體稟賦、從事同樣工作的員工,在不同的單位就職,他們在收入、福利、住房分配、發展機遇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
首先,“集團”因素對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影響巨大。對于改革初期中國城鎮的調查研究顯示,所在工作單位的規模大小、行政級別和所處行業,對職工的生活機遇、職業聲望和社會地位都有很大影響。邊燕杰利用天津市的調查數據發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有部門職工在各項經濟指標上都顯著優于集體和私營部門的雇員。①Yanjie Bian,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p.162-166;Yanjie Bian and John 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of Power: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1,no.5(October 1996),pp.739-758;Nan Lin and Yanjie Bian,“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7,no.3(November 1991),pp.657-688.魏昂德對于各種統計數據的分析也呈現,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的工資收入相比非國有單位有較大優勢。②Andrew G.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39-56.王天夫和王豐經測算后指出,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集團”類別,如地域、行業、所有制類型和單位級別等,可以解釋九十年代中期大約一半的收入增長差異。③王天夫、王豐:《中國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團因素:1986—1995》,《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郝大海和李路路發現國家壟斷部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封閉性,會產生相對于競爭性非國有單位在資源獲取和分配方面的優勢。④郝大海、李路路:《區域差異改革中的國家壟斷與收入不平等——基于2003年全國綜合社會調查資料》,《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謝宇和吳曉剛運用1999年在武漢、上海和西安三個城市的調查數據發現,在效益好的單位里工作的職工,其收入是效益相對較差單位職工的2.5倍。⑤Yu Xie and Xiaogang Wu,“Danwei Profitabilit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95(September 2008),pp.558-581.李駿也發現,所在單位的組織規模對職工收入的影響,在1996到2006年間幾乎翻了一倍。⑥李駿:《組織規模與收入差異——1996—2006年的中國城鎮社會》,《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5期。
其次,“集團”因素對于職工的收入外福利水平起了決定性作用。國有部門提供福利的能力要顯著優于非國有部門;在國有部門內部,行政級別越高,上級主管部門的財政預算越有自主性,單位也越有能力為職工提供福利。⑦Andrew G.Walder,“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7,no.4(August 1992),pp.524-539.研究者發現不同所有制部門職工的醫療費用支出有巨大的組間差異。⑧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99-101.養老和醫療保障在不同單位間的差異也十分顯著。⑨李實、趙人偉、高霞:《中國離退休人員收入分配中的橫向與縱向失衡分析》,《金融研究》2013年第2期。羅楚亮和李實發現,不同行業/企業間的工資性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如果考慮補貼與福利性收入,組織間差異就顯著提升,尤其體現在住房補貼與住房公積金上。⑩羅楚亮、李實:《人力資本、行業特征與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的經驗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0期。于良春和菅敏杰測量了不同行業員工的隱性收入和隱性福利,發現在2003年到2010年間,銀行業職工的隱形收入和福利逐年增加,與競爭性行業(通信設備、電子設備制造業)相比,從2003年的15.23倍,增長到2010年的18.29倍。?于良春、菅敏杰:《行業壟斷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因素分析》,《產業經濟研究》2013年第2期。
第三,單位類型仍然是決定職工獲取住房資源的主要因素。早期研究就發現,單位類型和行政級別等因素有助于職工獲得更好的住房條件,?[美]邊燕杰、[美]約翰·羅根、盧漢龍、潘允康、關穎:《“單位制”與住房商品化》,《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1期。這種影響并沒有被市場化改革削弱。利用2010年廣州市千戶問卷調查數據,劉祖云和毛小平發現,所在單位的行政級別越高,職工的住房階層地位也越高。①劉祖云、毛小平:《中國城市住房分層:基于2010年廣州市千戶問卷調查》,《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王寧和陳勝認為,住房產權的分化更多體現的是居民的市場能力,但也存在過去再分配機制下的優勢通過市場化機制放大的可能性。②王寧、陳勝:《中國城市住房產權分化機制的變遷——基于廣州市(1980-2009)的實證研究》,《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第4期。劉欣指出,單位制和再分配權力仍然對住房資源的分配產生重要影響。③劉欣:《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多元動力基礎——一種權力衍生論的解釋》,《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就住房套數而言,蔡禾和黃建宏發現,個體人力資本不能很好地解釋二套住房分化,相反,具有體制優勢的權力精英在二套住房獲得上保留了較大優勢。④蔡禾、黃建宏:《誰擁有第二套房?——市場轉型與城市住房分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4期。總而言之,隨著住房商品化的深入推進,市場因素的重要性雖然逐漸提升,但單位類型的影響會與市場化機制結合,進一步擴大住房不平等。⑤吳開澤:《房改進程、生命歷程與城市住房產權獲得(1980—2010年)》,《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5期;吳開澤:《住房市場化與住房不平等——基于CHIP和CFPS數據的研究》,《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6期。
最后,工作單位的特征還深刻地塑造了中國城鎮居民地位獲得的路徑和模式,體制內工作背景和干部經歷有助于本人或子代獲得更有利的社會流動機會或保持地位優勢。吳曉剛考察了1978至1996年間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下海”進入自雇職業的過程,發現在市場化改革早期,體制內非干部的邊緣群體更有可能成為第一批“弄潮兒”,但權力精英后來居上,取代前者成為自雇群體的主要來源。⑥吳曉剛:《“下海”:中國城鄉勞動力市場轉型中的自雇活動與社會分層(1978-1996)》,《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6期。劉欣發現,在轉型過程中,公職精英與市場精英存在兩條不同的地位獲得路徑:在相對封閉的權威型支配—服從階層關系中,政治忠誠者更有可能通過庇護式的社會流動在體制內獲得精英地位。⑦劉欣:《英才之路:通往轉型社會二元精英地位的雙重路徑》,《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4期。鄭輝和李路路把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體制內精英分為行政干部精英、技術干部精英和專業技術精英三類,并提出一個“精英代際轉化和階層再生產”替代模型。⑧鄭輝、李路路:《中國城市的精英代際轉化與階層再生產》,《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6期。呂鵬和范曉光對中國精英地位代際傳遞的研究同樣發現,大企業主更有可能具有體制內的工作背景。⑨范曉光、呂鵬:《中國私營企業主的社會構成:階層與同期群差異》,《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公有制部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在經濟精英、中產階級等群體的地位保持和代際地位延續上都得到了明顯體現。⑩李路路、李升:《“殊途異類”:當代中國城鎮中產階級的類型化分析》,《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6期。
二、組織內不平等的表現形式:組織特征與既有分層變量的交互作用
組織分層的另一個重要的表現形式是組織內分化,也就是組織在向成員分配資源和機遇時會采取差別對待的做法。在經驗研究中,往往會表現為組織特征強化或削弱了既有分層變量的影響。從既有研究發現來看,在不同部門、不同時期,組織的影響可能并不一致:在改革初期,某些體制內單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場因素帶來的不平等,但這種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顯著弱化;對于絕大部分單位來說,組織與性別、勞動人事身份等幾項重要的分層變量會產生交互作用,從而形塑組織內部的不平等分配。
對于改革中前期的研究發現,在某些國有單位內部,平均主義的分配特征確實削弱了市場因素帶來的分層效應,不少國有企業在市場化改革開始后仍然在內部分配上采取平均主義的模式,職務職級、績效、教育技能等因素在分配中的作用并不大。①Jon Cauley and Todd Sandler,“Agency Theory and the Chinese Enterprise under Reform,”China Economic Review,vol.3,no.1(Spring 1992),pp.39-56;Andrew Walder,“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vol.118,no.2(October 1989),pp.242-264.羅楚良分析了某壟斷型國有企業職工2002~2004年的收入變化,他發現企業內部基尼系數只有0.06~0.07,尤其是超額獎金的發放是高度平均主義的。②羅楚良:《壟斷企業內部的工資收入分配》,《中國人口科學》2006年第1期。在性別不平等方面也有類似發現:李春玲與李實分析了1988、1995和2002年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后發現,國有部門的性別收入差距是最低的。③李春玲、李實:《市場競爭還是性別歧視——收入性別差異擴大趨勢及其原因解釋》,《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2期。不少研究對這一結論予以呼應,認為在國有部門中,女性的收入劣勢不明顯。④亓壽偉、劉智強:《“天花板效應”還是“地板效應”——探討國有與非國有部門性別工資差異的分布與成因》,《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年第11期;張丹丹:《市場化與性別工資差異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1期;Pak-Wai Liu,Xin Meng and Junsen Zhang,“Sectoral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ese Economy,”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13(July 2000),pp.331-352.研究者指出,導致這種平均主義分配模式的原因是,隨著資源由上級主管部門控制的外部化模式轉變為以企業內部控制為主的內部化模式,國有企業資源的社會化占有也轉變為單位化占有,從而形成了利益共同體。⑤劉平、王漢生、張笑會:《變動的單位制與體制內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國有企業為例》,《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3期。
盡管上述研究認為組織削弱了某些分層因素的作用,但絕大部分研究者仍然強調,組織總體上維持、甚至強化了大部分分層因素帶來的影響,研究者們集中討論了兩類不平等,一類是組織內性別不平等,另一類則是因組織內身份和層級差異而形成的不平等。
在性別不平等上,組織作為提供工作的載體會通過職位分配、同工不同酬、低估女性的技能與業務價值來形塑和強化性別不平等。研究者指出,市場部門的性別工資差距十分顯著。⑥亓壽偉、劉智強:《“天花板效應”還是“地板效應”——探討國有與非國有部門性別工資差異的分布與成因》,《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年第11期;張丹丹:《市場化與性別工資差異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1期。由于缺乏正式的工資制度或是出于隱私保密機制,非公企業員工的工資大多由老板、合伙人或高管人為單向決定,企業方會利用信息不對稱、出于各種目的給予女性員工更低的薪水,形成薪酬歧視。⑦汪力斌、宮君:《關注女工程師的生產力——女工程師職場歧視狀況的案例狀況》,《生產力研究》2009年第12期;顏士梅:《企業人力資源開發中性別歧視維度及程度的實證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顏士梅、顏士之、張曼:《企業人力資源開發中性別歧視的表現形式——基于內容分析的訪談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民營企業往往因規模較小而缺乏健全的職工培訓體系,晉升流程也不夠完善和透明,女職工就會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獲得晉升和發展機遇。⑧毛海強、姚莉萍:《服務行業中女性的工資歧視研究——對某高校后勤集團的調查》,《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外資企業在雇傭階段的男女平等做得更好,⑨李磊、王小潔、蔣殿春:《外資進入對中國服務業性別就業及工資差距的影響》,《世界經濟》2015年第10期。但卻容易出現職業性別隔離和晉升上的“玻璃天花板”現象。①顏士梅、顏士之、張曼:《企業人力資源開發中性別歧視的表現形式——基于內容分析的訪談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在以扁平化、去科層化、平等主義自詡的高科技行業,性別不平等至少沒有被削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強化了。夏冰青對于互聯網企業的研究發現,這一行業的女性大多集中在行政類工作,與從事技術類工作的男性呈現職業的性別隔離,即便是從事技術工作的女性,也會被認為水平較低。②夏冰青:《依碼為夢:中國互聯網從業者生產實踐調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132—135頁。性別標簽通過科技行業特征、職場文化等因素不斷得到復制,并再生產了女性從業者在薪資、培訓、晉升等多方面的不利處境。③蔡玲:《科技職場中女性的職業處境與性別管理——以IT女性程序員為例的質性分析》,《青年探索》2020年第5期;梁萌:《加班:互聯網企業的工作壓力機制及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孫萍:《技術、性別與身份認同——IT女性程序員的性別邊界協商》,《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2期;孫萍:《性別的技術政治——中印“程序媛”的數字勞動比較研究》,《全球傳媒學刊》2021年第1期。
國有部門內部的性別平等狀況是否更好,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見。蔡禾和吳小平的研究發現,改革使得體制內單位的職業性別隔離程度迅速上升,到世紀之交時,體制內單位已經體現不出性別平等方面的優勢。④蔡禾、吳小平:《社會變遷與職業的性別不平等》,《管理世界》2002年第9期。朱斌和徐良玉利用多個時點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發現改革初期集體單位和私有單位的性別收入差距顯著高于國企,但2002和2013年調查則顯示,不同所有制的性別收入差距出現趨同。⑤朱斌、徐良玉:《市場轉型背景下性別收入差距的變遷》,《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在組織內身份和層級差異方面,既有研究主要關注因勞動人事身份和職務職級因素導致的層級差異。勞動人事身份導致的組織內分層主要指用工單位通過非正式用工形式招募不同勞動人事身份的勞動者,從而維持生產靈活性和用工低成本,⑥這里,作者傾向于不將人數眾多、規模龐大的互聯網平臺企業靈活用工所帶來的收入與福利保障分化看作是組織內分層,原因是對于共享經濟用工模式是否屬于雇傭與被雇傭關系仍然存在爭議,對于平臺用工是否應被定性為勞動關系仍不明確。可參見常凱、鄭小靜:《雇傭關系還是合作關系?——互聯網經濟中用工關系性質辨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李怡然:《困住騎手的是系統嗎?——論互聯網外賣平臺靈活用工保障制度的完善》,《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王天玉:《超越“勞動二分法”:平臺用工法律調整的基本立場》,《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謝增毅:《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關系認定》,《中外法學》2018年第6期等代表性研究。本文所論述的組織內分層指涉傳統雇傭關系,組織對于職工生活際遇產生影響的邏輯不能簡單推至平臺用工情境下,故而在文中沒有對這一現象的相關文獻做系統綜述和分析。其中尤以公有制部門的做法及后果更為突出。也就是說,公有制部門或單位會強化勞動人事身份帶來的收入和福利差異。因為受到用人編制限制、事權擴大、績效-成本壓力等因素影響,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一部分參照事業單位管理的央企招募了大量非編人員。⑦胡曉東:《我國政府“編外人員”隱性膨脹研究——一個基于我國地方政府的案例調查》,《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呂德文:《“混合型”科層組織的運作機制——臨時工現象的制度解釋》,《開放時代》2019年第6期;葉靜:《地方軟財政支出與基層治理——以編外人員擴張為例》,《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1期。政府部門的編制外人員,大部分實行企業化管理,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就業穩定性較低,幾乎沒有享受培訓、獲得職業晉升的機會。①呂芳:《中國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員”與“同心圓”結構——基于街道辦事處的實證分析》,《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楊云霞、黃亞利:《公共部門臨時工的身份沖突——對88份文本的實證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2期。胡曉東對北京某區政府系統“編外人員”的研究發現,逾四成既沒有簽訂合同,也未投繳社會保險,薪酬福利“既沒有以崗位評級為基礎,也沒有參照市場規律”。②胡曉東:《我國政府“編外人員”隱性膨脹研究——一個基于我國地方政府的案例調查》,《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有研究考察了醫院的編外人員,發現編制內外存在嚴重的同工不同酬現象,有超過七成編外人員沒有完全繳納“五險一金”;編外人員內部盛行平均主義分配,缺少晉升和薪酬福利增長空間。③馬效恩:《事業單位編外人員薪酬激勵問題及對策——以M市公立醫院為例》,《中國行政管理》2013年第11期。高校以“師資博士后”名目招募的青年教師隊伍也面臨很大的生存困境,包括軟硬件條件供給不足、期滿無法留任、精神上的壓力與自卑感等。④李晶、李嘉慧:《“雙一流”建設下的師資博士后:“青椒生力軍”還是“學術臨時工”》,《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第23期。
職務職級是另一個重要的分層變量,研究者發現,有些組織特征會影響職務職級帶來的收入或福利回報,擴大職務職級的效應。企業卷入市場競爭的程度會構成職務職級的交互變量,研究者發現,企業面臨市場競爭越激烈,職務職級之間的收入和福利差距越大。對國企的研究指出,國有企業改制程度越深,職務變量對于工資和收入的影響越大,經營者或中高層管理者往往從持有股份中獲取高額分紅,同時他們的職務工資和津貼也大為提高,因此不同職務、職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顯著擴大。⑤郭榮星、李實、邢攸強:《中國國有企業改制與職工收入分配——光正公司和創大公司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3年第4期;對于科技類互聯網企業的研究也發現,這些組織的業務架構不穩定,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某些管理或技術崗位的可替代性較低,因此組織內出現了明顯的科層制等級。⑥夏冰青:《依碼為夢:中國互聯網從業者生產實踐調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84—87頁。
三、組織間與組織內不平等的制度成因
前文中我們梳理了有關中國組織分層的文獻,主要呈現了研究者在這一議題上的經驗發現。這一節,我們將基于既有研究來歸納和分析組織不平等之制度成因,探究形塑中國當代組織分層模式的動力機制。研究者的分析觸及不同的學科和領域,對這些研究進行歸納和提煉后可以看到,研究者大體聚焦于制度主義視角的兩個切入點,一是制度慣性與再分配權力的延續,二是制度變遷以及對外部沖擊的回應。
(一)制度慣性與再分配權力的延續
制度慣性與再分配權力延續的視角特別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下中國組織間的諸多不平等現象。在既有經典文獻中,組織作為勞動力市場上的雇主,會對資源、回報、獎賞和機遇進行分配,由此導致了被雇者的生活機遇出現分化。如果在中國情境下討論組織的作用,組織作為資源分配之中介的作用更為顯著。相對于以市場機制分配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長期以來更倚賴再分配機制,而單位組織就是再分配機制的重要環節,因此,單位組織的規模、級別、所有制類型等因素就構成了組織間不平等的基礎和推動力。
改革后各類組織機構在占有和分配資源上的差異源于改革前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制度慣性所導致的再分配權力持續發揮作用,是當下組織間資源分布高度不均等的原因。早期一些海外中國研究者就對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工作單位產生了好奇,認為這些組織嵌入于科層體制中,地位各不相同,資源獲取能力也有很大差異。①Andrew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28-29.這種組織間差異延續至今,由此形塑了單位在社會分層中的重要性。②李路路、秦廣強、陳建偉:《權威階層體系的構建——基于工作狀況和組織權威的分析》,《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6期;林宗宏、吳曉剛:《中國的制度變遷、階級結構轉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會》2010年第6期;劉欣:《協調機制、支配結構與收入分配:中國轉型社會的階層結構》,《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研究者認為,再分配性質越強、市場化轉型程度越弱的組織,在資源獲取和占有上就越是居于相對優勢地位;行政性壟斷的存在扭曲了包括資本、資源、勞動力在內的各種要素的價格,由此對非壟斷行業或企業產生了不利影響。這些居于資源優勢地位的行業或單位組織,往往還能夠享受到更多與勞動力相關的公共服務與優惠政策,例如可以獲得更多的大城市落戶指標、租/購房優惠名額、各類人才或項目扶持資金等等,這些服務和政策可以幫助組織在勞動力市場上進一步固化有利地位,在招聘、雇傭和培養相同資質的員工時付出相對更少的成本。③陳釗、萬光華、陸銘:《行業間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鎮收入差距原因——基于回歸方程的分解》,《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也有研究者指出,行政壟斷背后的政治邏輯也帶有社會屬性,公部門受到國家規制更多,而國家規制意在穩定社會秩序、增強社會融合、防止社會斷裂,所以公部門的職業階層間收入差距較小,變動較慢,而較少受到國家規制的部門(新興市場部門)內部收入差距大,變動快。④劉精明:《市場化與國家規制——轉型期城鎮勞動力市場中的收入分配》,《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在經驗層面的表現是,行政壟斷部門、體制內單位、大型企業相較于競爭性市場部門、體制外單位、中小企業,其員工的收入水平、工作穩定性、福利待遇、享受公共服務的水平等都有明顯優勢。⑤陳斌開、曹文舉:《從機會均等到結果平等:中國收入分配現狀與出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年第6期;郝大海、李路路:《區域差異改革中的國家壟斷與收入不平等——基于2003年全國綜合社會調查資料》,《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制度不僅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了文化、觀念等非正式制度,無論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制”觀念,還是傳統文化中有關權威、等級的理念,都會持續對組織的分配與福利實踐產生影響。例如,法蘭西斯對于北京高科技行業的研究發現,社會與組織文化在這些企業也得到了復制與再生產,使得高科技企業在企業福利分配等方面與傳統單位制的組織有很多相似性。⑥Corinna-Barbara Francis,“Reproduction of Danwei Institutional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The Case of Haidian District’s Hi-tech sector,”The China Quarterly,no.147(September 1996),pp.839-859韓亦和鄭恩營分析了組織印記對企業福利實踐的影響,發現創建時期“企業辦社會”的傳統,深刻影響了國有企業在當下的福利實踐。⑦韓亦、鄭恩營:《組織印記與中國國有企業的福利實踐》,《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3期。中國傳統倫理下的等級與權威觀念則被用于解釋組織內的性別分層和職務職級分層。有研究發現,性別收入差異主要根源不是雇主歧視,而是文化偏見。①程誠、王奕軒、姚遠:《職場投入的性別不平等及其影響——兼論“出差”的收入效應》,《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1期。夏冰青也用“權威崇拜”的文化來解釋互聯網企業中的高管特權與組織分層現象。②夏冰青:《依碼為夢:中國互聯網從業者生產實踐調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107—110頁。
(二)制度變遷與回應外部沖擊
制度慣性固然會帶來組織惰性,但當組織面對制度變遷所帶來的外部沖擊時,也會形成適應性和變革性的力量,并由此對組織內的資源分配產生影響。制度主義者認為組織行為邏輯是為了適應制度環境,因此組織的結構和實踐不能有悖于外界認可的形式或做法,③李路路、朱斌:《效率邏輯還是合法性邏輯?——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私營企業中擴散的社會學解釋》,《社會學評論》2014年第2期。這一應對制度變遷的組織邏輯可以解釋許多組織分層的現象。例如,為了更好地進行制度性適應,中國的公有制部門(如政府、事業單位等)才出現了規模日益龐大的編制外人員隊伍,派遣工、臨時工規模的急速擴張,勞動用工體制的不穩定化加劇,都與基層治理的制度性約束和需求密不可分。④呂德文:《“混合型”科層組織的運作機制——臨時工現象的制度解釋》,《開放時代》2019年第6期;葉靜:《地方軟財政支出與基層治理——以編外人員擴張為例》,《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1期。而隨著近年來保障勞動者權益的相關法律法規與社會政策的出臺,公部門會面臨合法性壓力,從而有助于這一部門的從業者穩定化,私部門則面臨合法性和經濟性的雙重壓力,所以部門內部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程度也有所增強。⑤朱斌:《穩定化與結構化——新制度主義視角下的中國勞動力市場變化(2006-2017)》,《社會學研究》2022年第2期。
為了回應外部要求或壓力,組織架構會相應調整,強化或建立工會、職代會等次組織機構,這些機構會改變企業注意力的分配,從而影響企業資源向不同類型員工的傾斜,形成組織分層機制。比如,對于中國企業工會的量化研究仍然在討論建有工會的企業其工資與福利標準是否更高,⑥魏下海、董志強、金釗:《工會改善了企業雇傭期限結構嗎?——來自全國民營企業抽樣調查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朱斌、王修曉:《制度環境、工會建設與私營企業員工待遇》,《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年第6期;Yang Yao and Ninghua Zhong,“Unions and Workers’Welfare in Chinese Firm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vol.31,no.3(July 2013),pp.633-667.企業工會是否對于某些行業或職業群體會起到更大的福利提升作用(如勞務派遣工等),⑦黃偉、陳釗、陳耀波:《勞務派遣工工會:來自企業外的獨立力量及其維權效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3期;李明、徐建煒:《誰從中國工會會員身份中獲益?》,《經濟研究》2014年第5期;紀雯雯、賴德勝:《工會能夠維護流動人口勞動權益嗎?》,《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魏下海、董志強、黃玖立:《工會是否改善勞動收入份額?——理論分析與來自中國民營企業的經驗證據》,《經濟研究》2013年第8期。有工會的企業是更傾向于平均主義的分配還是機遇的差異化供給。⑧黃巖、劉劍:《激活“稻草人”:東莞裕元罷工中的工會轉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還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張力與協作。企業的現代化轉型,就是在充斥著非正式制度的組織中引入正式制度,企業的分配模式也會因此發生變化,⑨何軒、陳文婷、李新春:《賦予股權還是泛家族化——家族企業職業經理人治理的實證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08年第5期。次組織層次的機構,如工會等的工作方式和效能也會受到影響。例如,研究者發現,工會維權和提高工資的能力會被企業主的政治關聯所削弱;①楊繼東、楊其靜:《工會、政治關聯與工資決定——基于中國企業調查數據的分析》,《世界經濟文匯》2013年第2期。趙德余發現,即便有了正式制度,非正式的互惠機制、信任關系、非正式溝通仍然是工會成功介入企業職工工資決定機制并產生預期效果的重要條件。②趙德余:《工會組織在職工工資決定中的影響與作用:來自上海的經驗》,《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3期。
四、分析、挑戰與展望:找回“組織”
在前文中,作者對于近年來關于中國組織分層的研究做了簡要綜述,可以看到,研究者對于組織作為形塑中國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力量已達成了廣泛共識。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組織類型、組織形態、組織架構、組織間或組織內關系所發生的變化及后果。但目前,對于組織變化與社會經濟后果之間關聯性和因果性的分析還不夠充分,這也使得對組織如何形成社會不平等缺乏足夠深入的研究。作者將結合組織不平等研究方面的一些前沿文獻,指出中國組織分層研究可以推進和發展的幾個方面。
在海外社會學者對于組織分層的研究中,結合組織分析和分層理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組織分析的核心要素就是把組織看作是一個有著內外部動力機制的有機體,而不是一個內部高度同質化的、鐵板一塊的整體。組織分析者特別關注組織內外群體間關系的流變和多元力量的角逐,并認為這種關系與力量影響了組織如何分配機遇和資源,從而形成或改變了既有的分層結果。③Kevin Stainback,Donald Tomaskovic-Devey,and Sheryl Skaggs,“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to Inequality:Inertia,Relative Power,and Environments,”Annual Reviewof Sociology,vol.36(August 2010),pp.225-247.例如,道賓等人的研究指出,美國近三十余年強調員工多元化構成的人事制度改革實踐確實降低了工作場所的種族隔離與族群間機遇不平等,他們的研究提供了組織如何應對宏觀制度變遷并重塑組織分層動力機制的重要案例。④Frank Dobbin,Daniel Schrage,and Alexandra Kalev,“Rage against the Iron Cage:The Varied Effects of Bureaucratic Personnel Reforms on Divers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0,no.5(October 2015),pp.1014-1044.一項采用三萬七千余起商業并購案例的研究也發現,并購沖擊了組織惰性,改善了少數族裔和女性在管理層中的代表性,由此降低了工作場所的種族與性別隔離。⑤Letian Zhang,“Shaking Things Up:Distruptive Events and Inequal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27,no.2(September 2021),pp.376-440.還有一些研究分析了美國企業高管薪酬猛增現象背后的制度變遷、社會網絡與文化因素,認為兼并、去工會化、大企業間連鎖董事網絡的擴散都導致了股東價值最大化和管理主義意識形態(managerialism)的共進蔓延,并促發了高管之間的攀比,最終促成了管理崗位增加和管理層薪酬大幅提升。⑥Adam Goldstein,“Revenge of the Managers:Labor Cost-Cutting and the Paradoxical Resurgence of Managerialism in the Shareholder Value Era,1984 to 2001,”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7,no.2(April 2012),pp.268-294;Gopal V.Krishnan,K.K.Raman,Ke Yang,and Wei Yu,“CFO/CEO-Board Social Ties,Sarbanes-Oxley,and the Earnings Management,”Accounting Horizons,vol.25,no.3(September 2011),pp.537-557.
從組織內部的微觀機制來看,前沿研究聚焦于組織內部不同力量的沖突與爭斗對于不平等的影響,考察在工作場所權力如何起作用,又受到哪些因素的約制。①Kevin Stainback,Donald Tomaskovic-Devey,and Sheryl Skaggs,“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to Inequality:Inertia,Relative Power,and Environment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August 2010),pp.225-247;Amanda Barrett Cox,“Powered Down:The Micro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Attempts to Redistribute Pow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27,no.2(September 2021),pp.285-336.研究往往聚焦某些具體的因素或變量,對權力機制與互動模式進行細致的呈現和分析。例如,研究組織內性別或族群不平等的學者發現,在女性高管占比更高的公司,女性或少數族裔在晉升機遇、工作穩定性方面的劣勢相對更少,而這與高管群體的“同類群體”寬容(in-group tolerance)有顯著關聯。②Mark Egan,Gregor Matvos and Amit Seru,“When Harry Fired Sally:The Double Standard in Punishing Misconduc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30,no.5(October 2022),pp.1184-1248.關注社會網絡的研究則發現,管理層之間的社會網絡,會影響下屬職工的績效表現與資源獲取。③Emilio J.Castilla,“Bringing Managers Back In:Managerial Influences on Workplace Inequal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6,no.5(October 2011),pp.667-694.
反觀中國組織分層研究,仍然較少借鑒組織研究與組織分析的視角,更多傾向于將組織看作是一個同質化的整體,對組織內外部不同利益相關者互動機制的探索略顯不足,由此引發了對超越再分配-市場二元機制的理論突破不足,以及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關注不足。下面將針對這三方面的不足做一些闡述,并指出目前業已涌現出一些在視角和方法上有突破性的研究嘗試,試圖在社會不平等研究中找回“組織”因素,進一步推進組織分層研究與理論發展。
第一,對組織內外部不同利益相關者互動機制的探索不足。組織分層研究者較少關注組織間和組織內關系對員工境遇的影響,傾向于對組織作用進行化約,忽略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動與角力。周雪光等認為,國內社會學者對于組織的研究容易忽視非市場機制(如社會關系)、組織環境、組織文化等在組織轉型中的作用,沒有把組織看作一個有著獨特邏輯的實體。④周雪光、趙偉:《英文文獻中的中國組織現象研究》,《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6期。
沒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組織”運行的邏輯與機制,這使得中國組織分層研究容易與理論根基深厚的“組織研究”及“制度研究”漸行漸遠,而只是成為市場轉型背景下社會分層研究的一條支脈。這也使得組織分層研究在理論發展上受到分層研究所設定的命題之局限,容易看到中國組織變革之特殊性,但較難嵌入在一個更具普遍性的理論背景下考察中國的組織現象,也很少選擇多元研究方法去回應組織變革的根本性問題。
近年來,有一些研究者已經開始討論中國式組織的動力機制及其社會分層后果,例如石磊等討論了組織內部勞動力市場如何發揮作用,組織招聘/遴選/晉升標準如何確定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⑤石磊、李路路、趙忠:《內部晉升還是外部聘任?——組織規模與企業補缺路徑的選擇》,《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3期。朱妍考察了組織內非正式制度(社會關系)與正式制度(內部勞動力市場制度設置)在分配生活機遇上的替代性關系;⑥朱妍:《組織忠誠的社會基礎:勞動關系“嵌入性”及其作用條件》,《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2期。馬冬玲與其合作者考察了組織領導團隊的性別構成對性別歧視的影響;⑦馬冬玲、周旅軍:《女領導的臨界規模與組織性別歧視現象——基于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社會》2014年第5期;馬冬玲、周旅軍:《組織中的“蜂后”:事實還是想象?——基于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社會學評論》2018年第5期。經濟史學者研究了指令性計劃經濟時期工廠分配生活機遇的機制,發現企業內部黨政領導權力關系的變化會影響工農家庭出身的職工獲得就業和晉升的機會,解釋了不同出身職工的境遇在不同時期的變化,由此凸顯了資源分配背后的政治與制度機制。①林盼:《紅與專的張力:1949—1965年工人內部提拔技術干部的實踐與問題》,《學海》2015年第3期;林盼:《制度變遷、利益沖突與國營企業技術精英地位獲得(1949—1965)》,《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2期。此外還有在之前章節中提到的對次組織層次機構的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如何進一步擴展與深入下去,并與分層研究結合進而形成對中國組織分層機制的分析和理解,還有待研究者的努力和探索。
第二,對超越再分配—市場二元機制的理論突破不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研究者開始關注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轉型及其社會分層后果,討論再分配機制與市場機制在影響民眾收入、福利和生活機遇上的角力。組織分層這一領域也受到“市場轉型論”的極大影響,關于傳統“單位制”和新型“單位制”之分配作用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嵌入在“再分配—市場之爭”中。
再分配機制與市場機制的二元論,其背后的理論假設是政治邏輯與效率邏輯的對立,即認為再分配體現了政治邏輯,與市場機制背后的效率邏輯截然不同,甚至呈此消彼長的狀態。更進一步來講,這種二元對立的理論預設反映了不同的研究者如何看待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層中的政治因素與國家角色。②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no.5(October 1989),pp.663-681;Victor Nee,“The Emergence of Market Society:Changing Mechanism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no.4(January 1996),pp.908-949;Minxin Pei,From Reformto Revolution:The Demiseof Communism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3.許多研究者認為,國家以更隱晦和更有效的方式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與分配中,指出要理解中國轉型的社會經濟后果,就要重新認識中國的國家角色。③Marc Blecher and Vivienne Shue,Tethered Deer: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05;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94-96.周雪光在一篇研究綜述中就指出,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政治分配機制和市場制度機制本身就體現了國家權力的兩重性,而這種兩重性如何發生歷時性變化,這都是涉及組織制度變遷的根本性問題,目前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和回應。④周雪光:《西方社會學關于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狀況述評》,《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4期。劉精明也曾指出,在改革時期的中國,再分配權力與市場權力這兩個因素應被理解成一種混合體,它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結合,并形塑著社會的分層機制,而不能看作是非此即彼、壁壘分明的兩種路徑。⑤劉精明:《市場化與國家規制——轉型期城鎮勞動力市場中的收入分配》,《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但不少組織分層的經驗研究仍傾向于將市場邏輯與政治邏輯對立,或將其看作連續統的兩端,根據自己的偏好或研究的便利各執一端進行討論,并沒有考慮兩者通過各種方式結合成混合體的狀態。另外,中國的企業組織除了經濟性和行政性特征之外,還有社會性特征,從指令性計劃經濟時期的“企業辦社會”,到目前“類社區化”的企業組織,⑥Yi Hubert Han and Jingjing Yao,“Building Organizations as Communities:A Multicase Study of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Logic at Chinese Firms,”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April 2022),pp.1-30.都促使研究者追問,中國式組織(主要是企業組織)的架構、運行、管理與資源分配,究竟依據哪些邏輯,這些邏輯之間存在哪些組合關系。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摒棄簡單化的二元思維,進行類型學上的辨析與理論創新。
第三,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關注不足。組織分層研究對于不同類型組織的注意力分配十分不平衡,大部分研究仍然聚焦于城鎮組織,考察不同規模、不同所有制類型組織成員的生活機遇分化;當考察組織內分層,或是次組織機構對于分層的影響時,更多聚焦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對于其他類型的企業(如混合所有制企業、跨國公司等)研究不足。
除此之外,組織分層的研究對于農村生產性組織的關注度很低,有政治學和社會學者聚焦了農村民眾的財富分化及動力機制,但這些研究在組織分層研究中尚沒有收到足夠的回響。研究者對于非企業組織的關注也遠遠不夠,雖然有大量的國內學者關注基層政府行為,但對于這些基層組織會帶來什么樣的社會分配后果則幾乎沒有研究,包括對于公部門使用編外人員的研究也多討論其制度基礎,而不討論社會經濟后果。
近年來,隨著新技術的出現,涌現出了各種新型組織與雇傭形態,如平臺企業、零工經濟、創意階層聯合體等組織,對于這些新型組織及其社會后果仍然需要大量深入的研究,討論分層機制會不會隨著技術變遷而出現變化。這些組織往往以科技企業自詡,將去科層化、扁平化和平等主義作為自己的標簽,但事實是否如此?目前一些研究顯示,基于互聯網等技術而出現的新型組織在薪酬、福利和職業發展機遇方面都存在顯著的內部分層,而且由于生產過程的非正式性、自主性和靈活性等特點,內部分層被進一步固化了,與科技企業的初心漸行背離,更像一個傳統的科層制組織,等級森嚴。①夏冰青:《依碼為夢:中國互聯網從業者生產實踐調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84—87頁。但也有研究發現,科技企業的特征也能幫助雇員避免一些工作場所的歧視性實踐,使得少數族裔、女性群體利用規則獲得一些抵制性的力量。②Johanna Shih,“Circumventing Discrimination:Gender and Ethnic Strategies in Silicon Valley,”Gender and Society,vol.20,no.2(April 2006),pp.177-206.此類研究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新型組織現象及不平等后果。
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呼喚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周雪光和趙偉曾在一篇綜述中指出,中國的組織與組織分層相關研究因缺乏細致深入的個案研究而難以提供對微觀機制的系統理解,他因此呼吁理論貢獻要建立在對實際變化過程、社會制度與歷史背景的貼切把握之上,避免進行現成的、流行的概念和模式與經驗資料的拼湊。③周雪光、趙偉:《英文文獻中的中國組織現象研究》,《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6期。研究性別不平等的學者也指出,目前對于不同性質、類型組織中性別歧視的比較研究仍然罕見,對于組織特征如何影響組織內的性別分層,研究者還知之甚少。④李樂旋、馬冬玲:《組織中的性別歧視:國外研究綜述及展望》,《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要了解中國組織分層的機制,必須要深入到組織行為發生的場域中,了解與分析組織行為的邏輯及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影響。
只有深入細致的案例分析,才能為設計指標、收集和分析數據打下堅實的研究基礎。目前很多量化研究在測量組織分層的因變量時,仍聚焦于收入、社會保障覆蓋情況等指標,很多隱匿的福利無法被捕捉到。從組織分層的解釋變量或中介變量來看,測量指標的精確化有待提升。
組織分層研究還要增加縱向與橫向比較的視野,特別是要從歷史(主要是計劃經濟時期)組織現象中汲取給養。研究經濟史、企業史的學者對于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初期的企業分配模式已有大量研究,無論是關于工人群體內部分化,①劉亞娟:《上海“阿飛”:滾動的話語邏輯與基層實踐走向(1949—1965)》,《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5期。企業在提拔干部時對專業性的考慮,②林盼:《紅與專的張力:1949—1965年工人內部提拔技術干部的實踐與問題》,《學海》2015年第3期;林盼:《制度變遷、利益沖突與國營企業技術精英地位獲得(1949—1965)》,《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2期。還是農村經濟性組織的勞動力配置與工分分配,③董筱丹:《一個村莊的奮斗:1965—202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07—109頁;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64—276頁。歷史學者都貢獻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資料分析與類型呈現,有助于我們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制度演進與變遷。同時,組織分層還要多多借鑒海外組織研究,在比較的棱鏡中更好地了解中國組織分層機制與模式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本文聚焦于近年來中國組織間與組織內社會分層的經驗研究,呈現組織因素影響資源與機遇分配的社會經濟后果,并從制度延續與制度變遷的視角對組織作用進行分析與解釋。既有研究一方面極大提升了學界對于中國社會不平等之組織根源的理解,對社會分層與流動、轉型經濟社會分析、勞工社會學等分支領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另一方面也存在不足之處,即更多將組織看作鐵板一塊的實體,較少呈現組織內外的多元動力機制,對于組織研究與組織分析的思路、視角、方法與結論的借鑒較不充分。要進一步開拓當代中國的組織分層研究,需要研究和整合對中國各類組織本身的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要對中國的各種組織類型、組織形態、組織架構、組織間或組織內關系等進行細致而深入的(比較)案例分析、過程追蹤、歷史制度分析,同時通過結構化的問卷調查來系統地收集組織層次與組織—個體匹配的數據,采取質性與量化相結合的混合研究路徑,倡導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理論視角上,要避免再分配機制與市場機制二元對立的簡單預設,對于中國各類組織的資源分配邏輯及其變化保持理論上的開放,把組織放置于不同的制度情境中,理解政治、市場、社會等多種力量如何在組織分層中發揮作用,不同的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在哪些領域會相互抵消、強化或是制約,由此為組織分層提供新的類型化理論邏輯。這將幫助當代中國組織分層研究突破當前所設定的命題,回應組織變革的根本問題,參與到更前沿的理論對話中,修正和拓展理論,使這一領域煥發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