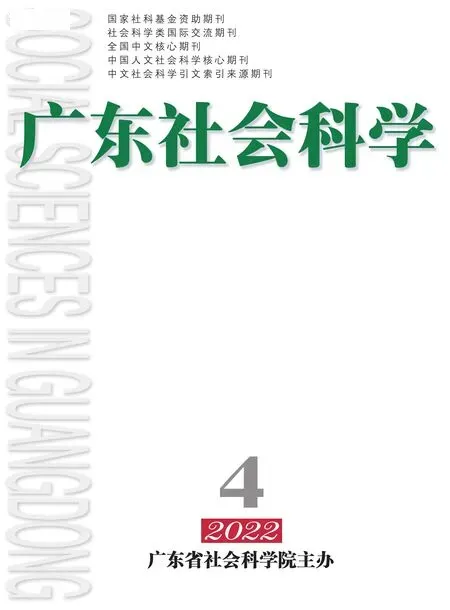股權轉讓合同對民法典的參照適用*
王 雷
股權轉讓合同是引發公司股權變動的重要法律事實,股權轉讓合同是《公司法》中的典型合同,屬于《公司法》第1條所指公司行為的具體類型之一,也是商法上的營利性商事合同,是我們觀察民法商法關系的一個重要窗口。股權轉讓糾紛還是“與公司有關的糾紛”的重要案由。
我國《民法典》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圍繞民法商法的適用關系,通說觀點認為:“在出現商事糾紛后,首先應當適用商事特別法,如果無法適用商事特別法,則適用《民法典》的規則。”①王利明主編:《民法》(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8頁。“我國堅持民商合一主義,民法規則統一適用于所有的民商事關系,并不存在單獨的商法典。《民法典》不僅適用于民事關系,而且適用于商事關系。商事活動的特殊性,由《公司法》等單行法體現。”②李永軍主編:《中國民法學》(第一卷總則),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第11頁。《公司法》對股權轉讓合同所配置的特別法律規范無法自足自洽,《民法典》的有關規定如何“適用”于股權轉讓合同糾紛?值得研究。
一、公司糾紛等商法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民法典總則編司法解釋》”)第1條第2款和第3款分別規定:“就同一民事關系,其他民事法律的規定屬于對民法典相應規定的細化的,應當適用該民事法律的規定。民法典規定適用其他法律的,適用該法律的規定。”“民法典及其他法律對民事關系沒有具體規定的,可以遵循民法典關于基本原則的規定。”從法律適用方法角度,無論是《民法典》還是《民法典總則編司法解釋》都未明確針對商事糾紛,商法沒有特別規定或者細化規定時,《民法典》處于何種適用地位。
商事糾紛優先適用商事特別法,當商事特別法沒有規定時,民事一般法并非處于簡單補充適用的地位。簡單補充適用民事一般法有可能忽視商事關系的特殊性質。公司糾紛等商法領域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方法表現出補充適用、類推適用、參照適用等多元法律適用方法和漏洞填補方法。
(一)商行為的類推適用和參照適用問題概述
民商事司法實踐中的類推適用十分豐富,但商法理論對商行為的研究卻很薄弱。①參見郭富青:《論商法類推適用的依據、范圍和正當性》,《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第37頁。參照適用是法定類推適用、授權式類推適用,股權轉讓合同等商行為具有營利性營業特點,以有償性為必要,天然存在參照適用買賣合同規定的可能。原《合同法》第174條、《民法典》第646條自然擴展了商法的法源,商行為有參照適用買賣合同有關規定的廣泛空間。又如,《公司法》對公司董事以公司名義實施的法律行為缺乏規范,應以類推適用的方法適用民法總則的規定,以填補該漏洞。②參見錢玉林:《民法總則與公司法的適用關系論》,《法學研究》2018年第3期,第51頁。
原《合同法》第52條第(五)項、《民法典》第153條第1款是公法進入私法的“管道”。原《合同法》第174條、《民法典》第646條、《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2條是作為一般法的民法在買賣合同制度中給商事特別法中的商行為留存的回歸“接口”,它們都屬于參照適用條款。
不同于補充適用,參照適用方法在充分尊重差異基礎上努力求同存異,同其所同、異其所異,既敬其所異又重其所同。有必要仔細考察股權轉讓合同在股權變動和合同履行環節上參照適用《民法典》物權編和合同編的可能。
(二)董事職務解除糾紛可以補充適用委托合同的有關規定
原《合同法》第410條規定委托合同當事人的隨時解除權,《民法典》第933條規定在委托合同當事人隨時解除權基礎上,進一步區分規定有償委托合同和無償委托合同中隨時解除對應的賠償責任。公司與董事之間存在委托關系,依股東會的選任決議和董事同意任職而成立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既然為委托合同,則合同雙方均有任意解除權,即公司可以隨時解除董事職務,無論任期是否屆滿,董事也可以隨時辭職。董事職務無因解除,只要公司解聘董事的決議有效,不需要考察解除的具體原因,也不取決于董事和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合同或者聘任合同,這實際上是類推適用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權規則。無因解除不能損害董事的合法權益。公司解除董事職務應合理補償,以保護董事的合法權益,平衡雙方利益,防止公司無故任意解除董事職務。從本質上說,離職補償是董事與公司的一種自我交易,其有效的核心要件應當是公平,所以強調給付的是合理補償。
我國《合同法》和《民法典》中明確規定了委托人因解除合同給受托人造成損失的,除不可歸責于該當事人的事由以外,應當賠償損失。《公司法司法解釋五》第3條第2款對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時的自由裁量權行使進行了相應指引。對《公司法司法解釋五》第3條第1款作反面解釋,董事任期屆滿前被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效力存在瑕疵的決議解除職務,其主張解除不發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人民法院在公司無因解除董事職務問題上,不做實質審查,不看決議中解除的理由或者原因,只做決議程序審查形式審查。解除的理由或者原因是對董事進行離職補償時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司法司法解釋五》第3條第2款對董事職務解除后的補償問題,實質上是《民法典》第933條有償委托合同的解除方違約損害賠償規則的具體化,《民法典》第933條在董事職務解除后的補償糾紛中處于補充適用地位。即便董事和公司之間存在勞動合同關系,當公司無因解除董事職務時,也不能簡單適用《勞動合同法》第46條經濟補償規則,不能混淆董事職務解除和勞動合同關系解除。
(三)公司法中的類推適用與參照適用問題概述
還有法院指出:“公司股東僅存在單筆轉移公司資金的行為,尚不足以否認公司獨立人格的,不應依據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判決公司股東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但該行為客觀上轉移并減少了公司資產,降低了公司的償債能力,根據‘舉重以明輕’的原則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十四條關于股東抽逃出資情況下的責任形態之規定,可判決公司股東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在其轉移資金的金額及相應利息范圍內承擔補充賠償責任。”①參見“海南碧桂園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三亞凱利投資有限公司、張偉男等確認合同效力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21年第2期,第1—35頁。該案例中的裁判方法并非參照適用,而是類推適用,針對公司股東單筆轉移公司資金的行為,類推適用《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4條關于抽逃出資股東補充賠償責任規則。
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判斷,可以補充適用《民法典》總則編第六章第三節規定。例如,股權轉讓合同的出讓人被羈押于看守所,懼于受讓人借助公權力對其不當刑事追責,被迫同意簽訂股權轉讓合同以求恢復人身自由,股權轉讓合同因出讓人受脅迫簽訂,出讓人有權根據《民法典》第150條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②參見“陳家榮、范天銘與許榮華股權轉讓糾紛”,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蘇民終1388號民事判決書。針對股權轉讓合同,補充適用《民法典》不能包打天下,股權變動模式、股權轉讓合同履行等問題上,要充分重視股權轉讓合同的特殊性。
從股權轉讓合同的法律適用上,我們可以發現,商事特別法沒有規定時,并非一概簡單補充適用民事一般法,而是要注意結合商事交易的固有本質,參照適用最相類似的買賣合同等相關規定。從宏觀上看,民法和商法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但在具體法律適用過程中,參照適用而非補充適用才是妥善處理民商關系的常態適用方法。還要特別注意股權轉讓合同當事人法定注意義務和約定注意義務,特別是前者對應提出的當事人的盡職調查范圍和程度。
以下著重就股權轉讓合同的法律適用方法進行分析,尤其是探討股權轉讓合同對民法典物權編和合同編有關規定的法律適用方法。
二、基于股權轉讓合同的股權變動模式
股權轉讓合同是引發股權變動的最重要最常見法律事實。股權變動的判斷標準復雜多樣,爭議頗多,現行法上至少包括股權轉讓合同、出資證明書記載、股東名冊記載、公司章程記載、公司登記機關登記事項記載,哪些標準是充分條件?哪些是必要條件?哪些是充分必要條件?基于股權轉讓合同的股權變動模式不能參照適用不動產物權變動模式的有關規定。
股權可以通過出資取得或者通過交易轉讓繼受取得。《公司法》第32條第2款和第3款分別規定股東名冊記載和公司登記記載的不同效力。通過出資取得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其股權設立采取對內修正的意思主義(以記載于股東名冊為必要)和對外登記對抗主義(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鑒于有限責任公司的封閉性和股東間的人身信任關系,我國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變動采取修正的意思主義模式。從交易法的視角看,在轉讓人和受讓人之間,采取債權意思主義的股權變動模式。從組織法的視角看,股權變動的事實需要通知公司且取得認可為必要。從外部第三人的視角看,股權變動的對抗要件是股權工商變更登記。其他股東優先購買權行使與否的意思表示,影響的是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而非股權變動的效果。股權變動發生后,受讓人基于新股東身份有權請求公司簽發出資證明書、變更股東名冊記載、變更公司章程記載以及變更工商登記。①參見李建偉:《公司法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42—243頁。
如學者所言,參考物權變動模式來論證股權變動模式的思路值得懷疑。②參見張雙根:《論股權讓與的意思主義構成》,《中外法學》2019年第6期,第1552—1577頁。與不動產物權變動模式不同,債權形式主義的股權變動模式未被實定法采納。根據《公司法》第73條和《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3條等,對基于股權轉讓合同的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變動而言,嚴格的形式主義或者意思主義均不合適,前者明確未被我國《公司法》采納,后者則忽視了使公司知曉受讓人受讓股權事實之必要。為此,“修正意思主義股權變動模式”認為股權變動的發生在最低限度須有股權轉讓合同(初始取得時對應股東之間投資設立公司的協議)加出讓人通知,這就兼顧了受讓股東和公司的利益。③參見李建偉:《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變動模式研究——以公司受通知與認可的程序構建為中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2期,第18—29頁。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完全依賴于出讓人的通知,若出讓人怠于通知,僅憑股權轉讓合同,無法給公司信賴受讓人為股東的外觀,應該課加給出讓人交付出資證明書的義務,受讓人持有出資證明書和股權轉讓合同,即可認定其為新股東,公司對此可以形成合理信賴。④參見林斯韋:《股權轉讓準用買賣合同規范》,碩士學位論文,中國政法大學,2019年,第36—38頁。受讓人作為新股東有權依據《公司法》第73條要求公司向自己簽發出資證明書、修改公司章程和股東名冊、辦理公司登記機關登記。
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變動采取債權形式主義。根據《公司法》第139條第1款,記名股票背書轉讓,背書一經完成,股權即發生變動。根據《公司法》第140條,無記名股票的轉讓,股票一經交付,股權即發生變動。簿記式記名股票轉讓無法背書,而是表現為證券交易所電腦系統中股東賬戶電子信息變化。
三、股權轉讓合同的特殊性
股權轉讓合同屬于《公司法》中典型的商行為,在股權轉讓合同的法律適用方法上,民法的地位遠非補充適用可以簡單概括的。股權轉讓合同與買賣合同最相類似但絕非等同,在有償性問題上,可以同其所同;在股權轉讓合同特殊性問題上,需要異其所異。
(一)法律或者公司章程對股權(份)轉讓的特別限制
國有資產(包括國有股權)的轉讓,應當嚴格按照《企業國有資產法》第47條、53條、53條等規定的程序進行。企業未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機構中公開進行國有產權轉讓,而是進行場外交易,其交易行為違反公開、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則,損害公共利益,應依法認定無效。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應當進場交易的目的,在于通過嚴格規范的程序保證交易公開、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避免損害國家利益。
類似地,《公司法》第138條規定:“股東轉讓其股份,應當在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場所進行或者按照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方式進行。”但該規定不能否定受讓人通過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取得股份的權利,也不影響當事人之間《股份轉讓合同》的效力。《股份轉讓合同》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受讓人已按協議完成了支付股權轉讓款的義務,故《股份轉讓合同》應認定為有效。①參見“荊紀國與陳黎明、湖南大康國際農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湘民初45號民事判決書,本案為2018年湖南省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受《民法典》的調整;股權轉讓合同的履行受《民法典》和《公司法》特別規定的共同調整。”②錢玉林:《股權轉讓行為的屬性及其規范》,《中國法學》2021年第1期,第210頁。《公司法》第71條和第72條是股權轉讓合同的特別法,以維護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特點。《公司法》第71條第4款規定:“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公司董事違反公司章程規定內部轉讓股權的,未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轉讓股權協議并不當然認定無效;股權轉讓款項的來源并不影響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③參見“徐德海訴楊春妹股權轉讓糾紛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終2997號。當然,《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9條,有些股東權利如股東依據《公司法》第33條、第97條享有的查閱或者復制公司文件材料的權利不能被公司章程或者股東間的協議“實質性剝奪”。
根據《公司法》第71條第1、2、3款,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向非股東轉讓股權的,需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且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經過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是股權轉讓合同得以順利履行的程序性條件。有限責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點,股東之間具有一定的信任與合作基礎,其他股東的優先購買權可以維持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關系的穩定性,同時又保障了股東退出的自由。最終未能取得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的,轉讓人須向受讓人承擔股權轉讓合同的違約責任,但不影響股權轉讓合同本身的法律效力。④有學者建議:“為避免在適用法上的分歧,修訂《公司法》時可以明示《公司法》第71條僅在規范股權轉讓合同的履行和股權轉讓人違約責任的立法意旨。”錢玉林:《股權轉讓行為的屬性及其規范》,第225頁。如果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作出特殊規定的,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
有限公司股權轉讓情形下,其他股東的同意權和優先購買權,是為了維護有限公司封閉性和股東間人身信任關系。《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16-22條分別對股東優先購買權中的“轉讓”、“通知”、“同等條件”、猶豫期、出讓股東的反悔權、優先購買權受侵害時的救濟進行細化規定。《民法典》第726-728條規定了房屋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立法未盡事宜,可參照適用《民法典物權編司法解釋一》第9-13條按份共有人優先購買權規則、《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16-22條股東優先購買權規則。
《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18條是對其他股東優先購買權之“同等條件”的界定,在《公司法司法解釋四》司法解釋施行前,實踐中可以類推適用《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10條。《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18條在《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10條基礎上又提供了新的考量因素——“轉讓股權的數量”,對按份共有人優先購買權的“同等條件”判斷反過來可以類推適用《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18條。
《公司法》第141條第1款對發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特定時間內不得轉讓的規定,以防止發起人的投機、欺詐行為,保護公眾投資者的利益。第141條第2款對公司管理層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轉讓做了限制規定。《證券法》第44條第1款歸入權制度能夠限制上市公司中特殊主體的股份轉讓,第40條和第42條規定對中介機構及其人員的股份買賣限制。法律對股份轉讓的限制,限制了股東對股權的處分權,股東違反相關法定限制轉讓股權構成無權處分,但此時不能參照適用《民法典》第597條第2款,在民法上,受讓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法律對交易的限制規定,鑒于股份的外觀主義特點,股東無權處分轉讓股權不會導致轉讓協議無效,而是通過適用或者類推適用歸入權制度,以兼顧交易安全和公司權益保護。
(二)股權轉讓合同不同于買賣合同的特殊規則
在股權轉讓糾紛案件中,受讓人已實際作為股東身份參與了目標公司的經營管理,并領取了該公司的分紅,轉讓人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返還購股款,原則上不能被支持,這是股權轉讓合同營利性營業特點的體現。
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的出讓人和知情的受讓人對出資不足承擔連帶責任。公司基本法律制度的三個面向是獨立人格、獨立財產和獨立責任。無論是認繳制還是實繳制,公司財產均包含公司注冊資本在內;認繳制下,公司股東雖然享有出資期限利益,但當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認繳出資的股東應向公司履行出資義務;并且,該出資義務被觸發后不因股權轉讓而消滅,否則將導致股東向償債能力較差的受讓人轉讓股權、逃避出資義務進而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8條,股東轉讓瑕疵出資股權時,公司或者債權人有權請求股東與受讓人在未出資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③參見“中鐵建業集團有限公司與中鐵建業物流有限公司、江陰市遠大燃料有限公司股東出資糾紛”案,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02民終1516號民事判決書。
股權轉讓合同中,轉讓人要承擔權利瑕疵擔保義務。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6條規定,雖然不知道或者不應當知道出讓股東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之受讓人對出資義務無須承擔連帶責任,但其所受讓股權的利潤分配請求權、新股優先認購權、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股東權利有可能被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作出相應的合理限制,參照適用《民法典》第612條或者補充適用《民法典》第148條,受讓人有權要求出讓人承擔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或者撤銷股權轉讓合同。
股權轉讓合同中,出讓人還可以參照適用《民法典》第616條、第617條規定,承擔物的瑕疵擔保義務。股權除包括股東自益權和共益權之外,還包括對公司的實際控制和支配,股權比例越高,控制和支配的程度就越高。當然,基于公司人格、財產、責任與股東人格、財產、責任的分離,股權轉讓合同參照適用《民法典》第610條“法定質量瑕疵擔保責任”似乎存在一定障礙,但參照適用“約定質量瑕疵擔保責任”無礙。當股權轉讓合同中存在約定瑕疵擔保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參照適用《民法典》第616條,因為結合目的解釋方法,公司債務、資產等因素直接影響股權的價值,出讓人對公司債務、資產等非轉讓股權之標的物的保證,也是對股權價值的保證。相反,如果股權轉讓合同中不存在約定瑕疵擔保的意思表示,哪怕公司負債累累、資不抵債、瀕臨破產,也不能參照適用法定質量瑕疵擔保責任,目標公司的這些財務狀況屬于受讓人盡職調查自行判斷、化解乃至負擔的商業交易風險,除非股權轉讓方違反告知義務未如實向受讓方披露目標公司的潛在風險、客觀經營狀況等。①參見“陳英、西藏鼎瀚創業投資管理中心股權轉讓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6513號民事裁定書。股權轉讓的受讓方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調查,并不因此免除轉讓方的告知義務,但股權轉讓合同中轉讓方的告知義務不能簡單等同于營業轉讓合同中轉讓方的告知義務,“營業轉讓合同與買賣合同相似,應當參照適用有關買賣合同的規定。”②王文勝:《論營業轉讓的界定與規制》,《法學家》2012年第4期,第103頁。股權轉讓合同中轉讓方告知義務程度須與所轉讓股權在公司股權結構中的占比相匹配。
四、股權轉讓合同對分期付款買賣合同規則的參照適用
(一)分期付款股權轉讓合同與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相似性論證
就分期付款買賣中的合同解除,相對比于原《合同法》第167條,《民法典》第634條第1款增加規定“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支付到期價款”這一要件,使得分期付款買賣合同中出賣人的解除權與《民法典》第563條第1款第(三)項法定解除權的構成要件保持一致,避免在法定解除權規則設計上的體系違反。分期付款買賣合同中出賣人的解除權有利于降低出賣人可能承受的價款不能收回風險,這在消費領域合同中尤其普遍。股權轉讓合同不同于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的買賣合同,但二者在有償性問題上具有類似性。根據《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2條,法律或者行政法規對股權轉讓合同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沒有規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民法典》第467條和第646條的規定,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股權轉讓合同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首先引用《民法典》第646條的規定,再引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第67號指導案例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分期付款合同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解除權規則持否定態度,分期付款股權轉讓合同,與一般以消費為目的分期付款買賣合同有較大區別,對前者,不宜簡單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解除權規則。①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第67號指導案例:“湯長龍訴周士海股權轉讓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532號。
參照適用是一種法定類推適用,是一種取向于規范目的的、價值評價式的思考論證過程。經由參照適用/類推適用,本質一致的事物在法律適用上被等量齊觀。“法學上的類推適用無論如何都是一種評價式的思考過程,而非僅形式邏輯的思考操作。法定構成要件中,哪些要素對于法定評價具有重要性,其原因何在,要答復這些問題就必須回歸到該法律規整的目的、基本思想。”②[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58頁。團體法上的合同能否準用交易法的規則,很大程度上須從團體法內部發現該合同的特有性質和目的。從法律評價上重要之點出發,在股權轉讓的轉讓人已經給受讓人完成股東名冊變更和工商登記變更的情況下,受讓人拒付股權轉讓款,出讓人價款不能回收的風險現實化,股權受讓人具有權利外觀,足以使得善意第三人受讓股權,如果不賦予出讓人分期付款解除權,會致利益失衡。③參見林斯韋:《股權轉讓準用買賣合同規范》,第10頁。
二氫吡喃并[2,3-c]吡唑類化合物(圖1)作為一類重要的含氮雜環化合物,可作為細胞周期檢查點激酶1(cell cycle checkpoint kinase 1,Chk1)抑制劑,具有潛在的抗腫瘤活性[8]。2016年,徐麗[9]將4-二甲氨基吡啶(4-dimethylaminopyridine,DMAP)催化合成得到的12個二氫吡喃并[2,3-c]吡唑衍生物對人乳腺癌細胞MCF-7進行了體外抗腫瘤實驗,結果表明具有一定的抑瘤作用。
股權轉讓合同能否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解除權制度?這給《民法典》第646條其他有償合同參照適用買賣合同制度提供了一個具體分析樣本。有學者認為:“于此情形,準用之功能不在于填補法律漏洞,而是提供更為精準的解除規則。”④楊旭:《〈合同法〉第167條對股權買賣之準用——〈指導案例〉67號評釋》,《現代法學》2019年第4期,第197頁。最高人民法院第67號指導案例在論證股權轉讓合同和買賣合同的相似性和特殊性時,未作充分有說服力的論證,導致股權轉讓合同不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解除權制度的結論可接受程度不高。簡單認定股權轉讓合同不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解除權制度,致使出現股權受讓人比消費者買方受到法律更高保護的明顯體系違反現象。股權轉讓合同和買賣合同的相似性(而非同一性)論證須結合被參照適用條款的規范目的、被參照適用條款的調整對象、履行的順序、是否已經發生財產權變動、出賣人是否存在價款回收的風險、分期付款的期數、債的類型、合同目的、交易安全維護展開。股權轉讓合同的特殊性(如基于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所賦予其他股東同意權和優先購買權的行使、股權價值的變動性、受讓人后續的經營管理等)成為不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解除權制度的核心理由,但如果股權轉讓合同的這些特殊性可以通過允許其他股東再次行使同意權和優先購買權、⑤參見吳飛飛:《論股權轉讓合同解除規則的體系不一致缺陷與治愈——指導案例67號組織法裁判規則反思》,《政治與法律》2021年第7期,第131頁。協議解除股權回轉后轉讓人的返還范圍等技術手段予以充分尊重,則允許股權轉讓合同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解除權制度即無障礙。
(二)被參照條款存在法律漏洞時的法律適用方法
即便成功論證分期付款股權轉讓合同與分期付款買賣合同具有相似性,分期付款股權轉讓合同可以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法定解除權規則,若被參照適用的分期付款買賣合同法定解除權規則自身又有漏洞,該如何彌補?此時離不開類推適用方法。有學者認為,從規范體系上看,對比原《合同法》第94條第(三)項,原《合同法》第167條第1款因缺少催告要件而存在漏洞,應通過整體類推的方式予以填補,以形成適用于股權買賣的完整規則。由此還可以充分展現原《合同法》第174條之法定準用的思考方法。①參見楊旭:《〈合同法〉第167條對股權買賣之準用——〈指導案例〉67號評釋》,第196—208頁。
筆者認為,原《合同法》第167條第1款解除權催告要件存在立法缺漏,原《合同法》第227條第1句后段同樣可以作為前述整體類推時被類推規范之一。這也說明作為法定類推適用的參照適用,并不能否定類推適用的存在空間。司法實踐中成熟的類推適用可以被轉化為立法上的參照適用。立法上的參照適用不是對司法裁判中類推適用的終結。當被參照適用條款自身有漏洞時,又離不開類推適用方法的接力,以濟其窮。《民法典》第634條第1款增加了解除權催告要件,彌補了這一法律漏洞。
五、股權轉讓合同對民法典善意取得制度的參照適用
(一)其他物權對所有權善意取得制度的參照適用
《民法典》第311條第3款規定:“當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權的,參照適用前兩款規定。”其他物權善意取得,可參照適用所有權善意取得規則。但《民法典》沒有明確規定股權能否善意取得。“運用商法外觀主義處理股權轉讓、質押和其他處分問題,較之于采用民法實質主義或者較為迂回的善意取得制度更加簡捷、便利和明確。這樣的話,股權善意取得是否有必要就值得討論了。”②施天濤:《商事法律行為初論》,《法律科學》2021年第1期,第109頁。外觀主義不等同于善意取得,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對善意相對人有更多要求。
(二)股權轉讓參照適用所有權善意取得制度時的類型區分和變通調適
圍繞名義股東處分登記于其名下的股權這類問題,《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5條將善意取得制度引入股權交易領域。此外,《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7條規定以不享有處分權的財產出資時的善意取得,第27條規定未向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的原股東處分股權時的善意取得。
股權不同于物權,有限責任公司的名義股東對外轉讓股權,受讓人基于對股權登記外觀的信賴有可能構成善意,但要滿足股權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完成股權變更登記,則須經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方有可能。而股權質押或者其他處分形式對應的善意取得則更容易,因為此時不涉及股東變更,無須遵循《公司法》第71條的強制性規定。因此,不能繞開《公司法》的相關規定,直接參照適用《民法典》物權編善意取得制度。③參見錢玉林:《民法與商法適用關系的方法論詮釋——以〈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4、25條為例》,《法學》2017年第2期,第92—95頁。股權轉讓參照適用善意取得制度時須做必要的變通調適。
參照適用的前提是擬處理案件事實與被參照適用的法律規定構成要件事實之間存在相似性。《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7條規定以不享有處分權的財產出資時對所有權善意取得制度的參照適用,本條類型化不足,導致涵括范圍過寬,也混淆了“參照適用”和“適用”的邊界。對此,應區分三種類型加以討論:第一,如果以出資形式無權處分的對象是動產或者不動產所有權,當然可以涵攝到《民法典》第311條第1款之下,此時屬于適用所有權善意取得制度,而非參照適用。第二,如果以出資形式無權處分的是其他物權,則可以涵攝到《民法典》第311條第3款之下,此時參照適用所有權善意取得制度即可,不屬于法律漏洞。第三,如果以出資形式無權處分的是股權、知識產權等財產權,無法涵攝到《民法典》第311條任何一款,構成法律漏洞,方存在對所有權善意取得制度的參照適用。
名義股東處分登記在其名下股權時,究竟屬于有權處分還是無權處分?若屬于有權處分,則不存在善意取得的前提。筆者認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名義股東對內對外分別通過股東名冊和股權登記展現其股東身份,其對股權的處分屬于有權處分,《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5條涵括了不應該等量齊觀的事實。“我國法律明確規定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推定為股東,既然如此,名義股東的股權處分行為就應被推定為有權處分。”①施天濤:《商事法律行為初論》,第109頁。當然,基于登記錯誤的名義股東處分股權屬于無權處分,可被納入《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5條的調整范圍。
針對《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所謂未向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的原股東處分股權的情形,筆者認為其更類似于“一物二賣”,而非類似于所有權無權處分。從對外關系上看,未辦理變更登記,股權變動未完成,原股東仍是股東,其對股權再處分,屬于“一股二賣”,系有權處分,并非無權處分,也就不存在善意取得的前提。因此,就《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對應的法律后果,參照/類推適用《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7條更為合適。須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法〔2019〕254號《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九民會紀要”)第8條就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變動區分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在對外關系上采取登記對抗主義的股權變動模式。未向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的原股東處分股權時,通過受讓人未辦理股東變更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即可解決,同樣不必類推適用善意取得制度。
結 語
股權轉讓合同是《公司法》中的合同,屬于《公司法》第1條所指公司行為的具體類型之一。股權轉讓合同屬于典型的營利性商事合同,是我們觀察民法商法關系的一個重要窗口。股權轉讓合同有參照適用《民法典》有關規定的必要性,也有因應其自身性質的特殊性。
股權轉讓合同有參照適用瑕疵擔保責任等買賣合同法律規則的可能,但對分期付款買賣合同中的法定解除權,則要慎重參照,以免不合宜的等量齊觀,但也非完全沒有參照適用分期付款買賣合同法定解除權制度的可能。
股權轉讓合同有參照適用所有權善意取得規則的可能,但須作類型細分和必要的變通調適。《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7條、第25條和第27條過于擴大了股權善意取得規則的適用范圍,宜結合股權變動模式特殊性和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作必要的目的性限縮解釋。
法律或者公司章程也會對股權轉讓作特殊限制,使得股權轉讓合同類似于但又有別于買賣合同。
股權轉讓合同關乎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私人利益,即便在股權轉讓合同可以參照適用《民法典》相關規定的情形下,也應允許轉讓方和受讓方自行約定排除可能的參照適用,展現股權轉讓合同當事人的個性需求。股權轉讓合同的法律適用方法和漏洞填補方法展現出民法在商法漏洞填補過程中參照適用求同存異的謙遜態度,而非補充適用的兜底式大包大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