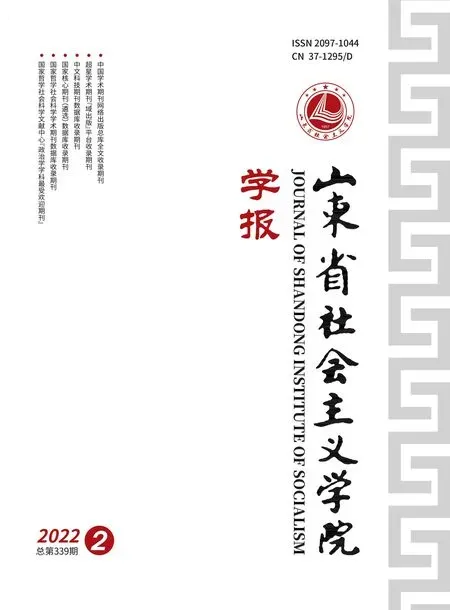儒道互補建構了中國人傳統(tǒng)的信仰世界
張 踐
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突出的標志之一,就是不以宗教文化作為自己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以此與基督教民族、伊斯蘭教民族、印度教民族等相區(qū)分。但是這不等于說中華民族沒有信仰,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多年而從未中斷,如果沒有信仰是不可能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的。正如林語堂《吾國與吾民》所指出的,“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中國的民族生命賴以活動”,可以說“道家及儒家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1]換一種說法,儒家和道家的互補建構了中國人傳統(tǒng)的精神世界,是中華民族文化信仰的底色,其作用相當于其他各種世界性宗教在信教民族中的作用。而且,其他自生的宗教、外來的宗教,也只能在儒道互補的基本文化信仰基礎上生存和發(fā)展。因此,了解儒道互補的文化結構,對于解析中國人的精神信仰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一、儒道兩家對古代宗教的理性主義繼承與改造
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和道家的創(chuàng)始人老子都是中國文明的“軸心期”——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著名思想家。一些史書記載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有孔子向老子學禮的傳說。春秋時期是一個所謂“禮壞樂崩”的時代,問題的實質就是夏商周三代在意識形態(tài)上占據絕對統(tǒng)治地位的古代宗教瓦解了,王權下移、巫覡散落、信仰瓦解,社會上出現了“疑天”“怨天”甚至公開懷疑、否定宗教觀念的理性主義文化思潮。從文化背景上看,可以說儒道二家同源,都源于古代宗教的母體,因此有“諸子出自王官”的說法,儒家出自“司徒之官”,道家出自“史官”(《漢書·藝文志》),它們都與古代國家宗教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按照西方著名宗教學家愛德華·泰勒的觀點,脫離人的靈魂、鬼、神的存在,是一切宗教的出發(fā)點,由此才產生從簡而繁的彼岸世界。①呂大吉指出:“在泰勒看來,一切宗教,不管是發(fā)展層次較高的種族的宗教,還是發(fā)展層次較低的種族的宗教,它的最深層、最根本的根據是對‘靈魂’或‘精靈’的信仰。”(參見呂大吉所著《西方宗教學說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47 頁)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孔子給予了不可知的回答。《論語·先進》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顯然,孔子沒有正面回答子路的問題,但是在宗教氛圍依然濃郁的春秋時代,拒不回答就是懷疑的一種表現。《論語·述而》又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也是孔子對彼岸世界心存疑慮的一種表現。可是為什么孔子不把自己心中的疑慮說出來呢?主要原因是孔子在政治上大力提倡恢復“周禮”,世人皆知,周禮就是古代宗教的集中表現,如果懷疑鬼神的存在,那么隆重的祭祀儀式是獻給誰呢?為了防止出現這種邏輯上的悖論,孔子提出了一種對宗教的主觀性解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鬼神是否存在,不是一個純客觀的問題,人相信鬼神存在鬼神就存在,如果不相信其存在,不參加祭祀,鬼神也就無所謂存在不存在了。這種主觀化的宗教觀,給后世儒家學者留下了極大的發(fā)揮余地,他們可以根據政治的需要,從各個方面對古代宗教文化遺產加以利用。
孔子承認最高主宰者的存在,相信“天”決定著人們的命運。不過,孔子對“天”的理解受“敬鬼神而遠之”宗教觀的影響,極力地使之自然化、人文化、理性化。孔子談論天、天命主宰作用的言語很多,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等。然而天意究竟是什么呢?在孔子的思想中,天有三層含義,即自然之天、義理之天、主宰之天。如他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基本取消了天神的人格形象,使天回歸了其原初自然之天的形象。天什么也不說,但是四時按照天意運行,百物按照天意生長,這種冥冥中的主宰,是孔子對人類當時尚不能認識、不能支配的自然規(guī)律和社會規(guī)律的一種模糊的把握。王亞南先生指出:“儒家不言鬼,不言神,卻昌言天。言神,在神學范疇,言天,進了一步,在玄學范疇。”[2]說明孔子已經從宗教走向了哲學,他所言“天道”更多地傾向于自然或社會的規(guī)律,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
由孔子開創(chuàng)的宗教人文化的道路,在后世的儒家學者中得到了繼承與發(fā)展,突出表現就是他們不否定古代宗教的各種祭祀活動,而是對各種祭祀活動進行了人文化、理性化的解釋,使其向人文化宗教的方向轉化。《禮記·祭統(tǒng)》說:“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治理國家的根本政治措施在于復禮,而禮的根本又在于宗教性的祭禮。但是祭禮并非祭祀外在的神靈,而是出于祭祀者本人的心理需要。“心怵”指祭祀者對于祖先懷念思念之情,這種情懷只有在祭祀儀式上才能得到釋放和滿足,故曰唯有賢者才能完全把握祭祀的意義。在這種主觀心理性質的祭祀儀式上,祭品是否豐盛、鬼神是否來享是次要的,祭祀參加者的心情和態(tài)度則是主要的。戰(zhàn)國后期的荀子完全從理性主義的角度進行解釋:“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jié)文貌之盛矣,茍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荀子·禮論》)把祭祀理解為寄托對逝去的祖先的“思慕之情”,符合孔子“祭如在”的精神,不過其理性主義精神又前進了一步,將宗教的本質從彼岸拉回了人間。正如新儒家學者徐復觀先生所說,“春秋時代以禮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發(fā)展,并非將宗教完全取消,而系將宗教也加以人文化,使其成為人文化的宗教”[3]。
道家在社會、政治領域中與儒家針鋒相對,但是在宗教觀上卻與儒家彼此呼應,也是用理性主義解析和利用古代宗教遺產。道家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老子》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老子》一章)“道”是一種非常玄妙的東西,不可言說,只能用理性去把握,但它確實是天地萬物的本源。老子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老子認為“道”是世界萬物的派生者,包括了傳統(tǒng)宗教的最高神“天”和“帝”。莊子繼承了老子的思想,他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莊子·大宗師》)道雖然不可見不可言,但是它“有情有信”,就是說它是確定的,是一種永恒的存在。“道”不僅先于天地和鬼神,而且“神鬼神帝”,賦予了鬼神靈性。
和儒家一樣,道家也不否定古代宗教的一些觀念、禮儀存在的合理性,如老子所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老子》七十三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七十九章)、“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老子》七十七章)等等。在夏商周三代積累的豐厚文化土壤上,道家不可能完全無視發(fā)達的古代宗教遺留的文化資源,但是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更高的哲學概念“道”,所以天神就下降為次要的概念了。如老子所說:“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圣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老子》六十章)以道來治理天下,傳說中的鬼神就不再神秘了。不是鬼神沒有了神性,而是這種神性不再會對人造成傷害。儒家使用理性主義的方法解釋宗教,道家則是用理性主義的方法超越宗教,其改造宗教的性質是一致的。莊子還用道家理性主義的宗教觀,解釋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些宗教觀念。傳說齊桓公到大澤邊上去打獵見到了鬼,但是駕車的管仲卻說沒有看見,回來后齊桓公就嚇病了。一個叫皇子告敖的人認為,并不是真的鬼傷害了他,而是齊桓公自己傷害了自己。他向齊桓公解釋說,雖然傳說中有許多的鬼,但是你在大澤見到的只是“委蛇”而已。由于皇子告敖所說的委蛇與齊桓公所見完全相同,齊桓公的心病立刻解除,身體也恢復了健康。這個故事說明,鬼神不過是人們的錯覺與想象的產物,鬼神對人的傷害,也是心理因素的作用。(參見《莊子·達生》)道家自然主義的天道觀,對于后世很多無神論思想家的學說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荀子的“天論”、韓非的哲學思想、王充“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論衡·自然》)的思想等。
二、儒道兩家的價值觀在傳統(tǒng)社會功能上的交融互補
宗教作為人類歷史上一種長期存在的文化現象,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必要的社會功能,不然早就在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中被淘汰了。著名宗教學家呂大吉先生指出:“按照社會功能學派的說法,宗教的社會功能主要在于它能夠維系社會的穩(wěn)定和一體性。”[4]例如,法國宗教人類學家涂爾干指出,“圖騰崇拜是其盡可能發(fā)現的最簡單的宗教”[5]。圖騰崇拜作為最初的宗教形式,其社會功能在于防止同一氏族內部的婚姻關系,防止亂倫關系的出現。可以說,組織社會,維持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性和統(tǒng)一性,是宗教最基本的社會功能。
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形態(tài)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宗法家族社會,因此存在最久遠、社會影響最大的宗教形態(tài)就是“宗法性傳統(tǒng)宗教”[6],也就是上文講到的產生于夏商周三代,并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經過儒家人文化改造的“禮教”。通過對天神、祖先、社稷、物魅、人鬼等進行一系列分等級的祭祀活動,將社會所有成員凝聚成一個有機的差序整體。如《禮記·曲禮上》說:“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也就是說,社會上所有人際關系如君臣的上下等級、父子親戚的親疏遠近、道德倫理的是非曲直,都是通過吉、兇、軍、賓、嘉諸禮的儀仗、程序、陳設等確定的。對于這種中國式的特殊宗教,德國宗教學家馬克斯·韋伯有一種“廬山之外”的清晰見解:“而安定的內部秩序,只有在一種非人格的、特別是超世俗的萬能力量(即天)的保護下,才能夠得到可靠的保證。……但是,天神之所以是勝者,是因為他是秩序之神,而非天使之神。這種宗教意識的轉變,是中國所特有的。”[7]韋伯注意到,中國以天神崇拜和祖神崇拜為核心的宗法性傳統(tǒng)宗教,也是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宗教,但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宗教相比,這種宗教之神是一種經過“轉變”的、非人格的“秩序之神”,而不是救贖之神。
孔子高度重視“以禮為序”的社會和諧,他認為當時的社會動亂就是由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一個“天下無道”(《論語·季氏》)的世道。他主張社會應當“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論語·學而》),也就是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成員都按照禮樂制度規(guī)定的方式生活,不逾矩、不僭越、和諧相處。《禮記·曲禮下》記載:“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遍。大夫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社會通過祭祀對象的規(guī)定,實際上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上下關系與范圍,維護了人間的宗法等級秩序。
《禮記·大傳》說:“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通過每個家族的祭祖儀式,在家族內部產生統(tǒng)一體的意識,這種統(tǒng)一體意識擴大,自然就延伸到宗族、鄉(xiāng)里、社會、國家。所以儒家提倡的治學思路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然把社會中的人們聯(lián)系成一個整體,成為維持社會一體性的超驗因素。在這樣一種個人、家庭、家族、國家的人際關系序列中,家庭高于個人、家族高于家庭、國家高于家族,形成了一種建立在差序格局之上的群體主義文化,國家至上、公而忘私、舍小家顧大家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民族精神。為家庭、家族、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的英雄,列為祭祀的重要對象。“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禮記·祭法》)儒家所倡導的生命終極價值是“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這種“三不朽”精神,對于儒家士大夫來說,就是他們超越生死的終極追求,使他們可以不用到彼岸世界去尋求精神安頓。
儒家宗教觀所倡導的群體主義價值觀在中國歷史上是主導的、積極的、引人向上的。然而在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社會中,公平正義、道德倫理的陽光并不總是普照所有人生。當人們處于貪官當道、惡霸橫行、官商勾結而求告無門的境地時,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論就只能引起人們的反感了。人們在正大光明的官方理論和殺人越貨的盜賊行為之間,需要一種既維護個人權益,又不受到主流文化打擊的價值倫理,這時候道家文化便派上了用場。從崇尚自然無為之道的立場出發(fā),道家尖銳批判儒家竭力提倡的宗法等級理論。老子說:“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是謂盜夸。”(《老子》五十三章)對于這樣一個“暗無天日”的社會,個人的能力十分有限,最好的辦法就是避世、游世,保全自己的生命與真性情。有人請莊子出山擔任高官,但是莊子說這個職務就如同宗廟中準備奉獻的“犧牲”,雖然披文采,吃美食,但是還不如沒人照顧的牛犢快樂(參見《莊子·列御寇》)。莊子還講了一個故事:山中有一種大樹叫做“櫟”,巨大無比,但是沒有一個木匠去砍伐它,因為這種木材什么用也沒有。大樹晚間托夢告訴匠人:“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莊子·人間世》)這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在冠冕堂皇的儒家說教面前固然顯得有些自私狹隘,但是卻可以給失意文人、市井小民、鄉(xiāng)野農夫以一種維護個人權益的口實,一種合理的生活哲學。道家的個人主義既維護了個人利益,又不傷害他人或國家的整體利益,即使不是統(tǒng)治者最需要的,至少不是他們害怕的。那些游離于政治權力結構以外的、有一定思想的人,如果都承擔起“天下興亡”的責任,散布“天命轉移”的思想,才是封建統(tǒng)治者真正忌憚的。所以歷朝的統(tǒng)治者對于道家文化都采取歡迎的態(tài)度,使之成為儒家文化以外的一種必要的精神補充。
可以說儒道互補是群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精神的互補,儒家的群體主義精神構成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對于穩(wěn)定古代的宗法社會結構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社會又是小農經濟社會,個體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生產細胞、生活細胞,社會的穩(wěn)定又需要尊重個人的利益和積極性。因此道家指向個人主義的“天道自然”思想,也是保持社會生產活力的重要基因。所以我們看到,每逢社會經歷了重大的戰(zhàn)亂,統(tǒng)治者都會祭出道家“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大旗,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恢復社會生產力。可是一旦社會經濟恢復,又會加強儒家倡導的“倫常教化”,整肅社會秩序,提升國家的控制力。儒道互補成為二千多年封建社會的主旋律,共同維持了中國的超穩(wěn)定社會結構。
三、儒道互補成為中國人傳統(tǒng)精神信仰結構的底色
儒道兩家在社會功能和精神信仰方面都是既有分野,又相輔相成,從根本意義上決定了中國人傳統(tǒng)的信仰結構及其特點。
精神信仰上的儒道互補主要表現在秩序與自由的關系上。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過:“人類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8]一個社會沒有秩序就不能存在,這個結論屢試不爽。在中國古代社會,維持社會秩序的宗教功能主要是由儒家闡釋的宗法性傳統(tǒng)宗教來維護的。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祭拜天地大神以及一些相關的被神化的英雄和專司神靈,乃是國家事務。……沒有信仰,世界無法保持秩序,所以,維護信仰在政治上甚至比對民生的關懷更重要。”[9]在中國古代,儒家的“禮教”承擔了論證社會等級秩序的主要任務,這一職責是任何其他宗教都不能染指的。《周易·賁·彖辭》說,圣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界,人是有思維、有欲望、有主觀能動性的,因此對人類的行為必須進行社會引導,儒家將其稱為“人文化成”。除了學校教育,歷代儒家還十分重視宗教性祭祀的教化作用。如前文所述,孔子對鬼神持存疑立場,但他并不否定祭祀鬼神的必要。他稱贊大禹說:“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恤。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莊子定義孔子的宗教觀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莊子·天下》)對于這種矛盾的態(tài)度,漢代劉向在《說苑》中引用的一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可作為解釋:“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說苑》卷十八)儒家“禮教”的喪葬、祭祀之禮,主要不是為了給亡靈饋贈祭品,而是為了教育兒孫,維護宗法家族社會必需的“孝道”。
然而由于“禮教”是一種經過儒家學者人文化、理性化、倫理化改造的準宗教,具有完善的宗教儀式,但是缺乏相應的宗教理論,不論祭祀禮儀的執(zhí)行者還是觀看者,都秉持一種“存而不論”“敬而遠之”的心態(tài),并不追尋這些禮儀背后的彼岸世界,因此就使得這些禮儀變得威嚴、空洞、冷漠、壓抑,缺少對于現實人生的心靈關懷,無法解決世人的生命焦慮。這時候,在道家自然主義宗教觀基礎上產生的“自由主義”哲學就派上了用場。周公開創(chuàng)的禮樂宗教主要由儒家繼承,在后世承擔起維系社會基本秩序穩(wěn)定的使命,而道家則站在儒家的對立面,對于儒家所宣揚的禮樂制度采取批判的態(tài)度。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道家理想的社會是“小國寡民”的原始氏族社會,而文明發(fā)展的階級社會則是從理想的“道”的狀態(tài)的倒退。“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在儒家看來,西周的禮樂文明就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最佳狀態(tài)。而道家則認為,世界的混亂就是由于禮樂而起,因為禮樂的背后,是人被分成了若干的等級。有了差異就難免有競爭,有競爭就會導致許多的苦難。在道家看來,春秋戰(zhàn)國的社會混亂,并不是社會下層民眾不服管教而致,而是西周以來的君子們建立的等級剝削制度所致。那么解決的真正辦法,就是統(tǒng)治者向“道”學習,“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舍棄社會上那些繁瑣的禮樂制度,回歸自然。
道家也意識到,人類文明已經發(fā)展了,整個社會不可能回到“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莊子·馬蹄》)的時代,只能通過個人的精神修煉,使精神與道契合,“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莊子·天下》),獲得一種個人精神上的自由。當然要獲得這種精神自由首先必須超越物質條件的束縛,“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莊子·跰拇》)這就是“人為物役”的異化狀態(tài),所以要自由首先要“無己”。此外還需要“無待”,即不依賴外部的條件。道家的理想人格,是超越了現實社會一切世俗價值的“至人”“真人”境界。《莊子·齊物論》說:“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要達到這一點,靠的是放棄對利益、名譽甚至生命的執(zhí)著。莊子說出了實現精神超越的具體方法,即“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莊子·大宗師》)忘記了自己的身體,忘記了世俗的智慧,精神離形體而去,便與大道合一,成為道家理想中的“至人”“真人”“神人”。當然很明顯,道家所提到的這種精神自由,只能是個人精神上的,甚至可以說是脫離社會現實的。然而在古代階級剝削壓迫的社會里,大多數人民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這種所謂的“精神自由”就可以派上大用場,給緊張的社會關系一種緩和或松動,防止因過多的利益對立而造成沖突。對個人而言,有一種合理的精神撫慰機制,可以防止因精神過度緊張而崩潰。道家認為通過無己、無功、無待的精神修煉,就可以達到超脫凡俗的神仙境界。莊子在《逍遙游》中形容神仙的世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這樣一種“自由”固然是虛幻的,但是在古代君主專制社會中,如果只有一種正面的教化,一旦這種教化失靈,容易造成人們精神崩潰。道家這種出世主義的哲學,則可以給人一種精神的慰勉。現實也是如此。二千多年來,中國的士人們年輕或順利的時候學儒家積極進取,年老之后或失意之時,還有道家的思想提供精神的港灣,紓解緊張、失落的情緒。梁漱溟先生給宗教下了一個定義:“所謂宗教的,就是以超絕于知識的事物,謀情志方面的安慰和勖勉的。”[10]以此標準來看待老莊的思想,雖然被我們定性為哲學,但是無疑發(fā)揮了宗教心靈慰勉的功能,而且這種慰勉功能是指向個人的,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成為道教生成的重要文化資源。
四、儒道互補成為歷史上外來宗教中國化的思想土壤
精神信仰上的儒道互補不僅確定了秦漢之后中國文化的基調,而且也成為其他宗教生成、輸入的文化土壤。道家認為,隱士們不僅應當通過“游世”來保全自己性命,而且應該通過“養(yǎng)生”來使自己的生命得到超越。超越一方面是身體上的,老子從“無為不爭”“抱雄守雌”的道家哲學推論出:“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后世道教學者對這段話的解釋多種多樣,由此推衍出的修養(yǎng)方法也各不相同,但“谷神不死”無疑為人們昭示了一個超越生命的總方向。老莊雖沒有建立宗教,但是他們的這些思想成為道教超越生命焦慮的思想淵源。不僅道教如此,其他外來宗教,如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初傳之際,也無不使用道家的這些范疇,“借殼傳教”。如漢桓帝在宮中初立佛祠,大臣襄楷奏曰:“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死,省欲去奢。”(《后漢書·襄楷傳》)這是在用道家的思想解釋佛教的教義。最早的編譯本佛經《四十二章經》說:“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住動天地。”這是用道家的“神人”形容佛教的羅漢。現存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唐太宗恩準景教傳教的圣旨說:“道常無名,圣本無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道常無名”“玄妙無為”等詞語,是在用道家的思想理解基督教。唐玄宗時代摩尼教士佛多誕受玄宗之命,于集賢院譯出《摩尼光佛法儀略》一書,介紹摩尼教的基本原理說:“我乘自然光明之道氣,從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室,示為太子。舍家入道,號末摩尼。”“光明道氣”“真寂境”都是道家的概念,由此可見,道家的思想土壤也是摩尼教初傳的文化中介。所以我們說道家消解了古代宗教的同時,又為新宗教的誕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道家關注個人精神自由的文化傾向,成為日后一切出世型宗教的“母體”,這些宗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生根,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夠填補儒家在個人精神慰勉方面的缺失。
自從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文化戰(zhàn)略之后,儒家文化成為社會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各種外來宗教僅僅借助道家文化的“殼子”還很難生根和成長。歷史上外來宗教中國化主要是與主導意識形態(tài)儒家文化的結合。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佛說阿彌陀經》卷下說:“佛言:……教戒開導悉奉行之,則君率化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婦。室家內外親屬朋友,轉相教語作善為道。”(《大正藏》第12 冊)雖然佛教教化民眾的方法與儒家有異,但是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完全一樣的,即在教化的過程中,也是君教臣、父教子、兄教弟、夫教婦,與“三綱”規(guī)定的主從順序完全相符。唐代高僧法琳在《辯正論》中指出:“且書有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愍傷不殺曰仁,防害不淫曰義,持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五德者,不可造次而虧,不可須臾而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身。”(《大正藏》第52 冊)這是用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使佛教理論與儒家倫理相一致。
為了論證伊斯蘭教在中國存在的合理性,明代回儒王岱輿提出“二元忠誠”論。他說:“人生在世三大正事,乃順主也,順君也,順親也。”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必須認同“認主獨一”的原則,但是在古代中國僅僅如此是不夠的,還需要“順君”“順親”,即表示對“三綱”的認同。中國古代的宗教治理不干涉民眾的信仰,但是教徒在社會義務方面必須恪守綱常倫理,這是政治認同。王岱輿還用伊斯蘭教的“五功”來詮釋儒家的“五常”:念經不忘主是仁心,施真主之賜于窮人為義,拜真主與拜君親為禮,戒自性為智,朝覲而能守約為信。這是對中華文化的全面認同,使伊斯蘭教與中國的宗法社會制度相適應。
明末基督教再次傳入中原,羅明堅、利瑪竇曾經剃去頭發(fā)、身著僧裝傳教,但是發(fā)現效果不佳。后來他們打出“援儒”“補儒”的旗號,以輔助政治的面貌出現。利瑪竇作《天主實義》一書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天主教:“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賢圣勸人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為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11]利瑪竇對中國的社會、文化、經典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中國當時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三綱五常”,因此著書立說,首先聲明對于綱常倫理的恪守。利瑪竇還附會儒家的孝道說:教徒行孝道要盡三方面的義務,即向至高無上的天父“上帝”盡孝,向一國之父“君主”盡孝,向生身之父盡孝。這也是一種對儒家綱常倫理的全面認同。利瑪竇說:“夫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安養(yǎng),乃無上共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忠,至無孝也。忠孝蔑有,尚存何德乎?”[12]他把踐行忠君孝父當成一切道德的根基。
所以我們說,中國歷史上,儒道互補不僅在原生文化層面上決定了中國人自己的精神信仰,而且也決定了中國人對外來宗教的選擇與改造,決定了宗教中國化的方向。歷史上,外來宗教需要認同、適應中國人儒道互補的信仰結構,才能實現中國化,在中國大地上生存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