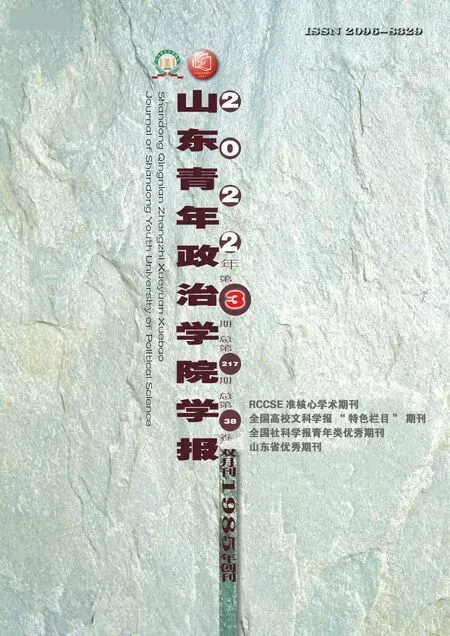《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明皇太子考
田志豪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濟南 250014)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現存兩個版本:一為小字本,也稱巾箱本,題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分上中下三卷,共17節;一為大字本,題為《新雕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記》。兩個版本皆藏于日本高山寺,皆有缺失。小字本上卷缺第一節,中卷缺第七節結尾和第八節前半部分;大字本第一卷缺一二三節,第三卷全失。文本的缺失阻礙了對其研究的深入。兩書分別于1916年、1917年由羅振玉先生影印,其后被整理出版。羅振玉在該書的跋中說:“宋代平話之傳人間者,遂得四種。”[1]初步判斷《詩話》為宋代刊本。
關于該書的成書年代可謂眾說紛紜,本文引以下幾種主要觀點:
根據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而中瓦子“為宋代臨安府街名,倡優劇場之所在也”[2],王國維先生推測《詩話》創作刊行于南宋,但此后他在《兩浙古刊本考·卷上》中將《詩話》列入“辛、元雜本”中,又提出該書是元代刊本。[3]魯迅先生持有相同看法,且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發,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皆首尾與詩相始終,中間以詩詞為點綴,辭句多俚,顧與話本又不同,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4]“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為宋時臨安書鋪,世因以為宋刊,然逮于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為元人撰,未可知矣。”[5]
除以上先生主張的宋元成書論外,還有南宋、晚唐五代成書兩種說法,共成鼎足之勢。胡適、胡士瑩先生均謂《詩話》成書于南宋,在他們的著作中各有提及。①曾炳建先生在《也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成書時代》[6]一文中,結合了宗教發展和地域劃分等因素,亦認為該書成書時間當為南宋;李時人、蔡鏡浩先生最早提出了晚唐五代成書說,他們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成書年代考辨》[7]一文中對《詩話》的藝術形式、思想內容、語言現象等方面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作為支撐自己判斷的依據。劉堅先生《<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寫作時代蠡測》[8]中據取經詩話的語言特點,也得出同李、蔡近似的結論。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就成書時間發表了意見,在此不再一一羅列。在沒有其它確鑿證據出現前,許多學者同意先以“中瓦子張家印”為證,將成書時間定在南宋為宜。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下稱《詩話》)就文本而言,時顯粗陋樸實之處,但是它標志著這一唐僧取經題材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其故事的情節人物等方面對以后出現的西游題材作品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在人物上,書中出現了猴行者形象,這也是整個西游故事體系中他的首度登場。猴行者的出現,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他的加入使得本書的虛幻色彩大大增加,為以后的神魔小說性質的確立設下了伏筆。作品毫不隱晦地突出了猴行者在取經過程中的作用。猴行者一開始以一白衣秀才的形象出現,似乎就預示著其識見的廣博。他自述曾“九度見黃河清”[9];“我年紀小,歷過世代萬千,知得法師前世兩回去西天取經,途中遇害”[10]。在取經的全過程中,猴行者不僅能降妖驅魔,更能充當取經路上的百科全書,為玄奘解疑答惑。在“《遇長坑大蛇嶺處》第六”一回中,唐僧師徒就有問答形式的對話出現,原文如下:
次入大蛇嶺,目見大蛇如龍,亦無傷人之性。又火類坳坳下下望,見坳上有一具枯骨,長四十余里。法師問猴行者曰:“山上白色枯骨一具如雪?”猴行者曰:“此是明皇太子換骨之處。”法師聞語合掌頂禮而行。[11]
本處出現的“明皇太子”,敘述簡略,僅一筆帶過。遍搜全文可以發現,“明皇太子”也僅存此一處,另外文中還有“明皇”的四次出現,可為我們的考證提供參見,現將原文附下:
波羅別是一仙宮,美女人家景象中。大孩兒,小孩兒,辛苦西天心自知。東土眾生多感激,三年不見淚雙垂。大明皇,玄奘取經壯大唐。程途百萬窮天日,迎請玄微請法王。[12](《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百萬程途取得經,七人扶助即回程。卻應東土人多幸,唐朝明皇萬歲膺。建造經函興寺院,塑成佛像七余身。深沙幽暗并神眾,乘此因緣出業津。竺國西天都是佛,孩兒周歲便通經。此回只少《心經》本,朝對龍顏別具呈。[13](《入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明皇時當炎暑,遂排大駕,出百里之間迎接,法師七人相見謝恩。明皇共車與法師回朝。是時六月末旬也。日日朝中設齋,敕下諸州造寺,奉迎佛法。皇王收得‘般若心經’,如獲眼精,內外道場,香花迎請。[14](《到陜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筆者查閱文獻,發現明皇太子換骨一事論及的有: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在《<西游記>考證》中引用了《默記》中對“玉骷髏”傳說的記載,認為這是明皇太子換骨升仙傳說形成的一端[15];張乘健先生《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史實考原》據《舊唐書》考據,提到“換骨”“頂禮合掌”可以證明白骨主人身份不凡,認為明皇太子即為太子瑛[16];蔡鐵鷹先生《<西游記>成書研究》征引了《佩文樂府》中的幾條“換骨”的相關記載,他關注到《傳燈錄》慧可換骨,認為“換骨”是在唐代被佛教所吸收,他還征引了《默記》中的“玉骷髏”傳說,并分析了“明皇換骨”事典的可能來源[17];曹仕邦先生則是從西游故事探源的角度出發,認為枯骨與隨后出現的白虎精是《西游記》白骨精的發端,他引用唐沙門志玄和尚傳中的狐貍掛骷髏成精的故事,探討重點是白骨與女妖之間的關系,但是對明皇太子的來源未進行細致探討[18]。經過查閱與分析可知,對于明皇太子的研究,在邏輯和史料上都存在不足,故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對《詩話》中出現的明皇太子換骨一事進行探索討論。
一、《詩話》取經時間為唐玄宗統治時期
如果直接從字面意思上來看,明皇當為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謚號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取其“明”字,可稱唐明皇。在唐朝,明皇稱謂已有,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19]“及輔弼明皇帝,號為賢相”[20]。李昭道畫作《明皇幸蜀圖》也可為一例證,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說:“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21]到宋代,明皇之稱謂出現更多。真宗追封趙玄朗為“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22]開宋代官方層面對“玄”字避諱之先。宋徽宗手抄《千字文》,其中“天地玄黃”改為了“天地元黃”。為避“玄朗”之諱,時人也多稱玄宗為唐明皇。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詩話》將玄奘取經的背景定在唐玄宗統治時期,這是時間上的誤植。根據《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文獻記載,唐僧取經時間為唐太宗時期無疑。據載當時唐太宗并不允許玄奘西行取經,也未給予玄奘以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只有在玄奘取經歸來時才予以接待,不僅如此,其后他甚至邀玄奘還俗為臣。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以太宗時期為取經背景這同作者欲處處彰顯西方極樂、佛法廣大的目的是不協調的,倘若真據實而作,其宣揚宗教教義的功效將會大打折扣,作者將時間推移到了禮僧崇佛、曾接受密宗大師灌頂的唐玄宗統治時期可能正是出于上述考量。而在其后出現的西游題材系列作品中,不僅重新使取經時間歸于太宗時期,還對取經途中的一些情節作了接木移花式的改造。比如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記載的高昌國主麹文泰與玄奘“約為兄弟”“度沙彌充給侍”、給予“所用之資”“馬”“手力”、發放通關文書、親送出城等親佛事跡[23]挪移劃歸到了唐太宗身上。其目的無非是使求取真經所擁有的普度眾生的價值得到官方的認可,令唐僧的取經之途顯得名正而言順,亦使得取經布道的現實追求能夠在統治者的支持下顯得更為意義重大。
將取經時間誤植于玄宗時期不僅見于《詩話》。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就發現其國平安貴族源隆國所作《今昔物語》卷七“唐玄宗初供養大般若經語第一”云:“震旦唐玄宗之代,玄奘三藏譯大般若經”[24],這里也誤以為玄奘是在玄宗時期進行的取經活動。日本對取經故事的改造都是基于我國的玄奘取經本事,我們或許可以作出一個大膽的猜測,即源隆國對取經時間的誤判可能是在來自中國的文獻傳播影響下產生的,他也許閱讀過傳到日本的《詩話》。如果上述推想成立,那么《詩話》要早于《今昔物語》被創作出來。但因《今昔物語》成書年代不詳,僅可據作者卒年對作品最晚成書時間作一區間框定。史載源隆國于承保四年(北宋熙寧十年,1077)離世,那么《詩話》產生并流傳到日本最晚也應早于這個時間。
查閱史籍可見,宋朝與日本之間確實存在過較頻繁的典籍交流活動。早在天元六年(北宋太平興國八年)日僧奝然就到宋求法。隨后又有寂昭與弟子諸人于長保五年(北宋咸平六年,1003)來宋。在寬弘五年(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治部卿源從英致函在宋的寂照:“所諮《唐歷》以后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唯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25]此函充分顯示出日本平安貴族對宋典籍的渴求,無奈商人重利輕文,以至于帶去的典籍寥寥可數。延久四年(北宋熙寧五年,1072)三月,日本僧侶成尋及其隨從七人來華,帶來了大量的日本典籍,其中包括南泉房(源隆國)的《安養集》,他還托先行返回日本的隨從將從宋搜集到的珍貴典籍帶回,并分送至包括大云寺經藏、石藏經藏等各處。[26]《詩話》也極可能是在宋日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以該形式被日本僧侶或去日經商的宋商帶去日本并流轉至高山寺的,可能因《詩話》不屬于正宗的佛教經典一類,所以并不被記載。
《詩話》最末說:“太宗后封猴行者為銅筋鐵骨大圣。”[27]此處太宗的突然出現令人費解,若非作者歷史概念薄弱似乎不能解釋。太田辰夫認為這句是南宋的刊刻者所加,綜合來看,這是存在可能的,但是這也可能與作者在太宗、玄宗之間選擇時間版本時的猶疑,或刊刻者印書時的粗疏失于核查相關。關于此處的諸多猜測因文章的部分軼失與史料的匱乏,尚無法論定。
二、明皇太子李瑛之死
歷史上的唐明皇共立兩位太子,前后分別是太子李瑛和太子李亨。李瑛被廢為庶人,旋后身死;李亨是唐玄宗第三子,最初被封為陜王。開元十三年唐玄宗設立“十王宅”,開元十五年(727),李亨被封為忠王,這以后他一直居于十王宅中,一直到開元二十五年(738),皇太子瑛廢死,明年也即開元二十六年(739)被立為皇太子。由于宰相李林甫素來支持壽王李瑁,因而對被立為太子的李亨數次攻訐,但玄宗并未因此疏離李亨。天寶五載(746),李林甫向玄宗奏稱皇甫惟明、韋堅密謀“欲共立太子”,他欲羅織李亨罪名,將其牽涉其中。但玄宗最終也未使此案涉及李亨,最后李亨安全度過了此次政治危機。玄宗對涉及太子李亨的案件一律審慎對待,使得李林甫等人并無可趁之機,從結果來看,玄宗的態度實際上對李亨形成了保護。開元十五年(756)時玄宗避安祿山之亂出離都城,陳玄禮等“謀于皇太子”[28],在馬嵬驛策動兵變。隨后亂軍殺死楊國忠,逼死楊玉環,兵變之激烈,矛頭已經直指玄宗。史書雖聲稱當地百姓留太子李亨討賊,但是從當時的情形來看,李亨與其父的分道揚鑣已成定局。在分兵討賊途中他一度十分窘迫,倉皇顛沛,最后于當年七月到達靈武,隨后在裴冕等人的扶立下于靈武即皇帝位,建元至德,是為唐肅宗。
通過對李亨相關記載的梳理可以發現,李亨為太子時未見異聞,本就缺失下文要論及的“神異化”的一些條件,且他為太子時雖多有波折,但還是得以登基承繼大統,最終李亨是于寶應元年(762)以皇帝之名位病死宮中。另外依據《詩話》的脈絡,取經之時明皇尚在位,在唐僧師徒取經過程中出現的明皇太子已化為白骨。據上可知,明皇太子只可能為李隆基第二子——已經故去的廢太子李瑛。根據《舊唐書》所載,開元三年(715年)正月,李瑛被冊立為皇太子。“瑛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于潞州得幸……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瑛于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于己,日求其短,譖于惠妃。妃泣訴于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謀于宰相,意將廢黜。”[29]但是時任宰相張九齡據理力爭,幫助太子度過了此難。到后來李隆基再受讒言,說李瑛兄弟三人同太子妃之兄薛銹“常構異謀”,這對于久經動蕩才爭得帝位的玄宗是不可忍受的,最終他下令將三子“使中官宣詔于宮中,并廢為庶人”[30],“同謀”的薛銹被配流,隨后被賜死在城東驛中。
《新唐書》所載與舊說稍有不同:“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銹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并廢為庶人。銹賜死’。瑛、瑤、琚尋遇害。”[31]在這里《新唐書》稱李瑛等人是受惠妃詭召,披甲執堅進宮,坐謀逆罪,為玄宗所廢,后則遇害。
三、廢太子瑛神異化諸種構成因素
(一)輿論的同情
對于唐皇一日殺三子的事件,輿論嘩然,朝野為太子瑛喊冤聲不斷。《舊唐書》云:“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死于故驛,人謂之三庶,聞者冤之。”[32]《新唐書》記載:“瑛、瑤、琚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33]《資治通鑒考異》中引獨孤及作裴稹行狀云:“公為起居郎,三庶人以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默,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間,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殷鑒,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34]司馬光就此說議論道:“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稹若敢為太子直冤,則聲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此事,蓋出于及之虛美耳。”[35]但這即便是出于獨孤及對裴稹的“虛美”,即裴稹其人并未為太子瑛等喊冤,但是廢立是封建王朝的大事,朝臣議論鼎沸的時況是可以想見的。生活于同時代的李白所作樂府詩歌《山人勸酒》有劉邦欲廢太子一事,顧有孝在所輯《樂府英華》中《山人勸酒》箋評分析說這是“白為明皇欲廢太子瑛而作也”。“三庶人”一案并未蒙塵太久,到寶應元年(762年)時,唐代宗“詔贈瑛皇太子,瑤等復王”[36],正式為其平反昭雪,恢復了三人的地位與名譽。到唐貞元三年(787年),德宗欲廢太子,李泌以前朝廢太子之事力諫,其中就提到了玄宗廢太子瑛之事:“至于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37]在李泌的據理力爭及引前朝之事力諫后,最終太子得以保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無論《舊唐書》《新唐書》都未見李泌諫德宗廢立處引用廢太子瑛一例,而司馬光《資治通鑒》卻征引了此例。與司馬光生活于同一時代的孫甫撰有《唐史論斷》,卷中《冊忠王為皇太子》一篇對太子瑛一事亦有議論,孫甫認為太子瑛遭廢死固然是惠妃、李林甫之責,但張說亦難逃其咎。[38]北宋時史家如此高密度的提及太子瑛一事,或許有當時存在相關議論熱點的可能,然而這是否與《詩話》成書時間及傳播影響相聯系還需進一步考證。
史書、文叢對于世人對三庶人一案的反應記載并不夠周詳,但是由提到的只言片語也可以窺見此事引起的風波應該不小。在信息傳播渠道有限的民間,在人民大眾所具備的幻想加工能力和出于鳴不平的目的驅使下,明皇太子的被殺順理成章地演化成了諸多的民間傳說。《詩話》里關于明皇太子的換骨之事,可能正是其中之一敷演而成。
玄宗皇后無子,廢太子李瑛為庶出,其母本伎人出身,母族力薄且亦受牽連,“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39],而且趙麗妃早在開元十四年(726年)就故去,在其遭誣廢為庶人時不能提供任何幫助,這樣的身世極易引起聽眾的同情。《詩話》的作者雖只一筆帶過明皇太子,但是在書末第十七回中出現了下述情節:王長者將去外國經商,并囑托續弦之妻好生看護先妻所留的癡那。王長者妻因感其夫偏袒癡那,不看覷己出的居那,出于嫉妒幾次三番試圖殺害癡那,但在佛法的護持下,癡那終于幸免于難。此事從本事上有演化的蹤跡可循,在北朝時的《付法藏因緣傳》中即有相類情節。這段情節,放置于文章最后一回,似乎隱約與武惠妃為使其子壽王李瑁繼承大統幾次譖害太子瑛之事相合。作為具有參與輿論和干預輿論職能的撰書人而言,這種安排可能是他對太子瑛的同情與除惡揚善的正義感驅使下的有心之舉。
(二)安撫鬼祟的民間信仰
武惠妃伙同其女婿楊洄誣告太子,自身受“祟”恐嚇,亦死。據《新唐書》載:“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40]這種說法符合人民的懲惡揚善的期待,也可見太子瑛等死后就已有化為鬼祟一類的異聞了,我們推測在民間的傳說就可能更多,《詩話》本身也當是這種傳說的代表之一。
《論語·述而》云“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一直以來都得到了中國士大夫們的積極宣揚,但民間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談異說奇的傳統。中國古代對于魂魄提及最早的是《左傳·昭公七年》中子產解釋伯有是否“能為鬼”的問題。
能。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日“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41]
根據子產所言,“匹夫匹婦”亦有魂魄,可見靈魂為生民所共有,但是王公大臣的魂魄因為能夠“用物弘”“取精多”,較庶民百姓之魂魄更為強大,甚至能夠“至神明”。可見對于王公大臣死后亦與常人不同的認知,古已有之。根據這個邏輯,太子瑛等死后,先為鬼祟,后至于神明,是說得通的。
而在中國古代,王侯將相,尤其是死于非命的王侯將相作為一個重要的子題被演化出神話傳說的例子原就不在少數。比如在筆記小說《堅瓠集》中有一則關于烏江廟的記載云:“烏江有項羽廟,頗靈異,舟楫往來必焚紙錢祭享,否則獲咎。”[42]據傳項羽死后在吳興一地也有廟祭祀,他被稱為憤王、祟君等名號[43],由這些名號可見項羽作為英雄人物死于非命后,正是出于恐其靈魂作亂的動機人們才為其興建了廟宇。六朝歷史、傳說中經常出現的蔣侯神,在臨都城北部鐘山上有廟祭祀,相傳他原是武將,死于非命,之后引起了許多災異。[44]在淮南當地流傳著許多淮南王升仙的民間傳說,這可能與劉安也曾以“作祟”的形式出現在了人們的生活中有關。[45]在人民眼中,將死于非命的人,尤其是一些英雄、顯貴進行神化可以達到安撫亡靈的功效。而這種安撫鬼祟并將其神化的傳統顯然并非只存在了一朝一夕。太子瑛死后作為鬼祟的出現,為以后太子瑛的進一步神化提供了可察線索,也應是欲安撫此類非命死亡之人的民間信仰的承繼。
(三)佛道融合及換骨
猴行者向玄奘一路解答的諸多神異事件,包括“明皇太子換骨”一事,這些都表明作者有意識地將故事情節加工出奇異色彩,也有意識地征用了許多民間傳說。這些帶有神異特征的情節充分顯示出了當時佛道趨于融合的態勢。
換骨本是道教用語,意指靈魂升天,留下尸骨。我國古代提及換骨的文獻歷來不乏,早在《列仙傳》中即有相關記載:“王可交棹漁舟入江,見一花舫漾于中流,有道士七人。一道士引可交上舫與酒吃,瀉之不出。道士曰:‘酒乃靈物,若得入口,常換其骨。’”[46]唐宋詩文中也可見對換骨一詞的征引。李商隱詩《藥轉》中有:“郁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47]范仲淹詩中有:“竊藥嫦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間看。”[48]歐陽修詩《寄答王仲儀太尉素》有:“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鐘。”[49]明人馮夢龍《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鬧華光廟》中則有對凡人如何換骨成仙的記述:“凡人成仙,脫胎換骨,定然先將俗肌消盡,然后重換仙體,此非肉眼所知也。”[50]
宋代王錘的《默記》中有關于明皇換骨的詳細記述:
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髑髏……元獻取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也,環異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嘆日:“此豈得于華州薄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于彼得之也。元獻因為僚屬言:“唐小說:唐玄宗為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捶擊其腦。玄宗臥未起,中其腦,皆作磐聲。上皇驚謂刺者日:“我固知命盡于汝手,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錄》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玄宗之髑髏骨也。”[51]
太田辰夫先生認為,這則玄宗升仙傳說中的玉骷髏、金丹這些神異物事都可能是明皇太子脫骨升仙傳說形成源頭的構成因素。[52]
蔡鐵鷹先生提出,換骨大概在唐代時為中土佛教所吸納,這對于揚佛作品《詩話》中出現了道教用語的釋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參見的是《傳燈錄》中有關慧可換骨的記載:“慧可初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翌日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日;‘此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頂如五峰秀出。”[53]作為一部以唐代為背景的取經作品,《詩話》雖然是“一部弘揚佛法的宗教書籍”[54],但是也兼有一些道教用語,體現出佛道合一的特點。明皇太子“換骨”僅為一條,還有如《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七回中,玄奘稱猴行者是“大羅神仙”[55]。又如該回中玄奘對于王母池處所結能增三千壽數的蟠桃表現出強烈興趣,在行者多次推辭不去偷取后,他仍慫恿猴行者去偷:“你神通廣大,去必無妨。”[56]此即顯示出玄奘對于長生的向往之意,而佛家則講究超脫生死,“不生不滅”,此處顯然有道教觀念之融入。另外還有第十七回中寫道:“七人上舡,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57]寫佛教徒修成正果,不以成佛而以升仙,其跡更顯。道教觀念匯入一部旨在揚佛的書籍中,這體現出佛道融合的特點,為明皇太子脫骨升仙出現在《詩話》這樣一部揚佛的作品中掃清了障礙。
最后,《詩話》中這具枯骨的長度,如原文所講“長四十余里”,顯然非常人之身軀所留,倒是與曹植的《神龜賦》“虵折鱗於平皋,龍蛻骨於深谷”[58]中的蛟龍所蛻之骨有所貼合。在中國古代的許多意象中,如此龐然大物,能占坳上四十余里,確實也只可能為龍蛇所留。作為皇家后裔,李瑛以皇儲之身脫胎換骨,留下了龍的尸骨,是符合中國神話傳說特征的。另外,在玄奘從猴行者口中得知這是明皇太子換骨之處時,他的反應是“合掌頂禮而行”[59]。合掌頂禮是佛教中極高的敬禮,由此可見被唐僧如此尊重的必是佛陀仙人或是帝王顯尊。這些細節都有力地扶持了這具遺骨就是廢太子李瑛脫骨升仙之后所留的觀點。
綜合上述材料,在佚失的首回及其他部分得到新發現予以補證之前,將明皇太子定為廢太子瑛,應為無誤。
注釋:
①胡適先生以西游故事體系切入研究,將《詩話》置于南宋背景中進行論述,分析了《詩話》的情節、結構、人物。(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上海書店,1979年,第325-334頁);胡士瑩先生對《詩話》的研究從版本講起,認為“該書刻工字體質樸中有圓活之致,證以王氏跋語,當為南宋晚期的刊本”,胡士瑩先生還作按語,認為取經故事在南宋以前就極為流行。(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商務圖書館,2017年,第258、2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