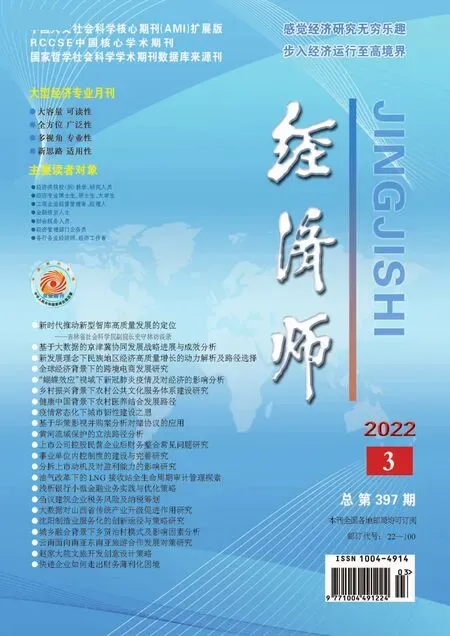公共危機治理中的科技風險決策機制優化研究
●郭美玲
當前,科技的迅猛發展不斷推動著經濟、社會運行,給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著科技支撐。但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科技本身具有的不確定性及潛在的負效應也使其成為不可忽視的風險源。因此,面臨越來越多難以預測的公共危機,如何規避科技風險,制定科學審慎、及時適度的科技決策,成為政府有效治理公共危機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
許多學者從不同視角研究了科技風險決策,但不難發現,研究大多是在某一時代背景下,站在科技風險內容角度或將決策主體割裂開來,缺乏在具體事件中分析多元主體如何協同決策的研究。孫壯珍(2018)提出社會媒體造成的風險溝通異化、知識社會產生的多種交叉沖突的價值觀、后常規科學的出現等成為科技風險決策者面臨的時代挑戰;文九,黃藝雅(2017)認為網絡時代下,大眾傳媒成為風險建構與定義的重要平臺,是公眾參與風險決策過程的契入點。筆者以早期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決策線索為研究對象,分析何種因素導致決策未能充分發揮科技的正面作用,以期構建一個科技群體,決策群體及公眾動態協調的科技風險決策機制,為高效應對公共危機助綿薄之力。
一、問題的提出
以往在危機爆發之前,總會呈現一些征兆,敏銳的管理者往往能夠提前感知風險,將危機扼殺在搖籃之中,但當代社會的主導風險已從自然風險逐步演變成人為不確定性風險,決策對象變成不確定性更高,具有更大科學爭議性的問題,需要從更長的風險鏈條出發建立決策組織,確立決策標準,評估不同決策方案的收益與風險,選擇最佳方案并付諸實施。一些傳統觀點認為,科技只是風險決策過程中需要關注的眾多因素之一,應該將公共利益的維護即社會、經濟的穩定放在風險決策的第一位,防止科技濫用,顯然不符合科技地位迅速上升的當代社會風險管理要求;另外一些學者認識到科技群體對風險的精準判斷在公共政策決策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強調將科技因素優先納入考慮主導決策。筆者認為,單純地強調公共利益或科技任何一方主導政策制定都不符合時代需要。
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令我們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背景下,要恰當進行科技風險評價與決策,就應該明確政府、科技專家、公眾在與科技風險相關的公共決策中的不同作用。首先,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占主導地位,政府官員應認識到科技風險的不確定性、不可逆性等特征,當科技專家出現分歧時,應根據具體情境作出決斷,重視公眾風險承受者的角色,將其引入科技風險決策程序,追求民主化;其次,認識到科技專家知識的有限性,風險常常是復雜的、不確定的且涉及范圍廣,有些不屬于科技專家專業知識范圍,科技專家對它們的認識是有限的甚至是錯誤的;另外,公眾參與科技風險決策是必要的,他們直接承擔科技風險,更能從實際出發思考科技決策的后果,監督科技專家和政府,維護社會利益。新冠疫情是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其上升為公共危機前,風險決策主體和利益相關方建立了怎樣的決策流程?對科技風險是如何評價并做出決策的?在面對類似的突發事件時,科技群體、決策群體、公眾應建立怎樣的科技風險決策機制實現從根源上治理危機?
二、新冠疫情防控中的科技風險決策困境
1.決策群體存在科技風險認知偏差。首先,維護公共利益始終是決策群體追求的最重要目標,即使是面對具有深度不確定性的疫情,決策群體仍然在科技群體對風險認知不清,沒有明確結論情況下,選擇提供一個安定的環境;其次,決策群體沒有正確評估科技會帶來的收益與風險,在依靠專家研究病毒、研判風險的同時也要考慮其知識的局限性,一旦研判錯誤,付出的代價將巨大,疫情放控期間,選擇性吸納與自己目標相一致的研究結論采取行動,忽視風險擴散程度,沒有利用搜索引擎大數據,科技預警作用未能充分發揮;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決策群體內部鏈條過長,導致決策的時效性低,尤其是直接接觸疫情的地方政府在對疫情有了更明確認知的情況下仍要層層上報,得到指示才做出決策部署,在風險擴散速度如此之快的情況下,防控的最佳窗口期難免錯過。
2.科技群體參與決策缺乏獨立性與多元性。科技群體對于風險的評估是基于研究發現的,應當具有相對獨立性,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在非常規決策中,風險評估往往需要更強的爭議才利于認識到“未知事物”的全貌。決策過程中,不同的科技群體雖然存在爭論,但未能引起重視。決策群體沒有批判性地考查存有爭議的科技知識,其他群體對決策影響效度低。
3.科技群體與決策群體互動的制度化水平與透明度低。雖然能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決策中,但臨時色彩濃厚,缺乏可持續參與的制度保障,是情景倒逼的結果,職能更側重于事中處置與事后應對,不利于危機爆發前做出準確判斷;另外,疫情初露端倪時,科技群體發現其存在并報送決策群體,決策群體雖然公布病例信息,發布確診標準等,但是與科技群體的互動過程,分歧有哪些,對外發布的共識是怎樣形成的,依據是什么等信息缺乏,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知識優勢的發揮。
三、公共危機治理中的科技風險決策機制優化路徑
1.完善決策機構內部的風險決策體系。首先,決策群體應正確評價科技能夠帶來的收益與風險,改變無論常態非常態決策時都把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目標放在第一位的思維定式,尊重科技群體內部的不同意見,結合具體情境做出決策。大數據時代應挖掘海量數據,主動定期監測評估風險,形成風險感知輔助系統,為決策群體從源頭上進行科學決策提供支撐;其次,應創建多部門大數據應急協同平臺,政府主導,科研機構、公民等積極參與,媒體輿論積極引導,實現信息及時共享,協同治理;另外,在風險高度不確定情況下,基于預防原則調整決策基礎,采取行動;最后,及時處理風險要求決策群體尤其是地方政府擁有充分的權力能夠以最快速度進行決策部署,列出事權責任清單。
2.推進科技群體參與風險決策機制制度化。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詢支撐行政決策的風險決策機制,推動重大科技決策制度化,建設高水平智庫并且注重專家結構多元化,研究領域、專業分工不同更有利于全面認知風險;立法保障科技群體的獨立地位,賦予科技群體參與風險決策的權力;科技群體內部制定共同價值規范,科技工作者應保持價值中立;此外,要把維護公眾個人的信息安全列入重要議事日程表,必須立法明確哪些情況下政府或其他機構能夠調用公眾的隱私信息,尤其醫療大數據更是要從國家戰略高度給予保護。
3.構建公眾風險溝通及參與決策機制。公眾是風險的最大承受群體,忽視公眾的心理因素與實際考慮容易導致信任危機,無論是科技群體還是決策群體都應該學會在修正環境中決策,正視公眾理性不信任的積極功效。決策群體應根據公眾所需主動進行信息公開,除了公共危機本身相關信息、應急預案及相關領域如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信息,還可以利用網絡新媒體技術把與科技群體對風險認知的交流過程,分歧、共識、疑問、專業科普知識等都應該向公眾交代清楚,一方面能夠緩解公眾焦慮,降低溝通成本,減少決策執行阻力,另一方面聽取外行專業人士的建議可以避免決策狹隘化,也可以及時回應公眾提供的替代性建議;公眾也應該提升自己參與風險決策的素養與能力,理性對待復雜風險下不斷修正的決策,認識到科技專家知識的局限性,辨別科技風險,更好地監督科技群體與決策群體。
四、結語
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科技化的風險社會,科技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思維方式的同時也內蘊著潛在的、難以承擔的風險。通過分析早期新冠疫情防控的科技風險決策過程,可以看出在高度不確定的風險面前,由于決策群體未能正確認知科技風險、科技群體的研判失誤等延誤了危機治理時機。這就要求決策群體加強內部風險決策體系,在面對類似的公共危機時,重新審視科技的合理性限度,盡可能避免科技風險的發生,科技群體也要制定合理的價值規范,提供更加準確的決策建議,利用當代技術提高決策互動的透明度,以充分發揮公眾的監督及參與決策作用,建構三者動態協調的科技風險決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