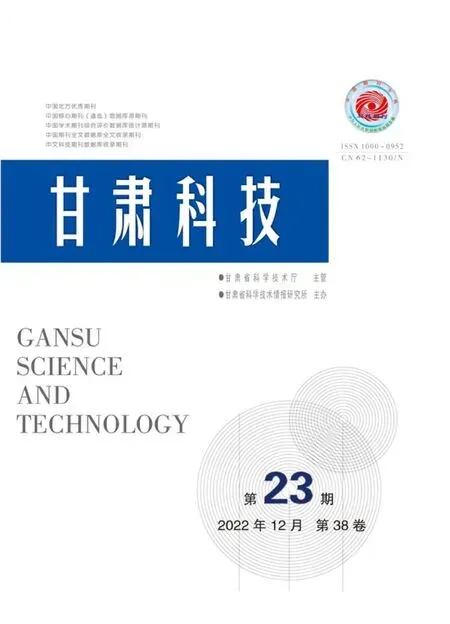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不同降壓目標值對動脈硬化程度的影響*
辛向斌,趙文姬,楊 威,劉凱元,陳 芳
(1.河西學院附屬張掖人民醫院心血管內2科,甘肅 張掖 734000;2.銀川市第一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甘肅 銀川 750000)
原發性高血壓是由遺傳與環境飲食因素在內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以體循環動脈壓力升高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心血管綜合征。隨著社會老齡化的來臨,中老年高血壓患者已成為高血壓控制與治療的主要人群。高血壓作為心腦血管事件的獨立預測因子被國內外研究所證實[1],高血壓所致的動脈血管結構和功能的改變,早期可表現為動脈彈性降低、動脈硬化等,且動脈硬化是高血壓導致靶器官損害的病理基礎。本研究通過2組間肱踝動脈脈搏波傳導速度(baPWV)與踝臂血壓指數(ABI)的比較,探索不同的降壓方案對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動脈硬化程度及外周血管病變的影響,探討優化選擇降壓方案的臨床意義。
1 對象及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于2017年1月就診于銀川市第一人民醫院心內科門診的60~80歲原發性高血壓患者。
1.1.1 納入標準
(1)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包括初診高血壓患者,門診隨訪3次平均收縮壓≥140 mmHg,正在接受降壓治療的高血壓患者。(2)年齡≥60歲。(3)簽署知情同意書。
1.1.2 排除標準
(1)確診繼發性高血壓;(2)收縮壓≥190 mmHg,或舒張壓<60 mmHg;(3)有診斷明確的嚴重冠心病伴不穩定型心絞痛而未經處理的高血壓患者;(4)嚴重心臟瓣膜疾病的高血壓患者;(5)有嚴重先天性心臟病、風濕性心臟病等心功能嚴重不全患者;(6)合并糖尿病而血糖目前控制不佳的高血壓患者;(7)嚴重肝或腎臟疾病;(8)有大動脈粥樣硬化性腦梗死或腦出血病史;(9)近1年內行血運重建手術及6個月內因急性心肌梗死或不穩定性心絞痛住院治療患者;(10)有明確診斷惡性腫瘤病史;(11)不自愿同意參加該項目研究者。
1.1.3 分組原則
按患者就診先后順序編號,將編號輸入完全隨機化系統產生分組(:1)標準對照組:收縮壓SBP(Systolic Blood Pressure)控制于131~150 mmHg(1 mmHg=0.133 kPa),舒張壓DBP(Diastolic Blood Pressure)控制于90 mmHg以下;(2)干預研究組:SBP控制于110~130 mmHg,DBP控制于90 mmHg以下。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資料收集
第一次就診時按前后順序給予統一編號,收集基線資料,最終納入206人入組。以完全隨機分組,2017年2月開始對各組患者在其可耐受的情況下使各組患者血壓達標,隨后根據血壓值達標情況調整用藥,自患者成功納入研究滿1年時,行動脈硬化監測,比較2組患者baPWV與ABI,數據分析得出結論(整個隨訪監測過程中血壓值60%以上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患者為合格研究對象)。
1.2.2 動脈硬化的檢測時間及方法
研究滿1年,由經驗豐富的高級技師統一使用日本COLIN公司生產的VP-1000 Type230型全自動動脈硬化檢測儀檢查,監測前患者仰臥休息5~10 min,根據最近研究[2],本研究通過測定的左右baPWV取兩側最大值做數據分析,以測定的左右ABI取兩側最小值做數據分析(由于失訪,最終人數與前不同)。
1.3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22.0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均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正態分布且方差齊性2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分類變量服從正態分布,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入組資料
(1)入組時2組間在一般測量資料、入組基線收縮壓、既往病史、生活習慣、疾病家族史、入組時血清生化常規、高血壓病程、入組前使用降壓藥物情況等之間比較,除2組間在利尿劑的使用情況組間比較P(b)=0.029<0.05,其余情況在2組間差異均無明顯統計學差異(P>0.05),見表1—表3。

表1 研究對象一般測量資料

表2 入組血清生化常規組間比較

表3 病程及入組前用藥情況組間比較
(2)入組后本研究限制使用A、C、D三類藥物,患者既往口服他汀類藥物及病情需要口服他汀類藥物的患者繼續口服藥物,2組患者在其選擇A類及C類降壓藥物的使用種類組間比較無顯著差異(P(a)>0.05),在選擇D類降壓藥物降壓時組間比較有統計學差異(P(b)=0.029<0.05),見表4。

表4 入組后用藥情況組間比較
3 結果
1年行動脈硬化監測時,2組間血壓符合研究要求,2組間動脈硬化檢測比較,標準對照組與干預研究組baPWV及ABI<0.9,2組間差異均有顯著統計學意義。去除入組后2組間使用利尿劑患者,baPWV與ABI<0.9,2組間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見表5。

表5 動脈粥樣硬化檢測及周圍血管病變發生率組間比較
4 討論
原發性高血壓是一種常見病和多發病,是導致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動脈粥樣硬化是多種心腦血管疾病的病理學基礎,而血壓值是導致動脈粥樣硬化中重要可控的危險因素之一。隨著降壓藥物的不斷發展,心腦血管事件的總體發生率及預后得到改善,但是一些即使血壓控制于當前指南推薦的血壓范圍的患者,其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仍較高[3],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探討高血壓降壓目標值。
2017ACC/AHA[4]高血壓指南指出SBP≥130 mmHg即診斷為高血壓,目前我國高血壓診斷標準仍沿用[5]:SBP≥140 mmHg和(或)DBP≥90 mmHg作為診斷高血壓的界值。在《中國高血壓基層管理指南》(2014修訂版)[6]中指出:老年(≥65歲)高血壓患者的血壓降至<150/90 mmHg,如果能耐受,可進一步降至<140/90 mmHg。段躍興等[7]在老年高血壓患者隨訪中發現,隨訪期平均收縮壓與各靶器官損害參數均有明顯的相關關系,且關聯性最強。因此,把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的收縮壓控制在合理范圍對靶器官的損害有顯著效應。
SPRINT試驗[8]結論顯示強化降壓(SBP<120 mmHg)較標準降壓(SBP<140 mmHg)在心血管病事件發生率降低了三分之一,全因死亡率降低了四分之一;而施仲偉[8]對其研究結果提出質疑。本研究通過對2組患者收縮壓降壓目標值的不同控制,通過動脈硬化檢測,比較對于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在不同降壓方案下的動脈硬化及外周血管病變方面的差異,討論中國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選擇不同收縮壓降壓目標值降壓方案的不同意義。
高血壓導致的心腦血管疾病發生的病理基礎為動脈血管結構和功能的改變,且血管壁彈性的改變較結構發生早,脈搏波傳導速度(PWV)作為反映動脈彈性的經典指標,可以很好的評價動脈管壁擴張性及僵硬度,且有大量研究表明[9]。而PWV的改變是作為血管結構和功能異常的總體反映,而baPWV代表了50%以上的主動脈PWV的變異性[10],國內外大量研究證實baPWV在動脈硬化程度具有重要價值[11],因此,baPWV檢測在高血壓發病過程中對血管硬化具有預測及評價意義;本研究基于2組間基線資料等比較無顯著統計學意義,經排除了利尿劑使用差異的影響后,2組間差異仍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表明本研究差異為其研究方案所致,即在動脈粥樣硬化程度的影響中,通過選擇干預研究組降壓方案較常規對照組降壓方案時,患者受益更為顯著。
經研究證實,作為敏感的診斷外周動脈有無缺血的無創指標之一的ABI,可用于高血壓靶器官損傷的評價以及心腦血管事件的預測[12]。楊進剛和胡大一[13]將ABI與下肢血管造影進行聯合、對比研究發現,可將ABI以0.9為閾值診斷外周血管病變。國內有相關研究表明,以ABI≤0.9作為檢測標準,對外周動脈狹窄≥50%的患者檢出具有較高的特異性和準確度。本研究中,將ABI<0.9作為診斷外周血管病變的標準時[14],P=0.035<0.05,ABI<0.9在2組間有統計學意義。本研究中行多因素相關因素分析顯示獨立相關因素在組間比較差異無顯著統計學意義,因此2組間ABI小于0.9組間差異為本研究方案降壓方案中收縮壓的不同所致。因此,通過對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選擇干預研究組降壓方案較常規對照組降壓方案時,外周血管動脈粥樣硬化性外周病變的發生顯著減低。
綜上所述,在本研究中,對于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的降壓方案中,在患者可以耐受的前提下選擇干預研究組降壓方案較標準對照組降壓方案在延緩動脈硬化程度及減少外周血管病變中更為有效,對于減少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遠期并發癥的發生可能更為獲益。但基于本研究樣本量小(僅限于寧夏地區中老年原發性高血壓患者),且隨訪時間短(僅為1年),對于該結論推廣及證實,仍需全國大范圍的臨床研究、長期隨訪及具體并發癥的比較進一步證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