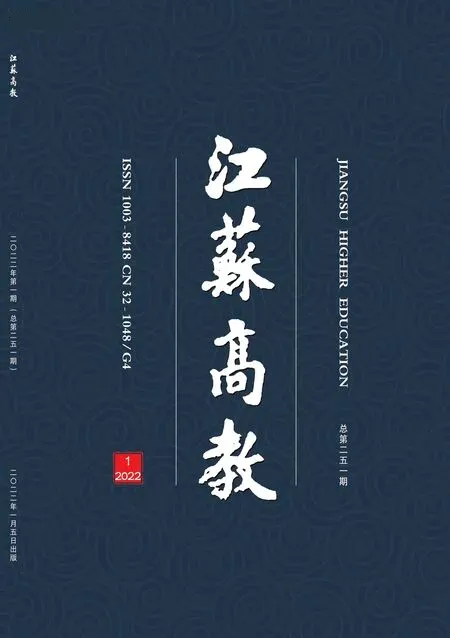新發展階段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及其拐點研究
馬浚鋒,胡陽光
(廣州大學 教育學院,廣州 510006)
一、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可持續嗎
在中國高等教育擴招政策的帶動下,1999-2002年中國高校以年均近30%的擴招幅度迅速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5%,1998 年為9.6%)。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全國普通高校 共2738 所,較1999 年(1071 所)增 長155.65%。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含本科層次職業院校21所),較1999年(597所)增長112.73%;高職(專科)院校1468所,較1999年(474所)增長209.70%。同期,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4183 萬 人,較1999 年(559 萬 人)增 長648.30%,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4.4%,高等教育進入后普及化新發展階段。與此同時,2000-2019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9.03%的幅度高速增長,2020年中國經濟即使受到新冠疫情沖擊,仍然實現2.30%增長,總量101.6萬億元,突破百萬億大關,較2000年增長912.96%。可見,高等教育規模高速擴張的同時,也在持續性地釋放高等教育紅利,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形成高等教育規模效應,拉動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例如,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GDP增速成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邏輯起點,而經濟發展卻又受限于地方人才緊缺,為滿足地方經濟發展的人才需求,一方面,中央政府以權力讓渡的形式開始了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由“單軌制”向“多軌制”轉型,以省級統籌為主,實行央地兩級管理,強調“舉辦權”與“管理權”的分化與下放,通過合并、劃轉等政策將原來部委屬高校劃轉為地方政府主管,161所中央部屬高校劃轉地方管理[1],構建了三級辦學二級管理的舉辦體制和管理體制,推動高等教育管理重心的下移。另一方面,行政發包制下的中央政府財權、事權的下放使地方政府具備籌資能力推進高等教育事業發展[2],地方政府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新大學運動”——各地大學城得以興建,獨立學院、民辦高校、地方大學等新型大學作為地方高等教育發展新興力量涌現,地方高等教育規模得以初步擴張,極大程度地保障了地方人才培養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協調性。
改革開放40年來,高等教育規模空前擴大,我國成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國,極大地提升了國民素質,有力地推進了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3]。大量實證研究也已經驗證了中國高等教育規模通過促進城鎮化水平[4]、提高國家創新能力[5]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拉動作用;方超、羅英姿基于高等教育彈性系數的分析認為,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發展呈現正相關關系,其規模程度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6]。鄭浩和張印鵬指出,1987-2011年間各省高校規模增長對國家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彈性為0.976(P<0.001),即高校規模每增長1%,可以拉動人均GDP增長0.976%;而且,這種拉動作用具有空間溢出效應[7]。高楊等基于1987-2015年31個省份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認為,中國高校數量規模對鄰近省域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8]。對于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規模,李鋒亮、王瑜琪基于2013-2016年不同層次高等教育與經濟增長的回歸結果顯示,本專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規模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067、0.037、0.016[9],結論與吳東姣、馬永紅[10]的研究一致。不可否認,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的高速擴張為社會經濟發展積累了人力資本存量,進而推動了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本文將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對社會經濟增長產生的拉動作用統稱為“高等教育規模效應”。
問題是,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可持續嗎? 如果不能持續,在越過拐點后,高等教育應如何轉型發展? 以往關于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的研究要么缺乏理論基礎,并沒有考慮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系;要么立足于以索洛-斯旺模型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本假定,即社會經濟增長速度所增加的勞動力需求恰好可以吸收人口的增加量,從而可以在充分就業下長期保持穩定增長,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只有受到源于勞動量制約時才會停止[11]。也就是說,以往研究將高等教育規模等同于人口(勞動力)供給,將高等教育紅利等同于人口紅利,忽視了以創新型人才培養為核心的高等教育質量紅利。而在經濟增長理論中,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任何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都會存在拐點,高資源依賴國家的經濟發展在資源匱乏階段極易陷入經濟衰退,即經濟發展拐點,拐點前后出現經濟增長落差[12]。那么,這也就意味著同樣存在高等教育規模效應拐點,即以現階段的高投入、低效益的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方式,傳統依靠規模擴張的高等教育紅利釋放方式的優勢將逐漸消失,高等教育規模的持續性擴張將不能持續地拉動經濟增長,表征為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提高了9個百分點,這既有擴招以后大學畢業生平均能力下降因素的影響,也與大量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力進入市場,產業結構沒有得到調整,需求沒有跟上來有關[13];然而,實際上在于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無法釋放高等教育人才紅利,無法使人力資本的充分利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14]。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實質在于高等教育新舊紅利的切換,即不再依靠粗放式的規模擴張,而是通過創新型人才培養釋放高等教育質量紅利來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構建高質量的教育體系、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優化人口結構,拓展人口質量紅利,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人的全面發展能力”。中央政府在國家整體戰略層面持續釋放出的政策信號是:以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為價值依歸,實現人力資本向人才資本轉換,持續釋放高等教育質量紅利,以創新驅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本文的基本立論是,當高等教育趕超策略和后發優勢帶來的規模效應逐漸喪失、趨近拐點時,以高等教育質量保障、人才培養質量為核心的高等教育內生增長動力的嚴重不足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制約,此時,通過創新型人才培養質量、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釋放的高等教育質量紅利將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為此,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在高等教育地方化趨勢加劇的背景下,哪些省域的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將先后趨近拐點,越過拐點后應如何順應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浪潮,實現高等教育轉型發展,釋放高等教育質量紅利? 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將要求我們建構概念來闡明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及其拐點的內在機理、作用機制,通過數理分析重新認識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及其拐點的現狀,為預警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轉型的臨界點提供實證邏輯。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一)過度教育:“高等教育規模陷阱”
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15]最早由美國教育經濟學家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在《過度教育的美國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一書中提出,對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勞動力市場提供高技能工作以充分利用人力資本的關系提出了若干問題。隨后,相關研究基于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16]、工作競爭模型(Job Competition Model)[17]、配置理論(Assignment Theory)[18]、職業流動理論(Career Mobility Theory)[19]對過度教育現象進行了大量探討。經濟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與收益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認為過度教育源于高等教育人力資本與職業需求的錯配。Maani&Wen對澳大利亞的過度教育現象對勞動力市場影響的研究發現,過度教育下的教育回報率存在個體異質性,澳大利亞本土學生、英語母語國家移民仍然能夠獲得2.7%、11%的收入溢價[20]。Broniatowska基于波蘭企業員工個人數據的回歸結果顯示,盡管過度教育對不同職業群體的工資影響大小不一,但是接受良好教育仍然能夠提高個人收益率[21]。從社會學的視角看,過度教育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現象,它影響著個人的社會階層地位、角色分配,并消解著教育作為一種社會流動機制的作用,Capsada-Munsech 則強調應從受高等教育的個體出發,探索過度教育的個體差異及其是否陷入教育投資陷阱[22]。然而,也有學者爭辯道,過度教育的負面影響大多局限于工作領域,認為教育與就業的錯配會降低工作滿意度和經濟收益,但不會影響整體主觀幸福感或社會分層[23]。由此可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并不必然導致過度教育現象的發生,過度教育的發生率不僅取決于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的供應,還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技術進步則有助于維持市場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24];而且各國過度教育發生率在高等教育各層次存在異質性。
按照西方正統經濟理論的說法,當每個人在他的收入和勞動生產率達到最大的地方工作時,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最大值;然而,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高學歷畢業生增長速度要遠遠超過當前經濟發展所能創造的與其學歷相匹配的職位,供大于求造成了畢業生在對應層次勞動力市場的相對劣勢,加劇了教育過度現象[25],其范圍逐步延伸至研究生群體[26],使人力資本并未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被充分利用。方超、黃斌也認為高校擴招政策在整體上不斷提高了中國勞動力的過度教育的發生率,由1999 年的28.10%上升到2013年的30.32%,勞動力市場無法吸收過量的高階人力資本[27]。張冰冰、沈紅基于2014 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數據認為配置理論對中國過度教育現象更具解釋力,中國過度教育由教育供給和經濟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失衡所導致[28]。這也就是說,只有當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相匹配時,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所帶來的人力資本存量才能得到充分利用、有效轉化為高等教育規模效應,拉動社會經濟增長,否則就會引起過度教育現象,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將陷入高投入、高成本、低效益的“高等教育規模陷阱”;而人力資本存量的充分利用依賴于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增量,根據新增長理論規模收益遞增的基本假設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勞動力市場需求取決于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所帶來的人力資本存量轉化為創新人才資本,拉動技術水平提高。這就意味著,當高等教育規模擴張不能通過高等教育質量轉換為創新性人才培養質量時,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將出現停滯,甚至拐點,此時盲目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將不再能夠對經濟增長產生拉動作用,高等教育發展重心應轉移到人才培養質量上。
(二)有增長無發展:“高等教育內卷化”
過度教育從個體教育投資與勞動力市場供需的匹配程度出發,認為人力資本與市場需求的錯配使高等教育投資邊際效用持續遞減,闡釋了集體性高等教育個人收益率下降將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側面反映出高等教育規模效應的不可持續性以及出現拐點的可能性。可見,過度教育是高等教育規模膨脹和人才培養模式僵化的結果;然而,過度教育對高等教育規模效應的解釋僅僅建立在高等教育個人收益率邊際遞減的基礎上,未能關涉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背后的社會收益率等問題。因此,本文有必要從高等教育投資的個人收益率擴展至社會收益率邊際遞減問題,并對兩者進行理論整合,充分闡釋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及其可能出現的拐點情況。
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盛行于20 世紀8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將經濟發展觀帶入傳統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這兩個概念加以區分使用,強調經濟發展除經濟增長之外,還應包括科教文衛等社會經濟結構的優化,避免社會經濟有增長而無發展[29]。經濟發展觀基于創新的內生增長理論,強調從技術進步、知識創新抵消人力資本邊際效益遞減傾向的角度說明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其基本假設是:如果一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完全是通過單純的要素積累所帶來的,那么在保持一般均衡的過程中,增長將會逐步放緩并趨于停滯,只有依靠技術進步所驅動的增長才是持續的[30]。例如,日本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從后發優勢中受益,具有很強的消化和掌握現代技術的“社會能力”;但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沒有從根本上將其模仿能力改造為真正自主創新的能力,經濟發展失去了動力和方向[31]。換句話說,在經濟增長向經濟發展的轉型過程中,職業結構將朝著高技術人才占更大比重的方向發展;如在納爾遜-菲爾普斯模型中,人力資本是創新的基本源泉,所以產出增長率取決于創新,然后取決于人力資本水平,而非人力資本的增長率[32]。
因此,如果高等教育繼續遵循規模擴張的“有增長無發展”模式,除了引發過度教育的知識失業,甚至是“智力外流”之外,從長期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供給將難以滿足高技術創新人才的市場需求,繼續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將難以形成規模效應,提高社會整體收益,結果導致人力過剩所造成的高等教育資源浪費與社會成本的提高(見圖1)。圖1中,OA 段為高等教育規模效應拉動經濟增長階段,通過技術模仿或外國技術轉移就能將高等教育人力資本吸納進現有勞動力市場需求中;但是,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繼續擴張,高等教育勞動力供給的持續增加,若不能通過知識創新改變現有技術水平,創造新的市場需求增量,就會出現高等教育人力資本過剩,高等教育規模效應也將達到拐點,高等教育投資的社會成本將超過社會收益,造成資源浪費。

圖1 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社會收益與成本
這就意味著,當高等教育規模效應趨近拐點時,高等教育規模的繼續擴張應建立在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效益的基礎之上,否則后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規模的盲目擴張將無法通過創新型人才培養釋放高等教育紅利,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將停滯不前,陷入規模增長而無質量發展的“高等教育內卷化”過程。“高等教育內卷化”的過程伴隨著過度教育的發生,同時也是知識失業的過程,一方面,過度教育導致了知識失業,但反過來,知識失業也助長了高等教育規模的進一步擴張。
如圖2所示,當勞動力市場需求能夠有效吸納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供給時,在考慮個人成本(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個人部分)后,預期個人收益將隨著受高等教育年限(本科→碩士→博士)增加而快速增加;但當陷入規模增長而無質量發展的“高等教育內卷化”過程時,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將爭奪勞動力市場有限的就業機會,那些被擠出的勞動者只好屈身俯就,尋找低一級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傾向于雇傭文化程度更高的勞動者從事原來由低一級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從事的工作。這樣,原本本科畢業生能勝任的工作,現在由碩士畢業生代替了,原本碩士畢業生能勝任的工作,現在被博士畢業生搶占了。勞動者為了防止就業機會被擠占,也為了擠占其他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其博弈最優解就是繼續提高受高等教育年限,那些讀完本科階段的學生現在不得不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繼續學習,那些讀完碩士研究生階段的學生現在不得不進入博士研究生階段繼續學習,如此下去,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就隨即增加了,推動高等教育規模持續擴張,導致高等教育事業建設“有增長而無發展”。

圖2 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個人收益與成本
三、研究設計
如前文所述(見圖3),自擴招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實現跨越式發展,通過增加社會需求和居民消費、帶動教育相關產業發展,進而增加就業機會對國民經濟增長發揮中短期效用[33];不僅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同時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34]。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力資本投資邊際遞減效應的逐步顯現,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力度卻出現了下降[35]。根據理論解析框架判斷,這可能是通過技術模仿帶來的市場需求逐漸飽和,難以繼續吸收高等教育勞動力供給的增量,高等教育規模紅利逐漸喪失,亦即高等教育規模效應趨近拐點;當高等教育未能通過人才培養、知識創新促進技術進步、創造勞動力市場需求增量時,有限的勞動力市場需求便加劇勞動者對就業機會存量的爭奪,進入“高等教育內卷化”過程。因此,為適應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以及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撐,客觀上要求提高我國勞動力的素質水平和人力資本的知識技能水平。高等教育紅利的釋放將由高等教育規模效應轉向質量效應,通過創新型人才培養,推動知識創新改變現有技術水平,創造新的市場需求增量。那么,在我國高等教育步入大眾化階段后,高等教育規模效應的表現力如何? 后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規模效應是否仍有較大利用空間? 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將于何時趨近拐點? 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在現有技術水平下,我國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當高等教育規模紅利逐漸喪失,不同“省情”下的各省域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很可能出現拐點。為了檢驗上述假設,本文采用2003-2019年我國境內31個省域(直轄市、自治區)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計量估計,并通過引入二次項函數構建相應的經驗模型,以期考察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非線性影響。

圖3 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及其拐點的理論解析框架
(一)模型構建和變量說明
在實證分析中我們常常假設因變量和自變量存在線性關系,然而在復雜的現實情況下,非線性關系可能才是變量間的一般表現形式。為描述這種非線性關系,應用經濟學領域通常在進行計量模型設定時加入平方項甚至是高階項,其中二次函數模型是在含有自變量一次項的基礎模型上,引入其二次項來刻畫自變量與因變量間的邊際效應[36]。當一次項和二次項均顯著為正,則因變量隨自變量增加而遞增;當一次項和二次項均顯著為負,則因變量隨自變量下降而遞減。而當一次項為正,二次項為負,則回歸模型具有倒“U”型的拋物線形態,即自變量存在一個值為正,此時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為零,在此點之前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為正,此點之后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為負;反之亦然,當一次項為負,二次項為正,則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存在正“U”型的非線性關系。典型的面板模型設定方式為:

式1中,Y、X、Z 分別為因變量、自變量和控制變量。α和β為的線性關系系數,它們的符號和顯著性是本文關注的核心,γ為控制變量的待估計系數,C 為常數項,ε為誤差項,i、t則分別是省份和年份。
根據研究假設,改進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與新古典經濟主義的傳統模型,構建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面板計量模型,基本表達式如下:

本文的因變量為經濟增長指標,研究采用各省份人均GDP來表征,為消除異方差問題對參數估計結果產生的偏誤,本文對該變量進行取自然對數處理,記作Lnpgdpit。自變量為高等教育規模指標,研究采用各省份高等學校本、專科階段畢業生數量和本、專科在校生數量分別占地區年末常住人口數量的比重來衡量,分別記作gradsit和stusit。本文的線性關系系數α1、α2是gradsit的一次項和二次項,β1、β2則是stusit的一次項和二次項,若兩個自變量估計系數的一次項顯著但二次項不顯著,則表明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呈簡單線性關系;若自變量估計系數的一次項顯著為正而二次項顯著為負或一次項顯著為負而二次項顯著為正,則表明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呈非線性關系,即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在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邊際遞減或邊際遞增的“規模拐點”。本文的控制變量為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一系列指標,具體包括:勞動力投入指標laborit,以各省按工商登記注冊的就業人數占地區年末常住人口數的比重來表示;資本投入指標capitalit,以各省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地區GDP的比重來表示;財政自主度指標fdit,以各省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例來表示;產業指標indusit,以各省第二、三產業占地區GDP 的比重來表示;人口指標popdenit,以各省人口密度來表示;其余向量與符號同式1一致。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下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情況
(二)實證結果
為了更好地判斷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拐點,研究引入高等教育本、專科畢業生規模和在校生規模的二次項構建面板數據的非線性回歸模型,并采取逐次添加變量的方式進行計量回歸,以減少實證結果的有偏估計。由于傳統的回歸元模型是將因變量與自變量的聯系嚴格限制成線性的,若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則須進行拉姆齊省略變量的回歸設定誤差檢驗(Ramsey RESET),又稱增冪回歸檢驗。由表2可見,我們對僅包含自變量一次項函數的回歸模型進行Ramseys RESET 檢驗,結果均在1%顯著水平下拒絕無遺漏變量的零假設,即原約束條件不成立,認為回歸模型的自變量存在高次項;同時,所有模型均通過Hausman 檢驗,且模型整體隨著變量的增加而具有較好的擬合效果。表2所展示的是具體回歸估計結果。

表2 回歸模型估計結果
結果顯示,模型(1)至模型(5)中的高等教育領域本、專科畢業生規模、在校生規模的一次項系數均為正,而且兩者都在1%統計學意義上顯著,表明高等教育的規模效應對地區經濟增長確實發揮著積極的促進作用,這一結果也與傳統的觀點相似。而在模型(6)至模型(10)中,我們的核心自變量一次項系數均為正,但二次項系數均為負,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高等教育本、專科畢業生規模、在校生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可能是一種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有且存在一個臨界拐點,即在臨界值之前的高等教育規模效應能夠發揮功用,隨畢業生與在校生規模的提高將有利于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但當這種規模超過臨界值之后,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可能會出現邊際遞減。在納入一系列控制變量的影響下,本、專科畢業生規模和在校生規模的線性估計系數也能獲得一致的結果,而且隨著將所有的變量全部添加至模型內,模型擬合程度也逐步提升,表明這一模型的解釋力度越強,高等教育發展在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可能存在“規模拐點”。此外,絕大多數控制變量都在不同程度的顯著水平下呈正值,符合經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結論,這說明勞動力和資本的存量、地方財政自主程度、第二三產業產值以及人口總量能夠顯著拉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由于模型中加入了自變量的二次項,我們可以通過變量間的非線性特征來確定臨界值,但必須考慮其估計系數的統計含義和樣本數據的取值范圍。由圖4可見,兩個曲線轉折點均在高等教育本、專科畢業生規模和在校生規模的數據區間內,且轉折點兩側均有足夠樣本,這說明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規模拐點”具有經濟意義。其中,畢業生規模和在校生規模的臨界值都分別小于其自身均值,即絕大多數省份處在倒“U”型曲線的左半支,高等教育規模效應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積累紅利對經濟增長依舊顯著,但這一規模效應對經濟增長的邊際影響呈遞減趨勢。進一步分析,對高等教育發展的“規模拐點”進行估測。一般而言,任意二次函數模型的轉折點的基礎公式為自變量一次項的系數與其二次項系數的兩倍之比的相反數,即TP=-(α1/2α2),對此可得出我國各省域在其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拐點情況,其中畢業生規模估計值約為0.486%,而在校生規模約為3.168%。具體來看(見表3),研究發現對于如貴州、山西等多數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及如廣東、浙江等部分經濟發達但高等教育發展較為薄弱的東部省份,這些地區的高校本科畢業生和在校生總量尚未及“規模拐點”,意味著這些省域仍可以通過擴大本區域高等教育規模助推地區經濟增長;而對于一些高等教育強省如北京、上海、湖北等地,在樣本年份期間已出現臨界拐點,甚至超越拐點的跡象,這說明了該類地區高等教育規模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接近或出現邊際遞減的態勢。

圖4 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系圖

表3 各省高等教育“規模拐點”的分位情況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基于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相關研究提出“高等教育規模效應”這一概念,結合包括內生增長理論、發展經濟學在內的經濟增長理論,從過度教育、有增長而無發展的“高等教育內卷化”角度闡釋了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及其拐點,并構建了計量模型對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及其拐點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邁向普及化階段的過程中,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拉動作用,存在高等教育規模效應,且在1%水平下具有顯著性,在控制了一系列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后,該結論仍然有效,與以往研究結論一致。
第二,在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計量模型中加入自變量(高等教育畢業生數量和在校生數量)的二次項后,回歸結果顯示自變量一次項估計系數為正,二次項估計系數為負,驗證了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兩者關系呈現倒U 型關系,證明了高等教育規模效應拐點的存在,省域本、專科畢業生規模估計值約為0.486%,而在校生規模約為3.168%;并通過U test穩健性檢驗,且在1%水平下具有顯著性,在控制了一系列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后,該結論仍然有效。這一實證結果支持了上述理論解析框架,導致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出現拐點的原因,筆者認為可以有以下幾個方面:①過度教育導致了知識失業,高等教育個人收益率邊際遞減;②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無法轉化為知識創新、技術進步,陷入規模增長而無質量發展的“高等教育內卷化”的過程,高等教育社會收益率邊際遞減;③在現有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高等教育人力資本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漸趨飽和,通過技術模仿、技術轉移產生的紅利逐漸喪失,當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后的人才培養無法促進知識創新,釋放高等教育質量紅利時,高等教育規模便無法促進技術水平進步,創造勞動力市場需求增量,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就會越過拐點,呈邊際遞減態勢。
第三,自變量高等教育規模(畢業生規模和在校生規模)的臨界值都分別小于其自身均值,樣本數據絕大部分落在左側區間,說明目前我國大部分省域的高等教育規模效應仍處于拐點左側,高等教育規模擴張仍然能夠促進地區經濟增長。我國部分省域的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已經趨近拐點,標志著這些省域正處于由經濟高速增長向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重要階段,預警著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由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高具有迫切性。我國個別省域的高等教育規模效應已越過拐點,意味著該省域高等教育規模的繼續擴張已無法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釋放高等教育質量紅利成為其發展重心。
基于以上研究發現,筆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其一,適度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繼續優化高等教育布局結構。一方面,鑒于我國大部分省域的高等教育規模效應仍處于拐點左側,由此可見,中國高等教育規模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十四五”規劃也提出60%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目標,說明現階段通過擴大高等教育規模,仍然能夠拉動地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系圖表明我國各省域高等教育發展程度與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源自高等教育布局結構的失衡;“211”“985”“雙一流”等重點大學建設政策的實施,使我國大學在迅速趕超世界一流的同時也加劇了大學身份固化,造成了區域間政策資源、財政資源、人才資源的不充分、不平衡,使高等教育布局結構的固化造成的省域高等教育資源不均成為高等教育質量差異化發展的一種常態,在現行的評價體系下,極易陷入“以資源配置為中介變量的結構質量化或質量結構化”的惡性循環[37]。因此,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要求優化高等教育布局結構,補齊省域間高等教育質量差異的短板,針對過度教育、知識失業、智力外流等現象,通過制度、政策引領“人才東南飛”轉向“人才西南飛”“人才西北飛”,實現人力資本的有效利用,延緩高等教育規模效應拐點的到來。
其二,加強高等教育質量監測,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機制耦合度。院校學術質量、教師教學效果與科研產出、學生學業表現是21世紀全球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三大主題,源于高等教育規模快速擴張時期社會各界對質量多樣性、穩定性的擔憂,1999年《博洛尼亞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推動了歐洲各國政府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政策的出臺,參照美國第三方評估體系,加速了歐洲各國質量保障系統、標準的成型,開啟了高等教育質量監測的嶄新篇章。新發展階段下,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心將由規模擴張、外延發展,轉向結構優化、內涵發展、質量提升,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其核心問題是在理論與實踐上解決由于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機制內各要素(高等學校分類、教育評價、資源配置)耦合度不高導致的無序競爭、資源配置不合理、辦學效益不夠高,高等教育整體水平和質量尚未很好滿足中國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矛盾。耦合度是指機制內各要素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要素功能得以充分發揮,機制得以有效運行。一個耦合度較高的質量保障機制意味著高等學校分類、教育評價、資源配置等要素的有效整合,導向功能、發展功能、調控功能有效發揮,保障人才培養質量和知識創新。因此,迫切需要圍繞質量保障機制耦合度的提高重構體現新發展階段特征、釋放高等教育質量紅利的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