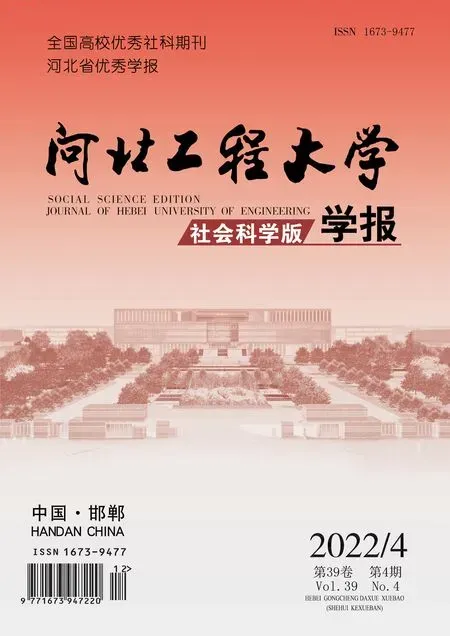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幸福悖論”現實表現與歸因及我國防范策略探析
張青衛, 吳楠
(河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401)
幸福始終是人類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標,是人對當下生活高度認同的心理狀態,對幸福的不斷追求時刻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然而,隨著生產力的迅猛提升和物質財富的不斷累積,當下人們卻陷入了“幸福悖論”的困境,即更多的財富并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甚至出現相反的趨勢。近年來,眾多經濟學家試圖通過構建幸福指數等經濟學手段來說明并破解這一悖論。但幸福歸根到底是人的幸福,脫離現實鮮活的個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條件來刻板地衡量幸福注定是存在一定缺陷的。我們應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對幸福悖論進行分析,洞察當代人的現實生活需要,深刻剖析幸福悖論的現實表現、內在根源及防范幸福悖論落地我國的策略,為切實增強人民生活幸福感、創造新時代的美好生活提供有效的策略支持。
一、深刻分析“幸福悖論”的現實表現
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于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論文《經濟增長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民的幸福》中提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盡管經濟體量的增長帶動了國家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改善了生活質量,現代經濟學更是構建于“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個核心命題之上,但財富收入的增長與幸福感提升并不同步的這一現實與人們通常以為的“富人一般應該比窮人幸福指數高”的現實相矛盾,我們把這一現象稱為幸福悖論或“伊斯特林悖論”。幸福悖論的主要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發達國家的幸福感并未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財富增長所帶來的并非是幸福提升而是貪欲以及占有大量資本并未感受強烈幸福。
(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幸福指數高于發達國家
從國際間比較來看,居民收入與幸福感的關聯程度不高。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在單個國家內部,例如從美國這個國家自身的數據調查和研究結果來看,收入達到某一水平,幸福感確實是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強的。富人報告的平均幸福感高于窮人。按這個調查結果進行猜測和推斷,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的國家,幸福水平就更應在世界范圍內名列前茅,但這種猜測與一系列現實的數據結果并不相符。
首先,部分發達國家的整體幸福水平并沒有隨GDP上升而同步增長。伊斯特林以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證明,1972至2002年的經濟增長和國民的整體幸福感下降之間呈負相關。他指出:“美國從1972年以來人均GDP雖然從17000美元增加到34000美元,但主觀幸福感的平均值卻呈下降趨勢”。[1]自2017年起,美國近五年的GDP排名始終保持世界第一,但美國在2020年5月下旬的民意調查顯示,僅14%美國成年人感覺“非常幸福”,而2018年同期這一比例為31%。同時,根據2022年世界幸福報告顯示,美國以6.977的幸福指數排名第16位。自2018年起,連續五年位列全世界第一幸福國家的芬蘭,五年來卻從未進入過全球GDP排名的前二十名。不僅如此,這種經濟發展水平和幸福水平不相等的情況還發生在其他發達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人均收入增長了6倍,但國民幸福程度卻無明顯變化;根據2022年最新數據,GDP總量排名第三的日本,其國民幸福指數卻排在全球第56位。
其次,部分發展中國家能夠位列各類世界幸福指數排名前列。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所提供的全球50個國家從1981到2008年的調查數據以及美國綜合社會調查所提供的1972—2010年的數據顯示,在發展中國家中,伊朗等多數國家呈上升趨勢。在英國新經濟基金在2021年發布的《幸福星球報告》中,位列第一的是中美洲的一個發展中國家,哥斯達黎加。第二名是努瓦阿圖,同樣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幸福并不完全取決于GDP總量和經濟發展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幸福指數要高于發達國家。
(二)財富增長所帶來的并非是幸福提升而是貪欲
物質需求的滿足是幸福感的重要來源,個人的經濟實力的增強能夠不斷滿足其物質需求,從而催生自身幸福感,然而現實卻表現為幸福感的背離。馬克思說過,“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2]這足見物質基礎對于人類生存的重要作用。生活于現實世界,每個個體都必然對生活條件產生需求和欲望,其中物質欲望是最基本的。在社會生活資料極其匱乏的時代中,對于財富和生產生活資料的大量占有必然能夠帶給主體巨大的心理滿足,從而衍生出巨大的幸福體驗。然而這種幸福體驗并不貫穿于人類社會的所有發展階段,自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以來,生產力呈爆炸式發展,絕大部分人所能擁有的物質財富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而人們的幸福感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大幅提升。
在西方現代化進程加速演變的過程中,經濟和財富的增長帶給人們的是欲望的不斷擴張而非幸福感的不斷增長。經濟增長的同時,人們對于物質的需求標準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更新發展。不僅如此,由于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人們的物質欲望呈指數倍增長。盡管社會大生產的繁榮、分工的精細化和科學技術的應用都使得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人的可支配收入也不斷增多,但是人們的欲望也在進一步增多。曾經只想要一臺電視機,如今卻想要更多、更新、更大、功能更全的科技產品。與此同時,人們在與他人生活狀況對比時產生的心理落差也使自身的物質欲望愈發膨脹。眾所周知,幸福作為人的一種感覺,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由于個人的收入、工作等差異,其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必然存在差異,這就導致部分人群由于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有所提高所帶來的滿足感在周圍環境的影響下被不斷削弱,并隨之對生活產生了比之前更高的期待與欲求。由此,無止境的物質欲望和現實生活狀況形成了無法填補的鴻溝。
(三)占有大量資本并未感受強烈幸福
在近幾十年的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中獲利最多的主體是握有生產資料等資本要素的群體。不同于廣大工薪階層的勞動者僅僅依靠薪水來維持生活,擁有更多資本就意味著收入來源范圍更為寬廣,比如可以依靠投資、租金等多種途徑獲取大量經濟利益。從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更多享樂方式和獲取幸福的手段的邏輯來講,占有更多的資本要素將會收獲更加強烈的幸福感,但現實卻表現為資產者處在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相互分裂的狀態之中。
毫無疑問,占有更多的資本代表著物質需求已實現一定程度的滿足。從馬克思的視角來看,資產階級的整個人生都圍繞著對資本的向往以及經濟活動所展開,對物質財富的貪欲和極度渴望是資本家一切活動的出發點。這促使著資產階級不斷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和財富積累。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化的條件下,資產階級通過無情殘酷地剝削無產階級來不斷創造剩余價值,實現資本增殖和自身物質財富的大量積累。這同時也導致了工人在勞動異化狀態下的物質幸福和精神幸福雙重的缺失。不僅如此,雄厚的財力也為資本家帶來了較高的社會地位,這使他們享受著大量旁人所不能及的社會資源,資本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物質享樂者。
然而,擁有更多的資本并不等同于精神幸福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資本家的精神幸福與物質幸福之間存在一定的落差。“除了對金錢資本的向往之外,資本家沒有自己的人生。在這種意義上,資本家自身也發生了異化。”[3]資本家的巨大物質財富及其精神空虛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實生活中依靠資本要素獲取財富的群體盡管過著紙醉金迷的享樂生活,但這種過于富足的物質生活恰恰折射出其精神生活極度貧瘠的現實狀況。在無限膨脹的逐利欲望驅使下和商品拜物教的影響下,對金錢和商品的占有被視為人生的最高價值,他們每個人都將占有更多的商品奉為圭臬。然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4]由于商業競爭,資本家難免不生出忌妒心,導致這種占有還具有排他性,即希望只有自己占有最大限度的財富和生產資料,這種利己主義思想和行為都限制了其精神層面的豐富程度。不僅如此,資本家不斷揮霍手中的財富,購買奢侈精致的物品,但卻在這種看似享樂的活動中陷入空虛。最終,物質財富的大量堆積卻帶來了精神財富的匱乏。
二、科學探究“幸福悖論”的現實歸因
盡管有許多經濟數據和社會現象都在某種程度上佐證了幸福悖論的可能。但幸福作為一種主觀感覺,難以完全依靠冰冷而又機械的經濟模型來測量,更無法通過單一的物質滿足而得到充分感受。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悖論,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錯誤價值觀的引導、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背道而馳以及勞動的異化和缺位。
(一)錯誤價值觀誤導了幸福取向
正確的價值觀能夠帶給人積極向上的情感體驗,而歪曲的價值觀則會阻礙人對幸福的感知力。人在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的生存發展和主觀感受都必然孕育于社會關系中,無法脫離社會共同體而獨立產生和存在。馬克思曾多次講到共同體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5]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而集體主義價值觀能夠有效增強人的幸福感知力,充分保障這一目標的順利實現。但西方資本主義推崇個人英雄主義,鼓吹個人私有利益神圣而不可侵犯,忽視集體的力量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作用,減弱了人民對真正幸福的感知能力。同時,一個國家的價值觀是對特定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恩格斯就曾在《反杜林論》中提到:“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6]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前提下,人們所奉行的價值觀主要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價值要求,這種價值歸根到底是為資本家服務的。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財富盡管取得了大幅度增長,但卻不斷造就現實生活中人的異化狀態和不幸福的現象。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造就了異化狀態,削弱了人對幸福的感知力。這種異化狀態首先表現為人和人的異化。商品拜物教將人之間的聯系從自然和社會關系改造成了物與物的關系。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催生了精致利己主義,以自我為中心、唯利是圖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高度分立狀態,主體間關系的惡化和不和諧的社會環境在極大程度上遮蔽了幸福的來路。其次是人和自然的異化。資本的核心目的就是為了獲取剩余價值并實現資本增殖,但增殖行為無法憑空產生,“資本的擴張必須通過物質化來實現,而物質來源離不開一定的生態空間支撐。”[7]資本主義國家始終以犧牲生態環境的方式來換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將生態環境作為一種免費的饋贈而肆意使用,從而造成了全球變暖等生態環境問題。人在惡劣的生存環境當中自然難以感受幸福。最后是國家間關系的異化,西方普世價值是資產階級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它始終強調其內在優越性繼而將其作為統一的文明范式進行推廣甚至強加于人。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的活動,最終將會導致國家之間的關系惡化甚至引發戰爭。在這種異化狀態中,人必然無法感到切身的幸福。
(二)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反向發展阻礙了幸福感受
物質財富充分涌流本應為精神財富的積累和幸福感的提升創設現實可能性,但現實卻是人被物質財富所奴役。物質需求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理想愿景和現實期盼都會促使人產生相應的物質需求,這種需求指導著人們自身的行為,激勵主體進行自覺的活動。物質財富是主體生命機能正常運轉的保障。可以說,沒有了物質財富,人的生存和生活便無從談起,更無法談及幸福與否。然而,在經濟飛速發展的當下,人們將對物的占有視作幸福的唯一來源,對工具理性的追捧日益瘋魔化,認為科技無所不能。事實上,過度的物質欲望是資本編織的美好陷阱,并非人的真實需要。“資本邏輯為美好生活樹立起虛假的、片面的評判標準,扭曲了一些人的生活觀念,即人們的真實需要完全被消費欲望所取代。”[8]在資本邏輯的裹挾下,泛娛樂化、拜金主義、消費主義、幻想不勞而獲等心態主導了人們的大腦,人們過度追求奢華無度的物質生活條件,以淺薄空洞的感官享受替代高尚深刻的精神境界的陶冶熏陶,只注重物質財富的積累而忽視精神世界的塑造,逐步為“物”所奴役。物質欲望不斷膨脹進而擠占精神世界的空間,人的精神世界日益空洞化、淺表化,只能將幸福和快樂寄居在對商品的購買所帶來的感官享受上,甚至造成社會關系的惡化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由此產生的幸福感猶如曇花一現,無法得到持久和深刻的滿足。
部分群體沉溺于物質和感官享受,忽視精神滋養,存在精神需求異化現象。人與動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不僅受到動物本能的支配,而且具有自身的思想,其行為是自覺的有意識的。人的多種物質性活動也不斷受到精神需求的支配。當物質需求的滿足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需求便躍升為人在需求層面上的主要矛盾,對精神幸福的渴求便成為人的活動的主導因素。然而,隨著數字化技術的成熟與運用、智能設備的易得性和便攜性以及媒體內容的新穎性。人們日漸沉迷于低俗化、碎片化、娛樂化的媒體內容,缺少深入思考,也很少有意識去培育深層次的文化素養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很容易出現迷茫和無所適從的精神空虛。不僅如此,精神世界的提升必然伴隨著主體自身的自由全面發展。個人內在都具有自我發展的需求,而這種需求的滿足必然需要充足的時間。馬克思曾談到:“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必需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么,他就還不如一頭役畜。”[9]但由于當代階級壓迫和剝削相較以前更加深入和隱蔽,使得人們將本該用于創新發展的閑暇時間用于加班,過度勞動的現象嚴重,導致人們的精神世界嚴重匱乏,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導致幸福的缺失。
(三)勞動的異化和缺位屏蔽了幸福體驗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異化現象嚴重,勞動者難以通過勞動確證自身的本質力量。勞動本應該是個人本質力量的體現,是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更是能夠為自身帶來無盡財富的必要途徑。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勞動卻成為僅僅能夠維持其生存的手段和禁錮自身發展的枷鎖。可以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不再體現為人的本能活動,社會勞動分工的日益精細化使每一個勞動者基本上都具有特定而相對狹隘的技術,這對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當下,勞動形式得到巨大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生產活動能帶給勞動者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機會,看似輕松靈活的工作形式實質上掩蓋了無限延長的工作時間和不斷機械重復的繁瑣工作,造成了現代人更深層的異化困境。在原有的工業資本主義階段,馬克思就曾指出過其對于勞動者生產志趣和生產才能的無情摧毀,如今,在科技支撐下的數字資本主義階段更是“將原本可供勞動者在勞動時間以外自由支配的身體,在算法的組織和控制下異化為可操縱的外表,將人自身異化為數字化生產活動的一環。”[10]在這種條件下進行勞動,是在不斷的否定自我,很難為人們帶來確證自身本質力量的幸福之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11]馬克思曾根據上個世紀的狀況總結道:“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12]
當前社會不僅存在勞動異化,還存在勞動缺位現象,人們在享樂主義中迷失自我、逃避勞動,導致幸福感不足。“幸福感是在勞動和奮斗中產生的,勞動的價值在于創造,為社會發展而創造價值賦予了人類勞動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13]享樂和享樂主義不同,享樂是人的自然需求,而享樂主義則是資產階級的人生價值觀,他們過度沉湎于物質享受,把享受凌駕于勞動實踐這一人的本質之上。馬克思曾指出:“享樂哲學一直只是享有享樂特權的社會知名人士的巧妙說法。”[14]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背景下,資本家的財富源于對無產階級無盡的剝削。在此前提下,盡管資本家的物質財富不斷攀升,但由于財富來的太過輕易,難以體會到親手創造勞動成果的獲得感。同時,在普遍的勞動異化狀態下,勞動者也無法感受到工作的樂趣和意義,在自身的勞動中難以收獲認同感和榮譽感,逐漸對工作感到倦怠,企圖逃避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環境所大肆宣揚的享樂主義熏陶下,人們把追求個人感官享受視為人生的最大目的,只顧當下不顧未來,逃避艱苦,不愿奉獻,懼怕奮斗,只愿沉溺于肆意揮霍和無盡享樂所帶來的泡沫式享受,最終將會導致精神上的痛苦和社會發展的凝滯。
三、積極探討西方幸福悖論現象扎根中國的防范策略
幸福悖論并不是人類社會本身存在的悖論,而是當下在私有制經濟發展過程中認識出現偏差而產生的現實社會問題。部分人群以物質享受和占有為快樂,以追求物質利益為人生的最高價值目標,忽視精神上的涵養和進步,甚至造成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和經濟上的貧富懸殊。可以說,在西方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人民幸福本就不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加之個人主義價值觀和異化狀態的廣泛影響,出現幸福悖論這類經濟發展高水平與生活幸福背道而馳的現象是必然的。當前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踏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偉大征程,在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謀求高質量發展,都是為了保障民生、實現人民幸福。通過積極探討和分析西方發達國家內部所出現的幸福悖論的現實表現及現實歸因,為我們積極防范幸福悖論在我國滋生、切實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提供了借鑒意義。要積極防范幸福悖論在我國滋生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以集體主義的價值追求支撐幸福愿景
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中蘊含著集體主義價值觀念。馬克思曾在書信中指出:“‘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5]事物是否有價值取決于它是否能夠滿足主體的需求,人們會本能性地趨近與自身價值相近或對自身有利的事物而遠離對自身不利的對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幸福悖論產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以資本邏輯為核心所產生的錯誤價值觀的引導。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只關注個人利益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始終關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生問題。馬克思曾指出,在未來社會“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16]鄧小平也在南方談話中曾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7]共同富裕的重點在于共同,是不落一人的富裕,內含有保證公平正義的集體主義觀念,體現了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共同富裕的集體主義意識。
我們要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以集體主義意識消解利己主義價值觀,推翻幸福悖論滋生的思想溫床。共同富裕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理想愿景的偉大歷史目標和構想,不斷推進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能夠極大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鏟除幸福悖論滋生的可能性。在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應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在向著共同富裕偉大歷史目標不斷穩步邁進、艱苦奮斗的過程中,每個個體不僅能體會到自身本質力量不斷涌現和得到確證的滿足,也能感受到逐步創造自身美好生活的幸福感。
(二)以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足的協同進步熏陶幸福感受
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協同進步方能催生堅實持久的幸福感。幸福感受無法脫離物質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幸福由物質單方面決定。盡管擁有各式各樣的商品和大量的金錢能夠給人們帶來快樂,但這種感覺終究是短暫、片面、易逝的,由單一物質刺激所帶來的滿足感將會在對物質利益的長久追求過程中被逐漸消解。整體而全面的幸福感受必然需要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的統一發展。人與動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有思想精神需要。馬克思將人的需要分為三個層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在物質財富能夠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人必然更加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進步。改革開放四十多年,黨帶領人民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人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極大滿足。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8],人民對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表明,幸福感的提升必然需要物質幸福和精神幸福協同進步。
防范幸福悖論,我們應在為人民服務中增強精神上的美好感覺,從而促進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協同進步,進一步提升幸福感。馬克思曾說過,“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的、真正偉大的人物……歷史把那些為共同目標工作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稱為最偉大的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9]馬克思的觀點不僅體現了他個人偉大無私的追求,更揭示了幸福感的根源就在于對他人、對社會的奉獻以及為人民幸福而奮斗的過程當中。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幸福和社會幸福并不是獨立的,個人幸福是社會幸福的基礎和表現,社會幸福則表現為一種整體性、總括式的廣大群眾的最大幸福。從這個角度來說,為人民利益和幸福作出貢獻的過程必然能為個人帶來精神上的巨大充實,進而增強個人的持久而深刻的幸福感受。我們要把個人的理想追求同民族復興、國家昌盛、人民幸福充分融合,在為人民服務中體現我們的人生價值、感受幸福生活。
(三)以奮斗幸福觀的積極踐行引領幸福追求
真正的幸福在勞動中方能得到充分涌現。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我的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20]勞動是個人本質力量的生動體現,現實的人生存生活必然無法脫離勞動。作為人本質力量的生動體現,實踐活動能夠帶給人極大的精神享受。每個人都對美好生活有著期待和設想,這種美好愿景和既定目標是個人勞動奮斗的精神推動力,在勞動中不斷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不斷接近自身的美好生活目標時,人們的內心就會涌現出巨大的幸福感。“經驗告訴我們,經歷越大的艱難險阻,付出的辛勞越多,日后我們反而更能收獲持久的幸福感。”[21]不論是出于生產的目的還是追逐自身目標的需求,只要個人在實踐活動中付出大量努力,哪怕最終并未達到本身期待的結果,但這個過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帶給個人極大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我們要大力倡導樹立奮斗幸福觀,在勞動奮斗中創造和感受幸福,以真切的幸福感抵御幸福悖論的怪圈。西方幸福悖論產生的原因之一是勞動的異化,人們的勞動及其成果都不屬于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無法感受勞動所帶來的樂趣。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是勞動的主人,更是奮斗的主導者,是美好生活的實踐主體。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奮斗本身就是一種幸福。只有奮斗的人生才稱得上幸福的人生。”[22]中華民族的歷史充滿了曲折坎坷,幾百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受苦受難的屈辱史,然而中華民族幾經磨難卻仍薪火相傳的核心密碼就在于從不輕言放棄,始終堅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向著自身的美好生活愿景努力奮斗。同時,奮斗也是激發幸福感的堅實動力。“奮斗本質上就是展現人類革命性力量的可靠手段,能夠幫助人們區別于動物,確證人之為人的本質力量,促使人們感受‘身為高級動物’的自豪。所以,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奮斗不僅能給人帶來物質財富,也能給人帶來精神愉悅,產生幸福感。”[23]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機遇和挑戰同樣增加,樹立奮斗幸福觀能夠激勵我們直面困難,勇于用頑強拼搏之姿打破發展困境,為滿足自身美好生活需要創造充足的條件,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積聚磅礴力量。在致力于實現中國人民普遍幸福的中國夢而勞動奮斗的過程中,人民的幸福感必然得到充分涌現。
幸福悖論歸根到底是對經濟決定論的現實反駁,對于幸福的感受理應建立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協同進步的前提之上。實踐證明,在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國家當中,能夠保障勞動者勞有所得,使人民在富足的勞動果實和充實的精神感受中體驗幸福。當前,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全新歷史起點上,對幸福悖論的深入分析能夠揭示幸福的獲取途徑,有助于充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個人生活的幸福感。相信,隨著人們朝著美好生活努力奮斗行動的現實演進,幸福悖論的怪圈必然不會降落在中國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