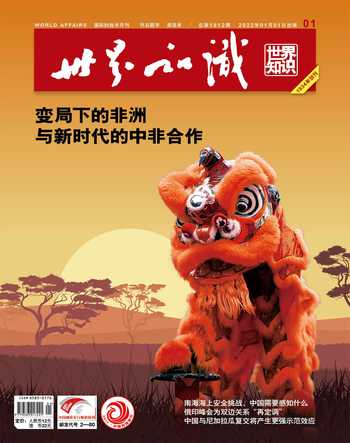變局下的非洲:危與機并存
余文勝
2021年非洲政治與安全形勢加劇動蕩,系統性危機開始顯現。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非洲經濟與社會危機凸顯,并向政治與安全層面傳導,固有的地緣矛盾、民族沖突和社會問題被激化。面對嚴峻復雜的政治安全形勢,非洲國家的擔憂加深,合力應對地區挑戰的意愿和行動進一步增強。
2021年,非洲共發生五次政變,馬里、幾內亞、蘇丹各發生一次成功奪權政變,尼日爾和蘇丹分別發生一次未遂政變。乍得總統代比陣亡后,軍方任命其子穆罕默德·代比為新總統并領導軍事過渡委員會,也被反對黨指責為“軍事政變”。政變曾是非洲國家權力更迭的主要方式,據相關研究數據,自上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非洲共發生了200多次政變,其中約一半成功奪權。2000年非洲統一組織(非洲聯盟前身)通過《洛美宣言》,規定任何“違憲更換政府”的成員國將被暫停資格。之后,非洲政變一度趨于減少,由前40年(1960年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四次,下降到后20年(2001年至2019年)的平均每年兩次左右。但2021年初迄今,非洲發生的政變和未遂政變次數明顯高于此前的平均水平。非洲政變“卷土重來”的原因,從內部看,疫情難控、經濟低迷、治安惡化導致社會矛盾加重;從外部看,外部對馬里、幾內亞等國政變僅口頭譴責,幾乎未實施制裁。國際危機組織專家認為,西方的默許為軍政權制造了有利氛圍,可能在非洲帶來“示范”效應。
一方面,地區大國成為“震中”。2021年,埃塞俄比亞、南非、尼日利亞等非洲大國政治與安全形勢出現惡化。作為非盟總部所在地、非洲“政治心臟”的埃塞陷入內戰已逾一年,埃塞政府軍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提人陣”)之間的沖突不斷升級,美英法等多國撤僑。埃塞內戰愈演愈烈,主要有幾個方面原因。一是部族矛盾難解。埃塞有80多個部族,奧羅莫族、阿姆哈拉族和提格雷族紛爭不斷,歷史積怨較深。“提人陣”執政時期(1991~2018年)實行的以部族劃區自治為基礎的聯邦制和現總理阿比推行的中央集權均導致部族矛盾激化,地方分離勢力四起。二是交戰雙方立場強硬,均拒絕停火和對話。三是外部勢力強力干預。美國和歐盟借提格雷人道主義危機批評阿比“侵犯人權”,中斷對埃塞的援助并實施制裁。鑒于各方立場難以調和,埃塞內戰有擴大化、長期化趨勢。2021年南非多地因前總統祖馬入獄,引發1994年結束種族隔離制度以來最嚴重的騷亂,造成多人死傷。騷亂是南非部族、黨派、階層之間矛盾日益激化的結果。此外,新冠疫情也加劇了南非經濟社會矛盾,2021年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32.6%,貧困人口激增。尼日利亞面臨極端組織襲擊、牧民與農民沖突、分離運動、有組織犯罪等多重挑戰,全國范圍內殺戮、綁架、搶劫事件頻繁發生,社會治安嚴重失序。尼總統布哈里在重壓之下尋求國際援助與合作,2021年4月要求美軍非洲司令部從德國遷往非洲。
另一方面,安全痼疾持續發酵。作為“非洲動蕩之弧”的薩赫勒地區局勢加速惡化,馬里接連兩次政變,乍得總統和叛軍交戰陣亡。在中部非洲,中非共和國大部分地區的武裝沖突持續,已影響到整個地區的穩定。剛果(金)東部安全局勢有所惡化,盤踞當地近30年的非法武裝暴力活動十分活躍,導致該地區出現新的難民潮。在西非,幾內亞灣仍然是全球海盜劫船和綁架活動的高發地區。據國際海事局報告,2021年1~9月,幾內亞灣海盜事件約占全球30%。在東非,埃塞、埃及和蘇丹圍繞尼羅河水資源的地緣博弈加劇。復興大壩爭端成為埃塞和東非地區穩定的重要威脅。南蘇丹盡管于2020年2月成立了過渡聯合政府并確定了基爾總統與前最大反對派領導人馬沙爾分享權力,但2021年該國安全局勢仍然動蕩不寧。
與此同時,2021年非洲經濟復蘇乏力,貧困人口增多,不平等加劇,社會矛盾激化,誘發社會動蕩和沖突。一是社會抗議增多。2021年,南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安哥拉等多國發生大規模游行示威,塞內加爾等國出現多年來罕見的社會騷亂。二是治安形勢普遍惡化,多國綁架、搶劫、襲擊等惡性案件頻發。南非放寬封鎖限制后犯罪率急速升高。尼日利亞多個州接連發生針對外國和當地公民的武裝綁架和襲擊事件。此外,烏干達、安哥拉、莫桑比克、納米比亞、博茨瓦納等國治安形勢也出現惡化。
“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利用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混亂和發展受阻,在非洲加速拓展勢力,主要呈現以下特點:一是暴恐烈度增強。2021年以來,非洲重特大暴恐事件多發,3月21日,尼日爾西部塔瓦大區多個村莊遇襲,137名平民死亡。5月30日,剛果(金)東部伊圖里省兩村莊遭襲,至少55人喪生。6月4日,布基納法索北部薩赫勒大區一村莊發生恐襲,造成超過160人死亡,這是2015年以來在該國發生的傷亡最慘重的襲擊事件。二是襲擊數量增加。據“武裝沖突地點和事件數據”(ACLED)項目的統計分析,預計2021年非洲與極端組織有關的暴力事件至少達5110起,比2020年創紀錄的4956起增加3%。三是地理范圍擴大。此前非洲極端組織活動主要在薩赫勒中部、索馬里、乍得湖盆地和北非地區,但2021年向西非沿海、中部非洲和東南非進一步拓展,如貝寧首次發生暴恐襲擊事件,烏干達接連發生爆炸襲擊,向來穩定的莫桑比克也淪為非洲新暴恐基地。四是“伊斯蘭國”加緊滲透。聯合國反恐負責人沃隆科夫指出,2021年初“伊斯蘭國”的分支“大撒哈拉伊斯蘭國”已在馬里、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殺害數百名平民,“伊斯蘭國中非省”在中部非洲尤其是莫桑比克的擴張將對地區安全產生“深遠影響”。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2021年經濟同比增長3.7%,低于發達經濟體的5.2%和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的6.4%。圖為南非約翰內斯堡街頭。
面對疫情、恐情、社情疊加下日益復雜嚴峻的政治安全形勢,2021年非洲國家領導人將安全問題作為主要關切,加大了合力應對的力度。在東南非,在2021年6月召開的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南共體)特別峰會上,南共體16國元首批準向莫桑比克派遣南共體待命部隊。在中部非洲,11月30日剛果(金)與烏干達軍隊發起聯合軍事行動,旨在打擊剛東部叛軍“民主同盟軍”。此外,盧旺達、喀麥隆相繼派遣軍隊支持中非共和國政府,打擊該國反政府武裝。在西非,地區組織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西共體)對政變多發十分擔憂,多次宣布制裁措施,以促使馬里和幾內亞恢復憲法秩序。在東非,地區國家和組織積極展開斡旋,謀求在埃塞俄比亞實現停火。
由于經濟結構單一,非洲對外依存度高,疫情對外貿與物流沖擊巨大,2021年非洲經濟復蘇相對緩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2021年經濟同比增長3.7%,低于發達經濟體的5.2%和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的6.4%。同時,非洲次區域經濟表現不一。據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東非和北非國家經濟多元化水平較高,發展韌性較強,其經濟增長都在4%以上。西非國家多數依賴資源出口,經濟表現不佳,2021年僅同比增長2.8%,西非經濟的“領頭羊”尼日利亞經濟增長僅為2.6%。南部非洲礦業、農業等地區支柱產業恢復較快,各國平均增長達3.2%,南非在2021年經濟增長預計可達5%。
在疫情沖擊下,長期困擾非洲的經濟痼疾更加凸顯。一是財政預算十分緊張。非洲國家政府財政創收手段有限,疫情暴發以來,非洲國家出口收入、稅收、僑匯等均大幅下降,政府幫扶中小企業、實施社會救濟和刺激經濟所能調動的資源十分有限。據世行統計,自2020年1月以來,非洲國家刺激經濟恢復的財政預算平均僅占GDP的2.8%,而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分別為17.3%和4.1%。二是債務問題依舊嚴峻。疫情暴發后,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非洲債務,并采取行動減緩其債務負擔,但非洲國家公共債務依然高企。2021年平均水平估計維持在56.6%左右,較2020年的65%有所改善,不過仍高于疫情前水平。據IMF統計,超半數的非洲低收入國家已經陷入債務困境或者處于債務高風險之中。三是社會不平等加劇。據非洲開發銀行數據,2020年疫情已經導致約30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2021年將約有3900萬人口陷入貧困。同時,受新冠疫情、氣候變化、供應緊張等因素影響,2021年以來非洲面臨食品價格進一步上漲壓力,導致該地區總體通脹上行風險加劇。
為應對新冠疫情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非洲國家采取多項措施,以刺激經濟復蘇和可持續發展。首先是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南非、尼日利亞等高度依賴資源能源出口的國家加快經濟轉型,啟動再工業化和能源改革計劃,以改變經濟高度依賴外部環境的脆弱性,刺激經濟更快復蘇。二是持續推進數字化。疫情下,電子商務、在線教育、移動支付等新經濟業態在非洲蓬勃發展,為遭受疫情打擊的傳統行業提供了新發展機遇。為支撐數字經濟的發展,非洲各國也在加緊完善網絡通信基礎設施,并將發展數字經濟納入國家長期發展規劃。數字經濟將有望成為非洲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非洲大陸自貿區建設也將帶動非洲海運市場的發展。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的研究發現,如非洲大陸自貿區協定實施順利,并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項目,預計到2030年,非洲船舶貨運量將從現在的5800萬噸/年躍升至1.32億噸/年。在全球海運加速復蘇的背景下,非洲大陸自貿區建設將提升非洲海運的效率,進一步釋放非洲貿易和運輸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