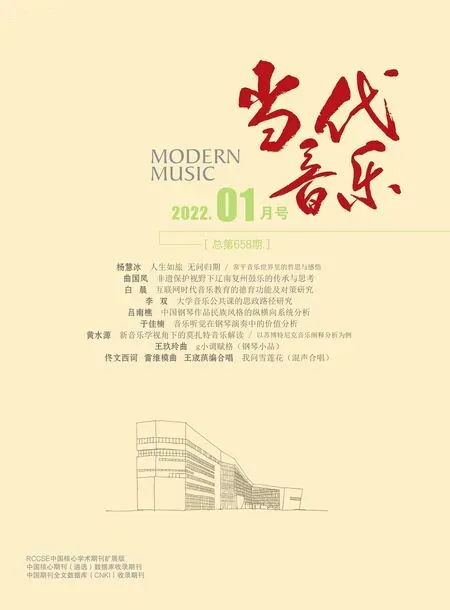古典主義與浪漫派的Turning Point(轉折點)
——論貝多芬晚期鋼琴奏鳴曲Op.110的啟示
彭逸偉 陶 陶
鋼琴奏鳴曲作品110作為貝多芬晚期奏鳴曲三部曲之一,其中深刻的哲學性與作品的藝術性奠定了古典主義浪漫派音樂作品的開端,從而開啟了西方音樂史的新紀元。這部降A大調鋼琴奏鳴曲創作于1821年,收錄于他的手稿系列阿爾塔利亞197。同系列還收錄了同樣創作于1821年的D大調莊嚴彌撒的部分樂章和最后一首鋼琴奏鳴曲作品111。這些作品中的宗教性與矛盾性,不得不引起演奏者與學者們關于貝多芬晚期創作生涯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的思考。作為一名人生每時每刻充滿著抗爭意味的音樂“斗士”:失聰,與侄子的家庭紛爭以及當時所處的經濟政治環境無一不令貝多芬的生活雪上加霜。根據西方音樂史所描述,在經歷了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1789—1815)后,整個歐洲籠罩在戰后的陰影下,社會經濟蕭條使得大型音樂作品的創作受到了困難與阻礙。另一方面,1802年貝多芬生理上的聽力問題日漸嚴重。[1]種種因素促使了其創作生涯意義上的扭轉,從創作中期的英雄與愛國主義到晚期作品中自我意識的覺醒,藝術性中自我靈魂的探索以及人類自我精神的升華。在本文中筆者結合鋼琴奏鳴曲110的音樂理論中的實例淺析貝多芬晚期鋼琴奏鳴曲的特性。
一、音樂作品中的連貫性與整體性
早中期的貝多芬奏鳴曲大部分為傳統意義上的奏鳴曲曲式,一般為快慢結合的三到四個樂章。而這部晚期奏鳴曲110則被許多學者探討為一首完整的曲式結構作品,原因在于其曲式結構的平衡以及音樂內容的連貫。[2]這里的平衡性體現在一二樂章與第三樂章結構上的分布。連貫性則首要通過如下幾個方面呈現。
(一)調性變化
首先,調性,在整部作品中穿針引線:第一樂章起始于降A大調,第二樂章結束于f小調又通過coda轉折到F大調,第三樂章開始于降b小調通過左手低音八度降C-降F-降G-G-降E連接轉折,在降E大調和旋停留兩小節后引出了降a小調的慢板(Adagio)。第一賦格部分又回到了降A大調,貝多芬在第一賦格結尾通過等音轉調從降A大調的屬和弦降E轉為升D,而后又馬上戲劇性的半音下移到還原D從而連接到第二個詠嘆調的g小調,詠嘆調的結尾處又從g小調轉為G大調,最后在曲尾的tempo primo回到了降A大調。

續表
整部作品通過調性循環的創作手法時刻提醒著聽眾和演奏者之前的篇章,從而將整個奏鳴曲融合為一體。
(二)節奏標記
其次,節拍在整部奏鳴曲的連貫性中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一樂章與第三樂章的賦格片段為3/4和6/8(Fugue)。為了使樂章之間的持續性延續到最后一個樂章,貝多芬將6/8拍減半為12/16,但同時增加了2倍音符的時值為十六分音符。這種節拍細微的改變對于聽眾來說,整體節奏的變化保持了一致,但對于演奏者在音樂處理方面需要理解音符時值的變化,以十六分音符為持續低音增加一種局促,緊迫之感,而降a小調詠嘆調更呈現一種歌劇色彩,增添悲鳴之意。在第三樂章賦格和慢板篇章的銜接處,貝多芬標記了“poi a poi di nuovo vivente”,“nach und nach wieder auflebend”皆為一點一點逐漸的回歸到生命與生氣的意思,在這里對于貝多芬標記含義的理解也需要演奏者具有高超的音樂技巧來詮釋。另外值得演奏者注意的是在第一賦格與慢板的詠嘆調再現部的銜接處,貝多芬使用g小調的以八分音符琶音的形式順聯到詠嘆調并標注緩慢的(ritardando)使快板的賦格順暢的過渡到如歌的詠嘆調,同時也使賦格(Allegro ma non troppo)與詠嘆調(Adagio ma non troppo)在聽覺效果上融為一個整體。嚴謹的貝多芬在每一次音樂時值或主題的改變都進行了音樂表情記號的標注如第168到169小節以及174小節的“回到第一主題的節奏”(tempo primo)。盡管第三樂章貝多芬在各種歌劇與樂器創作的形式之間轉換如宣敘調,詠嘆調,賦格,但尾章賦格變奏(174小節tempo primo)的最后一次呈現以第一主題的快板節奏伴隨著對賦格主題的音符時值的伸縮結束了整部作品,這在某種意義上加強了最后一個樂章的持續性、完整性和戲劇性。
(三)主題
如果我們將整部作品看作一個變奏曲曲式,第三樂章的第一次三聲部賦格主題可以看作第一樂章主題的倒置,而二次賦格的主題則為反向倒置。賦格主題為(降A-降D-降B-降E-C-F-降E-降D-C),第一樂章主題為(C-降A-降D-降B-降E-降D-降E-F-降E-降D-C),第二賦格主題為(D-A-C-G-B-升F-G-A-B)。第一樂章主題為下行三度上行四度循環,賦格主題為上行四度下行三度音程的循環,賦格第二主題為下行四度上行三度音程循環。由此第一樂章與第三樂章構成了一個圓圈形式,同時,貝多芬對主題進行了音時值的伸縮變化與組合,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演奏難度。四度音程作為動機同時也出現在第二樂章第41小節,在雙小節線后右手旋律以四度音程下行模進的方式伴隨左手上行三度一直持續到第95小節[3]。另外,第二小節右手高聲部旋律為(C-降B-降A-G-F-F-E),第三樂章詠嘆調主題旋律可以被看做二樂章主題在降a小調的變奏(降E-降D-降C-降B-降A-G)。這種將第一樂章主題以變奏形式再現穿插在二三樂章中,使整個奏鳴曲以變奏曲的方式成為一個整體。貝多芬晚期作品樂章之間的開頭結尾銜接處較為模糊,不同于其他部分早期中期奏鳴曲,樂章之間有非常清晰的分界。例如第二樂章結尾,貝多芬并沒有使用一個較為完滿的句號,而是使用了一個轉折號過渡到了第三樂章。
譜例1:
第一賦格主題

第一樂章主題

第二賦格主題

二、高度藝術性
(一)戲劇沖突
在晚期的貝多芬奏鳴曲中呈現出一種高度的戲劇沖突性與張力。在早期與中期作品中,貝多芬一貫的音樂表現形式為有強烈對比的強弱表情記號,例如在作品13悲愴和作品57熱情中的極強或極弱。晚期的作品則更傾向于純粹和抽象的音樂表達形式,在他晚期的奏鳴曲和弦樂四重奏中,一方面有著喜劇元素,同時又具有嚴肅的悲劇色彩。[4]這種新高度的作曲形式以多元化的形式在音樂藝術形態中體現。貝多芬在第一樂章中所渲染的如詩如歌般的氛圍實際上為作品109整體氛圍的延續。第一樂章開頭標記的“Moderato cantabile molto espressive”喻義第一樂章為如歌的,純凈的,具有表現力,動聽的。第一樂章展開部結尾處的c小調以下行音階伴隨著右手優美的旋律而并沒有過多渲染c小調本身的黑暗色彩。第二樂章主題引用了維也納的民謠“我們的貓有許多小貓咪”,第17小節到24小節引用了另一民謠主題“你是愚蠢的,我是愚蠢的,我們都是愚蠢的”。對于這些民謠旋律的引用使第二樂章充滿了幽默諧謔的色彩。而第三樂章的氛圍突然從第二樂章的諧謔轉為行板充滿了神秘氣息的孤獨感,宣敘調recitative旋律里的嘆息和悲鳴,詠嘆調Arioso更是充滿了黑暗和悲傷。這里的詠嘆調Arioso借鑒了莫扎特的歌劇《女人皆如此》“Cosi fan tutte”中第一幕“Di scrivermi ogni giorno”(每天寫給我)的創作手法,[5]其右手旋律以一種不流暢的,破碎的,甚至有窒息的意味去表達一種疲累和悲傷。如歌的第一樂章,幽默諧謔的第二樂章,突如其來在第二第三樂章的戲劇性轉折,第三樂章復雜的賦格與悲傷的宣敘調的轉換這些都使得這部晚期奏鳴曲達到了貝多芬藝術造詣以及當時時代背景下音樂創作的巔峰。
(二)宗教意義
作品的結尾樂章分別使用的兩種創作手法:歌劇的借鑒與賦格的運用,互相交替一直到結尾結束在降A大調主和弦上從某種意義象征著曙光的到來,靈魂的救贖。賦格在巴赫的作品中體現著宗教教義,同時巴赫認為一切音樂都應該歌頌上帝。如果詠嘆調旋律象征著痛苦和苦難——“Passion”耶穌受難曲,那么賦格則可以被比喻為來自上帝的救贖。1822年同時期完成的莊嚴彌撒所體現的宗教意味同樣可以體現在其晚期奏鳴曲三部曲中。根據Kevin Class的文章指出第一樂章開頭的主題在高聲部和低聲部的交替可以被視作為十字架的象征。[6]同時第一賦格主題與莊嚴彌撒羔羊頌中“Dona nobis pacem”具有相似之處:兩個賦格主題都構建與上行四度,6/8拍,以及后續詠嘆調的出現。而在“Donna nobis pacem”中貝多芬寫道“prayer for inner and out peace”“祈禱內心于外在的平和”,[7]這句話也同樣可以體現在作品110的結尾處。
(三)和聲的使用
貝多芬在古典學派教科書般的作曲框架內大膽使用了復雜的和聲和調性的變化,而和聲的重要性在音樂效果的影響力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第三樂章從113的降A大調轉為114小節的g小調中,貝多芬使用了和弦降A大調屬和弦降E-G-降B-降D,我們同時可以將此和弦同音轉調認作為是g小調的日耳曼增六和弦升C-降E-G-降B,緊接著從降E半音下移到D-G-B,此時我們已經在g小調的屬和弦上。對于聽者來說,和聲直接半音下移的戲劇化轉調引導出與賦格篇章完全不同的宣敘調的氛圍與情感。另外,貝多芬大量使用持續性的低音區渾厚的和弦,使低音的音響效果與高音區如歌般的旋律區分開來(譜例2)。這種在當時并不常見的對渾厚的和聲效果使用的作曲手法也被用于貝多芬最后一首鋼琴奏鳴曲中。同時對于音色變化的要求,貝多芬標注了最明顯具有提示性的弱音踏板的使用,使演奏者與聽者能夠明確對于音色變化的把握。
譜例2:

貝多芬音樂作品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僅作為純粹的古典主義,而是充滿了浪漫主義前衛的藝術思想,正如他作品的復雜性在當時的文化背景環境下并不能被部分人所理解,而貝多芬給予的回復則表示他的藝術作品是留給后人所品鑒。根據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對于浪漫派的釋義,浪漫派將自己與黃金古典時期割裂開來,站在貝多芬所為后世遺留下充滿矛盾與斗爭的藝術里程碑上,從而成為藝術形式的新主宰。[8]一些學者將莫扎特定義為純粹的古典時期作曲家,而貝多芬則被認為是浪漫派作曲家的始祖,可以說貝多芬的古典主義作品真正深刻地展示了浪漫主義作品的真諦,為整個后期所有的浪漫派作曲家開啟了先河,并影響了一代德意志作曲家,如舒曼、勃拉姆斯、柏遼茲、瓦格納等。同時,貝多芬十分尊崇巴赫與亨德爾,在他的信件中他曾寫道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是音樂中的圣經,貝多芬也充分的學習借鑒了古典樂派作曲中嚴謹的對位法。正是這種將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創作手法使貝多芬成為西方音樂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他大量使用了變奏曲式,穿插賦格在他的晚期奏鳴曲中(Op.101,106,109,110,111)。而這部晚期奏鳴曲110中其賦格的創作之困難,更是可以從他的手稿的反復修改程度中得以體現。
結 論
貝多芬在距離他離世的六年之前創作了這部作品,作為他的晚期代表作,降A大調鋼琴奏鳴曲在整體結構上可謂標新立異,無論是從彈奏技巧、和聲、音樂下暗涌的強烈情緒的表達,音色的想象力,結構的把握,節奏的掌控等都為演奏者增加了詮釋這部作品的難度。作為貝多芬的晚期作品之一與他其它眾多晚期作品一樣,遠遠超出19世紀大環境下聽眾們的評判標準,當人們還在尋找合適的傳統標簽來定義貝多芬的作品時,他的音樂與藝術價值已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后世作曲家們,貝多芬真正意義上重新定義了19世紀音樂創作的新概念。
注釋:
[1]Burkholder,J. Peter,Donald Jay,Grout,Claude V. Palisca.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10:568—573.
[2]Lockwood,Lewis.Beethoven:the music and the life.New York:W.W.Norton,2003:Chapter18.
[3]Rosen,Charles,Ludwig Van Beethoven.The classical style: Haydn, Mozart, Beethoven.New York:W.W. Norton,1997:497—506.
[4]Hughes,David G.,Thomas Forrest,Kelly.A history of European music:the art music tradition of Western culture.New York:McGraw-Hill,1974:371—375.
[5]Drake,Kenneth.The Beethoven sonatas and the creative exper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108—110.
[6]http://www.kevinclass.com/artists#/masterclassbeethoven110.
[7]Lowrance,Rachel A.“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Musical Offerings,Department of Music and Worship,1 May 2013,doaj.org/article/f9f404fb93f44e9ea02257c231008ea7.
[8]Sadie,Stanley,George Grov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1980:598—599.
——貝多芬和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