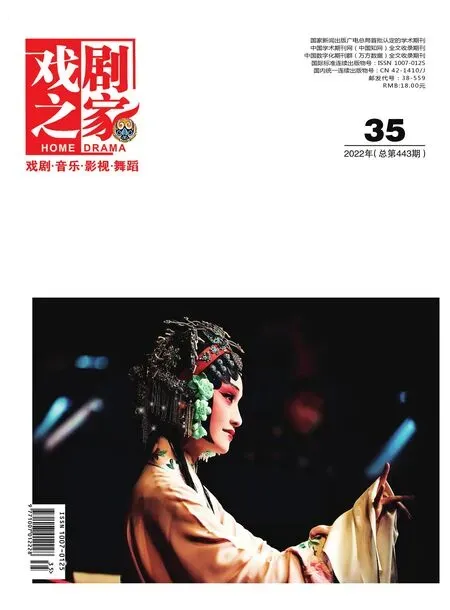方言電影的媒介表征與文化意涵
黃卓航
(湖北工程學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方言作為一種文化表達方式,具有特定的理論內(nèi)涵。我國地域廣袤,多種文化交織,呈現(xiàn)出多元并存的語言文化生態(tài)。方言作為地域性語言,繼承了文化的核心部分,承載著政治、經(jīng)濟、文化意涵,既是一種語言變體,又是一種文化傳播載體,被廣泛應用于電影藝術(shù)。方言電影以原生態(tài)的方言對白、地域鏡像豐富了電影語言內(nèi)涵,同時,方言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在從普通話到方言、從語言到影像的表達過程中,促進了主流媒體與非主流話語的融合。以方言為研究對象,以方言電影作為參照,通過分析方言電影的媒介表征和文化意涵,可以進一步挖掘方言電影的研究價值。
一、方言電影的媒介表征
(一)從普通話到方言
語言是文化的顯性表達。經(jīng)過口語、文字和印刷的傳播后,在當下的電子信息時代,語言作為基礎(chǔ)傳播媒介的價值更加突出。普通話和方言雖然是同一種語言,但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媒介效應。中國自春秋時期就有共同語和方言的區(qū)分。歷朝歷代對共同語的稱謂不盡相同,春秋時代稱其為“雅言”,漢代形成“通語”,明代推崇“官話”,辛亥革命后推行“國語”,20 世紀50 年代初確定“普通話”并推廣沿用至今。“普通話”是指以北方話為基礎(chǔ),以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而形成的共同語。共同語的形成有賴于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其對于傳播思想、普及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共同語的普及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選擇。在信息媒介迅猛發(fā)展的當下,以普通話為代表的話語體系表現(xiàn)在各種影音媒介中,其所表現(xiàn)的文化語境和社會潮流亦反映出普通話被廣泛關(guān)注和接受的事實。因此,語言觀可看作文化觀的凝縮。經(jīng)過長期的傳播實踐,普通話的敘事結(jié)構(gòu)被更加廣泛地應用在電影中,而方言敘事的立足點局限在人物的身份前史中,作為構(gòu)建人物身份關(guān)鍵的方言,反而較大程度受到地域背景的干擾。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方言作為語言基底,又表征著地域文化。“方言作為一種相對于普通話的地方性語言,忠實地反映了一個地區(qū)的歷史文化習俗,也維系著一個地域的人民共同的心理認同感,是各地民俗文化的直觀體現(xiàn)”[1]。因此,對于方言的闡釋和發(fā)現(xiàn),仍是我們探尋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徑。在電影中,方言符號的所指想象,展現(xiàn)為泛化的地域時空和鄉(xiāng)土人文,展現(xiàn)了建立在文化根脈上的語言基底。電影對白由于受到主觀創(chuàng)意和客觀條件的影響,或多或少都帶有方言特征,即便是普通話譯制片,也帶有北方方言成分,這既與演員的臺詞訓練有關(guān),又取決于劇中人物的身份特征。我國的方言形態(tài)多樣,分布廣泛,可以分為七大方言區(qū),在系屬上可以分為四個層次:方言、次方言、土語和腔,顯現(xiàn)出復雜的語言特征。
從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來看,相較于普通話的“陰陽上去”,不同地域方言的不同音韻結(jié)構(gòu)形成了更加豐富的語音流變,在電影中更容易引發(fā)戲劇效果。電影中的喜劇包袱往往與方言有關(guān),經(jīng)過處理的方言對白因獨特的語音調(diào)值,造成了聽覺的回響,進而在電影敘事中加強了聲音形象的構(gòu)建。換言之,作為電影的語言載體,方言既指向一種明確的語言對白,又作為聲音符號喚醒著觀眾的方言記憶,方言敘事進一步擴展了聲音的表達,引發(fā)了觀眾對聲音的記憶鉤沉。
因此,長期以來,普通話和方言作為語言媒介,被應用于電影創(chuàng)作,成為基本的聲音元素。但在大部分電影作品中,用普通話進行敘事是主流,方言只能作為人物身份特征零星地出現(xiàn)在人物對話中。這體現(xiàn)在話語體系的文化指涉上,因為“普通話是官方的權(quán)威的,方言是大眾的邊緣的。地域性的語言變體形式取代普通話出現(xiàn)在大銀幕上,反映的是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邊緣文化不滿現(xiàn)狀、顛覆權(quán)威、建構(gòu)自我、提升地位的訴求”[2]。因此,在媒介傳播視角下,方言介入電影,形成了方言電影這種質(zhì)樸本真的類型電影,其媒介特性使觀眾重新聚焦電影中的方言表達。電影廣泛使用方言,進而升格成方言敘事,即是非主流話語體系對主流普通話文化圈的挑戰(zhàn)。
(二)從語言到影像
電影是一門以聲畫為載體的綜合視聽藝術(shù),包含語言、聲音、文字等多種元素,兼具傳統(tǒng)媒介與新興媒介的多重屬性。在電影發(fā)展史中,幾個比較重要的歷史時期(如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都有方言電影的位置,這說明,電影作為一種媒介,本來就具有包容性,而方言正是這種包容性的體現(xiàn)。在從語言到影像的過渡中,豐富的媒介手段將地域文化具象化,使地域、鄉(xiāng)土、記憶等概念深嵌于影像之中。具有電影作者風格的導演如姜文、賈樟柯、畢贛等,都在方言電影中構(gòu)建了豐富的地域鏡像。當電影登上熒幕時,“也就意味著電影中的方言被更多的觀眾知曉,而這些方言所指向的北京大院、山西縣城、香港都市等不同地域的文化體驗也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3]。
另一方面,方言電影展現(xiàn)了電影的本性,“確立了它作為一種媒介的物質(zhì)屬性,這些媒介功能在人主觀性的驅(qū)使下被分配至各個經(jīng)驗領(lǐng)域,因而呈現(xiàn)出我們所能看見的各種感性形式,也因此,電影獲得了一種“寓言裝置”的地位:精神的力量加在電影媒介的物質(zhì)性之上”[4]。對于觀眾而言,精神的指歸在于電影想象的延宕。當電影以豐富的影像媒介傳播時,“觀眾不再處于‘觀影’與‘現(xiàn)實’的切換狀態(tài),而一直處于“虛擬/現(xiàn)實”的在場狀態(tài)”[5]。
因此,電影想象形成的第一階段是方言的物質(zhì)性表達,語音語調(diào)勾勒了人物身份,充分展示了電影敘事環(huán)境。當語言媒介強調(diào)身份在場時,人物的前史就暴露在了熒幕之上。此時的觀眾通過方言語調(diào)深陷與人物相呼應的人生經(jīng)驗中。第二階段是影像的媒介渲染。影像是元素的聚合,除卻聲音的呼喚,影像本身就能呈現(xiàn)豐富的環(huán)境視態(tài),“電影作為一種獨特的電子媒介,其中的地理空間對媒介地方感的塑造有著不可缺少的作用,一方面,電影中地理景觀的塑造加深了受眾心中的地域形象,另一方面,媒介通過對城市景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再現(xiàn),凸顯其地方感”。[6]在傳播學視域中,電影的媒介功能不僅體現(xiàn)了電影本體的諸多元素,還在符號生成、影像互動的傳播環(huán)節(jié)形成了完整的觀影體驗。
二、方言電影的文化意涵
(一)人與社會的沖突與和解
“方言”可分為社會方言和地域方言,這體現(xiàn)了“方言”的社會性和地域性。方言電影的影像空間凝縮著地域特征,其標志性的方言對白不僅深入刻畫了人物,還生動展示了地域環(huán)境。而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里,方言電影聚焦社會鏡像,展現(xiàn)社會規(guī)訓中的人生百態(tài)。在經(jīng)典電影《黑駿馬》中,白音寶格麗離開草原后遙望故鄉(xiāng),導演通過蒙古長調(diào)引發(fā)觀眾對家鄉(xiāng)、人生的思考和對理想的尋找。在城市文明與草原文化沖突時,白音寶格麗固執(zhí)地回歸鄉(xiāng)土文化,在自我規(guī)訓中找尋理想和現(xiàn)實間的平衡,最終達成了城市與鄉(xiāng)土文化的和解。
而電影《人生大事》聚焦武漢市井,在影像空間中構(gòu)建了充滿煙火氣的巷道,講述了莫三妹和武小文從相互抗拒到認同依賴的溫情故事。影片的核心即通過莫三妹的家業(yè)實踐展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喪葬文化觀,探討了現(xiàn)代文化中人倫價值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隨著現(xiàn)代都市的崛起,家族關(guān)系、鄰里關(guān)系慢慢失去淳樸的底色,顯現(xiàn)出異化扭曲的傾向,隨之呈現(xiàn)出失序的社會文化風貌。莫三妹的武漢方言和武小文的四川方言折射出不同地域的語態(tài),在影像空間中形成想象的共鳴,傳遞出城市文化融合后的包容精神。電影中人物的內(nèi)心矛盾和外物的擾亂,歸根結(jié)底是人與社會的抗爭與和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方言電影的文化底色是大眾共同創(chuàng)造的。當方言電影的影像空間展現(xiàn)出城市和鄉(xiāng)土的文化圖景,并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動態(tài)時,觀眾便透過熒幕生起社會語境下的電影想象。
(二)宏大敘事與思想闡發(fā)
方言電影的創(chuàng)作往往體現(xiàn)著導演的思想態(tài)度,而方言正是復現(xiàn)觀念和重構(gòu)記憶的絕佳載體。方言電影的視聽時空凝結(jié)著導演的思想,反映著導演的哲學或美學觀,如張藝謀、賈樟柯等導演在電影中廣泛使用方言,并在服、化、道、攝、錄、美、演等方面細致把握,形成了導演的身份標簽。張藝謀作為五代導演,在電影中呈現(xiàn)了諸多經(jīng)典的造型設計和畫面構(gòu)圖。在《紅高粱》中,他凸顯了兩種鮮明的顏色:黃土地的黃色和紅高粱的紅色。黃色代表黃土高坡的豪邁和厚重,紅色代表生命文化的理想和抗爭。通過影像的顏色對比,觀眾能獲得直觀的感觸,在回蕩的民族影像中得到思想的升華。
而賈樟柯在其影像創(chuàng)作中一以貫之地使用方言,并使影片獲得了一種現(xiàn)實的張力。《三峽好人》中,韓三明和沈紅這兩個外鄉(xiāng)人先后來到重慶奉節(jié)尋找和等候他人,畫面呈現(xiàn)了三峽的壯美風光,在三峽建設的宏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卑微無措顯露無遺。這種深入描繪社會現(xiàn)實的紀實風格反映著賈樟柯一貫的思想觀念。“賈樟柯最為關(guān)注的,是社會前行的滾滾車輪之下那些‘小人物’們的生存境遇及創(chuàng)痛,環(huán)繞他們生活和命運的各種‘聲音’實則承載著導演‘別有用心’的深層思考”[7]。方言電影將這種思想文化具象地反饋在影像中,形成了導演思想與電影美學并置的影像風格。
(三)真實與虛幻的藝術(shù)表達
方言電影的影像構(gòu)建在方言這一真實元素之上,并依據(jù)電影敘事線索形成獨特的視聽畫面,形成方言電影的藝術(shù)特征。一直以來,構(gòu)成電影敘事視聽元素的對白乃至配音,都是透過二次加工形成的。而方言電影通過現(xiàn)實的采風、演員的練習達到電影敘事的真實性和想象性。電影《一九四二》生動復現(xiàn)了河南大荒災,其中,以老東家為主要線索的電影敘事都建立在河南方言之上。以張國立為代表的演員進行了體驗式表演,其魅力在于真實共情。“如果角色的聲音形象與其生存環(huán)境的空間形象,乃至與其自身的形體形象發(fā)生分裂,乃至南轅北轍,那么,角色的整體形象便很難做到圓融飽滿、真實生動,當然也就談不上所謂人物性格了”[8]。
而在《路邊野餐》中,劇組在貴州實景拍攝,大幅使用真實的貴州方言,運用一鏡到底的拍攝技巧,形成了夢幻的“長鏡頭”。其所指涉的鏡頭空間、地理空間、朦朧的夢境,消解了現(xiàn)實場景的真實性,引發(fā)了超現(xiàn)實的想象,在搖晃的凝視和詩意的獨白中完成了電影敘事,其創(chuàng)新性的影像風格也在似夢似幻的回味中到達了電影藝術(shù)的極致。上述方言電影的敘事具有方言的本真質(zhì)地,并在真實的語言對白和虛構(gòu)的電影想象之間,構(gòu)建出令人回味的藝術(shù)特征。
三、結(jié)語
方言電影是一種語言文化類型電影,以方言的語言質(zhì)地凸顯語言的媒介作用,其表征為普通話與方言的互涉、語言與影像的交疊,實則是媒介話語體系的重構(gòu)與更新。方言電影細致地勾勒了地域空間,深入地闡釋了地域文化,用影像聚焦鄉(xiāng)土人物和地域,方言不僅作為具體的電影語言進行敘事,還彰顯了文化意涵,一以貫之地探討人物與社會沖突與和解的話題。方言電影體現(xiàn)了個人的生存境況,并以方言為核心創(chuàng)新藝術(shù)表達,營造了一種真實與虛幻并置的影像風格。無論是導演的創(chuàng)作思考,還是觀者的電影想象,都體現(xiàn)了方言電影的豐富意蘊。聚焦中國的方言電影,探索方言電影媒介與話語的融通機制,在影像時空中重現(xiàn)地域空間,使發(fā)散的電影想象重新向文化思考聚攏,可以為方言電影的觀念價值研究提供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