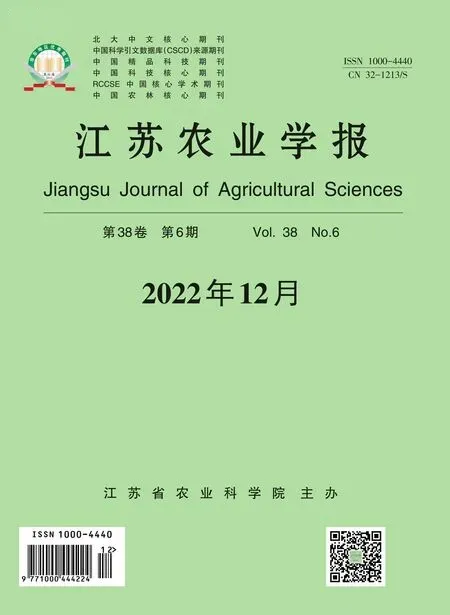PLGA納米疫苗佐劑的研究進展
肖慎華, 阿得力江·吾斯曼, 劉振廣
(1.南京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江蘇南京210095;2.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江蘇南京210095;3.新疆農業大學動物醫學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52)
近年來,隨著納米材料技術的快速發展,納米材料在疫苗佐劑方面的應用對疫苗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納米佐劑的優勢在于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納米尺寸效應、抗原負載能力、抗原緩釋效應及靶向性等[1-2]。與傳統佐劑相比,聚乳酸-羥基乙酸共聚物、聚乳酸共聚物、聚(ε-己內酯)、聚羥基丁酸酯等納米材料制備出的納米粒或微球可將抗原包裹或吸附在顆粒中形成良好的納米疫苗佐劑[3-5]。聚乳酸-羥基乙酸共聚物[poly(D,L-lactic-co-glycolic acid),PLGA]因其良好的安全性、生物相容性、藥物包封效果及藥物緩釋作用在疫苗佐劑領域得到了廣泛關注[6-7]。PLGA納米粒可將藥物或抗原包封在納米顆粒中,不但可保護藥物或抗原免受酶解,還能夠使藥物或抗原長期緩慢釋放,從而達到藥物長期作用或抗原長效免疫保護的目的[7-8]。
近年來,隨著對PLGA納米材料的深入理解和納米材料制備工藝的快速發展,學者們制備出了一系列不同相對分子質量、不同性質的PLGA原材料。PLGA是一種線性分子,水解后可分解為單體乳酸和羥基乙酸,由于這兩種單體是內源性的,很容易通過三羧酸循環在人體內代謝,因此以PLGA為載體進行藥物輸送或作為生物材料應用于機體所產生的毒性非常微弱[9-10]。PLGA通常用LAGA表示PLGA材料中的乳酸和羥基乙酸比,如LAGA為7 525,表示材料中乳酸含量為75%、羥基乙酸含量為25%。目前市場上常見的PLGA相對分子質量在5 000至150 000之間,其降解時間從幾個月到幾年不等,具體取決于PLGA的相對分子質量、共聚物比例和環境因素[11-12]。通常情況下PLGA相對分子質量越低,降解越快,因其末端羧酸的聚集和自身催化會導致納米粒的快速降解;LAGA越低,材料親水性越強、降解速率越高;酸性和堿性環境也會加速PLGA納米粒降解,相對而言PLGA納米粒在中性環境中具有良好的穩定性。PLGA不溶于水,但在常用有機溶劑如二氯甲烷、丙酮、氯仿、苯甲醇、乙酸乙酯中有良好的溶解性[13]。隨著對PLGA納米材料性質的全面了解和制備技術的發展,研究人員制備出了一系列不同大小、形狀和表面屬性的PLGA納米粒,并對這些納米粒進行了抗原負載方式、負載能力、佐劑活性及相關機理的檢測和評價[14-15]。本文以PLGA納米材料為研究對象,結合近年來PLGA納米粒作為疫苗佐劑存在的問題及相關解決方案,對PLGA納米粒的制備、檢測方法及影響其疫苗佐劑效果各因素進行了全面分析總結,并展望未來發展趨勢,以期為該領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理論基礎。
1 PLGA納米粒
1.1 PLGA納米粒的制備方法
納米粒制備過程不同,納米粒的結構有所差異。PLGA納米粒的常用制備方法有乳化-溶劑揮發法、乳化-鹽析法和噴霧干燥法[16]。
乳化-溶劑揮發法,是制備PLGA納米粒最常用的方法,常用于制備單層或雙層納米粒[17]。該方法首先是將PLGA溶于二氯甲烷、丙酮或乙酸乙酯等有機溶劑中,然后將藥物水溶液單獨或混合表面活性劑聚乙烯醇、聚山梨酯80或泊洛沙姆等一起均質,從而產生穩定的初乳或單層PLGA納米粒。雙層納米粒的制備方法是,形成初乳后再向初乳中加入表面活性劑,均質后得到穩定的雙層PLGA納米粒[17-18]。單層或雙層納米粒中的有機溶劑可通過磁力攪拌或低壓旋蒸的方法去除,除去有機溶劑后得到穩定的PLGA納米粒溶液。該方法操作簡單、可重復性良好,是試驗室制備PLGA納米粒最常用的方法,但該方法在大規模工業化生產中只適合于包封脂溶性藥物的PLGA納米粒生產,且均質過程耗能較高(圖2)[18]。
乳化-鹽析法,首先將含有PLGA和藥物的有機相加入到含鹽析劑(氯化鎂或氯化鈣)或膠體穩定劑(聚乙烯吡咯烷酮)的水溶液中,均質形成水包油O/W乳液,用大量的水進一步稀釋O/W,有機溶劑在水中迅速擴散,形成納米粒[19]。殘留溶劑和鹽析劑或膠體穩定劑可通過過濾去除。該方法制備的PLGA納米粒具有包封熱敏感性藥物(蛋白質、DNA和RNA)的優勢,但制備過程中由于有機溶劑在水中快速擴散,在納米粒形成后其表面常會產生小孔,容易導致藥物的滲漏[19]。
噴霧干燥法,是制備PLGA納米粒的新方法。該方法是將藥物分散在溶有PLGA的有機相中,將該混合體系噴灑在熱氣流中,形成納米粒氣溶膠,最后通過干燥氣溶膠的方式收集納米粒[21]。該方法具有快速、高效、實現工藝參數少等優點。但納米粒制備過程中會和熱氣流對撞,不利于對蛋白質、RNA等藥物的包封制備[20]。
除了以上三種常見制備方法外,人們還通過將溶解有PLGA的有機相放置在透析管內,通過透析袋內溶劑發生置換方式制備出了均質的PLGA納米粒[21]。有研究人員將溶質溶解在超臨界流體中,使壓力快速降低,達到高度飽和后導致納米粒的膨脹定型[22]。
1.2 PLGA納米粒的檢測方法
納米粒表征及穩定性等相關檢測對研究納米粒作用機制及納米粒的推廣使用具有重要意義。納米粒的大小有助于學者們確定納米粒的使用途徑、功效、藥物釋放情況和降解模式。用動態光散射、掃描電子顯微鏡、透射電子顯微鏡和原子力顯微鏡等檢測手段可確定納米粒大小、分布和形態等參數[23-24]。研究結果顯示,PLGA的相對分子質量對納米粒的粒徑、包封率和降解速度均有一定的影響。當PLGA相對分子質量較低時,末端羧酸含量相對較高,大量羧酸會導致PLGA納米粒的自身催化,從而加快納米粒的降解速率。PLGA納米粒的相對分子質量可通過尺寸排阻色譜法進行檢測[25]。研究結果顯示,納米粒Zeta電荷對納米粒體外釋放、黏附性、穩定性以及納米粒在機體和細胞內轉運特性具有重要意義[26-27]。納米粒的分散系數(PDI)可直接反應納米粒的分散狀態。納米粒的Zeta電荷、PDI及粒徑均可通過馬爾文Zeta電位儀進行檢測。納米粒在機體中的轉運分布情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疏水性[28-29]。研究結果表明,親水性顆粒的滯留時間比疏水性顆粒要長,通過檢測納米粒表面化學官能團,如通過X射線光電子能譜、傅立葉變換紅外光譜和核磁共振光譜等,可判斷納米粒疏水性能的強弱[30-31]。傅立葉變換紅外光譜和核磁共振光譜等方法同樣可用于檢測PLGA納米粒中藥物的包封情況及表面修飾PLGA納米粒的修飾程度和修飾物用量[32-33]。
2 以PLGA為基礎的納米佐劑
研究結果[34-35]表明,負載抗原的納米粒注入機體后可增強對機體抗原呈遞細胞(APC)的募集效果,納米粒能夠有效被大量APC攝取,從而增強機體對抗原的攝取率,與抗原單獨使用或傳統油佐劑相比,納米粒用作佐劑具有更好的免疫或治療效果。除了APC的高攝取率外,基于以PLGA為基礎的疫苗佐劑包封抗原后,因良好的緩釋效果能夠長時間釋放抗原,為機體提供更有效的免疫保護反應,能夠減少免疫次數,達到經濟有效保護機體的目的[35-36]。PLGA納米粒作為載體可負載單獨抗原或幾個不同的抗原[37]。研究結果[38]證明,抗原和佐劑共同傳遞,才能同時被細胞有效內化。此外,當抗原和PLGA濃度較低時就能夠有效刺激機體誘導強烈的T細胞免疫反應[39-40]。因此,從抗原使用劑量角度而言,PLGA包封的抗原能夠有效節約抗原用量。基于PLGA納米良好的安全性及佐劑效應,該納米佐劑引起了學者們廣泛關注。已知,納米粒的大小、形狀及表面電荷等均對納米粒佐劑活性的發揮有著重要影響[41-42]。因此,學者們圍繞PLGA納米粒展開了一系列研究,優化其粒徑、形狀及表面電荷,以求制備出更為有效的納米佐劑。
2.1 粒徑對納米粒佐劑效果的影響
為了制備出最佳疫苗載體,學者們對納米粒粒徑進行了優化,并對其機體作用途徑進行了檢測。An等[43]以PLGA納米粒為基礎,制備出了粒徑分別為20 nm、40 nm和100 nm的3種粒徑納米粒,比較不同粒徑納米粒淋巴結傳送效率及淋巴結內樹突狀細胞(DC)的有效靶向性。3種納米粒中,20 nm粒徑的納米粒最快進入淋巴結,且高效地被DC所攝取,進而快速誘導有效的免疫反應;40 nm粒徑的納米粒也能夠快速進入淋巴結,但被DC攝取效率低于前者,因此所誘導的免疫強度弱于前者;而100 nm粒徑的納米粒,進入淋巴結中的時間較長,但其免疫持續時間要強于前兩者[43]。經檢測發現,3種不同粒徑納米粒,進入淋巴結的時間和方式有所不同,因此介導的免疫反應強弱和持續時間均有所差異。粒徑為20~100 nm的納米粒,可直接進入淋巴管或細胞間隙將疫苗遞送至淋巴結,產生強烈免疫反應,即為細胞旁路途徑[44]。粒徑大于100 nm的納米粒,能夠在注射部位產生募集效應,經大量APC攝取后,將疫苗遷移至淋巴結中而產生長效免疫反應,即為細胞載體途徑[44-45]。不同粒徑納米粒對機體免疫反應類型的影響檢測試驗結果發現,粒徑在200~600 nm大小的納米粒介導能夠誘導機體IFN-γ高水平分泌,免疫類型偏向T helper 1(Th1)型免疫反應;粒徑在2 000~8 000 nm的納米粒介導,則誘導機體IL-4高水平分泌,免疫類型偏向Th2型免疫反應[45]。以上結果表明,PLGA納米粒的作用途徑及介導的免疫反應類型和免疫反應強弱均可通過控制顆粒大小進行調節。因此,納米粒大小對PLGA納米粒疫苗佐劑效應的發揮具有重要意義。
2.2 電荷對納米粒佐劑效果的影響
將抗原包封在PLGA納米粒中,能夠為機體提供長效而持久的抗原刺激,因此PLGA納米粒是一種良好的疫苗佐劑[46]。但有學者[47]發現,PLGA納米粒抗原包封過程中抗原和油相中有機溶劑直接接觸,對抗原活性產生一定影響,且單一的包封策略限制了納米粒的抗原負載效率。為了加強納米粒的抗原負載率,對PLGA納米粒采取了表面陽離子修飾策略[48]。常用陽離子修飾物有殼聚糖、聚賴氨酸、聚乙烯亞胺、聚多巴胺和陽離子脂質體雙十八烷基溴化銨等[49]。這些陽離子可直接通過靜電吸附對PLGA納米粒進行修飾,從而提高PLGA納米粒的抗原負載率[49-50]。經一系列的試驗發現,納米粒表面經陽離子修飾后,不但能夠通過靜電吸附負載更多的抗原,還能加強誘導機體產生強烈的細胞免疫活性[49]。納米粒的表面電荷對細胞的攝取作用具有重要影響[39]。試驗結果顯示,帶正電的納米粒更容易發生細胞內化,因為帶正電的納米粒更容易通過靜電作用被帶負電的細胞膜所攝取[50-51]。此外,帶正電荷的納米粒進入溶酶體后,能夠快速消耗溶酶體中大量H+,從而使細胞質中大量鹽離子內流,導致溶酶體破裂,產生有效溶酶體逃逸,而逃逸出的納米粒,通過MHC I分子呈遞,有效誘導Th1型細胞活化,產生強烈細胞免疫應答[52]。
2.3 形狀對納米粒佐劑效果的影響
納米粒形狀對其佐劑活性強弱也有一定的影響。納米粒形狀不同,導致不同納米粒和細胞膜接觸后形成的角度不同,被APC攝取的效率也不同。Niikura等[53]分別對圓球狀、橄欖球狀及棒狀納米粒進行了APC細胞的攝取率檢測,結果顯示,棒狀或橄欖球狀納米粒豎直和細胞膜接觸時所產生的阻力最小,易被吞噬,但當棒狀或橄欖球狀納米粒橫向接觸細胞膜時所產生的阻力要遠大于圓球狀納米粒,且納米粒接觸細胞膜時,因表面張力的作用,使棒狀或橄欖球狀納米粒更容易以橫向方式和細胞膜接觸。因此相對棒狀或橄欖球狀納米粒,圓球狀更容易被APC攝取[54]。因此,合理設計納米粒的形狀,對其在機體內發揮有效的免疫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3 PLGA納米佐劑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策略
盡管有關PLGA納米粒的研究很多,也從多方面對該納米粒的佐劑作用機制進行了全面分析,但PLGA納米粒在臨床運用卻很少[55]。其中,限制PLGA納米粒大規模應用的因素有以下幾點:(1)納米粒載藥量低,通常情況下PLGA納米粒具有良好的包封效果對大多數藥物和抗原均具有較高的包封率,如對雌二醇或黃原酮的包封率為60%~70%,但PLGA納米粒的載藥量卻很低,約1%左右,意味著100 mg質量的PLGA納米粒只能負載1 mg藥物。(2)抗原負載方式不完善,PLGA納米粒以包封的方式負載抗原,但納米粒制備過程中將會使抗原和油相中的有機溶劑直接接觸,影響抗原的活性。(3)無法做到納米粒和抗原分開保存使用,實際應用中佐劑和抗原的分開保存,通過簡單混合后就可使用,無疑是佐劑使用的最佳方式[56-57]。但PLGA納米粒以包封的方式存在顯然無法做到納米粒和抗原分開保存,為此,解決PLGA納米粒的抗原負載率,將其制備成類似于鋁佐劑的方便型疫苗佐劑,是推廣利用以PLGA為基礎的納米疫苗佐劑的關鍵技術問題。
近年來,有報道,可利用陽離子對PLGA納米粒進行修飾,使原來帶負電荷的PLGA納米粒表面經陽離子修飾后變為正電荷,再通過電荷吸附作用使納米粒負載帶負電荷的疫苗抗原[58]。陽離子修飾PLGA納米粒的抗原負載量和表面電荷有關,表面正電荷越強抗原負載率越高,但過高的正電荷會導致較大的細胞毒性[59]。因此,在較為安全的細胞毒性范圍內,陽離子修飾PLGA納米粒的抗原負載率受到了極大限制。
為了進一步改善PLGA納米粒的抗原負載率和抗原負載方式,有學者將PLGA納米粒和油乳液進行了組裝,將PLGA納米粒組裝成復合納米粒,從而提高納米粒抗原負載率、加強納米粒APC募集效果及誘導強烈細胞及體液免疫應答[60]。Xia等[60]以PLGA納米粒為外殼,以角鯊烯為油相,制備出了新型組裝Pickering乳液,復合納米粒佐劑結合了油佐劑和PLGA納米粒的優點。檢測得知,Pickering乳液表面為草莓樣結構,可為抗原提供巨大的比表面積,這種特殊的表面結構可有效利用乳液表面PLGA納米粒之間的縫隙吸附大量抗原,從而提高納米粒抗原負載率,加大載藥量;這種復合納米粒在乳液界面形成了一層殼狀覆蓋,便于抗原的緩慢釋放和傳遞;Pickering乳液凹凸的表面更有利于APC的攝取;Pickering乳液具有柔軟的角鯊烯內核,因此和APC接觸時因變形作用,接觸面積增加,APC在納米粒表面密集抗原的作用下引發多級免疫識別,產生強烈的免疫應答反應[58]。Song等[61]以poly(ethylene glycol)-block- poly(lactide-co-?-caprolactone)( PEG-b-PLACL)納米粒為外殼,以檸檬酸/角鯊烯為內核,制備出了復合納米粒。試驗發現,該復合納米粒佐劑具有良好的APC募集及抗原負載效果,同時還能誘導機體產生強烈的細胞免疫應答,對人卵巢癌細胞誘導的腫瘤具有良好的治愈效果[61]。
PLGA納米材料是具有生物相容性的良好疫苗載體。因此,合理地設計PLGA納米粒,通過陽離子修飾或組裝的方式對PLGA納米粒進行進一步處理,使PLGA納米粒成為具有高抗原負載率、高APC募集效果及鋁佐劑樣混合吸附抗原特性,是攻克PLGA納米粒的低抗原負載率,不完善的抗原負載方式等缺陷的有效策略。PLGA納米粒表面陽離子修飾或與油乳液等組裝將成為PLGA納米佐劑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