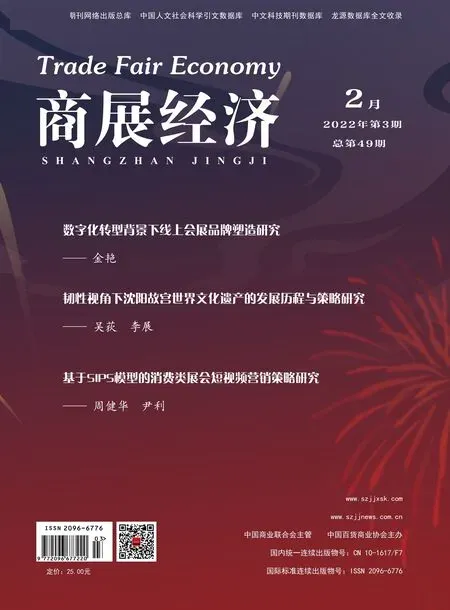中國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空間分異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
鄭慧彬 韓景 謝戚 葉朵朵 汪冰蓉
(南京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江蘇南京 210000)
1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對我國各地區的經濟水平和社會發展水平產生了深刻影響。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2011—2014年,中國總流動人口不斷增長,達到2.53億[1],已整體邁入人口流動性社會。鑒于國家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利好政策出臺及國內部分大城市對人口規模的管控,中國逐步調整流動人口規模[2],自2015年總流動人口數開始緩慢下降,但在總人口中仍占較大比例。人口回流及其空間遷移過程,勢必將對人口集聚的城鎮地區和人口流出的鄉村地區產生經濟、社會、生態等多方位影響,而且會使中國城市勞動力構成及我國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3],這說明流動人口的回流意愿是反映未來中國流動人口回流趨勢的主要指標[4]。流動人口回流有助于增進流出地與流入地之間的勞動力、資金等各項資源流動,也會對流出地的經濟發展產生潛在或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關注流動人口問題,有助于精準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對于鼓勵流動人口落戶和實現新型城鎮化都具有重要意義。
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在國家層面上略有不同,各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往往表現出異質性特征[4],所以流動人口回流意愿不僅受動人口自身特征影響,還受國內生產總值、社會保障制度等流入地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在空間上不完全流動,導致了城市間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異質性[5]。國外學者在流動人口及人口遷移領域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本地依戀和社會網絡會影響居住意向的前提下,Annell等人根據社會網絡理論解釋了本地滿意度對城市創意群體(如留學生)居住意向的影響機制[6]。推拉理論認為,回流勞動力的創業行為受到外部環境“推力”“拉力”的影響,“推力”是指限制回流勞動力從事創新創業的因素;“拉力”指流出地為回流勞動力創業提供的便利和政策支持等因素[7]。其中,Gmelch等認為家鄉的“拉力”是更為重要的因素[8]。
我國學者對人口回流影響因素的理論研究方興未艾,一種更為一致的觀點是:農村流動人口做出回流決策是基于比較收益、投資回報及個人的主觀偏好[9]。國內針對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從勞動者個體因素[10]、家庭因素[11]、政策因素[12]等方面進行分析,對于回流意愿空間分異特征的研究,從流動人口城市間轉移軌跡和規律[13]、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的空間差異[14]、城市人口流動空間類型[15]等角度開展研究,系統分析不同城市的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基本特征,有利于客觀地認識我國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空間分異規律,為各地區、各政府機構了解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空間分異特征、切實可行地制定有針對性的相關人口政策、引導流動人口落戶提供理論指導。
學術界致力于從整體上研究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影響因素,而且普遍聚焦于個人因素,從微觀視角展開,較少綜合考量流入地特征對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的影響,對區域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間特征及影響因素的研究也略顯不足。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地區區域差異明顯,城市類型多樣,而且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城市是跨省人口流動的主要吸引中心[16]。人口流動性強,外來務工人員多,可獲取大量有效數據樣本,在數據的代表性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鑒于此,本文基于2017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選取中國東部地區87個地級城市,探討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有助于地方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流動人口管理政策,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2 數據來源和變量選擇
2.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是2017年國家衛健委組織的一場關于全國流動人口的抽樣調查,該抽樣調查的樣本量覆蓋了全國32個省級單位中流動人口的集中流入地,采取分層、多階段和規模成比例的PPS抽樣方法,在各個鄉鎮、街道居委會中抽取居住在本地1個月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年齡處于15~59周歲區間的流入人口[17]。本文研究區域是中國東部地區,根據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將江蘇省、河北省等十省(直轄市)定義為中國東部地區。因三沙市無數據,故予以剔除。本文將在問卷調查中有回流意愿且將要返鄉的流動人口定義為回流者,在研究目標的基礎上,結合某些數據的變量數值缺失或異常的情況,刪除異常數據樣本,最后獲得有效樣本67915份。
2.2 變量選擇
梳理解釋流動人口回流問題影響因素的經典理論,主要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宏觀及社會融入理論、推拉理論、部門理論等[18]。基于古恒宇的研究,本文從流動人口特征和流入地特征兩個維度分別解釋流動人口回流意愿。流動人口特征因素包括教育水平(School:流動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外出務工年限(Year:流動人口的外出工作時間)、家庭經濟情況(Ratio:家庭月平均收入與支出比;Area:家庭承包地面積; Income:家庭承包地收入;Homestead:戶籍所在地是否有宅基地)、工作強度(Strength:一周工作時長)、住房因素(Found:擁有住房公積金流動人口比)、流出地社會網絡(Degree:與老家親屬關系的親疏程度)、家庭規模(Family:家庭人口數)。流入地特征包括經濟情況(Wages:流入地每月平均工資)、醫療保障情況(Medical:流入地社會醫療情況)、社會保障制度(Social:辦理個人社會保障卡)、就業情況(Employment:鄉村人口就業率;Rate:城鎮鄉村就業人數比)。變量名稱、變量描述及預期效應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類型、名稱、描述及預期效應
3 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及其空間分異特征
3.1 研究方法
研究通過空間分析法,利用東部地區空間數據,探究各區位因素間的關系,揭示區位因素特征和內在規律,實現對空間地理信息的認知。自然間斷點分級法(Jenks)是對一系列數據的近似精確值進行恰當的分組,運用分類間隔符加以數據區間的識別,使每個數據組間的差異達到最大。本文基于此方法,在數據值差異較大處設定邊界,將回流意愿比例劃分為五類。
3.2 中國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的總體統計特征
中國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比例總體較低,平均回流意愿比例為2.24%,空間分布總體呈現“南高北低”的態勢。其中,鹽城市、茂名市等南部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比例較高,分別達到7.5%、12.5%;萊蕪市、張家口市等北部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比例較低,分別為0.01%、0.42%。究其原因,中國東部地區中偏南方地區較偏北方地區而言普遍較為發達,在偏南方城市務工的流動人口經歷一定時間的務工、創業后,其回流意愿已不受經濟因素限制,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東部地區在偏南方地城市的流動人口具有較強的回流意愿[4]。數據顯示,在中國東部地區城市中:云浮市流動人口具有最低的回流意愿,僅有0%;茂名市的流動人口具有最高的回流意愿,達到12.5%。結果表明:廣東省內部城市流動人口具有較大的回流意愿差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東部地區一些省份經濟發展不均的現狀。具有較高回流意愿的流動人口分布的城市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
3.3 中國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間分異特征
3.3.1 基于城市群的異質性分析
根據2018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中提及的關于中國城市群的劃分方法,中國東部地區有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粵港澳大灣區兩大城市群。中國東部地區長三角城市群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空間分布如圖1所示,中國東部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空間分布如圖2所示。
如圖1所示,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為2.4%,其中,最高值出現在該城市群東北部,以鹽城市作為典型代表。中部回流意愿呈現聚集態勢,而且普遍回流意愿較低,最低值出現在鎮江市。沿海城市的回流意愿普遍高于內陸城市。

圖1 中國東部地區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空間分布
如圖2所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為1.7%,其中,最高值出現在該城市群西北部,以中山市為代表。其回流意愿呈現出明顯的分區特征、塊狀特征,回流意愿最低值出現在江門市。

圖2 中國東部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間分布
通過兩個城市群的整體分析發現,中國東部地區內陸城市流動人口的回流意愿普遍低于沿海城市。
3.3.2 基于城市規模的異質性分析
根據2014年國務院《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中城市規模的劃分標準,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300余個城市中有7座超大城市和14座特大城市。其中,中國東部地區包含上海、廣州、北京、深圳、天津5座超大城市,東莞、南京、佛山、杭州、青島、濟南6座特大城市。基于2017年數據,對這5座超大城市和6座特大城市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結果如圖3所示。
如圖3所示,我國東部地區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位于南方的超大、特大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均高于北方的超大、特大城市。在超大城市中,上海市流動人口具有最高的回流意愿,為1.7%;北京市流動人口具有最低的回流意愿,為1.1%。在特大城市中,位于南方的佛山市和南京市具有最高的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均為2.2%,位于北方的濟南市具有最低的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為0.5%。南北差異主要表現于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南方具有較好的天然地理、氣候條件,其招商引資能力強,南方各城市間的差距逐步縮小,其經濟因素已經不再限制其回流,北方則主要以大片區域的中心城市發展為主,中心城市與邊緣城市發展差異較大,故南方流動人口回流意愿高于北方。

圖3 中國東部地區超大、特大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對比
4 影響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的因素
4.1 模型構建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過建立多項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對各個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估計,經過似然比檢驗和Wald卡方檢驗進行顯著性分析,篩選出顯著的變量進行進一步處理,求出OR值、B值與P值比較影響程度。其中,多項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公式如下:

4.2 模型結果及影響因素
根據上述建立的多項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將中國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設為因變量,以教育水平、流出地社會網絡、外出務工年限、社會保障制度等因素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中國流動人口回流意愿驅動因素的Logistic模型估計結果
4.2.1 流動人口特征層面
教育水平對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產生負向推動力。其作為內部因素,對回流意愿產生負向影響。結果顯示:流入人口的平均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返鄉回流意愿越弱。該結論與諸多同類研究結論相似[19]。更高的教育水平能夠顯著提高流動人口的各項勞動技能,增強其在勞動力市場上各方面的競爭優勢,從而轉化為更高的經濟回報。從某種程度上說,教育是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壁壘,提高流動人口的教育水平也有利于較低階層者進入更高的階層,從而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另外,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打破社會壁壘,實現各階層之間的融合[20]。
流動人口與其親屬之間的聯系是影響其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外務工用來構建社會網絡的成本較大,而在其戶籍所在地已具備相當完善的社會關系網絡,使得流動人群具有更強烈的回流意愿。與戶籍地親屬關系更親密的流動人口回流意愿更強烈,反之則會受到抑制作用。流動人口在外務工需要重構社會關系網絡,而在外流動時間越長會導致與家鄉親屬關系越疏遠,也需要重構親屬間的關系網絡。同時,重構社會關系網絡需要消耗時間、精力和金錢等,致使遷移成本增加,同時導致流動人口在新的流入地融入成本和社會網絡重構成本增加,增強其回流意愿。
外出務工年限較大程度上影響流動人 口回流。從宏觀角度來講,外出務工時間越長,在當地建立的社會網絡聯系越牢靠,更能適應當地的就業環境,因此其回流意愿可能會減弱。但從微觀解度來講,考慮外出務工人員的個人因素,如果在外工作時間過長,會勾起他們的思鄉情結,其回流意愿也可能會增強,在這兩種情況下無法正確預測最終結果。根據模型的結果,外出務工年限與其回流意愿呈正相關,即外出務工時間越長回流意愿越強,因此從實然層面上來推測,對親人思念等因素比構建關系網絡影響程度更高,與前人結論相符[21]。
4.2.2 流入地特征層面
社會保障制度對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產生負向作用力。作為外部影響因素,流入地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回流意愿呈顯著負向關系。不同城市、不同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不盡相同,通過分析結果發現,社會保障制度更完善的城市的流動人口回流意愿較制度不完善的城市更弱。可能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更完善的城市,在保險、救助、補貼等方面更優[22],對于外出務工的流動人口,這些方面正是他們所著重考慮的。這一結論也與前人諸多研究結論相符。
5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主要結論
5.1.1 中國東部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總體偏低
中國東部地區地級及以上城市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動人口比例為2.24%。中國東部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存在明顯的地理分異特征,在不同的東部地區存在明顯不同的回流意愿。中國東部地區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在南北方呈現一定規律:東部地區偏南方城市的流動人口相比偏北方城市而言有較高的回流意愿。中國東部地區城市群內陸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普遍低于沿海城市。中國東部城市的規模與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在地域分布上存在較大差異,位于南方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回流意愿都高于北方。
5.1.2 中國東部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受多方面的影響因素共同作用
在其他同類論文研究的基礎上,選取研究頻次較高的15個影響因素分類進行研究,得出部分具有顯著性的因素。從內部分析,教育水平變量對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產生負向作用力,外出務工人員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回流意愿越弱;與親屬之間的聯系是城市人口回流意愿的重要動因;外出務工年限是影響人口回流的因素之一,根據模型估計結果, 外出務工年限在較大程度上影響流動人口回流,即外出務工時間越長回流意愿越強。從外部因素看,流入地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回流意愿產生負向作用力,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城市流動人口回流意愿較制度不完善的城市更弱。
5.2 政策建議
(1)對于回流意愿高的城市,通過降低流動人口在本城市的生活費用,健全本城市的社會保障制度,招徠流動人口留在本城市;對于回流意愿極高、極其想返回家鄉的流動人口,積極引導他們返回家鄉,積極響應國家“返鄉下鄉”“鄉村振興”的相關政策。
(2)對于回流意愿低的城市,通過加強城市相關監管,爭取減少因為流動人口涌入可能引發環境惡化、交通擁堵、秩序混亂的“城市病”問題,力求在流動人口涌入、大力發展的同時保持城市居民的較高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