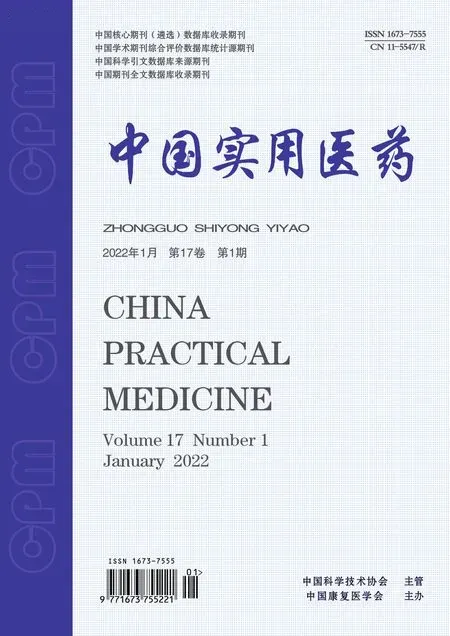針刺聯合西藥治療失眠的效果分析
盧立順
失眠中醫稱之為不寐、不得臥、不得眠等,是多種因素導致的睡眠障礙,患者表現為入睡困難、睡眠維持困難及日間功能受影響等,是一種常見的失眠障礙[1,2]。近年來,隨著生活節奏加快和生活壓力增加,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我國失眠患者明顯增多,失眠發病率呈上升趨勢,以往老年人、女性、生活壓力大人群及焦慮癥、心血管疾病患者是失眠的多發群體,但周琪等[3]調查發現,某地超過30%的學生存在失眠。由此可見,失眠已經成為影響全民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必須予以充分的重視。目前,關于失眠的治療方式較多,包括心理干預、藥物控制等,西醫多以催眠類藥物為主,雖有一定療效,但患者易產生依賴性,長期服用可能損傷肝腎等缺點,并未能完全滿足臨床需要。中醫藥在治療失眠中累積了豐富經驗,包括中藥湯劑、針刺、艾灸等,方式多樣,無用藥依賴,針刺作為一種綠色療法,在失眠治療中取得了顯著效果[4]。本文探究針刺聯合西藥治療失眠的效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1 月~2020 年12 月收治的120 例失眠患者,以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60 例。觀察組男26 例,女34 例;年齡22~60 歲,平均年齡(41.36±6.46)歲;病程6~19 個月,平均病程(13.05±2.35)個月;輕度失眠18 例,中度失眠31 例,重度失眠11 例。對照組男25 例,女35 例;年齡21~60 歲,平均年齡(42.03±7.01)歲;病程5~20 個月,平均病程(13.84±2.95)個月;輕度失眠21 例,中度失眠30 例,重度失眠9 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研究經過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1.2診斷標準 ①符合失眠的診斷標準[1],即入睡時間≥30 min,夜間覺醒≥2 次,睡眠時間<6.5 h,早醒等;伴有日間功能障礙;上述癥狀≥3 次/周,持續時間≥3 個月。失眠程度參照失眠嚴重程度指數(ISI)[5],輕度:偶發,時常驚醒或睡而不穩,早醒,對日間功能影響較小,ISI 評分8~14 分;中度:每晚發生,睡眠<4 h,尚能維持日間功能工作,伴易怒、焦慮、疲乏等;ISI 評分15~21 分;重度:徹夜不寐,嚴重影響日間功能,ISI 評分≥22 分。
1.3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符合診斷標準;年齡>18 歲;治療前2 周內未使用相關藥物;對研究內容知情同意。排除標準:存在針刺禁忌,如暈針、皮膚破潰等;妊娠期、哺乳期及近期有懷孕計劃女性;合并精神類疾病;合并傳染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礙等;合并嚴重焦慮、抑郁等。
1.4方法
1.4.1對照組 給予阿普唑侖治療,0.4~0.8 mg/次,1 次/d,根據癥狀調整劑量,最大劑量≤4 mg/d,睡前30 min 服用。連續服用2 個月。
1.4.2觀察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針刺治療。患者取坐位,選擇百會、神門、三陰交、內關等穴位,心脾兩虛者加心俞、脾俞、足三里,肝火上擾者加太沖、肝俞,采用華佗牌一次性針灸針(0.25 mm×40 mm),常規進針,進針后采用平補平瀉法,得氣后留針15~20 min,1 次/d,連續治療3 d,休息1 d,共治療2 個月。
1.5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①臨床療效,參照《中醫病癥診斷療效標準》[6],治愈:治療后,睡眠正常,伴隨癥狀消失,1 個月內無復發;顯效:睡眠時間延長,伴隨癥狀改善;有效:睡眠及伴隨癥狀有改善;無效:癥狀無改變或加重。總有效率=治愈率+有效率+顯效率。②比較兩組治療前后PSQI 評分,包括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質量、睡眠效率、使用藥物等7 項,0~3 分/項,總分為各項計分之和,分值越高表示失眠越嚴重。
1.6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 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為90.00%,高于對照組的75.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n(%)]
2.2兩組PSQI 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PSQI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PSQI評分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PSQI 評分比較(,分)

表2 兩組PSQI 評分比較(,分)
注:與對照組同期比較,aP<0.05
3 討論
失眠是常見的睡眠障礙之一,近年來其發病率不斷升高,長期失眠影響患者日常生活和工作,降低工作效率,甚至增加罹患其他疾病的風險。研究發現,長期失眠可誘發多種疾病,失眠也是多種疾病的合并癥狀,常相互作用,相互加重,如劉劍鋒等[7]研究發現失眠不僅是抑郁的一個癥狀,也是引起抑郁的重要因素,長期失眠加重抑郁程度。徐維芳等[8]則發現,失眠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中發病率較高,而失眠又是引起心血管疾病加重的促進因素之一。由此可見,失眠的治療對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西醫認為引起失眠的原因多樣,如不良生活、飲食習慣,疾病,心理壓力等,其治療目的在于改善睡眠質量,恢復日間功能,防止轉化為慢性失眠,減少失眠相關的軀體疾病或精神疾病[9,10]。目前,運動療法、行為干預被認為是治療失眠的綠色療法,但起效慢,效果難以維持,多數患者仍采用西藥治療。本研究對照組采用阿普唑侖治療,該藥是治療失眠的常用藥物,可加強中樞抑制性神經遞質γ-氨基丁酸(GABA)與GABAA受體結合,降低神經元興奮性,口服1~2 h 后,血藥濃度可達到峰值,故睡前使用可達到較好效果,但部分患者用藥后出現嗜睡、乏力、皮疹等不良反應,部分患者為求速效,過量服用出現精神錯亂、抖動、呼吸短促等,不適宜長期服用[11]。
祖國醫學將失眠稱之為“不寐”、“不得臥”等,關于其認識早在《黃帝內經》中便有相關記載,如《靈柩·口問》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素問·逆調論》記載:“胃不和則臥不安”,《難經》云:“臥之安者,神藏于心,魂歸于肝,意歸于脾……神機不安亦可生本病”。祖國醫學認為失眠的病因包括情志不暢、飲食不節、感受外邪、氣血不足等,這與現代人生活壓力大、節奏快、飲食不規律基本吻合。中醫認為失眠的基本病機在于陰陽、氣血失和,陽不入陰[12]。治療關鍵在于調節陰陽偏盛,恢復陰陽平衡。
本研究觀察組加用針刺治療,主穴取百會、神門、三陰交、內關等。百會穴位于顛頂,為百脈之會,而頭為諸陽之會,百脈之宗,針刺百會可通達脈絡,連貫周身,調節陰陽;神門可補益心氣,安定心神;脾為氣血生化之源,是生理功能正常運轉的物質基礎,三陰交為足太陰、足厥陰、足少陰之會,可調理脾胃;內關可調節心經氣血,具有寧心安神之功效,上述穴位是現代中醫臨床針刺治療失眠選用頻率最高的穴位,對改善失眠具有積極作用[13]。臨床治療根據患者不同證型,辨證加減,如心脾兩虛者,多表現為納差、腹脹、心神不寧、心悸怔忡等,可加心俞、脾俞、足三里等益氣補虛;肝火上擾者,多表現為頭暈脹痛、耳鳴、面紅目赤、急躁易怒、婦女月經量多等,可加太沖、肝俞清肝瀉火。研究顯示針刺通過刺激相應穴位可提高神經遞質及與睡眠相關的激素水平,如羅本華等[14]實驗發現,針刺干預氯苯丙氨酸(PCPA)失眠大鼠后,可良性調控5-羥色胺(5-HT)1A/Gαi/o/cAMP、5-HT2A/Gαq/11/PLCβ 信號通路,改善中樞5-HT 障礙機制,發揮治療失眠的作用。
本研究顯示,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為90.00%,高于對照組的75.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輔助針刺治療可提高治療效果。PSQI 評分是失眠診斷、預后判斷的主要參考依據之一,治療后,觀察組PSQI評分(4.24±0.51)分低于對照組的(9.53±1.17)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聯合針刺治療可顯著提高患者睡眠質量。
綜上所述,針刺聯合西藥治療失眠可提高治療效果,改善睡眠質量,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