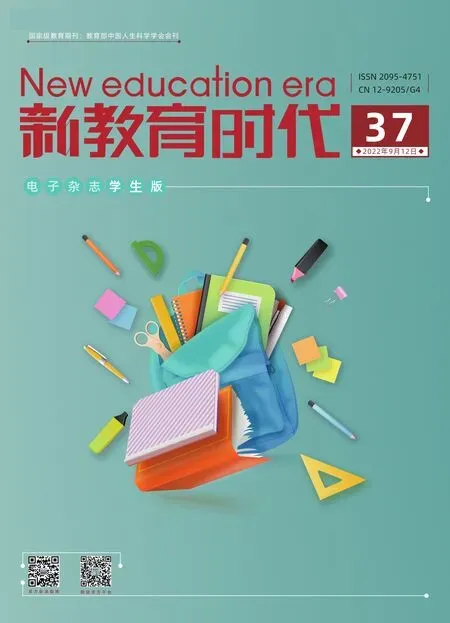懷斯與科爾維爾的藝術風格比較研究
萬濤濤 劉珊珊
(江西現代職業技術學院 江西南昌 330000)
在當代繪畫藝術中,懷斯與科爾維爾的作品深刻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的許多畫家,如傷痕文藝的代表畫家何多苓,羅中立等,在他們的早期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到懷斯對其畫面構圖及情景的影響。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就在中國辦過展覽的加拿大畫家科爾維爾,其畫作中的抽象性繪畫技法平面處理及稍顯荒誕的情景表達也影響了魔幻現實主義的畫家劉溢,以及近來全國美展獲獎的李善陽等許多青年畫家。懷斯與科爾維爾畫面語言、繪畫技法既傳統又現代,拓寬了現代具象繪畫的邊界,那種畫外之音,具象畫面所傳達的深刻的抽象精神內涵,正貼合了中國傳統藝術的意境表現,所以對中國畫家來說顯得尤為親切。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作品有著諸多的相似性,通過削弱畫面的敘述性營造出一種靜謐永恒的孤獨感與疏離感,畫面安靜和凝固具象卻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追求真實,都嘗試用較為傳統古典的表現手法進行畫面形式感的探索。在他的畫中有種極富哲學意味的超現實主義性,隱喻或象征了當代人所普遍具有的矛盾、困惑、虛無、迷茫等的精神狀態,本文通過兩位藝術家的生活環境,繪畫語言對比研究探索他們藝術形成的基本脈絡,以便對后來藝術家創作起到借鑒意義典型中國式的審美哲學文化潛意識。
一、家庭成長環境及生活背景
在欣賞懷斯與科爾維爾的繪畫藝術時,很容易被他們畫中非常私人化的人物場景所吸引,畫面雖然不是一個顯性的主題或是一個直觀可釋的故事但他們通過非常熟悉的事物抽象化成非常具體的符號性的組合傳達出更深層次的意味,這正是他們畫中最為迷人的特質,我們如果想要去解讀他,就需要對畫家的家庭生活背景、時代環境深入了解,從而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他們的藝術。
20世紀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地改變著這個世界與自然,各類藝術流派叢生,在二戰后的20年里,西方世界藝壇抽象畫興盛風靡一時,但同作為一戰后出生在二戰時期成長起來的兩位藝術家,他們的繪畫藝術看起來無疑是具象且似乎保守,他們像古典大師一樣勤勤懇懇耕耘并精確描繪,不被潮流風尚影響附會,創造了更為深刻的具象表現,反而引導潮流。
懷斯于1917出生在一個藝術世家,父親安康·懷斯是一位著名的童話故事插畫家,作為家里最小的孩子,懷斯從小患有慢性的靜脈疾病,體質虛弱,不能正常去學校接受教育,作為畫家的父親便成了他繪畫藝術的啟蒙者,而科爾維爾192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倫多,父母雖然沒有從事與藝術相關的工作,但是1929年九歲的科爾維爾因為一場嚴重的肺炎卻讓他在康復的孤獨中與繪畫結上了不解之緣。或許是同樣年幼遭遇疾病的經歷,讓兩位藝術家離開校園集體,在孤獨中,讓他們的作品形成了一種孤寂、靜穆、細膩的特質,也讓他們在孤獨中對周遭事物敏感而映像深刻。比如懷斯長時間跟隨在農場工作的父親,自然對田園與自然有著一股濃郁的情感。
作為繪畫及人生導師的父親,對懷斯的影響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但是1945年一起意外車禍,父親的離世對懷斯而言是極其悲痛的經歷,繪畫成了他排解憂傷的唯一途徑,作品也變得更為深沉。1944年至1945,年作為戰地藝術家的科爾維爾,親身體驗到了戰爭殘酷,及對戰爭記錄的嚴肅性及深遠意義。這些尤為深刻的情感經歷讓藝術家的作品有了意味深長的變化及隱喻,或者說一種更為深刻的事物正在內心根植醞釀。懷斯《1946年的冬天》這張畫中,曠野中奔跑的青年顯得那樣孤獨,草地上深深的車轍及陽光投射的強烈陰影像道道疤痕這是對那場車禍的隱喻。懷斯用繪畫去證明父親的付出沒有被辜負,他深刻感受到作為一個純粹藝術家的歸宿。在此之前,懷斯作為一個優秀的商業插畫家,一直在插畫與純藝術創作中掙扎,他的父親就是如此。懷斯明智且大膽地遵從自己的內心,選擇純藝術創作并得到家人的支持,他可以更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考。1947年至1948年的三幅作品《海風》《克爾》《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表現了他的超越與摸索,畫家抓住一種偶然經驗的刺激,讓他進入潛意識給予靈感,在平凡的空間中創造無限感的理想。科爾維爾1944年的作品《寂寞的奈梅亨》中,陣亡將士如同冰冷的機器一樣排列。這種表達戰爭的結果比直接描述戰爭行動場面的方式更為深刻,使人產生諸多聯想,最后讓人陷入一種深深的悲傷之中。因為經歷過殘酷的戰爭,科爾維爾強烈體會到創作出對戰爭的親身體會是自己的使命。在戰爭的經歷中,科爾維爾不斷面臨著藝術表達的兩個疑問。一個是對傳統藝術了解的缺乏,藝術源流及技法可以通過學習博物館的古代大師作品加以借鑒參考。另一個是作為戰爭毀滅的見證人,如何把主觀印像與對戰爭的思考統一起來。1952年及1953年的作品《碼頭上的四個人》《火車站的士兵與姑娘》是這一時期的探索,畫面表達的是一種的抽象記憶,在離別與思念中反映的理想形象。他不是對客觀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表現來自經歷記憶及想象。戰后,科爾維爾的職業生涯面臨在從教與商業藝術家的選擇,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母校的邀請,穩定的生活保障讓他遠離各類藝術活動的影響,有時間去消化吸收博物館的前輩經驗,并持續經營自己的藝術生涯。這一過程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科爾維爾也毅然辭去教職,全身心投入到藝術創作中去。
二、創作方法與藝術風格
成熟時期的懷斯與科爾維爾的繪畫風格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以極為精確的筆觸見長,細密且嚴謹,結構井然有序,邊緣性體清晰明了傳達出強烈的繪畫形式感,有古典時代大師遺風,從中可以感受到文藝復興時代大師波提切利對理想形象追求的傳承,及那個時代對理性與次序的把握。可以肯定的是,相比較古代社會,許多現代畫家會參照照片復制描繪,但是兩位畫家依舊遵照非常傳統的方式進行創作。科爾維爾就舉例說“照片是照出來的,而繪畫是創作出來的”。
1.工具材料的選擇
觀看懷斯作品容易被其中泛著啞光干枯深沉的棕褐色調吸引,像是泛著泥土的芳香體現著大地的雄渾,這是使用早期文藝復興最為常用的蛋彩畫顏色表現,在涂滿石膏的底板上用乳液(蛋黃)混合礦物顏色調色作畫,相較于油彩畫的光澤感,懷斯更喜歡蛋彩畫含蓄的色彩表現,不像油彩的緩慢干燥,蛋彩速干的特性也可以讓懷斯在畫室一遍遍地反復描繪一件作品,在耐心與工細的技巧中不斷接近畫的精髓
相較于懷斯使用更為古老的蛋彩作畫,科爾維爾通過不斷嘗試,在20世紀60年代選擇了一種現代工業生產的顏料代替那就是丙烯顏色材質,它們都有速干的特質,但丙烯化學性質更為穩定。他用無數細密的點狀筆堆疊觸描繪接近蛋彩畫的創作方法,但色彩更為明亮。
2.藝術觀念及創作過程
懷斯與科爾維爾繪畫的構思構圖都是通過一閃而念的映像得以啟發,歷經不斷醞釀及對草圖不斷修改而趨漸成熟。
通過描述身邊“通俗”的生活片段去表現永恒價值的命題,是科爾維爾鮮明的藝術特色,他從不認為生活是枯燥且平凡的,人民不能背離自己所有的基本經驗,他通過描繪平凡之物創造了不平凡,并在傳統中找到了與現代的關聯,科爾維爾崇尚法國古典大師普桑的名言“我不忽視任何細節”,他在十分精確構圖并描繪形體,每一個形象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設置,并注重他們的幾何形態與相互之間的關系,在這種理性的結構秩序中雜糅理想的形象表達。直到畫面中不能多一分,也不可少一分,這種創作方法可以在早期文藝復興大師弗蘭切斯卡的作品中得到印證。
注重繼承優秀的藝術傳統是科爾維爾與懷斯有別于現代流派畫家們的鮮明特征,美國雖然作為新興的移民國家,但他文藝根底里流淌著歐洲傳統寫實主義精神,這點可以從本土畫家霍默、伊肯斯、霍普等作品中得以體現。懷斯贊嘆前輩畫家霍普以一己之力創造了本土精神的繪畫,這種精神力量持續感染這他,他輕視那些趕時髦,只為去所謂的藝術圣地而遠離故土文化的藝術。懷斯早期作品受父親所崇拜的畫家影響,如丟勒、倫勃朗等,他對草地的精微細致的描繪可以在丟勒的畫中找到基因的傳承,他對肖像的熱衷,從倫勃朗對人物復雜狀態下精神升華的啟示,懷斯曾述說他創作《愛國者》這幅肖像畫的過程經歷,雖然畫的是一個具象的人,但他含有抽象的含義,他代表含有同一類精神的人,雖然單純但能產生無限情感,但懷斯不會刻意尋覓一個可畫的題材,他會保持大腦空白,隨時接納一種由信息而產生的共鳴,然后快速地畫出微妙的神情。這其實是記憶深處抽象的本質,在創作過程中人物并不是照片,他雜揉了藝術家的經驗與幻想。大多數藝術家僅僅注意對象本身所處的狀態,但懷斯卻探究形成他的各類因素,在正稿繪制《愛國者》時他會想象人物從戰場中走來,身上混合戰壕及木廠的味道,調出暗紅色的皮膚來自風吹日曬等等,具象的形象雜糅了許多這種抽象的想象。
3.隱喻的表達
懷斯與科爾維爾的繪畫特色有來自文學的啟發并與之具有相似性,充滿詩意的文學表達與哲學的隱喻思考。
科爾維爾廣泛的閱讀詩歌哲學與現代小說,繪畫中的形式感與文學的常用手法相似,用精確的構圖引導讀者站在畫家的角度觀看并與之交流,畫面中的元素符號也充滿隱喻的表達,這也是文學常用的表達手段,他的繪畫物象既是虛構的自然場景,又是隱秘的象征,如《柏林公共汽車》的空間結構及元素組合就是充滿這種文學氣質的作品。從1971至1978年畫家從構思到苦心孤詣幾易其稿,到最終完成,畫面中奔跑的女孩置于現代城市社會中,背景是運輸承載的公共汽車,前景是寫有公證人的廣告牌,地面的石板鋪設充滿次序感,既是具體的物象,但又處理成幾何形體的概括,一切都在暗示著高效秩序的文明社會。女孩在其中瘋狂奔跑,仿佛要逃離,但無陰影地處在騰空中的身體,仿佛她又是游離在這個時空中,毫無力量,仿佛要被時空吞沒。科爾維爾創造了一個夢幻的世界,他一筆一劃創造了符合這個世界的本身邏輯,但他又在某種程度上真實存在于我們的真實世界中。
在面對生命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問題,科爾維爾企圖探索具體的實質性的表達形式,這點與他推崇的作家康拉德十分接近或,康拉德認為文明是一段由黑暗混沌向光明清晰的進化過程,是由未知非理性的混亂漸變到秩序井然的狀態。這點與科爾維爾的創作過程接近,在現實生活的情感中理出頭緒,不斷從中擇取素材并加以草圖,按步驟嚴格構圖精細描繪,最后賦予具體的形式與秩序化的藝術體現。所以他的創作手法并不是客觀照相寫實主義的,而是從客觀具體形象的改造進化而來,其中結合傳統繪畫精確的幾何設計再與經驗技藝情緒的糅合,充滿隱喻的特質。這點在他作品《馬與火車》中表達的較為深刻,讓人頭意猶未盡。科爾維爾曾給詩歌做過插圖,具有文學的淵源,他讀到過南美詩人的一首詩,用頭腦對抗一個兵團,用匹黑馬去對抗一列裝甲車。詩歌描述的意味和極具張力的現場感啟發他創作了這幅作品,黑馬義無反顧地奔向了遠處疾馳而來的火車,還未到相撞的那一刻,懸而未決,但如此的結局是震撼人心的,工業機械物質與情感心靈肉體的對抗這是科爾維爾繪畫的詩作表現 。
懷斯的繪畫充滿鄉土詩意,其幼年成長時期一直沒有離開過老家村子,并難得接近學校與城市,自然對田園故鄉有種格外的濃郁情感。作為導師的父親也特別欣賞文學家對自然純樸的描繪,如梭羅福斯特與惠特曼的散文與詩。在父母與家庭教師的教育下,培育出他對文藝的愛好、敏銳的觀察力及對事物有深刻描述的才能。懷斯的繪畫主題就一直徘徊于自己的故鄉,懷斯的一些風景畫如《海風》也展現出意味深長的氣質,但他并不止步于此,因為戰爭創傷的時代大背景及父親的意外身亡,一些受難追悼的景象也時常以隱喻或象征的形式出現在畫面中,過分的不安及戲劇化的效果,懷斯在探索于平凡事物中創造無限的理想,《她的房間》中背景窗外的大海隱喻著海難風暴,前景深沉的木柜及雪白的海螺是棺木與白骨的象征。懷斯以其豐富的聯想與記憶賦予了這張畫悲涼莊嚴的隱喻氛圍。
懷斯不斷地描繪干枯的草地與白雪,讓人不可避免地聯想到蕭瑟的秋冬季節。那幽暗的房屋閣樓、逆光的窗戶讓人處于灰暗的視覺包裹,各類冰冷光線下物體的粗糙質感絲毫沒有溫暖之意,卻顯得深沉厚重,懸置的繩子衣物掛鉤等不對稱的構圖讓人時刻有種不穩定的威脅感。這些事物都是懷斯充滿隱喻的象征用以托物言志。這種表達方式與19世紀的美國文學有相似之處。“他們不愛明確地表明一件事情卻總是一語雙關”勞倫斯在他的《論美國古典文學》中有類似表達。
三、理性、秩序、寂靜與抽象的集合
綜上所述,我們對比懷斯與科爾維爾,他們年齡相差三歲,處于同一時代,幼年時期因為患病以及很少參與集體生活而依靠繪畫排遣孤獨,成長過程中都承受苦難,在職業生涯走向成熟的過程中,他們都毅然放棄較為穩定的職業,全力以赴投向純藝術創作的事業。家庭背景、創作方法、繪畫語言的諸多相似之處讓他們的繪畫氣質相近。
觀看懷斯與科爾維爾的繪畫作品總會讓人有種意猶未盡之感,充滿玄外之音。他們都崇尚繪畫的具象表現,但很大程度上他們的繪畫卻是蘊含抽象的意味,畫面中具象的形象只是他們表達抽象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現形式。通過對比不難發現他們畫面空間都有平面化處理,這和東方傳統繪畫繪制方法有共通之意,就如同中國傳統文人畫通過犧牲畫面的三維空間及過度的寫實性來強調畫面的意境所在。他們對畫面的物體背景加以提煉、精簡,刪除過多細節,運用留白的處理手法,讓人從具象的細節中抽離出來并關注于畫面整體結構的韻律,很大程度上給予觀眾無限的聯想空間。畫面物體也多呈幾何化概括,20世紀初的西方立體派等畫家就常用幾何形概括具體形象去表達一種抽象的意味,這點來源于古典主義的精神,古典主義強調穩定感和秩序感,而特定的幾何形體會強化這種感受,懷斯與科爾維爾的畫中有大量的水平線、垂直線作構圖的切割,形成一種莊重肅穆感,而其中包含著概括成三角形、方形、梯形等幾何形體的物體交相呼應,具有強烈對比的形式感。他們的這種創作方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們從生活場景中抽取,沉淀生活的細節,從中條理出秩序,通過不斷地對比、平衡,最終精確自己的構思,雖然追求畫面的形式美是極具現代性的,但是精神內殼是理性、寧靜的古典美。
這種理性主義精神是一種認識論與方法論,是西方思維方式與理論的根基。強調嚴謹的形式法則并講究秩序感,作為同屬于北美大陸新移民的后代,他們有西方傳統的直接影響,科爾維爾的作品在幾何構圖的設計下每個物象有其固有的幾何化的形態。懷斯作品在極致細致的描繪中隱藏了這種整體結構的幾何構圖設計,懷斯對人物特征氣息的把握精到,其嚴謹扎實的形體結構是文藝復興后期自然主義的延伸,但科爾維爾卻更多地在早期文藝復興繪畫的形式感中體會到與現代社會情緒的某些共鳴,人物具符號化偏裝飾性的描繪。或許懷斯有更多的家學淵源,對于描繪的真切是懷斯父親的立身之本,他把這些遺傳給懷斯,但懷斯在此更近一步,即更為深刻的形象塑造體現出的無限意義并不局限于插畫的故事敘述,科爾維爾在軍旅生涯的體驗中關切于物象之間的關系,幾何化抽象形態代了普遍的人,他們之間的結構關系處理是人們面臨的永恒命題。高調明晰的色彩對比壓縮了空間深度,幾何結構的圈定顯得寂靜永固,把這家庭、社會、自然等等這些永恒主題直面觀眾。如果說科爾維爾通過削弱物象本身著重描繪物象之間的關系去探究人類社會的永恒問題,那么懷斯則把對家鄉的熱愛賦予物象細節的本身,把結實的結構賦予物象構造永恒的雕塑感,像古代大師觸摸式的雕琢,色調統一沉穩厚重,構圖的空曠是思索的空間給予靜謐的惆悵感。深厚的傳統背景沒有把他們禁錮,他們致力于依靠傳統發掘自身世界的寶藏。
懷斯與科爾維爾一生都沉浸于自己的藝術世界耕耘,他們選材于自己最為熟悉的人和物,但他們的聲名鵲起并不是僅僅作為地方上或是區域內獵奇的具象繪畫大師,他們關注的是永恒的生活與生命的基本問題,這是他們具象表現中抽象精神的內核,并不隨時代潮流而湮滅,近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對于我們是誰?我們像什么?我們干什么?等等這些現代社會時刻面臨的問題在愈發明顯的呈現,他們作品的觸及與印證搭建了觀者與畫家之間的橋梁,便愈來愈受到矚目并得到國內外藝術家們的廣泛學習,對于立志用繪畫藝術去解決即將面臨的問題,他們豐厚的作品財富給予人們深刻聯想與啟示并時刻激勵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