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振興視角下民俗紅包的價值挖掘與傳承探析
張 璐 姜夏旺
通訊作者姜夏旺(1980—),男,浙江衢州人,湖南工業(yè)大學(xué)包裝設(shè)計藝術(shù)學(xué)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產(chǎn)品設(shè)計理論與應(yīng)用研究。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xí)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工作,并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結(jié)合時代要求繼承創(chuàng)新,讓中華文化展現(xiàn)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fēng)采。[1]民俗紅包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見證了中國幾千年來源遠(yuǎn)流長的文化傳承,傳統(tǒng)民俗紅包是人們在物質(zhì)文化滿足的基礎(chǔ)上對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種呈現(xiàn)載體,其蘊含著豐厚的美學(xué)、民俗學(xué)、設(shè)計學(xué)、社會學(xué)等學(xué)術(shù)價值。對傳統(tǒng)民俗紅包中所積淀的文化符號、思維方式和精神內(nèi)涵多元化價值的挖掘有助于弘揚與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2]以及構(gòu)建中華兒女共同情感的精神家園。
二、民俗紅包的歷史特征與變遷
通過對“紅學(xué)”“敦煌學(xué)”等歷史文獻(xiàn)與資料的查閱、大量的田野調(diào)查、紅包樣本收集與分析等工作后,從紅包的呈現(xiàn)形態(tài)、名稱、作用及意義并結(jié)合不同時期的變遷角度出發(fā),將近現(xiàn)代紅包的歷史特征變遷分為明清之前的紅包(紅包的啟蒙期)、明清時期的紅包(紅包的發(fā)育期)、近代時期的紅包(紅包的成熟期)、現(xiàn)代時期的紅包(紅包的流變期)這四個階段。
紅包最早的概念叫 “厭勝錢”(“厭”通“壓”),出現(xiàn)于漢代(1)班固.漢書·王莽傳[M].東漢,第六十九下,第855頁.,是作為求其吉祥之意的器物,其主要呈現(xiàn)形態(tài)為帶有各種不同裝飾紋樣的銅制錢幣,有驅(qū)邪祈福的作用。(見圖1)在《后漢書·清河孝王慶傳》中記載:“因巫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shù)。” 此處指的“厭勝”特指用迷信的方法來驅(qū)邪的意思。明清時期才正式有“壓歲錢”之說,對于這時期紅包的主要形態(tài)與意義,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中記載:“以彩繩穿錢,編作龍形,置于床腳,謂之壓歲錢。尊長之賜小兒者。亦謂壓歲錢(2)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10卷.。”(見圖2)近代時期的紅包依然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壓歲錢,但在材質(zhì)和裝飾上有了極大的變化,祈福的意義逐漸弱化,作為貨幣本身的價值更為突出,紅包封以紙配彩圖為主。印有“壽星公”“滿堂吉慶”等民間色彩濃厚的圖案。(見圖3)當(dāng)代紅包的功能呈現(xiàn)多樣化態(tài)勢,且“派紅包”的習(xí)俗變得意義多樣,趨于日常化。當(dāng)代紅包在圖案裝飾上出現(xiàn)卡通人物、多元插畫等,形式上出現(xiàn)趣味立體結(jié)構(gòu)、不規(guī)則形狀等,色彩也不僅僅局限于紅色。(見圖4)隨著數(shù)字時代的到來,新興的數(shù)字紅包也流行于大眾之間,盡管紅包的呈現(xiàn)形態(tài)及所利用的媒介與技術(shù)手段越來越多樣化,但都是對我國傳統(tǒng)禮俗文化與吉祥文化的弘揚與傳承。

圖1 漢代厭勝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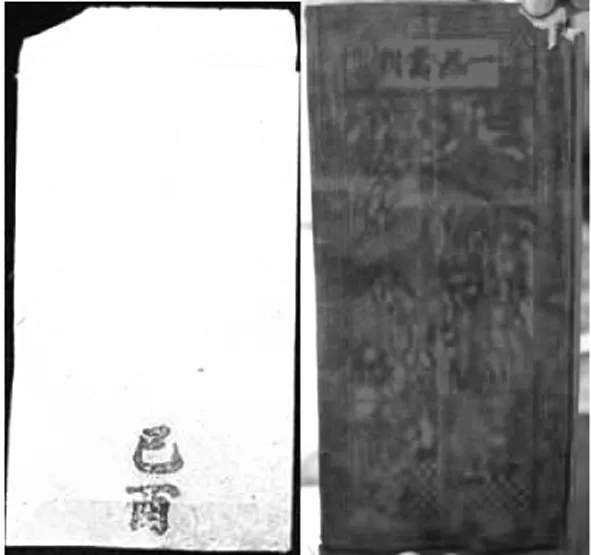
圖2 清代紅包封

圖3 民國紅包封

圖4 近現(xiàn)代早期紅包封
三、民俗紅包的價值挖掘與整理
(一)重拾民俗紅包蘊含的價值
隨著數(shù)字化時代的快速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人對實體紅包的意識逐漸淡化,亦或有著認(rèn)知的誤區(qū),單純地認(rèn)為紅包只是一種裝錢的袋子,是走捷徑的“金鑰匙”,[3]忽略了紅包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價值、美學(xué)價值等。基于時代快速發(fā)展下人們對于紅包內(nèi)涵的認(rèn)知差異與誤區(qū),所以對民俗紅包中所蘊含的“文化自信與美好生活”進(jìn)行價值重拾是極為重要的。
從紅包與歷史的角度重拾民俗紅包所蘊含的價值。紅包自誕生之日(漢代)起至今(2022年)已經(jīng)有2000多年的歷史,所以紅包的流變成了對應(yīng)時期文化的承載樣本。從漢代開始的厭勝錢到現(xiàn)如今的紅包都是作為人們對于美好生活向往與祝愿的物化產(chǎn)物,并沿襲至今。民俗紅包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于民間,傳承于社會,以小小紅包為載體服務(wù)于民族群眾,連結(jié)的是民族精神的文化根脈,是一種集體性的文化積淀,是人類物質(zhì)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呈現(xiàn)。[4]
從紅包與人的角度重拾民俗紅包所蘊含的價值。民俗紅包作為人們凝結(jié)情感歸宿和精神寄托的物質(zhì)載體,穿梭在年節(jié)、祝壽、婚慶等各種場景中,其所滲透出來的親情、友情、愛情和溫暖溢于言表,這也闡釋著中國人尊老愛幼、孝悌感恩的倫理道德。這也體現(xiàn)了民俗紅包背后更多的是禮儀文化、人際關(guān)系的滋養(yǎng),是我們生活昌盛的象征。
從紅包與社會的角度重拾民俗紅包所蘊含的價值。紅包的傳承和流變過程中透視著當(dāng)時社會風(fēng)氣、社會文化,更透視著政治文化的引導(dǎo)方向。紅包作為民俗禮節(jié)和精神文化的傳播路徑,對構(gòu)建和諧禮儀社會和維系社會關(guān)系是極為重要的,人們互贈紅包的互動行為正是維系人際關(guān)系的紐帶,更是情感與責(zé)任、擔(dān)當(dāng)?shù)纳鐣婷驳某休d。
(二)民俗紅包的價值構(gòu)成要素
1. 美學(xué)價值——真、善、美
紅包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寶貴財富,其蘊含的真、善、美是對我國先民思想、情感觀念的凝練,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紅包作為中華民族約定俗成的一種物質(zhì),是生活之美的創(chuàng)造,是中華美學(xué)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5]從古至今代代相承并隨之被賦予各種精神文化內(nèi)涵。民俗紅包美學(xué)價值中所蘊含的“真”正是根植于人們真實的社會生活以及人們對于社會生活的認(rèn)知,正如紅包所傳遞的吉祥文化,其是在先人無法與大自然抗衡的狀態(tài)下逐漸產(chǎn)生,并隨著時間和社會的演進(jìn)而逐漸豐富的。在紅包美學(xué)價值中所包含的“善”,是人們對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種積極態(tài)度,在人們饋贈紅包時,其所滲透出來的親情、友情、愛情都充滿善意與溫度。美學(xué)強(qiáng)調(diào)真與善的統(tǒng)一,而紅包的“美”正是人們在傳遞美好祝福與愿景中涵蓋的。
2. 設(shè)計學(xué)價值——設(shè)計規(guī)律與方法
對紅包設(shè)計學(xué)價值的挖掘主要體現(xiàn)在其設(shè)計規(guī)律與方法上,無論是字體演變、圖形演變、結(jié)構(gòu)演變、色彩演變等,均可從中窺探我國先民的審美演變及設(shè)計方法的迭代。在紅包字體設(shè)計中,所采用的設(shè)計方法主要為字體結(jié)構(gòu)變形設(shè)計、字體意境化設(shè)計、字體圖形化設(shè)計以及字體裝飾化設(shè)計。如圖5所示紅包基于形式美、意蘊美的法則對吉祥文字筆畫進(jìn)行可對應(yīng)的祥云紋、魚紋、如意紋等吉祥圖案的轉(zhuǎn)換設(shè)計,在不改變文字識別性的基礎(chǔ)上使得字體更具裝飾性與審美性,其所采用的是字體圖形化以及裝飾化設(shè)計方法。圖形設(shè)計作為紅包的視覺中心,其創(chuàng)作的主要方法為民間傳說的借用、宗教信仰的延伸、諧音寓意、象征符號的運用、以字為圖的搭配。例如在象征符號的應(yīng)用中,蟠桃、仙鶴、松柏是用來象征長壽的符號,牡丹、芙蓉、錢幣是象征富貴的符號。

圖5 《福祿/富貴/吉祥/如意》紅包
3. 民俗學(xué)價值——民族認(rèn)同、美好期許
對紅包民俗學(xué)價值的挖掘不僅有利于民俗紅包背后價值結(jié)構(gòu)網(wǎng)的完善,更有利于豐富我國傳統(tǒng)民俗文化。民俗學(xué)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的基因,是樹立民族精神和構(gòu)建國家意識的文化基礎(chǔ)。[6]紅包所體現(xiàn)的民俗學(xué)價值是我國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社會事象的映射,反映了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文化,[7]能夠讓我們認(rèn)識民族歷史與傳統(tǒng)禮俗文化,從而獲得民族認(rèn)同感。紅包具有祈福、禮儀、傳承、裝飾等功能,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勞動人民對民族傳統(tǒng)的認(rèn)可及美好生活的期許。紅包文化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對生活美好祝愿與期許的情感紐帶,其傳達(dá)出來的親情、友情、愛情的溫暖溢于言表,理所當(dāng)然地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4. 社會學(xué)價值——文化自信、社會和諧
從社會學(xué)角度審視紅包的價值,可以說在民族文化自信、華人情感紐帶及社會和諧等方面,紅包均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紅包文化作為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其所傳達(dá)出來的吉祥觀念背后蘊含的吉祥文化、擇吉文化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思想觀念和宗教信仰。中國傳統(tǒng)民俗紅包中所蘊含的文化優(yōu)勢讓中華兒女擁有更加堅定的民族文化自信,增強(qiáng)民族自豪感。在每年春節(jié)及傳統(tǒng)節(jié)日等重大場合,國內(nèi)民眾以及海外華僑都會進(jìn)行紅包派發(fā)的民俗活動,對這一活動的傳承凝結(jié)著濃厚的無價親情,闡釋著中國人尊老愛幼、孝悌感恩的倫理道德,這對社會和諧的維護(hù)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促進(jìn)了國內(nèi)民俗文化對外的傳播。
四、民俗紅包價值的傳承運用
(一)意蘊賦能:美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
民俗紅包是基于人們生活之美的創(chuàng)造,融入了中華民族對美的價值理解與表達(dá),反映著人們的美學(xué)觀,是中華美學(xué)精神體現(xiàn)形式的一部分。從古至今人們所創(chuàng)造的眾多吉祥文化符號,所反映出來的美學(xué)思想、美學(xué)特點、美學(xué)工藝、美學(xué)元素等共同組成了民俗紅包獨有的價值體系。對于民俗紅包所蘊含的美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可以貫串人們的生產(chǎn)與生活,有助于復(fù)興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激發(fā)人們對于美的物質(zhì)與精神上的追求,創(chuàng)造現(xiàn)代生活中更多的真善美,實現(xiàn)美的傳遞與關(guān)懷。
(二)形式賦能:設(shè)計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
民俗紅包設(shè)計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屬于應(yīng)用型操作,主要是將紅包藝術(shù)價值中的文化元素進(jìn)行轉(zhuǎn)化,經(jīng)過篩選、提煉、組合,將抽象的文化元素進(jìn)行轉(zhuǎn)化,從而轉(zhuǎn)化為具象的設(shè)計語言,再結(jié)合新興技術(shù)、工藝、材料、綜合性的設(shè)計手段等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給予民俗紅包多元化的呈現(xiàn)形式,以傳達(dá)民俗紅包所蘊含的吉祥文化與美好愿景。對民俗紅包設(shè)計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旨在根植傳統(tǒng),融會時代發(fā)展的新價值導(dǎo)向,開發(fā)更符合新時代人們情感需求并兼具生活實用價值與美學(xué)意義的優(yōu)秀民俗紅包作品,[8]以促進(jìn)傳統(tǒng)文化傳播,樹立文化自信。
(三)媒介賦能:民俗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
紅包中所蘊含的民俗與民眾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相關(guān),是中華民族集體再現(xiàn)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對于民俗學(xué)價值的傳承可以通過人們的思維記憶、儀式展演、圖像表現(xiàn)等方式進(jìn)行,而面對不同的民俗形式則需要利用跨媒介和語境的方式來進(jìn)行傳承運用。在這一過程當(dāng)中可以借助當(dāng)代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的信息傳播性能,讓傳播、接收、發(fā)散成為一種自由的個體或是大眾行為,形成一種全新的信息化語境的產(chǎn)生。將民俗紅包所蘊含的豐富的民俗學(xué)價值傳承運用好,要把民俗文化與當(dāng)今社會價值取向結(jié)合起來,以增添時代氣息與社會生活氣息,這也有助于讓民俗文化“活起來”,并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增強(qiáng)民族認(rèn)同感。
(四)精神賦能:社會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
民俗紅包所滲透出來的親情、友情、愛情都是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最好的詮釋,這也正與社會學(xué)價值所映射出來的維系民族情感、認(rèn)知與教化相對應(yīng)。對于民俗紅包社會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是構(gòu)建和諧禮儀社會、弘揚中華民族氣節(jié)與文化軟實力輸出的重要途經(jīng)。在對社會學(xué)價值的傳承運用中,可以通過承載著濃濃民族情誼、社會核心價值的產(chǎn)品形態(tài),給予人們豐富的精神體驗,以增強(qiáng)人們的內(nèi)在精神力量,為增強(qiáng)文化自信提供有力的支撐,進(jìn)而促進(jìn)社會穩(wěn)定與和諧。[9]
五、結(jié)語
通過對于民俗紅包價值構(gòu)成以及傳承運用的梳理與分析,準(zhǔn)確地傳達(dá)出民俗紅包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物化體現(xiàn),并大力弘揚紅包所傳達(dá)出來的正能量。讓人們了解小小紅包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內(nèi)涵以及更深層次的價值結(jié)構(gòu),感受中國傳統(tǒng)民俗文化的魅力,增強(qiáng)文化自信與民族認(rèn)同感。新時代設(shè)計師想要設(shè)計出既符合當(dāng)下人們審美要求又獨具文化內(nèi)涵的民俗紅包,必須在準(zhǔn)確理解民俗紅包的歷史特征與其多元化的價值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上,形成傳統(tǒng)民俗文化的物化呈現(xiàn)和文化支撐,讓我們的傳統(tǒng)民俗紅包在新時代下煥發(fā)生機(jī)與活力,傳遞濃厚的文化底蘊和民俗風(fēng)情,以此更好地反映和展現(xiàn)人們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