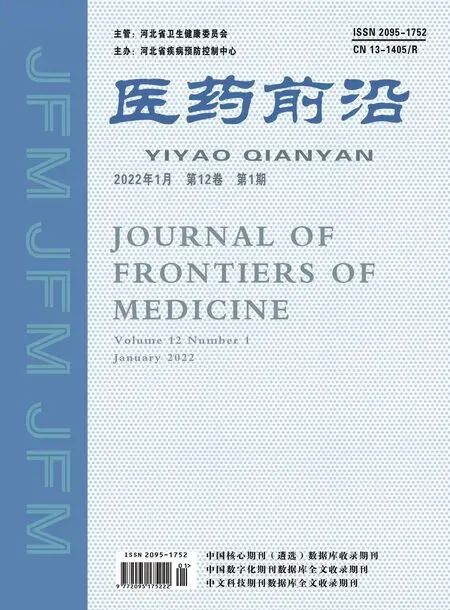針刀聯合理療和按摩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的臨床效果探討
余惠愛,陳敏茹,李鐘華,劉 奮,區燕云(通信作者)
(佛山市南海區第四人民醫院骨二脊椎專科 廣東 佛山 528211)
腰椎間盤突出癥是臨床上較常見的疾病,其是因腰椎間盤退行性病變,好發于中老年人群,該類患者主要表現為腰腿疼,給其日常生活、工作造成極大的影響[1]。該病主要由于腰椎生物力學在外力的牽拉下而造成平衡失調,長時間因各種損傷的作用下,其軟組織出現病理改變,例如瘢痕、粘連、攣縮等,從而導致腰椎生物力學平衡改變,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脫出[2]。臨床針對該病主要使用非手術與手術治療為主,其中非手術治療包含推拿、理療等,雖能起到良好的臨床效果,但其起效緩慢,導致患者依從性相對較低。但臨床實踐表明,80%~90%初發性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可通過非手術方式消除癥狀,提高生存質量。但手術治療的創傷較大,大部分老年患者不能耐受。中醫認為腰椎間盤突出癥屬“腰痛”范疇,可通過穴位按摩進行基礎保健治療,具有疏經通絡、消除炎癥的作用,能顯著減輕疼痛。同時,中醫針灸在該病中的應用效果逐漸凸顯,針刀作為中醫外治的重要器械,其有效的融合外科手術到與針灸針刺的特點,能有效疏通經絡,改善神經根微循環[3]。為此,本文就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開展針刀聯合理療、按摩治療進行探討,以便為日后臨床制定治療方案提供可靠的參考。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1 月—2020 年2 月本院收治的94 例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根據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與干預組,各47 例。對照組男25 例,女22 例,年齡38 ~67 歲,平均年齡(47.25±3.57)歲,病程1 ~7 年,平均(4.27±1.37)年;干預組男26 例,女21 例,年齡38 ~70 歲,平均年齡(47.41±3.62)歲,病程1 ~7 年,平均(4.22±1.31)年。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納入標準:①入組患者均符合《腰椎間盤突出癥分級康復診療指南解讀》[4]中相關診斷標準;②均經影像學檢查證實;③患者檢查資料完整,無缺失,對此次研究均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伴有脊柱炎、椎管狹窄等其他脊柱性疾病;②伴有重大器官嚴重障礙的患者;③伴有惡性腫瘤的患者;④伴有認知障礙、精神疾病不能配合疾病的患者。
1.2 方法
入組患者均給予基礎理療,即針對急性發作期囑咐患者使用硬板床休息,體位自由,維持3 周,每次臥床時間不宜過長,適當站立活動,囑咐患者佩戴腰圍,從而緩解腰椎負荷,臥床時解除腰圍。對照組接受按摩治療,協助患者選取俯臥位,操作者站于其右側,使用肘部點按腰背部肌肉、環跳穴,連續5 ~10 min;雙拳按壓脊柱兩側肌肉,5 min;拇指推撥臀上部肌肉,5 min;2 d/次,連續治療15 d。干預組基于此開展針刀治療,即協助患者選取俯臥位,常規局部消毒,于要腰骶椎椎旁壓痛處,行慢性疼痛治療,給予0.5%利多卡因局部麻醉(2 ~5 mL),給予針刀松解術,垂直進針,刺破筋膜后,給予點式松懈術,出針,治療后給予無菌紗布按壓止血(2 min),針眼處予以無菌敷料覆蓋。
1.3 觀察指標
詳細記錄兩組患者治療前后CT 檢查結果、血清炎性因子、疼痛介質指標、疼痛程度、腰椎功能及生活質量。(1)CT 定量分析:包含椎間隙高度、突出物體積、椎體滑移度。(2)血清炎性因子:包含血清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 IL-1β)。(3)疼痛介質:包含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 PEG2)。(4)疼痛程度使用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進行分析,使用游標卡尺標記0 ~10 刻度,由患者根據自身癥狀選擇疼痛程度,分值與疼痛程度呈正比。(5)腰椎功能:使用日本骨科協會評估治療評分(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JOA),共計0 ~29 分,分值與腰椎功能呈正相關關系。(6)生活質量使用世界衛生組織生存質量測定量表簡表進行評分(WHO Quality of Life-BREF, WHOQOL-BREF),包括社會、心理、生理、環境四個項目,每項25 分,分值與患者生活質量呈正比。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n)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 兩組血清炎性因子、疼痛介質指標比較
治療后,干預組患者TNF-α、IL-1β、5-HT、PEG2指標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血清炎性因子及疼痛介質指標比較( ± s)

表1 兩組血清炎性因子及疼痛介質指標比較( ± s)
IL-1β/(ng?L-1)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干預組 471.31±0.24 0.81±0.10 1.33±0.25 0.81±0.11對照組 471.29±0.22 0.98±0.13 1.31±0.24 0.99±0.13 t 0.4217.1060.3967.246 P 0.6750.0010.6930.001組別 例數TNF-α/(g?L-1)PEG2/(mg?L-1)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干預組 470.97±0.10 0.31±0.07 34.35±4.54 18.52±3.19對照組 470.98±0.11 0.48±0.10 34.85±5.21 23.77±3.71 t 0.4619.5480.4967.356 P 0.6460.010.6210.001組別 例數5-HT/(mmol?L-1)
2.2 兩組CT 檢查結果比較
治療后,干預組患者椎間隙高度高于對照組,突出物體積、椎體滑移度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CT 檢查結果比較( ± s)

表2 兩組CT 檢查結果比較( ± s)
突出物體積/cm3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干預組 47 12.11±2.13 13.88±2.61 0.30±0.14 0.20±0.14對照組 47 12.14±2.34 12.17±2.56 0.31±0.13 0.29±0.13 t 0.0653.2070.3593.230 P 0.9480.0020.7210.002組別 例數椎間隙高度/mm

表2(續)
2.3 兩組患者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比較
治療后,干預組患者疼痛程度評分低于對照組,且腰椎功能指標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比較( ± s,分)

表3 兩組患者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比較( ± s,分)
腰椎功能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干預組 476.37±0.92 3.58±0.72 14.26±2.31 22.39±2.83對照組 476.29±0.98 4.51±0.82 14.18±2.26 18.53±3.67 t 0.4085.8430.1705.710 P 0.6840.0010.8670.001組別 例數疼痛程度
2.4 兩組患者生活質量評分組間比較
治療后,干預組患者生活質量評分各指標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生活質量評分組間比較( ± s,分)

表4 兩組患者生活質量評分組間比較( ± s,分)
心理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干預組 47 17.15±2.18 21.51±1.25 16.63±2.26 20.73±2.21對照組 47 17.08±2.13 19.27±1.83 16.73±2.31 18.36±2.03 t 0.1576.9290.2125.414 P 0.8750.0010.8320.001組別 例數社會環境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干預組 47 15.83±3.02 20.54±2.63 17.65±2.08 21.63±1.97對照組 47 15.78±2.94 18.13±2.73 17.49±1.98 19.72±1.72 t 0.0814.3590.3825.001 P 0.9350.0010.7030.001組別 例數生理
3.討論
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發病機制相對繁雜,主要以腰椎間盤髓核、纖維環及軟骨板退行性病變等因素而致。該病患者病程長、臨床癥狀顯著,具有發病率高、易反復等特點,調查顯示,中青年人群中其發生率約為64.46%,該病對患者日常生活構成極大的影響,導致其生活質量降低,嚴重者會引發馬尾神經損傷,從而導致馬鞍區感覺障礙,影響大小便功能異常,甚至出現癱瘓[5]。針對該類患者理療與按摩最為常見,按摩具有活血通絡的效果,能有效緩解疼痛癥狀,但整體效果不佳,病情反復,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6]。
中醫學認為,腰椎間盤突出癥屬于“痹癥”“傷筋”等范疇內,該病主要是因經脈凝滯不通,不通不榮而導致疼痛而致,針對該類患者需以活血化瘀、疏風散寒、通經止痛等治療原則為主。本文結果顯示,相較于對照組,干預組患者且CT 檢查各項指標均顯著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T 檢查能有效探查患者椎間盤內部結構,對該病做出精準的評估,為臨床治療提供可靠的參考[7]。該檢查的直接征象表現為側方或正中椎管內局限性突出,密度與相應的椎管盤一致;間接征象可見硬膜外脂肪層結構狹窄、移位或消失,周圍骨結構異常改變,突出的髓核周圍表現為反應性骨硬化。為此,針對腰椎間盤突出患者CT 值與療效具有一定負相關關系。同時針刀能有效的松懈粘連,可改善局部微循環,緩解無菌性炎癥癥狀,促使炎癥代謝物吸收,從而降低血清炎性因子表達水平。PEG2 會導致血管擴張、神經水腫,是疼痛生產的重要介質;5-HT 受體分布于神經終于與外周組織中,其能參與疼痛、情感等多種調節[8-9]。而本文另發現,相較于對照組,干預組患者血清炎性因子、疼痛介質指標及疼痛評分均降低,且生活質量提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該治療方式能降低患者機體內疼痛介質與炎性因子的表達,從而緩解疼痛癥狀,促進炎癥吸收,改善臨床癥狀。小針刀治療重在松解疏通,有助于氣滯血瘀型腰椎間盤突出癥通絡止痛、疏風化瘀,針刀對疼痛結節點進行剝離與松解,松解突出髓核壓迫的受損軟組織及深淺筋膜,整復患病節段錯位的椎后關節,恢復生物力學平衡[10-11]。穴位按摩是中醫療法重要組成之一,能促使肌肉放松,減輕疲勞,改善人體功能,進而調節免疫力。按摩特定的穴位,能加快細胞代謝,促進有害物質排出,改善循環,減輕炎癥反應,進而消除腫脹,降低疼痛感[12-13];于此同時,給予理療能增強患者屈髖肌、腹肌肌力,促使突出腰間盤恢復,以改善腰椎功能,同時其能促進腰部血液循環,減輕炎癥反應,緩解疼痛,增強患者健康維護能力,促使病情恢復。
綜上所述,對于腰椎間盤突出癥的患者開展針刀聯合理療、按摩治療效果確切,可緩解患者的臨床癥狀,促進局部炎癥反應吸收,有良好的臨床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