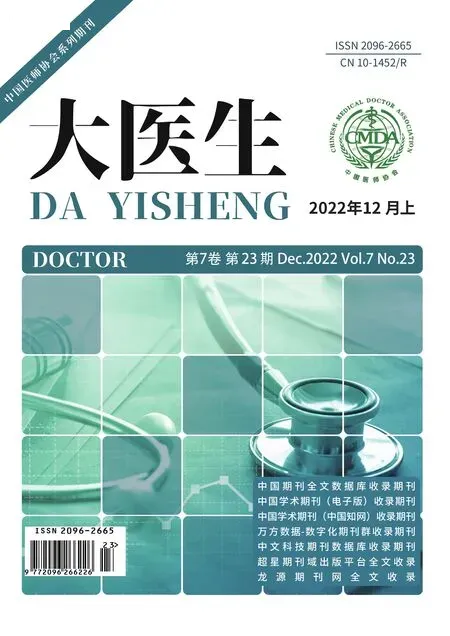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細菌感染的機制及治療研究進展
李爭爭,姜 鵬
(1.新疆醫科大學研究生院,新疆烏魯木齊 830054;2.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總醫院呼吸內科,新疆烏魯木齊 83000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目前公認的表型異質性炎癥性疾病[1],以持續氣流受限、對應呼吸系統癥狀為特征表現,此時氣流受限以不完全可逆、進行性發展為特征,會累及肺或全身各個系統,引起嚴重并發癥[2]。該疾病為危害人類健康的常見病,患病率、致殘率及死亡率高,是世界性的公共衛生難題[3]。COPD 臨床分為穩定期、急性加重期。研究指出,對COPD 患者而言,往往表現出下呼吸道細菌定植[4]。引起COPD 急性加重(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ECOPD)感染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細菌感染,目前對細菌感染發病機制多闡述為以下兩種理論:第一種是指定植菌群變化,新微生物到達支氣管上皮后則延遲免疫反應增加特定新菌株叢,AECOPD 發生概率增加。第二種是認為AECOPD 期患者處于穩定期時,定植病原體濃度水平較高,當細菌濃度增加后,炎癥反應程度隨之增加,一旦超出某個閾值后,則表現出臨床癥狀。如果未及時監測并制約纖毛清除與細菌生長不平衡因素,會引起COPD 惡化。近年來,有學者不斷探討AECOPD 致病病因,認為腸道菌群紊亂同樣是引起AECOPD 發作重要因素,但目前所涉及相關研究內容較少[5]。目前所觸發惡化炎癥反應所需微生物閾值是未知的,同時每種細菌的閾值都有所不同。而了解最常見可觸發菌群對臨床經驗性用藥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本研究就COPD 細菌感染的機制及治療情況進行綜述,現報道如下。
1 COPD 細菌感染分布
COPD 為臨床常見疾病類型,而AECOPD 為患者就診常見原因,其特點為呼吸系統癥狀加重,包括呼吸困難、咳嗽/咳痰惡化,上述癥狀超過日常變異水平,需要及時改變藥物治療方案。早期不及時進行準確治療則造成嚴重并發癥,抑制難度隨之增加。而感染作為急性加重主要觸發因素。國內相關研究指出,不同時期、不同地域AECOPD 期患者致病菌分布、耐藥情況有一定差異[6]。同時,部分文獻報道指出,引起AECOPD 為革蘭陽性細菌,如肺炎鏈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7]。當前COPD 病原菌分布、流行趨勢往往與時間差距、地域差距、地理氣候差異等因素相關聯。國內調查指出,884 例COPD 患者痰培養中,檢出細菌359 株,其中最為常見為銅綠假單胞菌、肺炎克雷伯菌、流感嗜血桿菌、肺炎鏈球菌、鮑曼不動桿菌、卡他莫拉菌,分別占比為21.7%、12.3%、11.7%、11.7%、7.8%、6.4%[8]。
1.1 COPD 穩定期細菌分布 健康人群中,呼吸道內存在數百種細菌定植,菌群共同作用下,會維持上呼吸道穩定性,構建上呼吸道正常菌群生態,并維持呼吸系統正常功能。大多數為無致病性的共生菌,同時也包括致病共棲菌,如肺炎鏈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卡他莫拉菌、流感嗜血桿菌、腦膜炎奈瑟菌、溶血性鏈球菌等。有研究顯示,當COPD 病情穩定時,近40%的患者能檢測到明顯的細菌感染[9]。認為呼吸道存在定植菌群者提出惡性循環假說:在吸煙、有害氣體吸入等始動因素作用下,呼吸道黏膜纖毛清除功能受損后,病原菌定植在上述位置,產物會作用于氣道引起一系列炎癥反應,進一步增加COPD 患者氣道黏膜分泌物,減弱纖毛清除活力,而氣道彈性組織離解后進一步損傷呼吸道黏膜。上述過程中,相互促進、循環往復并造成COPD 病情進展。上述細菌以持續周轉狀態為表現,因胞外產物釋放多種蛋白、低聚糖和肽聚糖等,分泌過多、作用時間長會引起氣道破壞、重塑。有學者指出[10],COPD 為氣道炎癥疾病,穩定期階段下呼吸道內細菌定植下,患者氣道炎癥水平較高,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8(IL-8)水平異常升高,處于高水平下并不會引起氣道急性加重,但往往會造成COPD 不可逆進展,為引起疾病加重重要因素。上述因素持續存在形成了COPD 的不完全可逆及持續進展。
1.2 AECOPD 細菌分布 AECOPD 期細菌感染有兩種機制,一種是COPD 患者原有的定植菌群超出某一正常可承受范圍出現的細菌感染引起的一系列炎癥反應;另一種為COPD 患者氣道中有新的菌種侵襲后所致一系列不良結局,不論哪種細菌感染均可引起AECOPD。也有相關研究證明,大腸桿菌也是AECOPD 期感染常見菌[11]。在病情加重期間,患者的微生物群有明顯變化,這種轉變的性質因患者不同而不同,也會因時間發生變化,因此治療應該是針對患者的,菌群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哪些微生物可以在惡化期間誘導,以更好地支持臨床治療。
2 COPD 穩定期定植菌群和加重期的聯系
COPD 以呼吸道固有免疫損害為表現,增加了外來物的易感性。疾病進展核心內容為炎癥,持續、慢性炎癥刺激下往往會影響正常肺部組織結構,造成肺結構變化、小氣道狹窄及肺實質病變,最終對肺泡與小氣道附著造成破壞,彈性回縮力降低且利于微生物定植。對COPD 患者而言,此時肺部防御系統受損下會影響到呼吸道正常清除能力,病原菌清除障礙會導致繁殖,穩定期表現為呼吸道細菌定植。而地區、時間、研究方法往往與定植種類相關,但多為致病力較小的正常菌群。當患者處于疾病發展階段,機體免疫力降低后,此時病原菌大量繁殖可變為致病菌,而流行最為廣泛的是流感和副流感嗜血桿菌、肺炎鏈球菌、卡他莫拉菌等。研究調查指出,穩定期COPD 患者中,32.6%為呼吸道定植菌[12]。當細菌定植后,往往會增加菌落數量,氣道炎癥反應下加重病情。當黏液大量分泌后則不利于肺部通氣,影響換氣功能,最終不利于黏膜纖毛清除,呼吸道阻塞程度加重,促使細菌定植在下呼吸道。在細菌毒力作用、外產物作用下,損傷呼吸道上皮并加重局部炎癥反應。若處于AECOPD時,常見危險因素則為細菌感染。調查結果指出,123 例COPD 患者急性加重期患者中,細菌感染數量高達12 種,陽性率67.1%,而病原菌分布上,以流感及副流感嗜血桿菌、肺炎鏈球菌、卡他莫拉菌等為主[13]。對其原因分析指出,不同地域、區域內所表現流行病學特征不同,而因不同衛生條件、抗生素使用習慣等,均存在一定差異。
3 腸道菌群與COPD 加重期的聯系
3.1 腸道菌群與COPD 關聯性 呼吸道、胃腸道上皮均有共同胚胎起源,在其根本上表明上述兩者生理結構、免疫功能表現相似。例如,存在廣泛表皮面積,且有豐富血管,由上皮細胞、覆蓋至上層黏膜層共同組成并發揮保護作用,其目的為抵御外來病原體入侵,并發揮屏障作用[14]。腸道菌群在嬰兒階段時開始定植、發育,其組成往往與宿主基因型、分娩方式、飲食及地域和年齡、抗生素的影響相關聯。而腸道菌群受到抗生素影響,與種類、給藥途徑、使用濃度等因素相關[15]。如喹諾酮類抗生素作用于厭氧菌效果較弱,無論口服或靜脈給藥,對腸道菌群所造成影響均較小,但經腸道排泄的β-內酰胺類抗生素則對腸道菌群影響較大。連續使用克林霉素7 d 后,腸道內菌群擬桿菌門多樣性顯著降低,在停藥后2 年內無法恢復至干預前狀態,在使用萬古霉素后,停藥22周后腸道菌群相對豐富可全部恢復至基線水平[14]。
3.2 腸道菌群與COPD 病情進展相關性 COPD 為一類以氣流受限為特征表現的中老年常見慢性呼吸系統疾病,COPD 患者發生炎癥性腸病、腸道癥狀的概率增高,而炎癥性腸病作為誘發COPD 和哮喘危險因素之一。腸道菌群數量、種類同樣能維持肺部健康,且具備顯著作用,宿主肺部免疫反應調節中腸道菌群對其作用機制稱之為“腸-肺軸”,可能為引起臨床COPD 發病重要機制之一,能進一步提高COPD 患者急性發作頻率[16]。目前對COPD 患者而言,穩定期、急性期均采取相應藥物治療達到控制疾病的目的,而藥物服用數量、劑量是否會影響菌群分布情況,當前尚未得出相應研究結果,但部分研究認為[17],藥物并不會對患者腸道菌群組成情況造成影響。對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COPD 患者,及時對痰液、糞便標本分析,第7 天時,腸道菌群減少,14 天增高,多樣性上并未呈現出改變。而對有頻繁應用抗生素病史患者而言,抗生素治療過程中并不影響腸道優勢菌群,進一步指出,長期使用抗生素往往會增加腸道菌群耐藥性。此外,分析吸煙情況對腸道菌群影響,不吸煙與吸煙患者長期處于穩定期或頻繁急性加重患者,未觀察到腸道菌群組成明顯變化。是否吸煙、支氣管擴張劑以及糖皮質激素應用情況,并未影響腸道菌群組成情況,提示腸道菌群對COPD 所致影響為代謝產物調控。目前調查指出,COPD 患者和健康對照之間氣道、腸道菌群關鍵差異,僅僅指依據菌群描述性分析,難以提供疾病機制與潛在療法應用依據[18]。仍需進一步對菌群-宿主互作機制分析,利用多組學方法,分析菌群特征、COPD 表型情況,在COPD 風險分層、預后評估等內容中,菌群特征可應用其中并具備顯著成效。
COPD 細菌感染兩種發病機制中,對穩定期患者而言,以下呼吸道定植為主要表現,相比較無細菌定植患者,有細菌定植表現出肺功能較差,生活質量偏低,急性加重發生情況較高。所以存在定植菌群的患者應該更加注重保護自己,遠離危險因素,而對COPD 穩定期患者而言,是否存在定植菌群成為患者是否需要接受進一步治療重要依據,但臨床如何治療、何時治療仍需深入思考。
4 COPD 和AECOPD 的臨床診斷與治療
4.1 COPD 診斷 COPD 診斷多依據臨床資料及臨床檢查,如病史、癥狀及肺功能檢查,及時排除同類所致類似癥狀、持續氣流受限等,經綜合分析確診。當前展開肺功能檢查后,多表現為持續氣流受限,作為確診COPD 必備條件,支氣管舒張劑吸入后,此時第1 秒用力呼氣容積占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70%,明確存在持續氣流受限;在臨床癥狀表現上,包括慢性咳嗽或咳痰、呼吸困難、反復下呼吸道感染史[19]。同時,計算機斷層掃描(CT)為診斷氣道阻塞性肺疾病有效方法,特別為早期無癥狀、無氣道阻塞、肥胖或者肺功能正常者。CT 應用能及早發現早期COPD 患者小氣道病變。
4.2 COPD 治療 上述階段治療主要選擇非藥物干預,其目標為癥狀減輕、降低急性加重的風險,許多對肺康復的研究表明體育鍛煉可減少急性加重期的風險。肺康復治療內容上,以藥物治療基礎上配合肺功能康復治療,內容上包括運動訓練、呼吸肌訓練、氧氣療法、無創呼吸機輔助通氣治療等。有氧運動鍛煉為一項較為安全的運動項目,經運動訓練并不能完全改善COPD 患者肺功能,但通過定期有氧運動,可以提高COPD 患者運動耐量、自我保健能力及活動能力,緩解COPD 患者呼吸困難及氣促等癥狀,提高患者肺功能,改善患者生活質量,進而促進患者機體康復[20]。但目前有關穩定期臨床治療及康復效果尚未做出統一定論,仍需進一步深入探討及分析。
4.3 AECOPD 診斷 AECOPD 以咳膿痰、呼吸困難等為主要表現,會造成肺功能水平下降,引發心力衰竭而導致死亡。AECOPD 診斷中,表現出以下幾類標準:癥狀明顯加重,如突然發現靜息時呼吸困難。COPD 基礎病情嚴重。出現新的體征,如紫紺、外周性水腫。加重時初始藥物治療無效。出現明顯合并癥。這不僅會增加患者痛苦和死亡風險,還會造成巨大的家庭經濟負擔。
4.4 AECOPD 治療 有研究表明,感染為AECOPD發生的重要誘因。急性加重主要由呼吸道病毒感染或細菌感染引發[21]。該時期治療以藥物治療為主,治療目標是盡可能減少急性加重造成的不良影響,避免后續不良事件的發生。其中抗生素是該時期的關鍵用藥。對有呼吸困難、痰量增加、咳膿痰3 種主要癥狀出現的AECOPD 患者,應給予抗生素治療;有兩種主要癥狀,如果膿痰增多是兩種癥狀之一,則需要機械通氣(有創或無創)[22]。抗生素治療的建議時間為5~7 d。抗生素的選擇應基于當地的細菌耐藥模式。通常,最初的經驗性治療是用氨芐西林加克拉維酸、大環內酯或四環素。需要機械通氣的病情加重患者,應對痰或其他肺部材料進行培養,如革蘭陰性菌(如假單胞菌屬)或對上述抗生素不敏感的耐藥病原體可能存在[22]。給藥途徑(口服或靜脈注射)與患者進食能力、抗生素藥代動力學有關,即便口服抗生素更可取。通過治療,患者呼吸困難、咳膿痰癥狀改善則表明成功[23]。
5 小結
COPD 穩定期有部分患者存在定植菌群,該時期的菌群不僅參與呼吸道正常菌群組成,維持呼吸道正常功能,還參與呼吸道慢性炎癥的進程。處于COPD 穩定期患者,定植病原體濃度較高,一旦細菌濃度升高相應炎癥反應程度隨之上升,高出一定閾值范圍后,臨床癥狀隨之產生,一旦未及時檢測并糾正,會影響纖毛清除、細菌生長之間平衡,觸發COPD 并引起惡化。微生物閾值數量與惡性炎癥反應觸發過程所產生結局存在未知,而每一種細菌所處閡值存在一定差異性。目前COPD 穩定期有定植菌群的患者是否需要治療仍未有相關的研究。AECOPD 細菌感染也可以是一種新的微生物到達支氣管上皮引起的一系列免疫反應。該機制在這兩種細菌感染機制中更為常見,且目前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其中革蘭陰性桿菌最為常見,而近年來常見菌群也有一定的變化,可以通過了解菌群的變化對臨床抗生素使用提供一定的幫助。綜上所述,兩種感染機制組成COPD細菌感染急性加重期常見的病理機制,當未發生感染時可針對患者情況予以相應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