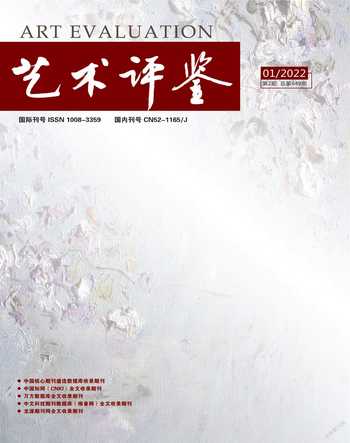心理學視角下對書跡的解讀
彩夢悅
摘要:凡書之“跡”,強調的是書法筆跡,往往能夠反映一個人的能力、情緒、個性,使觀者在欣賞技法的同時與作者精神上達到共鳴,這種視覺審美是否也能反映作者人品呢?答案是否定的,人品、道德有高低之分,但性格不分好壞。學書之初常強調“師法古人”,如王羲之、米芾等書法名家,但他們都處于不同時代和不同背景,所表現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個人特點。故心理與書法的關系極為密切,若審美偏好不同,結構與墨色所體現的抒情觀必然存在差異,運用心理學的某些觀點研究書法藝術及其規律,使學書者在摹其“形”的同時更加關注書家的內心活動,最終能夠得其“神”。
關鍵詞:書法 ?氣質 ?心理 ?性格
中圖分類號:J2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2)02-0055-04
一、書法與心理的關系
中國歷史上雖沒有明確提出心理學的概念,但早在西漢就有人已然明確書跡與心理學的關系。新天鳳五年,揚雄率先提出“書為心畫”的著名美學觀點,對后來的書法理論有著重要的啟示與指導作用。
現代心理學家認為,藝術作品的理想成果和審美水平主要取決于創作者原有的藝術素養和經驗積累,具體來講書法與心理的關系,就是書法與動機、情緒、想象、靈感、心態的關系。動機產生繼而衍生了創作的需要,正如馬斯洛將人類需求從低到高分為五種層次,書法藝術不僅以技法經驗為基礎,而且以書者的情性修養為內涵,若能達到自我實現的最高層次,那便是最高級也是最純粹的創作動機。論及書法與情緒的關系,更多體現在書體上。享有盛譽的《蘭亭序》和《祭侄文稿》雖然篇幅都不算長,但創作者的內心情緒卻十分強烈。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是王羲之與文人雅士在飲酒賦詩中趁興所寫,這種與朋友聚會時快然自足的情緒便移至筆墨,真正做到了氣韻生動、心手合一,可謂得其自然而兼其眾美;而顏真卿的傳世墨跡《祭侄文稿》,不僅向觀者表述了一段慘烈悲壯的故事,也傳達了顏真卿極為悲憤的內心情緒,更能看出顏真卿在書寫時的情緒變化,這種跌宕轉折的情緒躍然紙上,了無掩飾,實在是悲痛之情難以自抑。想象與靈感時刻充斥著藝術家的內心,他們往往從萬千世界中觀察入微,以達書法之妙。如東漢的蔡邕于僧眾掃帚拂墻過程中發明創造了飛白書;昔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多次觀公孫大娘舞劍,自此草書長進,這也反映出藝術家對不同藝術門類相互借鑒的深刻認識,想象亦是靈感迸發,只可意會,難以言傳。寫字還要講求書寫心態,其重要性可見一斑。長沙東牌樓簡牘屬于東漢末期中為數不多的簡牘,其中,簡五是東牌樓簡中的上言文書,由于是公文需求,行列整齊,字體細小,書寫的極其認真工整,類似的書寫心態在簡一二中也有體現,內容為上報荊南局勢的公文,力求持穩謹慎。不同書手表現出的創作心態也各不相同,敦煌漢簡中就有許多“不太講究”的書寫墨跡,不同于長沙東牌樓簡牘那樣受約束,簡單、自由是其主要的書法風格面貌,更加追求草率和簡捷。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然后書之。”從古至今遺留下的理論或是實踐都在證明心理與書法關系之密切。
二、書法審美偏好與人格氣質類型的關系
英國心理學家艾森克將人分成“穩定性+內傾型”(黏液質)、“穩定性+外傾型”(多血質)、“不穩定+內傾型”(抑郁質)、“不穩定+外傾型”(膽汁質)等四種典型氣質。在艾森克的人格氣質類型圖中,縱軸代表內傾與外傾,橫軸代表情緒的穩定與不穩定,這兩個維度所造就的氣質類型投射到書法的審美偏好上也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
(一)粘液質
粘液質作為氣質類型之一,其特點是感受性低而耐受性高,內傾性明顯,外部表現少,不隨意反應和情緒興奮性較低,反應速度慢而穩定。在日常生活中表現為心平氣和、溫和可靠、不易激動,情緒不外露,行動遲緩、冷靜而踏實、自制力強而易于固執。如果與現在了解的西方星座配對,具有粘液質類型的人十分符合金牛座的性格特點。這樣的典型書家例如作為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他的書風圓融遒逸、外柔內剛、疏朗溫潤,一派中和之氣象,與粘液質類型的契合度頗高,存世的《孔子廟堂碑》是其代表作,觀其字形猶如裙帶飄揚,但束身矩步,凜然不可侵犯之狀。古代的評書家論其人品時給出這樣的評價:“性沉靜寡欲,容貌儒懊而志性剛烈”,虞世南雖然話語不多,可是在稍顯嚴肅、不茍言笑的外表下,人緣卻是極好的,唐太宗重視其才學,譽其“忠讜、友悌、博文、詞藻、書翰”五絕,常常在處理政務之暇與虞世南共同討論經史,每每談論古代帝王政績的得失,虞世南必然規勸諷諫太宗。偶有一次太宗戲謔虞世南,作艷詩令世南唱和,虞世南回應道:“圣上之詩,制作雖工,然體不雅正。上之所好,下必仿效,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臣不敢奉詔。”太宗聞言大笑,表明以此玩笑來試其人品高低,遂賞絹五十匹以示褒獎。虞世南的書法風格平和中庸,為后世學書者之楷模,在賞其書跡的同時對其人品也是多加贊賞,類似虞世南如此的粘液質人格氣質類型,在古代書家中大多為文書官員,無論修養學識還是人品都極為穩重,胸襟氣度非凡,故學書者如一味追求形似而忽略字外功夫則相去遠矣。
(二)多血質
多血質的特點是感受性低而耐受性較高,具有可塑性和外傾性,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現為迅速敏捷、活潑好動,且為人直率熱情。多血質類型的人缺點往往是脾氣性格急且易怒,遇到事情通常不會低頭妥協。優點就是開朗健談、活潑悠閑、善于領導,能夠憑借堅韌不拔的毅力戰勝艱難險阻。從事藝術創造的人約占半數都是此類人格氣質特征。顏真卿作為唐朝新書體的創造者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開元二十二年,顏真卿登進士第,歷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在最高的監察機關任職,后因得罪權臣遭到貶謫,成為平原太守,才有了“顏平原”之稱。他的書法筆力雄強,沉著端莊,就如同他的人格一樣正直、忠烈、豪氣,楷書的嚴格法度氣勢磅礴,成為盛唐氣象的鮮明標志。號稱“天下第二行書”的《祭侄文稿》也出自他手,此稿的筆精墨妙得到歷代書家一致公認,是書法美與人格美完美融合的典范。
(三)抑郁質
抑郁質人格氣質類型的特點是感受性高而耐受性低,具有嚴重的內傾性。在日常生活中多表現為敏感多慮、孤獨膽怯,這種類型的人往往頗有才情,但卻困于自我與社會的矛盾之中,這種想象的最初積累離不開作者的人生經歷,這種變化往往導致創作者性情改變。比如晚明浪漫思潮影響下的徐渭,他是一個極為敏感而又脆弱的書家,看花敗而感懷人生,觀落葉則慨嘆時序,一生潦倒,抑郁而終,然而在文學藝術的眾多領域卻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不僅是畫家、書法家,在詩和戲曲領域也對明代和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了解過徐渭的人生,才懂其書法,家庭的不幸導致了他凄涼的童年,舉人的屢試不中和家破人亡,使得精神崩潰到極點的他連續九次自殺。晚年的徐渭將自己的悲憤和抑郁融注于筆端,以藝術語言來宣泄他一生的郁結和貧困,接連創作氣勢磅礴的狂草,不拘成法,特立獨行,下筆如槍戟,用墨如滂沱傾瀉,這樣的書寫效果無疑是震撼的,他以極強的自我意識賦予筆墨濃烈的主觀感情,但恃才傲物的徐渭卻堅決不為達官顯貴作畫,孤獨復雜的性格也成就了其狂放不羈、肆意灑脫的藝術風格。無論是橫豎畫還是斜向筆畫,都把對外部空間的占有發揮到極致,代表作《行草應制詠墨軸》中字距間的盡力壓縮,線條與空間的配合形成了強烈的對照,控筆自如的水平之高,這種壓抑中的放縱形成的郁勃之氣,從側面也彰顯了他的心理性格。縱觀歷史,往往是在社會和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敏感的文人容易產生心理劇變,表現在其他領域,藝術往往將上升到一個高的層次。
(四)膽汁質
膽汁質人格氣質類型感受性低耐受性高,具有外傾性明顯的特點,情緒興奮性高,但抑制能力差,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現為精力旺盛、情緒急躁、易怒不安。唐朝有“顛張”之稱的張旭憑借草書索筆揮灑,其性情狂放不羈,為人閎達倜儻,好飲酒,癲狂正是他容易情緒化、任性、意氣用事的表現,他將自己的喜怒憂悲傾注于狂草之中,飲酒后如醉如癡、如癲如狂,將草書的情境表現發揮到了極致,落筆常常一氣呵成,用筆肥厚,筆意精熟。清代包世臣評價其“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若泉流”,《古詩四帖》表現出驟雨急風的點畫特征,用筆中側并用、連綿環繞,結體或開或合,轉換起伏,似其性格的筆墨中呈現最大程度的自由揮灑,具有強烈的寫意精神。作為一位極具個性的書家,感情與筆墨的高度統一造就出他獨特的豪放書風,《書譜》中認為,書法藝術的本原系于人心,“書之為妙,近取諸身”,人的性格思想寓于書法作品之中。因此,張旭的膽汁質性格與書風的變幻是有關系的。
三、抽象的抒情
(一)字體結構
書法創作當中包含了很多元素,其中字體結構是關鍵之一。立體感強不強,全靠結構框架去支撐,若站在心理學的視域觀察,那些不同程度的字體結構往往也可以解構得出作者的觀念,具體來講,不同結構的視覺形式包括舒朗、險絕、稠密等空間的開合元素,在作品中整體呈現出來的形態氣質是不同的。如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整體結構舒朗,表達出的是一種流暢灑脫的審美內涵,使觀者身心愉悅,大有“龍跳山門,虎臥風閣”之勢。鐘繇的小楷,平仰覆、字勢、內齊等結構,這些都做的非常好,亦屬舒朗一路。字體結構緊密者類如龍門二十品中的《始平公造像記》,此碑的結構采用斜畫緊結,字的中上部分十分稠密,處處給人一種壓迫感,而下部的撇捺又十分舒展,扎實的體積給人一種陽剛之感,如此鮮明的對比使它成為魏碑中極具代表性之一,以方正險峻、剛毅雄強的特點流傳后世。
字形的中宮處于何等位置與其結構模式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相傳唐代歐陽詢創制了一種方便臨帖仿寫的界格形式,這九個小方格可以對照所臨寫的法帖進行字形練習,對于確定點畫的位置起到了精確臨摹的作用,最中間的格子便是中宮。中宮位置如果偏下,視覺效果則一反常規,元代的柯九思結字多取上展下斂勢態,非常具有辨識度,盡管中宮偏下,但點畫的挪位處理卻又十分平衡,橫勢縱勢參差顧盼,頗具意趣。許多書家作字時中宮都是靠上的,如歐陽詢在處理字形時往往字形偏長,主筆穩定且高聳挺拔,字勢縱橫分明,法度森嚴的結構與他為人拘謹內斂的性格十分相符。拘謹內向性格的人往往字形結構中宮緊湊,心胸大度之人往往字形結構開張,這種潛移默化的喜好與偏愛在字體結構中有較為典型的展現。
(二)墨色表現
我們常用“墨分五色”來概括墨的層次變化,分別是濃、淡、干、濕、枯五種,長期書寫所形成的固定習慣決定了書家書法作品的墨色表現。“書契既造,墨硯乃陳”,古代人寫字之前的很多時間都消耗在磨墨上,故墨與書法家的感情不言而喻,每件書作在墨色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濃淡體現,這也是書法藝術美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一般審美評價來看,干枯的墨色會使線條顯得更加遒勁和老辣,濕潤的墨色會使線條顯得豐潤和飽滿。清末明初的王鐸在書法創作中大量使用漲墨法,縱覽他的草書作品,將漲墨運用到了得心應手的程度。漲墨所表現的字給人一種呼之欲出之感,局部墨色的展現使得整篇效果氣韻生動,增加了字與字的對比和張力,讓欣賞者在黑白世界中領略其妙處。今人學草書也有許多人大膽借鑒王鐸,體現出酣暢淋漓的藝術效果。
劉墉的書法造詣頗高,也是乾隆皇帝身邊位高權重的寵臣,被稱為“濃墨宰相”,用墨厚重濃烈,珠圓玉潤,具有“肥、厚、清、靜”的特點,與他的儒雅氣質結合,使人感到儒家思想中溫良謙讓的敦厚心態。他用墨濃重在清代是出了名的,清代還有一位書家與劉墉剛好相反,喜歡用長峰羊毫以青黑色淡墨寫字,便是王文治太守,他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名動京師,受到褚遂良、董其昌的影響,加之潛心研究禪理,書風瀟灑如其人,追求淡雅秀逸的筆墨神韻,考取進士時名列探花,所以清朝此二人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的美譽。與劉墉書法相比較,王文治字如翩翩少年,巧妙靈動,因其下筆較輕,所以筆鋒上的活潑、輕快盡顯姿態,變化程度又都合情合理,反觀劉墉書如遲暮老人,成熟穩重,毫無草率和隨便的筆意。二人的形質神采不同,所以書法的差異也就湊巧展現在墨色上面,一濃一淡,各盡其妙。
參考文獻:
[1]王曉光著.秦漢簡牘具名與書手研究[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6.
[2]鄭林科,張乃祿主編.安全心理學[M].西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
[3]楊治良主編.簡明心理學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