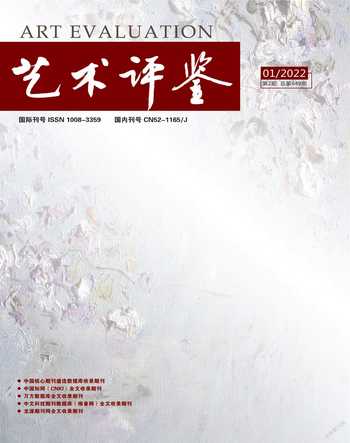當(dāng)下廣州地區(qū)粵劇唱腔流派藝術(shù)發(fā)展趨勢及原因探析
潘妍娜
摘要:粵劇中的唱腔流派藝術(shù)形成于20世紀(jì)30年代之后的粵港澳城市語境中,在廣大群眾中有著深厚的基礎(chǔ),新中國成立后內(nèi)地演出生態(tài)與創(chuàng)作機(jī)制的變遷,導(dǎo)致流派藝術(shù)的式微,當(dāng)下廣州粵劇舞臺上流派藝術(shù)呈現(xiàn)風(fēng)格融合與弱化的趨勢。造成流派變遷的主要原因是曾經(jīng)“演員中心制”的創(chuàng)作模式轉(zhuǎn)向“劇本中心制”,專業(yè)編劇、專業(yè)唱腔設(shè)計(jì)創(chuàng)作模式的形成,導(dǎo)致演員個(gè)性化創(chuàng)造空間的消失,使得舞臺表演中唱腔風(fēng)格的融合與弱化成為普遍的趨勢。
關(guān)鍵詞:粵劇 ?流派 ?融合 ?弱化
中圖分類號:J805?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2)02-0158-03
“流派”是戲曲藝術(shù)發(fā)展成熟的標(biāo)志,在粵劇表演藝術(shù)中,以個(gè)人藝術(shù)家獨(dú)具風(fēng)格的唱腔立“派”是其流派特點(diǎn),例如馬師曾的“乞兒腔”、薛覺先的“薛腔”,羅家寶的“蝦腔”,紅線女的“紅腔”、芳艷芬的“芳腔”等等,這些唱腔形成于20世紀(jì)30年代之后的省港城市語境中,有較深入的群眾基礎(chǔ)。當(dāng)下隨著廣州城市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加快,娛樂方式日漸多樣化,流派藝術(shù)如何在現(xiàn)代城市空間中傳承和發(fā)展是一個(gè)重要的問題。本課題通過對粵劇從業(yè)者、民間唱家、普通受眾的訪談,對粵劇唱腔流派藝術(shù)在廣州地區(qū)舞臺的現(xiàn)狀進(jìn)行考察與調(diào)研,希望探討眾多流派藝術(shù)在當(dāng)下廣州城市語境中的發(fā)展趨勢,以及分析影響其發(fā)展的原因。
一、唱腔流派的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語境:近代省港城市經(jīng)濟(jì)的繁榮
從歷史來看,粵劇中的唱腔流派主要形成于20世紀(jì)30年代之后的粵港澳城市語境中。城市經(jīng)濟(jì)的繁榮促進(jìn)了省港地區(qū)戲班的流動(dòng),粵劇市場前所未有的活躍,省港地區(qū)興建了大量戲院,在這樣的城市背景中,粵劇不斷突破舊傳統(tǒng),進(jìn)行了很多改革與探索,在音樂上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在一批優(yōu)秀演員的帶領(lǐng)下,表演藝術(shù)趨于個(gè)性化,形成流派,“薛”“馬”“桂”“廖”“白”就是較早的5個(gè)流派,其中薛覺先和馬師曾是較有代表性的兩個(gè)流派,“薛馬爭雄”曾經(jīng)是粵劇史上的一段佳話,正是優(yōu)秀表演藝術(shù)家在表演上的爭奇斗艷,才造就了豐富的唱腔流派文化。張紫伶在其研究中提出“與五大流派同期的各個(gè)行當(dāng)名伶,體現(xiàn)出當(dāng)時(shí)的名伶如何靈活交叉合作組班的現(xiàn)象,通過不斷地交流學(xué)習(xí)、共同創(chuàng)作、相互扶持,成就了五大流派,并培養(yǎng)提攜了下代的粵劇名伶。”
五大流派為之后的流派產(chǎn)生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尤其是薛覺先的薛腔對于文武生唱腔影響較大。澳門粵劇演員朱振華就對筆者說,大部分文武生的唱腔都是吸收了薛覺先的唱腔,即以薛覺先的唱腔為主,然后跟著自己的條件去發(fā)揮。蝦腔傳人演員劉建科也談到,羅家寶的蝦腔同時(shí)吸收了“薛”“馬”“桂”“廖”“白”,但其中主要是以薛覺先的唱腔為主,因?yàn)榱_家寶與薛覺先合作過多次,深受薛覺先的影響。
從年代來看,五大流派成為了流派的第一代,在五大流派的基礎(chǔ)之上,40—60年代是一個(gè)唱腔流派發(fā)展的新時(shí)期,隨著新中國成立之后,粵港分治,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唱腔。文武生在廣州地區(qū)主要以“蝦腔”“風(fēng)腔”“B腔”(陳小漢)為代表,香港地區(qū)主要有“任腔”(任劍輝)、“新馬腔”“狗仔腔”(何非凡),花旦唱腔廣州以紅線女“紅腔”為主,香港以芳艷芬“芳腔”、白雪仙“仙腔”為主。這些唱腔在兩地均有較穩(wěn)定的受眾群體。
二、當(dāng)下粵劇唱腔流派的發(fā)展趨勢調(diào)查:流派風(fēng)格的弱化與融合
為了了解粵劇唱腔流派的發(fā)展現(xiàn)狀,筆者對廣州地區(qū)粵劇專業(yè)團(tuán)體中的流派傳承人、粵劇從業(yè)者,以及民間私伙局中的唱家和大眾分別進(jìn)行了采訪,希望從不同的層面把握流派藝術(shù)的發(fā)展趨勢。
在課題組考察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流派風(fēng)格在廣州地區(qū)雖然有一定的群眾基礎(chǔ),但是基本上都是老一派的唱腔,近年來較少出現(xiàn)新的流派,唱腔風(fēng)格的弱化是一個(gè)普遍的趨勢,尤其是新編粵劇,很少會(huì)有以某一個(gè)唱腔流派進(jìn)行演出,取而代之的是對不同流派風(fēng)格的融合,這一點(diǎn)尤其體現(xiàn)于專業(yè)粵劇團(tuán)中的演員身上。
例如佛山粵劇院粵劇演員彭熾權(quán),盡管他是公認(rèn)的新馬腔的傳人,但是他仍然學(xué)習(xí)了很多別的流派唱腔,例如薛腔和蝦腔。而且他特別善于根據(jù)不同的人物使用不同的唱腔,有“千面老倌”之稱。他在采訪中特別提到根據(jù)行當(dāng)、角色選用不同老倌的唱腔。他告訴筆者:“我已經(jīng)吸收了很多唱腔,吸收了很多流派,我看的戲多,和他們學(xué)、甚至同臺做戲。薛派、新馬、羅家寶等我都熟悉。我知道風(fēng)格,但是我不是照樣搬。我會(huì)根據(jù)自己的聲音條件演繹人物,我聽多了,我看做什么行當(dāng)、角色,就會(huì)選擇用哪位老倌的唱腔,要服務(wù)人物,如果生搬硬套,觀眾會(huì)聽得出來不好。”
由此來看,作為一個(gè)現(xiàn)代粵劇演員,面對傳統(tǒng)流派風(fēng)格的時(shí)候,必然會(huì)把這些流派風(fēng)格運(yùn)用于表演實(shí)踐之中,用于塑造人物角色,并根據(jù)人物角色的不同,選擇不同的流派風(fēng)格。另一位課題組采訪到的廣州紅豆粵劇團(tuán)的副團(tuán)長陳振江,一位年輕的文武生,他對于唱腔流派的使用也有類似“流派服務(wù)于人物”的看法。他告訴筆者:“我們在攝取這些流派的過程當(dāng)中,很多時(shí)候可以把它運(yùn)用到人物上。其實(shí)我覺得每一個(gè)流派,它都有塑造某一個(gè)年齡段,或者是某一個(gè)階層的角色會(huì)特別好,就像我之前演的一個(gè)叫《三生》的戲,同一個(gè)人三世的故事,他到二世的時(shí)候,是一個(gè)心里特別貪財(cái),很市井的人物,那我覺得就讓他用“馬腔”(馬師曾唱腔)去塑造,就相對比較貼近,因?yàn)轳R腔的塑造是很市井的。”
這種帶有強(qiáng)烈個(gè)人特征的新唱腔在私伙局中也有一定的流行度,在筆者對私伙局的調(diào)查中也發(fā)現(xiàn),私伙局中的唱家們不一定會(huì)唱什么“腔”,但是可能會(huì)模仿某位演員的曲目和唱法。而對于大部分的粵曲愛好者來說,在學(xué)唱曲時(shí)也較少限于某一流派的曲目,而是追求多種流派風(fēng)格的融合。例如筆者課題組在對廣州笙歌樂府考察時(shí)遇到的唱家陳鳳萍老師,她是廣州市增城區(qū)戲劇曲藝家協(xié)會(huì)理事,師從著名粵曲子喉演唱家危佩儀。對于粵劇粵曲的學(xué)習(xí),陳老師認(rèn)為在初學(xué)唱粵曲的時(shí)候,“多聽多看多模仿”是關(guān)鍵,不一定非要局限于某一個(gè)流派,不管什么派別都要取其精華,甚至可以跨不同戲曲種類,如學(xué)習(xí)京劇和昆曲。陳老師建議如果學(xué)子喉(花旦唱腔)的話先聽“紅腔”學(xué)習(xí)發(fā)聲,因?yàn)椤凹t腔”所發(fā)出的聲音比較清亮,位置靠前,有利于發(fā)掘和打磨適合自己的音色。由此看來,“唱腔流派”這一概念在民間似乎也已被逐漸弱化;而對于“建立某一派別”的意識,似乎也沒有以往強(qiáng)烈了。
流派風(fēng)格弱化與融合帶來一個(gè)新的發(fā)展趨勢就是“個(gè)人風(fēng)格”正在逐漸代替“流派風(fēng)格”,例如一些當(dāng)紅花旦和著名的子喉唱家,如倪惠英、蔣文端、梁玉嶸、曾慧、李敏華等也是大多數(shù)人模仿與推崇的對象。對于個(gè)人著名演員的演唱風(fēng)格推崇,正逐漸代替“流派”這一概念。這些演員可能以善于演唱某一流派而出名,例如蔣文端和曾慧曾經(jīng)善于演唱“芳腔”,梁玉嶸善于演唱“星腔”,蘇春梅善于演唱“紅腔”,但是在今天的舞臺上,她們的演唱流派風(fēng)格并不明顯,尤其是在演唱非流派曲目的時(shí)候,他們對于流派風(fēng)格的融合,以及個(gè)性的創(chuàng)造與理解,更多形成了具有自己風(fēng)格的唱腔。因此,大眾對于他們的唱腔有時(shí)并不是在流派的基礎(chǔ)上認(rèn)同的,而是將其稱為“端腔”(蔣文端),“嶸腔”(梁玉嶸),或代之以“蘇春梅的紅腔”,以此區(qū)別于流派的原有風(fēng)格。
三、流派式微的原因分析:演出生態(tài)與創(chuàng)作機(jī)制的現(xiàn)代變遷對于流派的影響
總的來看,近代以來粵劇市場的繁榮與良性競爭是促使流派產(chǎn)生與發(fā)展的主要原因,而粵港兩地粵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同也造成了流派不同的發(fā)展路徑,香港地區(qū)研究者張紫伶關(guān)于香港粵劇流派的研究中提出:“香港粵劇流派的傳播進(jìn)程中,其形成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以及組織架構(gòu)體系。香港粵劇具有中西合璧、宜古宜今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與電影話劇‘文明戲’的互動(dòng)及高度‘自由’的表演舞臺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此外,香港商業(yè)化機(jī)制下的藝術(shù)生態(tài)與‘老倌’成長的規(guī)律、觀眾影響、大眾娛樂有關(guān),這些也影響著其流派的傳承與發(fā)展。”商業(yè)性是香港粵劇的主要演出生態(tài),這種生態(tài)一直延續(xù)了省港時(shí)期的粵劇演出環(huán)境,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粵劇的傳統(tǒng)唱腔與程式,也滋生出與內(nèi)地不同的流派風(fēng)格特色,如花旦“芳腔”,文武生“新馬腔”“任腔”等。
而內(nèi)地的演出生態(tài)則完全與香港地區(qū)不同,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隨著戲改的開展,劇團(tuán)國有化和對于舊戲的批判,以及社會(huì)制度向新中國的轉(zhuǎn)變,使得粵劇開始走向了一條“強(qiáng)國家,弱市場”的道路,在創(chuàng)作上以借鑒北方劇種為主,采用劇團(tuán)局內(nèi)人與劇團(tuán)外文藝工作者合作的模式,這成為各劇團(tuán)普遍應(yīng)用的一種模式。深受西方戲劇表演體系與音樂體系影響的外來文藝工作者們,通常采用“先進(jìn)的”西方話劇或歌劇音樂的目光審視傳統(tǒng)戲曲,由此認(rèn)為中國的戲曲存在諸多問題。傳統(tǒng)戲曲“演員表演中心”的劇場特質(zhì)被認(rèn)為是結(jié)構(gòu)松散、缺少專業(yè)編劇與導(dǎo)演所致;而板式與曲牌“一曲多用”的傳統(tǒng)創(chuàng)作方式,則被認(rèn)為是沒有專業(yè)作曲家的情況所致。在戲曲改革專業(yè)化要求的驅(qū)動(dòng)之下,原先“演員中心”的綜合創(chuàng)作模式分離為專業(yè)化的導(dǎo)演、編劇、音樂設(shè)計(jì)、唱腔設(shè)計(jì)、舞美設(shè)計(jì)等多個(gè)工作崗位,成為直到今天各戲曲院團(tuán)通用的創(chuàng)作方式與組合。
專業(yè)分工創(chuàng)作模式對于傳統(tǒng)粵劇唱腔流派的影響是巨大的,以往粵劇劇目的創(chuàng)作是服務(wù)于“大佬倌”的,而各個(gè)大佬倌根據(jù)自己的音色、聲音條件,可以創(chuàng)作適合自己的劇目,例如馬師曾的嗓音比較沙啞,比較適合表現(xiàn)市斤小人物,所以他的劇目大多是這種類型。而薛覺先的音色適合演一些比較大氣的人物,像范蠡,以才子佳人的戲?yàn)橹鳌T诖嘶A(chǔ)上形成類型化的表演是唱腔流派的一大主要特色。進(jìn)入到新中國以來,大佬倌一人挑一班的劇團(tuán)被改革后,眾多名家合并進(jìn)了國有劇團(tuán),由于專業(yè)編劇這一角色的介入,形成了“以劇本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模式,這種情況下為某一個(gè)人長期創(chuàng)作類型化的劇目已經(jīng)不太可能,在戲改的要求下,表現(xiàn)時(shí)代、表現(xiàn)新生活才是劇目創(chuàng)作的主題。因此,音樂服務(wù)于劇本,或音樂服務(wù)于人物才是創(chuàng)作的最高目標(biāo),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類型化”為標(biāo)志的唱腔流派的發(fā)展。
專業(yè)分工模式帶來的另一個(gè)影響是唱腔設(shè)計(jì)的專業(yè)化,受到西方歌劇音樂創(chuàng)作影響的這一崗位,多由接受過西方專業(yè)音樂教育且學(xué)習(xí)過作曲技法的音樂工作者擔(dān)任,唱腔設(shè)計(jì)這一職業(yè)的出現(xiàn),將曾經(jīng)自由靈活的唱腔表演固定化,這在戲改中被稱為“定腔定譜”。以往的舞臺上,大佬倌們有著極大的自由性,不僅可以根據(jù)自身?xiàng)l件與喜好設(shè)計(jì)唱腔,還可以根據(jù)每天不同的聲音情況與臨場發(fā)揮進(jìn)行調(diào)整,例如演員彭熾權(quán)就認(rèn)為,唱腔設(shè)計(jì)將譜子寫好的這種做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演員的靈活性,長此以往導(dǎo)致演員沒有創(chuàng)腔的能力,使得舞臺上的唱腔千篇一律。除了唱腔設(shè)計(jì),標(biāo)配的還有音樂設(shè)計(jì),因?yàn)楝F(xiàn)在的新編戲大多追求音樂的戲劇性,劇團(tuán)里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大樂隊(duì),不再是早期的五架頭,樂隊(duì)配置以民族管弦樂為基礎(chǔ),音樂設(shè)計(jì)必須將樂隊(duì)伴奏的樂譜固定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演員靈活發(fā)揮的空間。
四、結(jié)語
由以上分析來看,傳統(tǒng)的“演員為中心”的演出生態(tài)與創(chuàng)作機(jī)制之下,粵劇演員有極大的個(gè)性化創(chuàng)作空間,可以在固守程式框架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富有個(gè)人風(fēng)格的唱腔創(chuàng)造,但自新中國戲改以來形成的演出生態(tài)與以及專業(yè)分工模式,深刻改變了粵劇唱腔流派在內(nèi)地的發(fā)展,新編劇“以劇本為中心”所提出的“音樂服務(wù)于人物”這一理念,限定了“類型化”為標(biāo)志的唱腔流派的發(fā)展,而唱腔設(shè)計(jì)與音樂設(shè)計(jì)崗位的專業(yè)化,使得曾經(jīng)自由靈活的唱腔表演固定化,限制了粵劇演員活態(tài)的創(chuàng)造性與創(chuàng)造力,是唱腔流派在舞臺上衰落的核心原因。
參考文獻(xiàn):
[1]張紫伶.香港粵劇流派研究[D].北京: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2018.
[2]戲曲藝術(shù)革新不能脫離傳統(tǒng)[J].戲劇報(bào),1956(11).
[3]孫玫.試論新戲曲的“專業(yè)分工創(chuàng)作方式”[J].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