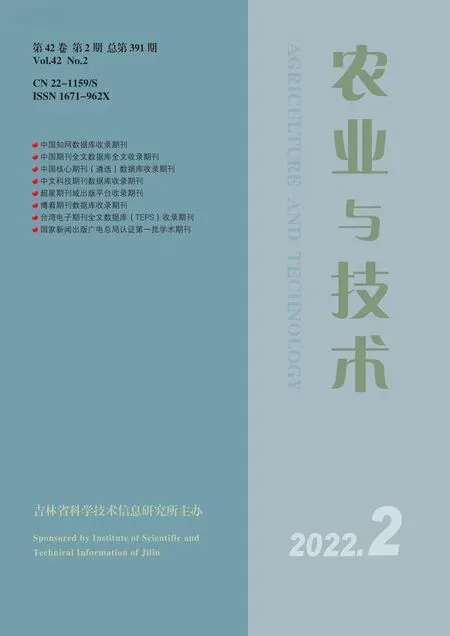基于兒童活動的西安長勝街公共空間景觀設計探析
史鉞豪 孟瑾
(天津城建大學建筑學院風景園林系,天津 300384)
根據《禮記》記載,“公”的中文含義為“公共、共同”,與“私”相對。秦代初期,“公私”開始有了抽象意義,并具有價值判斷的道德含義。由于城市公共活動空間逐漸演變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因社會發展長期演變從而自然形成的,還是由特定人為規劃建造的,其空間形態和整體布局在城市整體環境中都具有較為核心的地位,所以城市公共空間作為客觀的、實體的、能夠容納人及其活動的物質空間屬性是其最為基本的功能。
1 西安長勝街概述
長勝街地段內街巷結構完整,街巷尺度基本維持清末民國時期特征,保留有大量傳統院落和傳統建筑。長勝街地段以居住性質為主,沿街服務型商業發達[3]。街巷式組織即居住生活圍繞街巷進行。雖然位于市中心,但長勝街內日常公共配套設施嚴重不足,居民所享受到的基礎設施的公共空間品質與中等階層居民相比較差,只在街道北側有一處供住宅區使用的健身區,公共設施嚴重匱乏。
由于長勝街片區建成年代較早,基礎設施更新不及時,建筑密度極高,周邊多樣化的業態導致了公共空間嚴重不足的問題。這種情況對于小學生必要的基礎設施用地難以保證,城市化過程中公共空間的質量不被重視,特別是對于小學生人群重要的親子環境的營造極為少見等。本文通過調研小學生人群活動空間及活動方式研究其與長勝街整體傳統街道公共空間之間的關系與矛盾,以小學生的視角理解傳統街巷中的公共空間,從小學生人群的需求角度出發,提出利于長勝街小學生活動發展的合理規劃設計策略,提升城市傳統街巷空間兒童友好性。
2 長勝街公共空間存在的問題
長勝街內人群分布主要有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及固定商戶,小學生人群在此區域主要為本地居民或商戶的子女,大多在附近的碑林區雁塔路小學就讀。現有的場地條件已無法滿足孩童、攤販主、社區居民的現實需求。從小學生人群的角度出發,其從校園到場地內部停留最后回家的過程中首先考慮其路線的安全性,其次要考慮其游戲需要,同時場地內部將兼具課外教育學習等功能。以小學生日常通勤時間為主要調查研究時間,觀察記錄了小學生通勤時間在長勝街街道內的活動路徑、活動內容、活動分布及其與時間的關系。具體調查方法分別采用了實地拍攝考察法、跟蹤采訪和隨機調研法,并且現場實時觀察、拍攝、記錄調研區域從早到晚小學生的活動情況。通過前期調研發現,小學生是活動路徑覆蓋面積最廣的一類人群,年齡分布區間在7~12歲。
2.1 活動路徑混亂
調研發現,小學生駐足玩耍次數最多的地點分別有庭院、屋檐、大樹下、空地。在調研過程中跟蹤采訪了3名小學生,主要對其放學回家路徑和駐點進行調研和總結。調研對象1號,放學后解開一輛共享單車在李家村路逗留玩耍;調查對象2號,放學后先在健身器處玩耍,后回到街道內家中;調研對象3號,在放學后先與同學繞道至明勝路商業區逗留,然后返回長勝街街道內。以上調研情況初步表明,小學生喜歡灰空間,尤其是墻體或地面有“凹凸”變化的灰空間;小學生不會在乎回家路的遠近程度,甚至可以繞路,更注重路上的趣味性。
2.2 活動時間集中
小學生在長勝街街道內的日常活動內容在時間上有一定的規律性。通過觀察發現,小學生在集中一段時間內大量出現并活動于長勝街街道內,主要時間分布在8∶00,17∶00—18∶00,且在上學日內的活動人數明顯少于節假日,活動時間也大大縮短。
2.3 活動空間復雜
2.3.1 街巷邊界空間被侵蝕
邊界空間主要指長勝街街道兩側界面空間,此類空間一般由長勝街兩側商鋪前空間或林下空間組成,在街道內分布較為分散,空間類型為半開敞空間或覆蓋空間。由于此類空間符合小學生活動生理及心理需求,在橫向及豎向上有“凹凸感”,即橫向上空間的進深變化和豎向上的高差變化。同時,一些覆蓋空間可以給小學生活動提供安全感,所以小學生一般在此類空間中活動。而長勝街內由于建筑年代較久,街道也比較窄,所以邊界空間不斷被侵蝕,如圖1。
2.3.2 體育器械空間有隱患
這一空間位于長勝街北側,是長勝街內一處集中的公共活動健身區域,面積約為150m2,空間寬敞。該空間在使用時段的特征為17∶00—20∶00集中出現小學生在此區域活動。由于此空間有大量公共健身器材如雙杠、高低杠、乒乓球臺等,同時此區域內有觀賞性種植池,通過觀察發現,小學生在此區域的活動基本表現為鉆、跳、跑、挖土、玩花草等,見圖2。加之其他行人對體育器械的使用,造成了空間雜亂,對學生造成一定的安全隱患。
2.3.3 院落空間雜亂
長勝街街道兩側分散分布著小型老舊的傳統庭院空間,此類空間也是小學生在通勤路徑中最愛光顧的空間。狹窄的院落空間有利于兒童游戲中躲藏和玩耍。但此類院落空間由于大部分人群為租房客和外地商人,流動性過大,人群混雜,實質上有安全隱患,不利于小學生駐留和游戲。

圖1 街巷邊界空間

圖2 體育器械空間
通過總結3類活動空間發現,長勝街街道中小學生活動空間存在以下問題。
在行人安全性方面,高峰時段和關鍵位置所帶來的人流車流加大,這造成了交通事故發生概率的增加。長勝街由于靠近城市中心,步行游客和附近居民、非機動車都有著較大數量,由于現狀路網難以梳理導致交通集中且混亂,甚至不分流。所以小學生很容易與危險的車輛接觸導致面臨交通危險[5],如圖3。
在交通可達性方面,由于開敞區域老舊且疏于管理,這直接導致不適宜活動的灰色地帶區域增加。根據調查,大多數情況下小學生均為結伴玩耍,可在長勝街街道內這種區域并不能得到保證。
使用功能性方面,長勝街街道內普遍空間單調或阻礙物較多,小學生可進行的活動種類較少。因此,如果只是依靠一些特有的景觀因素或景觀小品,如沙堆、坡道、臺階、水泥臺等,這些要素很難集中到一個位置,兒童很容易乏味,更難以激發成年人陪伴兒童玩耍的興趣,如圖4。
空間使用性方面,由于缺乏綠地空間且業態復雜多樣直接導致衛生條件差,而建筑密度過高使得良好的通風光照等物理環境也變得奢侈[6]。多數小學生在訪談時表示,父母會在周末帶其去一些室內的大型游戲場所,那里開敞明亮干凈的環境會讓其玩得非常開心。

圖3 小學門口照片

圖4 放學路上障礙物較多
基于以上4點分析,在長勝街街道中,安全的、有質量的、有趣的小學生活動場地極為欠缺,主要原因在于空間單一、功能僵化、設施單調、缺乏自主性,這往往是在和城市各種權屬空間妥協之后的結果,所以針對于如長勝街等傳統街巷中的小學生人群,為其創造一個安全、健康的活動空間,應將其根本需求納入規劃設計中。
3 長勝街兒童活動空間設計策略
對小學周邊老舊街道的景觀空間改進應該首先考慮能夠滿足區域內兒童對空間的使用需求,兼顧多樣性需求的同時也要把握好內心期望需求。針對不同類型的活動空間進行針對性改造。長勝街街道中兒童活動空間的根本問題是公共空間的缺乏,因此建議在舊城改造的過程中,注重對公共空間的營造,為兒童提供安全且充足的戶外活動空間。并在空間活動模式上引入創新改造策略,通過改善兒童活動空間激發城市傳統街道空間活力[7]。
3.1 微圖書館引入
通過兒童將閱讀行為從圖書館帶到街巷,使圖書館為城市中心街巷空間植入流動微圖書館,將閱讀帶入長勝街小學生的日常生活中。閱讀活動以小學生為引子,引入城市傳統街巷空間,通過設計使小學生與閱讀空間更易發生關系,培養閱讀習慣,使閱讀成為兒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文化為媒介,在街道社區中形成讀書角,在提供聚會與休憩功能的同時豐富長勝街街道居民的文化生活,最終形成文化社區的營造活動。
3.2 色彩引入
通過在長勝街小學生聚集的區域以培養小學生戶外空間興趣為出發點,將色彩引入長勝街街道,改善其傳統老舊街道的灰色系沉悶風格,從臨街商鋪、招牌、鋪裝、墻繪等方面入手,如彩繪井蓋、墻繪、粉筆畫能夠豐富小學生課余活動種類,讓小學生童年充滿色彩而不是擁擠與單調,讓小學生能夠記住童趣,從而豐富長勝街居民文化生活。
3.3 削減障礙元素
通過對長勝街兒童放學后的行為觀察,小學生在放學路上依然精力充沛,喜歡跑跳打鬧,路上的臨時座椅、花草植壇、圍擋石球以及年代較早的一些電線桿都對兒童活動造成不同程度的阻礙,并形成較大的安全隱患。如調研發現放學路上木制座椅寬度并不實用,且僅隔1.2m,這不僅侵蝕了行人活動空間,還缺乏實用性。應削減座椅數量和寬度,增加空間使用率。
3.4 植物引入
在兒童放學路徑的凹凸空間中引入植物種植,在兒童聚集的地方引入綠植停車裝置,形成一定圍合空間;在回家街道路徑中,引入綠植休閑空間,以培養小學生種植興趣為出發點,老年人可來此將盆栽花卉分享展示,兒童也可以養成愛護花草的習慣,在滿足孩童游戲需求的同時服務于基地中的多種人群,從而達到一定的植物教育意義;在回家后巷空間中,引入特色小夜燈,與綠化種植相結合,創造兒童間交流的機會,同時為兒童帶來童趣。
4 結語
本文對西安長勝街街道內現有兒童校外活動空間進行詳細調研和分析后發現,在城市發展中進行景觀設計時,沒有任何環節用來平衡明確兒童權益,現有的絕大多數活動空間環境質量較差,很難讓兒童進行多樣的活動[8]。兒童本在城市化進程中扮演著最天真爛漫值得保護的角色,因此希望可以通過更新設計策略,使地段內小學生在回家路上有場地供其游樂玩耍并充滿樂趣與童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