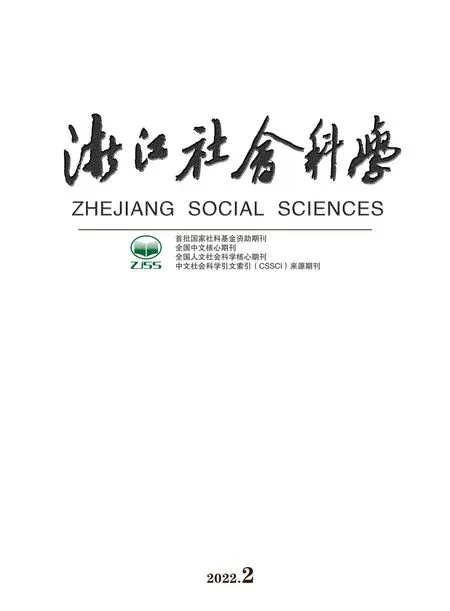論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及相關的元理論問題*
□ 陳 銳
內容提要 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問題是一個非常基礎的法理學問題。學者們大多認為,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是條件式的,其前件由“行為模式”構成,后件由“后果模式”充當。但其實,法律規范的結構不只是假言式的,而且包括全稱式,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通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明確規定義務或授予權利的全稱規范,二是規定因違反前述義務或侵犯前述權利而產生相應法律后果的條件式規范,故其邏輯形式通常表現為“全稱+假言”形式。由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問題衍生了一系列元理論問題,如法律規范是否具有真假值? 規范邏輯是否可能? 等等。為避免上述元理論的困擾,最好以“法律規范命題的邏輯結構”替代“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通過分析法律規范命題的邏輯結構,又發現:“法不禁止便允許”、“凡應當的都是可能的”等法諺并非總是正確的。這說明,封閉、靜態、形式化的規范邏輯系統雖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法律規范體系的某些特點,但它與開放、動態、現實性的法律規范體系之間仍有較大差異。
“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問題是一個非常基礎的問題,相關研究成果不是太多。對于這樣一個爭議不大的問題,似乎很難提出什么新見解。但若深究現有的研究成果,就會發現,其中仍有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第一,國內大多數學者受前蘇聯的影響,直接探究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①只有雷磊別樹一幟,探討“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②,而德國學者拉倫茨論述的卻是“法條的邏輯結構”③,這三者之間有無差異?為什么拉倫茨使用的是“法條的邏輯結構”,而非“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 第二,學者們經常不加批判地將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解為假言命題形式,那是否意味著:法律規范只有假言命題形式?第三,人們習慣上將法律規范的類型劃分為授權性規范、義務性規范與禁止性規范,分別用“允許型規范命題”、“應當型規范命題”及“禁止型規范命題”與之對應,這種對應有無問題? 若運用邏輯方法分析三種規范命題之間的關系,又能揭示哪些元理論問題?以下將針對上述問題展開具體分析。
一、是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還是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
這是一個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正如雷磊在“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一文中說到的:“中國學界長期對‘規則’與‘規范’未加以區分使用,直到最近十年才開始引介西方規范理論,將法律規則作為法律規范之一種來對待。”④雷磊發現,我國學者以往在探討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時,并未區分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只是籠統地加以研究。他認為這一做法不妥,因為“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在規范屬性上的不同決定了它們的邏輯結構亦有不同。”⑤為區別以往的理論,雷磊明確表示:“本文探討的是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一方面,它有別于法律規范的另一種類型,即法律原則”,“另一方面,法律規則也區別于法律條文。法律規則是法律條文的意義,而法律條文是表達法律規則的語句,兩者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⑥亦即,雷磊明確地說到,他只是探討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而將法律原則排除在外:“本論文的論證及其結論并不涵蓋法律原則,也不可用以一般性地指涉法律規范。”⑦
此處,我們不急于品評雷磊的做法是否妥當,再來看拉倫茨是如何處理該問題的。在《法學方法論》一書中,拉倫茨明確地說到:“任何秩序都包含很多規則,這些規則要求其指向的主體依照規則行事”,“法律規則可以被明確規定在制定法中,也可以得自所謂的習慣法,或者從現行有效的法規范中通過正確的推理而得出,還可以借助法律原則的具體化而得出”。⑧拉倫茨同樣區分了“法律規則”與“法律原則”,但并未如雷磊那樣論述“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轉而分析“法條的邏輯結構”:“法律規則采用了句子,即‘法條’這一語言形式,接下來要處理的就是這種法條。”⑨對于這一轉向的原因,或者說,對于“法條的邏輯結構”與“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之間的區別,拉倫茨并未明確地予以說明,我們只能從其透露的片言只語中推測大概的原因。我們注意到,拉倫茨曾強調:“法條是規定性語句”,可以“劃入命令語句(祈使句)的類別之中”⑩。同時,他還提到,陳述性語句“可以被加上‘真’或‘假’的謂語成分”?。從拉倫茨的這些片段性論述可以推測,他在分析法律規范時,受到了歐洲大陸流傳已久的“法律規范是否有真值”爭論的影響。?該爭論的結果是:大多數學者形成了共識,即認為,法律規范不能像陳述性語句那樣被賦予“真值”或“假值”,不能簡單、直接地運用邏輯方法進行分析,因此,不存在所謂的“法律規范的邏輯”,只存在“法律規范命題的邏輯”。?或許為避免上述麻煩,拉倫茨才轉向分析“法條的邏輯結構”,因為“法條是法律規范的語言形式”,是規定性語句,如此就可以避免“規范是否有真值”這一問題的困擾(即“約根森困境”)。
由于國內學者很少注意發生在歐洲大陸的、與法律規范有關的元理論討論,因此,人們經常不假思索地談論“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對于其后的元理論問題知之不多。但其實,由于法律規范不具備邏輯上的“真假”特性,因此,不宜直接分析其邏輯結構,也不宜在嚴格的意義上述說“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或“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除非如凱爾森那般,將“法律規則”界定為“對法律規范的描述”。?
當然,那并不意味著,不能運用邏輯方法分析法律規范。凱爾森在此問題上解說得非常清楚明白:“只要邏輯規則能適用于對法律規范進行描述的法律命題(它們有真有假),它們就能適用于法律規范,即便這種適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如果對這兩個法律規范進行描述的法律命題彼此矛盾,則這兩個法律規范就彼此矛盾,并因而不能同時被主張為有效的。”?也就是說,我們雖不能直接分析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但可以借助法律規范命題與法律規范之間的對應關系,間接分析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比凱爾森稍早一點的杜比斯拉夫在研究規范的邏輯特性時,做了大致類似的處理。他認為,只有在將要求性語句(requirementsentences,即規范)重構為有真假值的斷定性語句(assertion-sentences)之后,才可以分析規范的邏輯結構及規范的可推導性問題。?
綜上,若在不太嚴格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法條的邏輯結構” 混為一談; 但在非常嚴格的意義上,我們只能說“法律規范命題的邏輯結構”,對此學者們不可不察。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本文探討的是法律規范命題的邏輯結構,而非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或法條的邏輯結構。
二、為什么法律規范命題的邏輯結構不只是假言形式的?
在法律規范要素問題上,學者之間只存在些許爭議:有持“二要素說”者,有持“三要素說”者,還有持“新三要素說”者,更有持“多要素說”者?。但在法律規范的結構問題上,人們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即都認為,法律規范(或法條,或法律規范命題)的邏輯結構呈假言命題形式(或換一種說法即條件式),其前件是“行為模式”,后件是“后果模式”。如凱爾森認為:“法律命題是這種假言判斷,它們陳述出,在一種——國家的或國際的——向法律認知給定之法秩序的意義上,在由這一法秩序所確定的某些條件下,應當出現這一法秩序的某些后果。”?拉倫茨同樣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法條作為規范性語句的意義在于: 使法律后果被使用。根據它的邏輯形式,它是一種假言語句。這就是說,如果具體案件事實S 現實化了構成要件T,那么,法律后果R 對于該案件事實就總是適用。簡言之,R 適用于所有包含T 的案件。”?馮·賴特更是直接用充分條件假言公式表達法律規范,只是在到底該用“O(p→q)”(讀作“如果p,那么q”是應當的),還是該用“p→Oq”(讀作“如果p,那么q 是應當的”)上,頗為躊躇。?我國著名法律邏輯學家雍琦教授也曾將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表達為以下假言形式:“如果具有性質T 的人,并且出現情況W,那么,必須(禁止或允許)C,違者(或侵犯者)處以S。”
由上可以看出,將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解為假言形式,在法學家間頗為流行。但正如拉倫茨注意到的,“還有一類法條調整人或者人類聯合體的法律地位,例如,關于取得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國籍及住所的法條。命令說也只能將這類法條理解為不完整法條,因為它們的法律后果并未包含命令或禁止的內容”。也就是說,拉倫茨注意到,有一類法條根本沒有法律后果,這類法條如何能表達為假言形式? 為此,拉倫茨辯稱,這類法條是“不完整的法條”,“如果人們將取得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國籍等法律上的地位視為一種‘法律后果’,那么前述語句與其他規定權利或特定‘法律權力’ 之取得或喪失的法條一樣,都是完整的法條,雖然要等到它們作為其他法條發生其他法律后果的前提條件時,它們規定的法律后果的全部意義才會顯現。”亦即,拉倫茨認為,若將這類規范中的部分內容“視為”法律后果,則上述規范仍呈假言形式。
應當說,為維護“法條呈一種假言形式”這一帶有一定共識的觀點,拉倫茨可謂煞費苦心。但問題在于:是否所有此類規范都可轉換為假言形式?或者說,將所有此類規范全都“視為”假言形式是否妥當?筆者通過研究發現,有很多規范根本不帶有直接或間接的法律后果,因此,不宜將其轉換為假言命題形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該條款屬于普遍性法律規范,規制的是國家行為,且沒有附帶相應的法律后果。從邏輯的角度看,表達此類規范的命題是一個全稱直言命題,其中甚至沒有任何規范詞,此一命題很難如拉倫茨解說的那樣,間接轉化為假言形式的規范命題。誠如拉倫茨所見,在民法典中,很多法律規范是用全稱規范命題表達的,其種類遠超拉倫茨所說的“有關取得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國籍及住所的法條”。如我國民法典第二百零八條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登記。動產物權的設立和轉讓,應當依照法律規定支付。”該規定是由兩個帶有規范詞的全稱規范命題組成。又如,第一千零二條規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嚴受法律保護”,該規定同樣是通過兩個全稱規范命題表達的。眾所周知,在刑法中,有關罪名的規定絕大多數采用假言形式,但也有一些規范用全稱規范命題表達,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
其實,在法律中,另一種結構的法律規范——即“全稱+假言”形式的法律規范——也很常見。如《憲法》第五條第四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從邏輯的角度即可看出,該規范是由兩個規范命題組成:第一個是全稱規范命題,第二個可“視為”假言規范命題,即“若一切組織實施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則必須追究其法律責任”。這種結構的法律規范不只出現在憲法中,而且遍布所有部門法之中。由于其數量眾多,不勝枚舉,故不一一列出具體的例子。
應當說,“全稱+假言” 這一形式結構更符合“義務性規范”的特點,因為一個完整的義務性規范通常由兩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明確規定某類主體應承擔何種義務,第二部分進一步規定,若某類主體不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將承擔何種法律責任,及遭受何種制裁。其邏輯結構大致如下:
(1)法律主體S 應當(ought to do)實施行為p,或法律主體S 不得(be forbidden to do)實施行為p;
(2)若法律主體S 未履行上述義務D,則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R。
從邏輯的角度看,上述結構中的(1)是一個帶規范詞的全稱命題,指示法律主體應如何行為;(2)是一個假言形式的規范命題,指出若不履行相應義務,法律主體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邏輯學家卡斯特內達(Heckter-Neri Castaneda)在分析規范語句時得出了一個大致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義務性規范具有“二重性”特點,即一個完整的義務性規范通常包括兩部分:一是主要的義務規范,如“應當遵守諾言”;另一是次要的義務規范,如“如果沒有遵守諾言,則必須道歉”。次要的義務規范是對主要義務規范的一種補充,在主要的義務規范被違反后,次要的義務規范作為一種補救性義務而起作用。此處,我們不區分“主要義務規范”與“次要義務規范”,但認為,一個完整的義務性規范理應包括以上兩部分,因為在實踐中,人們就是如此設定義務的。如《民法典》第二十六條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撫養、教育和保護的義務。”第一千零六十七條進一步規定:“父母不履行撫養義務的,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給付撫養費的權利。”
至于授權性規范,很多是由“規范詞+全稱命題”組成,或直接由全稱規范命題表達。如,《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自然人依法享有物權。”該規范對應于一個全稱規范命題,意指“所有自然人都依法享有物權”。又如,第一百四十條規定:“行為人可以明示或默示作出意思表示。”該規范的邏輯形式表現為“規范詞+全稱命題”形式。當然,也有一些授權性規范采用了“全稱+假言”的形式,甚至還可能有更復雜的邏輯結構。邊沁在《論一般法律》一書中將一個授權性規范解構為:(1)最開始的條文是概括性許可的形式:“任何人都可以出口谷物到國外”;(2)排除性條款具有特定性禁令的效果:“除非市價超過每夸特44 先令”;(3)對第二級的排除性條款具有再許可的效果:“如果是為了國王軍隊的供給,可以繼續進行出口”;(4)針對最后提及的這項排除性條款的限制性條件,因而再次擴大了第一次禁令的范圍:“應事先從當地首席長官那里獲得許可證。”邊沁發現,這一完整的規范就是由一個直言語句和三個條件句組成。
綜上所述,法律規范命題的邏輯結構雖大多呈假言命題形式,但它并非唯一的結構形式。在各種各樣的法律文本中,“全稱+假言”形式的法律規范也很常見,它同樣是法律規范的一種重要形式。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法律規范在邏輯形式上直接表現為全稱規范命題。據學者陳顯武考察,德國法理論界對于法律規范邏輯結構及其特性的理解主要有兩種通常的看法: 第一種由法律涵攝模式之檢討出發,將規范理解為涵攝的大前提,將之表達為全稱量化模式,代表性人物有Herberger/Simon、Koch/Rüβmann、Alexy、Aarnio、Peczenik 等;第二種將規范理解為條件式,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魏因貝格爾。陳顯武的考察正好可以印證我的上述觀點。
當然,有學者可能會說,在邏輯上,所有的全稱命題都可化約為假言命題,因此,仍可以說,所有的法律規范在邏輯上都表現為假言形式。此一說法存在一定的問題,因為按此邏輯,所有的假言命題同樣可轉化為全稱命題,那是否意味著,所有的法律規范都表現為全稱命題形式?若如此,就犧牲了法律規范多姿多彩的特點,并會使法律規范的表達變得呆板起來。
三、與法律規范命題邏輯結構有關的元理論問題
人們習慣上將法律規范的類型劃分為授權性規范、義務性規范及禁止性規范,并分別用“允許型規范命題”、“應當型規范命題”及“禁止型規范命題”與之對應。而且,人們經常談及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如將“禁止”理解為“不允許”,將“應當”理解為“不允許不”,并總結出了“凡不禁止的都允許”等法諺。但人們很少對這些耳熟能詳的東西進行考察,探究其在邏輯上是否存在問題。其實,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可以揭示很多與法律規范有關的元理論問題,并發現其背后的深層次問題。
(一)“凡應當的都是實際存在的”、“凡應當的都是可能的”及“凡應當的都是允許的”?
由于這三個命題具有邏輯上的相關性,因此,放在一起討論。
明眼人一看,即會發現,第一個命題源于人們常說的“休謨問題”,即“‘應當’是否蘊涵‘是’”的問題,換句話說,能否從“應當”推導出“是”的問題。哲學家休謨發現,人們在日常的思維與論證活動中,經常由“應然”推“實然”。休謨對如此推導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這一質疑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同。
既然該命題已為休謨所批駁,為何此處還探討它呢? 這是因為該命題仍“暗含”在一些規范邏輯系統中。之所以說“暗含”,是因為一些有代表性的規范邏輯系統雖沒有明確提出該命題,但其語義理論卻將該命題引入進來。眾所周知,幾乎所有的規范邏輯系統在對語形進行解釋時,運用的都是“克里普克語義學”。按照克里普克語義學,所謂“應當”,是指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里都真;所謂“可能”,指至少在一個可能世界里是真的,而“是”則指在現實世界里是真的。由于現實世界只是眾多“可能世界”之一種,故“應當蘊涵是”。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大家都認為不能由 “應當”推導出“是”,邏輯上為何還要將它視為規范邏輯系統的一個元定理呢? 這與一些邏輯學家力圖打通規范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壁壘有關。按照一些邏輯學家的理解,在理想的世界里,所有“應為的行為” 都應被人們踐行,且應當為法律所調整,因此,“凡應當做的都是人們實際做的”。只不過在現實世界里,我們無法保證所有應為的行為都被人們實際踐行了。雖然該命題在現實領域為人們所摒棄,但并不表明其存在毫無意義,它至少揭示了某種邏輯真理。
第二個命題與第一個命題類似,同樣將規范世界與事實世界勾連起來,只是在程度上稍弱而已,即由“應當”推“可能”。哲學上稱該命題為“康德原則”,取材于康德的道德哲學三原則之一。對于該命題,法律人大多毫不猶豫地接受,絲毫不忌諱其也是“由應然推實然”。法律人常說:“法律不強人所難”、“法律不能把不可能之事規定為義務”,這兩句法諺其實是“凡應當的都是可能的”在法律領域的變種。在某種程度上講,“康德原則”為上述兩句法諺提供了元理論支持。但一些哲學學者對“康德原則”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康德原則”仍然過強,人們不能由“某個行為是應當的”,就推導說,“個人能憑自己的能力實現該行為”。陳波教授舉了兩個不支持該原則的反例:某人借錢時約定的期限到了,他應當歸還別人的錢,但此時卻身無分文;某人應當按時上班,但由于中途發生車禍而不能按時上班。這說明,這一原則仍違背人們的直覺。其實,“康德原則”是否成立,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可能”。在哲學上,“可能”有四種不同的意義:(1)邏輯上的可能性;(2)經驗上的可能性;(3)技術上的可能性;(4)相對于個人的可能性。由于法律規范是一種普遍性規定,針對的是普遍性行為,而非個體的特殊行為,因此,此處的“可能”并非指“相對于個人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法律上將某個行為規定為義務,只要該義務在“經驗上、技術上”能普遍實現即可,它不要求每個人都能現實地做到,故陳波所舉的反例不能證明“康德原則”在法律領域不成立。同時,此處的“可能”也不應指“邏輯上的可能性”,因為“邏輯上的可能性”只存在于理想世界里,此處的“可能”指的是一種現實可能性,故其包括“經驗上的可能性”與“技術上的可能性”。
第三個命題是所有規范邏輯系統都承認的定理,幾乎構成了規范邏輯賴以成立的基礎。它說的是:同素材的“應當型規范命題”(應當p)與“允許型規范命題”(允許p)之間具有一種差等關系,即若行為p 是應當的,則它一定是允許的;若行為p是不允許的,則它肯定是不應當的。
若對第三個命題做上述解釋,法律人肯定覺得,接受這一命題毫無困難。因為既然法律規定某個行為是應當的,則人們實施該行為肯定是允許的;反過來,若某個行為是法律不允許的,則實施該行為肯定是不應當的。這說明,這一命題不僅符合邏輯,而且符合人們的直覺與常識。但若結合前面的說法,即“應當p”表述的是義務性規范,“允許p”表達的是授權性規則,則上述命題又可能引發新的問題。因為上述命題的意思變成了:“若行為p 是義務性的,則它又是授權性的”,或者說,“凡義務性行為都是授權性行為”,這違反了現代人對授權性規范與義務性規范的理解。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這一方面說明,邏輯及日常生活中的“應當”、“允許”與法律中的“義務性規范”、“授權性規范”之間尚有一定的差異;另一方面說明,運用邏輯方法雖可以揭示法律規范背后的一些元理論問題,但同時會產生妥適性問題。這與邏輯系統只是一種封閉性、靜態性、形式性系統有很大關系,其難以準確刻畫具有開放性、動態性、實質性特點的法律體系的全部特征。若將邏輯世界理解為一種理想世界,規范世界就是一種現實世界;在邏輯世界里,矛盾是不允許存在的,而在規范世界里,矛盾與沖突無處不在,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存在上述一系列差異的原因,我們不能因為差異的存在而否認邏輯在規范分析上的作用。
(二)“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許的”與“凡不允許的就是禁止的”
“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許的”與“凡不允許的就是禁止的”,這兩個命題是規范邏輯的重要定理,幾乎在所有道義邏輯系統中都成立。在法律領域,人們經常提到幾個大致類似的法諺:“法不禁止便允許”、“法不禁止便自由”及“法無授權便禁止”;人們在述說上述法諺時,往往會加上一些限制:前兩個法諺適用于私法領域,遵循的是“權利推定”原則;后一法諺適用于公法領域,遵循的是“權力法定”原則。由此可見,上述二命題及與之相關的法諺在法律與邏輯兩領域都很常見,只是法律領域的限制比邏輯領域要多。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無反思地使用上述命題與法諺,將之視為邏輯真理或法律真理,其實,若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上述命題與法諺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
一般地,人們習慣上將“禁止”定義為“不允許”(即“Fp?┒Pp”)、將“允許”定義為“不禁止”(即“Pp?┒Fp”)。該做法表面上看起來并無不妥,但其暗含著引入了一個 “道義封閉原則”(deontic closure principle),該原則體現的規范思想可用圖示方法直觀地表示為:
在圖1 中,“圓” 表示整個規范系統,“Fp”與“Pp”呈矛盾關系,即非此即彼關系。通俗地說,它表達了這樣的思想:“不禁止的就是允許的”,或“禁止的就是不允許的”。該原則暗含著承認:規范系統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所有行為都為法律所調整,某個行為p 不是禁止的,就是允許的,哲學家們稱該原則為“道義封閉原則”。該原則雖然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但顯然不符合法律的現實情形。眾所周知,“法律不理會瑣屑之事”,法律只調整那些對于社會生活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與行為,因此,現實的法律系統不是一個封閉系統,而是一個開放系統,有很多行為并未進入法律的調整范圍之內。甚至可以說,法律只調整人類行為的一小部分。

圖1 封閉的規范系統
邏輯學家馮·賴特在建構道義邏輯系統時注意到了該原則隱含的問題,為此,他在“O”(即Ought,應當)、“P”(即Permit,允許)和“F”(即Forbid,禁止)三個規范算子之外,還設計了第四個規范算子“I”(即Indifferent,意指“道義中性的”),并提出了這樣一個道義命題:“Op∨Fp∨Ip”(讀作:“行為p 或者是應當的,或者是禁止的,或者是中性的”)。這說明,馮·賴特認識到,規范系統是開放性系統,在法律調整的行為之外,還存在大量未進入法律領域的行為。
在添加了規范算子“I”之后,規范系統變成了開放性的,用圖示方式表達為:
在圖2 中,“圓” 仍表示整個規范系統,“Fp”“Ip”及“Pp”之間呈反對關系,因此,在這樣一個開放性的規范系統中,“不禁止的就是允許的”與“不允許的就是禁止的”、“凡禁止的就是不允許的”等命題均不成立。反倒是“法不禁止便自由”這一法諺較好地反映了開放性規范系統的特點,因為“法不禁止”意味著“要么是允許的,要么法律未規定”。

圖2 開放的規范系統
此外,還有法律邏輯學家發現,“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許的”這一邏輯定理應用到法律領域,之所以出問題,與“允許”這一規范詞具有多義性有很大的關系。法律領域的“允許”至少可做兩種解釋:一是“法律明確授權的允許”,另一是“禁止的缺乏”。凱爾森也認為,“允許”至少包括兩種:“否定意義上的允許”與“肯定意義上的允許”,因此,在說“凡不禁止便允許”之類的法諺時,應首先弄清楚,此時的“允許”指的是什么。
總之,熟知非真知!一些法諺與邏輯命題雖被人們廣泛應用,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但細究起來,仍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元理論問題。這說明,這些邏輯命題與法諺有自己的適用域,若超出其適用域,真理就變成了謬誤。
(三)“應當做什么”與“可以不做什么”可以并存?
在各種邏輯系統中,命題“應當做什么”與“可以不做什么”之間是矛盾關系,二者不可并存。根據法律規范命題與法律規范之間的對應關系,在法律中,若一方面規定“應當做什么”,另一方面又或明或暗地規定“可以不做什么”,則意味著該法律內部存在規范沖突,這已成為一種常識。但這種常識在我國的法律領域似乎被人們顛覆了,因為在我國的一些法律中,人們經常看到兩者并存的情形。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眾所周知,該條款的出臺一方面是為了提高行政機關負責人的法治意識,促使他們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依法行政; 另一方面是為了有效化解行政糾紛,維護司法的權威與尊嚴。但據一些學者考察,該條款在實踐中的效果不佳,因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比率不是太高。
有人可能會說,這只能說明行政機關負責人法治意識不強,而不能說明任何其他問題。該說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并未切中要害,因為造成該狀況的主要原因還在于條款本身,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行政訴訟法》 中關于負責人出庭應訴的規定過于彈性,不具有拘束力,從其內容‘被訴行政機關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可以看出,雖然規定了‘應當’,但是并沒有規定應當的條件,也沒有規定‘不能出庭的’條件。”該學者側重從法理角度指出該條款存在的問題,但其實,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該條款的規定不合邏輯。從邏輯的角度看,該條款由兩個規范命題組成: 一是明確表述的,“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二是暗含著規定的,“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可以不出庭應訴”——說其是“暗含的”,是因為它可以從“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推導出來。這兩個規范命題相互矛盾,因此,與之對應的法律規范是相互沖突的。
按照邏輯原理,“由相互矛盾的命題可以推導任何東西”。具體到法律領域就是:若同一法律中包含相互沖突的規定,則行為人選擇任何一項規定都是既合法又合乎邏輯的。既然法律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就不能再規定其“可以不出庭應訴”,否則會大大削弱前一規定的強度,甚至抵消前一規定;并且,那等于給了行為人選擇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應訴,完全無可指摘。近年來,為彌補上述條款存在的問題,全國各地紛紛出臺了進一步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上述條款存在的邏輯缺陷。這說明,邏輯在立法中的作用不可小覷。
與上述條款具有類似結構的規定在法律中并不鮮見。如《勞動合同法》第十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第六十九條又規定:“非全日制用工雙方當事人可以訂立口頭協議。”從邏輯的角度看,這兩個規定肯定相互沖突,因為前一條款是全稱條款,它規定所有建立了勞動關系者都有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義務,但后一條款卻免除了部分人的義務,授權某些建立了勞動關系者可以訂立口頭協議,這等于部分否定了前一條款。此類相互沖突的法律條款出現在同一部法律中肯定不妥,因為它們在效用上相互抵消。不過,《勞動合同法》的這一規定比《行政訴訟法》的那一規定要明確一些,因為它限定了訂立口頭協議的范圍。
當然,有人會辯稱,上述這些規定雖不符合形式邏輯的要求,卻符合辯證邏輯的規則,因為它們處理的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在法律中的直接體現。在他們看來,《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第三款的準確意思是:在一般情況下,被訴行政機關的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在特殊情況下,可以不出庭應訴。此一說法雖有一定的道理,卻顯然夸大了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之間的不一致性;并且,我們無法否認,此類條款規定得不夠明確。人們會問:哪些情況屬于特殊情況? 在哪些情況下,被訴行政機關的負責人可以不出庭應訴? 正是由于法律對不出庭的情形規定得不夠明確,才使得被訴行政機關的負責人出庭比率不高。
或許為避免上述問題,一些法律在使用此類形式的規范時,會比較明確地劃定特殊情形的范圍。如《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離婚案件有訴訟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達意思的以外,仍應出庭;確因特殊情況無法出庭的,必須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
凱爾森曾專門研究規范沖突,稱上述這些類型的規范沖突為“雙邊的部分沖突”。也就是說,若一個法律規范一方面規定“某一類主體應當做什么”,另一方面又規定“該類主體(之中的部分人或在部分情形下)可以不做什么”,則無論站在哪個方面看,都存在規范沖突,但僅僅是部分沖突,因為只涉及“部分主體或部分情形”。凱爾森認為,這類規范沖突比“雙邊的全面沖突”要弱,并且,在法律中難以全然避免。
結 語
與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有關的元理論問題還有很多。如,一些法學家認為,法律規范的結構是條件式的,那么,作為前件的條件與作為后件的后果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邏輯關系嗎? 這種邏輯關系類似于包含在陳述句中的條件與后果之間的關系嗎?又如,由于法律規范的結構不只是呈假言命題形式,因此,規范沖突的類型會相應地增加,其種類甚至比凱爾森所歸納的還要多,但具體的規范沖突類型到底有哪些? 法律系統應排除何種類型的規范沖突,而容忍哪些規范沖突? 再如,由于規范不具有真值,因此,規范之間不能相互推導,即不能由立法者已頒布了某個規范,就推導出他肯定頒布了另外的規范,于是產生了這樣的問題:規范的權威性是如何傳導的? 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對上述元理論做全面的探討。
總之,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及其特性問題雖是一個老問題,但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簡單。著名法學家凱爾森在晚年曾專門對上述問題進行過深入而全面的討論,但對于其中的很多問題,并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甚至可以說,他只是拋出了很多問題,而回答的問題卻很少。本文更是一種淺嘗輒止式的探討,更多的問題需留待以后再解決。
注釋:
①直接探討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代表性文章有羅玉中:《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法學研究》1989年第5 期;李振江:《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分析》,《法學研究》1993年第1 期; 劉楊:《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新論》,《法制與社會發展》2007年第1 期; 魏治勛:《法律規范結構理論的批判與重構》,《法律科學》2008年第5 期;等等。
②④⑤⑥⑦雷磊:《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法學研究》2013年第1 期。
?該問題最初是由丹麥哲學家約根森提出的,其在1937年發表的“命令與邏輯”一文中提出:“陳述句有真假值,故可以建構起完整的真值語義學,而規范無所謂真假,如何運用真值語義學來判定其推論是有效的呢? ” 參見J?rgen J?rgensen.Imperatives and Logic,Erkenntnis,1937(7):288-296。阿爾夫·羅斯稱該難題為“約根森困境”(J?rgensen’s dilemma),參見Alf Ross,Directives and Norms,London/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1968,pp.235。后來,該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很多法學家與哲學家為解決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根據阿爾楚榮與布里津的研究,大多數學者明確地否認“規范邏輯”存在,代表性人物有邊沁(Jeremy Bentham)、奧 斯 丁(John Austin)、拉 茲(Joseph Raz)、約 根 森(J?rgen J?rgensen)、阿爾夫·羅斯(Alf Ross)、理查德·黑爾(Richard Hare)、曼弗雷德·莫里茨(Manfred Moritz)、本·漢森(Bengt Hansson),等等。只有少數學者堅持認為存在規范邏輯,著名的如卡林諾夫斯基(Georges Kalinowski)與魏因貝克爾 (Ota Weinberger)。參見Carlos E.Alchourrón,Eugenio Bulygin.The Expressive Conception of Norms,in Risto Hilpinen,New Studies in Deontic Logic.Dorgrecht:Reidel,1981,pp.95-124。還有學者(如塔麥羅)認為,存在兩種規范邏輯:一種是規范邏輯,其代表性的表達式為“It is obligatory(permissory)that A”,另一種是規范命題邏輯,其代表性的表達式是 “It is a fact that it is obligatory(permissory)that A”,前一表達式本身就是一個規范,后一表達式是一個規范命題。前一種規范邏輯是非真值函項性的,后一種規范命題邏輯則具有真值函項性質。參見Ilmar Tammelo.Outlines of modern legal logic,Wiesbaden,1969,pp.36。
?在《純粹法理論》第二版中,凱爾森明確地說到:“立法者頒布的法律規范和描述規范的陳述之間在邏輯上是有區別的。為了方便,我們用不同的術語來表示‘法律規范’(legal norms)和‘法律規則’(rules of law)”。參見Hans Kelsen,Pure Theory of Law (Second edition),translated by Max Knigh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73-74。其實,在“邏輯是否可直接應用于規范”及“是否存在獨特的規范邏輯”等問題上,凱爾森的思想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早期毫不遲疑地認為規范邏輯存在,中期提出變通方案:將邏輯直接應用于法律規則,間接應用于法律規范,晚期徹底否定邏輯可應用于規范,進而否定規范邏輯的存在。參見陳銳:《規范邏輯是否可能? ——凱爾森后期法哲學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年第2 期。
??[奧]漢斯·凱爾森:《純粹法學說》,雷磊譯,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96 頁。
?Walter Dubislav,“Zur Unbegr¨undlichkeit der Forderungssatze”,Theoria,1937(3):340.
?持“多要素說”者如馮·賴特與約瑟夫·拉茲。馮·賴特認為,法律規范的構成要素包括“特性”(character)、“內容”(content)、“適用條件”(condition of application)、“權威”(authority)、“主體”(subject)和“場合”(occasion)六者。參見George Henrik von Wright,Norm and Action,Routlegde &Kegan Paul Ltd,1963,p.70。約瑟夫·拉茲也認為,法律規范至少由“道義算子”(deontic operator)、“規范主體”(norm subjects)、“規范行為”(norm act)和“適用條件”(conditions of application)等四要素組成。參見Joseph Raz,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50。
?可參見Von Wright,“Deontic Logic”,Mind,1950(60):1-5;亦可參見Von Wright,Norms and Actions,London: Ro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