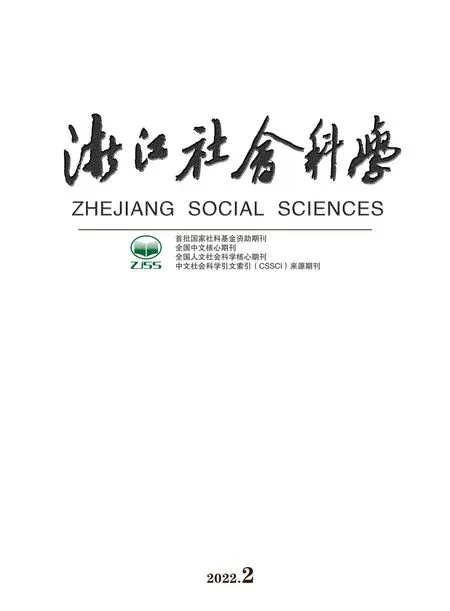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特征與建設(shè)路徑
——基于第七波WVS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
□ 張 忠
內(nèi)容提要 中國社會人際交往的“差序格局”特征決定了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研究不能采用西方“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二元對立的理論架構(gòu),而應(yīng)采用體現(xiàn)中國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連續(xù)統(tǒng)視角。本研究基于信任研究的連續(xù)統(tǒng)視角,通過對2020年最新發(fā)布的第7 波世界價值觀調(diào)查(WVS)中國大陸地區(qū)數(shù)據(jù)(2018)的分析得出如下結(jié)論:1.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依舊呈現(xiàn)出“從家人到熟人再到生人”的差序格局狀態(tài),對家人的信任極高,對熟人的信任較高,對生人的信任依然很低,且生人信任水平與第6 波WVS 數(shù)據(jù)(2012)之間無顯著性差異;2.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呈現(xiàn)出明顯的“連續(xù)統(tǒng)”特征,并非簡單的二元對立關(guān)系,雖然家人信任對生人信任無顯著性影響,但對熟人信任有顯著性影響,且熟人信任對生人信任存在顯著性影響。這一研究結(jié)果表明,當(dāng)前中國社會的生人信任水平依舊很低,人際信任建設(shè)仍然任重道遠(yuǎn);但由于熟人信任對生人信任的顯著性影響,因此重建熟人社會理應(yīng)成為當(dāng)代中國社會人際信任建設(shè)的重要參考路徑之一。
一、引言
自上個世紀(jì)90年代中后期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危機(jī)逐漸引起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以后,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研究已日益成為一門“顯學(xué)”。然而,任何對人際信任的研究都需要以一定的理論架構(gòu)作為參照,進(jìn)而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類型的性質(zhì)、形成條件、運(yùn)行機(jī)制等進(jìn)行分析,并在此基礎(chǔ)上探尋重建人際信任的路徑與策略。在此過程中,西方經(jīng)典社會學(xué)家關(guān)于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類型學(xué)研究或理想型劃分受到了國內(nèi)學(xué)者的關(guān)注,并成為觀照中國社會信任現(xiàn)狀、分析信任危機(jī)根源的重要理論來源與依據(jù)。當(dāng)然,也有不少研究者不認(rèn)同西方學(xué)者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類型的界定與描述,不過依舊未能擺脫西方學(xué)者理論框架的羈絆。在此背景下,堅(jiān)持本土化路線的研究者力圖突破西方學(xué)者的理論框架,建構(gòu)起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理論模型。這種理論方面的不懈努力雖然收到了成效,但后續(xù)實(shí)證研究的匱乏卻使得理論的“合法性”難以真正地確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能收到應(yīng)有的學(xué)術(shù)反響。本研究認(rèn)為,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特征的分析一方面不能盲目追隨西方學(xué)者的理論架構(gòu),另一方面在守護(hù)中國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立場上,也要從實(shí)證的角度對其理論模型進(jìn)行驗(yàn)證,從而對人際信任的重建提供實(shí)證依據(jù)與中國方案。
從體現(xiàn)中國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連續(xù)統(tǒng)視角出發(fā),本研究想要提出的問題是,在學(xué)界關(guān)注人際信任研究20 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究竟呈何特征?不同類型的信任之間是何種關(guān)系?對此種關(guān)系的揭示對當(dāng)代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建設(shè)有何啟示意義? 圍繞以上問題,本研究對2020年最新發(fā)布的第7 波世界價值觀調(diào)查(World Value Survey,WVS)中國大陸地區(qū)的數(shù)據(jù)(2018)進(jìn)行分析與討論,并試圖給出相關(guān)答案。
二、文獻(xiàn)綜述
(一)西方經(jīng)典學(xué)者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形態(tài)的論斷
眾所周知,國外學(xué)者早就探討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和現(xiàn)代社會中的信任問題,其中影響最大且爭議最多的當(dāng)屬韋伯、雷丁、福山等人的觀點(diǎn)。
韋伯在論述中國宗教時,區(qū)分了普遍主義信任與特殊主義信任兩種類型,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信任屬于特殊主義信任,并從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層面分析了中國人難以建立普遍信任的根源。他著重分析了儒家倫理對“孝”的過分強(qiáng)調(diào)——“百善孝為先”,在很大程度上增強(qiáng)了人們對家族內(nèi)成員的認(rèn)同,并指出“它意圖將個人歷久彌新地與其氏族成員牢系在一起,并將他嵌入氏族的模式中,不管怎么說,他是系于‘人’,而非事的職務(wù)”。①總之,“中國的倫理,在自然生成的(或被附屬于或被擬制成此種性質(zhì)的)個人關(guān)系團(tuán)體里,發(fā)展出其最強(qiáng)烈的推動力”。②而“倫理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的倫理的、禁欲的各教派——之偉大成就,即在于打破氏族的紐帶。這些宗教建立起優(yōu)越的信仰共同體,與倫理性的生活樣式的共同體,而對立于血緣共同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與家庭相對立。從經(jīng)濟(jì)的角度上來看,這意味著將商業(yè)信用的基礎(chǔ)建立在個人的倫理資質(zhì)上”。③據(jù)此,韋伯認(rèn)為基督新教的信仰共同體與經(jīng)濟(jì)生活方式更能促進(jìn)普遍信任的形成。
雷丁在其《華人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沿襲了韋伯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沒有宗教基礎(chǔ)就沒有道德契約,沒有道德契約就沒有企業(yè)家階層,沒有企業(yè)家階層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fā)展”。④他深入探討了東南亞海外華人企業(yè)賴以成功的精神資源,認(rèn)為支撐華人家族企業(yè)的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企業(yè)的新的“資本主義精神”,儒家文化是其精神內(nèi)核,諸如家長主義、人格主義、實(shí)用主義、孝敬、仁慈、互惠、責(zé)任、節(jié)儉等。但作者也指出,華人家族企業(yè)大多是小企業(yè),大企業(yè)少之又少,華人家族企業(yè)的優(yōu)勢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其劣勢。作者特別指出,有限的信任或信任危機(jī)限制了華人家族企業(yè)的發(fā)展,盡管華人企業(yè)家“在討論中也承認(rèn)對信任的渴望,明白自己的缺點(diǎn)所在,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似乎又無法克服”。⑤在雷丁看來,華人社會是一個縱向嚴(yán)格、橫向松散的結(jié)構(gòu)狀態(tài),華人“最主要的特征是完全相信自己的家庭,對朋友和熟人的信任完全取決于相互依賴的程度和投入到他們身上的‘面子’。你不會對他人的信譽(yù)妄下結(jié)論,你有權(quán)希望別人友好并遵從社會規(guī)范,但除此之外你必須料到,他們也和你一樣認(rèn)為自己和家庭的利益至上。能清楚知道自己的動機(jī)并將心比心,絕大多數(shù)人都將獲益良多”。⑥總之,雷丁認(rèn)為華人受家庭主義文化的影響,對家族以外的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承繼韋伯觀點(diǎn)的福山在其產(chǎn)生廣泛世界影響并為其帶來巨大學(xué)術(shù)聲譽(yù)的《信任:社會美德與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繁榮》一書中,論述了信任文化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關(guān)系。福山在考察了不同國家的文化后,將中國、法國和意大利南部歸為低信任文化國家,其根源是家庭主義文化以及社會中間組織的薄弱導(dǎo)致難以建立普遍化的信任。福山指出,中國儒教的核心“是把家庭奉為社會關(guān)系最完美的化身——中文稱為‘家’——家中的所有人都服從它。對家庭的責(zé)任勝過所有其他責(zé)任,包括對皇帝、對上蒼或任何其他的世俗或宗教權(quán)威的責(zé)任和義務(wù)”;“五綱中關(guān)鍵的關(guān)系是父子關(guān)系,因?yàn)樗⒘说赖铝x務(wù)‘孝’,或稱‘孝道’,這是儒教最重要且必須履行的道德責(zé)任。”⑦同時他將日本、德國和美國歸為高信任文化國家,其根源在于這些國家的文化具有自發(fā)組織社群生活的傾向,如日本的收養(yǎng)制度、德國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同業(yè)公會、美國的宗派宗教生活等,這些文化特質(zhì)都有利于提升非親緣關(guān)系的信任,從而有利于建立超越家族企業(yè)的大型現(xiàn)代企業(yè),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的繁榮。
(二)本土學(xué)者對西方學(xué)者相關(guān)論斷的回應(yīng)
面對西方學(xué)者將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視為特殊信任、家族主義信任的論斷,無論是中國港臺地區(qū)的學(xué)者,還是大陸學(xué)者都從理論分析與實(shí)證研究兩個方面做出了回應(yīng)。
港臺學(xué)者,主要是中國臺灣學(xué)者,試圖以組織中的信任研究為突破口,從中發(fā)現(xiàn)一些普遍主義信任的特征或因素。例如,高承恕等人在對臺灣地區(qū)企業(yè)內(nèi)外部的復(fù)雜關(guān)系進(jìn)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之后,認(rèn)為傳統(tǒng)的地緣、血緣關(guān)系并不能對此進(jìn)行有效解釋,于是嘗試性地提出了具有本土色彩的“信任格局”概念,并試圖用這一擴(kuò)大了親屬關(guān)系范圍的概念來重新描述老板與員工之間的關(guān)系。他們所謂的信任指的是一種“人際的信任(personal trust)”,“是一種針對特定個人的親近、熟悉所衍生的信任”。⑧在他們看來,在企業(yè)內(nèi)部“信任格局的形成會因關(guān)系、表現(xiàn)而異,親與才都是造成信任不同的因素;親與才是因,信任是果”。⑨后鄭伯壎在此觀點(diǎn)上又做了進(jìn)一步的拓展。
鄭伯壎通過對涉及臺灣民營企業(yè)和大陸國營企業(yè)中信任關(guān)系的已有研究資料的分析,發(fā)現(xiàn)“除了關(guān)系之外,忠誠與才能是影響上對下信任的重要因素,而仁厚與正直則是影響下對上信任的重要因素”。⑩由此,研究者認(rèn)為,隨著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演進(jìn)、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企業(yè)的增長,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與互動的日益頻繁,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也逐漸打上了普遍主義信任的烙印。
在大陸地區(qū),針對福山提出的“中國人對外人極度不信任”的觀點(diǎn),彭泗清認(rèn)為中國人是否信任他人不能簡單地以“內(nèi)外有別”來做為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作者兩次調(diào)查研究的結(jié)果表明,“人們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來增加對外人的信任程度”,“關(guān)系運(yùn)作是建立和增強(qiáng)信任的重要機(jī)制”;“在長期合作關(guān)系中,情感的關(guān)系運(yùn)作方法較受重視,而在一次性交往中,工具性的關(guān)系運(yùn)作方法較受重視;在經(jīng)濟(jì)合作關(guān)系中,人們除了采用關(guān)系運(yùn)作方法之外,還會采用法制手段來增強(qiáng)信任,關(guān)系運(yùn)作與法制手段可以共存”。?
楊宜音通過個案研究探討了“自己人”在信任建構(gòu)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認(rèn)為“自己人”這一概念表達(dá)了中國人信任對象的范疇以及如何將他人納入這一范疇的過程; 中國人自我的邊界是一條具有伸縮性的信任邊界,既有“區(qū)別內(nèi)外”的功能也有“自己人與外人內(nèi)外轉(zhuǎn)化”的功能;自己人這種信任建構(gòu)本質(zhì)是“關(guān)系性信任”。并且,作者預(yù)測“在交往不斷增多的情況下,它所包括的心理成分將與關(guān)系身份形成分離,有可能蛻化為人際間個人特性信任并成為契約制度信任的個體社會心理基礎(chǔ)”。?楊宜音的觀點(diǎn)盡管與彭泗清存在一定差別,但也有相似之處,即中國人是通過什么方式來信任“外人”的。當(dāng)然,這兩個研究只是在微觀層面對西方學(xué)者關(guān)于“中國人極度不信任外人”觀點(diǎn)的回應(yīng)。
針對韋伯和福山關(guān)于中國人的信任是一種“血親關(guān)系本位”的特殊信任,以及韋伯關(guān)于中國人缺乏以觀念信仰共同體為基礎(chǔ)的普遍信任的論斷,李偉民和梁玉成提出了質(zhì)疑。他們利用中山大學(xué)廣東發(fā)展學(xué)院2000年 “廣東社會變遷基本調(diào)查”項(xiàng)目的數(shù)據(jù)進(jìn)行了實(shí)證研究,結(jié)果表明:中國人雖然主要信任有血緣關(guān)系的家庭親屬成員,但也信任有著親密交往關(guān)系、無親屬關(guān)系的親密朋友; 中國人對無血緣關(guān)系但有一定社會交往與關(guān)系的其他人并非普遍和極度的不信任; 血緣家族關(guān)系并非制約中國人信任他人的惟一因素,關(guān)系中的情感內(nèi)涵也起到重要作用; 中國人以關(guān)系為取向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與根據(jù)有關(guān)人性的基本觀念信仰所確定的對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是各自獨(dú)立的,即并非相互包容或相互排斥。?該研究結(jié)果與韋伯和福山的觀點(diǎn)有較大差異。
對于西方學(xué)者的一個普遍性結(jié)論,即儒家文化對身處其中的個體的一般信任水平產(chǎn)生負(fù)效應(yīng)的論斷,胡安寧和周怡認(rèn)為,對這一議題的探討除了要進(jìn)行跨文化、跨地區(qū)的比較之外,還要在個人層面上探討某一社會內(nèi)部儒家文化對一般信任的影響。他們認(rèn)為,儒家文化對一般信任水平的影響可能存在兩種機(jī)制,即所謂的“關(guān)系機(jī)制”和“類別機(jī)制”。前者會強(qiáng)化一種親疏有別的差序格局,而后者則可能形成一種文化身份認(rèn)同的 “團(tuán)體格局”。他們通過對2007 中國居民幸福感及文化娛樂生活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分析表明,當(dāng)人們更多地重視儒家文化中強(qiáng)化差序格局的實(shí)踐與主張時,儒家文化與一般信任是負(fù)相關(guān)的關(guān)系; 而當(dāng)將儒家文化作為一種身份認(rèn)同的話,認(rèn)同者則表現(xiàn)出對他人的高信任;且儒家文化強(qiáng)化對“自己人”的信任并不會削弱對“外人”的一般信任。?然而,對胡安寧和周怡的研究結(jié)論,學(xué)者翟學(xué)偉并不認(rèn)同。他指出,研究背后的理論假設(shè)非常重要,對中國人而言,“真正影響到信任關(guān)系的是虛實(shí)相間的家庭生活,而非儒家思想本身”。?作者進(jìn)而提出,理解中國社會的信任不應(yīng)采取二元對立的理念架構(gòu),諸如有信任與沒信任、特殊信任與一般信任、正效應(yīng)與負(fù)效應(yīng)等,而應(yīng)建立一種關(guān)系視角來理解中國社會的信任。?
(三)二元理論架構(gòu)解釋中國社會人際信任形態(tài)的困境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可以看到,長期以來西方社會學(xué)家關(guān)于信任的研究一直就打上了二元對立的思想烙印,諸如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低信任文化與高信任文化、家庭主義信任與陌生人信任等。這種二元對立劃分的背后是西方學(xué)界關(guān)于個體與群體、理性與非理性、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經(jīng)驗(yàn)與價值等作二元式劃分的思維傳統(tǒng)在社會學(xué)領(lǐng)域的延續(xù)。這種二元對立的理論框架自然有其貢獻(xiàn),至少在研究之初,它能通過理想型的確立讓我們看到不同的信任類型的性質(zhì)、特點(diǎn)、功能、產(chǎn)生條件、運(yùn)行機(jī)制等,從而對不同的信任現(xiàn)象進(jìn)行區(qū)分。但這類理論框架的最大問題在于忽略了相互對立的兩種信任形式之間相互轉(zhuǎn)化的可能性,以及在兩者之間存在中間狀態(tài)的可能性。當(dāng)然,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這類理論框架是否具有跨文化的解釋力,也是一個需要審慎對待、甄別與驗(yàn)證的問題。同樣,我們還可以看到,本土學(xué)者在對西方經(jīng)典學(xué)者論斷的回應(yīng)中,試圖說明中國社會仍然存在普遍信任的因素或證明中國人是如何將外人納入自己人圈子的轉(zhuǎn)化機(jī)制,但仍然沒有突破西方經(jīng)典學(xué)者的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或家人信任與外人信任的二元理論架構(gòu)。這種二元式劃分的西方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顯然不同于中國的連續(xù)統(tǒng)式或關(guān)系性的學(xué)術(shù)思維傳統(tǒng),也很難用來準(zhǔn)確概括中國社會的實(shí)際情形。
首先,這種二元對立式的劃分遮蔽了在家人信任與外人信任之間存在的第三種信任狀態(tài),即熟人信任。費(fèi)孝通先生認(rèn)為中國人的交往關(guān)系呈“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fā)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是一種連續(xù)統(tǒng)狀態(tài)。因此,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研究顯然不能僅僅關(guān)注家人信任,或者以家人信任的特征來涵蓋一切。本質(zhì)上,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一個熟人(關(guān)系)社會,這種基于血緣與地緣關(guān)系的人際交往不僅涵蓋家人,還包括村鄰、鄉(xiāng)黨、同學(xué)、同業(yè)者等,這一層次的信任特質(zhì)與家人信任和生人信任之間均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顯然,缺失對這一環(huán)節(jié)的研究并不能把握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本質(zhì)特征和進(jìn)化方向。
其次,這種二元對立式的劃分忽視了不同國家的歷史發(fā)展形態(tài)。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進(jìn)入現(xiàn)代社會的歷程顯然要遠(yuǎn)遠(yuǎn)晚于西方社會。依據(jù)西方學(xué)者的邏輯,特殊信任無疑是前現(xiàn)代社會的主要信任特征,而普遍信任則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主要信任特征。眾所周知,韋伯眼中的中國社會其實(shí)不過是儒家與道家共同維護(hù)的“一個巫術(shù)的樂園”,?而雷丁、福山眼中的華人社會也僅僅是上個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的中國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等地企業(yè)界的社會狀況。將中國傳統(tǒng)社會和海外華人社會的信任形態(tài)與同時期較發(fā)達(dá)的西方社會的信任形態(tài)相比,無疑是一種不切實(shí)際的比較,因?yàn)樗雎粤瞬煌瑖遥ǖ貐^(qū))不同的歷史發(fā)展形態(tài)。實(shí)際上也是一種有失公允的比較,暗藏著西方文明的優(yōu)越感。
第三,這種二元對立式的劃分凸顯了一種靜態(tài)的信任發(fā)展觀。信任的進(jìn)化應(yīng)該是一個從家族(庭)內(nèi)部走向社區(qū)(村鎮(zhèn))、陌生人社會(城市)的過程,是一個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正如鄭也夫所言,“同陌生人建立信任,是人類信任進(jìn)化歷史中的最后一章。”?將中西方社會的信任形態(tài)作二元對立式的劃分,實(shí)際上是持一種靜態(tài)的信任發(fā)展觀,不僅是對中國社會的一種消極偏見,更重要的是看不到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中國社會中不同信任形態(tài)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與轉(zhuǎn)化的可能。
綜上,我們認(rèn)為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特征的研究,一方面要堅(jiān)持中國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即應(yīng)從連續(xù)統(tǒng)視角或關(guān)系性視角對信任類型進(jìn)行劃分,并準(zhǔn)確把握不同信任形態(tài)之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 另一方面也要從實(shí)證的角度來加以檢驗(yàn),并為中國社會的信任建設(shè)提供相關(guān)依據(jù)。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shè)
費(fèi)孝通對中國社會人際交往的“差序格局”特征的揭示,表明中國人的人際關(guān)系由內(nèi)到外呈親疏有別的形態(tài)。楊國樞認(rèn)為,中國人的人際或社會關(guān)系,依其親疏程度可以分為三大類,即家人關(guān)系、熟人關(guān)系及生人關(guān)系。家人關(guān)系是指個人與其家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及其他家人)之間的關(guān)系,熟人關(guān)系是指個人與其熟人(親戚、朋友、鄰居、師生、同事、同學(xué)及同鄉(xiāng)等)之間的關(guān)系,生人關(guān)系是指個人與生人(與自己無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持久性社會關(guān)系之人)之間的關(guān)系。?根據(jù)楊氏這一契合中國人社會交往現(xiàn)實(shí)的經(jīng)典分類,本研究將中國人的人際信任分為三種:家人信任、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鑒于“差序格局”的交往方式對中國人的長期影響,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1: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仍呈“從家人到熟人再到生人”差序格局特征。
西方經(jīng)典學(xué)者對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二元對立的劃分,僅看到了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之間的差異,而沒有看到兩者通過中間形態(tài)轉(zhuǎn)化的可能。如果從體現(xiàn)中國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連續(xù)統(tǒng)視角出發(fā),我們會假定從家人信任、熟人信任到生人信任是一個連續(xù)體,家人信任會影響熟人信任,而熟人信任會影響生人信任。由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中國社會的家人信任、熟人信任與生人信任之間的關(guān)系呈連續(xù)統(tǒng)狀態(tài),即家人信任影響熟人信任、熟人信任影響生人信任,熟人信任是連接家人信任與生人信任的重要一環(huán)。
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村落或社區(qū)往往由同一個大家族演化發(fā)展而來,村落一般也以姓氏命名,因此血緣信任和地緣信任往往纏繞在一起,具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性和融合性。通常中國人也稱“鄉(xiāng)鄰”為“鄉(xiāng)親”,家人信任的經(jīng)驗(yàn)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遷移到對熟人(族人)的信任上。進(jìn)入現(xiàn)代社會,熟人身份的異質(zhì)性增強(qiáng),但中國人仍習(xí)慣以對待家人的方式來對待熟識的人,諸如“同事如兄弟”“同學(xué)如手足”“戰(zhàn)友如親友” 等都反映了人們潛意識里對待熟人的信念。可見,以“擬親化”的形式將熟人當(dāng)作家人一樣來看待,仍是中國人信任熟人的一種重要機(jī)制。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1 中國社會的家人信任對熟人信任有顯著性影響。
在中國社會,雖然基于血緣關(guān)系的家人信任與基于地緣關(guān)系的熟人信任具有一種內(nèi)在的融合性,家人信任的經(jīng)驗(yàn)在一定程度上能輻射到熟人身上,但對處于“差序格局”最外層的生人而言,家人信任經(jīng)驗(yàn)的輻射效應(yīng)就會變得很弱。這是因?yàn)樵趶摹凹胰说绞烊嗽俚缴恕钡男湃芜B續(xù)統(tǒng)上,家人關(guān)系本質(zhì)上是一種“放心關(guān)系”,即“親人與信任之間具有極高的同質(zhì)性”,而家人與生人之間的異質(zhì)性很強(qiáng),既無血緣關(guān)系的相屬,又無地緣關(guān)系的勾連,因此家人信任的經(jīng)驗(yàn)很難遷移到生人身上。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2 中國社會的家人信任對生人信任無顯著性影響。
從人際信任的連續(xù)統(tǒng)來看,熟人信任居于家人信任與生人信任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它既受家人信任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生人信任。生人信任之所以受熟人信任影響,我們認(rèn)為一方面,生人信任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正如鄭也夫所言,“不可想象,系統(tǒng)信任(陌生人信任)會從親屬間的信任中直接生長出來,‘熟人間的信任’ 是從親屬到抽象系統(tǒng)間的中間環(huán)節(jié)。系統(tǒng)信任與熟人間的人格信任的關(guān)系,就像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二者似乎對立,實(shí)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繼承。沒有一個現(xiàn)代化社會是徹底打碎傳統(tǒng)后建立的。”另一方面,雖然熟人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地緣、業(yè)緣、學(xué)緣、趣緣等關(guān)系,但不可否認(rèn),這其中有很多“熟人”其實(shí)是從一開始的“生人”轉(zhuǎn)化而來的,因此這種將生人轉(zhuǎn)化為熟人加以信任的經(jīng)驗(yàn)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到生人信任。據(jù)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3 中國社會的熟人信任對生人信任有顯著性影響。
四、數(shù)據(jù)來源與變量測定
本研究采用的數(shù)據(jù)源于2020年最新發(fā)布的第7 波世界價值觀調(diào)查中國大陸地區(qū)的數(shù)據(jù)。上海交通大學(xué)國際與公共事務(wù)學(xué)院民意與輿情研究中心實(shí)施了問卷調(diào)查,調(diào)查對象的總體為居住在中國大陸31 個省、市、自治區(qū)以內(nèi)、并在抽樣區(qū)縣居住6 個月以上的18-70 歲的成年人。2018年在中國地區(qū)的調(diào)查采用了“GPS/GIS 輔助的區(qū)域抽樣”方法,按照分層多階段的PPS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to Size)抽樣方式獲取樣本,最終的有效樣本量為3036。
(一)因變量
本研究中因變量主要是熟人信任與生人信任。在世界價值觀調(diào)查(WVS)問卷中主要是通過“您對下面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 是非常信任、信任、不太信任還是很不信任”這一題項(xiàng)來測定人際信任的程度。置信對象主要包括:“家人”“鄰居”“熟人(同事、朋友)”“第一次見面的人”“與您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其他國籍的人”。每小題有四個選項(xiàng):“非常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非常不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為便于分析,本研究將“非常信任”和“比較信任”合并為“高信任”,編碼為“1”;將“不太信任”和“非常不信任”合并為“低信任”,編碼為“0”,從而生成一個二分變量。由于本研究所指的熟人信任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對鄰居、同事和朋友等的信任,因此所測量的熟人信任分別指的是對WVS 問卷中的 “鄰居”“熟人(同事、朋友)”的信任程度;而生人信任指的是對“第一次見面的人”的信任程度。
(二)自變量
本研究中自變量主要是家人信任和熟人信任。在WVS 問卷中,家人信任是指對置信對象中“家人”的信任,熟人信任是指對置信對象中“鄰居”“熟人(同事、朋友)”的信任,編碼方法同上。
(三)控制變量
參照國內(nèi)外同類研究的經(jīng)驗(yàn),本研究中納入回歸模型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地區(qū)、居住地、性別、年齡、年齡平方、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家庭經(jīng)濟(jì)滿意度、家庭收入水平、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社會地位、教育水平、職業(yè)狀況、一般信任等。
五、結(jié)果與分析
(一)當(dāng)今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格局分析
本研究運(yùn)用第七波中國大陸地區(qū)的WVS 數(shù)據(jù)考察了當(dāng)代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總體格局。表2 顯示的是中國社會居民在家人信任、鄰居信任、熟人(同事、朋友)信任、生人信任四種信任類型上從“非常信任”到“完全不信任”四種信任程度的頻數(shù)各自所占的百分比。由表2 可知,在家人信任這個維度上,高信任(非常信任與比較信任)的比例高達(dá)99.3%,低信任(不太信任與完全不信任)的比例只有0.7%;在鄰居信任上,高信任的比例為84.0%,低信任的比例為16.1%;在熟人信任維度上,高信任的比例為88.2%,低信任的比例為11.8%;在生人信任維度上,高信任比例為13.4%,低信任比例為86.6%。由于本研究所指的熟人信任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既包括鄰居信任,又包括狹義層面的熟人(同事、朋友)信任,因此綜合以上數(shù)據(jù)可知,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依舊呈現(xiàn)出“從家人到熟人再到生人”的差序格局特征,對家人的信任極高,對熟人的信任較高,對生人的信任依然很低。這與王紹光和劉欣、胡榮和李雅靜、李濤等、王佳和司徒劍萍、竇方等的研究結(jié)果相似。這說明,在當(dāng)代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關(guān)系仍然是影響人際信任的重要因素。由此,假設(shè)1 得到了驗(yàn)證。由于考慮到生人信任是反映一個社會的人際信任水平高低的重要標(biāo)志,本研究還將第7波WVS 的生人信任水平與第6 波的WVS(2012)生人信任水平進(jìn)行了卡方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第7 波和第6 波的生人信任水平之間無顯著性差異(X2=0.515,P>0.05)。這表明與2012年相比,2018年中國居民的生人信任水平?jīng)]有顯著性提升。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

表2 不同信任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
本研究認(rèn)為,雖然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呈“差序格局”特征,但不能簡單地用“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二元對立的觀點(diǎn)加以區(qū)分,而應(yīng)采用連續(xù)統(tǒng)視角重新認(rèn)識家人信任、熟人信任與生人信任之間的關(guān)系,從而為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信任重建提供實(shí)證依據(jù)。表3 主要呈現(xiàn)了家人信任對鄰居信任、熟人(同事、朋友)信任和生人信任的二元Logistic 回歸分析結(jié)果; 表4 則呈現(xiàn)了鄰居信任、熟人(同事、朋友)信任對生人信任的二元Logistic 回歸分析結(jié)果。
1.家人信任對鄰居信任、熟人(同事、朋友)信任的影響效應(yīng)分析。
由表3 模型1 和模型2 可知,在控制了一系列相關(guān)變量后,家人信任對鄰居信任、熟人信任仍具有顯著性的影響,具體為:對家人高信任者的鄰居信任發(fā)生比是對家人低信任者的7.57 倍;對家人高信任者的熟人信任發(fā)生比是對家人低信任者的3.44 倍。由此,假設(shè)2.1 得到了驗(yàn)證。家人信任是人際信任的起點(diǎn),首先從物理的時空角度來看,家人信任經(jīng)驗(yàn)的積累依賴于家庭這一特殊場域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雙重保證。就時間向度而言,家人之間的交往頻率是最為頻繁的,它提供了一種可以對成員的言行與承諾進(jìn)行預(yù)測的“穩(wěn)定性”;就空間向度而言,家的范圍是有限的,它保證了遵守諾言以及對失信行為進(jìn)行懲罰的“有效性”。其次從傳統(tǒng)的價值觀來看,儒家思想中以“孝”為核心的家庭倫理標(biāo)準(zhǔn)強(qiáng)調(diào)了血親成員之間的等級關(guān)系以及家庭內(nèi)部成員之間以“養(yǎng)”為主的義務(wù)關(guān)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強(qiáng)化了家庭成員間的認(rèn)同與依賴。家人信任的經(jīng)驗(yàn)之所以能遷移到熟人身上,筆者認(rèn)為,首先這是因?yàn)槿粘I钪腥藗兯佑|到的熟人大部分仍具有類似于家庭這一場域的時空特征,如鄉(xiāng)村、社區(qū)、單位等,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視為家庭的“放大化”。因此對熟人行為預(yù)測的“穩(wěn)定性”和對失信行為進(jìn)行懲戒的“有效性”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作用,因此對家人的信任經(jīng)驗(yàn)仍可以遷移到熟人身上。此外,作為儒家積極倡導(dǎo)的作為“孝”之倫理延伸的“忠”“義”“信”等亦可遷移到熟人身上。
2.家人信任對生人信任的影響效應(yīng)分析
由表3 模型3 可知,在控制了一系列相關(guān)變量后,家人信任對生人信任無顯著性的影響。由此,假設(shè)2.2 得到了驗(yàn)證。如前所述,家人信任經(jīng)驗(yàn)的積累有賴于家庭這一特定場域在時空上的保證,以及傳統(tǒng)“孝”道的維系。而與生人的交往則缺

表3 家人信任對鄰居信任、熟人(同事、朋友)信任影響的Logistic 回歸分析
(二)對不同類型信任之間關(guān)系的實(shí)證分析
乏類似于家庭這一特定場域的時空特征,即它在時間上是不穩(wěn)定的(隨意性的),在空間是不確定的(偶遇式的),表現(xiàn)出某種“脫域”的色彩。此外,盡管雷丁在分析華人社會的資本主義精神時所提出的“(儒家)真正的仁義從來不會有效地、可靠地擴(kuò)展到家庭范圍之外”的觀點(diǎn)過于狹隘,但如果說中國人的“仁”不是“普遍之仁”而是“差等之仁”,應(yīng)該不會有太大異議。從這層意義上來講,中國人“仁”的惠及面也是有親疏之分的。正如學(xué)者翟學(xué)偉所指出的,家人關(guān)系本質(zhì)上是一種“放心關(guān)系”,因而對家人的信任經(jīng)驗(yàn)顯然難以直接遷移到陌生人身上。
3.鄰居信任、熟人(同事、朋友)信任對生人信任的影響效應(yīng)分析
由表4 模型4 和模型5 可知,在控制了相關(guān)變量后,鄰居信任、熟人(同事、朋友)信任對生人信任有顯著性的影響,分別為:對鄰居高信任者的生人信任發(fā)生比是對鄰居低信任者的3.40 倍;對熟人(同事、朋友)高信任者的生人信任發(fā)生比是對熟人低信任者的4.69 倍。由此,假設(shè)2.3 得到了驗(yàn)證。事實(shí)上,學(xué)界以往對熟人信任與生人信任關(guān)系的研究分別得出了“無關(guān)論”“拮抗論”和“關(guān)聯(lián)論”三種相互矛盾的結(jié)論。如尤斯拉納就認(rèn)為,對熟人的信任(策略主義信任)與生人信任(道德主義信任)之間沒有聯(lián)系,也不可能產(chǎn)生遷移。因?yàn)榍罢叩幕A(chǔ)是具體的“個人經(jīng)驗(yàn)”,而后者的基礎(chǔ)是“信仰他人與你共有基本的道德價值”。根據(jù)信任的連續(xù)統(tǒng)理論,本研究假定熟人信任對生人信任具有影響效應(yīng),并得到了經(jīng)驗(yàn)數(shù)據(jù)的驗(yàn)證。我們認(rèn)為,熟人信任是走向生人信任的重要一環(huán),雖然家人信任對熟人信任有顯著性影響,但熟人畢竟不同于家人,在更嚴(yán)格的意義上熟人也屬于“外人”,如果對熟人不信任,那么個人的信任半徑將會向內(nèi)收縮,很難繼續(xù)向外延伸。此外,除了地緣的因素外,業(yè)緣、趣緣、學(xué)緣等也是構(gòu)成熟人信任的重要基礎(chǔ),而對這些人的信任則顯然有別于血緣意義上的家人信任與傳統(tǒng)地緣意義上的熟人信任,因而也是構(gòu)成生人信任的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

表4 鄰居信任、熟人(同事、朋友)信任對生人信任影響的Logistic 回歸分析
六、結(jié)論與討論
中國社會人際交往的“差序格局”特征決定了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研究不能采用西方“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二元對立的理論架構(gòu),而應(yīng)采用連續(xù)統(tǒng)的思維視角。只有這樣,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特征,并為重建人際信任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議。以往我國學(xué)者對西方學(xué)者的回應(yīng)要么是基于西方學(xué)者的理論框架,而忽視中西方社會的重要差異;要么是局限于“本土化”模型的理論演繹,而缺乏實(shí)證研究的支撐。本研究基于信任的連續(xù)統(tǒng)視角,通過對最新發(fā)布的第七波中國大陸地區(qū)WVS 數(shù)據(jù)的分析,從實(shí)證的角度得出如下結(jié)論:
第一,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依舊呈現(xiàn)出“從家人到熟人再到生人”的差序格局狀態(tài),對家人的信任度極高,對熟人的信任度較高,對生人的信任度依舊很低,且生人信任水平與第6 波WVS(2012)數(shù)據(jù)的生人信任水平之間與無顯著性差異。
第二,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呈現(xiàn)出明顯的“連續(xù)統(tǒng)”特征,并非簡單的二元對立關(guān)系,主要表現(xiàn)為:雖然家人信任對生人信任無顯著性影響,但對熟人(鄰居、同事和朋友)信任有顯著性影響,而熟人信任對生人信任存在顯著性影響,是連接家人信任與生人信任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對于家人信任、熟人信任與生人信任之間連續(xù)統(tǒng)關(guān)系的揭示,對于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建設(shè),特別是生人信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國內(nèi)雖然有研究者提出,“一個人如果在與自己關(guān)系親密的群體中都無法建立良好的特殊信任,那么肯定也不利于他與相對陌生群體一般信任關(guān)系的建立”,但尚缺乏實(shí)證數(shù)據(jù)的支撐。本研究的重要發(fā)現(xiàn)之一則是,熟人信任對生人信任存在顯著性影響,讓我們看到了熟人信任對生人信任的積極影響效應(yīng)。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就是一個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穩(wěn)定保證了傳統(tǒng)社會的有效運(yùn)行。當(dāng)然熟人社會的穩(wěn)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熟人之間的相互信任維系的。而這種熟人信任的長期維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鄉(xiāng)村共同體相對穩(wěn)定的人際網(wǎng)絡(luò)、家族(家庭)的聲譽(yù)機(jī)制、鄉(xiāng)紳鄉(xiāng)賢等的權(quán)威與聲望以及以祠堂和社廟所代表的超自然懲戒力量等的保證。今天,隨著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人們開始步入了一個“半熟人社會”乃至“生人社會”。從“家人信任到熟人信任再到生人信任”是一個完整的信任連續(xù)統(tǒng),熟人信任處于家人信任與生人信任之間,居于非常重要的過渡位置。如前所述,由于家人信任的經(jīng)驗(yàn)不可能直接遷移到生人身上,因此熟人信任的經(jīng)驗(yàn)積累對于生人信任就顯得非常重要。鄭也夫指出,人格信任(熟人信任)與系統(tǒng)信任(陌生人信任)“二者似乎對立,實(shí)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繼承”。由于生人信任建立的條件相對復(fù)雜,我們不能說良好的熟人信任必然會導(dǎo)致令人滿意的生人信任,但在較低的熟人信任基礎(chǔ)上則很難建立和維持一個生人信任水平較高的社會。在這一層意義上,熟人信任的重建依舊是通向生人信任的重要路徑。
帕特南在其產(chǎn)生世界影響的《獨(dú)自打保齡:美國社區(qū)的衰落與復(fù)興》 一書中運(yùn)用社會資本的理論分析了上個世紀(jì)后三分之一的時期里美國社區(qū)公民參與如何走向衰落的原因。帕特南通過對大量數(shù)據(jù)的分析后認(rèn)為美國公民在政治參與、公民參與、宗教參與、工作聯(lián)系、社會聯(lián)系、志愿活動和慈善活動參與、社會信任等方面均出現(xiàn)了下滑趨勢。其中在對“非正式的社會聯(lián)系”進(jìn)行分析時,帕特南指出,雖然“公民參與”、“民主協(xié)商”等是“更高形式的社會參與”,“但在日常生活中,是友誼和其他非正式的社會交往提供了關(guān)鍵性的社會支撐”,像諸如工作之后的聚餐、飲酒、打撲克、鄰居間的閑聊、跑步者之間的點(diǎn)頭致意等都能增加社會資本,提升社區(qū)凝聚力。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里,在許多活動上,我們與朋友、鄰居的經(jīng)常性聯(lián)系都出現(xiàn)了劇烈下降”,“我們和鄰居變得疏遠(yuǎn),拜訪老朋友的次數(shù)變得更少了”。他根據(jù)綜合社會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分析發(fā)現(xiàn),“1974-1998年間,美國人‘與鄰里共度社交之夜’ 的頻率下降了約三分之一”; 而另外的一些證據(jù)則表明,“與50年代中期相比,90年代鄰里聯(lián)系的緊密程度可能下降了一半多”。非正式的聯(lián)系其實(shí)更多的是熟人之間的聯(lián)系。熟人之間聯(lián)系的普遍降低也是美國社會資本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顯而易見的是,熟人之間聯(lián)系的削弱必然導(dǎo)致熟人信任的下降,而熟人信任的降低也會造成單薄信任(生人信任)的衰落。按照帕特南的邏輯,這種熟人間的信任也是促進(jìn)單薄信任(生人信任)的重要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因?yàn)椤斑@種信任(單薄信任)也隱隱植根于某種共同的社會網(wǎng)絡(luò)與互惠期待的背景之中”;且“這樣的社會信任與許多其他形式的公共交往與社會資本都有緊密的聯(lián)系”。因此,重視社區(qū)層面的非正式聯(lián)系與日常互動,也是增進(jìn)包括信任在內(nèi)的社會資本的重要路徑。
今天隨著城鎮(zhèn)化建設(shè)的加快、人口流動的日益頻繁,傳統(tǒng)熟人社會的格局正在被打破,人們在走出傳統(tǒng)社交圈子后,迫切需要在新的社區(qū)中重建熟人信任。今天的熟人信任已不同于傳統(tǒng)鄉(xiāng)村共同體或上個世紀(jì)80、90年代城市單位職工生活區(qū)中的熟人信任。現(xiàn)代社區(qū),特別是城市社區(qū),居民信息的非全知性、零星的社區(qū)活動、較少的鄰里互動和相對封閉的生活空間,使得社區(qū)內(nèi)的熟人信任建立緩慢而低效。本研究發(fā)現(xiàn),城市居民的鄰居信任發(fā)生比只有農(nóng)村居民的0.47 倍(見表3 模型1),存在顯著性差異,說明城市居民對鄰居的信任水平遠(yuǎn)低于農(nóng)村居民。而當(dāng)“殺熟現(xiàn)象”衍生的各種負(fù)面效應(yīng)被媒體一再聚焦和放大的時候,也給熟人信任蒙上了一層陰影。一個社會當(dāng)熟人信任都難以建立和維持時,生人信任的前景更難以令人樂觀。當(dāng)然,今天熟人信任的重建,不只是親友團(tuán)、老鄉(xiāng)會、同學(xué)聯(lián)誼會等“內(nèi)群體”關(guān)系的加強(qiáng),而更應(yīng)該是社區(qū)層面的熟人信任的重建。且這種社區(qū)層面的熟人信任重建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其更多異質(zhì)性因素的融入不僅使這種熟人信任從根本上有別于傳統(tǒng)基于地緣關(guān)系的熟人信任,同時它也將是通向生人信任的一條重要通道。當(dāng)然,今天社區(qū)層面的熟人信任如何重建,確實(shí)也是一個復(fù)雜的社會系統(tǒng)工程,它不僅需要由上而下的規(guī)劃與發(fā)動,更為重要的是需要人們自下而上的自發(fā)運(yùn)動。概而言之,重建今日的熟人社會,理應(yīng)成為當(dāng)代中國社會人際信任建設(shè)的重要參考路徑之一。
注釋:
①②③?[德]韋伯:《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319、320、277 頁。
⑦[美]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85 頁。
⑧陳介玄、高承恕:《臺灣企業(yè)運(yùn)作的社會秩序:人情關(guān)系與法律》,《東海學(xué)報》1991年第32 卷,轉(zhuǎn)引自鄭伯壎:《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本土心理學(xué)研究》1995年第3 期。
⑨鄭伯壎:《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本土心理學(xué)研究》1995年第3 期。
⑩鄭伯壎:《企業(yè)組織中上下屬的信任關(guān)系》,《社會學(xué)研究》1999年第2 期。
?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機(jī)制:關(guān)系運(yùn)作與法制手段》,《社會學(xué)研究》1999年第2 期。
?楊宜音:《“自己人”: 信任建構(gòu)過程的個案研究》,《社會學(xué)研究》1999年第2 期。
?李偉民、梁玉成:《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中國人信任的結(jié)構(gòu)與特征》,《社會學(xué)研究》2002年第3 期。
?胡安寧、周怡:《再議儒家文化對一般信任的負(fù)效應(yīng)》,《社會學(xué)研究》2013年第2 期。
??翟學(xué)偉:《也談儒家文化與信任的一般關(guān)系》,《社會科學(xué)》2013年第6 期。
?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 頁。
?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華人本土心理學(xué)(上)》,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