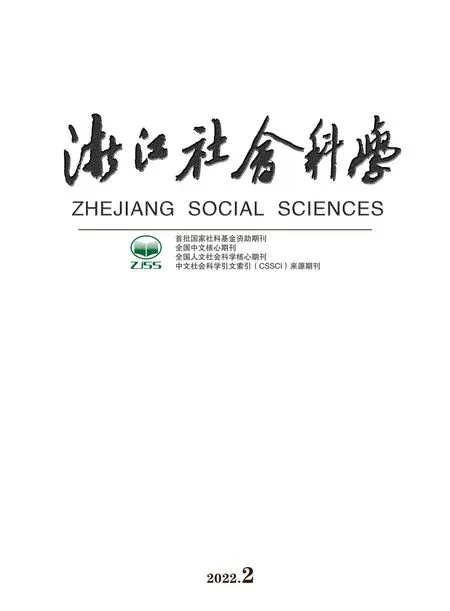項目制幫扶驅動共同富裕:一個分析框架*
——基于杭州市“聯鄉結村”幫扶項目的實證研究
□ 胡天禛
內容提要 項目制幫扶是新時期黨和國家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舉措,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項目制幫扶具有多種形態,作為對傳統科層制結構的延展和突破,其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制度控制能力與政策動員能力兩者的均衡。制度控制能力和政策動員能力的強弱差異形成了四種不同的運作形態,“強制度控制——強政策動員”模式是實現項目制幫扶有效運作的最優策略。杭州市“聯鄉結村”幫扶項目,通過縱向穿透、橫向協同、創新財政體制和雙向驗收強化了政府制度控制能力,通過聚合性動員、參與性動員、情感性動員相互疊加強化了政府政策動員能力,提供了項目制幫扶助力共同富裕的可行方案。
項目制作為一種既能夠體現國家意志又能夠帶入市場競爭的治理方式,已經充分嵌入到了當代基層治理之中。①近年來,各級政府通過開展項目制幫扶,解決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改善基層較低收入群體生活狀況,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和富裕程度,②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已有研究大多從“中央與地方關系”,即項目決策者或執行者的角度來分析項目制的運作機制,但無法很好地解釋為什么項目制幫扶在不同地區的幫扶效果呈現出較大差異的現象。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近年來實施的“聯鄉結村”幫扶項目為例,基于制度控制和政策動員的分析框架,對項目制幫扶促進城鄉統籌驅動共同富裕的機制與成效做一實證分析。
一、幫扶項目中的制度控制和政策動員
21 世紀以來,國家、城市與農村的關系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國家不僅不再汲取農村資源,反而試圖通過取消農業稅、低保政策、扶貧開發等治理手段向農村輸送資源,進而實現城鄉協調發展。③但在扶貧及其他基層實踐中,由于科層制中上下權力失控也出現了決策執行錯位的“共謀”④、“變通”⑤和“選擇性執行”⑥等現象。⑦項目制作為一種替代制度具有解決這類問題的能力,被廣泛運用于精準扶貧、對口幫扶在內的,以基層治理為目標的國家治理體系之中。
(一)制度控制
制度控制即項目制內部行政控制,是上級政府以制度化方式約束項目內部成員使其有效貫徹項目任務的機制。這一概念來自周雪光等的項目制“控制權”理論。制度控制意味著項目“委托-代理”關系的產生與組織層級結構有因果關系。項目制在內的政府組織結構是由其權力關系塑造的,這種權力關系被視為控制權在不同層級和部門之間的分配方式,從而形成了三種維度的控制權:目標設定權、檢查驗收權、實施激勵權。⑧在這種組織結構中,項目決策者往往將幫扶目標設定后逐級或直接下壓,并以數目字的方式對執行者做考核,借助“壓力型體制”,實現組織控制。⑨上級政府指定的干部晉升考核制度及其指標為基層政府官員提供了明確且強有力的政治激勵,將個人政治晉升與項目完成績效掛鉤,能夠顯著地影響項目成員的偏好與行為。⑩雖然觀點不盡相同,然而當前研究普遍認同,制度控制對幫扶項目中行動者行為及項目成效帶來制度性動力。
但是,在項目制的施行過程中當設計目標與實際執行之間存在偏差時,項目執行者雖無法拒絕執行政策,卻能通過理性考量決定是否有效執行相關政策。?例如在政策適用性低的情境下,基層政府因為執行壓力會交替選擇消極執行和運動式執行的方式,甚至形成“資源動員”?和“實動、暗動、偽動、緩動”?等執行策略。?下級政府為完成項目,進行“抓包”摻入自身意圖,既要完成項目要求的形式要件,又要基于實際情況“打包”項目,實現資源的重新配置,實現發展目標。?在考慮制度控制機制對幫扶項目成效提升作用的同時,還需考慮其附帶的“執行錯位”現象。在科層壓力和晉升激勵的雙重驅動下,基層干部對幫扶項目的總體性支配有所加強。?基層干部主導了幫扶項目申請、資源分配、運行過程和評估驗收等環節,將自身利益嵌入項目目標,使幫扶陷入“扶大不扶小,扶強不扶弱”的困境中。?
(二)政策動員
政策動員能力指的是政府自上而下促使村民或第三部門參與項目并配合項目執行的能力。?組織學研究視角下的政策動員有兩種含義,第一種強調群眾自下而上的動員,第二種強調政府通過調動資源,動員群眾來支持其所推動的事業,即政府自上而下的動員,本文選取了第二種定義。?中西學界普遍認為,第三部門在與政府互動中可提升公共項目的績效。?但是,國內學者探討項目制中的政策動員時選擇的出發點往往是政府內部動員,如運動型治理、多線動員、層級動員等,鮮有學者討論自上而下的政策動員對項目落實的積極意義。對于幫扶項目中政策動員能力而言,尤其缺乏深入探討。
政策動員通常被理解為非常規的政府非正式制度行為。具體到幫扶項目,項目成效體現于幫扶對象增收指標之上,社會參與亦是提升收入水平的要件之一。正如一位縣扶貧辦主任所說,“幫扶效果好不好,往往也要看社會參與得積極不積極。”因此,除了制度控制之外,政府對社會的動員也應視為影響幫扶項目執行成效的重要因素。項目制幫扶中的政策執行受到不同形式的動員約束:(1)政府側發動政策動員的能力。項目中政府的策略方法、資源運用和優先順序對政策動員的發起過程產生影響,策略方法運用得當,資源分配到位的政府行動會對社會團體形成較強的動員效果。(2)項目的組織化及響應程度。項目參與各方的組織力量和積極性對項目資金技術配置造成影響,項目的組織化程度越強,并且對政策動員積極響應是正向的,則會形成較強的動員效果。(3)幫扶對象及其所在社會網絡的能動性。處于項目制落實末端的幫扶對象所在社會網絡對項目執行的主動回應能力也會對項目落地效果產生直接影響,能動性越強則項目落實效果越好。
(三)幫扶項目治理及其變遷的分析框架
制度主義組織學認為,行政組織和社會行動者一起參與了制度腳本的再生產和重構。制度不僅是自上而下塑造的,也是自下而上的。依據前文所述,并考慮任務資源等外部因素,作者建構了一個四種理想型的坐標系分析框架。四種類型分別對應四種具體的幫扶項目治理模式,見下圖1。

圖1 幫扶項目治理及其變遷模型
強制度控制—強政策動員(模式1)。在這種治理模式中上級政府通過制度化方式強有力約束項目內部成員單位使其有效貫徹項目任務,同時政府能夠有效動員各方社會力量參與到項目執行的過程中。這一模式是幫扶項目制運作執行的理想狀態下的最優策略。弱制度控制—強政策動員(模式2)。這種治理模式強調政府對社會的動員以有效執行項目,在幫扶項目之中,項目執行者借助社會團體和當地社會網絡,將政策目標落地。弱制度控制—弱政策動員(模式3)。當上級政府未能有效約束項目成員單位執行工作時,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政策傳輸紐帶也呈現割裂狀況。此時,項目目標實現困難。強制度控制—弱政策動員(模式4)。這種治理模式中,上級政府能通過制度化方式強有力約束項目成員單位貫徹項目任務,上級組織為每位項目執行者分解任務、分攤責任,但由于社會力量薄弱,項目執行者需要親歷親為承擔幫扶督導等落地工作。在幫扶項目治理模型中,我們需考慮制度控制和政策動員以外影響治理模式形成的外生變量。基層政府的任務情境是由其所處的制度與社會環境建構的,包括項目制中的任務來自上級政府及其部門主官們創設的行政派生性任務和項目執行依賴人力和財力等資源。
由此,本文提出一個幫扶項目的理論假設(模型),這一理論假設有兩個層次。首先是靜態層次,除了常見的政府之間縱向府際關系的解釋變量以外,引入動員要素探討項目制中關鍵行動者的策略選擇和行為差異。此外項目制中的任務變量和資源變量作為外生關系共同影響了項目治理模式的形成。其次是動態層次,無論當地使用哪一種治理模式,如果在項目考核評估績效不達標的情況下,上級政府會動議使用制度控制或政策動員機制,強行改變現有項目治理模式,促進幫扶績效的提升。
行政力量在項目制運作之中仍然處于主導性地位,上級政府通過制度控制將任務傳遞至鄉鎮、村社執行者,并向多元主體募集項目運作資源;在社會網絡發達的村社,村兩委則可能將任務“分包”給村自治組織和積極分子,減少其問責壓力和工作壓力,從而實現一種“行政主導,多方協同,社會參與”的幫扶項目運作的新形態。
為驗證幫扶項目及其變遷模型的解釋力,以及總結“聯鄉結村”項目運作的經驗成果及優勢劣勢,作者于2014-2021年對浙江省杭州市受益于該項目的近30 個村社進行了歷時8年的田野調查。資料的收集方法包括參與觀察、半結構訪談和深入訪談。通過多案例比較研究方法,選擇幫扶項目中制度控制能力和政策動員能力差異較為明顯的3 個村作為比較組案例,以增強驗證理論命題的效度。
二、杭州市“聯鄉結村”幫扶項目的運作機制
2007年開始,杭州市通過設立“聯鄉結村”幫扶項目,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改善較低收入群體生活狀況,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和富裕程度,至今已經堅持近15年。15年來,項目主要目標一直圍繞著低收入農戶持續增收和發展特色產業提升結對村集體經濟,始終保40 個左右幫扶團隊,每個團隊由一位市領導擔任組長,每個團隊由10-15 家單位組成(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醫院、學校、商會等),其中一家市級部門牽頭,定點幫扶一個偏遠鄉鎮。相比較以往的扶貧開發政策,“聯鄉結村” 項目的組織機制大幅度地提升了幫扶工作的效率和精度,確保幫扶運作機制的長效落實。
從制度控制上看,其一,政府縱向層級關系的重新組合。幫扶項目中的權力關系雖然依舊是科層部門之間的分配方式,但是市領導掛帥層級高且將原有“市-縣-鄉鎮”三個層級打穿為“市-鄉鎮”兩個層級的特征,使得幫扶項目在維持組織的控制權同時,提升了縱向決策執行的績效。在實際工作中也得到了印證:幫扶團隊在開展工作時,一般直接聯系對口鄉鎮,財務直接結算,項目直接落地,人員直接對接。其二,多元主體協同的橫向關系建構。幫扶團隊由機關、企業、學校、醫院、商會等多部門組成,形成一個非正式組織,打破單位之間壁壘,有助于在幫扶行動中發揮各自優勢和特長。例如:積極推進農旅結合的鄉村,由旅游、規劃部門幫扶,同時旅行社又是幫扶團體成員,使得幾個部門能對幫扶項目迅速達成一致,有效避免了“看得見管不著”和“管得著卻看不見”的問題。其三,財政體制的創新設計。牽頭單位確定項目任務并負責召集各方籌措資金,提升了項目運作的連貫性和精準性。以往的農村財政受到很多掣肘,財政也無法有效傾斜。“聯鄉結村”項目開辟了一條財政“綠色通道”,幫扶單位從各自的辦公經費、利潤當中,省出一部分資金直接撥付到幫扶鄉鎮的帳戶中,實現了精準直達;市農辦對每個團隊均提供一定的保障性幫扶資金,使得團隊在行動之初就更有底氣。其四,檢查驗收的雙向壓力。牽頭部門和市農辦雙管齊下,對每年的幫扶資金籌措情況在一定范圍內公開的同時,對項目進展情況進行考核驗收,始終保持著對被幫扶鄉鎮和幫扶單位的雙向壓力。
總結以上“聯鄉結村”幫扶項目在制度控制層面的特征,我們將這種幫扶機制歸納為“幫扶集團制”,即重構傳統科層制的幫扶項目控制模式。傳統的精準扶貧項目受到鄉村振興局(扶貧辦)系統的總體統籌,扶貧部門系統分為國家、省、市、縣、鄉鎮五級,由省扶貧部門做統籌和宏觀決策,并對全省各類項目進行監督和考核。其中縣一級扶貧部門是項目入戶的主要推動者,既要落實上級扶貧部門的指示,又與幫扶單位駐村干部對接,組織扶貧工作指導培訓。而杭州市“聯鄉結村”項目扶貧的核心推動者是市領導及其牽頭單位,并由市領導和牽頭市級部門自主確定幫扶任務,召集各方主體組建幫扶集團,落實項目幫扶工作。幫扶項目由牽頭市級部門具體落實、督察和驗收,并向市領導匯報。這種“幫扶集團制”項目從市一級直接落實到鄉鎮村社,貫通了以往由市、縣、鄉鎮,并以縣扶貧部門為主要推手的層級控制模式。高配的項目層級不僅提升了基層幫扶干部對項目的工作積極性,還對項目的財政和社會資金到位有所助益。
從政策動員上看,其一,上級政府對多元主體的聚合性動員。市領導和牽頭單位對幫扶團隊中各個主體進行動員,使其在幫扶行動中發揮各自優勢和特長,聚合資金、人才、技術等資源力量,形成合力。其二,基層政府對村社農戶的參與性動員。基層政府為了提升項目參與程度對村社農戶進行動員,幫扶對象所在社會網絡積極參與,幫助特色產業落地,從而確保自主增收。其三,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的關系受到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情感性動員,“聯鄉結村” 所確定的牽頭單位與被幫扶鄉鎮,還與“走親連心三服務”“領導干部蹲點”“年輕干部走訪實踐” 等其他扶貧開發制度高度重合,使得牽頭部門的派駐干部對被幫扶鄉鎮的感情因素更加深厚,提升了幫扶工作的深度和精度。
總結以上“聯鄉結村”幫扶項目在政策動員層面的特征,我們發現在“幫扶集團制”中存在有層次的多重行動網絡。在幫扶力量整合階段,為聚合幫扶集團內部的資源力量,形成了一種由市領導和牽頭單位為核心,各方主體積極參與的資源聚合行動網絡;在任務向下傳遞階段,為實現項目任務與行政執行的有效對接,牽頭部門及其派駐干部與被幫扶鄉鎮之間形成了一種縱向項目執行網絡;在幫扶政策落地階段,派駐干部和鄉鎮干部、村干部共同成為項目落地的直接負責人,與傳統意義上的精準扶貧項目不同,“聯鄉結村”項目的一個牽頭單位對接一個鄉鎮及其所有村社,項目落實工作除了派駐干部之外,也需要依靠鄉鎮干部和村干部的協助、關系和權威。從而形成了一種派駐干部、鄉鎮干部和村干部三方聯動的基層幫扶行動網絡。
三、幫扶項目運作機制的實證分析
實證部分作者使用“制度控制—政策動員”的分析框架探討杭州市在“聯鄉結村”幫扶項目具體實踐中的運作機制,并分析其優劣勢,總結提煉值得推廣的做法。在“聯鄉結村”項目任務中,確保低收入農戶持續增收的項目是最重要、最棘手的,也是市委市政府最重視的一項任務。杭州市政府文件中反復強調“聯鄉結村”項目要“廣泛動員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充分調動鄉鎮、村和農戶參與項目的積極性、主動性”實現“上下互動,聯情結親。”因此,每個幫扶集團都希望通過行政力量動員基層政府和民眾的能動性,實現項目績效。但是,由于各個地區的管理任務、行政力量、資源稟賦和社會資本等要素大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幫扶項目治理模式。在實證研究中,我們發現了制度控制能力和政策動員能力強弱配比不同且動態變化的四個案例。本文分別選取A 村中藥種植推廣和村莊環境整治(生豬集中圈養)、B 村蓮子養殖入戶、C村橘子種植推廣作為比較組,梳理不同幫扶項目運作機制及其情況。
(一)中藥種植推廣:從“強制度控制、弱政策動員”轉為“雙強”
中藥種植項目起始于對A 村結對幫扶的早期。2010年以前,牽頭市領導、牽頭單位將任務派給結對的鎮政府,由鎮農辦和扶貧辦組織A 村行政人員落實項目承接問題。但效果并不理想。對于最開始的簡單派任務方式村民并不買賬。“雖然村里有中藥材培育的傳統,但也不是每家每戶都種中藥,村干部很難做工作,村民不配合。”之后,鎮農辦和村委組織本市領域專家、本村中藥材種植大戶宣傳中藥材產業的經濟效益,效果依然不好。一段時間過去,這種“上面熱下面冷”的局面仍然沒有改觀。
項目情況上報后,市領導、牽頭單位認為可以利用本地強大的社會組織(如鎮特色中藥材產業協會、村婦女組織和青年組織)和幫扶集團內的行業協會(如市農業科學協會)來動員貧困戶承接項目。同時,牽頭單位派出城鄉規劃專業干部駐村,幫助該村開展項目承接和扶貧開發工作,并將一部分考核責任落實到幫扶單位身上,使駐村干部、鄉鎮干部、村干部達成了幫扶目標的共識。鎮政府每個月進行“紅黑榜”排名通報,排名末位的行政村由鎮黨委委員約談其村書記、分管干部,累計次數增多則加重處罰。除了末位排名機制外,“紅黑榜”通報也將反復在鎮書記、鎮長等鎮領導所在的微信群和工作場所展示,極大加強了工作壓力。因此,駐村干部、鄉鎮干部、村干部被置身于同一權責場域之中,三方行動者之間的組織認同邊界逐漸模糊,扶貧工作目標也趨于一致。
同時,幫扶也將本地社會組織和幫扶集團的行業協會帶入政策動員之中。杭州市農業科學協會和鎮特色中藥材產業協會派駐熟悉中藥材種植的專家和中藥材市場的銷售,專家協同項目執行者通過農產品價格、分布、產量、價格趨勢等預測農業產品利潤,利用市場引導經濟作物種植,拓展了精準科技支農、延伸了涉農產業鏈。A 村婦女組織和青年組織組建“婦女勸導小組”和“青年播種團” 動員女性和青年村民種植適宜自身情況的中藥苗種。村主要干部和駐村干部“以身作則”種植中藥,再后來,由于A 村創業人員陸續回鄉承包中藥種植,還帶動了外鄉人來A 村創業,更對村民承接項目進行二次帶動,尤其是A 村的中藥產業還逐步輸出到其他村,當地的種植能手到其他村指導種植并擴大生產,助推了村民自發的意愿,形成了良性循環。
(二)村莊環境整治:從“弱制度控制、強政策動員”轉為“雙強”
相對于中藥種植這類脫貧項目,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村莊環境整治更普遍地受到全體A 村村民的重視,村民戲言“人可以少賺點錢,但不可以生活在豬糞堆旁”。村莊環境整治項目一直貫穿在A 村“聯鄉結村”幫扶的整個過程。最開始,推行生豬集中飼養是擋在環境整治面前的一大難題。早年,A 村30%左右的村民散養生豬,相比本鎮其他村社占比較高,且養豬戶平均收入水平高于非養豬戶。因此,不希望集中飼養的養豬戶和希望集中飼養的非養豬戶之間勢均力敵,針鋒相對,矛盾激烈。由于A 村的社會關系網絡較為復雜,在村莊環境整治項目上馬伊始,兩派之間爆發了組織性械斗,相關信訪案件陡增45%,引發了一系列社會治安問題。
相關情況上報后,結對市領導立即與鎮政府、村書記溝通,要求通過村莊環境整治項目,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發揮好“解鈴還須系鈴人”的作用。鎮政府要求村兩委每兩個月匯報一次與村莊環境整治相關的與村民溝通工作,要求每次匯報均見成效,直到“大多數村民均支持生豬集中飼養”。于是,村兩委組織數次有關生豬集中飼養的村民會議,討論之初形成意見鮮明的正反兩方面意見,支持集中飼養與不集中飼養的不相上下。在協商過程中政策動員亦充分介入,村級自治組織如黨支部、婦工委扮演說服反對集中飼養的養豬戶的角色;幫扶集團中的市畜牧、農林等專業協會則從技術角度向猶豫的養豬戶介紹集中飼養的優勢,并擔保提供技術支持。經過多次開會協商動員,研究討論相關情況,最終僅以“2 票之差”的微弱優勢決定啟動集中飼養。解決了生豬散養問題后,村莊的動物糞便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嘗到甜頭的村民,對后續幾輪的沼氣池推廣、村莊美化等工作,都非常支持。由此,村民不用大量砍伐山林來充當柴火,植被得到了有效保護,生態環境變得越來越好,為后來走上“農旅結合”的道路奠定了堅實基礎。近幾年,隨著村莊景區化的推進,外出村民及鄉賢紛紛從離土到歸鄉,積極投身到村莊的致富實踐當中,自發摸索并興起了民宿、釀酒、房車營地、戶外探險等產業,“新農人”自發創業,并積極向“聯鄉結村”的重點幫扶項目靠攏的趨勢愈發明顯,形成了制度控制和政策動員的相輔相成效果。
(三)蓮子養殖入戶:從“雙弱”轉向“強制度控制、弱政策動員”
2017年“聯鄉結村”項目開始在B 村運作。在B 村幫扶項目推行過程中,其最大的問題源于本村人口數量多,2020年上報常住1400 戶;但缺少群眾自治團體,社會中也缺乏有威望的行動者,群眾組織能力較差。同時,村兩委工作人員少,上級設計的指標按照脫貧戶為單位計算績效,使得部分村干部“干得多,罰的也多”,“既然做不做都要被罰,還不如逃避不做,最后搞得村干部都想盡辦法躲避敷衍扶貧工作”,并且蓮子養殖技術難度較大,養殖費時費力,村干部也不愿帶頭示范。經過一段時間,B 村蓮子養殖入戶工作的績效得分始終排在本鎮所有村社排名的末尾,也多次受到牽頭單位、鎮領導的通報批評。
在了解B 村基本情況后,市領導、牽頭單位會同鄉有關部門對B 村扶貧發展情況作了調研并召開了現場工作會議。市領導指出B 村境況的產生有其深層次制度問題。鎮政府應采取激勵措施調動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之后,鎮政府重新分配幫扶自助小組的成員和片區,并增派人手。在項目推行安排中,本村312 位被幫扶戶分成了9 小組(每組約30-40 戶),每個小組配備一位村干部負責蓮子養殖政策宣傳、督導工作。鎮政府和縣扶貧辦工作人員直接對村干部的工作進行定期評估,按照脫貧績效標準為各小組負責人打分。由此,形成了一種“村干部分組執行”和“上級監督考核”的非正式層級結構。這種形式很快得到了市領導的認可。之后,B 村所在鎮將此做法深化推廣,設立了專門的“聯鄉結村”項目管理小組,管理小組通過整合鎮內部項目工作數據,每季度向上匯報給鎮領導,并選出每個村排名第一和倒數第一的村干部給以獎懲。同時,市領導及牽頭單位通過聚合性動員,幫扶集團中的多元主體亦對B 村蓮子養殖入戶提供協助:市規劃局為B 村在內的該鎮其他11 個村編制了發展規劃,調整了用地指標,撥出更多蓮子養殖及旅游用地,使得觀賞蓮和食用蓮科學配比;某旅行社為B 村設計了“十里蓮花”主題的旅游線路;某大學則為B 村提供了蓮子養殖技術培訓,增進了產量。同時,在機關工委、婦聯的聯合建議下,蓮子、羊奶、藕、連子酒、莼菜等一系列農副產品,出現在了直播帶貨的屏幕,使得一些滯銷產品銷售一空;目前,B 村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蓮子產業鏈,村民人均收入水平也超過了鎮平均水平。
由此可見,B 村的村干部在落實幫扶項目時受到了來自市、鎮兩級政府的管理壓力。雖然幫扶集團內部的多元主體在市領導及牽頭單位的組織下被充分動員,但基層社會組織卻沒有被動員起來。村干部本身既有特定行政任務,除此之外還需兼顧每組30-40 戶的扶貧任務,工作量極其繁重。“部分村干部無法實質上承擔扶貧責任,他們將上下班路上或日常其他任務的巡查視為順便關照了幫扶對象的項目承接情況,并以此為基礎撰寫上報材料。”而對于另一部分干部而言,日常村務也可以轉化為扶貧工作,“如果被幫扶戶到村委會反映問題,也可以被看作在扶貧指導中發現和辦理的,也同樣可作為工作成果。”因此,B 村村干部開始逐步動員本村22 位黨員和退休村干部參與項目管理工作中,每個小組分別配備2-3 名黨員和1 名退休村干部協助村干部,對幫扶對象進行管理,引導種植蓮子。
(四)橘子種植推廣:從“雙弱”轉向“弱制度控制、強政策動員”
C 村所在街道毗鄰本縣政府所在街道,街道居民之間擁有較為緊密的社會網絡。雖然C 村人均收入不及街道平均水平,但也擁有相對良好的村民自治傳統,村民自組織程度發達。但在結對幫扶初期,社會力量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幫扶工作陷入了一種“粗放式管理”的困境之中。直到市領導在對C 村的調研時發現,C 村緊密的社會網絡可以成為推動項目落地的重要工具,并指示C 村所在街道,鼓勵C 村通過社會力量落實項目執行工作,實現消薄增收。
由此,C 村近年來形成了一種以“村委會為主體,社會力量參與”的扁平化幫扶項目運作機制。C村將橘子種植推廣項目具體落實工作攤派給非正式組織和村積極分子。首先村兩委將橘子種植推廣項目分解為明確的任務,在村民議事會、監事會上宣讀任務分解詳情,向本村非正式組織和村積極分子“分包”任務。其次,“任務依照執行流程被分為諸多模塊,包括勸導村民承接、督導村民完成、協助村干部上報等。”再次,承包者將獲得兩部分報酬,一部分來自村集體經濟按月撥付工作津貼,另一部分來自上級政府獎勵資金中抽取的部分。同時,幫扶集團中的農業技術協會和農科院通過對幫扶對象上門指導和線上授課等方式,分別為C 村的橘子選種培育和產銷策略提供了協助。
村委會依照上級政府對本村考核標準,將指標細化后分配給橘子種植推廣項目的承包者。在這種機制下,市、鎮政府并未實質參與到幫扶項目的宣傳倡導中來,而只是例行的監督考核,因此無需增加工作任務,增設行政單位。但這種模式也遇到一定風險:(1)非正式組織和村積極分子沒有負擔項目的法律責任,如果最終項目扶貧效果不達標,被問責的主體依舊是村干部,因此“村干部在預見第三方無法完成橘子種植推廣任務的情況下,依然會直接介入項目,直至落地”;(2)承包項目的社會力量未受到橘子種植及推廣有關專業培訓,也無義務參與縣扶貧部門為村干部、駐村干部開展的幫扶培訓,涉及項目承接后種植、養殖等技術工作,還需依靠基層干部或幫扶集團成員支持。因此,C 村村委為強化該模式的穩定性,將項目評估周期從原先的月度改為兩周一度,并設“村干部負責制”,讓每位村干部監督部分項目的執行效力,力所能及時需親力親為。
綜上而言,在幫扶項目運作前后,四個考察案例的項目運作機制、行動者、政策制度制定與項目落實效果均發生了動態變化。無論案例所在地使用哪一種治理模式,如果無法按期滿足項目考核評估指標,市領導隨即發起動議,促使牽頭單位和鄉鎮政府使用制度控制或政策動員機制,強行改變現有項目治理模式,促進幫扶績效的提升,最終實現項目任務目標。與此同時,政府內行動者和社會行動者被充分納入項目運作的議程之中,落實與兩種能力緊密相關的政策制度,反向夯實變遷后幫扶制度,并最終呈現出“行政主導,多方協同,社會參與”的幫扶項目運作形態。
四、結論與討論
基于制度控制和政策動員的分析框架,本文對浙江省杭州市“聯鄉結村”項目中4 組案例的運作機制做了比較,結果發現,項目制幫扶過程中的制度控制能力和政策動員能力強弱組合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制度控制和政策動員兼備的能力配比在幫扶項目推行中得到了最優的效果,其他治理模式在績效評估標準引導下,逐步向最優或次優治理模式變遷。
在案例中,我們看到“聯鄉結村”項目較之“項目制精準扶貧”和“跨區域對口幫扶”等其他扶貧制度,具備更為強大的組織力量。這一力量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重構傳統科層制的幫扶項目控制模式使其具備了較強的制度控制能力。這一項目制不僅穿透政府縱向間的層級,將原有“市-縣-鄉鎮”三個層級打穿為“市-鄉鎮”兩個層級;而且協同多元主體重構了組織之間的橫向關系,市領導掛帥統籌機關、企業、學校等第一、二、三部門合力集聚幫扶資源。相比科層制和其他項目制,該項目制度在強化目標任務、資金資源和檢查考核等組織控制的同時,又為基層項目執行留下了充足的行動空間。在傳統的精準扶貧項目不僅“項目到村”還要“項目入戶”的基礎上,杭州市“聯鄉結村”項目既對農戶收入提升,又對村集體增收設置了量化考評指標。這意味著“聯鄉結村”項目除了設計幫扶普通村民的入戶項目以外,還要考慮設立實現村集體“消薄增收”的入村項目。因此,村干部需要為入村項目游說鄉鎮干部,并通過鄉鎮向牽頭單位“請示授權”,申請該年度或下年度的村項目,將一種精準幫扶中縱向政府間的非正式互動納入到正式的行政過程中。
另一方面,政府積極將各方力量納入項目議程之中使“聯鄉結村”項目擁有了較強的政策動員能力。除了上文所述市領導高配帶來的政治勢能對集團成員集聚資源的聚合性動員以外,我們還需看到“聯鄉結村”項目中的以下三個側面:其一,對幫扶對象及其所在社會網絡的參與性動員。幫扶項目的目標是為了讓幫扶對象能夠自主增收,因而激發其參與積極性是項目成敗與否的關鍵。擁有良好社會網絡基礎的村社更有可能全面參與到幫扶項目中去。其二,政策動員需要制度控制的引導。社會網絡基礎較好的村社擁有“自下而上”社會動員天然優勢,但其未必一定能夠精準嵌入幫扶項目之中。案例表明,政策動員需要來自政府一側制度控制的引導,才能將社會力量放置于幫扶行動的正向場域之中。其三,政府之間行動者重塑的情感動員。“聯鄉結村”項目的派駐機制與“走親連心三服務”“年輕干部走訪實踐” 等其他扶貧開發制度中派駐機制的相重疊,派駐干部常年往來同一鄉鎮展開幫扶工作,建構了深厚的情感基礎。由此,“聯鄉結村”項目在兼備制度控制能力和政策動員能力的同時,呈現出“行政主導,多方協同,社會參與”的項目制幫扶運作新形態。
然而,研究發現,“聯鄉結村”項目依然存在一些問題。首先,項目幫扶以農為主,農民穩定增收任務艱巨。當前“聯鄉結村”項目為幫扶對象增收目標設定的幫扶領域仍然以農業生產為主,以提高工資性收入和勞務性收入的項目不多,而且農業生產收入受環境影響較大,其收入來源的可持續性不強且缺乏一定的抵御風險能力。其次,村社既是項目的執行者又是項目的幫扶對象,其集體經濟收入質效不高,持續增收后勁不足。一方面,在項目制幫扶中,村委是幫扶項目落地的具體執行者,將入戶和入村的項目任務妥善落地,另一方面,村社集體經濟又是“削薄增收”的幫扶對象。然而,村社在項目中獲得的幫扶真正有效改善收入結構的并不多,所謂的“高增長”多發生在低基數起點上,實際的增量并不多。以幫扶成效最好的A村為例,其2019年收入減支出僅余0.3 萬元,村集體已無力承擔稍大一些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從事經營性生產活動,對幫扶項目執行也產生了困難。再次,農村社會組織化程度比較低,項目產業鏈延伸困難。雖然案例中有部分社會被定義為社會組織化程度較高,但在經濟生產層面,大部分的幫扶對象仍以低小散的家庭經營為主。土地細碎化是造成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重要原因。以B 村為例,大部分的土地分散成點,且集中在一些低丘緩坡上,實施規模化、機械化耕種比較困難,更談不上產業鏈的延伸。另外,小農經濟思想是影響組織化程度提高的阻礙因素。調研發現,一些幫扶對象不愿意將手中的土地流轉給村集體,這就造成本身有限的土地資源要素更加難以集中利用。最后,區域產業聯動的緊密度不高,帶動效應未完全顯現。由于“聯鄉結村”項目集團成員資源集聚具有多樣性特征,在推進農業生產的同時,也提供了生態旅游產學研等技術支持。但是,在這一系列產業中旅游產業收入最高,對區域帶動效應也主要集中于旅游業。以A、B 村為例,通過客源分流享受到發展紅利的幫扶對象主要是民宿業主,更多幫扶對象缺乏有效的渠道參與到區域產業整體發展中。
杭州市“聯鄉結村”項目制幫扶是“發揮城鄉協調發展優勢,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創新。可以說,以城促鄉是提升城鄉協調發展,實現鄉村共同富裕的基本動力,而幫扶項目則是重要的實踐工具和有效載體。新時期實現共同富裕中的項目制幫扶不僅需要追求來自政府的高效執行,而且需要著力構建與社會多元主體的協同互動機制,在摸清真實幫扶需求基礎上,制定落實政策目標,讓幫扶項目在“田間地頭運轉起來”。
注釋:
①周飛舟:《財政資金的專項化及其問題——兼論“項目治國”》,《社會》2012年第1 期。
②劉培林、錢滔、黃先海、董雪兵:《共同富裕的內涵、實現路徑與測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年第8 期。
③參見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3 期;王雨磊:《數字下鄉:農村精準扶貧中的技術治理》,《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6 期。
④周雪光:《基層政府間的 “共謀現象”——一個政府行為的制度邏輯》,《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6 期。
⑤孫立平、郭于華:《“軟硬兼施”: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過程分析——華北B 鎮收糧的個案研究》,鷺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⑥孫宗鋒、孫悅:《組織分析視角下基層政策執行多重邏輯探析——以精準扶貧中的“表海”現象為例》,《公共管理學報》2019年第3 期。
⑦其他現象參見陳家建、邊慧敏、鄧湘樹:《科層結構與政策執行》,《社會學研究》2013年第6 期。
⑧周雪光、練宏:《中國政府的治理模式:一個“控制權”理論》,《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5 期。
⑨渠敬東:《項目制: 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5 期。
⑩周黎安:《行政發包制》,《社會》2014年第6 期。
?折曉葉、陳嬰嬰:《項目制的分級運作機制和治理邏輯——對 “項目進村” 案例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 期。
?陳那波、李偉:《把“管理”帶回政治——任務、資源與街道辦網格化政策推行的案例比較》,《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4 期。
?陳玲、林澤梁、薛瀾:《雙重激勵下地方政府發展新興產業的動機與策略研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0年第9 期。
?陳家建、張瓊文:《政策執行波動與基層治理問題》,《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3 期。
?渠敬東:《項目制: 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5 期。
?馬良燦、哈洪穎:《項目扶貧的基層遭遇:結構化困境與治理圖景》,《中國農村觀察》2017年第1 期。
?龔為綱:《項目制與糧食生產的外部性治理》,《開放時代》2015年第2 期。
?K.Deutsch,“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5,No.3,1961,pp.493-514.
?參見王詩宗、楊帆:《基層政策執行中的調適性社會動員: 行政控制與多元參與》,《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 期。F.Yang,Z.Zhangand S.Wang,“Enlisting Citizens:Forg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Local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Vol.5,No.4,2020,pp.1-18.
?參見D.Riley,“Civic Associations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Interwar Europe:Italy and Sp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9,No.2,2005,pp.288 -310;D.Putnam,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謝岳、黨東升:《草根動員:國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3 期; 王天夫、羅婧:《基層多元共治的路徑選擇: 動員、補位,還是重構?》,《河北學刊》2017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