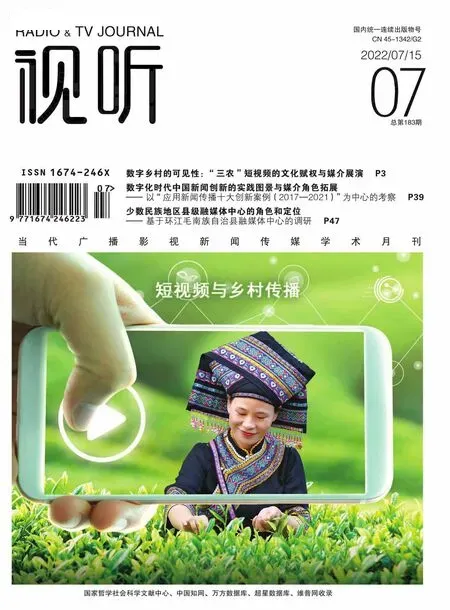《春江水暖》銀幕畫卷之審美意趣探析
劉 冉
近幾年,中國電影領域涌現的新力量不斷從中國傳統美學中汲取養分,為中國電影的民族化建設做出了有益探索。顧曉剛導演的《春江水暖》將中國傳統繪畫的卷軸美學移植到電影中,讓影像幻化成畫卷,探索出一種中國電影全新的美學樣態。
歌德曾說:“藝術要通過一個完整體向世界說話。”①所以,電影理應在電影語言、敘事以及影片意蘊方面都有所言,才能成為優秀的作品。電影《春江水暖》在言、象、道三個層面皆在構建獨屬于東方的審美意趣。其以中國繪畫的傳統技法對電影視聽語言進行建構,但沒有停留在形式層面的炫技,而是在鋪開富春江山水畫卷的同時展演了充滿煙火氣的平民史詩,從中見出眾生相。山水之自然與人間之煙火相融共生,而影片中的萬物也呈現出具有無限時空感的意境美,打造出一種獨屬于東方的時空觀和宇宙觀。
在進行藝術欣賞時,欣賞主體更偏向于將藝術作品當作整體,但在對其進行深入分析時,便會將其分為藝術語言、藝術形象、藝術意蘊。三者層層遞進,卻最終融為一個審美體。故本文從藝術作品的這三個層次對《春江水暖》進行審美意趣的探析。
一、山水畫卷:以傳統繪畫語言打造游觀體驗
藝術鑒賞是一個由表及里的體悟過程。觀者首先是被藝術作品極富魅力的外在形式吸引,而后經過注意、想象、情感等多種元素的作用來達到與藝術作品的共感,體悟暗藏在其中的深層意蘊。對于電影這種綜合性藝術而言,電影語言是吸引觀眾注意力不可或缺的要素,視聽魅力成為電影觀眾追求的重要體驗因素。而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下,電影語言將現代性與民族性相融合也是獲得觀者青睞的重要方式。電影《春江水暖》將傳統山水繪畫中散點透視以及移步換景等技法與電影的長鏡頭技法相融,極大地擴展了鏡頭的豐富性,同時輔以多樣化的運鏡來創造視聽上的“游觀”藝術體驗,為全新的民族化電影語言探索提供了有效的路徑。
影片在長鏡頭中鋪開生意盎然的自然山水畫布,以暢游的視覺體驗構建獨特的影像風格。從近幾年的電影創作中不難發現,新銳電影導演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對打造獨具一格影像視覺的野心。比如,畢贛以詩意的長鏡頭串聯起夢境與現實以完成對時間的重塑,萬瑪才旦以冷峻的鏡頭對藏地現實生活進行深度的叩問與挖掘,李睿珺則以細膩的鏡頭語言來捕捉農村的人情冷暖。顧曉剛導演的劇情長片處女作《春江水暖》將視角轉向浙江的小城,其長鏡頭運用旨在將鏡頭作為橋梁,讓觀者由影片本身進入意境美之中,也就是顧曉剛導演所言的“返回到東方審美傳統上去創作”。《春江水暖》用大量的長鏡頭展現了江南城市的山水風光。影片中有一段長達12分鐘的長鏡頭,即江一和顧喜比賽打賭誰先到達目的地。鏡頭自江一跳入江中開始便以平移的方式徐徐推進,讓觀者以直觀的視覺體驗,瀏覽著這幅江邊的“山水長卷畫”,頗有繪畫《富春山居圖》的古風味道。畫面中有江邊閑聊的人、游泳的孩童、嬉戲的小狗等,顯示出極強的包容性。隨著鏡頭的移動,觀眾還可以聽到女孩的歌聲、蟬鳴聲、樹葉的聲音,甚至還有江一游泳時急促的換氣聲。此時的聲畫關系并不是傳統視聽語言中的聲畫合一或同一,而是以聲音的不停變換來變換主體的視點。此時,聲音成為一個勾勒銀幕空間形象,并拓展其畫外延續的空間世界的重要因素②,讓觀眾在看似比較單調的長鏡頭中體味到虛實相生的美感與豐盈的世界。
《春江水暖》不僅展現了生意盎然的山水,更是將中國畫中移步換景和散點透視的獨特技法與長鏡頭相融合,以追求古典山水文人墨畫的意境之美,從而給觀者帶來獨特的審美體驗。如果場景是取景的空間維度和尺度,外場景就是場景的時間尺度③,《春江水暖》則巧用移步換景的技法打造了一個共時性的時間。影片在同一個鏡頭、同一個畫卷單元中,不斷地變換機位、景別,通過推拉、搖移、升降等多種運鏡方式,將多組景象與人物納入同一時空,同時以攝影機和被攝體的雙向運動形成奇妙的相對位置。不難發現,影片中時而呈現出隨江水涌動而流動的鏡頭,時而又躍升空中俯瞰山林以表達深遠意味。比如,顧喜和男友約會以及老三與相親對象見面,四人并置在同一時空中卻沒有碰面,從而形成了極其微妙的情感聯結。這個統一的時空關系里面呈現的是世間百態和人間煙火,而他們之間的組織形式,不是立體式的堆壘,而是平面的鋪陳,共時、平行的散點呈現④。這種巧妙的鏡頭語言不僅給觀眾提供全知視角,帶來游觀體驗,還給觀眾帶來一種合一卻不同一的情感體驗。
《春江水暖》以追尋傳統繪畫的創作路徑打造了一幅富陽的山水畫卷。這種超越常規的視聽語言使得鏡頭的主觀視點不斷地發生轉移,給觀眾帶來“游觀”般的審美體驗。但影片也通過電影語言來追求中國傳統繪畫的“氣韻生動”,在充滿意境的畫面語言中注入綿密的情思和深遠的詩意。
二、市井畫卷:市井與詩意相融中譜寫眾生相
藝術形象是藝術作品的核心,其不僅是藝術語言所要達成的目的,也是藝術意蘊被獲取的有效途徑。電影以視聽語言的魅力給觀者帶來沉浸式的快感,而更深刻的內容,諸如人生之哲思和生命之美感都有賴于人物在敘事中的展演。《春江水暖》為民族化的影像構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路徑,但是影片并沒有拘泥于景觀的空洞描繪,而是將瑣碎和繁雜的市井故事融入詩意的鏡頭,從而譜寫眾生相。
影片將現實作為底色,以多個豐富的形象來演繹時代變遷下的市井生活。電影如果作為“道”的生發,影像是具體的有,“道”是混沌的無⑤,電影就需要依靠人物形象和敘事來展開意義的探索。《春江水暖》整個影片是圍繞著顧家三代而展開的,將龐雜的群體形象以及鮮明的個體形象融入整個社會語境中,使得每個人物更為豐盈,從而具有真切的生命力。
顧曉剛導演在人物形象設計上突破人物身份的表層指示而直指其象征性,在以小見大的設置中來構建完整的敘事。顧家四兄弟的四種不同社會身份指涉著不同的文化生活:老大以飯店為營生,是市井生活的象征;老二以打魚為生,則隱喻著傳統的漁隱文化;老三以賭為生,其生活暗含著社會的另一側面;而老四的人物身份更具深意,他以拆遷工人的身份代表了現代化的建設,純真的人物特質使得他在劇中扮演著洞悉一切的旁觀者。顧家四兄弟多樣的身份設置使顧家得以成為龐雜社會的一個微觀縮影。而影片也巧妙地設置了多個對應或對立的意義主體,以此叩問人生,并展示出復雜的代際矛盾以及新舊事物的對立。比如,顧喜與男友以及老三和相親對象在江邊散步,兩組有著不同身份的人物并置在同一時空下卻難以相逢,其中便隱含著導演對于自由戀愛和相親的婚戀模式的思考。再如,老三要賬無果后站在陽臺上擺弄游戲機,鏡頭以卷軸式長鏡頭穿過一個又一個的窗口往下延伸,可以看到工人拆遷的場景與雜亂的陽臺,最后鏡頭落在正在拆遷的老四身上。老三、老四在影片中代表著不同的象征符號,而在拆遷的廢樓里讀著過去情詩的老四和擺弄著舊時游戲機且心系兒子的老三都被相似的鄉愁和濃郁的人情味牽連著。從形象層面來看,導演將人物心中洶涌的情感隱藏在靜謐的山水中。而從意義層面而言,影片則巧妙地設置多個對應或對立的意義主體,以形成循環往復的叩問和傳達悠長的情思。
影片將市井生活的萬象融入詩意中,化成綿綿的情思。“電影藝術是將景物轉化為情思,由目視入于神遇的創作和審美過程。”⑥顧曉剛導演以克制的敘事內容和具有象征意味的敘事空間展演著人生的真諦。影片中龐雜的社會群像描繪了家庭之矛盾、社會之變遷,但這些多重對立之形象最終融于悠長的意境中。《春江水暖》并非強調主體之間、新舊之間的矛盾沖突,而是為彼此的共存打造了一個和諧空間。
“大部分敘事會預先要求一個空間的環境,以此接納賦予敘事特征的時空轉變過程。”⑦在《春江水暖》中,家庭的瑣事與新舊交替的悲情都被隱沒在自然空間之中,諸如霧氣氤氳的江面、層巒疊嶂的深林。不難發現,該影片的空間設置有明顯的分立效果,即分為陸地空間、水上空間兩部分。陸地空間往往展演著瑣碎的生活,諸如相親、拆遷、治病、結婚等事件。而水上空間的敘事卻帶有一絲詩意,此空間成為劇中人物逃離喧鬧以及回歸平靜的“烏托邦”世界。水面在此代表著與陸地差異化的價值取向,其意及某種離散(而非需要逃避)的現實,卻孕育出了更為強韌的活性與意志⑧。當影片的敘事主體變成老二一家時,場景空間往往是在江中的漁船上,其中的情感極為平靜。比如,老二夫婦在面對母親的贍養以及兒子的婚姻時,均以極為克制的情緒來處理問題,傳達出兩人堅韌、平和的生活態度。影片中龐雜的人物和矛盾的生活在無限綿延的詩意中凸顯了溫情,電影在具象的形象中也就具有了綿長的意味。
《春江水暖》將生活融入無限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之中,不再拘泥于瑣碎的市井,而是以更具人文關懷的視角來豐盈和充實敘事,并通過充滿詩意的鏡頭展現世俗的紛擾,傳達出可貴的情感體驗,電影的時間和空間也由此得以延伸。
三、生命畫卷:萬物合一與時空超越
藝術意蘊潛藏在作品深處,以超越性賦予藝術作品以永恒生命力,其在藝術作品之中往往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哲思與神韻。就電影藝術而言,創作者更應該以虛靜之心去體悟并構建更遼遠的意蘊來獲取觀者的審美觀照。《春江水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了傳統美學中所崇尚的萬物合一的和諧之美以及時空無限之超越美。
影片在市井生活與詩意書寫之外構建了一種“萬物合一”的和諧之美。《春江水暖》整體呈現為一種和諧的美感,這種“和”更多的是體現為一種萬物生存之共時性。《春江水暖》以長鏡頭來呈現空間的變化,以傳統繪畫之技法給觀眾造成一種時間的共享性錯覺,從而使觀眾體會到影片中所營造的時間的連續性與空間的無限性。影片在場景的設計和構圖上以散點透視法包容了更多的景與人,多種景物和人物的并置有著遼闊的包容性,也就更容易體現出“萬物合一”的美感。而導演對于卷軸的執著,便可被理解為邀請觀者進入其設置的“時間機器”的努力⑨。
電影中,在冬季的一天,老四安撫兒子康康入睡。鏡頭一轉,仿佛進入夢境,呈現出康康和老四在被積雪染白的山林中打雪仗的情景。隨著鏡頭的移動,兩人的身影消融在層疊的山林中,鏡頭轉而落在霧蒙蒙的江面上(老二夫妻在打魚)。鏡頭再次落回山中,畫面的主體已經變成正在拜堂的顧喜和江一。類似的鏡頭在影片中多次出現。看似被隔絕的人物共享著同一時空,卻展演著截然不同的故事。通過空間的拓展來展演更多的場景,這種獨特的鏡頭處理方式體現了和諧的美感。審美觀照必須從對“象”的觀照進入到對“道”的觀照⑩,影片在敘事層面展演了市井俗事以及時代變遷中對過往之追憶、個體之觀照,但這些都以更全景觀的鏡頭被置入了更和諧的世界,即無限的自然,從而使得這幅風俗畫卷有了更具生命力的流動性。
萬物共享時空之和諧的背后深含著中國式審美獨有的“象外之象”的時空超越性。《春江水暖》里有一個十字坐標:橫向的是當下時代的社會圖景,縱向的連接過去與未來?。影片以春夏秋冬四季來賦予具體故事明確的時間概念,但導演在時空的處理上卻跳脫出一般的線性規定,以時空之無限呈現出超越之美。影片出現了諸多新舊對立的元素,諸如新人結婚拜橡樹、拜魚神、江中放生等民俗,以及佇立在江邊的高樓、拆遷等現代化痕跡,而導演卻將兩者巧妙連接在一個巨大的時空觀念下。比如,在顧家奶奶失蹤后,老大夫妻去放生,鏡頭再轉移時,一個披戴著蓑笠的釣魚者穿梭在山林中,之后奶奶便出現在漁船旁的一葉孤舟上。無論是失蹤歸來的奶奶還是來自古時的垂釣者,都帶有超現實的意味。導演有意安排這一情節,不僅在古今連接中給影片增添了神秘色彩,還給觀眾帶來一種時空穿越之感。
影片中時常出現頗具古意的鏡頭與富春江上的大橋、兩岸的建筑物相連。觀眾在這悠長的畫卷中,不僅可以看到古樸的過去時空,還可以瞭望現代的時空。看似有著割裂感的新舊元素便在獨具超越性的時空觀念中有了超然的韻味。在影片的結尾部分,潮濕卻閑散的夏季來臨,富春江的水面蕩起層層漣漪。在橫移的卷軸式長鏡頭中,顧家兄弟和母親在江邊乘涼,所有的人成為了畫卷中的微小個體。而在此刻,電影沿著時間回溯,宛如生活和生命的輪回,在不停地流淌中生生不息。此時,影片中的人也就有了更綿長的生命。
電影《春江水暖》并沒有拘泥于視聽語言的創新,而是在展現時代變遷下的社會圖景時,以超越性的時空觀念連接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使影片超脫現實意義而具有更加宏偉的宇宙觀。同時,恰是因為影片中時間的共時性和超越性,使得作品有了更深層的藝術意蘊。
四、結語
電影作品是對外界世界“象”的展演,需要借助電影語言和敘事來塑造藝術形象,但電影的藝術形象還需要突破有形的象而使影像具有人文關懷的底色,以有限的影像表達深沉、悠遠的哲思。電影《春江水暖》將中國繪畫內在的人文氣質和氣韻融入電影語言表達中,并在長畫卷中展開時代嬗變下的市井生活之萬象,同時融入眾生相融的自然宇宙之宏觀視野中,體現出東方哲學特有的韻味。電影之真義不在于華麗的影像,而在于其影像背后的氣韻與“道”。影片如果用悠遠的意境呈現無限的氣韻,于氣韻生動中展現生命之真義,那么即使是平凡的故事,亦可直抵人心。
注釋:
①[德]艾克曼 輯錄.歌德談話錄[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37.
②戴錦華.電影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③⑦[加]安德烈·哥德羅,[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電影敘事學[M].劉云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④周舟.《春江水暖》的東方美學試驗[N].中國電影報,2020-09-09(011).
⑤⑥劉思佳.論中國電影的“中國性”——“象”“氣”“道”的視角[J].當代電影,2020(08):166-171.
⑧⑨楊北辰.四季與永恒——《春江水暖》的時間-影像[J].當代電影,2020(06):14-16+2.
⑩葉郎.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顧曉剛,蘇七七.《春江水暖》:浸潤傳統美學的“時代人像風物志”——顧曉剛訪談[J].電影藝術,2020(05):98-103.
——以《在一起》中的《救護者》單元為例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