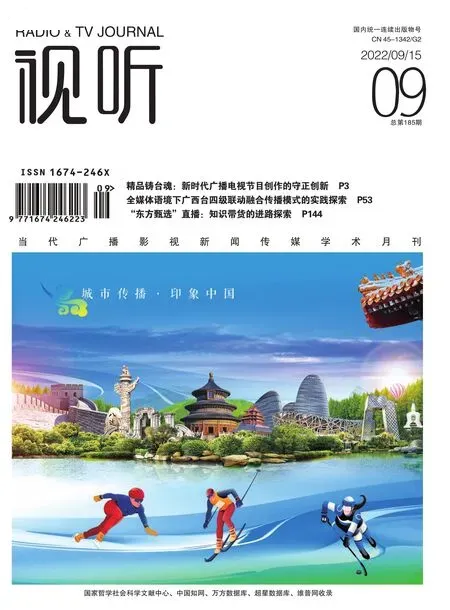接受·共情·縫合:主旋律電視劇《功勛》的國家敘事創新探析
王 莉
主旋律電視劇是指體現時代進步、傳承時代精神、代表最廣泛大眾根本利益的電視劇作品。從政治層面上看,主旋律電視劇是意識形態宣傳的大眾化載體,是家國情懷和民族精神的間接書寫①,具有鮮明的教育價值。2021年,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現實主義題材展播劇《功勛》創新了國家敘事的表達方式,以單元劇的形式攝錄了八位國之大匠背后“忠誠樸實”的時代故事,重現了新中國“站起來”這一歷史時期。該劇在敘事結構、審美品位、思想升華等層面都收獲了極高的評價,在意識認同、精神凝聚上提高了對受眾的感召力。
一、歷史敘事: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互嵌升華
接受美學注重對讀者的感受觸達和能動性的調動,即通過對受眾在閱讀、接受、反應和審美體驗的關注,將其一同作為創作主體,協作出具有受眾審美的作品②。以往的一部分主旋律電視劇困于政治題材的宣揚性,對歷史夸大講述,缺乏真實考究。《功勛》則高度重視受眾的接受心理,以“真實性”為出發點,將接受美學理論的“期待視野”“召喚結構”“隱含的讀者”等核心思想貫穿其中,契合當下信息泛濫時代影視劇創作者對受眾主體的視覺關注。
(一)歷史真實:在時代細節中嵌入宏大敘事
歷史真實是劇本創作的來源,是故事表達的根基。倘若離開真實,就會歪曲歷史,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無法體現真實與典型。《功勛》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為創作背景,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原則,實現了受眾的現實期待。
該劇從細節真實和時代真實兩個層面營造沉浸式視聽氛圍,滿足了受眾的意象期待。細節真實主要依靠場景的再現和人物的寫實兩種手法來實現。比如,制作團隊耗時數月復原延吉戰場,只為刻畫以李延年為首的連隊抗爭奪回346.6高地的偉績,還調用坦克、采用實地爆破等手段豐富視覺真實度。為了細致復原東方紅衛星,劇組精準研究器具上的每個管線和螺絲,逼真化刻現歷史場景,擊動受眾內心。《能文能武李延年》劇組不僅運用多種方言再現“聚全國之力反戰”的人民凝聚力,還通過小戰士陳衍宗嘴角的燎泡、連長臉上的暗瘡和疤痕凸顯妝造的寫實風,增強人物的可信度。在時代的真實上,該劇通過人物代入打動受眾。人物的表達狀態、處事方法、思考方式和精神風貌都盡力刻畫彼時的年代感。劇中,無論針對普通女性申紀蘭還是科學巨匠屠呦呦,都精準還原了彼時人物的做事風格和精神風貌,滿足了受眾對英雄的本真想象。
(二)藝術真實:在史詩質感中完成藝術升華
藝術真實抽象于歷史真實,歷史真實在審美理想的加持下升華為藝術真實。《功勛》在創作時藝術化擇取歷史,以接受美學視角切入,在敘事制作上滿足了受眾的期待視野,在效果表達上實現受眾審美的深層召喚,在視聽演繹的融合中完成藝術升華,促成了審美認同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
首先是對歷史真實進行藝術加工創造。在“高光”題材下,藝術化插入側面人物,從而牽動多線發展。在人物塑造上,注意營造血肉豐滿的個性特點。藝術性插入逃兵張安東一角,展現了李延年“能文能武”的偉光。在情節推動上,采取“雙線并行”策略,在工作線之外融入罕見的家庭線,豐富敘事角度,拓展受眾群體。
其次是鏡頭語言的運用極其考究,把藝術真實潑灑于虛實之間。該劇巧妙利用鏡頭藝術將移動端受眾轉化為潛在受眾。一方面是片頭的“視覺震撼”。八位功勛人物以演員帶妝的形象出場,人物的臉部在行進間出現“幻化”,由年輕人變成真人晚年的形象,通過服化道、攝錄美等諸般技術手段,盡可能藝術性地還原時代背景、接近英雄人物。另一方面是視覺的“質感呈現”。《能文能武李延年》用9臺6K攝像機拍攝,并采用大量運動鏡頭,營造沉浸式戰爭場面。
最后是鏡頭的“對比運用”和文本空白的合理采用,升華了劇作的主題思想。《無名英雄于敏》末尾,喧鬧的人群歡呼于戈壁徐徐上升的“太陽”。此時,鏡頭下轉,頭發毛躁、滿臉滄桑的于敏接過報紙,平靜的眼神里多了一絲驕傲和幸福。這組對比鏡頭表征著國家的強大,呈現了歷史敘事的藝術張力與精神感染力。
二、風格迭代:多元敘事變遷藝術審美
以往的一些主旋律電視劇多采用“正統”型敘事風格反映現實,“臉譜化”的嚴肅敘事模式忽視了受眾需求。在接受美學看來,作品如果出乎讀者閱讀預想,超出期待視野,讀者便會心情振奮,產生觀看興趣,激發更深度的觀看需求。《功勛》打破傳統,巧用喜劇風格和生活流的敘事方式讓主題劇屢次“出圈”,也完成了人物的鮮活塑造。
生活流敘事的場景還原,于民間敘事中增強貼近性。生活流敘事即生活化的敘事方式,用真實性的場景還原和人物塑造,增進受眾的熟悉感,消解宏大敘事的空洞性③。近年來,現實主義主旋律電視劇是國家主推的正能量電視劇,廣獲好評的背后是對生活流敘事的精準運用。《功勛》從生活流敘事視角出發,以民間敘事的方式帶給受眾親切感。比如,申紀蘭挨戶勸說婦女下地、紡織;大膽與男人競賽播種、耕地,以爭取男女平等的權益;帶頭參與掃盲宣傳,動員婦女上夜校……借助生活流敘事技巧,《功勛》傳遞了思想解放的主題價值,使得生活真實更自然地流動為藝術真實。
“正”劇“喜”出的審美變遷,破解嚴肅題材的說教性。以往的一些主旋律電視劇習慣有樣板式套路:對于故事情節、英雄人物、使命達成都規范在正式、悲壯基調之下,用苦情進行捆綁式演繹。《功勛》基于受眾觀影心理,契合市場流行元素,以“喜”為“正”形成全新的審美表征。以喜劇性情節設計展現劇中人物生活原貌,笑中有淚的喜劇元素疊加在宏大主題之下,在情緒渲染上極富表現力。在《申紀蘭的提案》中,以歪歪為首的男人起初反對女子“走出院”,隨著紡織組換回小米后,他以滑稽言語表露加入紡織組的決心,讓受眾在其前后態度的對比中笑中有淚。設置詼諧人物不僅強化了女性地位卑微的時代背景,也展現了在申紀蘭的號召下,男性從“嘲諷者”轉變為“追隨者”再到“倡導者”的角色變動,鋪墊了單元劇中所倡導的“性別同等”的思想主題。喜劇色調迎合受眾壓力陡然增大的社會現實,滿足了受眾觀看劇目時的娛樂心態,消解了宏大敘事的說教性。
三、英雄敘事:以平視視角實現本體回歸
人物是敘事的表達者,串聯著劇情的發展,載負著主題價值的表達,是電視劇的核心靈魂。《功勛》在人物塑造上突破單一的政治學視野,以平視視角切入,從家庭倫理、工作日常出發,輔以底層敘事風格展現英雄人物多樣面,從而回歸人物本體,進行英雄敘事。
(一)平視視角:以個體敘事書寫宏大主題
法國文學批評家熱拉爾·熱奈特在聚焦理論中指出,外部敘述者為劇作畫外音,內部敘述者為人物個體。在主觀鏡頭中,當人物感知和視覺感知一致時,個體視角則成為主體敘事角度,更新了固化的上帝視角和英雄視角。以個體倫理視角切入,《功勛》不僅凸顯了于敏式的科學家承擔國家建設、民族發展的重任,還側面展現了個體于日常中平凡而偉大的精神價值,在“完美與遺憾”中塑造了更為血肉豐滿的英雄形象。
家庭倫理下的缺陷設置,立體式淡化“臉譜英雄”。人類倫理以家庭為根基,承接血脈的倫理關系具有超強的穩固性④。《功勛》在人物塑造上突破單一政治學視野,通過倫理化的敘事方式,展現英雄人物多樣面貌。首先從妻子的女性視角入手,反襯男性角色對工作的癡狂。該劇真實建構了于敏妻子孫玉芹、張富清妻子孫玉蘭、孫家棟妻子魏素萍等偉大而又隱忍的女性形象。劇中,孫玉芹晚上突然宮縮臨盆,不敢貿然打擾丈夫做研究,只能委托鄰居照看女兒,獨自一人拿起搪瓷盆前往醫院。這側面折射出以于敏為代表的革命建設者忙于工作而疏于家庭的倫理矛盾,小視角展現易讓受眾為劇情觸動,進而成為事件的外部“參與者”,產生情感共鳴。其次從孩子的缺陷設置出發,將其感染力傳達給受眾。張富清因搶修水渠而延誤了家中發燒大女兒的病情,使其罹患腦膜炎,落下終身殘疾。憂心國家之難而失職于父親之責,表現了革命建設者家國難雙全的矛盾沖突。最后疏于關心父母的遺憾,使得功勛人物更具人間煙火氣。生性不媚俗的屠呦呦一心撲到工作上,擦肩未見父母,讓父親直言再也不想見她。這勾勒出了英模們鮮明的個性。該劇不刻意“神化”拔高英模,更新了以往英雄人物刻板化、符號化的形象。
(二)本體回歸:以年輕化表達實現共情激發
年輕化表達是本體回歸的表現形式,本體回歸是年輕化表達的前提。所謂年輕化表達,是從年輕受眾的審美偏好出發,摒棄傳統說教方式,增強敘事的故事性、可讀性。共情審美則是指敘事內容經過人物的典型性塑造更為貼近現實生活,經由情感和認知的共同作用⑤,在敘事上讓受眾由機械被動的觀看行為轉化為感同身受的主動體驗行為。《功勛》劇中雖沒有完美化藝術呈現人物,但在舒緩的故事中讓情節與人物更具合力,從細微之處感人,使人物與年輕受眾喜愛的偶像特性相貼合,與年輕受眾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進而讓受眾對劇情產生共情效應,讓信仰的力量潛移默化地淌進受眾內心。
該劇從人物性格、特性、情感等方面入手,在受眾多感官共同參與下,打造情感同頻的“想象共同體”,激發青年受眾的精神氣質,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多樣的性格塑造,增添了劇作的新鮮血液。在人物塑造上,該劇不以悲涼為底色,凸顯了艱難時光中稀有的積極、樂觀與浪漫。該劇塑造了屠呦呦醉心研究,不懂人情世故的“高冷范兒”,甚至還擷取了于敏與妻子空腹向往烤鴨時的現實浪漫……豐富的性格塑造了英雄人物的青年熱血,又添了幾分不羈和浪漫,劇作以此向年輕受眾的審美方式靠近,觸動情感外溢。其次是鮮活的情感流露,重塑了當代年輕人的愛情理念。袁隆平不懼流言,大膽追愛,倡導簡化式戀愛,質樸攜手的愛情凸顯了人物的鮮活性。“那時的愛情牽手就是一輩子”“那時的愛情才是真正的情感”等彈幕不斷劃過,年輕受眾在映射現實的親近感中,實現共情激發,在漸進反饋的心理期待中提升精神愉悅感,于娛樂狀態下產生認同與滿足感。
四、價值回歸:以意識縫合建構家國認同的集體記憶
主旋律電視劇不僅要在內容與形式上推陳出新,還要承擔起宣傳主流意識形態、實現家國認同的責任。《功勛》通過敘事錨點的細致描摹,讓受眾領略功勛人物的精神內核——“國之大者,為國為民”,“縫合”了受眾與主題價值的心理縫隙,增強了受眾認同,建構了家國認同的集體記憶。
法國電影人讓·烏達爾和美國電影人丹尼爾·達揚提出“縫合系統”理論。該理論以影視作品中意識形態抒發效果為研究宗旨,被奉為研究影視作品意識形態的工具。該理論認為電影借助組合手法,將不關聯畫面組成敘事表意的場景,“縫合”了受眾在接受心理、主題表達上的隔閡,走出了一條泛娛樂化環境下的突圍之路⑥。簡而言之,主旋律電視劇、“縫合系統”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可概述為:“縫合系統”鏈接正能量價值觀與主旋律電視劇主題,將主流意識形態依附在電視載體上,而意識形態通過載體在“縫合系統”理論引導下含蓄呈現。
為了完成“縫合”,《功勛》在創作中運用了敘事錨點策略。敘事錨點指錨定具體細節、情節⑦。超真實細節把控,使意識形態輸出更具靈活性。在《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戰斗日志記載著戰士的戰場表現,象征著成長與榮譽。因膽小沒上過戰場的文書是戰斗日志的記錄者。隨著戰爭激烈化,文書也從首次上戰場的畏懼退縮轉變為親身肉搏直至犧牲。其犧牲后無任何戰功描述。“向英雄致敬,珍惜生活,熱愛祖國”的彈幕表達了受眾的情感觸動。借由一本日志、一個戰士的心境轉變,劇作將抗美援朝戰士舍身為國的大無畏精神隱晦地表達出來,將主題思想巧妙地反饋給受眾,使得國家形象的感知與宣揚具有高度貼切的縫合力,拉近了兩者間的情感距離。
情節錨點易提高敘事的故事性,“縫合”受眾心理與主題表達間的情感認同。設置情節錨點,需引導受眾注意力,關照受眾觀劇時的情感轉變,契合其審美心理。《功勛》情節化設置了袁隆平研制雜交水稻時的艱難。袁隆平提出研發設想后遭到攻擊,受質疑被貼大字報,甚至遭人陷害拔出培植秧苗。此時,受眾情緒也隨情節一波三折被推至頂點。隨后,廢棄水井中撿拾的幾株遺留稻穗讓一度絕望的袁隆平奮起,讓受眾探知了其于困境中不斷銳意進取,只因心中滿懷“讓普通百姓吃飽飯”的家國理想。這段劇情蘊含了改革創新、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循序漸進的情節推進摒棄了敘事的空洞填補,暗合了現實競爭環境下的大眾情感心理,把握了受眾與人物之間的情緒鏈接。借助“縫合”系統,《功勛》成功隱藏或含蓄表達劇中的意識形態效果,借由英雄的抗爭與成長,襯托國家的強大與發展,喚醒了受眾內心深處的民族大義,建構了家國同構的集體記憶,從而讓受眾同時代共鳴。
五、結語
《功勛》找準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契合點,讓宏大主題扎根落地,輔以喜劇性人物設置,突破嚴肅生硬的敘事風格;從家庭倫理、日常生活感知宏大敘事下的個性化人物,實現本體回歸,借助人物的真實性與感染力激發集體共情;利用錨點精準“縫合”受眾與主題價值的心理縫隙,憑借年輕語態映照現實,打造構建認同的新方式,實現深層價值認同,奏響時代主旋律。總之,《功勛》在歷史敘事、生活敘事、人物敘事上滿足了受眾的觀影需求,消解了宏大敘事的僵化感、空洞感、單調感,使得人物更為立體,并于特定場景中建構集體認同,實現共情激發,觸達主流意識形態的更廣泛受眾,完成了國家敘事的創新表達。
注釋:
①孫家正.關于電視劇創作的三個問題[J].中國電視,1995(01):4-8.
②尹鴻濤,曹微微.接受美學視閾下的《墨子》英譯研究[J].上海翻譯,2021(02):56-60+95.
③徐小鳳.時代·共情:《山海情》平民視角中的多元敘事譜系[J].電影評介,2021(13):96-99.
④張永.家庭倫理與革命倫理: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的倫理歸屬抉擇[J].東南學術,2020(03):237-245.
⑤趙瑜,沈心怡.觀察類真人秀的共情效應及其觸發機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12):92-97.
⑥李孟婷.“縫合系統”理論在主旋律電視劇中的應用——以《隴原英雄傳》為例[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1(09):100-103.
⑦王志宏,伊文臣.借力影視藝術 講好奮斗故事——以熱播主旋律題材電視劇為例[J].當代電視,2021(04):41-4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