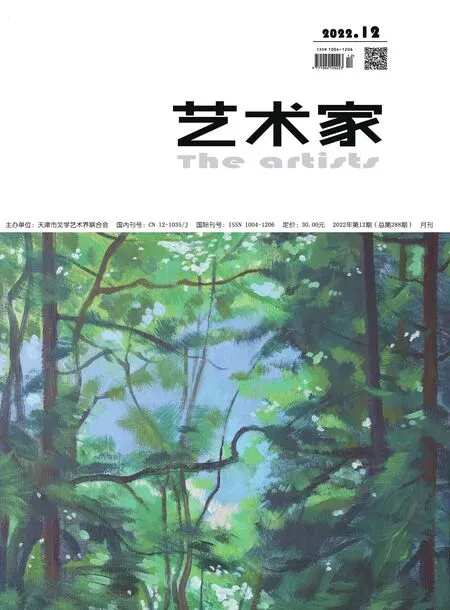普及與多元
——近代美術出版物的傳播研究
□徐 歡
中國近代美術期刊是各種藝術思想討論和發布的重要載體,也是藝術界發展的文本記錄者,它為我們了解近代美術發展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亦為中國美術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這些美術期刊的傳播內容涉及美術社團、教育、展覽、市場等大量美術資訊,不僅改變了中國美術相對封閉的創作與傳播方式,還為各種美術思想的形成、討論、發布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學術交流平臺,這種來自藝術與大眾雙向的互動對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進程有重要作用。近年來,有關美術期刊的傳播與研究一直是國內學者深入研究的重點領域,隨著對近代美術文獻管理的不斷完善,民國時期大部分重要的美術期刊得以系統而完整留存下來。
20 世紀的中國美術現代化轉型正亟須一種兼具時效性和規模性的傳播方式。在社會的巨大變革及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國藝術家們迅速聚集,集美術院校、美術團體與美術出版于一體,初步構建起中國美術現代化轉型的框架,此時的中國出版界也出現了數百種美術期刊。同時,留學生們帶回的西方先進的印刷技術與攝影技術也為中國近代美術期刊的發展助力。這個階段所呈現的藝術作品及藝術理念都極具時代性和批判性,亦能全面展示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進程。
一、近代美術期刊出版概況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感召下,各種美術團體及各類型的美術展覽蓬勃發展。據統計,1919 至1928年美術期刊出版量達39種,平均每年出版約4.3種,比第一階段高了10 倍。隨著20 世紀初期美術展覽會的興起,我國近代美術的展示與傳播又進入完全開放的視閾中,不僅拓寬了藝術的傳播路徑與互動平臺,還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及中西美術的融匯。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美育思想不斷普及,來自學校的精英教育需求與社會的大眾美育需求不斷增多,直接導致美術出版物的發行需求隨之增長。1918 年相繼創辦的上海中華專門美術學校出版的《中華美術報》、上海圖畫美術學校出版的《美術》,這兩本刊物是較早的美術專門期刊,雖刊行時間不長,但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文章,如鄧天吁《論中國之美術》、歐陽亮彥《西洋畫淺說》《中國畫與西洋畫之異同》等美術理論文章。從近代美術出版物的傳播內容來看,刊物在選材上不僅涵蓋大量傳統美術內容,還包括很多新興門類,如陶瓷、服飾、家具、圖案、建筑、廣告等,如1926 年出版的《文藝旬刊》、1930 年創刊的《藝術文獻》、1934 年出版的《美術生活》等刊物,都是集繪畫、雕塑、工藝、電影、設計等為一體的綜合類雜志。此外,亦有以藝術院校為主導的美術特刊,如《武昌美術專門學校校刊》《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周刊》《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刊》等。這些期刊以展示美術院校學生的習作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美術的大眾化進程。
除了將傳播內容作為刊行的重點之外,現代性的經營理念也開始全面介入期刊的出版、編輯和發行的各個環節,各類傳統出版社不斷向現代化的出版模式靠攏,并成功扮演了推動中國美術發展的“社會協同”角色,亦在美術資源與公眾之間架構了共享的橋梁,將美術從精英階層推廣到普羅大眾,體現了學術與商業的雙重價值,使美術期刊的出版傳播更廣泛。此外,20 世紀初的近代美術出版物在傳播過程中,遇到了發行難、成本高、大眾消費力弱等多重困境,其中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印刷技術,可以說,現代化的出版模式離不開現代化的印刷技術,而印刷技術的優劣更是決定了出版物的命運。為此,諸多畫報以其先進的印刷技術為亮點來宣傳,為了擴大其在出版市場上的份額,紛紛從印刷技術方面入手。一些雜志也確實因其精美的裝幀及印刷效果在眾多美術刊物中脫穎而出,流傳甚廣。
二、近代美術出版物的傳播策略
近代期刊創辦之初面臨來自社會、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困境,為此,眾多出版機構努力汲取西方報業的相關經驗,并根據不同時期的特殊環境,及時調整經營策略,明確自身的行業定位與受眾群體,力求找到一種適應自身并趨于完善的經營策略,我們亦可從諸多近代美術出版物的傳播中找到一些可借鑒的經驗。
(一)兼容并包的傳播理念
20 世紀初,動蕩不安的政局使近代中國不得不將目光投向西方社會,積極摸索中西文化的契合點。近代眾多美術出版物中的內容呈現出中西繪畫、工藝與設計、攝影與電影等多元并存的面貌。美術期刊的傳播內容不完全局限在繪畫上,而是不斷拓寬其外延。如上海圖畫美術學校校刊《美術》一刊被蔡元培先生贊譽“宏約深美”,這本刊物只出了8 期,設置了“美術界消息”“世界美術”欄目,報道海外及國內美術界消息,可見西方美術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之大。1928年創刊的《亞波羅》曾刊登諸多關于西方藝術的專文,對西方美術的引介有林文諍的《從亞波羅的神話談到藝術的意義》、金公復的《近代意大利美學》,在工藝美術方面有雷圭元的《近今法蘭西圖案運動》。1936 年12 月《藝風》雜志出版的“現代藝術專號”中刊發了常書鴻、孫福熙、呂斯百等人對國外現代繪畫藝術的全面介紹,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曾被美術界譽為“劃時代的論述”。

圖1 1936年《美術生活》第22期 比國現代美術展覽會出品
此外,諸多美術出版物還及時傳播西方最新的藝術動態,如《亞波羅》在第13 期中出現的“藝術藝壇”專欄,詳細報道了當時德、法、美、日等國家的設計展覽會情況,如“布魯塞爾的現代書籍裝訂美術展覽會”。更有甚者,為了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傳播國外藝術動態,還特地聘請駐外人員。如1926 年創刊的《藝術界》,為及時了解國際上的藝術界情形,特請國外撰術員多人,在美國紐約有良友公司經理伍聯德、在法國巴黎有季志仁、在意大利羅馬有陳之藩、在日本東京有高劍父等,力求及時將西方藝術界的動態傳播給廣大藝術讀者。此后,越來越多的美術出版物紛紛將視野投向國際,1936年《美術生活》刊登了諸多西方藝術理念及展覽,如第22 期的“比國現代美術展覽會出品”(如圖1)、第25 期的“現代木器設計”“德國雕刻家兼銀細工師佛利茲·梯爾及其作品”、第31 期的“柏林奧林匹克藝展一角”,多次對國外藝術展覽進行報道,將西方藝術輸入中國。
當然,中國近代美術期刊在積極輸入西方藝術的同時,也致力于對中國藝術進行“文化輸出”。1934 年創刊的《國畫月刊》明確其出版的兩大使命及職責,即“發揮固有藝術之精神,提高國際藝術地位”。眾多中國近代美術期刊從創刊之初就帶著宣揚中國藝術的使命,其主要呈現形式是對當時中國的一些藝術展覽進行報道。《亞波羅》第8 期上刊登了大量由林風眠發起的藝術運動作品,并認為此次展覽是“把東西方藝術推向更廣的國際間”。此外,1934 年《美術生活》在第2 期中刊登了“中國參加芝加哥博覽會政府專館模型”、第7 期的“歐洲中國美術展覽紀年特輯”、第23 期“倫敦展覽之中國古代美術珍品”等都是刊物主動將中國美術輸出的一種嘗試。這些美術期刊通過對中國藝術在國外展覽的報道,使中國大眾意識到必須把中國藝術傳播到國際。為此,當時諸多美術期刊也在海外發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藝術向外傳播的速度。如1927 年創刊的《湖社月刊》以其精美的印刷質量和高質量的文章,遠銷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古巴等國家和地區。縱觀這些近代美術出版物,它們的出版發行都為中西藝術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雅俗共賞的傳播立場
擴大受眾面,注重通俗性一直是近代諸多美術期刊秉持的辦報方針。1917 年蔡元培發表《以美育代宗教》一文,他將美育視為自由進步的象征和人性的自我解放,指出提高大眾審美的任務迫在眉睫。隨著西方新式生活理念的不斷深入,許多市民開始關注居家用品、家具陳設、房屋建造等,眾多進口洋貨也開始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形成了以中西交融為特色的生活及消費理念。這種現象也體現在美術期刊的傳播內容中,如1934 年創辦的《美術生活》對西式家居陳設進行過諸多介紹,其第1期“經濟住宅之一”、第3 期“上海最新式之公共住宅”、第6 期“新式西洋玩具”、第8 期“會客室器具的設計”、第14 期“現代照明之裝飾藝術”“室內小陳設”等將西方生活美學帶入中國人視野。其倡導的并不是盲目地追求西方的生活理念,而是逐步引導中國大眾接受并享受這種現代化生活,從審美意識及生活理念上產生新的轉變,可以說是高雅生活方式的一種傳播。
此外,1925 年創刊的《世界畫報》為了更加適應都市市民的閱讀習慣及興趣,在期刊中大量刊登漫畫作品,擴大了漫畫的占比,利用具有“化大眾”的漫畫藝術形式消除各個階層空間、地域的限制,使讀者能近距離觀察接觸其他階層的生活形態。諸多美術出版物也紛紛開始關注中下層市民的都市體驗,以漫畫、攝影等多種圖文結合的方式建構出一個與中上層市民生活不同樣貌的世俗城市空間,真實鮮活地投射出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和內心狀況。由此,高雅的藝術表現形式與接地氣的“世俗”藝術內容常同時出現在一本刊物中,但并不會顯得突兀,也擴大了出版物的受眾群。刊物中呈現出對傳統與現代、高雅與世俗藝術表現形式兼容并包的局面,這種雅俗共賞的傳播策略也為近代美術出版物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對當下美術期刊傳播的啟示
通過對近代美術期刊出版情況的梳理不難發現,近現代美術期刊能夠快速發展,都得益于其“廣而善”的材料甄選及開放的學術精神。對于藝術界的各種論爭,出版物中給予了不同觀點的充分呈現與碰撞。如1933 年孫福熙主持的《藝風》雜志,將有關對超現實主義的激烈討論刊登在同一期中,讓讀者能夠在一本刊物中汲取來自不同藝術家的論爭觀點。《美展》雜志也曾同期發表徐悲鴻和徐志摩關于現代主義藝術的辯論文章。編輯們對出版物內容的取舍并不會因個人偏好而有所偏倚,正是因為這些高質量的藝術文章的刊發,使近代美術刊物成為一個時代的藝術標桿。
其次,編輯宗旨、期刊定位是一個雜志的立身之本。近現代美術期刊個性鮮明,獲得了屬于自身相對固定的讀者群。如在20 世紀動蕩環境下,存在時間相對較長的《世界畫報》《美術》《藝林》等期刊,明確的編輯思路與重心才是它們的長存之本。其中《藝林》雜志在經歷了1928 年1 月的《藝林旬刊》,再到1942 年6 月停刊的《藝林月刊》,前后共出版190 期,時間跨度達14 年之多,實屬不易。此外,1912 年高奇峰創辦的《真相畫報》以圖畫為利器針砭時弊;1927 年創刊的《湖社月刊》注重對社團文化的宣揚,成為美術社團期刊的典范。此外,專題策劃也是近代美術期刊的特色,出版社有意識地結合特定的讀者群體來設置“特刊、專刊”等形式,制造輿論話題,吸引讀者關注。如1929 年《湖社月刊》曾在第14 冊、第27 冊相繼推出“雪景專號”和“畫馬專號”;1934 年《國畫月刊》推出“中西山水畫思想專刊”。獨具特色的專刊、專號的出版,不僅豐富了期刊的編輯內容,還擴大了受眾群體,挖掘了潛在的讀者,也為當代美術期刊的編輯及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最后,高水平的編輯隊伍對一本雜志的走向也有重要作用。近代多種美術刊物如《湖社月刊》《藝林》《故宮》的編者、作者多以專業美術社團或美術院校做依托,這樣嚴謹的一批學者和藝術家直接介入美術期刊的出版運作中,對藝術界的熱點問題進行集中深入探討,才有了近現代精彩紛呈的美術出版的局面,其令人嘆服的出版智慧和學術追求,對當代的美術期刊出版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