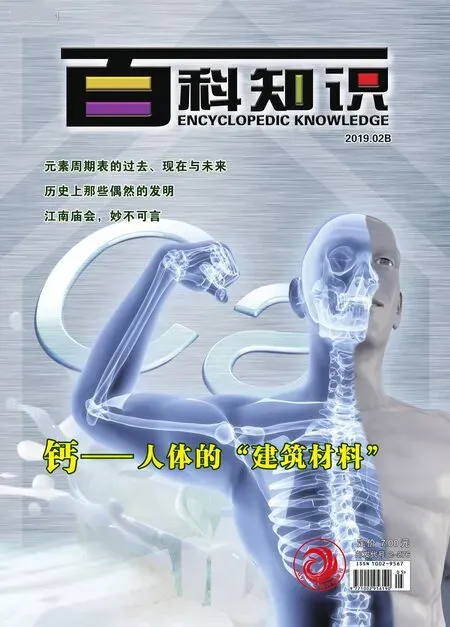景德鎮:傳承千年的工業遺產之城
韓晗
所謂工業遺產,是指那些具有歷史、技術、社會、建筑或科學價值的工業文化遺跡,無論是鐵路、橋梁、船塢、礦山,還是廠房、建筑、機械、設備,無不見證和記錄了工業技術的發展歷程以及社會的變革進步,從而成為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產、記憶遺產和檔案遺產。
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發展到今天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出口國以及唯一的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艱難起步與上下求索之路尤其值得我們發掘、傳播和銘記。為此,本刊將陸續介紹一些中國乃至世界上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工業遺產。
因為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都在歐美地區爆發,許多歐美城市積累了大量的工業遺址,因此“工業遺產”成為歐美國家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不過,被世界學術界公認的世界工業城市的鼻祖,卻在中國。
這座城市雖然沒有參與兩次工業革命,但在前工業時代卻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它早在1800多年前的東漢時期,就筑爐生產。這座城市里生產的商品是我們最熟悉的陶瓷,這座城市就是被稱為“世界瓷都”的景德鎮。
及至唐末及宋代,景德鎮的瓷器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及小亞細亞諸國。到了元、明、清三朝,更是一發不可收拾,瓷器與絲綢一道成為了世界各國認識中國的兩大名片,是海上絲綢之路上最搶手的中國商品。
很多人知道景德鎮是“世界瓷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景德鎮的制瓷業歷史相當悠久,源于東漢時期。
人類陶瓷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東漢時景德鎮筑爐所燒之物,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瓷,而是陶。通俗來講,陶是沒有上釉的瓷。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在冶陶的過程中無意間發現了上釉的技術,但是距離該技術的普及還有一段距離。
在人類文明的早期,許多技術、工藝是在不同地區同時發展的,取得突破的時間也相去不遠。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制陶技術走向成熟時,當時的古埃及、古希臘也出現了較為成熟的制陶技術。當時,人類面臨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幾乎所有的陶器都存在滲水的問題。在當時生產力并不發達的條件下,陶罐幾乎是家家戶戶的標配,事關每個人的用水大事。因此,如何解決陶罐滲水,成了當時全世界各民族“卡脖子”的技術難題。
漢代,中國正處于一個上釉技術的發展期,以青釉、黑釉為代表的陶器上釉技術領先于全世界。不過,由于上釉技術難度大、成本高,上釉的瓷器大多是王公貴族家的擺設或陪葬品,“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概率微乎其微。
可以這樣說,盡管當時上釉技術提升了,但是仍然沒有解決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雖然已經有人掌握了上釉技術,但卻未服務于提升生產力,沒有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過,東漢時期,在江南偏僻的一隅,一種給民用陶瓷上釉的技術悄然普及開來。史書是這樣記載的:“質甚粗,體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邇俗粗用。”
眾所周知,景德鎮因宋真宗的年號“景德”而得名。在漢代,此地籍籍無名,當時的景德鎮到底叫什么名字,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出定論。不過,這里出土的高嶺土,在當時聞名遐邇,被認為是最優質的冶陶材料。這里使用一種“淡而糙”的釉,因為不好看,難登大雅之堂,所以只能供普通人日常生活使用。在當時看來,景德鎮生產的陶器不過是一些生活用品,毫無藝術價值。
到了兩晉時期,這座江南小鎮被命名為新平鎮。“新平”的來歷現在已經不可考。此時,當地的陶器仍然被視作粗劣的物件,門閥貴族自然是看不上的,因此只能默默地服務當地及周邊的民眾。史書對于這一時期的景德鎮幾乎沒有任何記載,但是當地出土的大量六朝時期的碎陶片以及舊窯址證明了,在這座鄱陽湖畔的小鎮里,許多工匠們為了自己的一家老小,甘愿守著一爐窯火,盡心盡力服務于父老鄉親。
唐代,景德鎮終于有了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浮梁。今天,景德鎮還有一個下轄縣叫浮梁。浮梁最出名的一瞬間藏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當時的浮梁并不以瓷器聞名,而是以茶聞名。
唐代的景德鎮確實沒有今天發達,史學家認為,景德鎮的制瓷業興于五代時期。五代之前的景德鎮,只有一些燒碗制缸的民窯。唐代的中國處于一個瓷器制造的高峰期,如以浙江越窯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窯為代表的白瓷,在當時就聲名在外,被稱為“南青北白”,洛陽鞏縣的唐三彩更是大名鼎鼎。這些名窯燒制的瓷器光彩奪目,景德鎮生產的卻是“只供邇俗粗用”的簡陋瓷器,似乎沒有資格載入史書,更沒有資格被供奉在廟堂之上。
不過,史書里有一小段文字,像是對景德鎮瓷器的褒獎。“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铏之德。器慚瑚璉,貢異砮丹。既尚質而為先,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這是一篇在中國歷史上頗有影響的奏折—《代人進瓷器狀》,署名是饒州刺史元崔。饒州下面有一個浮梁縣,這個奏折就是告訴皇帝,浮梁縣的瓷器其實并不差,完全可以作為貢品,以供皇家使用。這篇奏折之后,浮梁在廟堂上聲名鵲起,成為晚唐又一個制瓷重鎮。這篇奏折的代筆者是唐代最著名的詩人之一—柳宗元。
2013年,景德鎮蘭田窯窯址出土了一只74厘米長的瓷腰鼓,這個發現震驚了中國考古學界。
這只極具異域風情的瓷腰鼓,向世人證實了一個長期以來無法確定的史實:早在晚唐,景德鎮就開始為西域的阿拉伯、波斯、印度諸國生產瓷器。在遙遠的異國他鄉,除了“南青北白”,竟然還有出產于景德鎮的瓷器。研究者還發現,景德鎮的瓷器一度遠銷日本,在日本佛日庵的“公物目錄”中有好幾件“饒州瓷”。這似乎有點顛覆想象,真是“墻里開花墻外香”,登不了廟堂之高,那就隨江湖之遠,走向世界各地。
到了宋代,景德鎮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瓷業重鎮之一。不過,在宋代,景德鎮只是“官窯”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未能與“五大名窯”—汝窯、官窯、哥窯、鈞窯、定窯齊名。雖然離今日“瓷都”的地位尚有距離,但當時的景德鎮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制瓷經驗。
從北宋到南宋,中國的經濟中心開始南移,制瓷中心也從黃河流域轉向了長江流域。大量制瓷技師因戰亂被迫背井離鄉,遷徙到南方,“五大名窯”格局徹底發生了變化,景德鎮逐漸成為“五大名窯”之外的“名窯”,質優價廉,名聲遠播。
宋元時期,景德鎮最大的成就是青花瓷的繁榮,這是南宋及元代中國與世界交往的見證。青花瓷是一種釉下彩瓷器類型,這類瓷器在唐代就已經問世。直至南宋,工匠們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獲得了一些來自西域的原材料,用以上色,令釉下彩瓷器呈現出獨特的藝術風格。
現在人們所說的青花瓷,也叫元青花,所用顏料是一種來自于今天伊拉克的藍色顏料—蘇麻離青。由于當時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客商在景德鎮定制符合他們審美風格的瓷器,蘇麻離青在元明兩朝很快被景德鎮的窯工們廣泛應用。鄭和下西洋時,還專門從印度帶來了大量蘇麻離青顏料。最早以漢字“青花”標注的瓷器,就收藏在伊朗的阿德比爾清真寺。
直到明代,朝廷才真正開始重視景德鎮的瓷器,在當地設“御窯廠”。有了皇家的扶持,景德鎮迅速占據了當時制瓷行業的大半江山。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清廷在景德鎮設置的“御窯廠”逐漸衰敗。與此同時,因為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與新技術的傳播,景德鎮的民間制瓷企業日漸崛起,物阜民豐,一度達到“日曬黃金夜不收”的地步,大量瓷行、瓷莊組成的商幫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1902年,江西巡撫柯逢時奏報請求開設“景德鎮瓷器公司”,一開始定義為“官督商辦”;到了1907年,又改為“商辦”,更名為“江西瓷業公司”,任命康達為總經理。從民窯、官窯、名窯到御窯,再到瓷業公司,曲曲折折,景德鎮走了1000多年。
江西瓷業公司成立后,聘請日本東京工業大學高材生張浩籌辦“中國瓷業學堂”,為我國陶瓷生產培養專業技術人才,改變了“師徒傳幫帶”的數千年傳統格局。辛亥革命之后,在“實業救國”的號召下,一批民族陶瓷企業在景德鎮嶄露頭角,以“珠山八友”為代表的陶瓷工藝美術大師,將景德鎮制瓷工業的技藝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1934年,江西省瓷業管理局成立,景德鎮制瓷行業步入了現代化、規范化與制度化的歷史新階段。
抗日戰爭時期,景德鎮成為了抗戰前線。1939年底至1942年7月,日軍飛機先后對景德鎮進行了16次轟炸,景德鎮人民不屈不撓,一邊堅持抗戰,一邊堅持生產。陶瓷技師們集體創作了許多“抗日主題瓷”,如在茶壺、水杯等一些日常用品上寫下“抗戰到底”“抗戰必勝”“誓雪國恥”“國家至上”和“民族至上”等口號,激勵全民族團結抗戰,成為“文化抗戰”中功彪史冊的一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景德鎮形成了“國營十大廠”的巍巍規模,不但是國內民用陶瓷生產、陶瓷雕塑藝術的中心,而且成為重要的特種陶瓷生產基地。例如,用于外科手術的氧化鋁耐磨陶瓷關節、用于發動機零部件的航空航天專用耐高溫陶瓷、用于城市水利系統的耐腐蝕陶瓷管道以及用于人民大會堂壁燈的高透光陶瓷等,這些服務于國計民生乃至國防工業的特種陶瓷,逐漸成為景德鎮瓷業的核心競爭產品。
如今的景德鎮,除了發達的陶瓷制造業,還擁有馳名四海的陶瓷工業遺產園區。許多陶瓷廠、車間因技術升級遺留下了大量工業建筑。如“國營十大廠”之一的宇宙瓷廠,目前已經改造成“陶溪川文創園區”,成為我國獨樹一幟的陶瓷工業文化園區,作為景德鎮的新名片,吸引著四面八方的游客。
從東漢那一窯爐火到今天的“世界瓷都”,景德鎮厚積薄發、生生不息,成為我國最重要的工業遺產城市之一。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教授曾言:“景德鎮是世界上最早的工業城市。”毫無疑問,作為蜚聲世界的工業遺產之城,景德鎮,既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
(本文作者系武漢大學景園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工業遺產”分支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