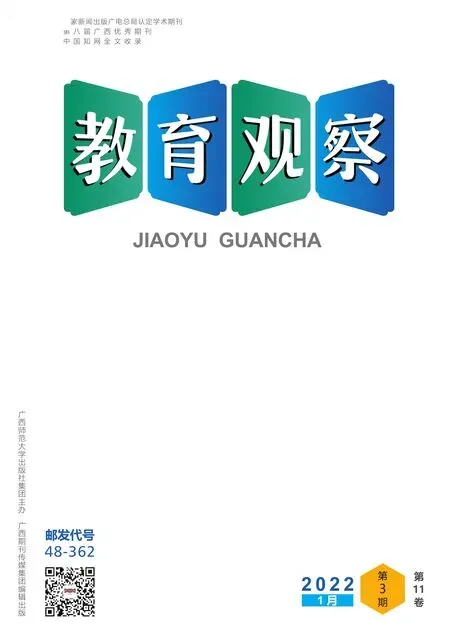幼兒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分析
——陜北貧困地區一名幼兒教師的個案研究
謝芬蓮,李軍靠
(延安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陜西延安,716000)
一、引言
在學前教育領域,幼兒教師的專業成長一直是學界重點關注的問題,研究者就其內涵、發展階段和影響因素及策略等方面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然而,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程度)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十分突出[1],幼兒教師專業成長也因其所在的園區環境、教師個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經歷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同時,已有相關研究多使用量化方法,這雖有利于對幼兒教師這一群體專業成長進行整體性探索,但卻有將人物化、簡約化的嫌疑[2],不利于探索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深層次原因。此外,還有部分相關研究采用文獻法,在某種程度上雖有利于對幼兒教師專業成長進行“學理性”探討,但研究之間難免重復。因此,本研究采用質性個案研究法,細致分析一名幼兒教師的專業成長之路。這名教師來自一所縣城幼兒園,該縣經濟水平相對落后。那么,這名教師的專業成長之路是否會有別于其他教師?目前對幼兒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事件、關鍵時期、關鍵人物、職業精神和職業理想[3-5]等因素的討論是否適用于本研究的個案?這名教師是如何突破環境和自身限制的?她對個人的專業成長之路有著怎樣的體驗?雖然本研究中的個案教師并不能代表其他幼兒教師,但對于這名教師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對幼兒教師專業成長的認識,上述問題的答案也可以為后續研究提供比較立體和豐富的圖像。
二、研究方法
(一)個案基本情況
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樣法,其特點是著重樣本的典型性[6],旨在為研究問題提供豐富的信息,引起相關群體的共鳴。研究者在2017年和2018年對陜西省某貧困縣區的一所幼兒園參與過兩次教育幫扶活動,對該幼兒園教師的了解較為細致。后來,研究者也一直和該幼兒園的某名教師保持著密切聯系。本研究中的個案為張梅(化名)老師。
張梅老師,1992年生,2012年就讀于陜西省內某高校,大專學歷,2015年參加工作,就職于陜西省內X幼兒園。2017年從該幼兒園離開到現在幼兒園工作,2019年被評為“縣級骨干教師”。張梅老師在任教中雖然遇到了很多困難和挑戰,但她懷著對學前教育事業的強烈情懷和努力,從新手成長為專業骨干。張梅老師的這些表現也與其他文獻中所提及的教師的專業成長經歷非常相似。
(二)資料搜集過程
本研究主要運用深度訪談法搜集資料。訪談共四次。第一次是2017年,在張梅老師所在的幼兒園,通過非正式訪談了解了她本人和其所在幼兒園的基本情況,之后的三次都是通過微信遠程電話訪談。第二次訪談在2020年4月進行,整個訪談過程大約60分鐘,訪談主要圍繞影響張梅老師專業成長的因素展開。分析資料時研究者發現一些信息需要進一步修正和補充,于是將文稿發給張梅老師讓其進行檢核和完善。第三次和第四次訪談分別是在2020年5月和7月,訪談時間30—60分鐘,是對一些信息的進一步追問,此外,張梅老師還補充了一些其他信息。最后,在論文成稿后,研究者將文稿發給張梅老師核對,以使資料更準確。
三、影響幼兒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
已有研究對幼兒教師專業成長因素的分析集中于教師個人因素和外部環境因素。根據田景正、吳荔紅、林菁等人的研究[5,7-8],可知影響幼兒教師專業成長的內部因素主要有教師的教育情懷和教師的專業成長動機,外部因素主要有關鍵人物的支持和關鍵事件的影響。通過對張梅老師的深度訪談,研究者認為影響張梅老師專業成長的因素同樣來自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
(一)內部因素
1.強烈的教育情懷
教育情懷是一個中國本土概念,表現為情感上的主動認同和回應[9],是教師執念追求教育的生命意義和堅守育人職業的內在動力與精神支撐[10]。張梅老師在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就提及了教育情懷的作用。如張梅老師談道:“我外出學習回來后,就覺得要把我學到的東西用到幼兒園,就是盡量讓自己的孩子和那邊的孩子差距小一點。”在張梅老師被評為骨干教師后,她說:“我覺得那只是一個稱號,我就想改變這個教學環境,我是發自內心地想改變這種情況,想給孩子更好的東西。”正是這種對學前教育事業強烈的教育情懷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促使張梅老師從一個新手教師成長為專業骨干。同樣,在已有關于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中,研究者也都認可教師的教育情懷和教育理想對專業成長的作用,認為其作為直接的動力原因,激發了教師的職業信念,從而促進了教師的專業成長。
2.專業成長動機:“一切為了孩子”
專業成長動機是影響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在核心因素,也是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內部動力。[11]在對張梅老師的訪談中,她提到的第二個影響自己專業成長的因素便是專業成長動機“一切為了孩子”。她說:“就是為了讓孩子好,就(因為)這點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教材改革)做下去。我很注重實際,就是為了孩子發展。我覺得不能違背我的職業操守吧。總之,就是要全身心投入工作,感覺你的時間啊、人啊什么的都要在工作上,就是為了孩子嘛。”因此,在張梅老師發現自己“以前(學)的東西不夠用(時),就經常加班”。正是“一切為了孩子”的專業成長動機促使她足夠努力,不斷推進自己的專業發展。
(二)外部因素
1.關鍵人物:幼兒園領導的支持
已有研究在探究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時,提及了關鍵人物的作用,認為其作為對教師影響較大的某個人,通常起著正面的、積極的作用。[4]根據人類發展生態學理論,對幼兒教師專業成長產生直接影響的關鍵人物主要有同事和家人。張梅老師在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同樣也提到了關鍵人物的影響——主要是幼兒園領導的支持。“我很感謝我們領導,我們領導覺得我可以,就給我提供一些平臺。領導就看你是否肯努力、是否愿意付出、能否帶出成績這些……我們領導覺得我很努力,就給我了許多外出學習的機會,我出去學了好多東西。”由此可看出,幼兒園領導對張梅老師的支持,如為其搭建學習平臺、給予外出學習機會、扮演張梅老師的“伯樂”、發掘張梅老師的潛力等,都有助于她的專業成長。
2.關鍵事件的影響
英國學者羅博·沃克在研究專業發展的過程中,提出了“關鍵事件”的概念。沃克認為職業生活中總存在著一些重要事件,從業者往往要圍繞這些事件做出關鍵性決策,這些事件就是關鍵事件。[12]對于教師而言,關鍵事件是指能夠強化當事者原有教育認知結構或引發當事者教育認知沖突的事件。[13]有學者在研究幼兒教師的關鍵事件時,將其分為成功型事件、挫折型事件、啟發型事件和感人型事件四種類型。[14]本研究中的個案張梅老師在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就提及了三種事件類型:挫折型事件、感人型事件和啟發型事件。
一是挫折型事件,即同事的不理解和缺少專家支持的雙重挫折。挫折型事件會對教師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也能促使教師對教學進行反思,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訪談中,張梅老師提到:“我們在改編教材時,因為有的老師有惰性,不愿改變,就覺得還是用原來的教材(好),改編教材很辛苦,大家還不理解,就不想費勁。我當時就又氣又難過……還有就是當時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專家來支持。”但如前所述,這些挫折型事件促使張梅老師對教學進行了深刻反思,她說:“其實,在一輪一輪修正教材時,我們也在不停地反思,就是怎么讓這個教學活動實施起來更有成效。比如,我們有一個關于中秋節的活動,以前都是節過完了才組織,但這次我們就想能不能在節前組織,然后再過節,讓孩子們先有個知識上的鋪墊,然后再體驗。其實,反思教學活動也是我們自己的一種進步和成長吧。”
二是感人型事件,即“當時很欣慰”。相比挫折型事件,感人型事件更能對教師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能引起共鳴,使教師產生職業幸福感。正如前文所言,張梅老師最初在進行教材改編時遇到了雙重挫折,后來張梅老師說:“每個年級(進行教材改編時)都是我親自和老師討論,大家討論很激烈,都是(出于)為了孩子好這種愿望。(老師們的)改變好大,當時很欣慰。更確切地說,其實這就是一種感動吧。我真的覺得就是大家都是為了孩子嘛,都是為了讓孩子(獲得)更好發展,所以我也就更加堅定了要做好這件事。”正是欣慰和感動的職業幸福感,引發了張梅老師“堅定做好這件事”的愿望,從而促進了張梅老師的專業成長。正如熊少嚴所言,教師職業幸福感與教師專業成長相輔相成,專業成長是獲得職業幸福感的重要內在動力[15],而職業幸福感則又進一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三是啟發型事件,即“覺得人家的教材特別好”。啟發型事件是對教師教育觀念、教育行為等產生啟示的事件,其引導教師做出反思并對當前教育活動做出改變。張梅老師就是在某次外出學習中獲得了啟發進而改變了原來的教育活動方式。“我學完回來后,就覺得人家的教材特別好。我也和他們的一個老教師交流了,然后我就把他們的教材拿回來,放到我們幼兒園,重新編我們的教材。編的時候,根據他們教材中的本土文化,還有我們的幼兒的接受度以及目前我們各方面的條件,把他們教材上有用的留下來,沒用的刪掉。”張梅老師正是受到外出學習這件事的啟發,才開始改編教材。而改編教材這件事也促進了張梅老師的專業成長。
總之,對張梅老師的專業成長產生影響的關鍵事件主要有挫折型事件、感人型事件和啟發型事件。蘇紅指出,關鍵事件有助于豐富教師的實踐知識,提高教師的專業判斷能力,同時也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干預提供了有效的切入點。[16]如其所言,這些關鍵事件的確是張梅老師專業成長的有效抓手,同時又豐富了張梅老師的教育實踐知識,最終促進了張梅老師的專業成長。
四、結語
綜上所述,影響幼兒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有強烈的教育情懷、專業成長的動機、關鍵人物的支持和關鍵事件的影響。相較其他地區幼兒教師的專業成長,貧困地區幼兒教師的專業成長之路似乎更為艱辛,這些教師既要處理好與同事教學理念的差距和分歧,如張梅老師提到的“同事的不理解”,還要面對教學資源的緊張、短缺問題,如張梅老師提到的“缺少專家支持”。但盡管如此,貧困地區的教師依然懷著對學前教育事業的強烈的教育情懷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憑借著自身足夠的努力與堅持不斷推進自己的專業成長。
此外,在訪談中,張梅老師還談到了貧困地區幼兒教師面臨的工資待遇低和工作壓力大的問題,其原話是:“老師的努力和收獲與工資不成正比,我自己內心很煎熬。老師基本上每天下午都要加班,我們一般五點下班,但回家就七八點了,學校里邊也不管,沒有條件。老師真的很辛苦,我真的做不到那種,只看到工作看不到老師的那種。我不忍心。”幼兒教師工資低、工作壓力大似乎是幼教界的一種“頑疾”[17-19],且相比發達地區,貧困地區的幼兒教師更加艱辛。這里提出這個問題,一是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不僅影響到了教師的心理健康,正如張梅老師所說的“煎熬”和“不忍心”,二是會影響幼兒教師隊伍的穩定性[2],進而影響教師隊伍整體的專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