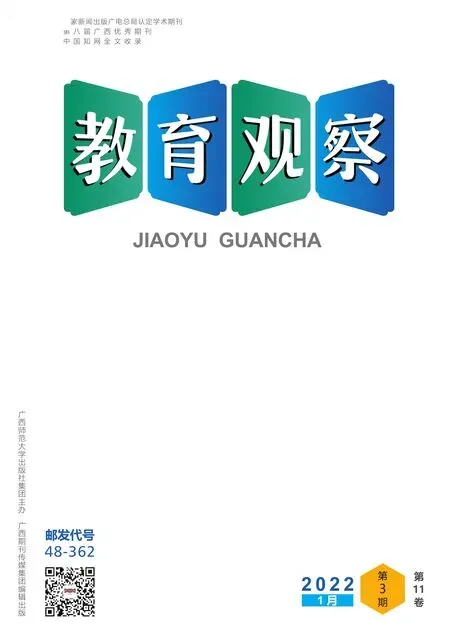2001—2021年國內誦讀教學研究評述:熱點、趨勢與問題
——基于中國知網計量可視化分析
王海峰,宋西雅
(山東建筑大學外國語學院,山東濟南,250102)
一、引言
誦讀于先秦時期誕生,到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迅猛,但是,到了近代,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致力于物質財富的積累,忽視了自身精神世界和道德的培養。針對這種情況,有學者甚至提出了“精神危機論”。[1]這就給教育界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如何尋找適當的方法解決當前人文文化不受重視的問題?誦讀教學的提出,是對這一需求的回應。此后,得益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專家學者的呼吁以及媒體的宣傳,誦讀與教育教學相結合的研究在國內流行開來。因此,為厘清近20年來誦讀教學研究的熱點、趨勢與問題,本文擬對中國知網2001—2021年的相關研究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根據誦讀教學研究的現狀,探究誦讀與教育教學相結合的可行性,并對該領域的研究進行展望,希望能夠推動本領域研究朝著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取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2001—2021年與誦讀教學相關的期刊文獻,采用計量可視化分析法和文獻分析法對這些數據進行研究。在中國知網以高級檢索形式,主題輸入“誦讀教學”,精準匹配,截至2021年2月10日,可得到3601條數據。在閱讀文獻摘要或全文后,手動剔除資訊、報紙新聞或與主題不相關的文獻數據,得到有效文獻3238篇。有效文獻中,學位論文以及學術期刊是研究的主要載體,占總發文量的97.16%,其中期刊論文占比90.49%,但CSSCI期刊發文量僅有36篇,占期刊總發文量的1.14%,這表明高質量研究成果相對欠缺。由于檢索結果的首條數據為2001年1月1日,末條數據為2021年2月10日,故將研究數據分析的時間跨度設為2001—2021年。具體指標見表1。

表1 誦讀教學研究文獻指標分析
(一)總體趨勢
將中國知網上與誦讀教學相關的國內論文數量變化以折線統計圖的形式呈現,如圖1所示。

圖1 誦讀教學研究文獻年發表量變化趨勢
從圖中可以看出,誦讀教學研究經歷了從緩慢增長到迅速發展兩個階段。我國誦讀教學研究起步較晚,2001—2008年有關誦讀教學領域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的文章局限于對誦讀教學的簡單介紹和構想,學者們對誦讀教學的研究也只是基于自己先前的教學經驗,研究的方向比較單一,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體系。自2010年起,我國關于誦讀教學研究的發文量增速提升,自此,誦讀教學逐漸成為學界的研究熱點。根據文獻分析得知,研究初期,學者們的研究重點往往聚焦在理論分析和思辨性總結層面,并未將構建的理論應用于具體的教學實踐。但2012年后,不少學者將研究重點轉移到了課堂實證研究。由此反映出研究是從理論到實證的漸變過程。2014—2019年,中國誦讀教學研究領域發文數量猛增,誦讀教學進入發展階段。2019年,誦讀教學研究領域的發文量比上年增加了132篇,達到這一階段年發文量的最高峰。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提出《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2],隨后教育部、國家語委印發了《中華經典誦讀工程實施方案》[3],從此誦讀教學活動在全國各地興起,誦讀教學及其研究得到了迅猛發展。2017—2020年,文獻數量穩步增長,由此,與誦讀教學相關的實踐與理論研究逐漸進入穩定發展階段。
(二)高頻次關鍵詞
關鍵詞是文章核心詞匯的凸顯,是文章的高度概括,因此,對某一領域相關文獻進行關鍵詞分析有助于把握該領域的研究熱點。[4]圖2列出了該領域出現頻次最高的10個關鍵詞。“經典誦讀”以359次居于高頻關鍵詞之首,由此可以判斷出誦讀教學研究領域的熱點。其他的重要核心詞匯有“誦讀教學”“小學語文”“小學語文教學”“誦讀教學”等。通過關鍵詞分析發現,中國誦讀教學的研究視角比較集中,主要是對教學策略與文化典籍的研究。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誦讀教學的研究領域較單一,尚未拓展出新的探索領域,這會間接導致學者研究動力不足。結合誦讀教學的高頻關鍵詞和具體文獻內容,我國當下誦讀教學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誦讀教學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誦讀教學教育理論成果和實踐案例的學習、誦讀教學基本內容的梳理;第二,誦讀教學的教學策略和教學過程的開展;第三,誦讀教育教學模式的構建。

圖2 誦讀研究高頻關鍵詞
(三)高被引文獻
文獻被引頻次是某一研究領域內的研究人員獲得同行認可的一種表現形式,可反映出該研究人員在學術群體中的被認可度與被信賴度,體現出論文對本領域研究發展的貢獻和影響。因此,為探究該領域的基礎性核心文獻,本文統計了中國知網數據庫2001—2021年間被引頻次排名前列論文,發現周慶元、張必錕、張心科、董玲平等學者的論文被引頻次較高,如表2所示。其中,《中國教育學刊》刊載的周慶元的論文《誦讀法的歷史演化與現時解讀》以107次被引頻次高居榜首。“面對新形勢,應更新誦讀法教學的理念,科學理解誦讀法的內涵;誦讀法不等于死記硬背,誦讀法的運用要符合現代學校教育的特點。”[5]這一觀點更是拓寬了誦讀研究的視角,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其次是張必錕在《中學語文教學》上發表的《學文言非誦讀不可》一文。周慶元和張必錕兩位學者是誦讀教學研究領域的先行者,有著豐富的理論修養和科研經驗,他們為今后誦讀教學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開拓了道路。

表2 高被引文獻一覽表(2001—2021年)
通過分析高被引文獻的具體內容得知,誦讀教學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學、語言學等領域。目前,關于誦讀教學的研究重點仍然在于教學策略及教學過程的開展,且研究學段主要集中在小學階段。少數涉及初高中階段的研究也僅局限于基于教學經驗的理論分析,并未深入具體的教學過程。同時,學者聚焦的研究學科也比較單一,很少有學者探究如何將誦讀與英語教學結合起來,這都反映出了目前關于誦讀教學的研究還有待于更深層次地探索。同時,知網中最高文獻被引頻次也僅為107次,由此可見誦讀教育的研究基礎還比較薄弱,需要更多學者的加入。此外,也有學者對傳統的誦讀教育模式進行了重新審視,提出了一些質疑和改進意見,這無疑也是誦讀教育研究的重要發展。[6-8]
(四)關鍵詞共現分析
聚類視圖側重于突出顯示關鍵節點和節點之間的連接。每一個節點代表該主題的研究領域,并且該節點下所有其他的研究主題都是圍繞此節點展開的。通過挖掘該主題的相關研究領域,可摸清此研究主題的發展情況。
圖3為誦讀教學研究熱點視圖,即高頻次關鍵詞共現網絡,節點過濾設置為出現頻次3次,關系分析為臨近節點分析,聚類分析闕值設置為3。如圖3所示,整個研究熱點視圖以“誦讀教學”為中心,構成一個基于高頻關鍵詞共現網絡的知識圖譜,與“誦讀教學”聯系密切的關鍵詞有“小學語文”“初中語文”“經典誦讀”。由此可以得出國內關于“誦讀教學”的研究熱點集中在中小學語文教學和經典誦讀這幾個領域。

圖3 關鍵詞共現網絡
三、存在問題及未來趨勢展望
上述研究從教育學、語言學、社會學、哲學等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學科豐富了人們對誦讀教學的理解和認識,同時也提出了我國誦讀教學研究的理念、內涵、任務、目標、問題、困境和未來思路。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我國誦讀教學研究是一個從理論分析構建到實踐研究逐步發展的過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很多方面仍有提升空間。因此,本文針對誦讀教學研究的現狀,從研究主題內容、研究價值取向和研究方法三大層面提出相關的建議,助力該領域研究的長遠發展。
(一)未來研究主題內容的廣度有待進一步拓展
目前,誦讀教學這一研究領域低層次、重復性研究較多,如目前涉及誦讀教學所應用學科的研究大多數局限于語文這一學科,關于其他學科是否可以采用誦讀教學法的探討相對較少,研究所涉及的學科不夠多元化。未來的研究可以著眼于將誦讀與英語教學以及高校思政課堂結合起來,進行誦讀教學資源開發,形成系統、規范和具有引領示范意義的誦讀課堂實踐教學體系。[9]還可以將現代的高新技術與誦讀教學方式結合起來,提高學生學習效果。同時,在誦讀內容的選擇上,較少有學者關注所誦讀的內容是否真正合乎時代,基本上局限于中華文學經典這一個領域,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各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誦讀的內容也應更加多元化、國際化、合理化,相關方面的研究也應跟上時代的步伐不斷精進。
(二)研究的價值取向有待進一步融合
目前,對于誦讀教學的開展,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無論是誦讀教學的意義、內容的選擇還是誦讀的途徑和方法方面,都存在不同的觀點。例如,張必錕提出在教學過程中應重視機械性誦讀,保證誦讀的強度[10]。而董玲平卻持有與之截然相反的觀點。他指出絕不可將誦讀與背誦畫等號,將死記硬背地記住古詩文的內容看作教學的重點。[11]關于誦讀的方法和途徑,各學者也是各執己見。張心科指出經典并不需要一字不落地背誦,應在嘗試回憶的過程當中慢慢理解,即運用想象力去強化記憶[5];而徐林祥等人則強調朗讀教學,提高誦讀教學有效性,同時創設教學情境,突出吟誦,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12]。各個學者應當求同存異,吸收借鑒彼此的長處,共同探討出適合中國國情、符合時代潮流的誦讀教學方案,為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助力。
(三)研究方法比較單一,應朝著方法融合的研究范式發展
目前,國內關于誦讀教學的很多研究局限于文獻研究法,大部分學者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提出自己的見解。為數不多的實證研究也只是基于學者的自身教學經驗進行教學分析,這種主觀性較強的實證研究成果的可推廣性受到質疑與挑戰。[5]未來關于誦讀教學的研究,可適當采用語料庫的方法,將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結合起來,開展基于語料庫的誦讀教學方法研究、基于語料庫的誦讀教學策略研究、基于語料庫的誦讀教學現實解讀研究等。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可以確保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和公正,提升研究成果的可信度。[13]
四、誦讀與英語教學
當下的誦讀教學多囿于漢語、古漢語、詩詞等,涉及英語教學的誦讀研究不多,也不夠深入。同時,當前的英語教學還是以應試教育為核心,僅僅以卷面成績來衡量學生英語學習的成效。[14]學習語言的最直接、最根本的目的是進行溝通和交流,而當前的英語教學模式似乎背離了這一核心。筆者認為,可以將誦讀和英語教學結合起來,增加實踐性和應用性較強的讀寫訓練,提高學生的詞匯記憶能力和口語表達能力。誦讀和英語教學的結合,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提升英語課堂的參與度,發揮學生在教學當中的主體地位作用。因此,將誦讀和英語教學結合起來,首先需要改變根深蒂固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以誦讀教學法為基礎,從強化發音教學開始,由淺入深地構建“層層漸進式”(感知—領悟—運用)教學模式。第一階段:語言作為一種工具,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因此,教師在設計教學內容時,應該將語言學習重心放在夯實基礎和營造語言的輸入、輸出環境上,人為地營造沉浸式的英語語言環境,這樣才能提高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使學生實現簡單的口頭與書面交流。[15]第二階段:指導學生在英語長句或段落中捕捉意群,只有掌握意群、停頓和重音,才能逐漸領會英語的節奏和韻律。第三階段:進行文章及其他課外材料的背誦朗讀及模擬訓練,不斷提高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五、結語
本文對誦讀教學研究領域當前的研究狀況、研究熱點和研究不足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研究發現,我國目前對誦讀教學的研究特別關注誦讀教學的理論研究、誦讀教學的教學策略、教學過程的開展和誦讀教育教學模式的構建。現有研究雖如火如荼,但亦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如研究對象的范圍有待進一步拓展、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需進一步完善等。因而,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只有通過科學有效的研究方法,樹立正確的研究理念,找準研究領域,才可以精準地把握誦讀教學的歷史、現實與未來,才可以助推新興研究者不斷探索誦讀教學的科學內涵、策略方法、目標設定和決策研究。誦讀教學模式的建設道路還很長,需要加強人才的培養,為未來誦讀教學研究的完善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