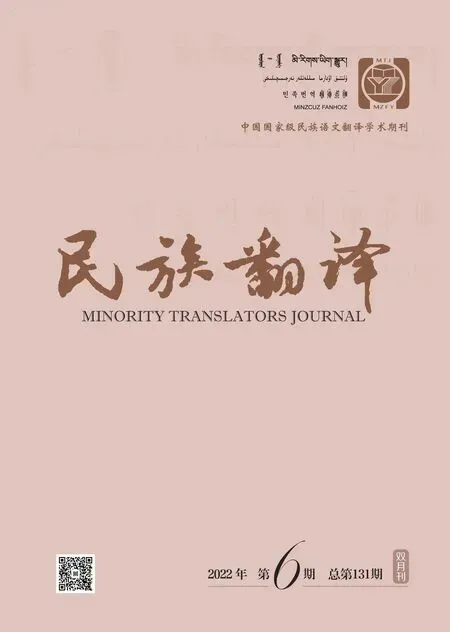生態(tài)翻譯學(xué)視角下文物說明牌漢英翻譯的問題及策略*
——以成都博物館民俗展區(qū)文物說明牌為例
石春讓 周記民
(西安外國語大學(xué)英文學(xué)院,陜西 西安 710128)
博物館是展示人類文明輝煌發(fā)展歷程的場所,蘊含著厚重的歷史和文化,也是城市的文化名片。博物館內(nèi)文物說明牌上的翻譯文本擔(dān)負(fù)著傳播當(dāng)?shù)匚幕墓δ堋?zhǔn)確的英語譯文能夠有效介紹宣傳文物,展示城市的魅力,增強博物館的國際影響力。近年來,成都發(fā)展迅速,城市建設(shè)取得了長足的進(jìn)步,已成為“網(wǎng)紅城市”,也吸引了大量的國際友人來參觀。其中成都博物館是最具人氣的景點之一。成都博物館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展出了從新石器時代到民國時期的近30萬件文物。其中,歷史文化陳列館民俗展區(qū)的文物展示了生活、生產(chǎn)、飲食、娛樂等方面的民俗風(fēng)情,內(nèi)容豐富,生動有趣,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然而,這個展區(qū)文物說明牌的英語翻譯卻存在著一些問題。筆者從生態(tài)翻譯學(xué)理論的“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視角進(jìn)行檢視和探討,并提出相應(yīng)的策略。
一、博物館文物說明牌翻譯的生態(tài)分析
生態(tài)翻譯學(xué)是中國學(xué)者胡庚申教授在生物進(jìn)化理論的基礎(chǔ)上提出的翻譯理論。該理論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生態(tài)平衡和協(xié)同進(jìn)化的原理和機制出發(fā),研究各種翻譯現(xiàn)象及其成因,從而獲得翻譯發(fā)展的規(guī)律,揭示翻譯發(fā)展的趨勢和方向[1]。生態(tài)學(xué)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從認(rèn)識論到本體論、從人類中心觀到生態(tài)整體觀的轉(zhuǎn)變。概言之,翻譯是一個動態(tài)的轉(zhuǎn)換過程,譯者必須不斷地適應(yīng)和選擇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才可能產(chǎn)出最佳譯文。也就是說,譯者只有在語言維度、文化維度和交際維度靈活地轉(zhuǎn)換、適應(yīng)和選擇,才可能產(chǎn)生最佳譯本[2]。
博物館的文物說明牌目的是客觀、準(zhǔn)確地反映文物本身的歷史內(nèi)涵和社會價值。其內(nèi)容包括展品的名稱、年代、發(fā)掘信息等,用以匹配展品,為參觀者提供展品的關(guān)鍵信息,文本短小精悍,風(fēng)格樸實。說明牌的翻譯實際上是譯者置身于展品、圖片、語言、文化、展廳等互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在語言層面、文化層面和交際層面開展適應(yīng)和選擇活動的最終結(jié)果。所以,譯者在翻譯博物館說明牌時,應(yīng)積極適應(yīng)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影響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各種因素,使譯文完整實現(xiàn)“三維”選擇轉(zhuǎn)換。
(一)語言維
翻譯是語言的轉(zhuǎn)換。語言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jìn)行的[3]。在翻譯博物館文物的說明牌時,譯者首先要把握文物術(shù)語翻譯的統(tǒng)一規(guī)范,力求譯文簡明、準(zhǔn)確和客觀。其次,還應(yīng)考慮中文和英文兩種語言的微妙差異,如詞結(jié)構(gòu)、句結(jié)構(gòu)、語義等,根據(jù)英語的語用習(xí)慣選擇合適的詞語、結(jié)構(gòu)和表達(dá)方式。最后,可以參考英美國家博物館的中國文物解說板上的特殊用語,從而與世界接軌,提高中國文物英譯的國際認(rèn)可度[4]。
(二)文化維
語言是植根于文化的,也是文化的重要載體。語言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內(nèi)涵,這些內(nèi)涵包括且不限于: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心理意識、思維方式、傳統(tǒng)習(xí)俗和宗教信仰。文化維度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化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關(guān)注雙語文化內(nèi)涵的傳遞與闡釋[3]。博物館文物說明牌譯文涉及文化、歷史、考古學(xué)等其他方面的知識。客觀上講,要翻譯好文物說明牌上的信息,譯員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yè)知識。譯者除了要有扎實的語言功底外,還要了解文化差異,掌握文物、展品翻譯所涉及的背景知識,發(fā)揮主觀能動性,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在譯文中再現(xiàn)文物的文化意義。
(三)交際維
交際維度的適應(yīng)性選擇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guān)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3],這要求譯者在傳遞語言信息和文化內(nèi)涵的同時,還要把原文的交際意圖在譯文中體現(xiàn)出來。具體地講,就是譯者還應(yīng)在譯語文本展現(xiàn)原語文本的預(yù)期交際目的。
英國翻譯理論家彼得·紐馬克將文本功能類型分為表達(dá)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呼喚功能(vocative function)、審美功能(aesthetic function)、應(yīng)酬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語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六種[5]。而博物館說明牌的文本具有信息功能和呼喚功能。博物館文物說明牌用短小的文本介紹文物的相關(guān)信息,召喚參觀者認(rèn)知文物。黃友義在討論外宣文本的翻譯時提出,為了達(dá)到向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譯者還可以遵循“三貼近”的原則,即貼近中國發(fā)展的現(xiàn)實,貼近國外受眾對中國信息的需求,貼近國外受眾的思維習(xí)慣[6]。博物館文物說明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外宣文本。所以,譯者在翻譯此類文本時,要突出譯文的預(yù)期交際目的,即滿足國際游客的期望和需求,使他們了解文物蘊含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相關(guān)信息,進(jìn)而尊重中國歷史和文化。
二、博物館文物說明牌的翻譯問題及策略
(一)語言維的翻譯問題及策略
本質(zhì)上,成都博物館的文物說明牌只呈現(xiàn)了一種類別的信息,即文物名稱。這實際上增加了翻譯難度,這意味著與文物有關(guān)的所有信息全靠文物名稱體現(xiàn)出來,所以一個文物名稱是一個高度概括了文物所有信息的名詞。一般來說,文物名稱由一個核心詞和多個修飾詞構(gòu)成,核心詞指稱文物的本質(zhì),多個修飾語闡釋文物的年代、出土地、材質(zhì)、功能、材料、形狀、顏色、裝飾、工藝和其特色等信息。英語中,如果一個名詞被多個詞匯修飾,可參照“OPSHACOM法則”——多個修飾性詞匯的排列順序是:“評述性詞(如,品質(zhì))+表大小形狀的詞+表新舊的詞+表顏色的詞+表產(chǎn)地(國籍、地區(qū))的詞+表材料的詞+核心詞”[7]。相應(yīng)地,譯者把文物名稱翻譯成英語時,需要準(zhǔn)確地翻譯核心詞和修飾性詞匯,還要把多個修飾性詞匯按規(guī)范的順序排列在一起。文物名稱英譯的語序可參照:“顏色/工藝/器形+材質(zhì)+中心詞+with+紋飾/局部特征”或“材質(zhì)+樣式+with+銘文/造型特征/所屬+用途”的格式[4]。如果沒有遵循上述規(guī)則,則會造成翻譯問題。具體來說,就會出現(xiàn)用詞錯誤、語序不當(dāng)、信息漏譯等。
1.用詞錯誤
用詞錯誤主要表現(xiàn)為名詞誤譯。
在“清至民國時期的香爐、熨斗、烘籠和缽”展柜陳列的“缽”(圖1),其名稱翻譯出現(xiàn)了誤譯問題。

圖1
原文:缽
譯文:Earthen Bowl
改譯:Copper Bowl
評析:缽,是形狀像盆而較小的一種陶制器具,用來盛飯、菜、茶水等,也是僧侶所用的食具。“earthen”一詞在《美國傳統(tǒng)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里的釋義為“made of earth or clay(由土或粘土制成的)”[8]2347。但通過觀察成都博物館中的實物“缽”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缽的材質(zhì)是銅,而并非陶土制。因此,這件文物名稱的英語譯文“Earthen Bowl”顯然是錯誤的,應(yīng)將“Earthen”替換為正確的譯詞“Copper”。
2.語序不當(dāng)

圖2
在該展柜中,“木雕樟木獅子香臺”(圖2)的名稱翻譯存在語序不當(dāng)?shù)膯栴}。
原文:木雕樟木獅子香臺
譯文:Wooden Lion-shaped Censer Burning Stage of Camphorwood
改譯:Camphorwood Censer Burning Stage with Lion-shaped Wooden Sculpture
評析:“木雕樟木獅子香臺”,即“樟木雕刻的獅子形態(tài)香臺”。很明顯,英語譯文中修飾性詞匯的排列順序混亂,即格式為“材質(zhì)+樣式+中心詞+材質(zhì)”,與上文提到的英譯規(guī)則不符。應(yīng)根據(jù)合英譯規(guī)則的“材質(zhì)+樣式+with+銘文/造型特征/所屬+用途”格式調(diào)整修飾性詞匯,譯為“Camphorwood Censer Burning Stage with Lion-shaped Wooden Sculpture”。
3.漏譯

圖3

圖4
在“清至民國時期的照明用具”展柜中陳列的“青花瓷燈盞”(圖3)和“銅質(zhì)龍紋燭臺”(圖4),其名稱譯文存在漏譯問題:
原文:青花瓷燈盞
譯文:Blue-and-white Oil Lamp
改譯:Blue-and-white Porcelain Oil Lamp
原文:銅質(zhì)龍紋燭臺
譯文:Bronze Candlestick of Dragon
改譯:Bronze Candlestick with Dragon Carvings
評析:從語言維來看,“青花瓷燈盞”的譯文里缺少“porcelain(瓷器)”一詞,這屬于顯性漏譯,應(yīng)予以補充完整。在文物名稱的漢語表述中,一些表述雕刻工藝的信息常被省略,譯者常因為沒有理解原文隱含的信息,而在譯文漏掉了這樣的信息。如果譯文中沒有呈現(xiàn)這樣的信息,就會使譯語讀者不明就里,或得不到全面的信息。這實際是隱性漏譯。如“銅質(zhì)龍紋燭臺”這個漢語名稱隱含了這件文物的工藝是“雕刻”(carving)。譯文里缺少“雕刻”之意,會導(dǎo)致譯語讀者無法了解這件文物的制作工藝。所以,譯者不僅要把原文的顯性信息全部翻譯出來,也需要把隱性信息翻譯出來。相應(yīng)地,上面兩件文物“青花瓷燈盞”可譯為“Blue-and-white Porcelain Oil Lamp”,“銅質(zhì)龍紋燭臺”可譯為“Bronze Candlestick with Dragon Carvings”。
(二)文化維的翻譯問題及策略
由于文物蘊含了豐富的文化、歷史信息,所以文物名稱也指稱了豐富的文化信息。文物名稱中的文化信息具有民族性、簡潔性的特征。文物名稱中的文化一定反映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文化意象可能與英語受眾存在相同之處,但更多的是不同之處。所以,把中華民族的文化意象翻譯成英語,就需要譯者采取保留原語意象、替換原語意象、省略原語意象等方法。由于文物名稱只是一個詞匯,所以,文化意象的呈現(xiàn)方式不可能帶有注釋。因而譯者在翻譯文物名稱中的文化信息時,可能出現(xiàn)文化意象轉(zhuǎn)換錯誤、文化意象轉(zhuǎn)換缺失等問題。

圖5

圖6
1.文化意象轉(zhuǎn)換錯誤
在“清至民國時期的花瓶和帽筒”展柜陳設(shè)的“青花折枝花紋瓷罐”(圖5)和“青花冰梅紋瓷瓶”(圖6),其翻譯出現(xiàn)了文化意象轉(zhuǎn)換錯誤的問題。
原文:青花折枝花紋瓷罐
譯文:Blue-and-white Porcelain Jar of Flowers on Branches
原文:青花冰梅紋瓷瓶
譯文:Blue-and-white Porcelain Bottle with Plum Blossoms in Winter
改譯:Blue-and-white Porcelain Vase with Plum Blossoms and Cracked Ice Pattern
評析:“青花折枝花紋瓷罐”即“青花瓷的帶有折枝花花紋的罐子”。折枝花花紋是唐代出現(xiàn)的一種絲綢紋樣,后來運用到瓷器上,在器物的顯著部位繪畫一枝折下的花卉,故名。其英文譯文應(yīng)為“Pattern of Broken Flower Style”。這里原譯為“Blue-and-white Porcelain Jar of Flowers on Branches”,將帶有文化意象的詞語“折枝花(紋)”錯譯為了“Flowers on Branches”,且缺少描述“花紋”的詞語“pattern”;另外,“of”也應(yīng)改為“with”。因此,這件文物的譯文應(yīng)為“Blue-and-white Porcelain Jar with Patterns of Broken Flower Style”。
“青花冰梅紋瓷瓶”,是帶有冰梅紋的青花瓷花瓶。“冰梅紋”又稱“冰裂梅花紋”,創(chuàng)制于清康熙朝,以仿宋官窯冰裂片紋為地,并于其上畫朵梅或枝梅的裝飾紋樣。顯然,這里的“冰梅”是文化意象詞語,并不是指“冬天的梅花”,而是“冰裂的背景的梅花紋”,故不能譯為“Plum Blossoms in Winter”,建議譯為“Plum Blossoms and Cracked Ice”。因為這件文物是花瓶,所以取“vase”一詞更為妥當(dāng),而非“bottle”;另需加上“pattern”一詞表圖案。所以,“青花冰梅紋瓷瓶”可譯為“Blue-and-white Porcelain Vase with Plum Blossoms and Cracked Ice Pattern”。

圖7
2.文化意象轉(zhuǎn)換缺失

圖8
在“清至民國時期的香爐、熨斗、烘籠和缽”和“清至民國時期的花瓶和帽筒”展柜中,“青花釉里紅荷花紋簋式爐”(圖7)、“五彩嬰戲紋獸耳瓶”(圖8)的翻譯存在文化意象轉(zhuǎn)換缺失的問題。
原文:青花釉里紅荷花紋簋式爐
譯文:Blue-and-white Round Burner Red Under the Glaze with Lotuses
要求系統(tǒng)的靜態(tài)速度誤差系數(shù)Kv≥50 s-1,γ≥40°,wc≥10 rad/s。試應(yīng)用MATLAB Simulink進(jìn)行滯后—超前校正。
改譯:Blue-and-white Glazed Round-mouthed Censer with Red Lotus
原文:五彩嬰戲紋獸耳瓶
譯文:Beast-ear Bottle of Kids Playing in Five Colors
改譯:Five-colored Beast-ear Bottle with Kids Playing Patterns
評析:“青花釉里紅荷花紋簋式爐”即“青花釉里工藝的帶有紅荷花紋的簋式香爐”。這里的“簋”字是中國文物的特有詞匯,“簋”在《漢語大詞典》中的釋義為:“古代祭祀宴享時盛黍稷的器皿。一般為圓腹,侈口,圈足。”[10]124另據(jù)《簡明古漢語詞典》,“簋”指古代青銅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也是重要的禮器,在祭祀和宴饗時,它和鼎配合使用[11]。簡言之,“簋”,即青銅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圓口,兩耳或四耳。該文物的英文原譯未把文化意象詞語“簋式爐”翻譯清楚,因而會讓國外游客產(chǎn)生疑惑。“burner”一詞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里的釋義為“the part of an oven or heater that produces heat or a flame(爐子或加熱器中產(chǎn)生熱量或火焰的部分)”[9]276,是一種烹飪工具,而這里的“簋式爐”指“簋式香爐”,此處不宜譯為“burner”,而應(yīng)譯為“censer”。
“五彩嬰戲紋獸耳瓶”是帶有兩個獸耳形狀把手的花瓶,瓶身有小孩嬉戲玩耍的彩色圖案,栩栩如生。這件文物說明牌上譯文中的“獸耳瓶”翻譯無誤,但文化意象“五彩嬰戲紋”的翻譯出現(xiàn)了問題,原譯“in five colors”同樣屬于文化意象轉(zhuǎn)換缺失的問題。“五彩嬰戲紋”即“帶有五種顏色的孩童嬉戲玩耍圖案(的獸耳瓶)”;“紋”也應(yīng)譯為“pattern”。因此,這件文物的名稱可譯為“Five-colored Beast-ear Bottle with Kids Playing Patterns”。
(三)交際維的翻譯問題及策略
展品說明牌還應(yīng)具有可及性,即說明牌上的文字易于參觀者理解、接受。倫敦大學(xué)傳播學(xué)系教授波萊特·麥克馬納斯認(rèn)為說明牌的文字須精煉,盡量使用簡單易懂的詞語,適當(dāng)運用日常生活用語甚至平輩社交用語能更有利于觀眾反復(fù)閱讀[12]。露易斯·拉韋利提出撰寫博物館文字說明時,最有利的方法是默認(rèn)閱讀對象為8-15歲的群體,效果更容易令大眾接受[13]。另外,可讀性也是展品說明牌應(yīng)具備的特點之一。觀眾參觀陳列展覽,與看書讀報最主要的不同之處,是場地、時間、條件給觀眾以很大的限制,觀眾是在站立和移動中觀看的。因此,對文字說明不可能反復(fù)琢磨。文字說明表述風(fēng)格一定要通俗易懂,突出重點抓住本質(zhì),可讀性強[14]。不僅如此,文字說明還要具有趣味性和藝術(shù)性,文字說明需要更多地追求個性化、風(fēng)格化的形式語言而不僅僅單純地傳遞信息,只有如此,才能提高觀眾參觀的興趣,使陳列展覽更加充滿活力和感染力[15]。如果文物名稱的譯文不能令參觀者清晰明確地理解文物所含信息,就易造成交際問題,具體表現(xiàn)為參觀者對文物名稱所含信息無法接受、或不能順暢地接受、或接收到錯誤信息。這可能是譯文中出現(xiàn)模糊信息、冗余信息、缺省信息所致。也就是說,譯文造成的交際不暢或交際失敗。
1.信息模糊
在“清至民國時期的香爐、熨斗、烘籠和缽”展柜中陳列的“銅烘籠”(圖9)的英譯,存在明顯的信息模糊問題。

圖9
原文:銅烘籠
譯文:Copper Roaster
改譯:Copper Warmer
評析:“銅烘籠”是用來取暖、烘干衣物的一種容器。漢語詞“烘籠”在《漢語大詞典》中的釋義為:“罩在火爐或火盆上的籠子。用以烘干衣物。多用竹或柳條編成。”[10]60“烘籠”最早起源于西南地區(qū),在潮濕陰冷的冬天是必備的取暖之物。“銅烘籠”即“銅制的烘籠”,在這里被翻譯為“Copper Roaster”,“roaster”一詞在《美國傳統(tǒng)詞典》里的釋義為“a special pan or apparatus for roasting”[8]6217(烘烤箱),是一種烹飪工具,沒有“取暖”的用途。顯然,這里將“烘籠”直接譯為“roaster”,將“烘烤箱”與“烘籠”混為一談,模糊了信息,會讓讀者誤解其用途。“烘籠”應(yīng)譯為“hand warmer”或“dryer”,因此,這件文物的名稱可以譯為“Copper Warmer”。

圖10
2.信息缺失
在“清至民國時期的花瓶和帽筒”和“清至民國時期的香爐、熨斗、烘籠和缽”展柜中,“帽筒”(圖10)和“天青蘭雉熏爐”(圖11)的翻譯存在交際維層面的信息缺失問題,會讓參觀者誤解文物用途。
原文:帽筒
譯文:Brush Pot
改譯:Hat-holding Cylinder
原文:天青蘭雉熏爐

圖11
譯文:Azure Blue Sandalwood Burner
改譯:Azure Blue Sandalwood Censer with Pheasant-shaped Handles
評析:“帽筒”是一種用來放置帽子的器具,大多為瓷制,中空,圓柱形。原譯“Brush Pot”的意思為“放置筆刷的鍋”,顯然是錯誤的。將文物的用途錯譯,會讓參觀者產(chǎn)生誤解,這樣就沒有實現(xiàn)交際維的轉(zhuǎn)換。根據(jù)原文和實物的樣貌,這里的“帽筒”應(yīng)譯為“Hat-holding Cylinder”。
“天青蘭雉熏爐”即“帶有雉形把手的蔚藍(lán)色檀香爐”。該文物原譯為“Azure Blue Sandalwood Burner(天藍(lán)色熏爐)”,雖然簡練,但不夠詳細(xì),缺失表示把手形狀的“雉”一詞,讀者無法了解該香爐的具體形態(tài),屬于交際維層面的信息缺失。根據(jù)上文提到的英譯規(guī)則,該件文物的名稱可譯為“Azure Blue Sandalwood Censer with Pheasant-shaped Handles”。
博物館文物說明牌上的文本雖然短小精悍,卻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和文化信息。將這種高度濃縮的文本翻譯成英語具有較大的困難。在生態(tài)翻譯學(xué)理論的指導(dǎo)下,從“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視角可以檢視博物館文物說明牌的譯文錯誤。為了提升博物館文物說明牌的譯文質(zhì)量,譯者需要綜合考察相關(guān)的各類環(huán)境因素,在“語言維”精準(zhǔn)轉(zhuǎn)換原文的基本信息,在“文化維”凸顯文物的人文特色,在“交際維”滿足游客和讀者的預(yù)期需要。由此提高博物館文物英語說明牌的翻譯質(zhì)量,進(jìn)而促進(jìn)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
*本文系全國科技名詞審定委員會科研項目 “中國術(shù)語翻譯理論史稿”(YB20200014)、 西安外國語大學(xué)科研項目 “新時代科技文檔漢英翻譯的優(yōu)化模式與評價機制研究 (XWB03) 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