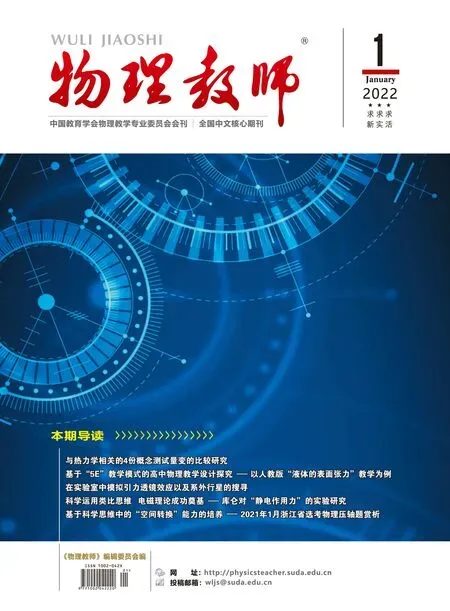與熱力學相關的4份概念測試量表的比較研究
方 偉 湯 莉 王盼伊 張 璟 袁 偉 袁 婧
(上海師范大學物理系,上海 200234;2.上海市星系和宇宙學半解析研究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234)
1 引言
立秋早晚涼,中午汗濕裳,人類生活在冷與熱的世界里,熱學相關知識可以認為是人類接觸最早、對人類生活影響最多的物理知識.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基于日常生活經驗形成了很多有關熱與溫度的概念,但這些概念很多并不是科學概念,更多的是基于直覺的前科學概念(也稱naive conceptions、misconceptions、preconceptions等).如認為熱量是一種存在于物體中的物質,并且在此樸素概念基礎上認為高溫物體所含熱量多;分不清熱量與溫度的概念;基于嚴寒冬天舌頭能被戶外鐵塊粘住但不會被木頭塑料等粘住而認為戶外鐵塊的溫度更低;基于井水冬暖夏涼的體感而認為夏天井水溫度更低;認為沸騰液面上方的水蒸氣溫度更高等,因而熱量、溫度等熱力學相關概念的教學顯得尤為重要.認知科學研究表明:人腦中固有概念的改變是非常困難的,知識并不是教師教會的,而是學習者通過與其腦中已有知識建立連接而建構起來的.如果新學知識匹配其頭腦中的已有圖式,則學習較快,但若要改變已在頭腦中建立好的知識圖式,則非常困難.因此需要基于研究的教學.[1]
20世紀70~80年代發端于美國的物理教育研究將科學研究范式注入物理教學之中,研發了各種客觀的教學測試工具,以便調查學生學習現狀,或評估教學效果.這些測試工具具體表現為針對某一部分物理知識的診斷性測試題目,但和一般試題不同,這些量表的試題經過前期大量調研、研究和試測,題干和每個選項都經過精心研究,具有很高的信效度,其功能類似于物理實驗中諸如電壓表、電流表一樣的測量設備.[2-4]比較著名的概念量表如力學概念測試(Force Concept Inventory,FCI)、簡明電磁學評估量表(Brief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Assessment,BEMA)和 Lawson科學推理能力測試量表(Lawson Classroom Test of Scientific Reasoning,LCTSR)等.[5]國外對熱量、溫度等熱力學相關的教學研究非常多,學者們也開發了多個與熱量、溫度等熱力學相關的測試量表.[6]在由美國物理教師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AAPT)和堪薩斯州立大學聯合開發并受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美國重要物理教育研究網站PhysPort上有95份針對不同物理學科領域、問題解決能力、科學推理、實驗技能、學習態度等方面的量表,其中有6套與熱學相關的量表如熱學概念評估(Thermal Concept Evaluation,TCE)、熱與溫度概念評 估(Heat and Temperature Conceptual Evaluation,HTCE)、熱力學概念量表(Thermodynamic Conception Survey,TCS)、熱力學過程與熱力學第一及第二定律量表(Survey of Thermodynamic Processes and First and Second Laws,STPFaSL),等等.[7]本文接下來將對與熱量、溫度、熱力學概念和過程等相關的4份概念測試量表進行比較研究和國內外研究綜述.本文作者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中也翻譯了這4份量表,中文版已被PhysPort官網采納.[8]
2 量表的介紹與比較分析
本節我們將集中對熱學概念評估(TCE)、熱與溫度概念評估(HTCE)、熱力學概念量表(TCS)和熱力學過程與熱力學第一及第二定律量表(STPFaSL)4份量表的內容進行介紹,并對它們進行比較分析.至于PhysPort上提到的另外兩份與熱相關的量表:TCI(Thermodynamics Concept Inventory)和 TTCI-T(Thermal and Transport Concept Inventory:Thermodynamics),本文將不涉及.對于TCI,其開發者表示該量表的開發仍在進行,不推薦使用.對于TTCI-T,PhysPort網站上并沒有量表可供直接下載,從其量表標題看內容大致被前4份量表所覆蓋,因此我們只重點介紹前4份量表.
表1列出了TCE、HTCE、TCS和STPFaSL 4份量表的具體信息,其中包括開發者及開發時間,題量、施測時間、施測對象及題目內容所涉及的概念知識點.除STPFaSL量表中的題目牽涉多個概念(見圖1)外,其他量表的題目都明確對應某版塊的概念.從內容上看,HTCE中熱量與溫度的概念和TCE中的非常相似,但TCE中有關熱量與溫度的題目專注于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測試題大多以對話場景出現,讓學生選取最認同的那個選項.HTCE中有3道題涉及溫度隨時間的變化曲線,TCE問卷中則沒有這類圖表題.TCS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前16題,主要涉及溫度、熱傳遞和理想氣體,適合初高中學生;后面的19題為第二部分,涉及熱力學第一定律、熱力學過程等,適合大學物理層次.教學實踐中,可將第一部分作為前測,將整個問卷兩部分一起作為后測.TCS中的問題2、4、5、6和熱學概念評估TCE中的第8、11、14、6相同,TCS中的問題1、3則和HTCE中的問題8、1相同.TCS有著比TCE和HTCE都多的熱力學概念,例如TCS中的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理想氣體概念,在TCE和HTCE中均無涉及.而且TCS中的題目也比HTCE和TCE中的要更復雜些,例如在TCS中有一題涉及活塞壓縮氣體的過程,該過程一共經歷5個步驟,每一步驟活塞位于不同的位置,相應的題目會問這個過程中的做功、吸放熱及能量變化關系.STPFaSL比TCS多了熱機、可逆與不可逆循環、熱力學第二定律等內容,但少了熱量與溫度的概念考查.對于熱力學第一定律,兩問卷的考查內容有相似之處,例如STPFaSL中的第10題和TCS中的第32-34題所用p-V圖幾乎相同,考查的內容也類似,都是相同始末狀態的不同過程的做功、吸放熱和內能變化.

表1 TCE、HTCE、TCS和STPFaSL 4份量表的詳細信息

圖1 STPFaSL量表各題涉及的知識點一覽圖(注:R表示解決此題必需此概念,I表示盡管沒有明確要求但解決此題暗含需要此概念,M表示提到此概念但專家們認為并不是解決此問題的必要條件.[10])
TCE、HTCE、TCS和STPFaSL 4份量表中的幾乎所有題目均為單選題(只有HTCE中的第24題為作圖題).這些量表中的題目之間往往并不完全獨立,例如HTCE中的第1-4、5-7、8-9、10-11、12-15、16-19、20-23、26-28題 均基于同樣的題目情景,因此盡管總共有28道題,但實際題目情景不過10個.同樣情況也出現在其他量表中,如TCS中的第8-10、11-12、13-15、16-19、20-25、26-28、29-31、32-34題,STPFaSL中的第1-2、3-4、5-8、11-13、23-25、31-33題,這類設計有利于全面考察學生對某個知識點概念的理解情況,同時還能互相印證,提高量表的信效度.對于TCE量表,盡管沒有類似的組題,但整個量表將所有問題都放在同一個形象化的類真實場景中,也就是一群學生小伙伴正在廚房或者自助餐廳里,這些學生善于觀察身邊的物理現象,并樂于向其他人提出自己的解釋,測試者則需從4~5個選項中選出最認同的那一個.綜合4份量表內容,結合國內實際,TCE、TCS的第1部分適合中學生,TCS的第2部分、HTCE、STPFaSL等問卷適合大學生,整個4份量表差不多能囊括國內從初中到大學的宏觀熱力學內容.
3 相關研究綜述
熱學概念評估TCE由澳大利亞科廷大學的Shelley Yeo和Marjan Zadnik于2001年開發.該論文至今已獲得230多次的相關研究的引用,是本文所介紹的4份量表里流傳最廣的.2012年,TCE的開發者及其合作者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對該量表進行了更細致的研究,通過對515名10-12歲的韓國學生的測試,給出了量表的4個概念組,并且發現相比熱傳遞及溫度改變、冷凍與融化兩個概念組,沸騰、導熱性與熱平衡兩個概念組題目的平均得分要低很多.[9]國內利用該量表進行研究的并不多,文獻[6]綜述了國外學生對溫度和熱量概念理解的研究進展,其中有對TCE的介紹,文獻[11]利用TCE量表進行了初中生學習熱量和溫度概念的研究,發現學生對熱量與溫度的概念掌握的并不好,文獻[12]借鑒TCE量表進行了中學生對熱學概念的認識現狀及其學習進階研究.
熱與溫度概念評估HTCE由David Sokoloff和Ron Thornton于2001共同研發.HTCE量表具有代表性的測量結果如表2所示.通過對澳大利亞和泰國的4所大學超過1000名學生的測試,顯示學生對冷卻率、傳熱速率、比熱容、相變等概念的理解最差,這和我們的測試結果是吻合的.這些結果可為教學提供參考.[13-14]

表2 HTCE量表在國外的應用結果
熱力學概念量表TCS由泰國清邁大學和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P.Wattanakasiwich等4位學者于2013年發布,目的是評估學生對熱力學基本概念的理解.在TCS出來之前,只有2001年發布的TCE和HTCE兩份評估問卷與熱力學領域的溫度、熱量相關,但沒有評測學生掌握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熱力學過程的量表.TCS量表由35道單選題組成,前面7題考查溫度與傳熱概念,與TCE、HECE大致相同,后面的28題涉及理想氣體定律、熱力學過程、熱力學第一定律等熱力學內容.量表從2009年開始設計,綜合了諸多前人的工作,經過了2000多名學生的多輪測試和研究,歷時4年才正式發布.[15]P.Wattanakasiwich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學生有如下一些錯誤熱力學概念:① 不正確地建立壓強與溫度的關系,以為溫度升高,壓強一定會增加;② 不正確地建立溫度與熱量之間的關系,認為熱量是一種可以注入某物體或者能從某物體中移除的物質;③混淆系統對外做功和外界對系統做功的區別;④ 以為吸收或放出的熱量是狀態的函數;⑤ 難以運用熱力學第一定律直接從p-V圖得出吸、放熱的大小.TCS量表可以作為前后測用在大學熱學課程中,來評估和檢驗學生熱力學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2015年,悉尼大學的H.Georgiou和M.D.Sharma利用TCS量表作為前后測來評估學生積極主動參與類的課堂和傳統課堂的教學效果差異,發現積極主動參與類的課堂的教學效果確實要優于傳統課堂.[16]Javad Hatami等人開發了一類熱力學的概念圖來作為評估課堂學習效果的工具,文中將該概念圖測試工具與TCS量表做了相關性分析,發現兩工具之間有中到強的相關性(相關系數為0.6).[17]P.Barniol與G.Zavala對TCS量表進行分析后指出,TCS量表的部分題目設計有些問題,他們對其進行了修正和完善.[18]
TCS量表并不含有任何關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內容,美國匹茲堡大學Benjamin Brown和Chandralekha Singh于2015年開發了熱力學過程與熱力學第一及第二定律量表STPFaSL,該量表由33道單選題構成,考查的知識點涉及熱力學過程、熱力學第一定律、熱力學第二定律、p-V圖、可逆過程與不可逆過程等.量表對2400多名大學生做過測試,信效度都很好,論文中基于STPFaSL量表測試結果給出了對熱力學過程、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教學建議.[10]
4 教學啟示與結語
本文介紹的4份量表中,除了熱學概念評估TCE有國內學者研究外,其余3份量表HTCE、TCS、STPFaSL均未檢索到有國內學者研究,這一方面和國內初高中物理中熱學所占比重較少有關,另一方面與當前國內基于實證的物理教學研究較少有關.這4份量表都是關于熱力學宏觀理論,也有學者開發了分子動理論等熱力學微觀理論的量表.[19-20]研究表明,學生能在概念量表測試中拿得高分,一般也能在傳統考試中取得高分,但反過來未必.需要指出的是,物理教育研究也不能過于迷信概念量表,概念量表不可能包括課程里的所有知識概念,概念量表也不能測試出學生的數學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不過有研究表明基于概念測試結果的、專注于基本知識概念理解的教學,有利于提高學生對傳統問題的解決能力.[1,21]
國內的教育研究有不少是關注政策的偏向宏觀性和邏輯思辨性的文章,還有不少是基于個人經驗性的文章,但基于實證、基于數據的物理教育研究還不多.在不少教育類碩士論文中,用于檢驗教學實驗的前后測試量表編制過于簡單和草率.量表相當于測量教育過程和結果的“尺子”,其編制是一個相當復雜和嚴謹的系統工程,一般要經過如下7步:① 通過訪談或開放式問題收集學生想法;② 利用這些想法編制題目,問題的各選項應包含收集到的學生的常見錯誤觀點;③ 找另一組學生來試測編制的題目,為確保學生是基于正確的原因才得到正確的答案,開發者要在測試后對每個試測的學生進行訪談;④ 將問卷分發給領域內的專家,以確保題目所考察的確實是該知識版塊的重要概念,同時也請專家核實答案的正確性;⑤ 基于專家和學生的反饋修改問卷;⑥ 向更大范圍的學生施測問卷,詳細檢測問卷結果的可重復性和各選項的得分分布,利用不同的統計方法來檢測量表的信效度;⑦ 再次修改量表.[21]可見量表并非如編制課后測試題那么簡單,要經過多輪測試和專家把關,這也是本文介紹4個涵蓋初高中直至大學層次的熱力學量表的原因,這些量表編制過程遵循了科學研究的規范,具有較高的信效度,用于教學實驗的前后測量較為可靠.由于國外學生的思維、成長環境、精力等與國內學生不同,導致學生的迷思概念可能也有不同,因而在利用這些量表開展國內研究時,要對量表進行試測和(或)適當改編,對量表的信效度要重新考查,最后得到適合國內學生的修正版量表.如果能基于物理教育研究的科學范式,自主開發出完全基于國內學生實情服務于國內物理教育研究的概念量表,則其意義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