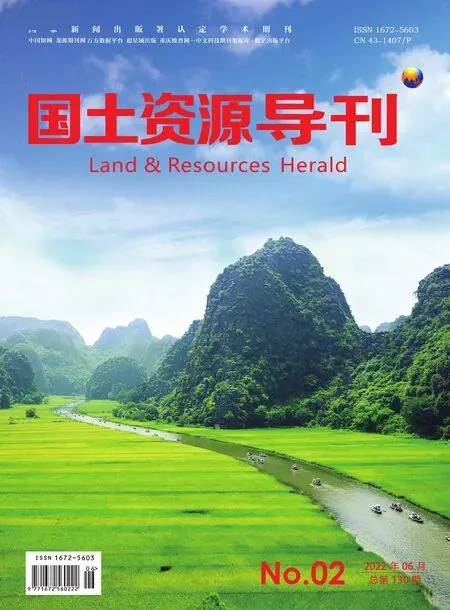耕地保護目標下的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工作探究
曾柳絮,賓聯明,陳柯夫
(湖南省土地綜合整治局,湖南 長沙 410119)
耕地是鄉村土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糧食生產的主要載體。近年來,國土調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均耕地資源與世界人均水平差距不斷加劇;多年來的高強度發展也極大破壞了農村耕地質量和生態。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是近年來自然資源部門助推鄉村振興,踐行生態文明的重要抓手。推進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新類型項目中保障鄉村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嚴格執行耕地保護目標,科學平衡土地資源開發和保護,值得深入研究。
1 耕地保護與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關系
1.1 耕地保護的內涵
耕地保護是基本國策。目前,我國對耕地保護的力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了堅守耕地數量底線、落實糧食耕種、保障糧食安全、維系社會安穩,從耕地的數量及用途明確了耕地紅線、永久農田特殊保護、耕地總量平衡、黨政同責、“田長制”等保護耕地的政策規定,防止耕地“非糧化”和“非農化”,形成了包括耕地數量、耕地質量以及農田生態3個方面的綜合保護模式。
1.2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內涵
以往單純增加耕地數量進行耕地保護,這些土地整治項目不能解決農村區域現有的耕地破碎、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不高、用地空間布局無序亂象和生態質量退化等問題。在原土地整治基礎上,自然資源部門在鄉村的固定范圍內以國土空間規劃作為科學指引,深入挖掘整治區域的發展潛力,以鄉村振興發展為主導確定區域整治目標定位,推進一種全地域、全要素和全覆蓋的多目標整治的綜合手段,對不同村莊類型開展農用地、建設用地、生態保護修復等差異化整治工程,即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優化當地“三生”空間、騰挪發展空間、激發資源要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鄉村的多功能轉型發展[1]。
1.3 耕地保護與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之間的關系
耕地保護是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實施的多目標之一。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不僅對整治后的耕地數量、質量等別及布局、永久基本農田的可調整情形做出了明確規定,而且提出占用耕地進行人造景觀、調整后的永久基本農田質量及布局不滿足要求等負面清單內容。全域土地整治實施中尊重土地要素特別是耕地,可通過綜合性工程促進農業產業發展,兼顧耕地數量、質量、生態需求的同時,加強耕地資源、資產、資本價值的相互轉化,強化耕地資源要素與功能的聯系,這是執行耕地保護目標的有力手段。
2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實現耕地保護的路徑
2.1 以規劃為引領
計劃實施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鄉鎮需要科學劃定綜合整治區域,構建耕地保有量在內的分類指標、明確用地結構布局及管控三線邊界,對綜合整治進行引導和約束[2]。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結合近期規劃的重點項目,統籌項目實施,在保障耕地數量、質量、生態的同時,引導產業用地、宅基地等建設用地的規范使用,減少違法占用耕地行為,從源頭上“堵疏結合”。
2.2 增加整治區耕地數量
通過農用地開發、廢棄建設用地復耕和高標準農田建設等途徑,要求新增耕地面積比例不低于5%;進行永久基本農田調整的,同步要求永久基本農田新增面積比例不低于調整的5%。通過小田變大田,減少零星分散圖斑,優化耕地布局,提升農業的規模化、機械化和現代化水平。
2.3 提升整治區耕地質量
可進行耕地提質改造、損毀耕地復墾、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等工程,對整治區域內新建的建設項目占用耕地進行表土剝離存放,改善耕地的理化性狀,提升耕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加強基礎地力,降低用工成本,減少化肥投入,多途徑提升耕地質量。
2.4 推進整治區農田生態保護建設
針對整治區農田生態系統中存在的問題,從全域生態系統的角度,開展綠色、生態農田整治及修復、生態網絡的連通,通過對生態基礎設施及生物多樣性恢復進行工程實施,結合綠色產業技術模式和生態種植模式,促進農藥化肥減施增效,提升資源循環利用效率,減少耕地污染,提高防御自然災害能力,恢復和提升農田景觀及生態系統服務。
2.5 拓寬耕地保護資金渠道
打破原有單一部門資金投入耕地保護的狀況,通過地方政府整合涉農部門資金,引導社會資本及金融資本投入,鼓勵市場化運作,推動適度規模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更易形成多部門、多渠道的資金共同進行耕地保護的新局面。
2.6 顯化耕地復合功能
引導耕地利用向適度規模經營、農機農藝現代化、聯合生產多樣化、生態循環化、農業現代化轉變,以田園綜合體建設的方式來發展特色、循環、休閑、教育、科普和旅游等農業產業,提升耕地多功能價值,并將價值回歸農民,增加他們的收益,激發其參與耕地多功能管理的積極性,降低耕地的非農建設、非糧食種植的傾向,促進耕地保護創新發展。
3 耕地保護目標下的全域綜合整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土地資源的全域綜合整治是鄉村地區未來發展的方向,目前全國還處于試點推行階段,無財政專項資金,僅輔以可調整永久基本農田、新增耕地指標優先在省內交易作為支持政策,暫未形成成熟的耕地保護目標下的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模式,在工作推進中存在以下問題。
3.1 地方政府積極性有待提高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試點主要靠地方政府統籌資金投入建設,而新增耕地指標收益要求反哺整治區域,顯化耕地復合功能的耕地保護更需要地方政府統籌謀劃、久久為功,在整體經濟下行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壓力下,可短期快速增長地方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單一的補充耕地方式更受地方政府歡迎。
3.2 新增耕地率達標問題
經過多年的土地開發整理,各地適宜開發的耕地不多,隨著新增耕地開發要求越來越嚴格,囿于試點新增耕地率5%的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對自然稟賦一般、位置較為偏遠的土地進行開墾,不僅達不到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區域相對集中連片的要求,開墾后的耕地更存在撂荒可能。
3.3 調整永久基本農田問題
調整永久基本農田是破解農村用地瓶頸、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助推鄉村振興的一項支持政策,但在實際工作中,地方政府調整基本農田的真實原因可能并非是與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密切相關的整治工程或者相關聯的農民安置、農村基層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設施配套及農業產業發展等,存在借道調整的傾向,甚至與耕地保護理念存在沖突。
3.4 耕地資源存在隱形損失可能
地方政府對耕地的生態文明建設簡單認為是耕地景觀化,土地整理流轉后的規模經營或者以“為民增收”等為由、部分耕地用于非農建設,均有造成耕地“非農化”和“非糧化”,形成耕地資源隱形損失的可能。
3.5 農民參與程度不足
農民參與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耕地保護缺少法律支撐,缺少足夠的知識儲備,更多的是以政府部門為主導,尚未全面建立耕地多功能價值顯化機制以及向農民的價值回歸機制,農民參與廣度和深度不夠[3]。
4 工作推進建議
4.1 強化頂層設計
執行耕地保護政策、推行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均涉及多層級、多主體,為加強耕地保護,可從頂層設計上把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作為新增耕地的主要來源,進而確定相關部門職責,調動各方參與積極性,加強規劃指引,強化目標考核及獎懲機制。疊加耕地保護、鄉村振興、生態保護修復以及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等政策,充分發揮相關政策紅利。
4.2 探索耕地保護目標下的全域整治模式
整治區應處理好土地資源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景觀建設、農業發展等整治目標要深度融合耕地保護目標中的數量、質量和生態要求,結合利益主體可獲利性,把耕地保護理念全過程貫穿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選址、立項、實施、后期管護,加強產學研協作,總結提升各地試點經驗,形成耕地保護目標下的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模式。
4.3 明確專項資金
設立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專項資金,帶動、引領涉農資金、社會資本共同投入綜合整治與耕地保護,減輕地方政府資金籌措、新增耕地面積壓力。把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中耕地保護的重點放在保護現有優質耕地、改造中低產田以及建設高標準農田上。對實施全域土地整治中耕地保護成績突出的地方政府予以專項資金獎勵,調動地方實施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顯化耕地復合功能的積極性。
4.4 規范調整永久基本農田
對于涉及永久基本農田調整的,要明確調整是否有利于破解整治區域的耕地碎片化問題,是否有利于推動產業向園區集中、居住向社區集中、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是否有利于耕地保護和土地集約節約、改善人居環境。
4.5 加大農民參與力度
村民是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直接受益者和重要參與主體,應加強耕地保護宣傳培訓,建立農民參與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機制,建立政府部門及村民之間的雙向溝通機制,豐富村民參與形式,讓村民真正有效參與,發揮主體作用,享受政策紅利。
5 結語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不失為助推鄉村振興、踐行生態文明,高度執行耕地保護的有力手段。雖然還處于試點階段,相關措施和建議有待下一步的科學論證,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