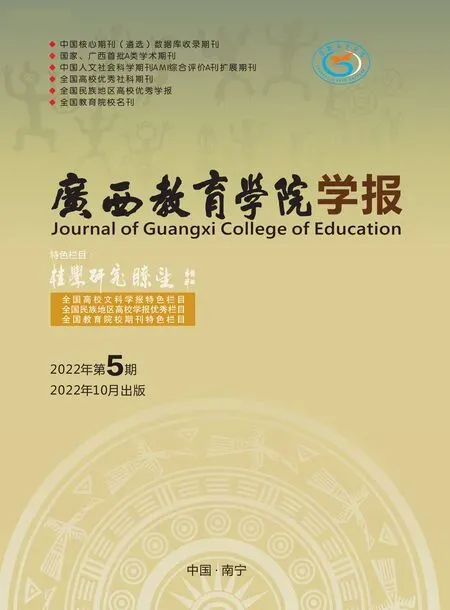懷特海的智慧教育觀及其對(duì)西方哲學(xué)史教學(xué)的啟示
汪文勇
(湖南文理學(xué)院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湖南 常德 415000)
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是歐洲19至20世紀(jì)杰出的思想家,在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哲學(xué)、教育學(xué)等方面都卓有建樹。他一生先后在英國和美國的大學(xué)從事教育和教育管理工作。他的教育思想深刻而富有創(chuàng)見,其中關(guān)于智慧教育的思想對(duì)于西方哲學(xué)史教學(xué)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懷特海的智慧教育觀
(一)培養(yǎng)智慧是教育的目的
懷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文中認(rèn)為,“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培養(yǎng)積極的智慧”[1]。那么,智慧到底是什么?懷特海認(rèn)為,“一個(gè)人只有習(xí)慣于擅長運(yùn)用大家都熟知的道理,才能說最終擁有了智慧”[1]45,而這也是智力培養(yǎng)的終極目的:“以恰當(dāng)?shù)乃季S解決相應(yīng)的問題”[1]33。由此可以看出,智慧是與知識(shí)相關(guān)的。一方面知識(shí)的學(xué)習(xí)是教育的一個(gè)重要的目標(biāo),沒有知識(shí)的基礎(chǔ),一個(gè)人很難有智慧;但另一方面,一個(gè)人雖然可以獲得知識(shí),但可能仍然沒有智慧,“知識(shí)的要義就在于知識(shí)的運(yùn)用,表現(xiàn)為我們的靈活掌握,體現(xiàn)在智慧的光芒之中”[1]38。因此,智慧還關(guān)系著“知識(shí)的運(yùn)用、問題的解決、經(jīng)驗(yàn)的升華,智慧是對(duì)知識(shí)的掌控”[1]36,簡而言之,智慧主宰知識(shí),智慧是掌握知識(shí)的方式。
對(duì)于懷特海來說,教育的目的并不僅是為了傳授知識(shí),傳授知識(shí)的目的也并不是為了純粹地通過考試。教育的規(guī)律、教育的核心、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們掌握怎樣運(yùn)用知識(shí)的藝術(shù)”[1]6,而所謂的知識(shí)的應(yīng)用,是指“把知識(shí)與生活事件聯(lián)系起來,這關(guān)聯(lián)著我們的感覺、知覺、希望、欲望和能調(diào)節(jié)思想的精神活動(dòng),這些事件構(gòu)成了我們的生活”[1]4。由此可見,教育并不是為了知識(shí)而知識(shí),知識(shí)是要面向生活而運(yùn)用的,是與生活中的各種事件、經(jīng)歷、活動(dòng)息息相關(guān)的。
(二)培養(yǎng)智慧的教育要面向生活
懷特海說,“教育只有一個(gè)主題,那就是豐富多彩的生活本身”[1]8。“教育就是引導(dǎo)個(gè)體去認(rèn)識(shí)生活的藝術(shù)。所謂掌握生活的藝術(shù),就是當(dāng)一個(gè)人面對(duì)生活的真實(shí)情境的時(shí)候,他能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潛能,靈活采用各種方式,熟練解決所遇到的種種問題。”[1]47知識(shí)也并不只是與記憶、智力相關(guān),而且與在應(yīng)用過程中的感知覺、情感欲望、精神意志等相關(guān)。所以,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理論知識(shí)必須是面向?qū)嶋H生活的,應(yīng)該服務(wù)于讓學(xué)生更好地理解、體驗(yàn)、發(fā)現(xiàn)生活,具有“重要的應(yīng)用價(jià)值”[1]7,只有這樣才能防止知識(shí)變得僵化。因?yàn)槲覀儾皇堑却竽X準(zhǔn)備好了所有的知識(shí)和能力再去面對(duì)生活的挑戰(zhàn)。與此相反,人的大腦是不斷地對(duì)外界的刺激作出相應(yīng)的精細(xì)、敏銳、永無休止的反應(yīng),是在不斷地成長的。所以培養(yǎng)智慧的教育總是要面向?qū)W生的實(shí)際生活,引導(dǎo)學(xué)生在生活體驗(yàn)中進(jìn)行思考與探索。如果這種教育是教授知識(shí),那么必須把知識(shí)放到一個(gè)有機(jī)聯(lián)系的知識(shí)整體和課程體系中去,激發(fā)學(xué)生的興趣,讓學(xué)生理解知識(shí)的系統(tǒng)性和在生活中的應(yīng)用價(jià)值;如果是傳授思想,那么思想對(duì)于學(xué)生的潛在價(jià)值和對(duì)于生活的意義也必須得到展現(xiàn);同樣如果要訓(xùn)練學(xué)生的某種能力,那么這種能力也必須能在生活實(shí)踐中得到鍛煉。教育不是為生活準(zhǔn)備良好的工具,教育本身就應(yīng)該是豐富多彩的生活的一部分,否則教育就會(huì)退化成一種孤立的、碎片化的、無意義的知識(shí),扼殺學(xué)生的活力和興趣。
(三)培養(yǎng)智慧以人的主動(dòng)性為基礎(chǔ)
在懷特海看來,不管是教授知識(shí)、傳授思想,還是培養(yǎng)能力,都必須關(guān)注人的大腦活動(dòng)的主動(dòng)性。懷特海認(rèn)為,傳統(tǒng)的把人的大腦比作為被動(dòng)的工具的觀點(diǎn)是“最致命、最錯(cuò)誤、最危險(xiǎn)的觀點(diǎn)之一”[1]7,因?yàn)槿绻麑W(xué)生的大腦只是接收知識(shí),而不去應(yīng)用、驗(yàn)證,只是讓學(xué)生死記硬背應(yīng)付考試,那只能扼殺了學(xué)生的興趣和活力,養(yǎng)成一種“惰性思維”。所謂惰性思維就是“只是通過大腦去接收某些觀點(diǎn),而不去應(yīng)用、驗(yàn)證或與其他新事物有機(jī)地融合起來”[1]2。惰性思維在教育活動(dòng)中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輕則讓學(xué)生感覺學(xué)習(xí)枯燥乏味,無法激發(fā)學(xué)生的興趣和活力,重則會(huì)影響整個(gè)民族教育的成敗,屆時(shí)“未經(jīng)良好教育的民族將不得不聽候命運(yùn)的裁判”[1]18。從懷特海的哲學(xué)思想來看,他的哲學(xué)實(shí)際上是一種機(jī)體哲學(xué),把事物看成是具有主體性、創(chuàng)造性、選擇性的有機(jī)體,這個(gè)有機(jī)體是一個(gè)關(guān)系性的存在物,一切機(jī)體都在經(jīng)驗(yàn)世界、感受世界、領(lǐng)悟世界、攝入世界,而這經(jīng)驗(yàn)世界的過程,同時(shí)是機(jī)體創(chuàng)造性生成和發(fā)展的過程,機(jī)體的“存在”(being)就是由它的“生成”(becoming)構(gòu)成的。作為教育過程中的主體之一,學(xué)生理所當(dāng)然是一個(gè)具有能動(dòng)性和主動(dòng)性的機(jī)體,這個(gè)機(jī)體會(huì)自主地根據(jù)自身的條件去吸收和掌握所需要的知識(shí),在這個(gè)過程中不斷地成長和發(fā)展。所以,在教育的過程中,教師要發(fā)揮學(xué)生的主觀能動(dòng)性,讓學(xué)生主動(dòng)思考、理解、發(fā)現(xiàn)、拓展、體悟、發(fā)展,而不是把學(xué)生當(dāng)作盲目、被動(dòng)、空洞、一成不變的容器,灌輸和強(qiáng)加給他們不感興趣的東西。所以,懷特海說:“學(xué)生的心智是一個(gè)不斷發(fā)展的有機(jī)體,不是像一個(gè)空匣子那樣可以隨隨便便地收納什么新知識(shí)。”[1]36教育的過程類似于生物體吸收營養(yǎng)的過程,美味可口的食物才會(huì)讓人胃口大開,激發(fā)進(jìn)食的興趣。
(四)培養(yǎng)智慧就是培養(yǎng)一種風(fēng)格
懷特海認(rèn)為,風(fēng)格是教育素養(yǎng)中最重要、最有用的一部分,所以在教育中應(yīng)該培育風(fēng)格意識(shí),這種意識(shí)被懷特海視為最本真的思想素養(yǎng)。他說,“所謂風(fēng)格意識(shí)是一種審美意識(shí),是對(duì)所遇事物的精彩之處的不由自主的、發(fā)自內(nèi)心的欣賞。”[1]15風(fēng)格意識(shí)是一種審美意識(shí),體現(xiàn)了懷特海對(duì)于美及審美的重視。根據(jù)懷特海的過程哲學(xué)的觀點(diǎn),審美價(jià)值是比邏輯理性更高的因素:“邏輯諧和在宇宙中是作為一種無可變易的必然性而存在的,但審美的諧和則在宇宙間作為一種生動(dòng)的理想而存在著,并把宇宙走向更細(xì)膩、更微妙的事物所經(jīng)歷的殘缺過程融合起來。”[2]懷特海宣稱,最好把人類和世界的歷史都描述為對(duì)美的追求。教育就是要追求真善美,求真和審美不是相互獨(dú)立、各不相關(guān)的,真的事實(shí)為美的價(jià)值提供了可能性,而作為價(jià)值的美為事實(shí)的真提供了意義。在懷特海看來,真和美在根本上具有同一性,真比假更有助于美的表現(xiàn),同樣美也可以成為真的內(nèi)在因素之一,越真的越可能具有美感。反過來看,追求美必定也會(huì)憎惡和排斥假惡丑。所以,懷特海說,具有一定風(fēng)格的管理者會(huì)憎惡浪費(fèi),具有一定風(fēng)格的工程師會(huì)節(jié)約材料,“風(fēng)格是智慧的終極德性”[3]。教育要培養(yǎng)智慧就是要培養(yǎng)建立在真和善的基礎(chǔ)之上的、對(duì)于美的欣賞和追求的境界,是在真和善的基礎(chǔ)上所達(dá)到的更高境界,這也是不斷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
二、懷特海的智慧教育觀對(duì)西方哲學(xué)史教學(xué)的啟示
(一)西方哲學(xué)史教學(xué)要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智慧
由于西方哲學(xué)史覆蓋時(shí)間長、流派多、人物多、內(nèi)容博雜,具有較強(qiáng)的思辨性、理論性、抽象性,同時(shí)每一個(gè)重要的知識(shí)點(diǎn)和重要人物的關(guān)鍵思想的闡釋都是經(jīng)過極度精簡,有一定的模糊性和非直觀性,離學(xué)生的親身體驗(yàn)和現(xiàn)實(shí)生活有一定的距離,學(xué)生理解起來有一定難度。如果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僅僅停留在具體知識(shí)點(diǎn)的傳授和識(shí)記,學(xué)生很快就會(huì)因?yàn)榛逎橄蟮膬?nèi)容和枯燥乏味的學(xué)習(xí)過程而產(chǎn)生畏難情緒和飄浮心理,教學(xué)效果難以保證。因此,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必須回歸哲學(xué)的本性,也就是哲學(xué)是一門“愛智慧”的學(xué)問,是對(duì)智慧的追求和熱愛。這種智慧不是生活中的小聰明和小計(jì)謀,而是對(duì)有關(guān)世界、社會(huì)、人生的終極性問題的根本性的思索和回應(yīng),是“關(guān)于人的存在方式及其與世界關(guān)系的反思”[4]。這種智慧的培養(yǎng)固然要以知識(shí)的習(xí)得為基礎(chǔ),但又不等于現(xiàn)成的知識(shí)。智慧體現(xiàn)在對(duì)知識(shí)的運(yùn)用上,是要在反思性、批判性和探索性的學(xué)習(xí)過程中,自己去回答人生在世的根本性問題,自己去獲得世界的真理、社會(huì)的真相、人生的真義。這種回答除了理論層面的意義,不可避免地涉入個(gè)人的生存,是為了給自己提供一個(gè)安身立命之本,為生命支起一個(gè)最高的支撐點(diǎn),構(gòu)建一個(gè)能夠詩意般棲居的生活方式。
(二)西方哲學(xué)史教學(xué)要立足于學(xué)生的生活世界
現(xiàn)當(dāng)代,作為時(shí)代精神精華的哲學(xué)越來越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生活和社會(huì)實(shí)踐,在某種意義上,哲學(xué)不再只是一門抽象的理論學(xué)科,而是一種作為生活方式和實(shí)踐方式的哲學(xué)[5]。因此,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也要立足于學(xué)生的生活世界。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西方哲學(xué)史教學(xué)內(nèi)容較多、理論性較強(qiáng),如果只是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脫離現(xiàn)實(shí)生活,沒有現(xiàn)實(shí)針對(duì)性,學(xué)生學(xué)習(xí)和接受起來就會(huì)存在一定的困難和抵觸情緒。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要針對(duì)學(xué)生的思想實(shí)際,通過理論聯(lián)系實(shí)際,結(jié)合與學(xué)生密切聯(lián)系的生動(dòng)實(shí)例,從學(xué)生的生活世界的各種經(jīng)驗(yàn)和經(jīng)歷來闡述各個(gè)思想流派和哲學(xué)家的思想。講授的內(nèi)容不能貪多求全,要有選擇性地針對(duì)教材中的重點(diǎn)、難點(diǎn)和疑點(diǎn),結(jié)合典型實(shí)例講解,使抽象的哲學(xué)概念形象化,使深?yuàn)W的理論通俗化,做到深入淺出,舉一反三,由點(diǎn)及面,主次突出。只有這樣,才能使學(xué)生從自己的親身體驗(yàn)來真正體會(huì)和領(lǐng)悟教學(xué)內(nèi)容,使理論世界與學(xué)生的生活世界真正融合起來。正如懷特海所說,“過去的知識(shí)唯一的用處就是武裝我們以應(yīng)對(duì)現(xiàn)在”[1]3,西方哲學(xué)史所涉及的理論知識(shí)應(yīng)當(dāng)在教學(xué)過程中,讓學(xué)生根據(jù)自己的實(shí)際重新生成情境化、過程化、本土化、個(gè)性化的知識(shí)用來解決學(xué)生自己在世界觀、人生觀、價(jià)值觀等方面所面臨的實(shí)際問題和困惑。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是要開拓學(xué)生的知識(shí)視野,塑造多樣的思維方式,培養(yǎng)學(xué)生健全的理性精神和豐富的人文素養(yǎng),使其熱愛生活,悅納自己,讓人成為人,成為全面的人,自由的人。
(三)西方哲學(xué)史教學(xué)要激發(fā)學(xué)生的主動(dòng)性
“哲學(xué)本質(zhì)上不是一種知識(shí)體系,而是系統(tǒng)的反思性批判性思維活動(dòng)”[6],這在西方哲學(xué)史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所以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不能搞單向的知識(shí)灌輸和一味地死記硬背,這樣的做法只是把學(xué)生當(dāng)作接受知識(shí)的容器和考試的工具,懷特海認(rèn)為這是非常錯(cuò)誤和危險(xiǎn)的做法,會(huì)形成他所批評(píng)的惰性思維。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在課堂上要求特別注意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的主動(dòng)性,及時(shí)找到學(xué)生關(guān)心的難點(diǎn)和興趣點(diǎn),發(fā)動(dòng)學(xué)生積極參與到課堂中來,以專題研討、課堂辯論、自主講課、案例式教學(xué)、論辯式對(duì)話等形式,盡可能創(chuàng)造師生雙向交流的、積極而自由的氛圍,“積極而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思維習(xí)慣只會(huì)在比較自由的氛圍中產(chǎn)生”[1]38。通過啟發(fā)式教學(xué)給學(xué)生留下思維空間,讓他們獨(dú)立思考,自主發(fā)現(xiàn)真理,自我生成意義,自己得出相關(guān)結(jié)論。這樣有利于提高學(xué)生的思維能力,同時(shí)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主動(dòng)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在這個(gè)過程中,還要鼓勵(lì)學(xué)生勇于懷疑和批判既有觀點(diǎn)和思想,鍛煉和培養(yǎng)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發(fā)現(xiàn)、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回歸到反思性、批判性的哲學(xué)思維本質(zhì)。
(四)西方哲學(xué)史教學(xué)要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價(jià)值感
哲學(xué)是理性的活動(dòng),表面上看,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似乎更多地只涉及學(xué)生的理性精神的培養(yǎng)。但從西方哲學(xué)的發(fā)展來看,價(jià)值也是哲學(xué)發(fā)展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懷特海對(duì)風(fēng)格意識(shí)培養(yǎng)的重視其實(shí)就是對(duì)價(jià)值感的重視,而審美意識(shí)不過只是其中的一種。這里的價(jià)值主要是指對(duì)善與惡、美與丑、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義等的判斷和認(rèn)同。懷特海認(rèn)為,“不管是科學(xué)、道德還是宗教,最終的驅(qū)動(dòng)力都是價(jià)值感和重要性”[1]48。這種價(jià)值感不斷地轉(zhuǎn)化成促使人及人類社會(huì)不斷進(jìn)步的力量,而其中最突出的力量就是美感,因?yàn)椤皩徝狼楦锌梢宰屛覀儷@得最為生動(dòng)形象的理解,而如果無視審美的價(jià)值,那么所有的思想認(rèn)識(shí)就會(huì)大打折扣”[1]49。懷特海在《意義的分析》一文中也說:“我自己的信念是,在現(xiàn)階段,因最受忽略而最富成果的起點(diǎn)是那個(gè)我們稱之為‘美學(xué)’的價(jià)值理論部分。我們對(duì)于人類藝術(shù)或自然美的價(jià)值的欣賞,我們對(duì)于強(qiáng)加于我們之上的明顯的粗俗和毀損的厭惡,所有這些經(jīng)驗(yàn)?zāi)J蕉急怀浞值爻橄螅瑥亩蔀橄鄬?duì)明顯的東西。而它們顯然揭示了事物的真正意義。”[7]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不能僅僅停留在專業(yè)知識(shí)的教育上,而是要對(duì)心智的所有方面都要重視。學(xué)生要成為和諧發(fā)展的人、全面發(fā)展的人、一個(gè)完善的人,必須有正確的價(jià)值觀,對(duì)哲學(xué)史上偉大的思想和理論體系以及其他人類文明成果的精華要有最基本的價(jià)值認(rèn)同和鑒賞力,對(duì)真善美要有強(qiáng)烈的認(rèn)同和追求,對(duì)假惡丑要有明確的摒棄和憎惡。這樣的學(xué)生才能是既有深刻智慧又有較高審美能力的人,才是一個(gè)健全的人,達(dá)到了自由境界的人。
三、結(jié)語
懷特海的智慧教育觀與他的過程哲學(xué)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他的過程哲學(xué)的實(shí)質(zhì)就是企圖在存在與生成、運(yùn)動(dòng)與靜止、推理與常識(shí)、邏輯與直覺、永恒與歷史、科學(xué)與人生、理智與感情、事實(shí)與價(jià)值之間取得某種平衡,從而調(diào)和現(xiàn)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史上分析哲學(xué)與大陸哲學(xué)的巨大分歧[8]。而他有關(guān)智慧教育的思想同樣也是為了處理一系列的矛盾關(guān)系,包括:專業(yè)知識(shí)與人文素養(yǎng)、知識(shí)與智慧、理論與應(yīng)用、事實(shí)與價(jià)值、理智與感情、技術(shù)與人文、能動(dòng)與被動(dòng)、灌輸與啟發(fā)、目的與手段、主體與環(huán)境、物質(zhì)主義與人文主義、自由與規(guī)訓(xùn)、浪漫與精確等。這些矛盾往往都涉及一些深刻的、根本性的哲學(xué)問題。在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過程中,不管是教書還是育人,不可避免地會(huì)涉及這些矛盾關(guān)系。怎么處理這些矛盾關(guān)系,沒有簡單的一刀切的方法,需要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至少這些矛盾關(guān)系的提出,能夠讓教師在西方哲學(xué)史的教學(xué)中進(jìn)一步思考智慧的教育和教育的智慧,能夠讓教師在教學(xué)中更全面地認(rèn)識(shí)相關(guān)的問題,以便在矛盾關(guān)系的不同方面保持必要的張力,而這需要教師以一種大智慧不斷地思辨、探索、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