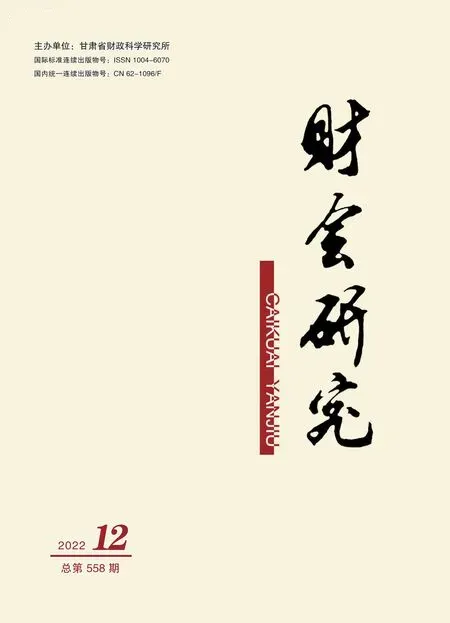雙重股權結構:文獻綜述與研究展望
■/ 唐貴鑫 黃 鈔
一、引言
雙重股權結構作為一項特殊的股權結構制度安排,對我國資本市場的高質量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進入21 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要求我國企業結合云計算、智能化與互聯網技術等方式不斷地進行轉型升級,為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源源不斷注入新活力。尤其是我國科創型導向的企業為此也提出了變革組織設計架構和控制權重向創始團隊傾斜的內在需求,因此已存在一百多年的雙重結構受到了眾多新興科創型企業的青睞。那么在此背景下,影響企業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的因素有哪些?企業實施后所產生的經濟后果有哪些?本文通過文獻梳理,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二、雙重股權結構制度背景與發展現狀
不同于傳統“同股同權”的股權結構模式,雙重股權結構又稱雙層股權結構、二元股權結構,是將給予部分股東同等的股票數量,但每股股票擁有更大的表決權或其他權利的一種股權架構。公司股票由此被分為了高投票權和低投票權股票兩類,雖每股的現金流權相等,但高投票權的股東能主導公司的日常經營。雙重股權結構最早興起是在1898年美國的國際白銀公司,在距今一百多年期間,理論界和實務界對該項股權結構眾說紛紜,對是否保留該制度存在著較大分歧。雙重股權結構一直活躍于西方證券交易市場,以美國、瑞典、加拿大等為代表國家,采用雙重股權結構的上市均受到了法律庇護,在美國資本市場上,采用雙重股權結構的上市公司占到了10%;以英國、法國為代表的國家,對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保持著中立態度,但仍有機構投資者對其有著抵觸心理;以韓國、德國為代表國家,明文規定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存在于資本市場當中;以香港和新加坡為代表的地區或新興國家,在為提高資本市場競爭力的多方面因素考慮下,為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敞開了大門。
我國最早于2018年香港證券交易所發布新規并允許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上市,次年6 月份,在科創板首次引入同股不同權的制度安排,允許國內上市公司采用雙重股權結構,滿足了國內優質高科技公司對雙重股權結構的迫切需求,緩解了其他資本市場帶來的競爭壓力。優刻得公司于2020年1月在科創板掛牌上市,成為我國滬深A股第一家以雙重股權結構上市的公司。近幾年,科創企業數量增長迅猛,采用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比例持續上升,截止2020 年末,共有104 家科創型公司采用雙重股權結構。
三、雙重股權結構驅動因素
從國外相關文獻發現影響公司選擇雙重股權結構有著諸多因素,包括公司屬性(Lehn et al,1990)、公司長遠創新發展戰略與人力資源投資(Taylor et al,1998)、研發費用投入(Jordan et al,2014)和公司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Banerjee et al,2013)等。從國內相關文獻研究來看,創始人異質性資本越高(杜媛,2020)和股東異質性越大(魏良益,2019),公司更傾向于以雙重股權結構上市。基于我國非正式制度背景下,將企業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契約集,從關系型合約視角研究發現公司具有越多的關系型合約,雙重股權結構越受到創始人或股東們的青睞(藍紫文等,2022)。
從公司層面出發,特別是在我國國有企業混改制背景之下,引入雙重股權結構有利于引進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外資等參與混改,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進而提升經營管理效率(張繼德等,2017)。因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有著獨有的特征,其對應也會做出相應的股權結構模式調整,企業處于創業階段時,因公司經營管理活動的大量資金需求,需額外從資本市場獲取股權融資,引進雙重股權結構旨在保護創始人或管理層權益,防止其控制權被稀釋,避免惡意收購(DeAngelo& Rice,1983;DeAngelo& DeAngelo,1985),緩解公司面臨著資金短缺的限制約束,為企業長期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從個人層面出發,創始人為了獲得個人滿足感(Gompers et al,2010)和保證自身職位安全(Chemmmanur& Jiao,2012),也會考慮選擇雙層股權制度。鄭志剛等(2016)通過阿里巴巴的案例研究發現該公司選擇投票權配置權重向創業團隊傾斜的“同股不同權”股權模式架構,有助于將股東與創業團隊之間利益捆綁,促使短期雇傭合約關系向長期合作伙伴關系發展,最大限度地激發創始團隊的創新性思維(Anand,2018),實現更加專業化、深度化和職業化的分工協作,提高管理層經營決策效率。由此,引入雙重股權結構能夠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從而提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魏良益,2019)。
從資本市場層面出發,早在1898年,美國國際白銀公司首次將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相分離,把股票分成了高投票權和低投票權的普通股,為上市公司實施雙重股權結構開創了先河。隨后我國香港證券交易所在2018年允許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赴港上市,直至2019年科創板開板,允許特殊表決權機制的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允許上市,逐步實現了我國內地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接軌,避免紅利長期流失在外,進一步促進我國資本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我國資本市場有序、健康的高質量發展。
四、雙重股權結構經濟后果
(一)企業創新
石曉軍和王驁然(2017)以外部環境為視角,使用互聯網上市公司數據,考察了外部投資者的短期業績敏感性對雙股制企業的創新有著促進作用,而且這種差異性特征存在于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鄭志剛等(2021)則以2009-2018 年我國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業為樣本,研究表明實施了雙重股權結構的上市公司其研發投入明顯增加,并探討雙重股權結構通過降低高管非正常原因離職的可能性、激勵企業創始人擔任CEO 及鼓勵持續且穩定的人力資本投入,從而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同時在我國資本市場缺乏有力的外部監督機制的情況下,為了彌補外部監督的不足,需設計出與雙重股權結構配套的內部監督機制,因此日落條款作為一項“隱性約束”加入到公司章程當中,能夠加強對高投票權股東機會主義行為的內部監督約束,使其高股票權股東與低股票權股東之間的利益競爭關系得以均衡(沈朝暉,2020)。所以相較于未引入日落條款的企業,實施了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的研發投入越高。此外,雙重股權結構實施的企業能穩固管理團隊在企業中的核心地位不被動搖,激勵出管理層始終保持不斷求索進取的鉆研精神,埋頭耕耘于企業業務模式構建,減少因低級決策失敗行為而被解雇的風險概率。在企業創新活動過程中,需大量資金投入,而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能從多渠道方式進行外部融資,緩解企業創新所面臨的融資約束(周開國等,2017;郝向超等,2018),提高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況且在當今資本市場經濟不景氣和市場競爭壓力激烈的情況下,經理人會專注于長期市場前景,避免為實現企業短期經營目標而采取短視行為(Jordan et al,2016;Bebchuk & Kastiel,2017),從而有助于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水平(Chemmanur & Jiao,2012),更加提高企業在行業中的核心競爭力。
(二)盈余管理
根據自利人假設,管理者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盈余管理成為了管理者謀求私利的手段之一。在雙重股權結構下,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相分離程度加大,兩者分離程度影響了盈余信息質量,其背離程度越大,企業表現出的盈余會計信息質量越差(朱松,2006)。陳晶璞和鄭維維(2020)研究發現擁有高表決權的管理層對企業盈余管理程度影響更為明顯。在該股權結構下,管理層通過擁有更少的股票權掌握著更多的表決權,導致控制權過于集中,在利益分配上,管理者會利用會計估計變更及會計政策運用的相關知識來操縱利潤,造成濫用權力的風險(Jordan Bradfor et al,2014),甚至犧牲企業價值(Gomes et al,2001),以致滿足自身利益需求,達到短期業績考核目標。喻凱和許蕊(2018)進一步地把盈余管理細分為了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和歸類變更盈余管理,實證檢驗發現,相對于單一股權結構而言,采用雙重股權結構制度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在對股權結構不同進行分組后,發現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更有可能從事歸類變更盈余管理的操縱。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內部管理者為了追求控制權帶來的私利,會通過盈余管理行為來披露有利于自身偏好的會計信息,向外界傳遞出企業虛假的財務信息,降低了盈余信息披露的可靠性(Wong,2002)。也有相關文獻研究表明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所披露的會計信息未能及時反映企業當前的經營狀況及制定的發展戰略(Khurana et al,2013),因此管理層以信息不對稱為便實施盈余管理行為(Ting Li et al,2017)。以上行為不僅損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讓外部投資者利益蒙損,甚至會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質量。
(三)企業績效
雙重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會產生消極或積極影響作用,學術界還未形成一致的結論。根據委托代理理論,企業股東與管理者的目標都是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管理者作為股東在公司的代理人,對企業有著絕對的經營權,此時管理者可能利用信息優勢為謀求更高的薪資報酬和職位晉升,由此提高了代理成本。在雙重股權結構企業中,擁有高投票權的股東往往在企業中擔任高管,以代理人的身份參與到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之中,通過持有多數表決權股票掌握著企業控制權,使其兩權分離程度越大,出現內部人控制現象,以極小代價的資本來運作企業的絕大部分資金流轉,風險責任與利益不對等,這更有可能導致代理費用增加。(張繼德和陳昌彧,2017)。此種情況下,擁有多數表決權的股東或管理者很有可能利用職務之便謀求更對利益,比如增加在職消費、專用性資產等,這些隱蔽性方式增強了塹壕防御效應(McGuire et al,2014),導致企業資源得不到合理優化配置,企業績效下降(Andrade et al,2017)。相反,基于雙重關系理論中的利益趨同效應,所有者通過一定數量的股票作為激勵機制使管理者與股東們的利益趨同,避免了管理者短期行為,也留住了擁有異質性資本的創始人繼續投資企業未來發展,尤其是當創始人作為管理者經營企業時,會為了企業長足發展而源源不斷注入新動力,從而提高企業績效(陸宇建,2016)。根據管家理論,管理者是以實現自我價值為內在機理,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滿足,有著集體主義和合作主義精神,對企業內部組織有更強的認同感,促進團隊成員合作共贏,共同創造企業價值。管家理論認為管理者充當管家這一角色,為了造就企業,實現自我價值最大化的同時也與股東目標相一致,他們會付出稀缺的知識資本,以自身努力經營好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提高企業績效與價值。
(四)審計定價
雙重股權結構在西方市場已盛行百年有余,西方學者也在早先研究了關于雙重股權結構與審計定價之間的關系。Fan & Wong(2005)以東亞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控制權與現金流權背離程度越大,審計收費越高。Khalil et al(2008)則利用加拿大實施了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為樣本,同樣發現兩權相分離程度越大,審計收費越多。但Lobanova et al(2020)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該文以美國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兩權分離程度與審計收費呈顯著負向關系。隨著雙重股權結構在2019 年登上我國資本市場的舞臺,有不少學者關注到了雙股制對審計定價的影響。其中王燁(2022)研究發現,相比于單一股權結構,我國實施了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會顯著提高審計收費標準。在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中,擁有高表決權的股東往往擔任企業的管理者掌控者企業的日常運營,憑借其更大的控制權和信息資源優勢,很可能滿足于私有利益,引起內部人與內外部投資者代理問題產生和代理成本增加(王驁然和胡波,2018)。除此,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內部人侵蝕企業財富的動機更強,謀取更高的貨幣性薪酬(杜媛等,2021)。因此內部人為了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行為,會操縱企業應計利潤,減少相關信息披露(Khurana et al,2013),造成信息不對稱。并且在雙重股權結構下,中小股東的內部監督能力遭到削弱,內部控制機制無法發揮有效作用,因此審計師在審計工作中會降低對內部控制的依賴程度,增加了進一步的實質性程序,從而審計成本增加。另外,由于信息披露減少和信息不對稱,處于信息劣勢的外部審計師只有通過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去獲取充分且適當的審計證據,及時發現企業存在的較高重大錯報風險,從而進一步擴大實施測試范圍,實施更為嚴格的審計程序以減低檢查風險,最后得出合理的審計意見,為此審計師必然會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根據審計保險理論,當投資者利用了審計師出具的不合理審計意見后遭受損失的,向法院提起訴訟,一旦存在錯報,審計師將面臨相應的賠償責任。尤其是在新《證券法》出臺以后,明確了審計師連帶責任范圍,加大了對審計師的懲罰力度。因此審計師為了彌補較高的訴訟風險,將會通過提高審計收費來補償其承擔的更多風險溢價。
(五)股價高估
在高低投票權股票引發控制權與現金流權高度分離的情況下,Forst et al(2019)研究發現持有高投票權股票的管理層更加注重個人利益需求,有強烈的動機從事機會主義行為,忽視對企業的責任感。為了使私欲得到滿足,他們通常會對壞消息進行封鎖和故意隱瞞,提供企業虛假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不為外部投資者所熟知,因此對壞消息的“捂盤”行為會造成企業股價被高估,令投資者利益受到損害。Francis et al(2005)研究發現,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較少公布企業私有信息,并且會發布滿足自身利益偏好的報告。由于高投票權的管理層擁有更大的控制權,被董事會替換的概率較小,承擔的負面消息的壓力也較小。所以他們會選擇性地披露信息,用于掩蓋自身攫取利益的行為,并對外隱藏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況(Li & Zaiats,2017)。楊菁菁等(2022)考察了雙重股權結構及兩權分離程度對公司股價的影響,發現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造成了兩權的高度分離,加劇了代理沖突,導致管理層發生“捂盤”行為,顯著地提高了公司股價。進一步發現,基于機構投資者的監督、信息優勢和賣空供給效應,機構持股能夠明顯地緩解雙重股權結構對公司股價高估的正向效應。
五、研究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通過梳理現有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目前學者們主要從公司層面、個人層面以及資本市場層面三個方面探討了雙重股權結構的驅動因素;從企業創新、盈余管理、企業績效、審計定價和股價高估五個方面研究了雙重股權結構所帶來的經濟后果。對于雙重股權結構驅動因素的研究視角較為全面,而對企業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產生的經濟后果還有待展開及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結合我國國情和制度背景下去思考。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我國才允許采用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在證券交易所上市。隨著我國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在我國資本市場上活躍起來,引起的相關問題定會成為未來研究的重點方向。
(二)展望
基于現有文獻,未來關于雙重股權結構的研究可以從以下方面展開:就驅動因素而言,雖然雙重股權結構早已存在,但進入我國資本市場正經初期階段,在后期階段國家針對雙重股權結構的政策性法律法規等方面的修改或出臺,那么企業實施雙重股權結構時將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具體影響會是關注的重點;其次,隨著雙重股權結構在我國企業中逐步興起,相關的經濟后果也會隨之浮現。可以結合新《證券法》的修訂內容來研究企業雙重股權結構制度,比如該法明確規定了要求企業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努力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不受侵犯,據此實施雙重股權結構的企業內部控制人嚴重削弱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行為得到有效遏制。此外,還可以基于我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企業投融資、公司治理、研發操縱、企業ESG表現、產權性質等多個方面細化具體的研究視角,從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視角研究企業實施雙重股權結構所帶來的經濟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