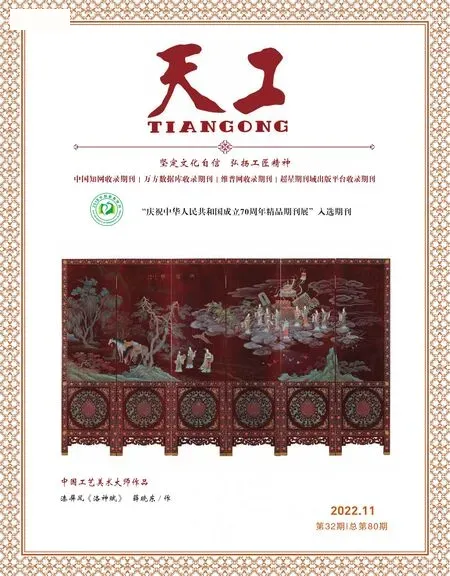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整理與研究
馮云浛 聊城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
一、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特色與概況
山東省運河區域的木版年畫是包括東昌府木版年畫、泰安木版年畫、魚臺木版年畫、滕州木版年畫的區域性年畫,種類多樣、歷史悠久,是人民喜聞樂見的一種藝術形式,反映了人們樸素的風俗和信仰,承載著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希冀,具有鄉土性和親民性。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產生、發展、興盛、衰落的過程中不斷積淀、創新,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風格特征。
在運河文化的滋養下,區域內年畫的風格都帶有一定的共性,如藝術特征上的線條粗獷有力、色彩鮮艷明亮、造型夸張雄威、構圖緊湊飽滿等;藝術題材上的門神類、神像類、喜慶吉祥類、神話傳說類、歷史故事人物類、演義小說類等;吉祥寓意上的福、祿、壽、喜、財等。除形式上的互融共通之外,各地木版年畫因各地風俗的不同,也存在不同的地域特色,主要體現在顏色差異與制作工藝上。
不同地區木版年畫的藝術特色與當地的審美情趣密不可分,而這種審美情趣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用色上,如東昌府木版年畫和泰安杜家莊木版年畫喜用紅、黃、綠、紫、黑等顏色,而魚臺木版年畫慣用丹青勾勒線條,整體給人帶來一種清新脫俗的美感,且畫面常用的是朱砂紅和雪花綠兩色,其他顏色則按照不同比例均衡分布,留白居多,各類顏色互相搭配,形成“紅為骨、綠為筋、黃藍搭配畫才鮮”的藝術風格。滕州木版年畫一般用大紅、粉紅、橘紅、橙綠、黃、黑六色套版,最多達七色。關于制作工藝,各地木版年畫制作流程大體相同,包括定稿、刻板、印刷、配色等環節。但各環節在具體的制作工藝中又存在差異性,如東昌府木版年畫創作的獨特之處是該類作品僅靠手工印制,后期無其他手繪輔助步驟。泰安木版年畫和魚臺木版年畫采用套印、半印半繪兩種形式,而滕州木版年畫則改變了之前傳統的一版一色印刷,采用了印制與手繪結合的方法。藝術形式的普遍性以及差異性的共通感,使得每個地區不僅有著藝術相似性,還有著獨特的地域特色。
2004年,隨著國家有序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山東省運河區域的木版年畫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新面貌、新角色重新走入民眾的現實生活。東昌府木版年畫于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泰安木版年畫于2008年入選泰安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魚臺木版年畫于2007年入選濟寧市第一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滕縣木版年畫于2015年入選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創新發展的根本基礎和不竭動力,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提高文化自信、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手段。雖然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自開展以來在政府的主導下已取得顯著成效,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每個人對美的理解不同,每個地區對美呈現形式的影響也有差別,從而使得民眾創造的傳統美術形式樣式浩繁,品類雜多”[1]。因此,我們應該探索多種形式的保護方式,多渠道進行探索創新,吸引多方力量參與其中,形成合力,創建各具特色且效果頗佳的保護模式。
二、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比較與發展
山東省運河區域的木版年畫種類多樣,百花齊放,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大致可分為神仙信仰、歷史故事、吉祥喜慶、花鳥蟲魚等幾類。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最經典的題材為門神,其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桃符,發展到唐代升華成了具有人格意義的神荼、郁壘畫像。每逢年節,當地民眾便將門神類神像貼于門上,用以驅邪辟鬼,衛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門神是中國民間最受民眾歡迎的保護神之一,也是民間藝人反復雕刻的經典題材。但又因所處地域的不同,各地對于門神的雕刻手法、表現技巧不盡相同。如東昌府木版年畫近代以來較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從而較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原汁原味的藝術風格。門神形象粗獷高大,人物頂天立地,人物造型生動形象且簡潔,有“天下第一門神”的美稱。泰安木版年畫的門神色彩較為鮮艷明亮、構圖飽滿,門神形象高大魁梧,有一種“穩如泰山”的氣質神態。魚臺木版年畫的門神更加側重于線條的運用,尤其是視覺對比下產生的線條的粗細、曲直、疏密、長短變化等,其線條時而細膩輕柔,時而遒勁有力,充滿了節奏感與韻律感。滕州木板年畫深受漢畫像石雕刻技法的影響,其門神形象粗獷古拙,線條剛勁挺拔,其旌旗上的“帥”字是正反印制,民眾認為正“帥”防外賊,反“帥”防家賊。此外,滕州民眾多認為,其當地所產的門神具有護衛家中財產的作用,因此也被尊稱為財神。
在傳統社會中,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民眾往往將一些本身解釋不了的奇怪現象看作鬼神的互滲,然后予以膜拜、祭祀,以祈求神靈庇護。隨著科學的進步,人們認知水平的提高,逐漸揭開原始崇拜神秘的面紗,鬼神論逐漸淡化,人們對于門神的信仰也逐漸弱化。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傳統的手工年畫漸漸被速度快、成本低、圖案樣式多的機器印刷所取代,人們的消費觀念、審美情趣的改變,都成為山東省運河區域的木版年畫發展的桎梏,從民眾日常生活的實用品演變為藝術品、收藏品,逐漸消失在大眾視線。但是就傳統文化保護而言,我們必須認識到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民間藝術形式,其背后有很大的文化價值和意義,其所蘊含的是超越社會變遷、維系情感交融的特殊紐帶,是保持民族文化連續性的血脈之一。因此,開展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有助于完善文化物象與區域文化研究,能夠為系統研究民俗物象、社會發展與運河文化的關聯互動提供借鑒,進一步完善運河文化資料庫的建設。同時,長期而持續的研究工作有利于探索其與區域社會文化經濟的變遷、地方文化創造之間的偶聯,闡釋山東省運河文化在當今社會建設中的精神特質與現實價值。
三、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傳承與保護
目前,從事泰安木版年畫的第六代傳承人王連陽先生、魚臺縣陶氏木版年畫第九代傳承人陶運航先生均已年過五旬,東昌府木版年畫第五代傳承人欒喜魁先生和滕州王樓木版年畫第十一代傳承人王振軍先生更是八十有余。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傳承方式主要有師徒傳授、家庭傳承和作坊傳承,傳承范圍、方式與受眾人群十分有限。傳承人從事木版年畫傳承的初衷不一,或出于對傳統藝術的熱愛,或將其作為貼補家用的方式,傳承的結果是延續了當地木版年畫的技藝,維系了該類藝術形式的延續,但個人的力量必然是有限的,保護傳承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還需要多方主體的參與,如政府、商界、新聞界等。政府應強化其主導責任,構建完善的民間藝術可持續生態系統傳承體系,實現文化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變。商界應堅守本心,在追求合法權益的同時,不擠壓傳承人的傳承空間并保證其經濟利益的獲得,自覺遵守、維護市場秩序;新聞界應利用多種媒介記錄、保存、傳播完整且真實的民間藝術,保障傳承人的話語表達,挖掘民間藝術背后蘊含的深刻內涵,向全社會樹立、闡釋正確的價值觀,加強社會認同感。
當下,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傳承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后繼乏人。目前,從事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傳承的人群普遍存在老齡化問題,因從事該行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并不理想,難以維持家用,導致青年缺乏對該手藝的學習興趣,形成了愿意教卻無人愿意學的窘境,后繼乏人甚至后繼無人的現象較為普遍。要想實現對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活態傳承,必須依靠傳承人,“傳承人是保護與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主體,沒有離開傳承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也沒有離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人”[2]。所以應及時采取合理有效的舉措,以完善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傳承機制。
首先,政府應加大對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保護力度,加大對保護傳承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在財政上的資金支持,結合當地情況和山東省運河區域木板年畫的發展現狀制定具體的條例細則。例如,2019年6月28日,廈門市第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了《廈門經濟特區鼓浪嶼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條例》。這項條例的頒布使鼓浪嶼文化遺產的保護更加規范、嚴格,明確的規章制度對于保護文化遺產也有切實的可操作性。其次,了解消費需求,大膽進行創新。文化企業嘗試開發年畫文化衍生品,如抱枕、文化T 恤、背包等。如起承文化公司以年畫為基點所創作的“一團和氣”背包,在保留了傳統元素的同時增加木版年畫作品的趣味性,實現了實用性與審美性的統一。還可以將木版年畫這種當地獨有的民俗文化與現代包裝設計相聯系,重視山東省運河區域木板年畫衍生視覺產品的制作,推動其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傳播。如第十一屆全運會會徽的設計,就是以民間年畫“四喜人”為創作基點,提取、歸納民俗文化的色彩搭配,創作其經典會徽。再次,可以將其與網絡技術相結合,利用電商平臺為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傳統工藝開辟新的經營渠道,如天津大學2019級面塑研培班的王俊鋒就利用線上網絡銷售平臺開設了淘寶店鋪(王子面塑工作室),宣傳和售賣自己的面塑作品,不僅獲得了經濟效益,還為面塑文化的宣傳增加了新路徑。在圍繞項目投入的同時,開辟以傳承人為中心的保護嘗試。文化單位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多種渠道進行傳播,組織開展相關年畫集體性活動,喚起手工藝人、民眾對于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藝術傳承的自覺意識。通過舉辦年畫展覽、茶話會、座談會、研討會等活動,如,2006年6月13日,在西安國際展覽中心舉辦“首屆全國木版年畫聯展”,參展成員為來自全國各地的木版年畫的代表傳承人,并同時開展了“中國木版年畫保護和發展座談會”,分析討論了木版年畫的生存現狀、保護傳承、發展前景等問題。掌握相同類屬技藝的傳承人通過交流不僅提升了自身技藝,還更新了自身理念,培養了文化認同意識,提升了文化自信。除此之外,傳承人現場演示木版年畫的刻版、印制工藝,參展觀眾也可以現場近距離地親身體驗、感受傳統木版年畫制作技藝的藝術魅力。
除此之外,還應提倡“非遺+教育”模式,將非遺融入現代教育體系,推動非遺自身的傳承與發展。將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引入校本課程,聘請校外專家、民間藝人到校授課,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培養青年一代積極參與到年畫的傳承中。例如,霓南義校就結合溫州傳統文化工藝甌塑開設了當地的校本課程甌塑漁民畫,讓非遺走進課堂,激發下一代的從事熱情,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學校教育中的活性傳承。還可以通過傾斜性政策組織專題培訓、提供相應平臺,鼓勵學生學習相關技能,成為高素質的新一代傳承人。例如,2016年6月13日,文化部在濟南舉辦“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木版年畫第二期培訓班”,秉承“強基礎、增學養、拓眼界”的原則,推動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讓年畫以多種形式、多種角色、多種渠道成為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地方政府、文化企業以及文化單位等多方主體為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提供合了理化的支持。
保護木版年畫,并不是讓其與現實的社會生產脫節,“應該是在不違背和破壞其核心價值和核心技藝的情況下,將其引入生產領域,讓更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當代人的生活中去,讓現代人享受祖先留給我們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使之在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得到積極保護”[3]。木版年畫在傳統社會的傳承是靠著作坊式的生產來實現的,各生產環節應相互協調,生成互惠圖景,使得參與其中的各方都得到相應的收益,從而促成該技藝千百年的傳承發展。
四、結語
山東省運河區域木版年畫歷史悠久,是我國年畫發展的標本,是運河區域農耕社會文化發展的縮影,也是進行傳統教育的生動教材。當下,木版年畫逐漸淡出民眾視線,民俗寓意逐漸減弱,更多的是變成了宣揚當下社會文化的載體,其自身的傳承現狀也不容樂觀。開展相應的整理與研究,讓民眾認識到其重要性,提升傳承保護意識,也為山東省運河區域非遺保護提供決策咨詢,促進相關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為同類區域文化研究提供可資參考的保護模式和技術藍本。運用多種形式拓展其原本狹小的生存空間,既可以豐富與提升當代社會的審美趨向,又能更大限度地滿足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山東省濟寧市老年大學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