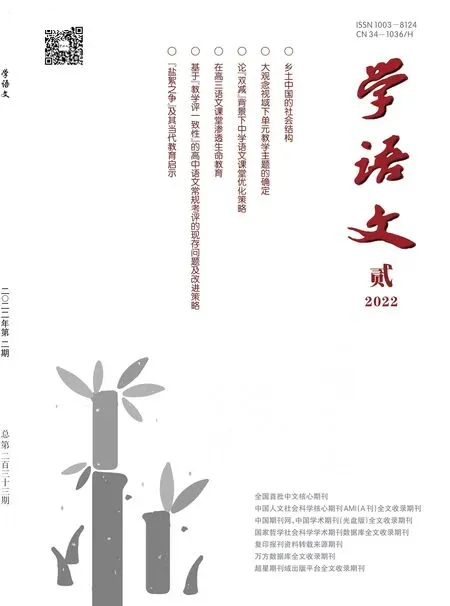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
□ 陳文忠
費孝通談《鄉土中國》內容時說:“在第一部分,我分析了社會關系的一般模式,認為中國是‘差序格局’(親屬的模式),西方是‘團體格局’(成員平等)。從這一差異性出發,我發展出中西道德模式上的不同:(西方)普遍的愛與(東方)系于私人地位的偏愛。”[1]這段話內涵豐富,在對比中告訴我們,《差序格局》和《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前后相聯,著重分析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模式和道德模式,是全書“第一部分”的核心篇章。
第二章“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由《差序結構》和《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兩篇構成,談論密切相關的兩個問題,即“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模式”和與之相聯系的“鄉土中國的社會道德模式”。“差序結構”和“維系著私人的道德”,這也是作為“熟人社會”的鄉土中國,不同于“陌生人社會”的兩大特點。
一、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差序格局》的論述思路
不同于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差序格局”。何謂“差序格局”?它有哪些特點?它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篇圍繞這些問題逐層展開。全文20段,可分6個層次。
1.“私”與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1—3段)
《鄉土本色》從鄉下人“愚的毛病”說起,本篇從鄉下佬“私的毛病”說起,都采用描述現象引出問題的方式;這也是作者“用散文筆法寫人類學著作”的特色。當時有的“鄉村工作者”認定“愚貪弱私”是鄉下人的“罪惡”,于是以傳教精神去“教育”鄉下人。費孝通則與之不同,他把“鄉村工作者”居高臨下式的“價值判斷”,轉化為從基層上去看的“事實判斷”,從社會學角度指出:“這里所謂‘私’的問題卻是個群己、人我的界線怎樣劃法的問題”;中國傳統劃法不同于西方,因之“要討論私的問題就得把整個社會結構的格局提出來考慮”。于是進入中西社會結構格局的比較分析,以探尋“私”的社會學根源。
2.西方社會成員平等的團體格局(4—5段)
何謂“團體格局”?作者沒有下定義,而以捆柴為喻,描述了團體格局的特征:一個團體由若干人組成;團體內外的界線是清楚的;團體中人的關系是相同的,如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均事先規定;與“捆柴”不同的是,一個人可以參加幾個團體。然后,以最基本的社會團體“家庭”為例,指出“家庭在西方是一個界限分明的團體”,家庭成員只包括“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未成年的孩子”。概言之,“團體格局”是西方“陌生人社會”的結構模式,每個團體中的人,關系相同,地位相等,享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團體內外界線分明。
3.鄉土中國親屬關系的差序格局(6—10段)
作者論述“差序格局”同樣沒有下定義,而是從“伸縮自如”的中國人的“家”說起,然后以“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為喻,對“差序格局”作了形象化描述:
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同心圓波紋”是“差序格局”的精妙比喻。然后,舉例說明“差序格局”在中國社會中的體現:一是“親屬關系”。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系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么一個以親屬關系布出去的網,但是沒有一個網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二是“地緣關系”。鄉土中國中地緣關系也是“同心圓波紋”,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為中心,劃出一個富于伸縮的社會圈子。西方界限分明的“團體格局”爭的是權力,中國伸縮自如的“差序格局”卻是攀關系、講交情。這一部分是全文重心。
4.差序格局與人倫綱紀(11—13段)
正面論述后,作者便從人倫綱紀和自我主義兩方面,進一步探尋“差序格局”的歷史文化淵源。首先,“差序格局”與傳統人倫綱紀是一致的。儒家最講究的是人倫。倫“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倫是有差等的綱紀、次序;“差序格局”就是“人倫差序”。“倫”的字源語義分析和《禮記·祭統》里所講的“十倫”,從不同角度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差序格局”是以“己”為中心“推”出去的。孔子注重的就是水紋波浪向外擴張的“推”字。在孔子看來,從己到家,由家到國,
5.差序格局與自我主義(14—16段)
其次,以“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奉行的是一種自我主義。傳統的自我主義不同于西方的個人主義。在個人主義下,一方面是平等觀念,一方面是憲法觀念。傳統的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在費孝通看來,自我主義不限于一毛不拔的楊朱,儒家也包括在內。二者的區別在于:楊朱忽略了自我主義的相對性和伸縮性;孔子則會推己及人,中心雖是自己,卻會依著需要而推廣或縮小。
6.差序格局與“私”的問題(17—20段)
明白了鄉土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就可以明白傳統社會中“私的問題”了。在以“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里,“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公式,而不是一種價值的判斷。在這種公式里,你說他私,他是不承認的。因為,“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這也是“差序格局”與“團體格局”的區別所在。經過這一番分析,“私的問題”的根源得到了學理解釋,簡單化批評,不免主觀。
最后,作者總結了鄉土中國“差序格局”的三個特點:
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因之,我們傳統社會里所有的社會道德也只在私人聯系中發生意義。
從社會關系、社會范圍到社會道德,概括了“差序格局”相互聯系的三個特點,總結前文,引出下文,由此轉入“鄉土中國社會道德模式”的論述。
二、鄉土中國的社會道德:《維系著私人的道德》的論述思路
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是以“己”為中心推延出去的“差序格局”,鄉土中國的社會道德則是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它不同于團體格局中的“普遍的愛”的道德體系。圍繞這個中心,全篇中西比較,逐層分析。全文16段,可分5個層次。
1.社會結構格局的差別引起不同的道德觀念(1—2段)
開篇兩段是全文引言,從中西社會格局的形成,談到道德觀念與社會格局的關系。“團體格局”是從原始“部落”形態中傳下來的。部落形態的游牧經濟,“團體”是生活的前提。中國是安居的鄉土社會,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和別人發生關系是次要的。因之,鄉土中國便采取了以己為中心推延出去的“差序格局”。這是對上文的補充,也借以引起下文。社會結構格局的差別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觀念。因為,道德觀念是在社會里生活的人自覺應當遵守社會行為規范的信念。它的內容是人和人關系的行為規范,“是依著該社會的格局而決定”。這是總論,下面分述。
2.“團體格局”中是“普遍的愛”的道德(3—7段)
從社會格局的差異性出發,費孝通“發展出中西道德模式上的不同:(西方)普遍的愛與(東方)系于私人地位的偏愛。”換言之,西方“團體格局”中的道德體系就是“普遍的愛”。這一部分可分四個層次。首先,“團體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觀念建筑在團體和個人的關系上。團體對個人的關系,就象征在神對信徒的關系中。其次,“團體格局”中的道德體系深受宗教觀念的影響。在象征著團體的神的觀念下派生出兩個重要觀念:平等和公道。再次,所謂“平等”,首先是指在“天父”面前人人平等,為之在基督教神話中親子間個別的和私人的聯系被否定了;進而在西方社會中發展出人人平等、天賦人權的觀念。在執行上帝或團體的意志時,牧師和官吏等“代理者”的權力,須由“受治者”的同意產生。最后,所謂“公道”,同樣首先指神對每個人的公道,人人都可分得神的一份愛;然后便在團體格局的道德體系中產生了權利的觀念。為了防止團體代理人濫用權力,又產生了憲法。從道德體系的宗教來源、平等和公道的“普遍的愛”,到道德觀念以及憲法制度,脈絡清晰。
3.“差序格局”中是維系著私人的道德(8—12段)
“差序格局”中的道德體系與之相反,在以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是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克己”“修身”是道德體系的出發點。首先,社會范圍從自己推出去的基本路線有兩條:一是親屬關系即親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二是朋友關系,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忠信。孝、悌、忠、信都是私人關系中的道德要素。其次,在差序格局中并沒有一個超乎私人關系的道德觀念。“仁”似乎是個超乎私人關系的道德觀念,但當孔子說明仁是什么時,卻又退到“克己復禮為仁”“恭寬信敏惠”這一套私人間的道德要素了。仁這個觀念只是邏輯上的總和,一切私人關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
4.“差序格局”中缺乏個人對于團體的道德要素(13—15)
在團體格局的社會中,公務,履行義務,是清楚明白的行為規范,中國傳統中是沒有的。“忠”的觀念與之相仿,實質并不如此。“忠”或解釋為“對人之誠”,和衷字相通,是由衷之意。忠字甚至不是君臣關系間的道德要素。君臣之間以“義”相結合。忠君并不是個人與團體的道德要素,依舊是對君私之間的關系。在公私的沖突里,團體道德的缺乏看得更清楚,即使負有政治責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間的道德。
5.“差序格局”中的道德標準不能超脫人倫差序(16—18)
經過以上比較分析,最后總結全文。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絡,它是一種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因此,傳統道德里不另找出一個普遍性的道德觀念來,所有的道德價值不超脫差序的人倫。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此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一邊痛罵貪污,一邊又為親屬的貪污諱隱,在差序社會里不覺得矛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一定要先問清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才決定拿什么標準。團體格局的“普遍的愛”類似墨家的“愛無差等”,和儒家的人倫差序正相反。
三、“差序格局”與“等差之愛”
《差序格局》是全書最富原創性的篇章,“差序格局”則是作者對中國社會學最著名的理論貢獻,也是中國社會學對世界社會學理論的最大貢獻。
學術著作是概念的體系。閱讀學術著作應抓住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在此基礎上把握全書的理論體系。“差序格局”是全書的核心概念。所謂“抓住概念”,應同時兼顧四個方面:一是淵源演變,即概念的來源和演變;二是理論內涵,即定義;三是概念外延,即相關事實;四是邏輯關系,即概念之間的區別與聯系。
首先,“差序格局”至少有遠近兩大來源。遠源可追溯到《荀子·榮辱》:“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是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為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以為寡,夫是之為人倫。”潘光旦在《說倫字》中說:“這段話說得最好,好在最足以做這個倫字的注腳。”[2]634它與“差序格局”至少有雙重潛在聯系:一是傳統社會人倫差序格局形成的原因,即“是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二是人倫差序與社會分工,即每個人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各盡其能,各司其職,這便是“人倫”。荀子“人倫差等”與費孝通“差序格局”的內在聯系隱然可見。“差序格局”的近源,則是潘光旦在《明倫新說》《說倫字》《倫有二義》及《說五倫》等系列文章中對中國傳統社會人倫差序格局的研究和闡述。鄭也夫曾把潘光旦和費孝通的相關論述作了排列對比,清晰顯示出“差序格局”思想生發的脈絡。他認為:“費孝通是在潘光旦研究基礎上,抽繹出‘差序格局’的概念”;“費孝通的貢獻在于道出了一層潘未明確表達的意思:‘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并提出了一個精當的術語‘差序格局’”。[3]這一看法是有依據的,因而得到學界認同。
其次,“差序格局”的內涵如何界定?如前文所引,在《差序格局》中作者用“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為喻作解釋。然而,比喻是不能完成理論思維的。“同心圓波紋”的意象頗為精巧,但含混的詩意想象取代了清晰的學理界說。在這種形象化描述中,人們見到的是一種極有洞見和啟發的思想,而不是一種嚴格的學術論斷。或許有鑒于此,在晚年出版的《社會學講義》中,作者對“差序格局”作了更為明晰的解說。他寫道:
鄉土社會的結構有個特點,就是以一己為中心,社會關系層層外推。我稱之為“差序格局”。差序就是像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波紋,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愈推愈薄:我,我的父親、母親,我的兄弟,兄弟的老婆,嫂子家的弟兄,我孩子的舅舅等,構成一個由生育和婚姻所結成的關系網。這個網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正所謂“一表三千里”。這和以個人之間契約來結成的團體不同。[4]145
根據作者在《差序結構》中的論述以及上述生動具體的補充說明,我們不妨下這樣一個定義:所謂“差序格局”是指鄉土中國社會結構的模式,它以“己”為中心,以親屬關系為基礎,依親疏遠近的人倫差序,呈“同心圓波紋”一圈圈推延出去所構成的社會人際關系的網絡。在文化人類學中,所謂“社會結構”,就是指“一個社區里長期存在而且起十分重要作用的人際關系網絡”[5]53。
再次,“差序格局”有那些特點?上述定義包含了“差序格局”幾個特點:一是以“己”為中心的“自我主義”。在這種格局中,自己是中心,是投入水中的“石子”,一切關系以“己”為中心一圈圈推延出去。二是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熟人格局。“己”作為“石子”投入“親屬關系”的水中,雖然推延出去的人際關系有親疏遠近之別,但無不與自己有“親屬關系”而構成一個熟人社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差序格局”揭示了“熟人社會”的結構特點。三是公私或群己關系的相對性。在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富于伸縮性的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對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內看可以說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是私,是己。四是特殊主義的倫理原則。這就是作者所說的,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一切普遍的標準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拿出什么標準來”。
最后,“差序格局”是人類歷史上鄉土社會的某種普遍現象。據考察,“差序格局”所顯示的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特征,也體現在西方“鄉土社會”的研究中。費孝通以“同心圓波紋”來形容“差序格局”,這在西方近代社會科學有關親屬及社會關系的研究中也不少見,只是以更加學術化的“多重同心圓”(concentriccircles)來表述。英國歷史學家梅因和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都曾提出“多重同心圓”說。梅因指出,在羅馬時代,家庭為基本群體,由地位最高的男性傳承人掌控;若干家族組成氏族,若干氏族組成部落,部落集合成聯邦,其關系結構呈“多重同心圓”狀。滕尼斯也曾以“多重同心圓”說來表示家庭結構:家庭戶一般為三層結構,呈一系列同心圓形態:最內圈由主人及其妻子(們)組成;第二層是其子女;最外圈則是男女仆人。[6]很顯然,西方的“多重同心圓”與中國的“同心圓波紋”,結構相似內容則有本質區別,但仍不乏相互照明的意義。
此外,費孝通指出,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因此,傳統社會的道德也只在私人聯系中發生意義,是一種“維系著私人的道德”。費孝通的“維系著私人的道德”與賀麟的“等差之愛”說頗有一致之處。1940年,時任西南聯大教授的賀麟發表了著名論文《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指出“就實踐五倫觀念言,須以等差之愛為準”。賀麟認為,與“等差之愛”相反,“非等差之愛”足以危害五倫的正常發展,大約有三途:一、兼愛,不分親疏貴賤,一律平等相愛。二、專愛,專愛自己謂之自私,專愛女子謂之沉溺,專愛外物,謂之玩物喪志。三躐等之愛,如不愛家人,而愛鄰居,不愛鄰居,而愛路人。這三種非等差之愛,一有不近人情,二有浪漫無節制愛到狂誕的危險,均屬非正常之愛。愛有差等,乃是普通自然的心理事實。所謂“等差之愛”,就是與人倫差序相對應的差等之愛,也就是以“己”為中心自然推延出去的近人情的愛。賀麟指出:“說人應履行等差之愛,無非是說,我們愛他人,要愛得近人情,讓自己的愛的情緒順著自然發泄罷了。所以儒家,特別是孟子,那樣嚴重地提出等差之愛的教訓以維系人倫間的關系。”[7]54—55這里簡單介紹賀麟的“等差之愛”說,既有助于認識“差序格局”與“差等之愛”的內在聯系,也可以看到費、賀理論潛在的淵源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