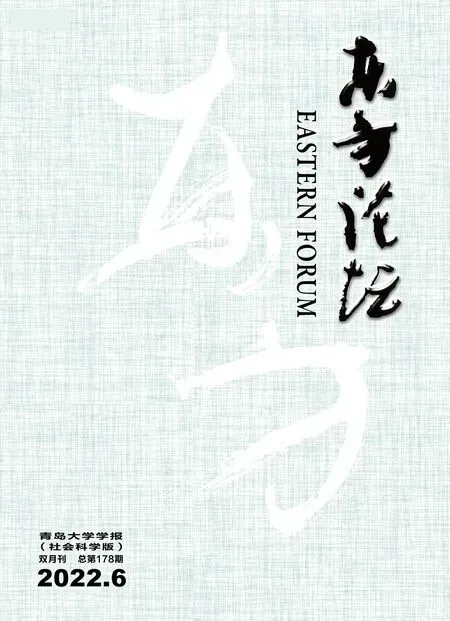“詩”與“思”的印象和闡釋
——伍爾夫、布魯姆對喬叟的觀照
胡 藝 珊
中國計量大學 人文與外語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現在能夠沉下心來閱讀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人,大概已經很少了。在國內不同版本的外國文學史中,喬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是14—16世紀歐洲文學或世界文學史中的一個知識點,大多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文學概述中,不過一兩段文字的篇幅。當然,大浪淘沙,能夠在源遠流長的世界文學史中占據一兩段乃至三兩行的位置,這樣的作家,無疑已經聲名遐邇,青史留名了。但是,與一般概述作家不同,喬叟在文學史上的獨特之處就在于,既承前啟后,是“英國中世紀文學的集大成者”①聶珍刊主編:《外國文學史(一):古代至16世紀文學》,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2頁。、文藝復興時代英國人文主義文學的開創者;又有奠基之功,是“英國文學之父”②《外國文學史》編寫組:《外國文學史(第二版)》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11頁。“英語文學之父”③聶珍刊主編:《外國文學史(一):古代至16世紀文學》,第151頁。。如此聲名和地位,每一項都不同凡響甚至是里程碑式的。但在國內多數版本的外國文學史中,這樣一位作家,無論其人還是其作品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評價,這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讀者的閱讀和接受。
如果究其原因的話,大抵是因為喬叟的光芒被另外兩位作家遮蔽了。其一,作為一位英國作家,喬叟幸而不幸地和莎士比亞同在一個時代。所謂幸,是因為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能夠和莎士比亞包括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萬提斯同屬一個時代,同屬巨人行列,這于新舊交替時期的喬叟是何其榮幸。所謂“不幸”,則是因為莎士比亞作為一位巨人,其偉大戲劇詩人的地位至今無人超越,其熠熠生輝的光芒,遮蔽了同時代另一位英國詩人喬叟的光彩。所以,如果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文學史甚至整部英國文學史首選一位大家的話,則非莎士比亞莫屬。其二,作為同是寫出了短篇故事集的作家,出生和創作早于喬叟約三分之一世紀的薄伽丘,其《十日談》領先奠定了在歐洲短篇小說史上的開創地位。正是意大利文藝復興三杰之一的薄伽丘,遮蔽了同屬一個時代的喬叟。對于一般的讀者而言,如果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故事集中選擇一部作品閱讀,描寫男女之情、塵世歡娛的“人曲”故事《十日談》,大抵會吸引更多的讀者。因此,無論是作為英國作家還是作為故事集作家,喬叟就這樣被冷落了。
但文學作品的地位和價值不以讀者的多寡論,而且經典就是經典。經典作家及其經典作品即使再沉寂,也會在沉寂處散發光芒,并得到慧眼的批評家的肯定和欣賞。比如喬叟,比如《坎特伯雷故事集》,比如伍爾夫(亦譯為伍爾芙)和布魯姆筆下的喬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
說到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年)與美國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1930—2019年),他們是不同時期不同身份甚至不同風格的兩位批評家。20世紀30年代,當作為小說家和隨筆作家的伍爾夫已經完成了《墻上的斑點》《達洛衛夫人》《到燈塔去》《歲月》以及《一間自己的屋子》和《普通讀者》Ⅰ《普通讀者》Ⅱ的時候,美國的布魯姆則剛剛跟在姐姐身后,每天奔走在家和公共圖書館之間。時光荏苒,轉眼到了1970年代。布魯姆執教于名牌高校,成為了批評界的領軍人物,而伍爾夫卻已在幾十年前,以一種平靜又近似決絕的方式,自沉于離家不遠的烏斯河。從時間點上看,伍爾夫和布魯姆的生活時代有過短暫的交集,但就各自的寫作、理論建樹及文學批評而言,他們是屬于不同時代的人:一位在20世紀前三十年聲名遐邇,一位聲譽鵲起于20世紀70年代之后。從身份看,伍爾夫是作家,是女性主義者,是文學批評家。而布魯姆從一開始,就是學者,就是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當然,他們各自所受的教育不同。伍爾夫是在父親的悉心引導下,以幾乎完全自學的方式,成為了20世紀有影響的意識流小說家和散文大師,并以《一間自己的屋子》成為女性主義的先驅;而布魯姆則是名校出身,畢業于康奈爾和耶魯大學,且有長期在耶魯、紐約和哈佛大學執教的經歷,是著名的文學教授。由此種種可以看出,無論是時代、國別、身份以及教育背景,伍爾夫和布魯姆是不同圈子的人。
但是文學閱讀和文學批評又把伍爾夫和布魯姆聯系在一起——對閱讀對經典的熱愛與熱情,以及他們共同的師承或偶像塞繆爾·約翰遜。當伍爾夫將自己的兩部隨筆集命名為《普通讀者》時,在序言中,她借用約翰遜博士的話表達自己的閱讀態度,“能與普通讀者的意見不謀而合,在我是高興的事……”①[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3頁。。如果說伍爾夫以“普通讀者”為隨筆集命名,是在闡明自己的閱讀和批評態度,并含蓄地表達了對約翰遜博士敬意的話;在布魯姆這里,則是旗幟鮮明直截了當——“我的英雄偶像是塞繆爾·約翰遜博士”,“我理想的讀者(和終生的英雄)是塞繆爾·約翰遜博士”,“塞繆爾·約翰遜博士是文學批評家中最聰敏的人”,是“我師法的批評大師”,是“各民族中空前絕后、無與倫比的批評家”,“他是西方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迄今難有與之比肩者”。如此盛贊,在布魯姆的文章中不時出現在《如何讀,為什么讀》《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文章家與先知》的“序言”、“前言”或“導言”中,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和《文章家與先知》的專節論述中。
至于伍爾夫與布魯姆之間的聯系,從生活的時代看,伍爾夫肯定不知道布魯姆,但布魯姆卻對伍爾夫大為欣賞。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被《紐約時報書評》認為是“以崇高的勇氣和驚人的學識”并“充滿激情”寫作的著作。該書22個章節,除卻第一章“經典悲歌”外,布魯姆以21個章節,探討了包括莎士比亞、但丁、喬叟、塞萬提斯、塞繆爾·約翰遜博士及華茲華斯、簡·奧斯汀、惠特曼等20多位作家及其作品。布魯姆將《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所論20余位作家,以19世紀之前、19世紀、20世紀為時間節點,劃分為“貴族時代”“民主時代”和“混亂時代”。而在20世紀“混亂時代”的7個章節中,布魯姆選取了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博爾赫斯、貝克特等近10位作家,并將他們分別與莎士比亞、惠特曼做了比較。對于伍爾夫,布魯姆則單設一章《伍爾夫的〈奧蘭多〉:女性主義作為對閱讀的愛》來表達對她的激賞。盡管布魯姆自謙“自己尚無資格去評判女性主義批評”,但他欣賞伍爾夫“對閱讀超乎尋常的熱愛與捍衛”。布魯姆甚至用“情欲沖動”和“世俗的神學”來表述伍爾夫對閱讀的熱愛。布魯姆將伍爾夫與佩特和尼采相提并論,稱他們為“天啟式的審美家”,而伍爾夫是“最后一個高雅審美家”。2000年,當布魯姆出版《如何讀,為什么讀》一書時,在前言中,關于“如何讀”,布魯姆借用了伍爾夫《普通讀者》Ⅱ中《我們應該怎樣讀書?》中的文字,并不無風趣地將伍爾夫對怎樣讀書的建議稱之為“迷人地警告”。對于她的那些給讀者的許多建議,布魯姆表示“從頭至尾都欣然采納”。
二
布魯姆在其著作《史詩》前言中說:“關于想象性文學的偉大這一問題,我只認可三大標準:審美光芒、認知力量、智慧。”①[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頁。可以說,正是因為對作家作品的審美、認知和智慧,才使得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伍爾夫和布魯姆,在對待文學閱讀、文學欣賞和文學批評時,有諸多相通之處。其中包括他們對喬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評價和欣賞。
眾所周知,伍爾夫是意識流小說家,也是散文隨筆作家。除卻意識流小說,伍爾夫發表在報刊上的大量書評和隨筆即文學批評隨筆,構成了其文本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伍爾夫有“傳統散文大師、新散文首創者”“英國散文大家中的最后一人”的美譽。相比于其小說,伍爾夫的隨筆篇目多,計二百余篇;寫作時間長,伍爾夫由隨筆開啟其寫作生涯,并貫穿于整個創作生命過程中。但在伍爾夫生前,由作者自己選定并結集出版的只有1925年的《普通讀者》Ⅰ和1932年的《普通讀者》Ⅱ。兩本《普通讀者》不過40余篇,大致占伍爾夫隨筆文章的五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伍爾夫在選擇篇目時的嚴格審慎甚至挑剔。盡管在伍爾夫去世之后,由他人整理編輯出版的隨筆集同樣筆致灑脫、文采斐然,蘊蓄著認知的智慧和審美的光芒。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在《普通讀者》中,伍爾夫隨筆中最精華的文章都編選其中了。或者說,被選入《普通讀者》中的文章,無一不是其隨筆的精華。正如倫納德·伍爾夫所坦言的那樣:“即便是許多不理解、不喜歡甚或嘲笑弗吉尼亞小說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她在《普通讀者》一書中所體現的非凡批評才能。”①[英]倫那德·伍爾芙:《〈一個作家的日記〉序》,《伍爾芙日記選》,戴紅珍、宋炳輝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3頁。正是在最能體現伍爾夫非凡批評才能的隨筆集《普通讀者》Ⅰ中,除卻序言《普通讀者》一文,真正意義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寫喬叟的《帕斯頓家族和喬叟》。這樣的編選,既是伍爾夫的看重,又使喬叟站到了“英國文學之父”和“英語文學之父”的位置上,同時也讓讀者隨著伍爾夫的隨筆,回到了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回到了喬叟。在通向坎特伯雷的路上,跟隨著香客的朝圣之旅,領略600年前的詩人所創造出的藝術世界。
而在布魯姆的著作和文章中,但凡說到經典和經典作家,喬叟一定會是被提到的名字。《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可以視為布魯姆對歐洲文學傳統帶有總結的論著。在《序言與開篇》中,作者“無可避免地帶著一種懷舊之情”研究了26位作家,“并試圖辨析使這些作家躋身于經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們成為我們文化權威的特性”②[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頁。。在布魯姆看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對作家的選擇并非像看上去那樣隨意而為,“所選作家的理由是他們的崇高性和代表性”③[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2頁。。在闡明為何選擇諸如但丁、喬叟、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和為何不選擇諸如彼特拉克、拉伯雷、斯威夫特、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等作家時,布魯姆表示“我實際上是在論述代表各個民族之經典的人物”④[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2頁。。在所選英國的經典作家中,喬叟與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和狄更斯等大家一起,毫無懸念地榜上有名。
在《西方經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首篇《經典悲歌》中,布魯姆坦率地強調“經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詞匯”⑤[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16頁。,“一切強有力的文學原創性都具有經典性”⑥[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20頁。。作者充滿激情地寫出了在紐黑文的一個暴雨之夜,在重讀彌爾頓的《失樂園》并感到莫名的震動,即獲得那種“既覺生疏又全神貫注”“離奇”的首要效果及“驚世駭俗的陌生性”感受之后,布魯姆筆鋒一轉,“我認為西方經典中只有很少幾部作品比《失樂園》更重要——如莎士比亞的主要悲劇,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但丁的《神曲》,托拉經,福音書,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以及荷馬史詩”⑦[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21頁。。在此,比令布魯姆感到莫名震動的《失樂園》更重要的少數幾部作品中,喬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赫然在列。布魯姆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閱讀態度:“我認為,為了服膺意識形態而閱讀根本不能算閱讀。獲得審美力量能讓我們知道如何對自己說話和怎樣承受自己。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閱讀他們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自我的成長……心靈的自我對話本質上不是一種社會現實。西方經典的全部意義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獨,這一孤獨的最終形式是一個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⑧[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24頁。布魯姆甚至還不無傷感,“我們擁有經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姍姍來遲。人生有涯,生命終有竟時,要讀的書卻前所未有地多。從耶和華文獻作者和荷馬到弗洛伊德、卡夫卡及貝克特,經歷了近三千年的旅程。但丁、喬叟、蒙田、莎士比亞及托爾斯泰是這一旅程所必經的深廣港口,每一位作家都足夠我們以一生的時間去反復閱讀……”①[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24頁。在經典旅程所必經之深廣港口中,布魯姆僅僅列舉了五位作家,喬叟即在其中。
而在幾年之后出版的著作《如何讀,為什么讀》中,布魯姆說到為什么讀經典的理由,“我們讀莎士比亞、但丁、喬叟、塞萬提斯、狄更斯、普魯斯特和他們的匹敵者,是因為他們都不止擴大生命。實際上,他們已變成天恩,真正的、舊約圣經意義上的天恩……”②[美]哈羅德·布魯姆:《如何讀,為什么讀》,黃燦然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4頁。在這里,布魯姆使用了“天恩”一詞,延續了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經典悲歌》中關于“經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詞匯”的表述。而在視為“天恩”所列舉的6位作家中,喬叟依舊在場。
布魯姆對喬叟的集中論述是在兩部著作中。一是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的“貴族時代”,布魯姆以八個章節,論述了包括莎士比亞、但丁、喬叟、塞萬提斯、蒙田和莫里哀、彌爾頓、塞繆爾·約翰遜博士、歌德等9位作家。其中,《喬叟:巴思夫人、贖罪券商和莎劇人物》一章,布魯姆以近兩萬字的篇幅解讀了喬叟及其作品。二是在21世紀初出版的《史詩》中,布魯姆以自己對史詩的理解,論述了包括荷馬史詩、維吉爾、紫式部、但丁、喬叟……以及托爾斯泰、喬伊斯等作家及其作品,可謂上下三千年縱橫東西方。在導言中,布魯姆這樣闡明:《史詩》所選作家作品看似散漫,但卻有一個內在的結構,即其一,“雅威作者或J作者最偉大的希伯來散文史詩”包括《創世記》《出埃及記》,“它們是羊皮卷上最早寫上的一層文字”③[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導言》,第5頁。;其二,五部全景式散文史詩,包括《白鯨》 《戰爭與和平》《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斯》等;其三,兩部美國現代短史詩《荒原》與《橋》;其四,“較早的時代”“風格迥殊”的著作,包括《貝奧武夫》《源氏物語》《神曲》《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八部作品。
當然,作為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布魯姆一生著作豐富。除卻《影響的焦慮》《影響的剖析》等理論著作,單是作家作品批評,就有《雪萊的神話創造》《莎士比亞:人的創造》等;以體裁劃分,又有《劇作家與戲劇》 《短篇小說家與作品》等論著。而在論作家作品的著作中,《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如何讀,為什么讀》《史詩》,都是布魯姆有影響的著作。其中,對于喬叟,布魯姆既有長文集中論述又有序言、前言及導言中的多次強調。可見,在布魯姆這里,無論是作為“西方正典”還是作為“偉大史詩”,喬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其經典地位都無可置疑。
三
一位是現代英國女作家,一位是當代美國評論家。隔著一條時間的河流,當伍爾夫和布魯姆在不同時空中,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喬叟的欣賞和高度評價時,因為批評方式不同,兩位批評家的欣賞和批評,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與風格。這是因為,文學批評家作為文學批評的主體,其出身經歷與精神氣質決定了各自批評文本的風格特色。伍爾夫是女作家、意識流小說家、散文大師,還是女性主義者。出身和經歷,極度敏感的詩人氣質以及“神明的稟賦”,這一切,構成了伍爾夫在文學接受、文學創作、文學欣賞與批評中最重要的品質——對心靈對文學性無與倫比的感受能力。體現在文學創作中是意識流小說,體現在文學欣賞與文學批評中,則遠離了學院派批評的理性和思辨、概念與邏輯以及規范與方法,而切近了重感覺、重內心體驗、重印象描述的印象批評。伍爾夫的批評是散文是隨筆,是批評文章的散文化或小說化。或者從另一角度說,伍爾夫集普通讀者、小說家、文學批評家于一身的身份,又強化了其作為印象派批評家的特質。
當伍爾夫以近乎寫小說的形式書寫著文學批評時,一篇關于喬叟的長篇隨筆,竟然是由15世紀居住在英格蘭諾福克一個家族的書信引起的。在《帕斯頓家族和喬叟》一文中,首先出現的不是喬叟,不是《坎特伯雷故事集》,而是幾百年前的帕斯頓家族。隨筆一開篇,伍爾夫靈動而富有想象力的筆觸,流連在600年前帕斯頓家族的城堡、鐘樓、寒鴉、廢墟、斷壁殘垣、地勢險峻的海濱遺址、布羅霍姆修道院……以及修道院里約翰·帕斯頓沒有墓碑的墳墓。在伍爾夫兜兜轉轉地用了幾千字篇幅寫出了帕斯頓家族的故事和傳說之后,1466年,約翰·帕斯頓在倫敦去世了,遺體被安葬在布羅霍姆修道院。當“約翰·帕斯頓墳頭的燈火早已熄滅”,繼承人小約翰·帕斯頓還是沒有給父親置辦墓碑。帕斯頓的宅子里有利德蓋特和喬叟的詩。“當風掀起了地毯,煙氣刺痛著他的眼睛,約翰讀著喬叟,任時間流逝著,做著夢……生活是粗糙,憂郁,令人失望的。……利德蓋特和喬叟的詩像是一面鏡子,鏡中的人影簇擁在一起晃動著,輕快,靜默。他看見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天空、田野和人們,但是更加生動和完整。”①[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2頁。當不明所以的讀者正在為帕斯頓家族的傳說、城堡、墓碑所迷惑的時候,終于,曲曲折折地,喬叟出現了。經由帕斯頓家族繼承人小約翰的閱讀,喬叟自然而然地走進了讀者的視野。或者說,伴隨著伍爾夫散漫的、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讀者走近了喬叟。
與行文表面的興之所至不同,在看似不著邊際的筆觸中,伍爾夫敏銳地感覺到了喬叟所以成為偉大作家最內核的特質,那就是:
其一,喬叟有著“杰出的說書人的天賦”,能夠讓讀者“把故事念完”。這是喬叟作品所以能吸引讀者的拿手本領。與《十日談》10天講100個故事不同,近30萬字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只寫了24個故事,幾乎一半的故事稱得上是一部小中篇。如何在朝圣路上讓聽者聽進這些故事,或者說,對于讀者來說,能否念完這些故事,這要看寫作者的才能。而喬叟具備這樣的才能和天賦:“他具有杰出的說書人的天賦,對于今天的作家這大概是最難得的一種天賦了。……因為說書人講故事的時候不僅要對事實有無比的熱忱,還要有技巧,不可過于賣力或過于激動,不然我們就會囫圇吞棗,把各個部分胡亂拼湊在一起;他必須讓我們能夠駐足停留,給我們時間思考和觀察,而又能說服我們不斷前行。”②[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3頁。就這樣,聰明的、富有想象力、具有杰出講故事天賦的喬叟,被伍爾夫從600多年前帕斯頓家族灰暗陰沉的舊宅,引領到了讀者面前。然后,讀者像小約翰一樣地讀著喬叟,任時光流逝,做著夢,但還是“從書本中獲得了一種奇異的陶醉感”。在伍爾夫看來,喬叟之所以有如此天賦,是因為所處的時代和寬大的天地。“那時的英格蘭是一片未經踐踏的土地。喬叟的眼前展開的是一片處女地,草木連綿不斷,只點綴著小市鎮和零星的一兩座建造中的城堡。肯特郡的樹叢后面沒有別墅的屋頂探頭窺探;山坡上沒有工廠的煙囪冒著煙……”喬叟時代的鄉村“她的開墾或野性狀態給予詩人的影響遠比其給予散文家的要深刻”。“如今,鄉間的風景已經面目全非……天分稍遜的詩人現在只能拘束在狹小的天地里,在鳥巢上、在鐫刻著一道道歲月的皺紋的橡子上作文章。那更寬大的天地已經失落了。”①[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3—14頁。喬叟之所以成為喬叟,在伍爾夫看似漫不經心、主觀隨意的描述中,被生動而詩意地表達出來。
其二,“驚人的多樣性”以及“自有自己的世界”,與杰出的說書人天賦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是喬叟作為一位作家的獨特性,也是其作品中人物的獨特性。如果說,在《十日談》中,是100個故事由10位講故事人講述,因而無論是講故事人還是故事本身,都有性格或主題上的重復或相似的話,《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24個故事,無論是講故事人還是故事中人,都是獨特的“這一個”,而且是喬叟的“這一個”。在伍爾夫看來:“《坎特伯雷故事集》顯示出驚人的多樣性,然而在深層次,貫穿著一個始終如一的典型。喬叟自有自己的世界;他有自己的小伙子;有自己的姑娘。如果在莎士比亞的世界里遇見他們,我們認得出他們是喬叟的人物,而不是莎士比亞的。”②[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4頁。聯系到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勇敢明達但又溫和的武士、天真靦腆的女尼、慷慨好客的自由農,自稱“在教堂門口嫁過五個丈夫”的巴斯婦……可以說,沒有運用典型理論,但喬叟故事里人物性格的多樣性、豐富性甚至典型性,伍爾夫敏銳地感覺到了。
其三,偏偏的力量,一種寶貴的天賦。喬叟生逢新舊交替時代,此時的英國文學尚不發達,英語還被達官貴人所不齒。與莎士比亞創作的成熟甚至登峰造極不同,喬叟質樸而本色,對自己的思想保持單純的忠誠。在這種屬于早期英國文學的質樸和本色中,伍爾夫看到在喬叟作品中“他從未想到他的格麗西達可以再潤色或改動。她周身沒有一點模糊的地方,沒有猶疑;她不證明什么;她滿足于成為自己”③[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6頁。。而“這就是偏偏的力量,一種寶貴的天賦……”④[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6頁。像所有偉大的作家一樣,喬叟在自己的作品中從不對任何人任何事情做道德的判斷。但正是在不判斷中,“我們知道他認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惡的;說得越少越好”⑤[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6頁。。在伍爾夫看來,喬叟不同于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雪萊,后者的篇章屬于神甫,有無數的警句規勸像護身符一般。但喬叟“作為真正的詩人他并不給出答案……”,“喬叟讓我們沿著自己的路走下去,一路和平凡的人做著平凡的事情。他的道德教訓蘊含于男男女女彼此相處的方式”⑥[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20頁。。而這就是作為“普通人”的喬叟所創造出來的世界:“這是詩的世界……這里飄蕩著一種特別的單調氣息,而這正是詩的魔力……”⑦[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20頁。。
其四,喬叟是一位詩人,目光注視著眼前的路。與喬叟作品“詩的魔力”“偏偏的力量”緊密聯系的是喬叟的詩人氣質。因為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喬叟給讀者的印象是一位擅長講故事的作家。但真實的情形是,喬叟從開始就是詩人。這位詩人經歷了從宮廷詩人到偉大詩人的變化,一種在視野、風格、氣質上的擴展和演變。在現實生活中,喬叟出入宮廷,但靠近的是普通人的現實人生。所以,“喬叟的目光注視的是眼前的路,而不是未來的世界。他幾乎從不陷入虛無的冥想”①[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8頁。。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無論是故事主題還是所寫景象以及語言都是世俗而鮮活的——公雞、母雞、稻草、牛糞、農家場院以及樸素的田野都進入了詩人的視野。因為貼近生活、貼近了凡人俗事,喬叟的作品生機勃勃,充滿明快的生活氣息。“喬叟毫不靦腆,無所畏懼。他總是貼近描寫的對象……”②[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18頁。即使是寫老人的胡子茬,即使是寫老人脖頸上松弛的皮膚……。“喬叟有一種本領,他把最平常的詞句和最單純的感情排列在一起,各自都熠熠生輝;如果拆開來,就會光彩頓失。因此,喬叟給予我們的愉悅和其他詩人不同,因為它和我們的所感所見更加貼近。吃,喝,好天氣,五月,公雞母雞,磨坊主,老農婦,花朵——看到這些尋常事物這樣排列在一起令人有特殊的感動,因為它們如同詩一般觸動我們,而又像野外所見一般鮮明、清晰、準確。”③[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Ⅰ,石云龍等譯,第21頁。非常可貴的是,作為小說家的伍爾夫敏銳地把握住了喬叟骨子里的詩人氣質。在對詩意世界的描寫和對詩性的把握上,伍爾夫和喬叟心有靈犀。600年前的詩人喬叟采用的是鮮明清晰的語言和意象,并由此傳達出最單純、最素樸也最詩意的世界。這樣的世界,在伍爾夫這里,有著最單純也最深刻的認同。
當伍爾夫在《普通讀者》Ⅰ中,以首要篇幅表達了對喬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欣賞后,時隔三分之二世紀,布魯姆則在其著名的《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以近兩萬字篇幅寫出了《喬叟:巴思婦人、贖罪券商和莎劇人物》。在《史詩》中,布魯姆又以《杰弗里·喬叟(1343—1400)·〈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文,再次以幾乎同樣篇幅論述了喬叟及其作品。如果說,伍爾夫是“普通讀者”,是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其對喬叟的批評是印象批評,是在直覺感悟和印象描述中,以散文化、小說化的方式,極具詩性文學性地表達了對喬叟的欣賞的話,與伍爾夫身份經歷不同的布魯姆,其批評則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因為是學者是教授是理論家與批評家,其學識與視野、激情和勇氣,使得布魯姆無論是理論建樹還是作家作品批評,都既有論述的深度和廣度,又有思辨的力度,同時文采郁郁,激情沛然。
《喬叟:巴思婦人、贖罪券商和莎劇人物》一開篇,布魯姆就明確提出:“除了莎士比亞,喬叟要算是英語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這一斷言雖然只是對傳統評價的重復,但在世紀之末它對我們卻極有價值。閱讀喬叟或自古以來他在文學上少數幾位對手的作品——如但丁、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可以使人產生恢復洞見的愉快效果,我們所有人在面對紛至沓來的的曇花一現式名作時也許會禁不住失去理智,這些作品如今給我們帶來了危害,促使人們放棄美學的求索,而喬叟在其作品中堅守著文化正義。”④[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2頁。短短幾百字的開篇,寫出了喬叟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和地位、其作品的洞見以及對文化正義的堅守。如此宏闊的氣勢,源于布魯姆的學識和理論修養。與一般理論家和批評家不同的是,作為理論家,布魯姆蘊蓄于心的經典作品,構成了其學養中為一般理論家所不及的文學經緯;作為文學批評家,布魯姆理論根基深厚,有思辨的銳氣和激情。體現在文學批評中,既游刃有余,又高屋建瓴。盡管是論喬叟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但布魯姆不是就作品論作品,就人物論人物,甚至不僅僅是就喬叟論喬叟。文章首先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比較的視域中,探討喬叟何以有能力將作品中“那些真正讓人信服的男男女女”“描寫得如此歷久彌新”上。布魯姆借用喬叟傳記作家和評論家的闡釋,分析了喬叟所處的時代,其人物的原創性以及獨具個性的反諷,以此顯示喬叟的承前啟后以及里程碑地位。
正是認可“想象性文學的偉大”標準是審美光芒、認知力量和智慧,及至世紀之交寫作《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和《史詩》時,布魯姆“將文學批評的功能多半看作鑒賞”①[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前言》,第3頁。,并認為“文學最深層次的焦慮是文學性的”②[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15頁。。這里,布魯姆用了“文學性”的表述。20世紀20年代,當雅各布森提出“文學研究的對象并非文學而是‘文學性’”③趙一凡等:《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92頁。時,是對傳統文學批評的反撥。在雅各布森看來,“‘文學性’,即那種使特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如果文學批評僅僅關注文學作品的道德內容和社會意義,那是舍本求末”④趙一凡等:《西方文論關鍵詞》,第592頁。。與雅各布森等形式主義批評家們從語言修辭角度闡釋文學性不同的是,布魯姆是從審美層面來談文學性的。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開篇《經典悲歌》中,布魯姆不無憂慮地指出:“回避或者壓抑審美在所謂的高等教育機構中是普遍的風氣”⑤[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19頁。,“審美語境中的遺忘是具有毀滅性的……”,“這樣一來就把審美降為了意識形態,或頂多視其為形而上學。一首詩不能僅僅被讀為‘一首詩’,因為它主要是一個社會文獻……我與這一態度不同……”⑥[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15頁。。可以說,布魯姆的“文學性”,強調的是文學的審美意義。同時,在人本和存在的層面上,布魯姆有對人性的體味與思索,“我們閱讀喬叟和莎士比亞之時,要么成為經驗的批評家,要么以過于清醒的頭腦,索性不閱讀。在這里,‘經驗的’(experiential)自然是指人性地觀察他們和自己……”⑦[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6頁。。這與僅僅關注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不同。布魯姆甚至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對從社會的角度去解釋一位大詩人的反諷姿態總是心存戒備的,這是由于大詩人的氣質和自信不是任何武斷定論所能解說的。喬叟的姿態是一種如此宏大的意識,它導致一種四處彌漫和獨具個性的反諷……”⑧[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4頁。正是在“文學性”的層面上,布魯姆肯定喬叟是一位“大詩人”。
因為是大詩人,所以喬叟的故事集“更具有原創性和經典性”,有“極大的世俗性,而且有著幾乎完美的反諷特色”⑨[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6頁。。布魯姆甚至將喬叟這樣一位“完美和精彩的反諷作家”,“上溯到耶和華文獻作者”——“喬叟真正的文學前輩也許就是耶和華文獻作者,而他的真正傳人則是簡·奧斯汀”⑩[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7頁。。至于喬叟與莎士比亞的關系,是“他最豐富的遺產便是創造了英語世界中僅次于莎士比亞的眾多文學形象。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人物形象上已經萌生了莎士比亞最具有原創性的想像力:表現特定戲劇人物的內在變化”①[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7頁。。布魯姆的文章開篇就呈現出一種恢弘的、大開大合的氣勢。這位學識驚人的批評家從容地穿行于文學史中,從上古時代到中世紀再到文藝復興,從奧維德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再到莎士比亞直至奧斯汀。看似信手拈來,自在從容,實因視野開闊,格局廣大。
《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的《喬叟:巴思婦人、贖罪券商和莎劇人物》一文,意在探討巴思婦人、贖罪券商與莎劇人物的關系。文章第三大部分,布魯姆直扣主題,“喬叟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寫了兩位最具有內在性和個性的人物:巴思婦人和贖罪券商,一位是偉大的活力主義者,另一位近似于真正的虛無主義者”②[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8頁。。布魯姆將巴思婦人與福斯塔夫相聯系,將贖罪券商“同他的遠房子嗣伊阿古和愛德蒙”聯系起來,甚至還聯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斯維德里蓋洛夫和斯塔夫羅金。當然,“喬叟最出色的創作是巴思婦人和贖罪券商,這是莎士比亞明確認識到并從中獲益的,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別的文學啟迪可與之相比。要了解莎士比亞受到了何種觸動,我們就要回到真正的經典化過程本身……”③[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8頁。布魯姆分別借用“純凈英語的源泉”和“泉邊天鵝”的比喻指稱喬叟和莎士比亞,而莎士比亞“暢飲著喬叟語言的獨特甘醴,塑造新型的文學人物……”④[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8頁。。
像幾乎所有的讀者一樣,布魯姆對于《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那位“好婦人”“當然印象深刻”。正如布魯姆所說,當作者寫作巴思婦人時,“喬叟顯然是被她迷住了”,而讀者在讀這個人物時,大抵也會被迷住。即使忽略或忘記了故事中其他人物,也不會忽略甚至會著迷于巴思婦人充沛的活力、旺盛的情欲、坦率的毫不掩飾的及時行樂甚至有意張揚的放任。與一般道德批評家不同的是,布魯姆認同喬叟傳記作家霍華德的說法,“即這位婦人確實討人喜歡,不管道德家們如何急于反對她……”。布魯姆甚至還認為:“如沒有這些人物,文學將會變得暮氣沉沉,生活也會缺少文采。”⑤[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9頁。當然,對于很多讀者來說,巴思婦人所講的故事已經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最能顯示其個性的是她那篇興致勃勃的開場白——“巴思婦人的開場白是一種坦白,但更像一篇得意的辯護或自贊”⑥[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9頁。,“這位婦人叫人敬畏的是她無盡的激情與活力:性欲的、語言的和論辯的。她旺盛的生命力在文學史上從無先例,后來者中也只有莎士比亞所創造的福斯塔夫可與之媲美”。布魯姆還不無風趣地說:“想象這位婦人和胖子福斯塔夫騎士的碰面當然是合理的文學想象。福斯塔夫比那位婦人更聰明機智,但他即使用上全部精力也無法使她安靜下來。”“這是我們應當賦予她的最高贊頌,且將道德批評家們的合唱都丟在一邊:她的身上惟有生命力,即對更充沛生命活力的永久祝福。”⑦[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90頁。
布魯姆在文章中還引用了巴思婦人那段著名的詩句:“可是基督啊,每當我想起,我年輕快樂的時光……”布魯姆認為:“上述十一行詩句包含了巴思婦人的記憶和欲望,但又承認時間已經改變了她的形象。如果說喬叟作品中有哪一段突破了自己的反諷,那么非此莫屬……仍然雄赳赳的巴思婦人對這一反諷所說的最豪邁的一句話是:‘我曾在我的時光里擁有自己的一切。’‘我的時光’是得意之辭;……不過,其中的傷感是顯而易見的,這也證實了她對衰落的現實體認:老去的欲望行將朽敗,不過她也明白,最適合自己的是及時行樂,這是一種世俗或經驗的智慧……”①[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92頁。有意味的是,當布魯姆寫作《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時,已經花甲之年,與近60歲寫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時的喬叟年齡相近。也許是人生體驗的共鳴,布魯姆對喬叟關于巴思婦人的書寫感同身受,“喬叟當時已近六十歲,深感垂垂老矣,因而賦予她滔滔不絕的口才,這既適合這個人物也適合她的創造者”②[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92頁。。當然,對巴思婦人口才的解讀和闡釋,大抵也適合有“世俗或經驗的智慧”又激情沛然的批評家布魯姆。
也許是意猶未盡,10年之后,當布魯姆在《史詩》中論述喬叟及其作品時,又再次引用了巴思婦人的“啊,上天,上天!我想我曾一度年輕快活……”“我有過屬于我的好日子”的告白,將其稱為“英雄的哀調”“著名的浩然回音”“與福斯塔夫一樣,巴斯婦是哀調的壯麗比喻”。“這是喬叟著名的章節之一,這些章節正是莎士比亞的活力的先聲。”③[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7頁。布魯姆甚至將巴思婦人、福斯塔夫與堂吉訶德、桑丘·潘札及龐大固埃等“組成了一個家族或同盟”,認為他們“專事游戲之道,而與社會秩序或嚴謹的精神背道而馳。游戲之道在其嚴格的界限內所帶來的是自由,即不受個人超我困擾的內在自由。我認為這就是為什么人們要閱讀喬叟、拉伯雷、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的原因”④[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93頁。。如果說,在大多關于巴思婦人的評論中,更多解讀的是巴思婦人的活力充沛或不加掩飾的欲望或及時行樂的話,在布魯姆人性化的理解中,就將巴思婦人的無所顧忌、個性張揚提升到了一個追求自由、不受束縛的高度。布魯姆甚至還很坦率:“比起這兩位已陶醉的活力主義者來說,他們周圍的一切都引不起我們多大的興趣。”⑤[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93頁。
在不無風趣地寫出了巴思婦人之后,布魯姆轉到贖罪券商,“把巴思婦人與福斯塔夫聯系起來是文學批評的老生常談,但我從未見到有人思考過,莎士比亞最重要的反面人物極可能和贖罪券商一脈相承,他們是《奧賽羅》中的伊阿古和《李爾王》中的愛德蒙……”⑥[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94頁。。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對巴思婦人的解讀更多是布魯姆對人性、生命意義上的狂歡與享樂以及個性張揚與自由的理解,因而文筆輕松甚至不無風趣。對贖罪券商的認知,則是“十足的宗教騙子,販賣假的圣骨,膽敢拿基督施予的救贖做交易”的“十足的壞蛋”,貪婪、猥瑣、奸邪、人性之惡一應俱全。布魯姆將贖罪券商和文學史上幾位臭名昭著的邪惡人物聯系在一起,因此論述更有鋒芒,筆力老到犀利。“作為一個漂泊者,贖罪券商的故事有獨特的世界,它與喬叟的其他故事毫不相同,但它對我來說似乎是喬叟詩作的頂峰,處在了藝術的極限,無人能夠超越。”⑦[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94頁。至于贖罪券商和莎劇人物的聯系以及和現實人生的聯系,則是“贖罪券商和伊阿古的要害就是那慣于背叛信任的超凡智力。只有喬叟有能力教給莎士比亞表現的奧秘,他的偉大經典性最終在于贖罪券商這一陰郁的先知形象,這一形象的后代仍在生活中和文學中與我們相伴”①[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99頁。。這是《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論喬叟一文的最后一句,以此作為對贖罪券商一類人物的結語可謂入木三分、力透紙背又發人深省。
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布魯姆以三分之二的篇幅探討了巴思婦人和贖罪券商與莎劇人物的聯系,在此后出版的《史詩》中,巴思婦人和贖罪券商依然是被論述的主要人物,而且與《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觀點一脈相承。“約翰·福斯塔夫爵士無疑是巴斯婦的兒子,而赦罪僧對因機弄權的機會的享受則預示了依阿古的虛無主義”②[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99頁。,“在莎士比亞創造依阿古和愛德蒙之前,赦罪僧確是英國文學里所能找到的關于墮落的最有力表現”③[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13頁。。同樣與《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脈相承的,是布魯姆在《史詩》中論及喬叟的立場和姿態。當布魯姆寫作并出版《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和《史詩》時,正是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作為理論家和批評家的布魯姆,其學術經歷伴隨了20世紀西方各種流派各種名目的文學理論發展演變過程。但在布魯姆看來,“為方法而瘋狂的整整一個世紀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可追配這些前人的批評家,并且也不太可能很快會有”④[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6頁。。此時的布魯姆“記憶力仍相當頑健”,既有不惑之年寫作《影響的焦慮》時期的意氣風發,又有幾十年的學術蘊藉與沉淀。尤其可貴的是,對文學的熱愛和激情及對“文學性”這一“文學最深層次的焦慮”,使布魯姆在理論家和學者之外,又是一位“大作家式的批評家”,這與伍爾夫是作家中的批評家異曲同工。與伍爾夫是“普通讀者”遙相呼應,在《史詩》之《杰弗里·喬叟》篇中,布魯姆也表達了同樣的批評立場,“我并不是喬叟學者,因此僅以一般文學批評者和喬叟的普通讀者的立場,寫作這篇文章”⑤[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0頁。。
在《史詩》之論喬叟文章中,無論是巴思婦人、贖罪券商還是其中“武士的故事”都已經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何以在“偉大史詩”的意義上論述喬叟的作品,并顯示在作家傳承的意義上,“也許正如喬叟是斯賓塞的源泉,他也是莎士比亞的偉大源泉”⑥[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2頁。。在布魯姆看來,“批評也許是被亞里士多德的形式主義永遠地摧毀”⑦[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5頁。,“喬叟與莎士比亞同有的力量,其中一些東西正也解釋了在理解此二人之時,文學批評何以屢屢失敗,尤其是出自形式主義者的批評,或過于沉迷代碼、規矩,以及而今所謂的‘語言’……”⑧[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2頁。與多數理論家和批評家不同的是,布魯姆深諳理論卻又超越理論,熟讀喬叟作品并對相關批評熟稔于心,故能從容游弋于各種文獻之間。對于布魯姆而言,無論是理論家還是理論抑或作家作品及批評,都可以信手拈來,得心應手又無掉書袋之感。正如布魯姆所意識到的那樣:“莎士比亞過于浩大,擱不進任何傳統,喬叟也是如此。”⑨[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4頁。對于《坎特伯雷故事集》來說,“如斯恢弘、如斯深刻的詼諧著作,幾乎容不得文學批評應用任何規則”⑩[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4頁。,“弗洛伊德原就無法追及喬叟和莎士比亞,他追上了蒙田和盧梭,這已經是朝向內心的漫長道路。然而赦罪僧就是內心……”①[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5頁。所以,“沒有哪種代碼或方法能夠幫助我們解讀喬叟。批評家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成為活力充沛的詮釋者,以侍奉這樣一種藝術,這種藝術的責任僅意在將更強的活力帶進一種無界限的時間”②[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9頁。。毫無疑問,布魯姆——“西方傳統中最有天賦、最具原創性和最富煽動性”的批評家,就是這樣一位“活力充沛的詮釋者”。
當然,當布魯姆在花甲之年“無可避免地帶著一種懷舊之情”解讀喬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時,大抵也是帶著一種“回鄉之感”的,正如他所說,“我們不應當把喬叟本人、詩人喬叟和朝圣者喬叟三種身份截然分開:這三位合成了一個令人喜愛的諷刺作家”③[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7頁。。而喬叟的作品“已經成了作者生命的一部分。生活作為一種朝圣之旅的形象——與其說是奔赴耶路撒冷不如說是奔赴審判——與喬叟的坎特伯雷朝圣的構思原則結合了起來”④[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第86頁。。如果借用布魯姆意思的話,當我們閱讀布魯姆的批評時,我們也不應該把普通讀者布魯姆、理論家布魯姆和大作家式的批評家布魯姆三種身份截然分開。而閱讀經典和批評經典的過程,無疑也是一次朝圣的過程。因為在布魯姆心目中,經典已經成為“天恩”。
有見地的批評家對經典的認知是相通的,不受時間與空間、性別與身份的限制。當伍爾夫在《普通讀者》中對喬叟極盡欣賞之后,幾十年過去,美國批評家布魯姆對喬叟評價的深度與高度,與伍爾夫感性而富有想象力的直覺印象相得益彰。可以說,無論是視域的遼闊,是高屋建瓴的理解,還是對作品的盎然興趣與勃勃興致,伍爾夫與布魯姆,他們對喬叟及其作品,是讀進去了,而且讀出了感覺。所以,無論是作家伍爾夫,還是“大作家式的批評家”布魯姆,他們的文學批評,也就成了文學欣賞與文學批評中堪稱經典的文本。正如布魯姆在評價塞繆爾·約翰遜博士時所說的“約翰遜使我們看到批評作為一種文學藝術廁身智慧寫作的古老體裁”⑤[美]哈羅德·布魯姆:《文章家與先知》,翁海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63頁。,“約翰遜叫我們知道,批評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其權威仰賴于批評家的人類智慧,而非理論或實踐的正確或錯誤”。在布魯姆的理念和理想中,“一如既往,文學批評將繼續作為詮釋的智慧與智慧的詮釋”⑥[美]哈羅德·布魯姆:《文章家與先知》,翁海貞譯,第64頁。。可以說,就批評作為“詮釋的智慧與智慧的詮釋”而言,約翰遜博士的文學批評是,伍爾夫和布魯姆的文學批評亦如是。
當然,伍爾夫和布魯姆的批評方式又是不同的。海德格爾曾經這樣說過:“本書的一系列闡釋無意于成為文學史研究論文和美學論文。這些闡釋..乃出自一種思的必然性。”“這些闡釋乃是一種思(Denken)與一種詩(Dichten)的對話。”⑦[德]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2頁。大家和大家是相通的,在對“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和對喬叟作品的闡釋上,海德格爾、伍爾夫、布魯姆都是大家。如果套用海德格爾的話看伍爾夫和布魯姆,那就是,當伍爾夫在寫作《帕斯頓家族和喬叟》時,應該不會想到會成為文學史研究論文;而布魯姆在寫作《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史詩》中關于喬叟的文章時,肯定是有著著書立說的意氣和抱負,有意于寫成文學史研究論文和美學論文的。不約而同的是,他們的闡釋也是“一種思與一種詩的對話”,殊異的是他們各自不同的“思”的方式。如果說伍爾夫之“思”是直覺和感悟,布魯姆之“思”則是高度的思辨和融會貫通。前者寫出了喬叟的天賦、力量和詩人魔力,后者寫出了喬叟作品何以是經典何以為偉大史詩。從這個意義上說,伍爾夫和布魯姆關于喬叟及其作品的闡釋,本質上也是“詩”與“思”的對話。
經典的意義是無限的、深遠的。正如布魯姆所說的“弗洛伊德原就無法追及喬叟和莎士比亞”,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是“天啟式的審美家”伍爾夫,即使是“西方傳統中最有天賦、最具原創性和最富煽動性”的文學批評家布魯姆,也難免無法完全追及喬叟及其作品。這是批評的局限,也是任何批評都無法超越的局限。而不得不承認的局限是,對于多數讀者尤其是本文論者而言,面對伍爾夫和布魯姆,面對他們才氣縱橫的文學批評,肯定也是無法追及甚至遙不可及。行文至此,借用布魯姆一段話作為此文的結語也許是必要的——“喬叟儕(躋)身于最偉大作家的行列——這些偉大作家挫敗幾乎所有的批評——這是他與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托爾斯泰同有的特質。另有一些賦有近似雄偉規模的作家——但丁、彌爾頓、華茲華斯、普魯斯特——激發頗為神妙的批評(其中更多是庸論),而喬叟,一如其寥寥數位儕列,賦有如斯強大的模仿力量,輕松地令批評家繳械,于是批評家們或是無事可做,或是仍有無數事可做”①[美]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