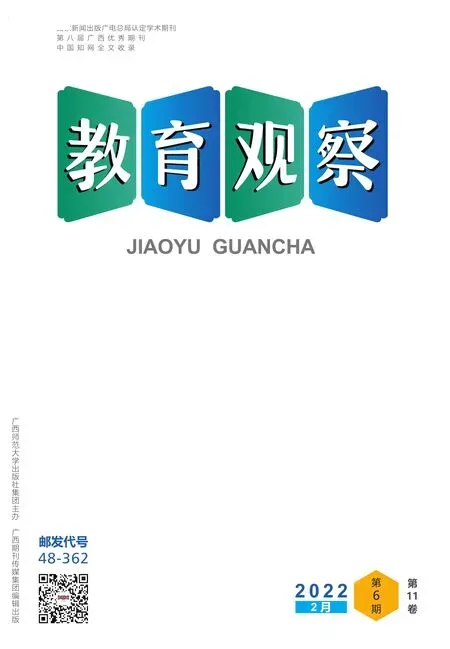STREAM活動中大班幼兒調查活動存在的問題及策略研究
王夢婧
(1.廈門市第九幼兒園,福建廈門,361000;2.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上海,200241)
近年來,STREAM活動備受關注,涉及S(科學)、T(技術)、R(閱讀)、E(工程)、A(藝術)、M(數學),涵蓋多個學科內容,非常考驗幼兒的綜合能力。調查活動貫穿于STREAM活動的始終,幼兒不斷萌發各種問題,需要運用各類工具搜集資料、記錄表征、解決問題、分享經驗。然而,筆者發現,調查活動存在諸多問題,一定程度上阻礙了STREAM活動的深度開展。依托廈門市第九幼兒園正在開展的課題“基于STREAM理念的幼兒園閩南本土文化教師課程領導力研究”,筆者在班級開展一系列基于STREAM理念的主題活動,歸納調查活動中出現的問題,并嘗試提出解決策略。
一、問題提出
(一)調查表設計欠妥,忽視幼兒年齡特征
金融大辭典將調查表定義為在統計調查中用于搜集、登記原始資料的表式,它是調查方案的核心部分。[1]然而,縱觀各類調查表,存在以文字形式呈現為主、調查問題不明確、記錄形式單一等問題。其設計忽視了幼兒理解書面內容的年齡特征和記錄表征的個體差異,幼兒往往不知所措。調查表設計欠妥,將影響幼兒自主閱讀、理解和提取有用信息,阻礙閱讀能力的提升。“STREAM”在“STEAM”中加入R元素,更加強調幼兒自主閱讀能力的培養。
(二)資源呈現形式不佳,幼兒無法活學活用
虞永平教授指出,經驗產生于主體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只有支持幼兒拿資源“做事”,才有可能將課程資源轉化為幼兒的經驗。[2]調查資源是一種寶貴的課程資源。然而,調查活動中這些資源往往以調查表的形式呈現,調查記錄雖圖文并茂,可當我們拿著一名幼兒的調查記錄去問另一名幼兒時,往往發現他們很難看懂彼此的調查內容。有些家長雖搜集了大量視頻資料,但不適合幼兒觀看、理解。這些豐富多樣、富有特色的原始資料,該以何種形式呈現,才能真正做到讓幼兒愛看、會看、懂運用?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三)調查結果缺乏梳理,阻礙幼兒系統習得科學知識
由于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撐,幼兒所收集到的調查結果十分豐富。然而,有些教師僅選擇簡單將調查報告隨意粘貼在墻面的做法。堆積的信息未經處理、加工,并不能轉化為知識。如在“鳥兒如何造窩”調查活動中,幼兒所收集的資料涉及不同鳥類、不同造窩方法和技巧,如果教師只是未經分類、梳理便將調查報告貼在墻上供幼兒觀看,那么幼兒很難形成對造窩不同方式特點的系統認識。STREAM活動強調知識的系統性,雜亂無章將不利于幼兒系統地學習科學知識。
(四)調查結果缺乏交流,降低調查的實效性
《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以下簡稱《指南》)中指出,要“支持幼兒與同伴合作探究與分享交流,引導他們在交流中嘗試整理、概括自己探究的成果,體驗合作探究和發現的樂趣”[3]。然而,盡管有的教師有意識引導幼兒進行談話交流,但分享形式局限于調查者“一言堂”,其他幼兒很快便失去了傾聽的興趣,這會影響調查者的信心與動力。談話活動是分享調查結果最常見的形式,然而調查結果往往分享過后便被束之高閣,調查發揮的作用戛然而止。
(五)調查活動缺乏系統性,不利于幼兒深度學習
調查活動具有問題導向性,具有以問題為出發點,幫助幼兒認識客觀事物的特性,以便幼兒解決問題。在STREAM活動開展過程中,幼兒會不斷遇到新問題,產生新的調查動機,每一次調查活動之間都是相互關聯的。雷有光等人指出,幼兒的學習是一個連續發展的整體,幼兒對經驗的深度學習是建立在淺層經驗的感知和體驗的基礎上的,不能割裂幼兒經驗發展的連續性和整體性。[4]然而,筆者發現幼兒的調查活動就像一口口淺淺的井,彼此孤立,點到為止。此外,STREAM活動涉及天文、地理、數學等不同學科經驗,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對教師的人文社會科學素養有較高的要求。教師如果沒有提前對調查對象做功課,將會在調查活動開展過程中處于茫然的狀態。比如,在“鳥類的天敵是什么”的調查活動中,如果教師沒有事先對鳥類天敵做研究,就無法對幼兒的調查結果做出合理的評價,幼兒的學習也將停留在淺層階段。
(六)家長缺技巧、勤代勞,影響調查活動的質量
家長在發展幼兒STREAM經驗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幼兒園對家長的“調度”缺位,當前,諸多家長缺乏相應的理論和行動來支持幼兒STREAM教育。[5]家長更傾向于讓孩子參加教學活動來學習STEM相關的知識和技能,而往往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引導孩子自然地探索STEM相關知識的機會。[6]很多家長不理解幼兒開展調查活動的意義,有的家長甚至不相信幼兒具備開展調查活動的能力。有的家長缺乏與幼兒有效溝通的技巧,且工作繁忙。種種因素使得家長代勞快速完成調查表的現象普遍存在。雖然有時候調查報告回收率很高,但卻很難在調查報告中看到幼兒主動參與的痕跡。
二、解決策略
(一)優化調查表設計,幫助幼兒理解與使用
筆者發現,調查表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呈現,既適合家長閱讀,也符合幼兒年齡特點。生動有趣的圖片和符號能夠幫助幼兒獨立閱讀理解調查的問題。比如,“小鳥愛吃什么”這個問題用小鳥叼著小蟲子的圖片和問號來表示,能夠滿足幼兒自主閱讀理解的需求。
調查問題應精小、明確、通俗易懂,讓調查更具有目的性。《指南》指出,5—6歲幼兒在成人的幫助下能制訂簡單的調查計劃并執行。[3]但筆者在實踐中發現,幼兒圍繞主題所萌生的問題具有隨意、寬泛等特點,需要教師適時引導,讓問題更聚焦。例如,在建造紅磚燕尾屋的活動中,幼兒萌發了“紅磚燕尾屋的墻怎么搭高”的問題。這個問題較為寬泛,如果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幼兒將很難精準地找到想要的答案。經過師幼討論、觀察紅磚燕尾屋墻體的細節圖片,教師引導幼兒漸漸將問題聚焦為“紅磚燕尾屋的墻體怎么用磚塊砌成”,由此協助幼兒更高效、精確地找到相關答案。此外,家長是調查活動必不可少的幫手,配以簡短、清晰的親子互動指導語能夠幫助家長快速理解自己在調查活動中的職責,提高親子互動的科學性。
(二)豐富調查形式,搭建共享平臺
1.豐富調查形式
閱讀相關文獻發現,幼兒調查活動搜集信息的途徑多以網絡搜索為主,導致信息重復率高,幼兒缺乏親身體驗與感知,調查存在照本宣科的傾向。[7]由于幼兒年齡小,他們獲取信息具有直觀性、親身感知性,幼兒調查需走進大自然與大社會,親身體驗,觀察、傾聽自然或社會中的事物,用不同方式感知與發現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科學現象,探索現象中的原理與方法。[8]如“鳥窩”主題活動中,幼兒帶上望遠鏡、記錄單,尋找幼兒園大樹上的鳥窩,結果發現了好幾個黑乎乎的窩,幼兒就此產生分歧,生成了“到底是蜂窩還是鳥窩”的調查活動。幼兒通過親子調查在網絡上搜集了大量蜂窩和鳥窩的圖片、視頻。考慮到安全性和專業性,幼兒園邀請了在消防支隊工作的消防員家長前來勘察,并對這位家長進行了采訪。閱讀角也被幼兒帶來的圖畫書和教師投放的各類百科全書填滿了,幼兒經常利用閑暇時間來這里閱讀,加深對鳥窩、蜂窩的認識。結合實地勘察、網絡搜索、采訪專業人士、閱讀書籍等多元調查方式,幼兒的調查熱情高漲,調查目的性更強了,調查也更深入了,所獲信息相互驗證、互相融通,幼兒獲得的新經驗也得到了鞏固和強化,幼兒還樹立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2.搭建共享平臺
資源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有一百種語言、一百種陳述自我的方式。筆者在調查表中提供了多種資源呈現形式讓幼兒自選,如幼兒繪畫表征、網絡視頻或者圖片、幼兒錄音或者拍攝等。幼兒可根據自己的喜好和能力自由搭配組合來呈現調查結果。比如,在“鳥類的天敵是誰”調查活動中,有家長協助幼兒在微信群發送了貓撲食小鳥的精彩慢鏡頭視頻,并在調查表中用生動形象的筆觸畫下了這一場景。在幼兒介紹該調查表時,教師在大屏幕上呈現這一視頻,資源動態可視化使調查結果不再以單一的繪畫表征形式呈現,有助于幼兒快速理解調查內容。又如,在制作推車活動中,幼兒帶上記錄紙和拍立得調查園內推車,觀察、記錄其外形、構造等,并將相應照片粘貼在記錄表上。我們發現,圖文并茂的共享形式讓幼兒在介紹時更加自信、從容,思路更清晰,語言更流暢,聽眾也更專注。個性化的資源組合形式滿足了幼兒多元表征的需求,讓調查內容以最靈動的方式訴說自己的故事。
(三)及時加工信息,助力幼兒解決問題
工程思維包括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和分析能力。[9]其中,幼兒是否能夠正確理解調查信息將直接影響到幼兒是否能夠分析和解決問題。調查中,家長將與幼兒共同搜集到的各類視頻、圖片發到班級群。筆者發現,來自網絡的影像資源良莠不齊,有的視頻雖畫面精彩,但內容過多,有的視頻沒有配音,有的視頻畫面跳轉速度過快,這些都不適合幼兒觀看與理解。教師可以根據幼兒年齡特點對視頻進行后期處理,或剪輯關鍵部分,或利用“慢鏡頭”功能,抑或根據視頻內容重新為視頻配上慢速、簡潔、易懂的配音解釋。比如,在“織布鳥是怎么做窩的”調查活動中,一位家長搜集到一個展示織布鳥從選址到完成造窩任務的完整過程的視頻,視頻聚焦造窩動作細節,畫面清晰,可惜是英文配音,幼兒無法聽懂。于是,教師進行消音處理,為每個造窩步驟配上簡單、童趣的介紹語。如當織布鳥完成圓環編織任務時,教師配音道:“快看,織布鳥編織出了一個小圓環,漂亮嗎?”經處理的視頻深受幼兒喜愛。
(四)多維度活用調查表,拓寬幼兒經驗
調查表缺乏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幼兒經驗的持續獲得。筆者結合實踐經驗,分別從墻面創設和集中教育活動兩個方面入手,進一步活用調查表,拓寬幼兒相關經驗。
1.巧用墻面引發經驗碰撞
將調查結果按照不同維度進行整理,以適合幼兒理解的方式呈現在墻面,將有助于幼兒發現更多調查結果的秘密。幼兒會發現,同一個調查內容,可能會有不同的調查結果;同樣的調查結果,可能會有不同的記錄形式。比如,在“鳥窩是怎么做成的”調查活動中,教師仔細解讀幼兒的調查記錄表和所搜集的網絡資源,創設了“造窩的秘密”主題版面,將幼兒的調查結果按照造窩形式的不同進行重組,裝訂成冊,供幼兒翻閱。教師還將幾種不同記錄形式的調查表單獨列出,引導幼兒觀察樹狀圖、發散圖、列表式、步驟圖等不同記錄方法,拓寬幼兒的表征思維。
2.有效鏈接集中教育活動
調查結果呈現了幼兒的已有經驗和興趣點,是教師設計生成性集中教育活動的重要依據,我們能夠從一份份調查結果中大致判斷幼兒對調查問題理解的深度、廣度,是否存在理解誤區,對什么問題最感興趣等。比如,在“鳥窩是怎么做成的”調查活動中,通過整理、分析調查結果,筆者發現幼兒主要探索了燕子、織布鳥、人工木質鳥窩的建造方式,可見,關于鳥類的造窩方式,幼兒的探索范圍較窄。于是,筆者生成了“鳥兒造窩的秘密”集中教育活動,以具有代表性的調查報告為活動導入,引出啄木鳥、棕灶鳥、火雞等更多不同鳥類的其他造窩方式,結合不同難度的記錄表幫助幼兒了解鳥類造窩使用的材料及造窩技法,使幼兒更深刻理解鳥類造窩的智慧。
(五)編織調查關系網,拓展調查深度與廣度
實踐發現,同一主題下的不同調查活動之間是相互關聯的,本次調查內容可能是上一個調查活動派生出來的新問題,也可能是在探究過程中產生的新困惑。比如,在“鳥窩”主題活動中,班級先后開展了“鳥窩是怎么做的”“鳥窩開口朝上不怕淋雨嗎”“小鳥愛吃什么”“鳥類的天敵是誰”“小鳥是怎么吃食物的”“小鳥的爪子是怎么抓東西的”等多次調查活動,調查問題隨著做鳥窩、制作喂鳥器等相關活動的開展不斷衍生出新問題,由鳥窩逐步聚焦鳥類的生活習性,調查由淺入深,調查線索縱橫交錯,共同織出一張鳥類秘密的網,讓幼兒的學習“看得見”。每一次調查活動,教師都應和幼兒共同解讀調查結果,協助幼兒梳理出新的調查思路,生發出更多有意義的調查活動。
(六)巧用家長資源,提高調查活動的專業性
家長來自各個學科領域,他們本身就是豐富的幼兒STREAM資源。而幼兒教師的知識結構比較有限,單靠一個人獲取資訊的途徑較少、思路較窄。面對同一個調查問題,不同家長會以不同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通過不同的軟件、平臺進行搜索,他們與幼兒共同搜集的資訊是海量的。此外,有的工程活動具有較強的領域專業性,需要獲取專業支持,而有的家長就是此類資源最佳提供者。比如,在建造閩南紅磚燕尾屋的活動中,筆者遇到了水泥如何混合、墻體如何堆砌的專業問題,這些問題通過網絡查詢雖然部分能夠得到解決,但是卻沒辦法實時解決幼兒不斷冒出的疑惑。為此,班級中某在房地產行業工作的家長就邀請了在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來幼兒園指導幼兒進行水泥攪拌、墻體堆砌。幼兒拿著記錄板、照相機,提前備好的采訪問題,與工人進行了熱烈的交談。這樣的調查活動為幼兒提供了與專業技術零距離接觸的絕佳機會。可見,家長資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STREAM活動的深度與廣度。
綜上所述,我們需要重視調查活動在STREAM活動中的重要性,正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時刻關注優化調查表的設計,豐富調查形式,搭建有效的分享平臺,促進交流,引導幼兒及時對調查資訊進行加工與分析,多維度運用調查結果,同時關注調查活動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巧用家長資源,為STREAM活動的開展賦予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