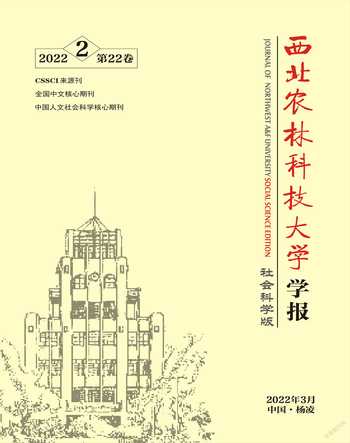數字治理:數字鄉村下村莊治理新模式
摘 要:數字鄉村建設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舉措。數字鄉村建設以數字空間為手段,構建數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數字治理,能夠提高鄉村數字化治理能力,推動鄉村治理轉型。數字空間的鄉村治理運作改變了鄉村治理的內容和形式,突出體現為完善村民協商自治、促進治理權力多元化、構建村民集體身份認同。同時,數字鄉村建設運用數字信息技術,重構傳統鄉村治理,促使鄉村治理主體增能、治理方式創新和治理共同體再造。數字治理以治理信息化為基礎,提高了鄉村治理效能,但也會產生數字負擔,增加治理成本。因此,數字治理要合理運用數字評價系統,以改善村民生產和生活為目標,提升村民“數字素養”,不斷縮小城鄉“數字鴻溝”。
關鍵詞:鄉村振興;數字鄉村;數字空間;數字治理;鄉村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2-0009-07
收稿日期:2021-09-30"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2.0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20CSH055);安徽大學農村社會發展研究中心2021年安徽高校科學研究重點項目(SK2021A0011)
作者簡介:丁波,男,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數字鄉村與基層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建設數字鄉村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數字鄉村”概念;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把數字鄉村作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1],并提出“數字鄉村是伴隨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以及農民現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內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轉型進程”[2]。2019年12月頒布的《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也將“建設鄉村數字治理體系”列為“推進管理服務數字化轉型”的五大任務之一[3]。隨著數字化、信息化和網絡化在農村社會發展中的運用,數字鄉村已成為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向。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綱要》指出要“著力發揮信息化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基礎支撐作用,構建鄉村數字治理新體系”,并提出“把數字鄉村擺在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位置”,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向鄉村延伸,提升鄉村治理信息化水平,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4]。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可以說,數字鄉村建設著重于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增強農村的數字化發展能力,以數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為手段,提高鄉村數字化治理能力,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和轉型。
當前,學界關于數字鄉村背景下推進鄉村治理轉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關于數字鄉村治理內涵的研究。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以數字信息技術重構鄉村治理要素[5],增強鄉村治理能力,改變鄉村治理過程、治理內容、治理方式等,優化鄉村治理體系[6];另一方面,數字治理能夠彌補以往鄉村治理缺陷,順應數字時代發展趨勢,不斷提升鄉村治理能力[7]。二是關于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治理的內在關系研究。數字鄉村建設推動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表現為多元主體共治、治理決策智能、治理基礎和治理環境改善[3],以此改變鄉村治理結構,擴充鄉村治理主體,創新鄉村治理機制和治理方式[6];同時,數字鄉村建設通過數字化治理手段,推動治理主體、治理要素、治理結構的協調整合,進而有效提高鄉村治理效能[8]。三是關于數字鄉村治理的特征研究。數字鄉村治理不僅具有彈性再造治理空間、靈活設置治理機制、協同參與治理流程的特征[9],而且擁有數字化的內在韌性治理發展趨向[10]。
總體來看,既有研究多關注數字鄉村治理的內涵、特征和形式,但對數字鄉村治理推進鄉村治理轉型的運行機制和治理邏輯,以及數字治理對鄉村治理的多重影響關注較少。“作為一種社會趨勢,信息時代的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網絡構建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11]。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在鄉村治理實踐中數字化的虛擬空間逐漸崛起,并推動鄉村治理內容和形式發生新的變化。因此,本文聚焦于數字鄉村背景下的鄉村治理轉型,沿著“數字鄉村-數字空間-數字治理”的分析路徑,研究“數字空間”在鄉村治理中的運作,分析數字鄉村重構鄉村治理的內容和形式,并基于此提出新時代數字鄉村的治理模式,最后探討數字治理作為鄉村治理模式的雙重效應,以期對原有數字鄉村研究做出補充。
二、數字空間的鄉村治理運作
數字技術凸顯數字空間的實效性。數字空間成為人們生活、生產和社會關系的重要工具手段,使得個體能夠突破時空分離,從而改變個體的行動特征和群體的聯結方式,優化社會運作機制。數字空間作為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其鄉村治理運作分別體現在促進村民協商自治高效開展、推動鄉村治理權力的多元化發展、構建村民新的集體身份認同。
(一)數字空間與村民協商自治
隨著農村勞動力外流的加劇,鄉村治理面臨村民參與程度低的實踐困境。村莊內紅白喜事、民俗文化活動等,能夠促進村民之間的合作和聯結。但這類集體活動隨村莊人口減少也在減少,鄉村治理空間相應被擠壓。同時,空心化村莊中留守群體對村莊公共事務關注度低,導致鄉村治理效能低下。村民自治是基層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通過村民自治能夠選舉代表村民利益和訴求的“當家人”。然而,隨著勞動力外流,村民參與村莊自治的積極性越來越低,村莊在選舉中出現參選率和投票率較低的現象嚴重影響著村民自治制度的實際運行。
數字空間將多元治理主體重新匯聚在同一治理空間中,村莊公共事務和議題被發布于數字空間,分散在各地的村民可以針對村莊公共事務和議題進行協商自治和公共決策,從廣度和深度上增強村民自治的民主性。數字空間所形成的虛擬公共空間突破了現實空間的阻隔,為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議事協商提供平臺。數字空間中不同主體的話語權能夠充分表達,從而有效推動自我管理、自我監督和自我服務[12]。
當前,農村年輕人多在外地務工,只有在逢年過節時村莊才“人氣旺”,平時村莊公共事務很難接收到村民的意見反饋,鄉村治理的自下而上機制并不暢通。為此,通過創建鄉村QQ群、微信群等“微平臺”,使外出人員能夠及時了解村莊發展變化,并為村莊發展建言獻策,增強村民身份認同和歸屬感。“微平臺”有利于提升鄉村治理的集體行動意識,拓展數字空間的公共性。目前,農村建有黨員微信群、外出人員微信群等不同類別“微平臺”,使在外村民能夠參與村莊公共事務和集體行動。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微信群的主要議題是“工作和工資”,黨員服務群的主要議題是“矛盾調解、例行開會”,村民微信群主要議題則是“娛樂和村莊發展”。
(二)數字空間與治理權力多元化
在以往鄉村治理中,治理主體既有正式治理權威,也有非正式治理權威。鄉村治理主體通常是熟悉地方性知識的村莊精英,他們擁有村莊的治理權威。數字空間作為鄉村新型治理空間,其特征不同于現實中的治理權威和權力結構,它具有分散化、匿名化和符號化特征,所以導致治理空間的權力結構產生變化。一方面,數字空間的各個主體的自由度較高,不受空間位置的影響,每個網絡主體都有對公共事務和議題發表言論的自由。數字空間權力和權威中心的標志是其他網絡主體的認可,而這一前提是依靠數字空間中的言論觀點成為數字空間的意見領袖。因此,數字空間的交往互動方式不受現實治理空間的控制,往往更在乎言論的合理性、正確性和邏輯性,所以現實治理中的權力和權威對數字空間的影響較少。另一方面,數字空間能夠帶來不同的話語資源,通過村民和社會力量的參與,形成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發展路徑。數字空間使得村莊公共信息傳播更為分散,公共決策主體更加多元,政策實施由村民協商自治決定[13]。鄉村治理主體受年齡、知識結構、數字技術等影響,其在數字空間往往并不是處于中心位置。與此相反,有些在現實生活中沉默寡言的村民,卻在虛擬數字空間中處于中心位置,成為數字空間的意見領袖,主導數字空間的公共事務和議題走向。因此,數字空間的存在,使得治理權力和權威發生改變,從而影響鄉村治理權力的運作。此外,數字空間是村民普遍參與的信息交流和交往聯絡的社會空間[14],在數字空間中,通過QQ、微博、微信等網絡平臺,以電子布告欄、電子信箱、博客等形式,村民可以在虛擬網絡中進行跨地域溝通和交流,客觀上加強了村民居住地和鄉村住所地之間的信息互通,提高居住地和住所地之間的治理效率,實現村民信息的互通共享,防止出現“兩不管”的雙重治理模糊地帶。
(三)數字空間與集體身份認同構建
曼紐爾·卡斯特認為,網絡空間中群體是以社會認同為中心而集結形成[15]。數字空間作為鄉村社會公共空間的延伸,村民在數字空間中消除疏離感與陌生感,使村民逐步從“私人領域”轉向“公共領域”[12]。數字鄉村通過運用數字空間,一方面提高了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使村民足不出戶就能夠了解村莊各類公共事務。外出務工的村民雖然遠離村莊空間,也能知曉村莊發展的動態。另一方面數字空間強化了村民身份認同,尤其是外出務工人員的自我認同,通過將分散各地的村民集聚其中,再造了村民的集體認同,同時增強了外出務工人員的凝聚力和集體感。數字空間作為彌補傳統公共空間萎縮的重要平臺,承載了傳統公共空間的社會交往功能,能夠重振鄉村治理的活力[13]。
農村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齡化,使得村民對原有村莊的認同感減弱,村莊公共性逐步流失。首先,村民外出務工進入城市,久而久之,他們對鄉村社會認同感慢慢降低,尤以年輕的外出務工者最為顯著。長期在外打工的青年村民,他們向往城市生活,但由于多重原因形成“融不進、回不來”的身份認同困境,通過數字空間的互動,能夠增強其地域共同體意識,強化對于其所屬村莊的身份認同。其次,數字空間能夠喚醒鄉村社會記憶。鄉村社會記憶具有情感性,它是村民共同的情感記憶和文化基礎。數字空間通過微信群圖片、朋友圈等形式,喚醒村民對于集體或兒時鄉村生活的記憶。村莊集體記憶是鄉村代際傳承、鄉村秩序建構、激發村民對鄉村的情感的重要紐帶,也是塑造村民鄉村認同的重要力量[16]。鄉村社會記憶的喚醒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民身份認同,強化離散化的村民對家鄉的認同感。最后,治理主體通過數字空間將在外居住的村民聯結起來,使村民外在資源信息能夠在數字空間進行匯聚和交換,并依托鄉土情感進行公共交往,擴充和整合村莊的外在治理資源。總之,村民在數字空間的持續互動,能夠增進其相互之間的公共交往,促使原子化的村民參與集體行動和公共事務,強化村民的集體認同感和歸屬感[12]。
三、數字鄉村的治理邏輯
鄉村治理研究主要關注“誰在治理”的治理主體、圍繞“如何治理”的治理方式以及聚焦“治理怎么樣”的治理共同體的三個維度[17]。數字鄉村以其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特點形塑著鄉村治理主體、治理方式和治理共同體[18]。數字鄉村通過數字空間的運用,改變治理主體、治理方式和治理共同體,從而推進鄉村治理轉型。
(一)數字鄉村與治理主體增能
當前,人口外流意味著傳統村莊共同體的作用減弱。傳統鄉村社會是實體治理關系,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是面對面的互動。然而,人口流動使得這種實體治理關系缺少正常運行的條件,導致鄉村治理面臨“治理對象缺場”困境。作為新型治理空間,數字空間推動治理關系由實體關系向虛擬關系轉變,將遠距離的不同空間主體拉近到同一虛擬治理空間,賦予治理主體跨越時空的治理能力。
數字鄉村使得治理主體能夠通過數字空間的聯結紐帶進行“遠程辦公”,避免出現由于治理對象的“不在場”而造成無效治理的困境。數字鄉村的治理主體增能,主要是應對村莊空心化的結構困境,通過數字空間的運用,治理主體能夠對“不在場”的治理對象實施“線上”治理,進而增強數字鄉村的治理能力。第一,數字鄉村通過構建虛擬治理空間,充分調動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第二,數字鄉村依托“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治理網絡體系,大力推進信息共享、業務協同、部門聯動、上下貫通,整合各類信息,構建共享信息數據庫,加快互聯網與鄉村治理和服務體系的深度融合。第三,數字鄉村充分發揮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在引導村民互動互助、參加村莊活動和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創新鄉村治理形式。數字鄉村的虛擬治理空間目標主要是以先進的鄉村管理和服務理念、利用現代技術手段,打造“資源數字化、應用網絡化、流程規范化”的智慧化鄉村管理和服務體系。數字鄉村的虛擬治理空間提高了鄉村管理和服務工作效率,使信息資源開發不斷滿足管理村莊、服務村民的需求。
(二)數字鄉村與治理方式創新
傳統鄉村社會作為一個封閉性共同體,村民外出流動的頻率較小。隨著改革開放后城鄉流動的加速,村莊邊界逐漸由封閉向開放轉變,村民的流動性增強,并在流動過程中不斷改變社會交往。當前,農村社會結構由“熟人社會”轉向“半熟人社會”,農村的傳統聯結紐帶逐步減少,農民之間的交往關系減弱。農村流動人口主要是在城市務工,而且以青年人居多。村莊發展缺少主體力量,導致鄉村社會的衰落。農村人口的外流使村莊呈現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齡化的困境。鄉村治理關系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不在場”的治理。缺少治理對象參與,表現為“人戶分離”,即村民戶籍仍然在村,但工作生活在城市,國家權力也難以下沉,導致鄉村治理的低效和懸浮。治理主體中“身體缺場”,使“缺場交往”逐步取代“在場交往”[19]。
數字鄉村的治理基礎是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治理主體通過數字空間對遠離在居住地的流動人口進行有效治理。數字鄉村的治理平臺不僅包括數字信息平臺,還擁有信息化的數字信息系統。例如,數字鄉村通過數字信息系統,自動撥通村民電話,傳送村莊各種活動信息。自動撥通電話系統能夠提高宣傳效率,節約治理主體的時間精力。
(三)數字鄉村與治理共同體再造
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應該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礎上、緊密聯系、排他的社會聯系或共同生活方式”[20]。鄉村社會的傳統共同體包括地域共同體、價值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等。傳統村落是熟人社會的共同體,表現在相似的價值觀、利益觀和人際圈,并且是基于“倫理”和“人情”的農村社會結構。而當前村莊人口外流所導致的村民經濟利益上的分化和心理上“陌生人化”的趨勢,打破了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基礎,并逐漸形成“關起門過日子”的普遍心態[21]。
數字鄉村共同體不同于傳統封閉的共同體,它是兼具開放和流動的治理共同體。數字鄉村的治理共同體再造的基礎是重建聯結紐帶,治理共同體在聯結紐帶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并特色鮮明。作為新型治理共同體再造的重要聯結紐帶,數字空間跨越地域空間的阻隔,將分散和“不在場”的治理對象組織動員起來,有利于改善治理關系。在數字空間中各個主體間的溝通主要是依靠網絡節點進行,其聯結方式不是傳統“面對面”的交往和聯系,而是依靠數字信息的溝通。數字空間作為自由話語的空間,促使村民“共同在場”和“公共交往”。村民可以不受實體空間的限制,通過數字空間“在場”參與鄉村治理,重建治理共同體,促進數字空間中的各個行為主體形成持續互動和共同行動。簡言之,作為數字鄉村的聯結紐帶,數字空間是再造村莊新型治理共同體的重要基礎。
四、數字治理的內涵特征及其正負效應
(一)數字治理的內涵特征
顧名思義,數字治理是指以數字信息技術為手段的治理行為。然而,數字治理中的數字信息技術不僅僅是治理手段,更是一種治理效果的體現。一方面,鄉村治理運用數字信息技術提高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數字信息技術幫助鄉村治理升級,打造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鄉村治理體系。數字鄉村的數字治理是通過數字空間的治理運作,構建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數字技術組織體系,以促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5]。數字治理作為新時代鄉村社會的重要治理模式,不僅表現為治理方式的數字信息技術運用,而且體現在治理過程中村民“數字素養”的提升。換言之,數字治理是通過數字信息技術實現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和集體活動的數字治理行為。
數字治理不同于傳統治理模式,治理主體通過數字空間的聯結紐帶,將治理行為從“線下”轉為“線上”,實現不同地理空間跨越的“線上治理”。治理主體憑借數字信息技術,能夠跨越地理空間阻隔實施精細化、精準化的治理。這里的數字信息技術不但有常用的微博、微信、QQ等網絡媒體,而且還有網格化人工巡查網絡,借助視頻監控、大數據分析等數字信息化手段,及時獲取和處理村民的各項事務,以應對鄉村治理中的各種問題,實現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治理。
此外,數字治理不僅強調鄉村治理中的數字信息技術運用,還突出治理對象“數字素養”的提升。在數字鄉村建設中,作為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村民“數字素養”不斷得到提升,有利于推動鄉村治理轉型和縮小城鄉“數字鴻溝”。村民“數字素養”的提升主要體現在村民生活向度和鄉村治理向度:一方面村民運用數字信息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改善生活質量;另一方面村民利用數字信息技術參與鄉村治理,在數字空間中建言獻策,暢通鄉村治理的自下而上溝通渠道。簡言之,數字治理將傳統治理手段與數字信息技術相結合,緩解了治理對象流動性強的難題[19],提升了村民“數字素養”,增強了鄉村治理能力。
(二)數字治理的正負效應
數字治理依賴于數字信息技術,但在實際治理過程中存在數字治理的雙重效應:一方面數字治理可以提高鄉村治理效率,便于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另一方面,數字治理也造成鄉村治理任務倍增,導致鄉村治理壓力加大。
1.數字治理信息化與有效治理。數字治理信息化是推動數字鄉村的重要措施,治理信息化不僅能夠整合公共資源,而且可以為村民提供及時有效的便捷公共服務,進而提高鄉村治理效能[22]。治理信息化的前提是完善的治理數據庫。完善的治理數據庫有利于村民的差異化和個性化需求發展,優化了治理資源,進而提高鄉村治理效率。數字鄉村運用數字空間,建立真實與虛擬相結合的治理單元,不斷完善“線上鄉村”的各項功能,使得“線上鄉村”整體涵蓋社保、醫療、教育、人口管理等多元化服務,提高回應村民訴求的速度和效率,提升服務的精細化與精準化水平[23]。目前,數字鄉村采取信息化的主要措施是推進互聯網信息技術融入鄉村治理,促進互聯網技術與鄉村治理深度契合,提高鄉村治理效能[22]。鄉村治理主體通過治理信息化,提高治理與服務效率,促使治理與服務活動更加精細化、專業化。治理信息化作為數字治理的重要形式,它有利于增強鄉村治理能力,推動鄉村治理轉型。例如,數字鄉村建設中的“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在便民服務中心設立“互聯網+政務服務”的工作臺,工作臺包含公眾號的內容和功能介紹、操作步驟,并有村干部進行引導和幫助。上級部門在后臺能夠及時準確地看到每個村民注冊、運用公眾號的人數。服務公眾號作為便民服務措施,方便了村民辦理相關事務。
2.數字治理負擔與治理限度。默頓認為一項技術的運用,不但要考慮其正功能,還要考慮其負作用,而且還要關注技術運用的潛功能。同樣,數字治理具有標準化、規范化的治理特征,迎合了科層制官僚人員的喜好,在基層治理中廣泛推廣和運用,方便上級政府對基層治理的監控和檢查。但數字治理所代表的技術治理和治理硬度,導致治理主體過分依賴數字表面和技術手段,并在治理過程中注重量化考核和專項治理,進而產生基層治理的懸浮化。一方面,數字治理使得基層為想方設法達到上級政府的數字要求而采取各項非常規治理行為,導致治理目標發生異化。同時,治理目標的數字要求,通過“層層加碼”,使得基層的治理任務和治理壓力劇增;另一方面,雖然數字治理能夠適應目前治理新形勢的變化,如對流動人口的有效追蹤和管理等,但數字治理過密化的技術發展增加了治理成本,而且影響了治理效能的邊際優化[24]。此外,數字治理缺乏傳統“面對面”治理的情感溫度,使治理過程中情感距離加大,不利于治理的情感溝通和新型治理共同體再造。
五、結 語
在鄉村治理過程中,要合理運用數字評價系統,發揮數字信息技術的積極作用,使數字信息技術成為提高鄉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同時,要重視以數字治理為代表的技術治理趨向,努力將數字治理與鄉村振興相結合,推動數字治理背后的鄉村高質量發展。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振興的推進程度并不能完全依靠數字來體現。當前,鄉村振興主要在于推動農村的內涵式發展,因此評估一個地區的農村發展狀況時,不僅應關注農村發展的各項數字,而且也更關注這些數字之外的內涵建設。例如,農村人居環境、村莊生態環境、村莊鄉風文明等。數字治理不僅要看數字表面的“光鮮亮麗”,更要看到數字背后的“真實成績”,使得數字真正反映發展的真實性。總之,數字鄉村的數字治理不僅僅只是提高鄉村數字化治理水平,更是要切實改善村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提升村民“數字素養”,進一步縮小城鄉“數字鴻溝”。
參考文獻:
[1] 劉少杰,林傲聳.中國鄉村建設行動的路徑演化與經驗總結[J].社會發展研究,2021(02):13-22.
[2] 郭美榮,李瑾,馬晨.數字鄉村背景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發展現狀與提升策略[J].中國軟科學,2021(07):13-20.
[3] 江維國,胡敏,李立清.數字化技術促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研究[J].電子政務,2021(07):72-79.
[4] 常凌翀.縣級融媒體創新數字鄉村治理的內在邏輯與推進路徑[J].中國出版,2021(14):37-41.
[5] 劉俊祥,曾森.中國鄉村數字治理的智理屬性、頂層設計與探索實踐[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1):64-71.
[6] 王薇,戴姣,李祥.數據賦能與系統構建:推進數字鄉村治理研究[J].世界農業,2021(06):14-22.
[7] 沈費偉,陳曉玲.保持鄉村性:實現數字鄉村治理特色的理論闡述[J].電子政務,2021(03):39-48.
[8] 沈費偉.數字鄉村韌性治理的建構邏輯與創新路徑[J].求實,2021(05):72-84.
[9] 韓瑞波.敏捷治理驅動的鄉村數字治理[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4):132-140.
[10] 沈費偉.數字鄉村韌性治理的建構邏輯與創新路徑[J].求實,2021(05):72-84.
[11] 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王志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569.
[12] 楊冬梅,單希政,陳紅.數字政府建設的三重向度[J].行政論壇,2021,28(06):87-93.
[13] 鞠真.虛擬公共空間對基層治權的重塑——基于A鎮實證調研[J].天府新論,2019(05):106-115.
[14] 劉少杰.網絡空間的現實性、實踐性與群體性[J].學習與探索,2017(02):37-41.
[15] 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M].曹榮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416.
[16] 郭明.虛擬型公共空間與鄉村共同體再造[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6):130-138.
[17] 李祖佩,梁琦.資源形態、精英類型與農村基層治理現代化[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2):13-25.
[18] 鄭永蘭,信瑩瑩.鄉村治理“技術賦能”:運作邏輯、行動困境與路徑優化——以浙江F鎮“四個平臺”為例[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3):60-68.
[19] 何鈞力.高音喇叭:權力的隱喻與嬗變——以華北米村為例[J].中國農村觀察,2018(04):2-16.
[20]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78.
[21] 錢全.分利秩序、治理取向與場域耦合:一項來自“過渡型社區”的經驗研究[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5):88-96.
[22] 陳榮卓,劉亞楠.城市社區治理信息化的技術偏好與適應性變革——基于“第三批全國社區治理與服務創新實驗區”的多案例分析[J].社會主義研究,2019(04):112-120.
[23] 朱士華.以信息化打造農村社區治理新圖景[J].人民論壇,2018(18):66-67.
[24] 王雨磊.數字下鄉:農村精準扶貧中的技術治理[J].社會學研究,2016(06):119-142.
Digital Governance:A New Model of Village Governace Under Digital Countryside
DING B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Digital countrysid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 key measure to modernize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Digital countryside uses digital space as a means to build digital,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digital governance,improve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and promote rur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The ope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digital space has change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rural governance, which is embodied in improving villagers’ consultative autonomy,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governance power and constructing villagers’ collective identity.At the same time, digital villages use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construct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and promote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s,governance mode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As the governance mode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digital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ization of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governance,but it will also produce digital burden and increase the cost of governance.Therefore, digital governance should make reasonable use of digital evaluation system to improve villagers’ production and life,enhance villag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constantly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digital countryside;digital space;digital governance;rural governance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