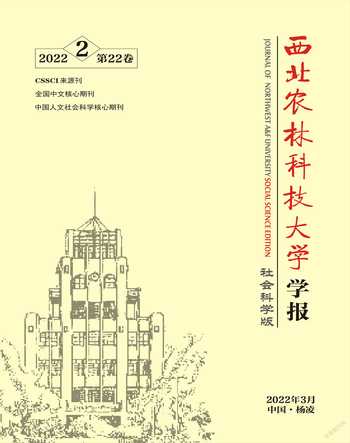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烙印效應








摘 要:就業經歷對個體后期成長過程中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特征有著重要影響。基于新型職業農民的混合截面數據,采用Probit、Oprobit、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模型,從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兩個維度綜合考察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結果表明:新型職業農民的非農就業經歷能夠通過發展能力烙印,促進其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政策支持能夠強化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的影響。進一步分析發現,不同個體非農就業經歷對其成長影響存在差異。應重視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的經濟和社會效應,多渠道促進新型職業農民能力提升,構建和保障新型職業農民成長壯大的政策支持體系。
關鍵詞:非農就業經歷;新型職業農民;烙印理論;拓展性成長;效益型成長
中圖分類號:F328;C9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2-0063-11
收稿日期:2021-06-28"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2.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9ZDA115);廣東省軟科學項目(2019A101002115);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020A1515011202)
作者簡介:雷顯凱,男,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
通信作者
引 言
“產業興才有鄉村旺”,關鍵在人才,尤其是能夠帶動鄉村產業發展的人才。其中,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新型職業農民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著積極的示范帶動作用,是破解“誰來種地”難題的關鍵主體。
與傳統農民不同,新型職業農民是以農業為職業、懂技術會經營、收入主要來自農業并達到相當水平的現代農業從業者[1-2]。目前,學術界對新型職業農民的成長環境、經營收入,特別是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進行了多角度研究[3-5]。越來越多的具有經商、務工等不同就業經歷的“三鄉人才”進入農業生產經營行列而成為新型職業農民[6],使得新型職業農民隊伍迅速發展壯大。截至2020年,全國新型職業農民數量突破1 700萬人。根據《2020年全國高素質農民發展報告》數據顯示,近50%的新型職業農民為新生力量,其中以進城務工返鄉人員和大中專畢業生為主,相當部分新型職業農民具有非農就業經歷。新型職業農民經營績效也發生了可喜變化。與2018年相比,2019年新型職業農民的人均農業純收入提高了5.43%。有學者通過對新型職業農民調查分析發現,雖然新型職業農民年平均收入高于傳統農民年收入,但遠低于自己預期年收入水平[7]。將新型職業農民從農業領域“新進入者”(或者再次進入者)培育成“領域能手”,必須分析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發展的非農就業經歷和其影響。
烙印理論為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與其成長的關系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視角,它強調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尤其是在敏感期的非農就業經歷對其一些特質可能產生的重要影響[8]。經歷是指個體對某件事情的親身體驗,如果這類事件具有影響范圍廣、影響程度強和時間上有一定持續性的特點時,便會給個體打上更深的能力和認知烙印[9]。在研究對象上,現有研究多從組織或者組織內部角度探討烙印效應對農民成長或者經營績效的影響。關于經歷對個體的影響研究則主要集中在農民饑荒經歷、從軍經歷和知青經歷等方面。如早年的饑荒經歷對后期農戶土地租出行為有阻礙作用[10],但對農戶農地調整意愿有促進作用[11]。另外,相關研究議題主要集中在新型職業農民的非農就業經歷與其培育和收入方面[6,12]。事實上,作為一個有機生命體,新型職業農民的成長過程不同于傳統農民,有其自身的特質,比如較強的學習意識、合作意識和風險意識。但這方面的相關研究比較缺乏。本文基于烙印理論視角,以廣東省676份新型職業農民問卷調查數據為樣本,分析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所形成的能力烙印對其成長的影響。考慮到個體成為新型職業農民后,政策支持也可能會對其成長產生影響,因此,選取政策支持作為調節變量做進一步拓展分析。
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1)豐富和深化了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對其成長的影響分析,為研究新型職業農民成長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2)從能力提升和政策支持兩個方面探討了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進一步揭示了內生動力和外生助力的合力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
一、研究假設
(一)非農就業經歷助推新型職業農民成長
新型職業農民的非農就業經歷代表了新型職業農民在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之前的知識儲備,是影響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重要初始條件。楊學儒等的研究發現,創業者先前的創業經歷豐富了個體經驗,進而推動所創辦的農業企業發展[13]。具體的,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主要作用可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非農就業經歷有助于新型職業農民思想觀念轉變,推動其快速接受農業新知識新技術。與其他生命有機個體一樣,新型職業農民的成長會經歷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對于剛進入農業生產領域的新型職業農民來說,由于先前就業經歷積累的經驗可以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其克服“新進入者”缺陷。比如,在城市長時間居住和工作,可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個體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
2.非農就業經歷發揮路徑依賴作用,降低新型職業農民生產經營風險。新型職業農民的非農就業經歷是其把握市場機會、實現成長的重要資產[14]。面對復雜的經營環境和海量信息,非農就業經歷中的一些行業知識儲備可以推動新型職業農民形成自己獨特認知結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會受到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雙重影響,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新型職業農民會傾向于關注已有的相關知識,依賴先前的相關經歷積累的經驗,降低農業生產活動中的風險沖擊。總的來說,作為“經濟人”,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為追求經濟報酬最大化,新型職業農民會依據自身資源稟賦,在成本收益比較結果的基礎上做出合理的決策行為,促進其成長。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一個研究假設:
H1:非農就業經歷助力新型職業農民成長。
(二)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成長:能力提升的中介效應
非農就業經歷會給新型職業農民打上能力烙印,促進行為能力的提升。賦能是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內生基礎[15]。在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基本相同的情況下,農業生產經營效益出現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個體能力的差異。現代農業發展主要依靠知識經濟、高科技產業,而知識經濟要求新型職業農民具備洞察市場能力、市場應變能力以及豐富的經營管理能力。可以說,通過多渠道對新型職業農民賦能是促進其成長的必由之路。非農就業經歷作為個體的寶貴財富,對新型職業農民的成長起著重要作用。這種作用不僅直接影響其成長,還可以通過非農就業經歷提升可行能力,間接影響其成長[6]。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非農就業經歷拓寬社會網絡,推動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社會網絡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縮小收入差距[16]。現代農業生產活動改變了以往封閉型特征,向以市場為導向的開放型轉變,從生產資料的投入到農產品銷售等環節都需要信息收集、分析以及政策解讀能力,缺乏相應的社會資源就不利于實現生產經營增收目標。有非農就業經歷的新型職業農民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建立了一定的社會網絡關系,這類新型職業農民如果初次或者再次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就可以通過社會網絡獲取信息和其他有形或無形資源。社會網絡帶來的經濟效應與其規模大小息息相關,豐富的社會網絡關系意味著新型職業農民接觸到的組織或者個體數量也就越多,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可能越豐富。既往非農就業經歷幫助新型職業農民建立以“業緣”為主的社會網絡,突破了“地緣”和“親緣”網絡的限制,擴大了其社會網絡規模,為其成長提供了信息等關鍵性資源。
2.非農就業經歷可以積累農業生產資金,助力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生產資金是農業生產活動不可或缺的要素,直接影響新型職業農民生產經營決策。新型職業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必要前提是積累了一定的經濟資本。相對于傳統的小農戶,新型職業農民生產經營規模更大,有了一定的經濟資本,可以更好滿足農業生產需要,引進新的生產技術,弱化經濟約束。比如,購買種子和機械設備的經濟約束也就越低。與務農相比較,外出務工最明顯的例證就體現在個體物質財富的積累[17],而且對于有過非農就業經歷的新型職業農民來說,會更容易獲得經營資金和客戶資源[3]。
3.非農就業經歷豐富個體人力資本,促進新型職業農民成長。人力資本在新型職業農民農業經濟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提高農業技術使用效率、學習新的生產技術等。新型職業農民在非農產業就業時,該行業的專業知識、要求、標準和價值觀會伴隨時間的推移給個體打上烙印,獲得相應的知識和經驗,形成其理解和指導日常工作的認知模式。石智雷等的研究發現,非農就業經歷使得農民思想觀念得以改變,他們更容易接受新事物[18]。周廣肅等的研究發現,早年的上山下鄉經歷能夠提高個體投資能力和強化風險意識[19]。外出務工使得新型職業農民學習了其他行業的知識,開拓了視野,改變了原有的知識和思維模式。當其再次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時,非農就業經歷獲取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可以幫助新型職業農民快速適應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有“體制內”就業經歷的新型職業農民因其熟悉政府單位的運作規律,使得其對農業政策的把握能力和理解能力更強[20]。能力越強越利于新型職業農民優化農業生產要素資源配置,降低生產經營成本,促進其成長。總體上,對于新型職業農民而言,非農就業經歷為其提供了不同的知識和信息,使得其在進行農業生產經營決策時,可以參考或借鑒過去的規范、經驗和策略,降低其對環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判斷。特別是對于初次就業或者某個行業“新進入者”來說,所處的環境發生重大改變,原有的認知水平或結構受到新環境的挑戰。比如,當返鄉創業的個體成為新型職業農民后,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他們將會面臨農產品的種植和銷售等各種決策選擇,因此新型職業農民的非農就業烙印會在農業生產需要作出決策判斷的過程中顯現出來,從而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產生重要影響[21]。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個研究假設:
H2:能力提升在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成長關系中發揮中介效應。
(三)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成長:政策支持的調節效應
非農就業經歷使得新型職業農民積累了更為豐富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物資資本,可提升自身能力,促進其成長。但新型職業農民成長又會受到外部環境,如農業政策支持的影響。農業政策支持是各國政府保護和促進本國農業發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22]。新中國從成立到現在,農業政策由最初的索取向現在的反哺轉變。取消農業稅、實施農機具購置補貼等農業支持保護政策,在擴大農業生產規模、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和促進農民增收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新型職業農民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中,政策支持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新型職業農民能否獲得政策支持,直接或間接影響其利益和市場競爭力,比如,優惠融資和政治談判能力等[23]。此外,政策支持還可以發揮激勵和調控的作用[24]。總的來說,政策支持可以通過發揮資源補充效應,影響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成長之間的關系。
政策支持是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一個外在保障,通過發揮資源補充效應影響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為促進新型職業農民的快速健康發展,政府一般會給予新型職業農民更多補貼或稅收優惠政策,使得新型職業農民的平均補貼水平或者優惠力度高于傳統小農戶,從而通過資源補充機制促進新型職業農民發展。主要表現為直接和間接的兩種形式,一是直接的資源獲取。財政手段通過直接的生產資源補充作用于新型職業農民,比如,家庭農場補貼和農民專業合作社補貼等。對于剛進入農業領域的新型職業農民來說,農業產業是一個新的領域,農業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成本和生產經營風險,激勵新型職業農民增加農業生產經營投入、擴大生產規模。二是間接的信號傳導。新型職業農民獲取相關政策扶持,表明其積極響應政策導向,以此向外界傳遞出新型職業農民與政府關系良好的信號,有利于新型職業農民通過多種渠道獲得外部資源,促進其成長[25]。同時,新型職業農民在充分利用非農就業經歷所積累的資源進行農業生產決策時,會根據可能獲得的農業相關政策支持積極做出相應調整,即政策支持對新型職業農民生產經營起著促進作用。對于有外出務工經歷的新型職業農民來說,獲得政策支持更有利于生產績效的提升[26]。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三個研究假設:
H3:政策支持能夠強化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
二、數據與變量選取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9年12月和2020年3月在廣東省進行的新型職業農民問卷調查。得益于較好的政策支持和經濟條件,廣東省新型職業農民數量和生產經營效益得到了快速發展,截至2018年底新型職業農民數量達到74萬人。2018年廣東省農業農村廳公布了多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示范基地名單,不同培訓時期新型職業農民來源地區不同。根據各個培訓時間點的實際情況,為保證數據質量,課題組采取隨機抽樣的方式對參加培訓的新型職業農民發放調查問卷。兩次調研共發放690份調查問卷,收回683份。在剔除存在異常值的樣本后,本文最終使用676份有效問卷,問卷使用率為98.98%。針對本文研究重點,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包括:(1)新型職業農民所在村莊層面特征,如村所在地理環境和距離鎮政府遠近等;(2)新型職業農民個體特征,如就業經歷和培訓經歷等;(3)新型職業農民生產經營狀況,如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農業生產經營類型、雇傭勞動力和農業保險等。
(二)變量選擇與測量
1.被解釋變量:新型職業農民成長。作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借鑒李旭等的研究[27],從拓展性和效益性兩個方面衡量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用“與上一年相比,新型職業農民生產經營規模變化程度、生產經營收入變化程度”分別作為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的代理指標。
2.核心解釋變量:非農就業經歷。根據調查問卷的設置,如果個體在成為新型職業農民之前有非農就業經歷,賦值為1;若沒有非農就業經歷,賦值為0。
3.中介變量:能力提升。根據前文分析,新型職業農民之前的非農就業經歷可能會促進其行為能力的提升。依據調查問卷“非農就業經歷對您從事農業的影響”的題項,包括開闊了個人視野、建立網絡關系、培養管理能力、具備市場拓展能力、積累農業生產資金等五個題項,參考朱紅根等的研究[28],對選擇項賦值,新型職業農民選擇該項賦值為1,反之則賦值為0,最后對選擇項進行得分加總,分值越大,表明能力提升越強。
4.調節變量:政策支持。政策支持是指政府為激發新型職業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而制定的稅收減免和財政支持等相關政策或措施。本文主要依據“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后,是否獲得農業相關補貼”作為政策支持的代理指標,獲得政策支持賦值為1,未獲得政策支持賦值為0。
5.控制變量。參考石智雷等的研究[18],主要從新型職業農民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環境選擇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從事農業生產年限、是否村干部、家庭從事農業生產人數和距離鎮政府遠近等變量(見表1)。
(三)模型構建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新型職業農民成長,從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兩個維度衡量。其中,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用“與上一年相比,生產經營規模情況”變量表示,取值是0與1,屬于二分類變量。基于此,文章選用Probit模型進行實證檢驗,方程如下:
Prob(Y*1i=1)=φ(αEi+βCi)(1)
式(1)中,Y*1代表被解釋變量,為拓展性成長,若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則取值為1;若沒有,則取值為0。i表示不同的新型職業農民。在方程式右邊,E表示非農就業經歷,C表示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形特征等8個控制變量,α、β為待估系數。
效益性成長用“與上一年相比,收入變化情況”變量表示,取值是1、2、3,這種有序離散數值表示的,屬于有序變量。基于此,文章選用Oprobit模型進行實證檢驗。Oprobit 模型是典型的受限被解釋變量模型的一種,其核心思想是通過對可觀測的有序數據建立 Oprobit模型,從而研究不可觀測的潛變量變化規律的研究方法,由于無法觀測到 Y* 2的具體數值,因此,可將潛在的效益性成長Y*2看作是一種潛變量,Y* 2的線性方程可表示為:
Y*2i=aEi+βCi+εi(2)
式(2)中,Y*2代表被解釋變量,為效益性成長,E表示非農就業經歷,C表示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形特征等8個控制變量,i表示不同的新型職業農民,α、β為待估系數,ε為服從標準正態分布的擾動項。與二元 Probit模型一樣,Oprobit模型參數也將采用最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
三、實證檢驗結果與討論
本文運用Stata 15軟件分別對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成長進行Probit和Oprobit回歸分析。在進行實證檢驗之前,首先分別從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兩個維度,對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MaxVIF=1.56,MinVIF=1.02,MeanVIF=1.18,MaxVIF小于10。可見,解釋變量之間沒有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一)基準回歸估計結果
表2報告了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實證檢驗結果,其中,第Ⅰ列和第Ⅱ列報告了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的回歸結果,第Ⅲ列和第Ⅳ列報告了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效益性成長的回歸結果。
一是非農就業經歷有助于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從第Ⅰ列和第Ⅱ列的回歸結果看,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分別為0.576和0.601,表明非農就業經歷能夠促進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部分驗證了研究假說1。首先,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具有高風險特征。作為農業生產者,新型職業農民對是否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具有重要的決策權。對于具有非農就業經歷的新型職業農民而言,在非農就業活動中他們經歷了更多的新鮮事物,增長了見識,造就其特有的心理素質使得能從容應對農業經營風險。其次,新型職業農民既往非農就業經歷會通過個體的習慣等潛移默化地影響后期的風險偏好和行為決策。這種非農工作經歷給新型職業農民烙下深刻印記,賦予了新型職業農民不怕失敗的“企業家精神”,使得其敢于擴大生產經營規模。此外,具有非農就業經歷的新型職業農民積累了經濟資本和經營能力,作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新生力量也具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凝聚力,能夠基于自身的優勢,推進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產業化。
二是非農就業經歷有助于推動新型職業農民效益性成長。從第Ⅲ列和第Ⅳ列的回歸結果看,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效益性成長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分別為0.733和0.679,表明非農就業經歷能夠促進新型職業農民效益性成長,部分驗證了研究假說1。過往經歷是新型職業農民的親身體驗。正如前文分析,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不僅可以積累人力資本,豐富其知識儲備,拓寬社會網絡,幫助其在獲取專業化信息上處于有利地位,促進其農業生產經營增收;還可能因其工作環境或者組織文化的差異影響其內在的認知基礎,如價值觀。加之先前非農工作積累的經驗可以轉移,可見,雖然是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的“新進入者”,但是新型職業農民的非農就業經歷增強了其先機意識和風險意識,對市場的敏感性把握較強,對新品種新技術新裝備適用能力較強,推動其收入的增加。
三是控制變量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存在差異性。村里的水利灌溉設施建設情況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成長均產生顯著影響,且影響方向一致,也說明了村莊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對新型職業農民生產經營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文化程度僅對新型職業農民效益性成長產生顯著影響。年齡、家庭農業經營活動從業人數僅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產生影響。
(二)作用機制檢驗
正如前文理論分析,非農就業經歷可能會促進新型職業農民能力提升,進而對其成長產生影響。此外,新型職業農民成長過程中也可能會受到農業政策的影響。基于此,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分別采取中介和調節模型檢驗能力提升、政策支持在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成長之間的關系。表3報告了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4報告了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首先,在表3中,能力提升在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成長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具體來看,相比較第Ⅰ列,第Ⅲ列中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影響的系數有所降低,能力提升均在1%的水平通過正向顯著性檢驗。根據經典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表明能力提升在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關系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不是完全中介效應。同理可知,能力提升在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效益性成長關系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不是完全中介效應。說明了非農就業經歷會給予新型職業農民打上能力烙印,促進其成長。部分驗證了研究假說2。
其次,在表4中,政策支持強化了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效益性成長的影響。第Ⅱ列和第Ⅳ列結果顯示,非農就業經歷與政策支持交互項系數在10%的水平通過正向顯著性檢驗,表明政策支持可以強化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效益性成長的影響,說明了新型職業農民在從事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外部環境對其影響也不可忽視,驗證了研究假說3。
(三)穩健性檢驗
非農就業經歷是否會影響新型職業農民后期成長,在實證檢驗中存在著很大的困難。主要是因為個體就業經歷是內生的,與其工作的環境有著很大的聯系,這些環境可能直接決定著新型職業農民未來的選擇。這意味著簡單地估計非農就業經歷對其成長的影響可能會存在估計偏誤。為此,下文進行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再估計。為確保研究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非農從業年限(年)作為非農就業經歷的代理變量,再次估計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非農從業年限均值為6.41。結果顯示,無論是作用方向還是顯著性水平都與表2的結果較為一致,說明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結果較為穩健(見表5)。
2.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估計。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重新估計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選擇核匹配進行檢驗,并選擇K近鄰匹配方式進行比較(見表6)。結果顯示,匹配前后,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的影響沒有發生顯著變化,而且均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與表2的結果相一致。此外,兩種匹配結果相差較小,且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其效應方向和顯著水平是一致的,說明結果具有穩健性。因此,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結論沒有因為匹配方法的差異而發生變化,表明了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有助于其成長的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四)進一步的探討
1.非農就業經歷對不同類型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正如前文分析,總體上,非農就業經歷有利于新型職業農民成長,但是對于不同類型的新型職業農民來說,非農就業經歷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本文依據新型職業農民的定義對新型職業農民類型進行細分,進一步探討非農就業經歷對不同類型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第Ⅰ列到第Ⅳ列的研究對象分別為種植大戶、家庭農場主、農民專業合作社帶頭人和農業企業負責人。表7報告了分析結果。
非農就業經歷對種養殖大戶、家庭農場主和農業企業帶頭人的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影響程度存在差異,表明了非農就業經歷有助于推動種養殖大戶、家庭農場主和農業企業帶頭人的成長。非農就業經歷對農民合作社帶頭人效益性成長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非農就業經歷對其效益性成長影響程度較小。
2.不同類型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正如前文分析,不同類型非農就業經歷對個體能力提升影響不同。基于此,進一步從非農就業經歷角度分析務工、經商和從政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表8報告了不同類型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的影響非農就業經歷還包括從軍、求學和從醫等其他經歷,但每種經歷獲得樣本量較少,因此本文未將其納入研究范圍。。第Ⅰ列中,務工、經商和從政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均產生正向的影響;在第Ⅱ列中,從政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效益性成長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采用廣東省新型職業農民混合截面調查數據,分別運用Probit、Oprobit模型,從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兩個方面,探討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并運用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模型檢驗能力提升和政策支持在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成長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非農就業經歷能夠促進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能力提升在非農就業經歷與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效益性成長關系中均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說明非農就業經歷能夠提升新型職業農民行為能力,進而對其成長產生積極影響;政策支持能夠強化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的影響;文化程度等控制變量對新型職業農民的成長影響存在差異性。采取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和PSM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后,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影響依然成立。進一步的異質性研究結果表明,非農就業經歷對不同類型新型職業農民成長存在差異;不同類型的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成長影響程度也存在差異。
可見,為進一步推動新型職業農民成長,順應新時代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要求,培育更多高素質的農民,以此引領中國農業農村實現現代化,助力2035年遠景目標的實現,必須充分發揮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的積極效應。
首先,重視新型職業農民非農就業經歷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應。新型職業農民的非農就業經歷使其形成特有的認知基礎和行為能力,且這種影響具有持續性。在制定生產經營決策時,新型職業農民應積極樹立經歷就是財富的意識,充分挖掘非農就業過程中所積累的資源,消除舊烙印產生的負面影響。
其次,多渠道促進新型職業農民能力提升。新型職業農民能力的提升是其拓展性成長和效益性成長的基礎。政府應持續加大并采取差異化措施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實現補短板、強弱項、助成長、促發展。比如,具有非農就業經歷的新型職業農民在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的專業知識相對薄弱,因此應加強對這類新型職業農民的農業專業知識技能培訓,減少由于專業知識不足而引發的決策誤判,以及深層非農就業經歷烙印的非理性影響,以有效降低生產成本,降低農業經營風險。新型職業農民也應緊抓機遇,不斷提升自身學習能力。
最后,政府積極扮演平臺搭建者、服務提供者等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著力構建和保障新型職業農民成長壯大的政策支持體系。比如,創新政策性和商業性農業保險制度,為新型職業農民生產經營與事業發展保駕護航。當然,也要注意強化差別化政策支持的協調發展效應,避免“一刀切”。對規模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組織,提供貸款差額補貼或者根據種植面積、帶動農民就業數量采取累進補貼制度,降低新型職業農民的生產經營風險,為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營造良好的環境,推動新型職業農民更強更優地發展。
參考文獻:
[1] 葉俊燾,米松華.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理論闡釋、他國經驗與創新路徑——基于農民現代化視角[J].江西社會科學,2014,34(04):199-204.
[2] 崔寧波,宋秀娟,于興業.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發展約束與建議[J].江西社會科學,2014,34(03):52-57.
[3] 朱啟臻,胡方萌.新型職業農民生成環境的幾個問題[J].中國農村經濟,2016(10):61-69.
[4] 徐輝新.常態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機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J].農業經濟問題,2016,37(08):9-15.
[5] 羅明忠,雷顯凱.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農業經營性收入的影響[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20,35(04):103-112.
[6] 羅明忠,雷顯凱.非農就業經歷、行為能力與新型職業農民經營效率[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5):29-38.
[7] 陳建偉.新型職業農民身份對農業經營收入的影響:基于傾向值匹配方法的分析[J].東岳論叢,2019,40(11):162-173.
[8] 曾春影,茅寧,易志高.CEO初次進入職場時的經濟形勢與企業盈余管理——基于烙印理論的實證研究[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8,40(07):68-81.
[9] MALMENDIER U,YAN G T.Over Confidence and Early Life Experiences: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1,66(05):1687-1733.
[10] 汪險生,郭忠興.早年饑荒經歷對農戶土地租出行為的影響[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03):103-112.
[11] 洪煒杰,羅必良.饑荒經歷、地權偏好與農地調整[J].中國農村觀察,2020(02):100-116.
[12] 高峰.參軍經歷、資本積累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J].青年研究,2021(01):15-25.
[13] 楊學儒,李新春.地緣近似性、先前經驗與農業創業企業成長[J].學術研究,2013(07):64-69.
[14] 柳建珅,何曉斌,呂淑敏.流動經歷、社會信任與縣域企業互聯網融資——來自全國縣域企業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01):133-144.
[15] 羅明忠,唐超,吳小立.培訓參與有助于緩解農戶相對貧困嗎?——源自河南省3278份農戶問卷調查的實證分析[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6):43-56.
[16] 于福波,張應良.外出務工、社會資本與農戶內部收入差距[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40(08):90-103.
[17] 石智雷,楊云彥.外出務工對農村勞動力能力發展的影響及政策含義[J].管理世界,2011(12):40-54.
[18] 石智雷,王佳.外出務工經歷與農村勞動力新技術獲得[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02):48-56.
[19] 周廣肅,邊曉宇,吳清軍.上山下鄉經歷與家庭風險金融資產投資——基于斷點回歸的證據[J].金融研究,2020(01):150-170.
[20] 戴維奇,劉洋,廖明情.烙印效應:民營企業誰在“不務正業”[J].管理世界,2016(05):99-115.
[21] 曾憲聚,陳霖,嚴江兵,等.高管從軍經歷對并購溢價的影響:烙印——環境匹配的視角[J].外國經濟與管理,2020,42(09):94-106.
[22] 鐘甫寧,顧和軍,紀月清.農民角色分化與農業補貼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應——江蘇省農業稅減免、糧食直補收入分配效應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8(05):65-70.
[23] 朱紅根,康蘭媛.家庭資本稟賦與農民創業績效實證分析[J].商業研究,2016(07):33-41.
[24] 肖小虹,王婷婷,王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農業政策的演變軌跡——基于1949-2019年中國農業政策的量化分析[J].世界農業,2019(08):33-48.
[25] 楊洋,魏江,羅來軍.誰在利用政府補貼進行創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場扭曲的聯合調節效應[J].管理世界,2015(01):75-86.
[26] 羅明忠.個體特征、資源獲取與農民創業——基于廣東部分地區問卷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2(02):11-19.
[27] 李旭,李雪.社會資本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成長的影響——基于資源獲取中介作用的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9(01):125-133.
[28] 朱紅根,宋成校,康蘭媛,等.家庭農場經營代際傳遞有利于提高農場績效嗎?——基于種植業家庭農場實證分析[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3(01):44-60.
The Brand Effe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on the Growth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LEI Xiankai,LUO Ming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Employment experienc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thinking style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later growth process.Based on the mixed cross sectional data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this article uses Probit,Oprobit,mediating eff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models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on the growth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expansion growth and profitable growth.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can promote their expansive growth and profitable growth through development of capabilities;policy support can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on the expansive and profitable growth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s,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on their growth is different.Based on this,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and innovate agriculture-related support policies and differentiated cultivation to enhance the behavioral capabilities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Key word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branding theory;expansion growth;profitable growth
(責任編輯: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