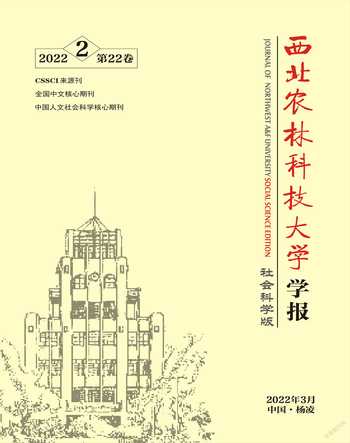森林文化價值的法制表達與《森林法》的文化擔當

摘 要:森林的生態價值、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形成了森林價值的統一體系,各價值之間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系,更是一種互促共進的關系。森林文化是人類認識和使用森林資源過程中形成的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物。生態文明入憲背景下,森林文化價值的法制表達直接關系人民身心健康、生活質量及幸福指數。在梳理森林文化價值法制表達的歷史脈絡及時代需求的基礎上,探究其演進規律與內在邏輯,指出森林法則的人本氣息應進一步加強、森林法制理論價值體系需進一步拓展、森林價值體系在《森林法》中應進一步統合,最后提出“總則明確規定+分則相對細化”的技術路徑以充分實現《森林法》的文化擔當。
關鍵詞:森林;森林文化價值;森林法
中圖分類號:D92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2-0140-06
收稿日期:2021-08-16"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2.16
基金項目:陜西省林業科技創新專項(SXLk2020-05-03);陜西省生態脫貧項目(20210101);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軟科學研究項目(2019131040)
作者簡介:吳普俠,女,陜西省林業科學院高級工程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林權制度改革、生態修復與林業產業。
通信作者
“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1],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到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時引用的經典名句。21世紀是生態文明的世紀,“可持續發展理論”“兩山理論”與“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體理論”等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依據和方向遵循。2015年發布的《中國生態文化發展綱要(2016-2020年)》指出生態文化是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的核心理念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支撐。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并進一步闡明“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2020年《民法典》“綠色原則”的確立將綠色文化的價值理念深刻融入到當代的法制體系。2021年3月12日,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召開的中國森林資源核算研究成果新聞發布會上,項目總負責人江澤慧指出:“森林在為美好生活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的同時,還提供了約為3.10萬億元的文化價值”[2]。由此可見,森林文化是生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綠色原則”的重要載體。因此,當代《森林法》的文化價值擔當尤為重要。
一、森林文化價值構成與森林價值的多維統一
(一)森林文化價值的構成
森林(林木)具有其獨立、多樣的文化內涵。學術界對森林(林木)文化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與表述,或對森林文化進行總體性研究,或對特種樹木進行研究,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更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基本達成了一些共識:一方面,森林文化以森林為背景或載體;另一方面,森林文化體現了森林的人化[3]。政策制度層面對森林文化的規定局限于某些特殊的領域或片面的具象化,如關于古樹名木的規定、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的論述等。一般認為森林文化是人類認識和使用森林資源過程中形成的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物,包括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其構成見表1。
(二)森林價值的多維統一
森林的生態價值、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形成了森林價值的統一體系,各價值之間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系,更是一種互促共進的關系。
《森林法》總則第一條突出強調了森林的生態價值,踐行了習近平總書記及黨中央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新理念、新思想與新戰略,立法技術和立法質量也進一步提升。但隨著國際國內社會的巨變和轉型,國家和民族文化成為國際競爭和國內發展的源動力和方向標。森林文化所具有的國家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等特征要求我們不僅應從社會層面進行宣傳和教育,同時也應注重森林文化價值制度層面的規制與引領作用,加強國家文化建設與文化治理。
本文特別強調森林文化價值對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的推動和提升作用。一方面,森林文化價值引導經濟生產活動。森林文化產品主要滿足人們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進而產生情感上的共鳴。森林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催生了更多的森林文化形態,森林公園、國家公園、自然景觀、林下經濟等已經發展成大眾文化,成為現代城鄉居民休閑、娛樂、康養、療愈的重要載體、空間和場域,是新時代森林文化價值的重要體現。這種沉浸式消費的意義和快感,成為文化消費產業的營銷對象,大眾對森林文化價值的需要決定新生的森林經濟活動方向,受眾對于森林文化價值的認同和滿足是森林文化經濟活動成功的前提。因此,文化價值成為經濟活動策劃的核心,較高的文化價值往往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森林文化價值促進生態價值的實現。森林生態價值主要體現在凈化空氣、提供氧氣、消除噪聲、調節氣候、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生態價值是人類經過長期實踐和探索所總結和凝練一種價值體現。生態學家沃斯特指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本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4]事實上,森林的文化價值對森林生態價值的實現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森林生態價值、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是一種互為促進和相互影響的關系,在制度規制的層面也應統一和協調。
二、森林文化價值法制表達的歷史脈絡
(一)古代習慣法的啟蒙
人類文明是從森林中“走出來”的文明,人類的農耕文明是在擠壓森林空間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人類農耕時期對于森林這個神秘的“故居”仍然心存敬畏與感恩。從中國森林法則的發展歷史來看,古代雖沒有形成系統的法典法則,但關于森林及森林文化的價值在歷代律令中很早就有了認識與體現。夏朝《逸周書·大聚解》記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西周時期頒布的《伐崇令》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呂氏春秋·孝行覽》中的《義賞》篇規定“ 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寡人之于國也》規定“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宋太祖頒布詔令對造林、護林有功的獎賞進行了規定。在中國歷朝歷代的國家治理和政治實踐中,特別是在律令中,體現著平衡、節制、有序、適度、內斂的生態智慧和生態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我們理應促進傳統生態文化和生態倫理的現代轉型[5]。
(二)近代對森林法則的漠視
工業革命帶來的轉變使中國走上了一條謀求快速發展的道路,此時的森林法則著重對森林的經濟利用進行規范,旨在更高效地利用林木進行社會財富的積累。光緒二十三年(1897),光緒帝以世界潮流所趨,督促各地發展農林事業,下詔諭云:“桑麻絲茶等項,均為民間大利所在。督飭地方官,各就土物所宜,悉心勸辦,以浚利源。”于是設專官、興學校倡辦林業[6]。與此同時,對森林資源的消耗和攫取也導致生態危機接踵而至,因此人們便開始重視森林的生態保護,相關立法也從注重其經濟效益轉換為保護森林生態功能下的經濟利用。1914年,北洋政府公布我國第一部《森林法》,從此中國揭開了依法治林的序幕,并涉及到了“保安林”的保護、獎勵與責罰等,強調了森林的生態效益[7]。但該階段戰亂頻發,嚴重掣肘相關法律的實施,最終多落為一紙空文。可見,近代以來森林文化在法則中受到了冷落與漠視,其所具有的文化價值仍未被徹底發掘,因此,人們對于森林的保護僅限于在法律強制力約束下的補償與修正,而非在森林文化價值理念指導下主動保育。
(三)現代《森林法》的復興
新中國成立后,穩定的社會環境給予文化蓬勃發展的土壤,中國森林文化研究逐漸繁榮,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涌現出一批著名學者,如黨雙忍[8]、蘇祖榮[9]、郭風平[10]、樊寶敏[11]等。此時的森林文化研究已經由傳統的感性欣賞轉化為科學的理性分析,并呈現出細分學科的發展態勢,生態倫理學、生態道德、生態文學等概念相繼提出,對人與森林和諧共生的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然而這種文化的發展與研究對立法的影響甚微,森林法重心仍然在平衡森林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上。1998年特大洪水和沙塵暴引發人們對森林資源配置模式的思考,以往被忽略的森林文化價值重新回到立法者的視野。1998年修正的森林法除在經濟、生態價值維度對森林資源進行規制外,還將森林的文化價值納入其中,著重保護古樹名木和具有特殊價值的植物,并對非法采伐、毀壞珍貴樹木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體現了該時期對森林文化價值的認識與重視,并引發各個層級及各省市對該類對象的專門立法。隨著自然保護區體系建立,森林公園、森林休閑旅游、森林康養、森林療愈等的出現,森林文化的價值更加凸顯。2019年修訂的《森林法》使用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來表述立法目的,雖未明確肯定森林文化價值的重要地位,但森林文化價值對立法的影響已經有所體現,這為今后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基本范式。同時《森林法》規定:“在不影響生態功能的前提下可以適當發展林下經濟和森林旅游。”從森林基本法層面為森林文化價值的發揮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森林法》文化價值法制表達的時代必然與優化路徑
(一)《森林法》文化價值法制表達的時代必然
后工業化、后城鎮化時代,中國經濟穩步增長,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轉變,人們對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森林法制的價值體系應進一步拓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及本土性,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在相關法制的精神中應當被固定和倡導。
同時,在基本法中對森林價值進行均衡規定的立法模式也為域外實踐所采納。韓國2005年出臺的《森林文化·休養法》強調充分發揮森林多種功能,鼓勵建立自然休養林、自然觀察教育林、風景林來滿足人們對森林的多元愿望[12]。英國1967年制定的《森林法》規定,應保護具有特別感價值的植物群;對于在果園、花園、教堂墓地或公共休憩用地上種植或生長的果樹或樹木,委員會不得隨意處置,因為該類林木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價值,法律有必要對其進行嚴格保護[13]。這些國家通過科學的立法讓森林文化價值得到更大程度的發揮。文化本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分散立法既不能窮盡森林文化所有形態,苛求立法事無巨細的制定包羅萬象的森林文化,實為立法不能承受之重。立法本就是一個將繁雜社會現象濃縮只言片語的過程,既然無法做到巨細無遺的涵蓋所有文化形態,在基本法中明確引入森林文化價值,通過上位法來宏觀指導下位法的實施就更為必要。
(二)《森林法》文化價值法制表達的優化路徑
1.森林法則的人本氣息應進一步加強。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秩序、社會矛盾及社會治理面臨新的時代轉向。習總書記的引典“觀俗立法則治”,以及他提出的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論與思想,無不體現著對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視、發掘與傳承,對轉型期中國社會法制發展提出了新方向與新遵循。同時著名的馬斯洛需求理論指出當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達到富裕階段時,人們便更加注重求知需求、審美需求等精神層次的滿足,在不斷豐盈精神世界的過程中來實現自我價值。2020年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同時,社會文明的跨越式進步也帶動著人們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滿足。森林作為具有療愈、觀賞等獨特價值的生態體,其所孕育的既傳統又現代的優秀文化愈發得到人們的重視與實踐。在此背景下,立法理念的成熟與適度轉向也成時代必然。法制從來不是冷冰冰的說教,它是人類創造的唯一駕馭和規制人類行為的科學,它從人類思想行為中產生并最終走向并運用到人類的各種活動,不可避免的要融入人類豐富的人本氣息。
2.森林法制理論價值體系需進一步拓展。學界一般將森林資源的價值分為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文化價值,三者共同構成了森林的價值體系,以此種森林價值體系為基礎而制定的《森林法》條文中更多強調了森林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對森林的文化價值有所忽視。如前文所述,森林資源三種價值之間關系密切,互促互進。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對森林資源的利用著重于其經濟價值,過度索取的惡果又讓政策制定者注意力轉移到生態價值上,法律制定與修改也呈現出這一變化趨勢。進入新時代,隨著國際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和需求的變化和轉向,政策制定者的頂層設計不斷強調文化價值的重要性,突出擴大文化價值的引領作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應適時跟進。在森林法律體系的基本法《森林法》中明確森林文化價值的地位和作用,對森林文化價值進行適度規定,不僅可以優化立法結構,同時也可以避免森林價值理論的體系缺陷,讓森林價值體系在法則中全面體現,將生態文明觀徹底融入森林基本法中。
3.森林價值體系在《森林法》中應進一步統合。全面檢視涉及森林文化價值的立法和司法解釋,呈現出規章制度獨立規定、分散式立法、下位法更為具體、基本法缺失較為突出的分布態勢和特征。2011年實施的《國家級森林公園管理辦法》以及2016年修訂的《森林公園管理辦法》都對森林文化價值中森林旅游這一方面進行了詳細規定,2016年北京市實施的《森林文化基地建設指導原則》通過森林文化基地建設推動森林療養、森林體驗、森林教育的開展。2020年2月1日實施的《貴州省古樹名木大樹保護條例》第四條明確規定了文化傳承的原則等。這種態勢和特征與以往我國對人與森林關系認識的局限性有關,缺乏對森林文化價值的重視,加上我國森林資源分布的不均衡現狀,致使各部門在規范制定的過程中產生了強烈的利益博弈,種種因素最終形成了森林文化價值在森林法中的弱勢地位。立法中對森林文化價值沒有明確規定,政府缺乏發展森林文化價值的制度基礎,法官缺少援引法條保護森林文化的制度依據,因此,在《森林法》中進一步統合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
四、《森林法》文化價值擔當的基本策略
《森林法》是實現森林文化價值的最優規范載體,應合理建構法律條文以表達森林文化應有的價值定位。《森林法》應明確確立森林文化價值的核心地位,更有效的從制度層面發揮森林文化價值,引領法律其他價值的實現。《森林法》應采取“總則明確規定+分則相對細化”的立法模式和技術,將森林文化價值擴充至基礎地位,以保障《森林法》立法邏輯的自洽性、價值方向的全面性與總分則內容的協調性,實現對森林資源的整體性保護[14]。
(一)總則明確規定
為更高效地發揮森林文化價值的作用,構建價值維度間的協調關系,可將森林的文化價值在《森林法》中予以“總則化”表述。總則與分則是共通規定與特別規定的關系,其中總則部分扮演著雙重角色,即指導與補充分則[15],因此,森林文化價值的“總則化”不僅在價值方向上發揮著引領性作用,注重解決《森林法》中的共性問題,還對具體條款的適用起到補漏性作用。據此,應結合現行《森林法》總則結構進行完善。
森林文化價值的總則化,首先可以對《森林法》立法方向進行引導,改變以往忽視森林文化價值的觀念,確立森林文化價值的重要地位。總則可從宏觀角度回答《森林法》中的基本問題,有利于分則更明晰地規定森林文化價值相關具體問題。其次可以補充分則中遺漏或不明確的條款,起到兜底補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的總則不僅對本法分則有指導作用,對于下位法涉及到森林文化及其價值的部分均可以進行有效回應,增強了森林法律體系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這樣規定,一方面契合了“建設生態文明,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立法目的,落實“突出森林主導功能、發揮多種功能”的價值期待,明晰森林文化價值的立法定位;另一方面在立法層面理順了生態、經濟及文化價值的邏輯關系,優化了森林價值體系,也為森林文化的現實需求提供了規范依據,完善了森林法律體系,更大限度地保護森林生態并滿足人民大眾的各種需求。
《森林法》總則部分以立法目的、適用范圍、基本原則、責任主體及相關權利義務為立法的技術路線,其中,第十二條規定了各主體對森林資源保護所應承擔的宣傳教育及知識普及義務,間接彰顯出人文林業的教化功能,因此,若將森林文化價值納入總則之中,第十二條可明確“推動森林文化建設”的指導性義務,落實森林資源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期待,給予其相應的法律地位,實現森林生態、經濟、文化價值的協調共存。除明確其價值定位之外,對于相關措施的規范設計也應在總則中予以落實,第五條對于森林生態保護及林業發展所投入的資金支持也可涉及森林文化領域。同時,第十三條規定的表彰、獎勵同樣也應給予在森林文化建設方面取得顯著成績的組織或個人。通過對該三條法律規范內容的擴展,森林的文化價值在總則中得到了合理表達,且實現了將其“總則化”的調整目的。
(二)分則相對細化
分則特別規定的適用應與總則保持協調統一,因此森林文化價值這一抽象表述可適當通過分則的具體條款予以闡釋與落實。
《森林法》第四十條“對古樹名木和珍貴樹木的保護”以及第四十二條有關“森林城市和美麗家園建設”的規定,雖在一定程度上能體現森林的文化價值,但其條款內容更側重于森林保護與造林綠化,除此之外,分則部分對于森林文化價值的規定鮮有體現,可見涉及森林文化價值的法律規范并沒有得到系統地表達。從立法邏輯來看,若要在分則中對森林的文化價值進行相對細化規定,可將其編入第六章“經營管理”之中,該章將森林分為公益林和商品林兩類,首先對公益林的概念、區域劃定及管理主體進行了規定,在此之后,第四十九條從生態和經濟價值角度明確了公益林的用途、經營方式及經營理念,同樣對商品林也進行了類似的立法設計。由此可見,該章是保護森林生態及經濟效益的立法,但森林文化效益的缺失,其條文設計并不能完全實現立法價值。通過在分則中的補充規定,將森林文化價值內涵融入《森林法》之中,既是對總則總括性規定的呼應,又保持了分則價值體系的平衡,矯正了價值體系在分則中的失衡。
《森林法》是基于森林價值體系構建的森林資源配置的基本法。在我國,森林文化法制化源遠流長,中國森林法則的發展歷程為森林文化的法制化提供了歷史依據。同時“可持續發展理論”“兩山理論”“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體理論”為森林文化的法制化提供了寬厚的理論基礎。《森林法》作為具有強制約束力的行為規范,需要在調整“人林共生關系”時為公眾提供正確的價值導向[16],通過對相關權利義務的調整使人們建立對森林資源的文化價值認同,從而在思想根源上引導人們自主、自發地重視森林的保育與修復,加強公眾保護森林的參與度,以提高林業的社會貢獻力和公眾的文化自信力。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J].求實,2015(01):3-8.
[2] 胡利娟.我國森林提供的文化價值為3.10萬億元[EB/OL].(2021-03-12)[2021-08-21].http://www.kepu.gov.cn/www/article/dtxw/99de8c7e47b54972aaccd97a5d7104d1.
[3] 張義.近年來國內森林文化研究進展[J].中國農學通報,2009,25(21):122-126.
[4] 趙紹鴻.森林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7.
[5] 張云輝,賈斌英.“森林文化”縱橫談[J].遼寧林業科技,2008(02):44.
[6] 潘岳.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遵循[N].光明日報,2018-11-02(10).
[7] 陳嶸.中國森林史料[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2:3.
[8] 黨雙忍.以生態空間之治推進美麗中國建設[J].西部大開發,2019(12):78-81.
[9] 蘇祖榮,蘇孝同.森林文化與森林文化產業[J].福建林業,2014(01):16.
[10] 郭風平.中國森林文化之我見[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05):90-95.
[11] 樊寶敏.中國森林思想發展脈絡探析[J].世界林業研究,2019,32(05):1-8.
[12] 李祗輝.韓國自然休養林發展及啟示[J].世界林業研究,2020:101-105.
[13] 李劍泉,田康,陳紹志.英國林業法規政策體系及啟示[J].世界林業研究,2014,27(02):70-76.
[14] 吳凱杰.環境法體系中的自然保護地立法[J].法學研究,2020(03):123-142.
[15] 吳尚聰,萬穎穎.終身監禁對于死刑的“功能替代”及其“總則化”構建——以死刑制度改革為切入點[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3(02):29-32.
[16] 樊寶敏,李智勇,張德成,等.基于人林共生時間的森林文化價值評估[J].生態學報,2019,39(02):692-699.
On the Legal Expression of Forest Cultural Value and the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of “Forest Law”
WU Puxia1,CUI Caixian2*
(1.Shaanxi Academy of Forestry,Xi’an 710082;2.Northwest Aamp;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Forest culture is the entire spiritual activity and its products formed in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forest resources.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legal expression of forest culture valu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quality of life,and happiness index.The ecolog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s of forests form a unified system of forest values.Each value is a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moreover,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progress.Based on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lineage of the legal expression of forest cultural values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exploring its evolution law and internal logic,pointing out that the humanistic atmosphere of forest law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the value system of forest law theory needs to be further expanded,and the forest value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unified in the Forest Law.Finally,we propose the technical path of “Clear General Provisions + Detailed Specific Provisions” to fully realize the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Forest Law.
Key words:forest;forest cultural value;forest law
(責任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