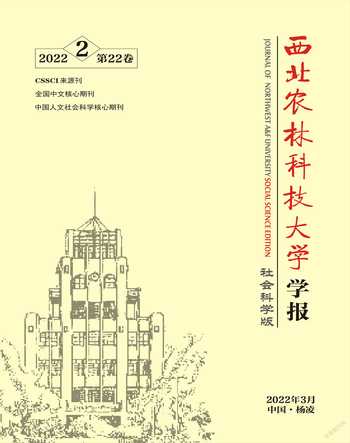收入渴望、非農(nóng)就業(yè)與脫貧戶收入








摘 要:在推進脫貧攻堅與鄉(xiāng)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時代背景下,精神貧困治理的重要性逐漸凸顯。根據(jù)陜西省周至縣807戶脫貧戶的調(diào)研數(shù)據(jù),對精神貧困進行量化分析,構(gòu)建了收入渴望、非農(nóng)就業(yè)和脫貧戶收入的理論框架,實證分析收入渴望對脫貧戶收入的影響機制。結(jié)果表明:(1)收入渴望對脫貧戶家庭總收入、工資收入以及其他類型收入之和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最為顯著。(2)收入渴望有利于提升以家庭勞動力投入為標(biāo)準(zhǔn)的非農(nóng)就業(yè)水平,并間接影響家庭工資收入。(3)在中介機制中,由于調(diào)查對象的特殊性,脫貧戶家庭人口結(jié)構(gòu)特征對非農(nóng)就業(yè)和工資收入的影響較戶主特征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基于以上研究結(jié)論,提出應(yīng)激發(fā)目標(biāo)人群收入渴望、創(chuàng)造勞動力升級環(huán)境、繼續(xù)加大公共資源投入力度等政策建議。
關(guān)鍵詞:精神貧困;抱負(fù)失靈;脫貧戶;非農(nóng)就業(yè);家庭收入
中圖分類號:F328/C913.7"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2-0074-12
收稿日期:2021-07-21"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2.09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項目(42075172);陜西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目(2018S04)
作者簡介:陳光,男,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經(jīng)濟管理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收入不平等與貧困治理。
通信作者
引 言
現(xiàn)行貧困標(biāo)準(zhǔn)下,中國農(nóng)村貧困人口已于2020年全部脫離絕對貧困,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然而貧困是一個復(fù)雜的動態(tài)變化過程,盡管貧困人口在扶貧組合政策的推動下擺脫了絕對貧困,但部分地區(qū)和家庭脫貧可持續(xù)性不強、穩(wěn)定性不足的問題仍然存在[1]。由于部分幫扶對象的主觀能動性不強,對幫扶資源利用不足[2],在前期脫貧政策打破外部約束的慣性下,脫貧群體的主觀態(tài)度可能會成為影響脫貧成效的重要因素。
Sen的可持續(xù)生計框架被廣泛用于貧困成因的探索,卻始終無法解釋部分貧困人口在外部約束被削弱時仍缺乏內(nèi)生動力的困境[3]。有學(xué)者指出,在后脫貧時代的減貧政策中,要著重關(guān)注脫貧主體的主觀發(fā)展能動性,著力解決精神貧困問題[4]。對文化水平偏低、勞動技能缺乏但具有勞動能力的脫貧群體,公共部門不僅要根據(jù)勞動市場需求加強就業(yè)技能培訓(xùn),還要加大“扶志扶智”力度,增強其自身“造血”功能[5]。
收入增長是中國“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脫貧政策的最核心指標(biāo)和最基本要求,保證脫貧人口收入水平長期穩(wěn)定增長是穩(wěn)固脫貧成效的基本任務(wù)。由于脫貧群體數(shù)量龐大且多處于自然條件差、資源匱乏的深度貧困地區(qū),為了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越來越多的農(nóng)村勞動力開始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脫離出來,轉(zhuǎn)而通過非農(nóng)就業(yè)獲取工資性收入。據(jù)國務(wù)院扶貧辦統(tǒng)計,2019年超過70%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選擇外出就業(yè),工資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占比超過65%[6]。在這一背景下,引導(dǎo)農(nóng)村勞動力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逐漸成為農(nóng)村減貧的主要手段[7]。根據(jù)就業(yè)地點的不同,非農(nóng)就業(yè)可以分為“離土不離鄉(xiāng)”的本地非農(nóng)就業(yè)和“離土離鄉(xiāng)”的跨區(qū)域非農(nóng)就業(yè)[8]。后者在收入上的減貧效應(yīng)明顯大于前者,但在降低多維貧困上表現(xiàn)較弱[9]。非農(nóng)就業(yè)的減貧效應(yīng)不僅體現(xiàn)在通過增加非農(nóng)工資收入緩解家庭經(jīng)濟貧困,同時還能通過對留守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重新配置增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10]。
“渴望提升收入”是個體主觀能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激勵個體家庭物質(zhì)資本、人力資本等投資行為[11]。通過提高脫貧戶收入渴望水平促進其家庭非農(nóng)就業(yè)成為后續(xù)減貧的一條可能路徑。已有文獻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礎(chǔ)和參考,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內(nèi)容上,對渴望影響貧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渴望對各類投資的影響,其作用于收入的機理研究仍有待拓展;研究方法上,國內(nèi)對精神貧困的定量實證研究相對較少,對精神貧困與收入可能存在的雙向因果關(guān)系考慮不多,對收入渴望測度的科學(xué)性也有待提升;研究對象上,由于樣本分散及其真實收入獲取難度大,目前以脫貧群體收入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文獻也有待豐富。因此針對以上研究局限,在“幫助農(nóng)村低收入人口提高其內(nèi)生發(fā)展能力”和“幫助脫貧人口就地就近就業(yè)”的2021年一號文件政策背景下,本文借鑒尤亮等提出的“渴望投資減貧”理論分析框架[11],基于陜西省周至縣807戶原建檔立卡戶的調(diào)研數(shù)據(jù),實證分析收入渴望對脫貧戶收入的影響,以及非農(nóng)就業(yè)在收入渴望影響脫貧戶收入中所扮演的角色,為可持續(xù)減貧、促進脫貧攻堅與鄉(xiāng)村振興有效銜接提供政策依據(jù)。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shè)
貧困人口所面臨的內(nèi)部約束與外部約束是影響脫貧成效和脫貧穩(wěn)定性的重要因素。在精準(zhǔn)扶貧、精準(zhǔn)脫貧政策的有效落實過程中,貧困人口發(fā)展的外部約束逐漸被解除,轉(zhuǎn)而需要關(guān)注其內(nèi)部約束。Flechtner提出在貧困治理中貧困人口的渴望是值得關(guān)注的重要內(nèi)在約束[12]。由于貧困人口長期生活在物質(zhì)資料匱乏且信息流動較差的環(huán)境中,對其渴望的形成產(chǎn)生錨定效應(yīng),導(dǎo)致農(nóng)村貧困群體渴望水平普遍較低[13]。在脫貧過程中表現(xiàn)出缺乏志向、無心脫貧等不利于擺脫貧困的心理和行為特征[2]。胡小勇等將這種由長期物質(zhì)貧困所導(dǎo)致的“抱負(fù)失靈”(aspiration failures)和“行為失靈”(behavioral failures)稱之為精神貧困[14],是貧困個體主觀發(fā)展動力缺失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
“渴望”(aspiration)又作“抱負(fù)”“志向”之意,表達了個體的特定目標(biāo)以及想要實現(xiàn)目標(biāo)的偏好或愿望,這種愿望會激勵個體為實現(xiàn)目標(biāo)而投入時間、努力或資金[15]。Ray根據(jù)人的社會屬性特征,將個體通過觀察與周圍人的差距而形成的欲望定義為渴望,并提出“渴望窗口”(aspirations window)的概念[16]。根據(jù)渴望的定義,個體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環(huán)境決定的,他人的行為結(jié)果是其渴望的形成依據(jù)。個體渴望跨越了多個可能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維度,如Bernard和Tafesse指出,個體存在對收入的渴望、教育的渴望、社會地位的渴望等[17]。本文只針對收入維度的渴望進行研究。Genicot和Ray指出收入渴望作為內(nèi)生動力因素,對引導(dǎo)個體增加投資以實現(xiàn)目標(biāo)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18]。據(jù)此,尤亮等提出渴望投資貧困的減貧理論框架,指出收入渴望可能促使貧困個體將增收動機轉(zhuǎn)化為行動,進而為實現(xiàn)渴望的收入水平增加物質(zhì)資本、人力資本等各類投資[11]。管睿等將農(nóng)戶的風(fēng)險偏好、抱負(fù)水平、自控能力等三個維度的表現(xiàn)擬合形成內(nèi)生動力指標(biāo),用以測度內(nèi)生動力對農(nóng)戶收入的影響,結(jié)果表明內(nèi)生動力的培育能提升農(nóng)戶利用生計資本的能力,從而有效提高農(nóng)戶的家庭收入[3]。在農(nóng)村勞動力流向城市的現(xiàn)實背景下,非農(nóng)收入在農(nóng)村家庭總收入中的占比逐漸增大,這種趨勢可能導(dǎo)致增收效應(yīng)在農(nóng)戶的工資收入上表現(xiàn)得更直接。基于以上分析,脫貧戶的內(nèi)生動力可能顯著促進其家庭總收入和工資收入,因此提出以下假設(shè)(本文所提假設(shè)均以原假設(shè)的形式表述):
假設(shè)1:脫貧戶的收入渴望對其家庭總收入沒有影響。
假設(shè)2:脫貧戶的收入渴望對其家庭工資收入沒有影響。
由貧困導(dǎo)致的“現(xiàn)狀偏見”和低渴望會抑制個體利用當(dāng)前資源對未來投資的意愿,從而導(dǎo)致持續(xù)性貧困[13,19]。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當(dāng)個體長期處于貧困狀態(tài)時,其自身經(jīng)歷和與其相似的他人經(jīng)歷經(jīng)常表明,通過自身努力擺脫貧困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20]。反之,若個體渴望水平得以提升,則會促使其增加投資并改變對未來的態(tài)度。
在渴望與人力資本投資關(guān)系的研究中,Jensen發(fā)現(xiàn)為印度貧困村莊中的年輕女性提供參觀電話呼叫中心的機會后,其表現(xiàn)出較高的職業(yè)渴望,勞動力市場和職業(yè)培訓(xùn)的參與率顯著上升[21]。同樣地,為貧困家庭提供關(guān)于教育回報的具體信息,可以有效降低學(xué)齡兒童輟學(xué)率[22]。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貧困人口多處在相對閉塞的環(huán)境之中,并未意識到投資人力資本的未來收益。但是通過實驗,使其了解目標(biāo)的可行性和投資的高收益后,能引導(dǎo)其提升渴望水平,進而增加人力資本投資,這同樣符合Genicot和Ray的觀點[23]。人力資本的低水平投資所導(dǎo)致的弱就業(yè)能力,是制約農(nóng)村人口擺脫貧困的關(guān)鍵因素[24]。渴望與投資的關(guān)系表明,有更高收入渴望的個體會更加注重人力資本投資并期待相應(yīng)的回報,根據(jù)人力資本的“干中學(xué)”效應(yīng),非農(nóng)就業(yè)者可以通過學(xué)習(xí)相關(guān)知識和工作經(jīng)驗加強人力資本積累[25]。非農(nóng)就業(yè)可以被看作是對個體自身人力資本的投資。在市場化條件下,脫貧戶較高的收入渴望水平可能會促進其家庭勞動力投入非農(nóng)就業(yè)。據(jù)此,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3:脫貧戶的收入渴望對其家庭非農(nóng)就業(yè)水平?jīng)]有影響。
近年來,非農(nóng)就業(yè)的減貧作用已被廣泛證實。如許路遙提出,勞動力從農(nóng)村流動到經(jīng)濟相對發(fā)達的國家或地區(qū)實現(xiàn)跨區(qū)域就業(yè)后,其工資收入的增加對家庭總體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顯著作用,有助于減緩其家庭收入貧困[26]。但非農(nóng)就業(yè)的增收效應(yīng)會因個體收入水平的高低有所差異主要表現(xiàn)為隨個體收入分位點的上移呈現(xiàn)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并且對中高收入群體的影響最為顯著而對低收入群體的作用并不明顯[27]。樊士德和劉一偉等提出農(nóng)村勞動力向非農(nóng)行業(yè)轉(zhuǎn)移不僅能直接增加家庭絕對收入,還能有效降低家庭陷入貧困的相對概率,對不同的貧困和福利衡量指標(biāo)而言結(jié)果均比較穩(wěn)健[28-29]。此外,非農(nóng)就業(yè)增強了農(nóng)村人口的社會流動性,能夠顯著增強其對科技、金融及生態(tài)扶貧等活動的參與意愿[19]。可見,非農(nóng)就業(yè)對緩解農(nóng)村家庭貧困具有重要作用,對農(nóng)村人口的文明進步也具有積極意義。
根據(jù)上文分析可知,通過非農(nóng)就業(yè)獲取的相對穩(wěn)定的工資收入對減貧具有重要作用。非農(nóng)就業(yè)還可以間接作用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領(lǐng)域,通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提升帶動家庭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收入增加,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農(nóng)戶土地規(guī)模有限而非農(nóng)就業(yè)機會短缺的背景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長期處于“過密化”狀態(tài)[30]。隨著家庭勞動力的適度退出,各生產(chǎn)要素投入比例的調(diào)整能夠緩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邊際收益遞減現(xiàn)象,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和土地產(chǎn)出率。其次,非農(nóng)就業(yè)收入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提供的資金、技術(shù)能實現(xiàn)對勞動力的替代,促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提升[31],這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提升帶來的收益可以被部分反饋給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工人。最后,農(nóng)業(yè)收入易受自然災(zāi)害和市場價格波動等不穩(wěn)定因素影響,而非農(nóng)就業(yè)較少受到外部因素干擾,因此增加非農(nóng)收入能有效分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風(fēng)險引致的農(nóng)戶收入風(fēng)險,降低家庭收入的不確定性。引導(dǎo)農(nóng)村勞動力適度參與非農(nóng)就業(yè)能有效分散單一收入來源風(fēng)險,提高家庭收入結(jié)構(gòu)穩(wěn)定性,最終達到穩(wěn)步提高脫貧家庭總體收入水平的目的。渴望與投資的關(guān)系表明,渴望作為個體內(nèi)生動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資本投資水平,而投資又是帶動脫貧人口穩(wěn)收增收的關(guān)鍵渠道。結(jié)合本文研究對象,收入渴望較高的脫貧戶可能更傾向于加強自身知識技能的積累,帶動和增加家庭在非農(nóng)就業(yè)上的勞動力投入。脫貧戶非農(nóng)就業(yè)水平的提高又能為家庭提供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從而提高脫貧戶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4:脫貧戶非農(nóng)就業(yè)對提高其家庭工資收入沒有影響。
假設(shè)5:脫貧戶非農(nóng)就業(yè)在收入渴望對家庭工資收入的影響中沒有起到中介作用。
二、數(shù)據(jù)來源及研究方法
(一)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數(shù)據(jù)來自課題組于2020年7月對陜西省周至縣原建檔立卡家庭的實地調(diào)研。周至縣是陜西省西安市惟一的原貧困縣,其縣域面積廣闊,自然條件多樣,屬秦巴山連片特困區(qū),作為樣本區(qū)域具有較強的代表性。由于周至縣經(jīng)濟環(huán)境在原西北地區(qū)貧困縣中處于中上水平,是全國脫貧攻堅總結(jié)表彰大會的受表彰縣,縣域脫貧戶表現(xiàn)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他較落后的原西北貧困縣脫貧戶在未來幾年的發(fā)展趨勢。
課題組從山區(qū)四鎮(zhèn)和沿山五鎮(zhèn)的全部建檔立卡家庭中按照鎮(zhèn)、村人口規(guī)模隨機抽樣并開展問卷調(diào)查,樣本數(shù)據(jù)來自96個行政村的826個脫貧家庭,剔除無效樣本后最終獲得807份脫貧戶數(shù)據(jù)。同時課題組以脫貧戶2019年家庭情況為基礎(chǔ),根據(jù)村委會資料對被調(diào)查家庭過往5年的人口變動和收入等情況進行核對,以保證數(shù)據(jù)能夠充分反映脫貧戶實際情況。最終樣本人均收入和樣本家庭人均收入的均值分別為12 195元和13 077元,略高于當(dāng)?shù)?.4萬戶脫貧戶總體的11 431和11 979元。盡管對樣本收入的單樣本T檢驗證明樣本均值仍存在差異,但綜合來看,本研究樣本抽取仍具有較強的科學(xué)性和代表性。
(二)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脫貧戶收入。目前關(guān)于貧困的研究中,貧困指標(biāo)通常是用各種形式的收支均值標(biāo)準(zhǔn)和方差標(biāo)準(zhǔn)表示,其核心仍然是貨幣標(biāo)準(zhǔn)。本文擺脫對特定標(biāo)準(zhǔn)的依賴,直接以脫貧戶2019年的家庭人均總收入和家庭人均工資收入作為因變量。相比于家庭總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在回歸中能夠消除家庭規(guī)模經(jīng)濟的直接影響,更能表現(xiàn)人數(shù)與家庭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系。直接研究收入的優(yōu)點是簡潔、更接近事物本質(zhì),影響路徑更為直觀,但缺點是對因變量正態(tài)分布的需求暴露得更明顯,同時相比于非定比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類型,收入對檢驗方法的檢驗力要求更強。
2.核心解釋變量:收入渴望。“渴望”一詞表達了某種目標(biāo)以及想要實現(xiàn)目標(biāo)的偏好或愿望[17]。渴望是個體愿意投入時間、努力或金錢去實現(xiàn)的目標(biāo),在本文中,個體首先對其自身未來可能實現(xiàn)的最佳收入水平進行預(yù)判,然后以此為目標(biāo)會驅(qū)使個體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而采取行動。在收入渴望的形成過程中,個體會受到自身渴望實現(xiàn)情況及其周圍人收入狀況的影響。在收入渴望的度量中,Stutzer將受訪者報告的“足夠”收入或“最低”收入作為收入渴望的代理指標(biāo),這兩種測量方法的研究結(jié)果較為一致,即隨著個體所在社區(qū)平均收入的上升其收入渴望也會提高[32]。根據(jù)收入渴望所具有的相對收入的特征,Dalton采用的測量方法是,先向調(diào)查對象展示當(dāng)?shù)卦率杖敕峙鋮^(qū)間表,然后詢問受訪者月收入達到多少時才能使其滿意[33],這種測量方法更能體現(xiàn)收入渴望的內(nèi)涵。本文在借鑒Dalton測量方法的基礎(chǔ)上,首先詢問受訪者對2019年全國農(nóng)村人均年收入水平與15 000元的主觀判斷(低于、稍低于、等于、高于、稍高于15 000元)和主觀幸福感等指標(biāo),對受訪者的收入認(rèn)知進行初步判斷,并告知其正確答案,讓受訪者建立對收入的統(tǒng)一感受,體現(xiàn)了社會比較和相對收入特征。然后向受訪者展示一張依據(jù)全國家庭收入分布和當(dāng)?shù)厥杖胨皆O(shè)計的家庭人均月收入?yún)^(qū)間表(見表1),詢問其家庭人均月收入達到多少時才會感到初步滿意,該答案即為受訪者的收入渴望。表格中對相關(guān)收入意義的標(biāo)示為受訪者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框架,能夠提高問項效力,避免受訪者因沒有參照物而作出過度偏離實際的回答。
3.中介變量:非農(nóng)就業(yè)。黎翠梅將“家庭非農(nóng)勞動力人數(shù)與家庭勞動力總?cè)藬?shù)之比”(后文簡稱“務(wù)工比”)作為能夠反映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的非農(nóng)就業(yè)變量[34]。本文同樣采用這一指標(biāo),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群體中受雇務(wù)農(nóng)和工農(nóng)兼業(yè)等行為也被算作非農(nóng)就業(yè)。
4.控制變量:本文首先通過引入控制變量來處理遺漏變量問題,所有變量定義及其描述性統(tǒng)計見表2。在控制變量的選取中,參照以往研究貧困和收入的相關(guān)文獻,本文從戶主、家庭、地理等3個層面確定控制變量。為了反映脫貧戶的真實情況,本文對金融資本、社會網(wǎng)絡(luò)、家庭存款等難以直接觀察的變量暫時不予選取。通過相關(guān)性分析,在排除存在明顯相關(guān)性和高度共線性變量的同時,盡可能多地選取自變量進行探索性分析。本文中所有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遠(yuǎn)小于10(最高不超過2.7),不存在高度共線性問題。
(三)模型構(gòu)建
本文主要應(yīng)用了中介效應(yīng)法,并根據(jù)收入和非農(nóng)就業(yè)的變量類型,將多元線性回歸作為檢驗中介效應(yīng)的基本方法,首先采用檢驗力較弱的逐步回歸來檢驗上文假設(shè)。中介效應(yīng)檢驗的基準(zhǔn)模型構(gòu)建如下:
Yi=α0+α1Xi+α2Ci+e1(1)
Mi=β0+β1Xi+β2Ci+e2(2)
Yi=γ0+γ1Xi+γ2Mi+γ3Ci+e3(3)
上式中,Yi為脫貧戶i的特定類型收入,Xi和Mi分別是脫貧戶i的收入渴望和非農(nóng)就業(yè)情況,Ci是其他控制變量。公式(1)表示收入渴望對脫貧戶收入的總效應(yīng),公式(2)表示收入渴望對中介變量非農(nóng)就業(yè)的影響,公式(3)表示收入渴望通過中介變量非農(nóng)就業(yè)對脫貧戶收入的影響,其中γ1為收入渴望影響脫貧戶收入的直接效應(yīng),γ2為收入渴望通過非農(nóng)就業(yè)對脫貧戶收入產(chǎn)生的中介效應(yīng)。本文通過聯(lián)立方程對可能存在的內(nèi)生性加以考量,方程構(gòu)建和參數(shù)估計結(jié)果見下文內(nèi)生性檢驗部分。
三、實證結(jié)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圖1是樣本脫貧戶2019年的家庭人均總收入與家庭人均工資收入情況。圖1中散點全部位于斜率為1的直線上或是其右下方,斯皮爾曼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56,體現(xiàn)了工資收入與總收入之間較強的相關(guān)性。擬合線與斜率為1的直線的夾角明顯小于其與橫軸的夾角,這表明即使在全部為農(nóng)村居民戶口的脫貧戶樣本中,工資收入在當(dāng)下仍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同時值得關(guān)注的是,脫貧戶的總收入分布呈正偏態(tài),輪廓較為平滑,但其工資收入分布存在雙峰現(xiàn)象,這是由于總樣本中存在107戶無工資收入家庭。為了便于分析,這107戶在后續(xù)部分分析中被剔除,使樣本的家庭人均工資收入能夠通過對數(shù)轉(zhuǎn)換基本滿足正態(tài)分布要求。
圖2是脫貧戶的收入渴望分布情況,其橫軸刻度間距是相等的。但在對表1的設(shè)計中,每一個收入檔位并非等距,隨著數(shù)額的增大其間距也在增大,因此使得脫貧戶的收入渴望集中在左側(cè)。同時由于表1中收入意義的說明和錨定作用,脫貧戶收入渴望集中在農(nóng)村家庭水平、稍高于農(nóng)村家庭水平、全國家庭水平和城鎮(zhèn)家庭水平等數(shù)值錨點附近,變成了實質(zhì)上的準(zhǔn)定類變量。所有樣本家庭的非農(nóng)就業(yè)均值為0.66,這說明在脫貧戶群體中,非農(nóng)就業(yè)已經(jīng)成為了脫貧戶家庭勞動力的最主要流向,這與上述工資收入的主導(dǎo)現(xiàn)狀相符。同時在有工資收入的700戶脫貧戶中,其收入渴望水平約為2 065元,遠(yuǎn)高于無工資收入人群的平均渴望水平1 246元,這一結(jié)果初步說明了收入渴望與脫貧戶工資收入的相關(guān)性是可能存在的,但其他猜想有待進一步驗證。
(二)收入渴望影響脫貧戶收入的直接效應(yīng)分析
表3是一組探索性回歸結(jié)果。其中回歸(1)至回歸(3)的因變量均為家庭人均總收入,其研究樣本分別為總的807戶脫貧戶、有工資收入的700戶脫貧戶和無工資收入的107戶脫貧戶。回歸(4)的因變量為家庭人均工資收入,樣本為有工資收入的700戶脫貧戶。從表3結(jié)果來看,脫貧戶收入渴望在1%顯著性水平下對其家庭人均總收入和人均工資收入均有穩(wěn)定正向影響。通過比較回歸(1)至回歸(3),可以看出收入渴望對于脫貧戶工資收入的影響可能在所有收入類型中是最大的,對無工資收入家庭擁有的其他類型收入的總和也依然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通過比較回歸(1)、(3)與回歸(4),相比家庭人均總收入,戶主特征對家庭人均工資收入的影響更加微弱,其戶籍人口、撫養(yǎng)比和疾病負(fù)擔(dān)等家庭人口結(jié)構(gòu)特征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更加明顯。這是因為在脫貧戶群體中,戶主通常為最年長的家庭成員,較弱的身體條件和勞動技能讓他們難以成為獲取工資收入的主力。以上結(jié)果和分析有效地拒絕了本文假設(shè)1的原假設(shè)。
表4中回歸(5)至回歸(8)的因變量均為家庭人均工資收入,與表3中的回歸(4)構(gòu)成了一組較完整的變量分層回歸,對應(yīng)上文的公式(1)。相比單變量回歸,多元回歸的調(diào)整決定系數(shù)最高提高到0.217,這表明增加控制變量能夠明顯提高回歸的擬合水平,同時收入渴望的系數(shù)降低,這表明其與被遺漏變量的關(guān)聯(lián)也在引入控制變量后被部分消除。在引入家庭特征后,原本影響顯著的戶主年齡、婚姻等特征也變得不再顯著,這部分體現(xiàn)了脫貧戶家庭特征對戶主個人特征影響的遮掩效應(yīng),戶主特征對家庭人均工資收入的影響通過其家庭特征來體現(xiàn)。回歸(8)的調(diào)整決定系數(shù)最高,這表明控制變量的引入并非越多越好,家庭人口結(jié)構(gòu)對家庭人均工資收入起到了主要解釋作用,控制變量選取仍需優(yōu)化。以上結(jié)果和分析有效地拒絕了本文假設(shè)2的原假設(shè)。
(三)收入渴望與非農(nóng)就業(yè)關(guān)系檢驗
表5為收入渴望對中介變量非農(nóng)就業(yè)的影響,對應(yīng)上文的公式(2)。回歸(9)至回歸(12)分別表示在不添加任何控制變量和依次加入戶主、家庭和地理位置三個層面的控制變量時,收入渴望對中介變量非農(nóng)就業(yè)的影響。隨著控制變量的加入,模型的擬合水平出現(xiàn)明顯提升且收入渴望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脫貧戶非農(nóng)就業(yè)水平,該結(jié)果拒絕了本文假設(shè)3的原假設(shè)。
在回歸(12)中,脫貧戶地理位置對其家庭非農(nóng)就業(yè)水平的影響不顯著,這說明空間距離已經(jīng)不是阻礙脫貧戶務(wù)工的主要制約因素。戶主婚姻和戶籍人口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負(fù)向影響脫貧戶非農(nóng)就業(yè)水平。這可能是由于與正處于婚姻狀態(tài)的脫貧戶相比,獨居單身務(wù)工的脫貧戶對務(wù)工比比值的影響較大。同時在脫貧戶群體中,在家庭非農(nóng)就業(yè)勞動力數(shù)量相對穩(wěn)定的情況下,家庭人口較多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非農(nóng)就業(yè)水平。家庭撫養(yǎng)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非農(nóng)就業(yè),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脫貧家庭老幼數(shù)量的增加會迫使有限的家庭勞動力更多地投入務(wù)工以獲得更高的收入。
(四)收入渴望影響脫貧戶收入的中介效應(yīng)分析
上文實證結(jié)果顯示,脫貧戶收入渴望對非農(nóng)就業(yè)產(chǎn)生顯著正向影響,對家庭人均工資收入同樣產(chǎn)生顯著正向影響,但非農(nóng)就業(yè)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仍不清晰。根據(jù)上文結(jié)果,在對非農(nóng)就業(yè)中介效應(yīng)的分析中,部分變量被剔除以使得模型設(shè)置能夠兼顧解釋性和簡潔性。對應(yīng)公式(1)至公式(3),采用逐步回歸檢驗法,檢驗非農(nóng)就業(yè)在收入渴望影響脫貧戶工資收入的中介效應(yīng),結(jié)果如表6中回歸(13)至(15)所示。
表6為收入渴望通過非農(nóng)就業(yè)對脫貧戶工資收入產(chǎn)生的影響。回歸13的結(jié)果顯示,在不添加中介變量時,脫貧戶的收入渴望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其家庭人均工資收入。回歸14的結(jié)果顯示,脫貧戶的收入渴望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其家庭非農(nóng)就業(yè)情況。回歸15的結(jié)果顯示,在將核心解釋變量和中介變量同時加入回歸后,收入渴望和非農(nóng)就業(yè)的系數(shù)分別出現(xiàn)了明顯的下降和升高,但仍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家庭人均工資收入。非農(nóng)就業(yè)系數(shù)的明顯上升,一個原因可能是務(wù)工比這一比率對非農(nóng)就業(yè)特征的代表性不夠,收入渴望可能還會通過勞動強度、就業(yè)類型等途徑影響最終的工資收入水平,如收入渴望較強的人會通過投資自身技能來獲取薪酬更高的工作機會。以上結(jié)果和分析有效地拒絕了本文假設(shè)4和假設(shè)5的原假設(shè)。
四、內(nèi)生性檢驗
根據(jù)上文的理論分析,收入渴望、非農(nóng)就業(yè)和工資收入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內(nèi)生性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脫貧戶收入渴望與家庭人均工資收入之間的雙向因果關(guān)系,即個體收入增長也會導(dǎo)致其渴望水平的增長[32]。因此本文采用黎翠梅等的做法,通過聯(lián)立方程模型將內(nèi)生性考慮在內(nèi),也是檢驗?zāi)P头€(wěn)健性的一種方式[34]。依據(jù)尤亮等的研究結(jié)果,本文將主觀幸福感和戶主婚姻等變量引入模型[35],建立聯(lián)立方程如下:
Yi=f(Xi,Mi,Ci,Coopi)(4)
Xi=f(Yi,Ci,Coopi,Wbi)(5)
Mi=f(Xi,Ci,Marri,Wbi)(6)
其中X,Y,M的含義與公式(1)至公式(3)一致,C為共同控制變量,包括戶主年齡、戶籍人口、撫養(yǎng)比、疾病負(fù)擔(dān)四項,Coop為合作組織參與情況,Wb為脫貧戶主觀幸福感,Marr為婚姻狀況。
表7和表8分別是對聯(lián)立方程使用作為有限信息估計法的OLS估計和作為系統(tǒng)估計法的3SLS估計的結(jié)果。由于內(nèi)生性的存在,OLS估計結(jié)果存在不一致問題,但檢驗力最強,因此表7中的結(jié)果與上文表6中依次檢驗的結(jié)果近似。同時人均工資收入、戶籍人數(shù)和主觀幸福感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影響其收入渴望,驗證了脫貧戶收入渴望和工資收入之間雙向因果關(guān)系的存在。控制變量中,選取的所有家庭變量和戶主婚姻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影響脫貧戶非農(nóng)就業(yè)。表8所使用的3SLS估計充分考慮了不同方程擾動項可能存在的相關(guān)性,通常表現(xiàn)出檢驗力更弱的特點。在核心變量的關(guān)系中,僅有收入渴望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影響人均工資收入。在其他控制變量中,家庭變量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影響人均工資收入。所有自變量對收入渴望的影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不顯著,僅有家庭撫養(yǎng)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對非農(nóng)就業(yè)仍有正向影響為節(jié)省篇幅,部分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未在表7和表8中列示。。
綜上所述,在考慮收入渴望、非農(nóng)就業(yè)和脫貧戶工資收入三者之間的內(nèi)生性后,聯(lián)立方程模型的結(jié)果與基準(zhǔn)模型基本一致。總體來看,在任何情況下,假設(shè)2的原假設(shè)都可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被拒絕。而脫貧戶收入渴望與工資收入的關(guān)系,在檢驗力較強的檢驗中會呈現(xiàn)相互促進的雙向因果關(guān)系。在脫貧戶收入渴望和非農(nóng)就業(yè)關(guān)系的3SLS聯(lián)立方程檢驗中,收入渴望對非農(nóng)就業(yè)影響的標(biāo)準(zhǔn)誤較大,說明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不足。同時在對非農(nóng)就業(yè)中介作用的檢驗中,非農(nóng)就業(yè)僅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結(jié)合3SLS估計中標(biāo)準(zhǔn)誤較大的問題,可以看出,表現(xiàn)非農(nóng)就業(yè)的務(wù)工比可能并不是收入渴望影響工資收入的主要中介變量,但務(wù)工比的中介作用依然能夠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假設(shè)5的原假設(shè)。
五、結(jié)論與建議
低收入群體的貧困到底是因為環(huán)境資源的限制還是其自身主觀能動性的缺乏,抑或兼而有之?較強的收入渴望是否會成為推動脫貧戶窮則思變的主要因素?本文基于陜西省周至縣807戶原建檔立卡群體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探討了脫貧戶收入渴望、非農(nóng)就業(yè)與其家庭收入之間的關(guān)系。研究結(jié)論顯示:一是脫貧戶的收入渴望對其家庭工資收入和其他類型收入都有顯著影響,同時脫貧戶收入也會影響其收入渴望,與相關(guān)文獻結(jié)果一致。二是脫貧戶的收入渴望顯著影響其家庭非農(nóng)勞動力的投入,而非農(nóng)就業(yè)在收入渴望對家庭工資收入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三是在脫貧戶收入渴望通過非農(nóng)就業(yè)影響家庭工資收入的影響機制中,撫養(yǎng)比、疾病負(fù)擔(dān)等家庭人口結(jié)構(gòu)特征對家庭非農(nóng)就業(yè)情況和工資收入:(1)要以脫貧戶的收入結(jié)構(gòu)為基礎(chǔ),將脫貧戶按照其客觀自生能力的強弱分類,通過各種激勵措施提高有潛力的脫貧戶成員的主觀能動性,增強其收入渴望,減少不必要的“等靠要”現(xiàn)象。(2)對有務(wù)工能力的脫貧戶成員,要盡可能通過務(wù)工技能培訓(xùn)等多種形式,提高務(wù)工機會和勞動技能,增強其收入獲得感和工作選擇范圍。(3)在對原有脫貧戶進行政策傾斜和物資幫扶的基礎(chǔ)上,對務(wù)工者家中留守老幼分別在健康、教育上加大支持,解決務(wù)工者的后顧之憂。
已有研究指出,社會比較、渴望適應(yīng)、自我效能感和個人控制點等因素對渴望的形成均有影響[36]。因此,對于固守“等靠要”思想但有發(fā)展?jié)摿Φ某蓡T,可考慮從以下方面著手激發(fā)其收入渴望。第一,可以通過社會比較機制拓寬個體周圍可比較群體范圍,樹立與其背景相似的成功榜樣;第二,要提供能夠讓減貧對象感受到勞有所獲的有效幫扶措施,引導(dǎo)其將增收成果向內(nèi)歸因,分享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成果,增強其自我效能感;第三,要消除貧困人口所面臨的外部約束,通過移民搬遷、基礎(chǔ)設(shè)施供給等方式,提高其資源可得性,減少發(fā)展起步階段的難度,增強其發(fā)展信心。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僅通過錨定收入檔位來確認(rèn)脫貧戶的收入渴望,使得這一數(shù)值的確定在標(biāo)準(zhǔn)一致的同時更容易受到脫貧戶當(dāng)前收入的影響,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員水平也不盡相同。同時以務(wù)工比來代表非農(nóng)就業(yè)也存在變量表現(xiàn)不充分的問題。在未來的研究中,一是可以通過多種指標(biāo)來完善對脫貧戶主觀能動性的判斷;二是在對困難群體主觀能動性的研究中,要多關(guān)注家庭決策者而非戶主特征;三是在對非農(nóng)就業(yè)的研究中,采用非農(nóng)工作內(nèi)容、非農(nóng)工作條件等多種指標(biāo),從多角度豐富對非農(nóng)就業(yè)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左停,李澤峰,林秋香.相對貧困視角下的貧困戶脫貧質(zhì)量及其自我發(fā)展能力——基于六個國家級貧困縣建檔立卡數(shù)據(jù)的定量分析[J].華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1(02):32-44.
[2] 杭承政,胡鞍鋼.“精神貧困”現(xiàn)象的實質(zhì)是個體失靈——來自行為科學(xué)的視角[J].國家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2017(04):97-103.
[3] 管睿,王文略,余勁.可持續(xù)生計框架下內(nèi)生動力對農(nóng)戶家庭收入的影響[J].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9,19(06):130-139.
[4] 張玉武,張奇,馮元.后脫貧攻堅時代農(nóng)民的“精神貧困”如何治理?[J].社會與公益,2020(06):90-92.
[5] 賈海彥.基于心理與行為雙重視角的脫貧內(nèi)生動力研究[J].湖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21(02):132-144.
[6] 程國強,朱滿德.2020年農(nóng)民增收: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與應(yīng)對建議[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20(04):4-12.
[7] 柳建平,王璇旖,劉咪咪.勞動力非農(nóng)就業(yè)的減貧脫貧效應(yīng)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甘肅14個貧困村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J].西安財經(jīng)學(xué)院學(xué)報,2019,32(04):100-108.
[8] 朱農(nóng).離土還是離鄉(xiāng)?——中國農(nóng)村勞動力地域流動和職業(yè)流動的關(guān)系分析[J].世界經(jīng)濟文匯,2004(01):53-63.
[9] 韓佳麗.貧困地區(qū)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減貧的路徑比較研究[J].中國軟科學(xué),2019(12):43-52.
[10] 柳建平,張永麗.勞動力流動對貧困地區(qū)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影響——基于甘肅10個貧困村調(diào)查資料的分析[J].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09(03):63-74.
[11] 尤亮,劉軍弟,霍學(xué)喜.渴望、投資與貧困:一個理論分析框架[J].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18(05):29-44.
[12] FLECHTNER S.Should Aspirations Be A Matter of Policy Concern?[J].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2017,18(04):517-530.
[13] DALTON P S,JIMENEZ V,NOUSSAIR C N.Exposure to Poverty and Productivity[J].Plos One,2017,12(01):1-19.
[14] 胡小勇,徐步霄,楊沈龍,等.心理貧困:概念、表現(xiàn)及其干預(yù)[J].心理科學(xué),2019,42(05):1224-1229.
[15] BERNARD T,TAFFESSE A S.Aspirations:An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With Validation Using Ethiopian Data[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14,23(02):189-224.
[16] RAY D.Aspirations,Poverty and Economic Chang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12.
[17] BERNARD T,DERCON S,TAFFESSE A S.Beyond Fatalism: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Self-efficac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 in Ethiopia[EB/OL].(2012-11-22)[2021-07-12].http://cdm15738.contentdm.oclc.org/utils/getfile/collection/p15738coll2/id/127273/filename/127484.pdf
[18] GENICOT G,RAY D.Aspirations and Inequality[J].Econometrica,2017,85(02):489-519.
[19] 苗欣,吳一平.中國農(nóng)村貧困戶勞動力轉(zhuǎn)移的減貧效應(yīng)分析——基于河南省12個貧困縣1 211份調(diào)查數(shù)據(jù)[J].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1,61(03):43-50.
[20] APPADURAI A.The Capacity to Aspire: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59-84.
[21] JENSEN R.Do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ffect Young Women’s Work and Family Decisions?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di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127(02):753-792.
[22] JENSEN R.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125(02):515-548.
[23] GENICOT G,RAY D.Aspirations,Inequality,Investment and Mobility[EB/OL].(2009-07-22)[2021-07-18].https://pages.nyu.edu/debraj/Papers/GenicotRayAspirations2009.pdf.
[24] MACOURS K,VAKIS R.Changing Households Investments and Aspirations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s: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ansfer Program[EB/OL].(2009-11-15)[2021-07-18].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103711468159916345/pdf/WPS5137.pdf.
[25] LUCAS R E.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S1):1-31.
[26] 許路遙.我國農(nóng)民工數(shù)量與農(nóng)村居民家庭收入關(guān)系的實證研究[J].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4(09):2761-2764.
[27] 楊晶,鄧大松,申云.養(yǎng)老保險、非農(nóng)就業(yè)與農(nóng)戶收入差異[J]. 江西財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2019(03):65-74.
[28] 何洋.普通話水平與農(nóng)村勞動力非農(nóng)就業(yè)——基于CFPS 2016的實證分析[J].西安財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2020(05):106-114.
[29] 劉一偉,刁力.社會資本、非農(nóng)就業(yè)與農(nóng)村居民貧困[J].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8,17(02):61-71.
[30] 錢龍,洪名勇.非農(nóng)就業(yè)、土地流轉(zhuǎn)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變化——基于CFPS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16(12):2-16.
[31] 孫伯馳,段志民.非農(nóng)就業(yè)對農(nóng)村家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J].現(xiàn)代財經(jīng)(天津財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2019,39(09):97-113.
[32] STUTZER A.The Role of Income Aspirations in Individual Happines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2004,54(01):89-109.
[33] DALTON P S.Income Aspirations and Cooperation:Experimental Evidence[Z].Working Paper,2010.
[34] 黎翠梅,李靜,葦傅沂.農(nóng)地流轉(zhuǎn)、非農(nóng)就業(yè)與農(nóng)民減貧[J].經(jīng)濟與管理,2020,34(05):10-18.
[35] 尤亮,楊金陽,霍學(xué)喜.絕對收入、收入渴望與農(nóng)民主觀幸福感——基于陜西兩個整村農(nóng)戶的實證考察[J].山西財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2019,41(03):16-30.
[36] 尤亮,霍學(xué)喜.渴望:概念、形成機理與展望[J].外國經(jīng)濟與管理,2020,42(01):140-152.
Income Aspiration,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Income of Poverty-alleviated Households
——Taking Zhouzhi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EN Guang,WANG Juan,WANG Zhengb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amp;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the importance of spiritual poverty manage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807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in Zhouzhi County,Shaanxi Province,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piritual poverty,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come aspiration,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the income of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come aspiration on the income of the households who were used to be in absolute poverty.The results show that:(1) income aspi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income,wage income and the sum of other types of income,among which the impact on wage incom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2) Income aspiration is beneficial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non-farm employment based on household labor input,and indirectly affects household wage income.(3) In the intermediary mechanism,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respondents,the influence of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households 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wage income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Finally,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 stimulating the income desire of the target group,creating the environment for labor upgrading, and continuing to increase the inclin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Key words:mental poverty;aspiration failure;poverty-alleviated household;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household income
(責(zé)任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