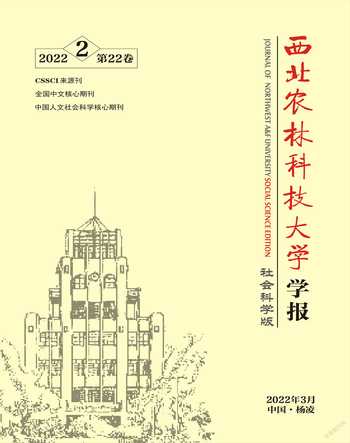高山狹縫道通天
摘 要:就已故著名教授石聲漢音韻學遺札,習讀鑒賞并加以考索,判定為自課修練古音學的珍存。所見與其生前傳囑的“校勘道路”和“絕學狹縫”等,若合契符,實古農學不二法門。石氏藏修音韻法,總賅為“三段四途”:即學識-修煉-致用三個階段。其中修煉過程最見功力,要之為四大途徑:一是熟讀《廣韻》,以通中古音系,上推下聯貫通古今音理;二是系聯《易林》韻腳,模仿清儒歸納上古韻部而驗之;三是抄練《說文》諧聲偏旁,以明音近意通和因聲求義之理;四是參與方言調查,勘驗古音之“化石”,明近古及當今語音演變之履跡,略知“禮失而求諸野”之古道。
關鍵詞:音韻學;《廣韻》;上古音;說文
中圖分類號:H131.6;F3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2-0146-05
收稿日期:2021-07-01"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2.17
作者簡介:張波,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古農學。
石聲漢先生孝賢哲嗣,珍獻先父音韻學遺札多種數帙;特囑吾儕先睹賞鑒,且為作評介并以網傳,替古農學振興復奠堅基。顧念先師后學之倫常,義不容以學識淺陋逃難塞責。遂塵出少壯年兩度赴京進修音韻訓詁學筆記簿冊,溫故思罔,略復聲韻音理知識及學科語境。如此,方始習讀思索先生遺帙,試探妙道旨趣,領悟修練功法,展望后學承襲之路徑。
所見先生遺札軼稿,多蠅頭微書,瀟灑俊秀賞心悅目。惜紙張系困難歲月造物,質劣屑薄缺殘,觸之欲破不任翻檢。經史君全社輔裱復印,才得展閱鑒讀。遺軼主件約為四類:讀《廣韻》札記;《焦氏易林》札記;《古今韻準》抄習;《譯音表》及方言論稿;其余字表散篇,皆與四者相關。總是先生字墨章法風韻猶存,可思文意而兼賞書藝,令人愛不釋卷。其女石定枎老師特委托史全社代存,以提供知音者參閱,共享這筆獨特的古農學遺產。
一、“點”與“小縫”——石氏藏修音韻學之道
古人有“藏修之道”,與本段所論不謀而合。石先生晚年曾有遺世教言,現復述重溫以昭明其核心學術路線:“古代農書的寶庫,究竟從那一個‘點’攻進去,過去大家的認識都不很明確。我是習慣于舊的校勘道路,便想從小學上先鉆出一個小縫,自己先‘進去’,找地下宮殿的大門,然后把大門打開,讓大家再進去清理。”
石先生所言何意?怎么踐行,古農學寶庫宮殿若何境界?如今“遺言”與“遺帙”兩相契合,交互輝映順理成章,多年的迷茫困惑若撥云霧見晴天。茲知先生所謂“點”,即古農學科之重點、難點、突破點,實在小學范疇。小學有文字、音韻、訓詁三科,而所謂的“小縫”,特指音韻之學。蓋石先生面壁古農學,篤定走傳統校勘學道路,通過鉆研音韻學的縫隙,從而獨登古典農學之高峰,本文命題遂油然而生。
大凡染指音韻學,尤其濡沫較深者,皆知斯學確屬冷門絕學,難教難學,更難會通致用。知音者如魚吞水冷暖自知,即欲治音韻必經苦學、修煉、致用三個階段:先學基本概念和音理常識;再通過音韻文獻或方言調研實練;然后運于專門研究領域。石先生早在1928年致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家信中便稱:“漢十四五歲時,曾以《切韻指掌圖》所述三十六字母之用法,為探索門徑,閉門自造于玄想中。參以幼年家父所教詩詞及《詩經》轉葉諸例,自習音韻一年。當時無師訓可尋,一切但憑諸幼稚之推測,自構空中樓閣。及入武昌大學生物系,此調久已不彈。偶聞黃季剛(侃)先生講授時,一往聽之,知彼所謂音韻學者,漢向未得窺其門徑。”于此可知石先生少青年間,已得潛潤音韻之學,且親聆乾嘉學派殿軍黃侃音韻傳教,見識傳統與新派兩種音韻教習方法,實屬先得優質音學教養之有幸者。
新中國成立后,石先生音韻則進入修煉和致用階段,同時在《齊民要術今釋》校注中進行,既取得農書校勘成果,也幸留修煉音韻遺札存之后世。20世紀70年代間,家人以其中兩帙,呈國中最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王力先生評章。二賢斷為修煉音韻功力之遺帙,驚異石氏治學勤奮與鉆研之深。唯惜當時家人集逸未全,鑒論者未見遺物全豹,也無緣詳知《齊民要術今釋》音韻學實用成就。而今統覽全部遺帙,石先生修煉致用的思路和方法盡在其中,實不乏創新和神奇之處,正是后學循道效法之捷徑。故下面段落,將逐項分析遺帙修煉目的旨意,揭啟“點”與“小縫”的藏修之密,展示古農“地下宮殿”,引導后學進而發掘整理,實現石先生殷殷遺愿。
統觀石先生的遺言和遺帙,宛如穿越式實訓情景教學課。《禮記·學記》:“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漢儒解為專注向學,為精研深究和勞逸相得的學術境界。石先生修治音韻學之經歷情狀,鮮有知其詳者,稱之藏修倒也合宜;論其古音校注農書成就,謂之名山大業亦是人所景仰。
二、《廣韻》——通貫古今聲韻音理之津梁
石先生遺帙以修煉《廣韻》門法為大宗,標題《讀廣韻札記》集成巨冊。前綴緒語,記述《廣韻》一書歷代版本,雖多為摘錄,亦見精選卓識。遺文僅留千二百余字,似欲結論長篇,尚未及舒展即暫收筆,或有待日后續記增益。全札連篇累牘,詳錄《廣韻》小韻反切,條例清晰字跡爽快,亦見態度肅然。久治音韻者不難洞明其中消息:《廣韻》反切正是傳統音韻學精要和核心所在,為構建中古音系的不二法門,兼當開門啟戶的鎖鑰。石先生抑或特意傳遺后學,以領悟其中妙道。
音韻學屬歷史語言學,經歷由古及今的發展過程,可分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以及隨中古時期形成的等韻學。但學治音韻學必從唐宋中古音開啟門徑,奠定堅實古音概念和音理知識基礎;然后上推秦漢及以前之上古音系,再下聯元明清之近古音系統。中古是音韻學久蓄勃發和全面成熟時期,層出不迭韻書韻圖便是顯著奪目的標志,傳統音韻學的實踐和理論成果盡在其中。中古音學以《廣韻》學術價值至高,包羅各地的語音資源,集成有魏晉以來的韻書材料,堪稱廣通古今南北語音的要道橋梁。
《廣韻》為讀音識字兼義項的工具書,又是唐宋詩詞韻文的國頒官制范本;然權衡其至高無比的歷史語文價值,正體現在中古文字的反切注音。《廣韻》有 3 890個反切,包含452個反切上字,1 195個反切下字,據反切之法可得一字的讀音,字字可寶。古人又參考梵語創造出等韻學原理,從反切系統中總結出聲、韻、調和清濁、等呼、轉攝等概念,形成漢語獨特的描述語音學。石先生親手抄錄熟讀小韻反切,勤做《廣韻》音系的基本功,正是傳統音韻學修煉不可闕如之常規之法。
近世西學東漸現代語音學傳入,中外學者有以科學的音位和音值等理論,推新研究《廣韻》和反切系統,找出現代意義的聲母和韻母,最終用國際音標寫出音讀,稱之為“擬音”。石先生在《廣韻》擬音方面也用足了功夫,制作有縝密的聲韻相配的《字表》,構建有獨特而規范的古漢語擬音體系。古音構擬起自民國初年,始于來華做方言調查的瑞典學者高本漢,早期學者多參用高氏中古擬音體系。上世紀50年代擬音者漸多,則遵循北大王力先生古漢語擬音系統。石聲漢先生獨處遠辟西北農學院,完成了傳統和現代音韻結合修煉過程,對《齊民要術今釋》數百疑難古字作出構音注解,從現代音到中古上古音都有國際音標或拼音之注。石氏自標的擬音,大得國內外注家的認可,海外漢學家贊許為“賈學之幸”,古音的注釋精確令人嘆服。《讀廣韻札記》僅有小韻反切和字表遺存,而本文主筆者曾見石先生常用《廣韻》本,對小韻反切多在書眉作出擬音;并由此心生求學音韻的訴求,遂有上述赴京進修音韻訓詁學的往事,自贅陳言,僅證書眉擬音其事鑿然有據而已。
從少年時《切韻指掌圖》,到《讀廣韻札記》遺帙,再到《廣韻》書眉和古農書校注的擬音標記,石聲漢先生修煉音韻學足跡清晰可鑒,從狹縫攀登至學術巔峰精神,當仰高山而敬之。
三、《易林》——推衍上古音之妙道
《焦氏易林札記》及相關資料,為遺帙之大宗,乃石聲漢先生欲推衍上古音系,別具匠心而獨辟蹊徑。上古音主要指從殷商到魏晉時期的語音,歷時早而音系研究和發明較晚,宋元后上古音才萌發崛起。明清古音家擯棄千余年葉音變讀繆說,遵循漢儒實事求是精神,使上古音研究走上科學之軌道。其法要領在忠實歸納系聯《詩經》韻腳字,絲連繩引建立上古韻部;又通過離析《廣韻》之韻部,與中古音銜接貫通。歷代古音學家前仆后繼不懈探索,其中以顧炎武等位成就影響最大。前修未密后出轉精,至晚清上古韻部格局確立,致后來者無開新駐足之地。上古聲母系統構建也小有成績,聲調研究則大不如意。總因上古文獻資料畢竟有限,除《詩經》外其余韻文和聲音材料,均不足構成聲韻系統。故石先生遺世的《焦氏易林札記》,所做的大量《易林》音韻資料,其目的意圖很值得后人考究。
《易林》一書,西漢焦延壽所撰,又名《焦氏易林》,漢代易學一流派。《易經》六十四卦,計卦爻辭不過450條;《易林》法則是易之每一卦各變六十四卦,得4 096占變之辭,稱為林辭,皆成四言韻語。或許因為占卜之書,且筮法早逸未廣傳后世,四庫文獻中評定地位不高,鮮登大雅之堂,學界民間少見普用《焦氏易林》。近今之世聞一多評贊“蓋其事雖《易》,其詞則詩。”錢鐘書也從文學價值考量其歷史意義,直將《焦易》與《詩經》相提并舉。即便不論其筆意簡妙和古雅玄理,數千篇前漢四言詩,成萬計韻腳字,秦漢藝文中獨此一書。石先生博識古籍,但從不以“易說”論學,尤其鄙夷占筮事,避之唯恐不及,故知其染指易學當別有用意。
石先生《焦氏易林札記》一大本,另外有《焦氏易林韻析》《易林叢出爻辭總錄》等帙冊。王力、呂叔湘先生僅見札記片段,判斷擬為該書做“索引”,遂以所需讀者少而否定之。今觀石先生所記《易林》全部遺文,可見搜集到《易林》多種版本,隨文信手似的校正勘誤和批字,古農校注家的能事躍然紙上。遺文重點實在連篇累牘的音韻剖析,各卦林辭(即詩篇)按字母為序排列,每四字韻(即詩句)也依序編排,以便系聯調整。所見系聯結果,只有部分入聲歸納為上古韻部,其余部分因遺帙有散失而未能得其全貌。想必平上去之舒聲,理應完成在入聲之先,不難判斷《焦氏易林》韻腳字的分類歸部基本完成。石先生對此書為何如此著力用功?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主要在于修煉上古音功夫,解決古籍校勘中的音韻問題,以為校注古農書之用。當時石先生已制定龐大的古農書整理規劃,夜以繼日校注骨干農書,絕不可能再做跨學科其他研究項目。關于規模龐大、格局非常的《焦氏易林札記》,綜合各方面見識作如是判斷。
四、《說文》——聲音通訓詁之小學樞紐
石先生抄寫的《韻準》札記,石體小楷細錄,小篆題名下附“據朱駿聲”,與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后附《古今韻準》盡同。古人或前輩文人慣以抄書為強記之法,所謂眼過千遍不如手過一遍;凡稱過目不忘者,多經抄寫深化理解和記憶,石先生亦善用此法強學苦煉。《韻準》抄練雖小札,所錄內容為同諧聲偏旁字和同聲或同源文字,直關朱駿聲大著中的“通訓定聲”原理。然更大學術背景,還在書名中“說文”二字,道明石先生曾深潛《說文》領域,全方位修煉乾嘉學者的小學功夫。
清代學術以文獻考據為風尚,文字訓詁類小學之書用為利器,治《說文解字》者數逾百家,而以段玉裁為首的《說文》四大家聲名最著,朱駿聲以《說文通訓定聲》赫然其中。大約20世紀30年代初,石先生就購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常置書櫥文案,為手頭肘后工具之書。晚年似更傾心《說文通訓定聲》,蓋因段注形音義三者兼善俱佳,而朱氏獨辟蹊徑,舍形重聲,更切用修煉上古音者參用。朱氏將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定為形體之事,形聲擬為文字孳乳;精創在轉注和假借兩者,即所謂通訓之說。前人定義始終含糊不清,朱氏則直言,轉注即詞義引申,假借即同音通假,《說文》六書說由此豁然俱明。
《說文通訓定聲》與文字訓詁多有發明,主題落腳仍在定聲,創新唯在音韻,是石先生晚年兼愛并重段朱兩家之緣由。朱氏將《說文解字》原書體例作創新編排:解散固有540部,以上古韻十八部為大系統,部統之內又以諧聲之聲符為綱,建883個諧聲系列,立1 137聲符,秩次井然有序。同聲符滋衍字聯綴一起,每字之下一如書名,分為三部分內容。首先部分是“說文”遵從許慎原說解,或稍加增補調理引證;第二部分通訓主要講轉注和假借,轉注引申,假借同音通假,較原書和前人都講得合理明徹,學術價值最高而精彩;第三部分定聲是用先秦韻文用韻證明古音,凡同韻押者叫“古韻”,不同韻相押者叫“轉音”。全書正是按古韻部列綱統領,派以析而支以分,自稱“將使讀古書者應弦合節,無聱牙詰詘之疑”,觀其書也不為過分自詡。
石聲漢先生勤習熟練《古今韻準》分部和諧聲同源字,隱含著深邃的聲韻音理。音韻學從關注上古詩歌的和諧押韻,到文字孳乳紛生的諧聲時代,方覺同聲旁者必同部的音韻現象。至清代古韻部全面揭示后,“音近義通”的規律遂成共識,于是乎開辟出“因聲求義”的治學途徑。《說文》系統學術研究者大都精于此道,文字、音韻、訓詁即小學領域,無不重視三者結合,而尤重音義之間的關系。聲音通訓詁成為傳統語言文字學之紐帶,故石先生與《說文》及小學修煉亦不惜功力。
五、方言——語失而求諸野
古語“禮失而求諸野”,擬之于古音何嘗不也同理!遺帙中還散見有關于方言音韻信息,抑或為其修煉古音的又一天然通道。石先生語言巧能得之稟賦,常用音韻學原理考察各路方音,自言能懂長江以南多地方言。青年時在大瑤山生物科考,兼采蒐集少數民族語言和歌謠,翻譯出刊《瑤歌200首》;同時對瑤民土語,與當地方言進行比較性研究,頗得辛樹幟先生褒獎,鼓勵撰稿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初立于中山大學,石先生學治音韻憑依近水樓臺,得西方現代語言學之先聲,語音知識更加全面篤實。數年后石先生又入國立編譯館作專職譯員,此館薈聚世界多種語言,可謂萬國語輶軒使者群集一堂,其語言學見識漸富有國際視域。
遺件中還有石先生特制《譯音表》兩大張,為研究漢語音韻和譯文自用工具圖。表例前序簡述各民族語言殊異的聲韻之理,深論音素結構不同的原因,采文言文表述,語精而意賅。凡例八條俱現中古至近現代聲韻縱橫關系,例字選自《廣韻》《四聲切韻表》《切韻指掌圖》等,《譯音表》當是石先生構擬中古音的基本參照。關于方言,序中明列為一條,強調方音的輕重、清濁、吐氣、帶音等發聲方法,皆與當時國語不同,又將近似音以小組法合并,以省簡篇幅利于表用。特為方言三致意。
方言有別于雅語,今人定義為區別于標準語、只通行某地域的語言。方言是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現象,關乎所在地自然、社會、風土、民情等況,負載本地區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積淀的珍貴遺產。雖限于方域之地,卻保留著完整的語言系統,有獨立的語音結構和詞匯語法體系,被稱為地區歷史語言的“活化石”。方言學與音韻學同屬廣義的語言學,兩科層次系統有差別,但學科交叉點卻異常顯著,在中古音領域如影相隨。音韻學以《切韻》音系為樞紐,展現宏大的聲韻系統;方言學同樣離不開《切韻》的參照系,現行的《方言調查字表》即以廣韻音系為框架編制而成。通過參與方言調查,熟悉中古《切韻》語音系統,上推下聯上古和近古音系,便能學得鮮活的音韻學知識。石先生遺札啟示的上述各種音韻學修煉方法,大約方言法可稱務實途徑,適合當下教學或自修采用。蓋音韻學當屬歷史語言學,一般修煉方法總是以文獻性語音材料為對象;所謂的口耳之學,實賴文字記述,籍“二官”之職無法傳聽真正古音古聲。故學習者在初具語音和音韻學知識后,經過一番活生生方言修煉,禮失而求諸野,當不失為理論實踐相結合的音韻教育模式。
六、結 語
石聲漢先生音韻遺札展現案頭,睹物思人,舊景復萌;謹為小結語,以就教先生,祈臧否本文臆論之得失。其一,先生所謂“小縫”,抑古農核心學術所在,命為“校勘道路”。今謬妄為之訓解:小者,小學也;縫者,小學中音韻學也。可得哂笑頷首否?其二,先生遺札所見凡治音韻之學,必經學識-修煉-致用三階段,修煉中段最吃功夫。修煉門法指示要為四途:熟讀《廣韻》匯通中古音系;巧取《焦易》通押上古韻腳;參用諧聲音旁通訓《說文》;參贊方言調查感知近現代音變。“三段四途”之賅,是否恰意?其三,今當新時代,古農學宜創新發展,學科范疇欲拓展至國學經史子集領域;而以古農書校注為圭臬則固守不移,音韻訓詁兩把小學利器秉持不棄;永葆本校冷門絕學至上水平,將是后學不懈奮進之新夢!
篇末試代為先生發以心語:學也,修也,道在其中矣!
Study on Shi Shenghan’s Reading Notes About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ZHANG Bo,SHI Quanshe
(Northwest Aamp;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and appreciation of famous late Professor Shi Shenghan’s reading notes about phonology,and finds out they are valuable documents of Professor Shi’s self-stud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The “collating path” and “slit in lost body of knowledge” in the notes are consistent with what he talked about,and they are two inevitable ways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e.Professor Shi’s stud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can be concluded as “three stages and four paths”.The three stages mean learning,practicing and applying,of which the practicing is the most effective.The four paths are:(1) thoroughly reading the book of Guangyun to make clear the changes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2) with reference to rhyme of Yilin, imitating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to induce and test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3) studying homophonic side in Shuowen to know how to find out the meaning of a word from its pronunciation;(4) participating in investigation of dialect to inquest the “fossil” of"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nd trace the footprint of its changes in history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old principle of “finding the lost knowledge from the folk”.
Key words:phonology;Guangyun;Chinese phonology in ancient;Shuowen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