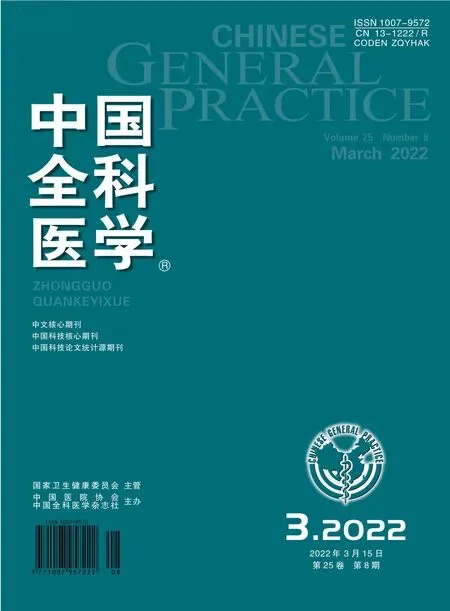極早產兒3 歲內體格指標追趕生長的特征性研究
秦巧稚,趙雪琴
本文價值及局限性:
本文著重研究了極早產兒前3 年的體格生長發育情況,這部分早產兒宮內孕育時間短,各組織器官成熟度低,體格發育及神經系統發育均落后。本研究通過對各時間段體格指標的監測,可以較客觀地評估極早產兒各時間段追趕生長的情況,并根據測量指標進行更好地營養干預。同時,本研究揭示了極早產兒的生長模式,為臨床促進極早產兒追趕生長提供了參考。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將神經系統發育追趕情況納入研究,完善極早產兒的生長發育評估。
隨著醫療技術及營養支持水平的不斷提高,早產兒的出生率及存活率逐漸升高。我國每年出生的早產兒居世界第二[1]。早產兒早期的生長模式不同于正常足月兒,需通過適宜的追趕生長以縮小與同齡足月兒的差距。追趕生長是指早產兒在生長發育過程中去除某些阻礙生長的因素(營養不良或疾病等)后出現的加速生長[2],以恢復到原有的生長軌道上。近年研究表明,低出生體質量兒童早期的快速追趕生長可能會增加成年后代謝性疾病和心血管病的發病風險[3]。目前主張低出生體質量兒童應采取“適度的追趕生長”,這樣既避免了由于早期生長不足增加腦發育和體格發育落后的風險,又減少因過快追趕生長而增加成年后的慢性病風險。然而目前“最適宜”的追趕生長模式仍沒有標準,加強生長監測和合理評估是有效的探索手段。極早產兒胎齡小,各組織器官發育成熟度相對更低,更需要重點關注他們的追趕性生長。目前國內對于早產兒體格指標的長期監測研究相對較少,國外已有對早產兒的遠期隨訪,但對極早產兒的研究仍屬罕見。本研究對我院出生的極早產兒進行3 年生長發育的回顧性研究,探索其追趕生長模式,為極早產兒出生后的隨訪提供參考,降低體格追趕生長失敗率。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7 年08 月至2018 年09 月在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診治并在兒保門診按時體檢的120 例極早產兒(胎齡28~32 周,出生體質量860~1 499 g)及同時間段出生的121 例足月兒作為研究對象,收集其在本院體檢的體格指標資料。早產兒體檢頻率參考《中國兒童體格生長評價建議》[4]:出院后6 月齡內1 次/月,6~12 月齡1 次/2個月,1~3 歲1 次/3 個月。排除標準:有外科手術史、發育異常、遺傳代謝性疾病、體格指標數據不全。本研究經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批號:2021ky300)。
1.2 分組 根據小于胎齡兒(small for gestation age,SGA) 及 適 于 胎 齡 兒(appropriate for gestation age,AGA)的定義[3],參照Fenton 早產兒生長曲線查找各胎齡相應體質量[5],將出生體質量在同胎齡平均體質量的第10 至90 百分位的極早產兒歸為AGA 極早產兒組,出生體質量在第10 百分位以下的極早產兒歸為SGA 極早產兒組。其中AGA 極早產兒組109 例(男60例、女49 例),SGA 極早產兒組11 例(男7 例、女4例),同時間段出生的121 例健康足月適齡兒(男60 例、女51 例)歸為足月兒組。
1.3 方法
1.3.1 資料收集 AGA、SGA 極早產兒組及足月兒組在矯正年齡40 周,矯正年齡3、6、12、24 月齡,矯正年齡36 月齡進行生長發育監測。并由兒保科醫師采用相同測量工具對其體質量、身長、頭圍進行監測,體質量精確至0.01 kg,身長和頭圍精確至0.1 cm。
1.3.2 評價方法 參照2006 年 WHO 7 歲以下兒童生長標準進行Z 評分。Z 評分=(實際測量值-該性別該月齡平均值)/該性別該月齡標準差。正常Z 評分范圍為-2~2。生長速率=(后一年齡Z評分﹣前一年齡Z評分)/兩個年齡點間隔時間(月)。由于兒童生長發育存在地區差異,本研究選擇了同地區的足月兒作為參照。
1.4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23.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Kruskal-Wallis H 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極早產兒120 例,出生胎齡28~32 周,其中SGA 極早產兒組11 例(男7 例、女4 例),出生體質量0.86~1.15 kg,出生身長33.5~41.2 cm;AGA 極早產兒組109 例(男60 例、女49 例),出生體質量0.96~1.59 kg,出生身長36.9~45.3 cm。足月兒組121 例(男60 例、女51 例),出生胎齡37~40 周,出生體質量3.06~3.73 kg,出生身長49.8~51.0 cm。
2.2 三組體格指標Z 評分比較 SGA 極早產兒組的三項體格指標Z 評分在矯正12 月齡內均為負數,12 月齡后均追趕生長至正值;AGA 極早產兒組的體質量、身長Z 評分在矯正6 月齡后追趕生長至正值,頭圍Z 評分在矯正12 月齡后追趕生長至正值;足月兒組體質量、身長、頭圍Z 評分均大于0。SGA、AGA 極早產兒組和足月兒組各項體格指標Z 評分在矯正12 月齡內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三組在矯正24 月齡及36 月齡時各指標Z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三組體格指標Z 評分比較〔M(P25,P75)〕Table 1 Comparison of Z-scores of body weight,body length and head circumferenceamong three groups
2.3 三組體格指標Z 評分的追趕趨勢 三組體格指標Z評分均呈一定的追趕趨勢,但出現追趕高峰的時間點及特征均不同。
2.3.1 體質量 三組體質量Z 評分在矯正6 月齡內追趕明顯,AGA 極早產兒組及足月兒組的Z 評分追趕峰值出現在矯正3 月齡前,SGA 極早產兒組追趕高峰在矯正3~6 月齡時;矯正6 月齡后各組Z 評分仍在增長但趨勢逐漸變緩,矯正12 月齡后趨于平緩,見圖1。

圖1 三組各月齡體質量Z 評分追趕趨勢Figure 1 The trend of catch-up growth for body weight z-score among three groups at different months of corrected age
2.3.2 身長 三組身長Z 評分早期均追趕明顯但特點不同,AGA 極早產兒組和足月兒組以矯正6 月齡內增長趨勢明顯,AGA 極早產兒組矯正6~12 月齡之間追趕趨勢較前期降低,矯正12 月齡后追趕趨勢趨向于足月兒;SGA 極早產兒組矯正3 月齡之前追趕較慢,矯正3~6 月齡之間出現追趕高峰,矯正12~24 月齡SGA 極早產兒組仍有追趕趨勢;足月兒組Z評分整體平穩增長,見圖2。2.3.3 頭圍 極早產兒兩組頭圍Z 評分表現為追趕性生長,AGA 極早產兒組在矯正3 月齡內追趕明顯,后持續增長至矯正12 月齡;SGA 極早產兒組在矯正3 月齡后追趕趨勢明顯,矯正12 月齡后逐漸變緩,矯正12 月齡時SGA 極早產兒組及AGA 極早產兒組頭圍Z 評分均低于同齡足月兒組,見圖3。

圖2 三組各月齡身長Z 評分追趕趨勢Figure 2 The trend of catch-up growth for body length z-score among three groups at different months of corrected age

圖3 三組各月齡頭圍Z 評分追趕趨勢Figure 3 The trend of catch-up growth for head circumference z-score among three groups at different months of corrected age
2.4 三組體格生長速率的變化 AGA 極早產兒組各指標生長速率最快出現在矯正0~6 月齡期間,SGA 極早產兒組各指標生長高峰見于矯正3~6 月齡,矯正6~12 月齡生長也較為迅速。三組在矯正40 周~12 月齡期間的體質量生長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三組的身長及頭圍生長速率在矯正40 周~24 月齡期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三組在矯正36 月齡時各指標生長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三組體格生長速率比較﹝M(P25,P75)﹞Table 2 Comparison of growth rates assessed by body weight,body lengthand head circumference among three groups
3 討論
早產兒由于宮內發育時間較短,各項體格發育指標明顯落后于足月兒,且追趕速度不均衡。追趕生長是2歲前幼兒的正常現象,出生體質量較低的嬰兒,為了接近遺傳所確定的生長軌道,就要采取追趕生長以回歸到正常的范圍之內,其中AGA 早產兒的追趕生長好于SGA 早產兒[3]。研究表明,生長是預先設定在某個階段或時期發生的,早產兒在出院后至矯正年齡2~3 月齡內存在一個生長發育的“機會窗”,如果錯過關鍵時期,可能無法彌補,即使短期的生長受限也可能影響早產兒的身體健康,甚至影響其大腦的生長和發育[6-7]。掌握這些關鍵期,可以幫助早產兒更好地進行生長追趕。極早產兒的生長速率明顯慢于足月兒,SGA 極早產兒更是落后,需要高度重視極早產兒的早期追趕生長。建立科學的早產兒管理制度、定期監測早產兒體格生長指標、為每個早產兒量身制訂合適的追趕方案、科學合理喂養、實施有效干預措施等,對促進早產兒體格指標達到適宜的追趕生長具有極高的臨床意義及社會價值。
本研究選擇生長發育指標中的體質量、頭圍、身長進行為期3 年的動態監測發現,極早產兒體格生長在矯正12 月齡內的各項體格指標Z 評分追趕趨勢顯著,Z評分從負值逐漸追趕為正值。各組間體格指標生長速率高峰期不同,AGA 極早產兒組及足月兒組速度最快在矯正3 月齡左右,SGA 極早產兒組則相對落后,與相關研究[2]結果一致。這可能與早產兒輔食添加時間及方式[8]、容易出現喂養不耐受、蛋白過敏發生率高等有關。各體格指標之間也存在速度差異:極早產兒組體質量的追趕生長主要在矯正6 月齡內,6 月齡后各組仍在增長但趨勢逐漸變緩;AGA 極早產兒組身長及頭圍在矯正6 月齡內增長趨勢明顯,后逐漸變緩;SGA 極早產兒組身長及頭圍追趕峰值出現在矯正3~6 月齡之間,晚于AGA 極早產兒組。SGA 極早產兒組各體格指標生長速度早期落后明顯且追趕速度不均衡,與國內其他研究結果一致[9]。
有研究已經證明極低體質量早產兒在矯正12 月齡時生長追趕失敗率為50%[10-12]。本研究中極早產兒體質量、身長和頭圍均有明顯的追趕性增長,無追趕失敗案例。KNOPS 等[13]發現AGA 極早產在10 歲時沒有表現出發育不良;然而,許多SGA 早產兒表現出持續發育不良。NAGASAKA 等[14]發現,3 歲時早產兒身材矮小的發生率是足月兒的2 倍,而SGA 早產兒身材矮小的發生率是足月兒的4.5 倍。ZHAO 等[15]發現SGA 與低體質量、身材矮小息息相關。SGA 早產兒維持正常的體格生長需要更好的營養支持,容易出現喂養不耐受、蛋白質過敏、宮外生長遲緩等并發癥[16],這些均會對其生長追趕產生長遠影響,導致其體格甚至神經運動發育落后于同齡兒。
本研究中極早產兒生長遲緩的發生率低于發展中國家[10-12],在矯正12 月齡時三項體格指標與WHO 提供的12 月齡同性別兒童的平均數差值小于一個標準差,這受益于營養支持水平的提高和常規隨訪的改善。有研究者認為早產兒的追趕性生長通過細致的監測和積極干預會明顯加快[17],消除不利因素,早產兒就會有追趕上普通兒童的潛力。
對早產兒的長期隨訪表明,出生后體質量快速增長可能會增加未來罹患代謝性疾病的風險,尤其在SGA早產兒中較為明顯[18-19]。早產兒需要攝入更多蛋白質,其生長速度才能與相同孕周的正常胎兒生長速度更接近,長期隨訪表明,出生后體質量增加較快會增加后期心血管疾病的風險[20-21]。相反,一項縱向研究顯示嬰兒早期體質量的快速增長沒有影響青春期的代謝狀態,但兒童時期體質量迅速上漲會導致青春期代謝異常[22]。幼兒期和青春期的生活方式比早期生長追趕和營養干預更容易引起代謝性疾病[23]。根據目前的證據,早產兒生長緩慢和生長過速均會對其長期健康產生影響。因此合適的生長追趕方式對早產兒非常重要,但是加強喂養并不等于過度喂養,高質量的喂養模式需要定期隨訪、適當干預、充分的醫患溝通和合理的家庭喂養,以強化早產兒神經發育、降低肥胖率及營養不良發生率。對于早產兒體格指標的隨訪可以延長至青春期,以明確追趕性生長對代謝的遠期影響。
綜上所述,早產兒的追趕生長一般出現在矯正24月齡以前,極早產兒早期體格追趕生長與足月兒有明顯差距,組內不同體格指標出現追趕高峰的時間點不同。SGA 極早產兒組各體格指標生長速度早期均落后于AGA 極早產兒組且追趕速度不均衡。定期的隨訪及干預可以減少生長追趕失敗率。
作者貢獻:趙雪琴進行研究設計與評估、資料收集整理、修改論文并對文章負責;秦巧稚進行研究實施、資料收集、整理、撰寫論文。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