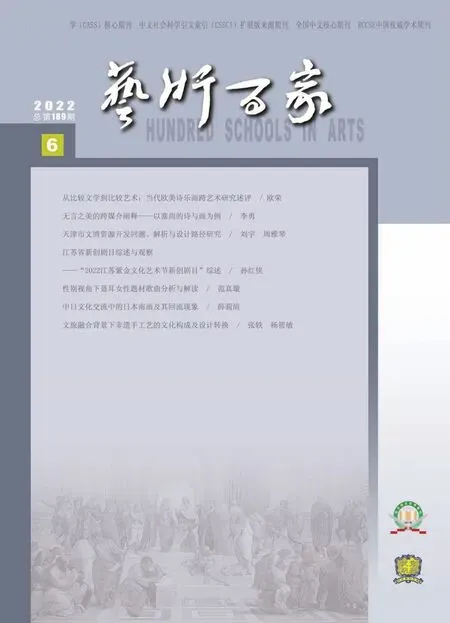論展覽標簽“去中心化”*
——以觀念藝術策展實踐為語境
顧也天
(南京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當代藝術最有趣的話語之一總是這樣:“你認為有必要往墻上貼解釋性的標簽嗎?還是僅僅掛上作品而讓觀眾自己去領會?”我始終認為,如果藝術家沒有激烈反對,有時你也可以說服他們,附上發人深思的解釋性文本確實對觀眾幫助很大,不管是藝術家的文字還是策展人的文字。就算你并不同意標簽上的文字,也能給參觀者某種可供批判的東西。
——安妮·德·哈農庫德(Ann d’Harnoncourt)
2006年,時任費城美術館館長安妮·德·哈農庫德接受瑞士策展人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采訪時,談及解釋性標簽(interpretivelabel)的魅力,有過如上一段論述[1]182。在這里,她十分巧妙地把標簽與展覽中各個權力者的話語權相關聯,并肯定了標簽的作用。本文即以此展開。
藝術展覽在迎來指數級的數量增長后,目前已陷入一種困境:觀眾面對琳瑯滿目的展品以及展覽標簽(以下簡稱“展簽”)感到不明就里,甚至有“挫折感”,通過解釋性文字想要傳達給觀眾的知識、理念并沒有真正被觀眾所接受。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展簽內容不夠科學,二是其呈現方式過于傳統、單一,導致難以引人入勝。
目前展簽領域的語言學和傳播學有許多成熟的案例和豐富的研究。比如,美國的亞德里安·喬治(Adrian George) 所著《策展人工作指南(The Curator’sHandbook)》,為展簽制定了詳細標準;美國博物館學家貝弗利·賽瑞爾(Beverly Serrell)在《展覽標簽:一種解釋性的方法(ExhibitLabels: AnInterpretiveApproach)》一書中,對展簽寫作及分析進行了詳細闡述,此書已兩次修訂(1996)(2015);美國的弗里曼·蒂爾頓(Freeman Tilden)在他的著作《解釋我們的遺產(InterpretingourHeritage)》中,也對信息傳達系統做出了范例式的解答,他的解答甚至已經成為公認的標準。此外,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每年評選“展覽標簽寫作卓越獎(Excellence in Exhibition Label Writing Competition)”,對展簽的寫作和分類建立了標準;我國學者周婧景還以此獎在2016—2018年的評選為例,撰文著重研究了展覽中說明(解釋性)文字的空間認知心理,提出“促使注意指向實際對象”的做法[2]53-62。以上這些優秀展簽或規范盡管未必是先鋒式的,但的確代表了傳統展簽寫作的最高水準。
當代藝術展覽,尤其是實驗性或學術性的展覽,本身對觀眾的知識儲備和感知習慣有一定要求。能深入人心的藝術傳播,應當建立在能讓大眾接受吸收的話語體系基礎之上。所以,在承認展簽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如何通過展簽促成展品與觀眾的對話?又如何更好地呈現能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展簽內容? 這些都是本文將要努力解決的問題。
有必要指出,在討論文字與視覺藝術的關系時,前提是藝術文本的轉向,其中包含了哲學的語言傳播轉向和藝術的流派批判轉向。比如,立體主義、未來主義和抽象主義的發展為文本概念奠定了堅實基礎——喬治·布拉克(GeorgesBraque),他的某些立體主義畫作因將文本融入作品中而聞名(如圖1);當雷內·馬格麗特(René Magritte)在他的超現實主義畫作上寫下著名的“Ceci n’est pas une pipe(這不是一支煙斗)”(圖2)時,他把藝術家創作時的解釋性文本移到了理解作品的中心位置。因此,筆者認為,圖像與語言之間關系的建立是20世紀視覺藝術的重大發展。有此筑基,我們就可以為展望展簽的未來而積極尋找突破性的新事物。

圖1 喬治·布拉克《向J.S.巴赫致敬》,1911—1912,布面油畫,現藏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左);

圖2 雷內·瑪格麗特《圖像的背叛》,1928—1929,現藏于洛杉磯藝術博物館,www.ReneMagritte.org(右)
一、展簽的“去中心化”
本文選擇從20世紀60年代末興起的觀念藝術入手來討論展簽,是因為圍繞展覽實踐的語言(媒介)發生了更廣泛的轉變。藝術家們常以概念取代實物,使藝術得以擺脫傳統形態(即所謂“去物質化”),如將裝置和雕塑簡單地稱為“作品”,而展覽更常被稱為“項目”[3]。舉辦機構、策展人、藝術家們也越來越多地將制作工作置于前臺,從而將“制作”延伸為“意義”的一部分。但這仍然使策展人的活動與藝術家的創作密切相關。北美作家、策展人露西·R·利帕德(Lucy R.Lippard)作為觀念藝術的旗幟性人物,曾明確提出:
語言的材料和觀念的可能性與不斷發展的策展方法密不可分。通過鼓勵對一些標準的博物館學信息——藝術家傳記、策展聲明、展覽清單、展覽標簽——進行重組,并允許觀眾/讀者變為內容參與者,顛覆了作者身份的概念,制定了一種參與式的觀眾觀,策展人、藝術家和觀眾互換角色,共同參與意義的建構。[4]
在20世紀70年代的觀念藝術浪潮中,文化激進主義概括了該運動的發展。它激發了行動主義對于策展實踐的驅動力,反之倒逼其積極推進當代藝術機構和策展人的發展[3]。這類混合實踐創造了一個跨學科的、有價值,卻又質疑的關鍵空間。多數觀念藝術家制作了用批評解釋的作品,同時他們又質疑批評的功能,對藝術領域內的語言概念及寫作行為進行了新的闡釋。但即使有著藝術的顛覆,他們還是不可思議地避免將自己的感官和見解加到觀眾身上,完成了驚人的語言轉向。
本文將觀念藝術帶入展覽中的微觀領域,是因為圍繞展簽實踐的語言也發生了化學反應般的轉變。展簽的實質是傳遞信息。觀眾可以根據接收到的信息賦予其特定的指示方式,來構建概念式作品的實質。實際上,這就是將展簽分解為一種傳播工具的模型,連同展品塑造為一個整體的宣傳語境。此外,展簽因為縮小了觀看和生產之間的距離,所以削弱了機構、策展人或藝術家其中一方或多方權力主體的作用,并使得傳統權力在展覽世界中的行使發生了動搖。這就導致了反體制傾向被注入了美術館和畫廊的微觀領域。筆者稱之為展簽“去中心化”的過程。
“去中心化”的概念有必要加以明確。長久以來,文字展簽的制作及接受嚴格遵循英國學者蓋農·卡瓦納夫(Gaynor Kavanagh)提出的傳統信息“三單元(three-unit)”交流模型[5]41,即發送者—消息—接受者(sender-message-receiver)的步驟。在傳統美術館模式下,文字系統表現為機構—展簽—觀眾的模型。這種優先級層級在意識的層面就誘導了觀眾——圖片優先于文字。在這種等級制度(非越級)的傳遞模式下,藝術家和批評家、策展人的角色是明顯獨立的,展覽中的展簽和藝術品的角色也是明顯獨立的。但在觀念藝術興起后,越來越多標新立異的展覽顛覆了人們對傳統美術館模式的認知,先進的策展方法催生了嶄新的展覽和展簽系統。本文所稱“去中心化”,并非是指去除展簽在美術館或畫廊被關注的中心位置這個“中心”,而指的是展簽中被闡釋內容的來源和制作從傳統權力主體——機構轉移至策展人、藝術家甚至是觀眾,由此,展簽概念中的話語權從機構層面解放出來;同時,對于展覽中看似必要存在的物件(如作品和展簽)的功能進行人為主體意志的賦予,探究傳播媒介之于其的地位和作用。下放但不分散的權力在封閉的空間以及開闊的場地中被相關的主體顛覆性地運用,創造出一批新型、有效、有趣的展覽,不僅討論了展簽如何、何時以及為什么會“成為形式”,更解構和探索了展簽位置的問題。
但是,如果在觀念藝術語境下討論展簽的去中心化問題,我們需要提出前提。首先,藝術家和策展人的身份是相對模糊的,展簽和作品的界限也是難以界定的。2007年第12 屆文獻展(Documenta 12)主張“展覽作為一種媒介”[6],那么我們真的只需要考慮宏觀的展覽本身嗎? 傳統藝術理論一直囿于“自主”“作者身份”“展品”“藝術作品”甚至“人工制品”等概念的理解。但其實如果從觀念藝術出發,就會發現這些困擾可能太過局限于“批判媒介”的框架之中。美國策展人亞利桑大·亞貝洛(Alexander Alberro)認為,一旦藝術語言被認為“在‘觀念藝術’的框架內”,作品和文本之間的區別就變得模糊了。[7]19同樣,由于1970年代的策展人經常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傳統的展覽制作形式,激進地使用各式各樣的策展方法,導致了其傳統的“聯絡員”身份開始瓦解。也正因為如此,傳統展品的界限從“藝術作品”向外擴展,轉變或模糊為展覽中其他看似已經定義的物件。對觀念藝術中“什么是展覽的必需品”問題的討論,事實上要回到其出發點——“傳達”功能,即:展覽需要什么?展覽需要作品嗎? 作品又需要什么? 正是由于話語權的主體被機構大膽分散,展簽的語言、工具和類型獲得了極大的想象空間,從而解放了展簽作為“媒介”在其中的功能,才能夠讓我們尋找到單一主體的多種功能邊界。
另外,在“信息”展覽中,觀眾對于藝術作品和展簽的貢獻也是不可或缺的。不過,難道觀眾也是展簽去中心化的內容之一嗎? 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用觀念藝術的語境來研究展簽,是為了在更迭的展覽世代中尋找展簽位置的平衡點。無論是上述“展覽是媒介”,還是語言和傳播總需要的發送者和接受者,權力的交接最終落在了觀眾的意志中。去中心化的過程要求任何動態的展覽都要做到發送和接受的平衡,也盡量期待在一次展覽中權力能被全部體現。同樣,以這樣的視角來審視沒有展簽的《施樂書》(見下文)——以極端方式重新詮釋了“關注作品本身”的主題,也意味著允許觀眾徹底挑戰機構層面的話語權。它好像正面呼應了十年后(1980年)英國作家約翰·伯格在其《觀看之道》(WaysofSeeing)中所談及的語言的展簽“到底是為觀眾提供了解釋還是限制了觀眾的批判性思路”[8]的問題,并予以先行實驗。
二、展簽在觀念藝術中的策展實踐
利帕德的“數字展覽系列(NumberShows)”,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綜合性案例。這些展覽于1969年至1973年在美國各地及英國倫敦巡回展出,每一場展覽都選取一個復雜而具體的數字作為名稱:“557,087”(西雅圖,1969)、“955,000”(溫哥華,1970)、“2,972,453”(布宜諾斯艾利斯,1970)以及“c.7.500”(瓦倫西亞,1973)。展覽其實是以首次舉辦城市的人口數量命名的,且幾乎不包括繪畫,而是以最廣泛的、最概念化的、基于現場語境的裝置,以及完全基于印刷的文字和圖片作為展品的。利帕德重點使用了一種索引卡片(index card)隨機分發和閱讀(如圖3及圖4),內容涵蓋了展覽中的一切必要和非必要的要素,例如藝術家及展品清單、作品信息、展覽批評、詩歌,以此集納為一個目錄(catalogue)。例如“c.7.500”中,雙面的卡片由26 名藝術家在巡回展覽中完成[4]220;“557,087”以及“955,000”的單面卡片,則是由利帕德向參加的藝術家發出征集邀請,并附上了其論文和附屬信息[4]158。由此可見,卡片扮演了展簽的角色。作為展簽的替代品,它不僅傳遞了傳統展簽所要表達的信息,更在此基礎上大膽拓展出了“策展人作為藝術家”和“藝術家作為展簽撰寫者”的新功能。通過調查新興一代藝術家并在展覽中展出,引出了她構思已久的反傳統傾向。由于讀者或觀眾可以扔掉他們不喜歡的卡片,利帕德認為,“展覽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公眾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看法”,“提供的體驗越開放,或越模糊,觀眾就越被迫依賴于自己的感知”[9]。也就是說,作品、藝術家和展簽都無法控制觀眾看待作品的方式,這樣不同的觀眾就會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件展簽。既然藝術物品(art object)已經打破了美學邊界,與之伴生的展簽似乎也能如法炮制。加之她的藝術作品“去物質化(dematerializetion)”的觀點[3],使得無論是物理上還是概念中的展品都能夠完成自我價值的建構,實現解放性的“說”和“記錄”。所以在觀念藝術的語境下,展簽概念的擴張更加符合由策展人率先指導發起的、藝術家制作的制作模式。美國作家保羅·奧尼爾(Paul O’Neill)在《策展的文化和策展一種(或多種)文化》(TheCultureofCuratingandtheCuratingofCulture(s))中說:“這種卡片其實是一種缺席的來自藝術家的指引。”[10]14即使展廳中沒有物理意義上的實際作品,單單是卡片目錄就可以完成所有策展人的概念和作品的傳遞,觀眾也可以將卡片作為紐帶來關聯展覽和不在場的藝術家。“開放的模糊性”代表了利帕德的策展工作,同時也有她倡導的策展方法的隨意性(或武斷性)——包括她主導卡片目錄;以及她的開創性出版物《六年:1966 至1972年藝術的去物質化》(圖5)①,這是一種書籍形式的策展工作,書中任何一段文字都可以視作一個作品與解釋型展簽的融合。由此看來,同為美國觀念藝術家的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的觀點“藝術品的創作過程從根本上說是非理性的”[7],同樣適用于展簽中:策展人主導的展簽創作,要求制作者做出除作品意義和內容之外更多的選擇。可見,此類展簽明顯地擴大了策展人的聲音。

圖3 一張“955,000”中的引索卡片,1970,The Estate of Barry Flanagan(左);

圖4 一張“c.7,500”中的引索卡片,1973,Lucy Lippard(右)

圖5 《六年:1966 至1972年藝術的去物質化》的封面,也作為展覽“六年”的海報,200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右為該書中文版封面)
在挑戰機構權威、表達藝術家權力方面,美國非傳統的畫廊經營者、藝術品經銷商、藝術家的倡導者和多產的概念項目發起者賽斯·希格勞勃(Seth Siegelaub) 的“越級(trespassing)” 做法更加激進。“557,087”就是由他設計了“包裝、印刷和一般業務”[4]。他主張即興表演,即宣傳、文本資料和在場性是藝術的“主要信息”,而不僅僅是事后的想法。例如,他于1968年組織和出版了《施樂書》(TheXerox Book),既展示了與自己的策展觀念和實踐相關的7位藝術家的作品,又利用了非常規的展覽方式——書本形式。他以影印的書籍作為平面式和壓縮式的畫廊,要求每位藝術家創作25 頁作品(如圖6及圖7)。希格勞勃印刷藝術,卻沒有印刷展簽。《施樂書》掙脫舉辦場地的束縛,沒有設置展簽的原因首先歸結為“去物質化”,即:無展簽的展覽并不是摒棄展簽,而是自由地解放展簽的功能,讓傳統的印刷媒介融入打印的觀念藝術作品中。這樣,毫無疑問最大化地散布了藝術家創作時的意志,傳遞了藝術家想要發出的聲音。“此類新實踐在20世紀60年代的興起和《施樂書》復制版的傳播,強調了藝術家能夠完全控制其作品的能力,而不是依賴畫廊或者專業出版商。”[10]22藝術融合(artfusion)在觀念藝術中既表達了創作現場與展覽現場的一致性,又傳達了展簽功能的附加性,即希格勞勃所倡導的表演式的藝術信息。與此同時,與“數字展覽”相似的是,展簽中也有成本太高(影印書籍頁數過多)的局限性,導致無法進行大量實驗,所以《施樂書》因為成本昂貴而復制本極少。但作為商業性質的觀念藝術探索,它是展簽的去物質化方面的先鋒性實驗。希格勞勃此舉,激勵了更多的藝術家再次認真思考如何將大規模復制、收藏和建檔作為重要的藝術媒介[11]。

圖6 《施樂書》掃描版中羅伯特·貝里(RobertBarry)的第一、第二頁,2012,Sigelaub/Wendler(左);

圖7 《施樂書》掃描版中索爾·勒維特作品的其中四頁,2012,Sigelaub/Wendler(右)
筆者還注意到了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MoMA)]的一個展覽,叫“信息(Information)”。作為觀念藝術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國際調查式的展覽,它突出了那些推動政治、基于過程或需要觀眾參與的前沿藝術家②。在這個展覽中,雖然注明了策展人是卡尼斯頓·麥克希恩(Kynaston McShine),但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參與是沒有經過策展人干預的③,保留了最大限度的開放性[12]。這個展覽中的部分藝術品和展簽也相互“交換”了信息、模糊了邊界。有一些文字類作品,如漢斯·哈克(Hans Haake)的《MoMA 參觀者選票》(PollofMoMAvisitors)(圖8),給參觀的人以投票的權利,并把選票張貼出來。就解釋性而言,不同于獨立設置式展簽的“去神秘化的自我呈現”,選票作品與展簽同時具有“呈現和制造神秘”的意義,在沒有策展限制的前提下使用了臨時展簽,解放展簽傳達權的同時限制了解釋功能,集藝術家闡釋和觀眾想象于一身,從而成為現場藝術的元素。解釋性文字的增加是以犧牲藝術品的“審美自主權”為代價的。這樣的作品刻意規避了傳統的博物館分類,挑戰了機構的權威。作為類似觀念藝術的里程碑,它確立了現場在展覽中的重要性,也明確了民主(觀眾、藝術家、策展人或多方主體決定)概念式的展簽在展覽中使用的可能性。所以自21世紀初以來,博物館一直在收集表演藝術作品,因為藝術品和展簽都被認為是具有生命力而非靜止的,并最終改變了博物館收集和展示藝術品的方式。

圖8 漢斯·哈克 《MoMA 參觀者選票》中的四張選票,1970,現藏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圖9 漢斯·哈克《提交作品目錄和提案》,1966,現藏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三、展簽的存在形式
展簽本身可以成為感知對象嗎? 為什么要把展簽放在墻上? 為什么要把展簽放在目錄上? 制作一個沒有任何展簽的空間和將一個展簽貼在白墻上有什么區別? ……這些在傳統觀念里成為問題的問題,今天已經不再是問題。我們將展簽的物理存在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制作展簽是一種意志行為。展簽的去中心化過程始終圍繞著展覽中最重要的話語權主體進行權力的分散和分配,以觀眾為目的的結構重新定向催生了展簽在展覽中新的位置嬗變。
利帕德的去物質化思想給去中心化過程帶來了展簽擺放思路上的轉變,20世紀60年代末出現展簽的藝術形式危機也許肇因于此。1969年,英國的“藝術& 語言(Art & Language)”團體出版了第一期《藝術-語言》(Art-Language),引言即提出:“在觀念藝術的框架內,藝術的創造和理論的創造現在被視為不可區分的,因此被納入一個個獨立的實踐中。”[13]1-10展簽的創新和呈現方式的轉變也不例外。
“文本的加入”和“文本的取消”代表了當代藝術實踐中一個重大的概念性突破。前者指的是在圖像中加入文字,或是以文字取代圖像;后者則指展覽中除了作品之外沒有任何解釋性的文字,包括展簽。觀念藝術興起所引發的對于文本和展簽的思考是更深層、更重要的,而不僅僅是視覺藝術和圖像美學的一種轉移。必須承認,在藝術作品的表現方面,沒有一種形式本質上優于另一種形式,藝術家可以使用任何形式,從文字(書面或口頭)的表達到實體的藝術品呈現,都是一樣的。那些文字也不例外,它們是從藝術的觀念出發的,那么它們是藝術而不是文學,其中的數字也不是數學,只要它們符合藝術慣例。從一種以語言和寫作為媒介的批判性實踐,轉變為一種通過藝術家和藝術作品來吸引觀眾的實踐,從文本作為媒介到展覽制作作為一種話語的、創造性的實踐,這是一個創新策展模式的過程,且這種模式是方法論式的、爭論性的、極富主觀色彩的。
從已經有實質性轉變的展簽呈現模式來看,除了以紙質文字伴隨在作品旁的傳統展簽,目前還有以下幾種:1.展簽與視覺畫面同時出現在作品中;2.展簽替代視覺畫面,僅以文字出現在作品中;3.不出現展簽,僅以作品占據整個展覽空間。雖然其中部分可能與文本藝術混淆,但從展簽的角度來說,這種概念式的展簽形式所傳達的意義不同于文本藝術。首先,利帕德提出的“去物質化”貫穿了整個觀念藝術活動。但去物質化不僅僅表現在藝術作品中,更導致了其綜合結果表現在展覽中一切與藝術作品相關的元素中。例如展覽場地從“白立方(WhiteCube)”變為室外空間,甚至不用場地,而是轉移到紙張上(如《六年》《施樂書》)。回到展簽中,無論是作品還是文本,都是圖像和語言的綜合體現,是狹義上的“媒介”,是廣義上的“策展方法”中的一環,最終的結果是展覽意志的解放促成了展覽形式的解放。希格勞勃的印刷展覽更是分發和宣傳了人們閱讀紙張的“當下時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現場藝術的一部分。無形展簽的表現形式越是廣泛與包容,就越能與當時發生的所有其他所謂的革命性(如展覽場地方面)保持一致。這就是將展簽視為策展批評的物理延伸。所以“多才多藝”的展簽遇見不再滿足于繪畫形式的藝術時——行為、表演、裝置、視頻、聲音以及它們的拓展,這些創新性的藝術形式作為展覽的第一要素,沖擊了傳統形式的展簽,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老生常談的“不設置展簽”。顯然,美術館和畫廊不期望展簽作為“潛意識意義”[14]出現在觀眾眼中;但它從有形上升到無形,任何一個展覽中的元素都可以探尋它戲劇性的精神意義。
人們總是自發地以興趣為主導,聚集在展覽中自己所喜歡的作品前,與作者或是其他觀賞的人溝通交流。隨著認識論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觀點都承認有關事物的描述和分類都是易變的,嚴格的分類甚至會被認為是在削減意義[15]25-39。同時,移動互聯網技術以及表演和現場藝術的快速發展又改變了觀眾欣賞藝術的方式,去中心化式的網絡社交平臺、無展簽化的表演等都使觀眾能夠自主對信息進行搜索和分類,進而添加屬于自己的展簽。因此,信息的分類、解讀方式越多元化,大眾處理信息就越更加自由。對于意義多元性的討論、人們接受藝術習慣的改變,都推動了展簽表現形式的自由變動。有一些美術館和畫廊已經有所行動,嘗試進行展簽的非線性的、碎片化的內容表述,以拓展觀眾的意義解讀思路——例如VR 和元宇宙展廳。與此同時,在去中心化的展簽表現形式方面,也有可能造成這樣的矛盾局面:穩定的展簽秩序可能會固化展覽和社會的立場;而去物質化、去語言化的呈現方式,則有可能會讓展覽空間喪失基本的邏輯。展簽應當帶領觀眾探索藝術作品中可能令人興奮和激動的內容,從中收獲審美上或意識上的進步,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困惑;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是,無論是哪種展簽,都不能剝奪觀眾自己觀察作品的機會,通過展簽,策展人和策展機構要能夠鼓勵或吸引觀眾自己去觀看、去理解作品,以防止展簽成為美國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學者喬治·威納(George Weiner) 口中的“名副其實的密碼學杰作”[16]。
總之,去中心化過程催生了混合媒介的產生:權力主體的話語權不是絕對分割的,展簽的民主化也應納入話語權的考慮——展簽依賴的存在性在機構、檔案和藝術品以及策展人之間的界限波動。
四、余論
本文沒有界定展覽標簽(exhibitionlabel)和展品標簽(exhibitlabel)。廣義上來說,前者系統地囊括了展覽中所有的文字,而后者是為傳遞展品信息而設置的文字。本文中的“展簽”偏向于前者,是因為在去中心化過程中,展簽的形式發生了去物質化的變質,而構成要素上發生了去語言化的傾向——這些革命性的改變是從觀念藝術中的藝術作品的延伸出發的。展覽作為更加綜合的活動,要說起“更廣泛的狀態”的活力,還得是展覽中無數個微觀元素的積累,復興(reinvigorate)展簽多樣化、不拘一格的形式。
那么問題來了,去物質化、去語言化作為去中心化的部分展現,沒有實體存在的展簽可以被傳播和收藏嗎? 這就好像當代策展界所面臨的現代藝術研究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ICA)]兼泰特美術館策展人露西·貝雷(Lucy Bayley)在2019年曾發出的疑問:如何實踐性地傳播博物館中的表演(performance)和現場藝術(live art)信息?[17]這些問題都將為后續研究和理解展簽在機構、藝術家和策展人的話語權方面提供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只有對展簽賦權的問題有了更深刻的把握,才能充分理解展簽在展覽中處于何種地位。隨著一些美術館和畫廊摒棄白立方(White Cube)的概念——如梵高美術館在2021年8月7日的社交媒體賬號上就明確表達了反對白立方的觀點(圖10),他們把墻面刷成各種與作品主題相對應的顏色,以便更好地展示作品。即使是觀念藝術中的概念與模式,也漸漸顯得不合時宜,越來越多更加新式的展簽被人們接受和使用。展簽不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視覺藝術的輔助品,而是與聲音、口頭或書面文字、裝置、視頻等統一為一個整體,是給觀眾帶來全方位藝術體驗的實驗部分,有時甚至成為展品的重要組成。

圖10 梵高美術館在社交媒體上的一則分享(2020年2月7日),Van Gogh Museum
當代美術館和畫廊應當將展簽的去中心化的過程融入其形式和構成要素中,也應當適當地讓展簽的制作和接受變得越來越民主化。就像露西·利帕德的目錄,用卡片實現了對作品與展簽之間、藝術家與策展人之間的結構探索,以及對真實性和原創性的批判。展簽的編撰、設計、書寫或打印、放置和信息傳達,是符合這種藝術模式的。這種模式,使得展簽獲得了與圖像相同重要的定位。新展簽實踐處于當代藝術思想、語言理論和傳播學的交匯點,所以應該特別關注文本與圖像、語言與主觀性之間的復雜聯系,因為這關系到上述展簽角色的重新定位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策展理論不能推翻展覽的實際藝術體驗,策展人也不能過分陷入文本驅動(catalogue-driven)下的語境,以防止在展覽中文本絕對優先于其他藝術體驗,因為展簽不能保證解釋藝術的全能性(omnipotence)。
① 《六年:1966 至1972年藝術的去物質化》為觀念藝術領域中最為重要的著作,利帕德還在書中表明了她的女權主義傾向。《六年:1966 至1972年藝術的去物質化》僅是該書的簡稱,其全部標題為《六年:1966 至1972年藝術的去物質化:關于若干美學范疇的交叉信息參考書:由加入文本片段、藝術作品、文件資料、訪談和研討會的參考文獻目錄組成,按時間排序,聚焦所謂的觀念、信息和想法藝術,涉及當時美洲、歐洲、英國澳洲和亞洲等地的諸如極簡、反形式、系統、地景和過程藝術之類尚未明確指定的領域(略帶政治色彩)》。(〔美〕露西·利帕德著,繆子衿等譯.六年[M].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8.)
② “政治”在西方藝術語境下的含義與中文不同,指的是個人或集體意志與想法的某種導向性。米爾佐夫在其《視覺藝術導論》中指出:政治是一種意識,即認識到文化是人們界定自身身份的場所,而且它按照個人和團體表述其身份的需要而變化。(〔美〕尼古拉斯·米爾佐夫著,倪偉譯,視覺文化導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③ 如圖9,其中一位藝術家代替策展人提交了作品目錄以及展覽提案(事實上每位藝術家都提交了),提案的格式也非常“觀念藝術”。2020年,在展覽50 周年之際,MoMA 發布了提案合集目錄以紀念這場里程碑意義的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