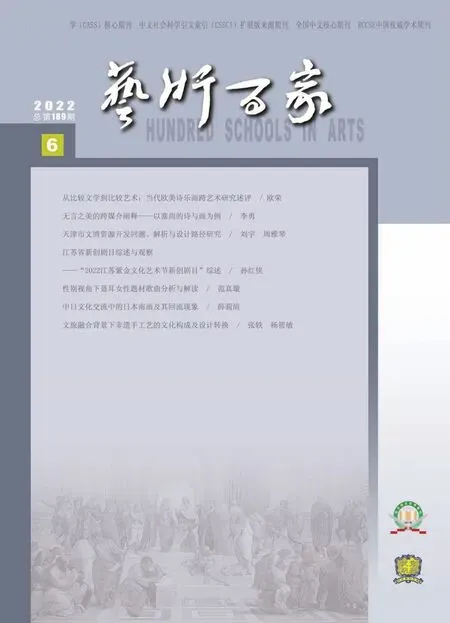創新設計視域中的“編織”異構*
徐旻培,李嘉樹
(南京藝術學院 設計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著眼當下,“創新設計”作為設計學的新興專業進入了大眾視野。與建筑、視傳、產品這些限制設計對象的專業不同,創新設計已經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方法和固定的產品。創新設計具有三個核心特征——交叉性、新視角、流動性,它甚至突破了地域、文化、時間、空間、虛實的限制,并且創作出前所未有的產品與系統。目前,基于不同學科的創新方法有很多,不論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能找到創新的切入點。
“編”與“織”均為形聲字,皆從“糸”。“編”是將條狀物交叉組織起來,引申為編排;也指穿聯竹簡的繩子,引申為書籍。“織”的本義則是布帛,或紡織布帛的活動,后者可引申為“構成”。編織是人類最古老的手工藝之一。《周易·系辭下》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1]86意指古人借鑒了卦象中的離卦①,用手將繩子編結成羅網,用來畋獵捕魚。時至今日,一方面,從事編織相關行業的人員對傳統材料與技藝的運用已經駕輕就熟,另一方面,伴隨著工業4.0 時代的到來,“編織”的社會性與實驗性也日漸得到強化,其語意在不斷變化與彌散。近些年,從事相關研究的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設計師也以更加開放、包容、互動、交叉的方式開展著自己的工作。在此背景下,“編織”通過創新設計的催化,原本一些非典型性特征被高頻利用,并很快進入了大眾視野。由此可見,“編織”一詞包含產品物件、行業技藝、構建思維、組織行為等多重含義,而“編織”也因此與交叉、跨越、包裹、縫合、紐合、拼接、纏繞等詞語關聯起來。
斯賓塞·約翰遜(Spencer Johnson)曾說,“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本身”[2]77,這在創新設計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今“編織”的內涵早已離人們的固有認知相去甚遠。它到底是一種傳統工藝,是一種技術手段,是一種設計方法,還是一種思辨邏輯? 抑或全部都是? 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使其語義變得籠統而微妙起來。但不論怎樣,由推演到范式,由程序到物態,由類像到語法,由內核到外延,圍繞它的創新活動大量出現,進一步推動了相關理論與創作的發展。當我們將視野轉向創新視域中的“編織”時,虛實、跨維度、符號等特征或許可以作為研究的重點,為后續的創新設計實踐提供新的思路。
一、虛實:由實而虛與以虛馭實
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編織”工藝開始打破“實”的原貌,逐漸向“虛”傾斜,由實而虛的發展趨勢為創新設計應用激活了更多可能性。區別于傳統編織工藝的手工化制作,數字時代設計師們憑借更加高效且智能的手段完成與機器、圖紙、作品之間的對話。現如今,大量從業者通過人工智能、數字建造等手段,對“編織”的組織架構、產品物件等進行規劃重組乃至拓展、創造,使相關生產活動從工地、作坊轉移至智能廠區、機器人流水線。從前以作坊為單位的生產活動雖然鮮活直觀,但是人與物直接對話的傳統模式在現今快節奏的社會環境下已日漸式微。因此,當我們經歷了漫長的經驗造物階段后,以匠人的“實”作為主要生產力的時代已漸漸落下帷幕,虛擬化、數字化逐漸成為編織工藝的未來發展主題。在此背景下,一些與編織相關的概念設計正在變為現實。比如谷歌研發了一款Project Jacquard 面料,他們把芯片、導線等電子材料直接織進服裝中。[3]88用戶在織物上進行觸控操作,借助導線將數據傳輸至芯片,最終達到遠程操控設備、感知現實的目的,甚至為連接虛擬世界做好了準備。此時的“編織”已成為一種連接虛擬與現實的重要介質。又如Teamlab 藝術團隊通過跨域藝術創作來探索藝術、科學、技術和自然界的交匯點。由藝術家、程序員、工程師、CG 動畫師、數學家和建筑師等各領域的專家組成的設計團隊在虛擬技術的幫助下,使光影的表現形式超越于物質層面。相關作品通過實時投影、體感交互等方式,將以往局限于屏幕上的影像投射至整個空間,從而強化作品的可變性與創新性。此時,對實物的映射不再是作品的主題,觀賞者以光為媒,編織疊影,體現為超現實的“體”與“空間”,材料與物象都被虛化了。
在設計者把傳統工藝置于數字平臺上進行創新性設計的同時,人們也迫切希冀虛擬空間中的產物能夠轉化到現實生活中,“以虛馭實”相應地成為實現這一過程的核心手段。簡單來說,虛擬化的數字技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并控制設計實踐的發展,并進一步探索未來設計發展的可能性。作為當下最熱門的數字技術之一,機械臂建造便以虛擬化的數字平臺為中介,利用材料自身屬性,通過算法的開發將外部模具的需求降至最低,從而更直觀地挖掘材料自身潛力,在“以虛馭實”的過程中達到設計目標。以ICDITKE②的設計實踐為例,其多年前就以數字化、機械化的方式針對纖維技術進行了大量實驗性研究。在其設計的仿生展館昆蟲亭子(圖1)中,設計師們便借助機械臂建造的技術手段,研發出一種用于模塊化雙層纖維復合結構的纏繞方法(圖2)。具體來說,這種機器人無芯纏繞方法使用兩個協作的六軸工業機器人,在機器人固定的兩個定制鋼框架效應器之間纏繞纖維。雖然每個組件的邊緣取決于效應器,但最終的幾何形狀是通過隨后鋪設纖維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將在樹脂中浸漬過的纖維束在兩個效應器框架之間相互拉緊,再將纏繞的纖維相互重疊并拉緊,以使二者相互形變,最終按照計算機生成的獨特纏繞句法程序完成雙曲面模塊的制造。整個系統憑借計算機不斷更新的反饋與效果模擬,使復雜形態中每個部件的纖維排列、密度和方向都精確按照建筑結構和制造方式進行校準與優化,突破了傳統纖維材料與形式的制約。可以說,作為建構技術的一部分,計算機的纏繞算法也成為“編織”的一種虛擬語言并被應用于創新設計領域,“以虛馭實”的概念也因而得到了充分展現。

圖1 ICD-ITKE 設計的昆蟲亭子仿生展館及其單元模塊示意

圖2 ICD-ITKE 建構技術圖解示意
二、跨界:模糊的邊界
近現代以來,人們對具象物的認知度逐漸提高,這種高度認知的自信似乎伴隨著隔閡的情緒將物件品類甚至專業門類目別割裂開來,學科壁壘在森嚴的劃分制度中悄然形成。然而,早在19世紀,戈特弗里德·森佩爾(Gottfried Semper,1803—1879)便擺脫建筑史固有認知,認為建筑是由編織藝術發展而來的,建筑就像織物,起到保護、覆蓋、包裹和圍繞的作用。[5]124“編織”的語義也隨之衍生到了更注重構造的建筑領域。森佩爾所提出的理論在融合紡織與建筑的同時引發了行業共情,為后續相關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這在當時顯得尤為重要。進入20世紀,普利茲克獎得主約翰·波特曼(John Portman,1924—2017)提出的城市編織理論則進一步將編織與建筑的聯系納入更為宏觀的城市設計視域。該理論站在整體的城市立場,關注與協調建筑群的體態、尺度、肌理、材料等元素之間的關系,使其具有內在統一性,從而營造一個和諧統一、整體有機的城市。[6]36當具體到城市的路網系統、供能系統時,它們的經緯、避讓、穿插、放行、正逆等設計邏輯與編織邏輯相互對應,城市編織理論也由此得到證實。總的來說,當功能主義大行其道,多數具象物被人們解構剝離至物態本源,這種突進更似抽象意識的破土飛升,仿佛讓人們于萬物中找到統一的關鍵詞,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學科壁壘。當下,人們已經習慣于從不同視角來審視研究對象,這就為不同學科提供了多元而科學的思考路徑,人們得以將關系網、體系網、神經脈絡、計算機編程、科學模型、文藝作品線索等與“編織”聯系起來,并對其進行交叉研究。然而,理論研究的創新難以完全支撐設計實踐,因此,對“編織”材料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同樣值得關注。
創新設計的重大突破離不開材料的跨界發展,而基于學科跨界,材料與物理、化學、信息等的融合已隨著科技的發展進一步加強。長久以來,編織材料主要以細密的絲狀產物為主,相對固定的表現形式約束了人們的認知。伴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理念的創新,“編織”無論在其形態上還是行為上,都呈現出跨界的態勢,并在復合材料出現后初見端倪。編織材料通常以自然纖維的面貌出現,如植物中的纖維材料、動物中的膠原蛋白、昆蟲和甲殼類動物中的幾丁質等,雖然僅寥寥幾類,但我們不得不驚嘆,大自然通過改變纖維的排列方式和密度,以及纖維矩陣中的化學成分,在有限的材料調色板上,建立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樣化系統。該系統跨越多個層次結構,其固有的各向異性也跨越了從微觀到宏觀的幾個量級。大自然利用自然纖維系統可能存在的異質性和局部變異性,進化出了更多的纖維材料,使得纖維材料品種多不勝數。即便這樣,在人類想象力的驅動下,現存的纖維材料種類對人類不斷擴大的需求而言仍然顯得捉襟見肘。因此,當所需材料的屬性大大超出自然范疇時,人們便會通過各種干預手段進行材料創新,借此跨越“編織”在形態與行為層面上的界限。以碳纖維的制作過程為例,科學家首先對自然纖維進行碳化、石墨化處理以制得碳纖維,再采用前驅纖維作為原料,使用熱處理工藝制得碳纖維長絲,最終將碳纖維長絲與玻璃纖維交織結合起來,獲得新型復合材料。在具體實踐中,上文所提到的ICD-ITKE 便是以碳纖維束纏繞玻璃纖維的方式來對其創新設計作品進行搭建(圖3),從而滿足設計師對構建物穩定性的要求。由此可見,在材料的跨界創新中,科學家與設計師們突破了傳統編織技術在建造領域的瓶頸,憑借新型復合材料的特性來織建更為復雜的作品,從而實現了學科跨界,使邊界變得模糊。

圖3 ICD-ITKE 作品中碳纖維與玻璃纖維的纏繞構件
三、維度:多維與擬多維
創新設計理念所提倡的技術交叉與思辨,使傳統“編織”在新技術中得以延續。新技術的出現不僅促進了數字建造與計算機算法的結合,還跨越維度的界限,在科學和藝術之間架起了橋梁。相較于以往平面化、裝飾化的編織藝術作品,現如今織物已能夠在藝術家的創作中輕易形成類似莫比烏斯環、折疊空間、矛盾空間等復雜形態,從而使“編織”以多維的表征形式拓展了其自身屬性。因此,編織的概念已經從傳統纖維藝術中經緯線的小空間中釋放出來,通過延續、解構、再創造,衍生到整體的建筑空間甚至更大范圍的戶外空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洛桑國際壁掛雙年展上,當人們還在探討壁掛作品是否應該擺脫傳統平面繪畫模式時,波蘭藝術家阿巴卡諾維奇(Magdalena Abakanowicz,1930—2017)的作品《紅色阿巴康》,便創造性地以其懸掛在空中并向前突出刺狀物的構成形式,向世人宣告編織已不再局限于靜態表達(圖4)。[7]27在這件作品中,鋒利的刺刀狀物體完全穿破了圍合的橢圓形織物,犀利地指向遠方,在偶發的形態中挑戰了原有創作觀念。由此可見,阿巴卡諾維奇作品中自發性、偶發性的創作技巧,不僅詮釋著靜態作品的多維屬性,同樣也擴展了“編織”作品創作手法的無限可能。

圖4 瑪格達萊娜·阿巴卡諾維奇《Abakan Red》(紅色阿巴康),1969
如果說時間與空間的介入使“編織”擁有了多維特性,那么建筑設計視域中的分形與拓撲理論則幫助“編織”順理成章地跨入了擬多維的平臺。曼德布羅特(Benoit B.Mandelbrot,1924—2010)在《大自然的分形幾何學》中首先提出了分形(fractal)這個特定的詞語,開創性地將分形集合定義為部分與整體以某種所呈現出的形式相似的形,將分形理論引入了數學領域。[8]19而林秋達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于分形理論的建筑形態生成》[9]19中將分形理論引入建筑設計領域,利用分形理論的自相似性與多維性,提出了建筑設計應更加注重建筑自身乃至與環境之間的體量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傳統建筑設計觀念。具體來說,在分形理論的指導下,建筑結構可以被分為多個子系統,而眾多子系統仍然由更低一級的系統組成,最終以一種循環遞進的形式進行維度上的轉化。其中,“編織”的網格、偏移、對稱、互補、循環、遞進等邏輯無疑符合分形理論的跨維度特征,為“編織”的擬多維呈現提供了可能(圖5)。以建筑表皮的設計為例,“編織”便在分形理論的基礎上呈現擬多維的構成形式:一維線條形成的二維表面相互交疊纏繞,從而使表皮具有一定的空間深度,最終構成了看似動態的三維建筑表皮。[10]43

圖5 利用Chaotica 分形軟件調整公
分形理論探討的是形態維度連續變化的問題,而拓撲學探討的則是形態或空間在連續性變化下的不變性質。[11]12可以說,拓撲學方法論的發展,很大程度上為以數字技術為主的創新設計提供了技術理論支撐。而拓撲學中的拓撲變形法在數字技術的運作下,拓展了設計作品的可能性與可變性。“編織”契合拓撲變形法,利用各種形式使客體得以流變,最終達到無限預想的目的。就如一件織物,在材料恒定的情況下,樣式與針法可以無限變化,最后在形態或空間的變化中得到呈現(圖6)。由此可見,“多維”從此不再是設計師們提出的口號,而成為一種創新設計樣態。

圖6 編織的拓撲變形參數生成的“編織”圖形
四、符號:承載與托喻
編織與符號的聯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的結繩記事。《周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1]87《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12]458由此可見,“編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行為與符號的“表達面”與“內容面”。和語言文字一樣,作為人造物的“編織”同樣是人類活動的直接行為符號,例如,通過符號所承載的信息,人們可以了解苗繡與雕題文身的關系,知曉為什么掇繡粗狂而自由,理解管羽繡(羽毛管刺繡)背后的游牧文化等。可以說,作為人類文明的載體之一,也作為學者們的歷史解碼器,編織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在藝術與設計層面,人們不僅提取編織的符號系統與樣式邏輯以為己用,也汲取其漫長篤厚的歷史人文傳統,以將編織行為與符號意義納入創新設計領域。具體來說,編織行為的符號承載與托喻功能可以體現于對自然界的映射以及對藝術形式的創新上。
人類對符號的探索最初源于對自然界各種生物的描繪。但是,人的想象力總是先于大自然而疲竭。[8]4在進化過程中,人類不斷模仿自然,從而提高生產力。因此,科學家們提出了以研究并模仿自然界生物體為重點的仿生學理論。從人類模仿蜘蛛進而織網捕魚開始,“編織”便與仿生學有了交集。從生產工具到生活用品再到建筑結構,許多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發明都源于仿生學。有別于建筑師圣地亞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1951— )在其仿生建筑作品中對人體結構特性的探究,ICD-ITKE 更注重研究自然界動植物所蘊含的微小結構特性,并借此探究編織行為的符號意義。
ICD-ITKE 利用分形、拓撲、仿生等相關知識,創作了一系列創新設計作品——“編織建筑”(圖7)。在設計前期的研究中,ICD-ITKE 發現并證實甲蟲翅膀為其腹部提供的強大保護是搭建仿生建筑形態的合適榜樣。這些輕質結構的實現條件,也使得新型碳纖維增強聚合物材料具有施展空間,成為實現復雜自然幾何形的最好材料。在具體設計中,ICD-ITKE 用計算機生成面貌不一的編織樣式,以機器人制造的方式將生物結構轉換成仿生結構。因此,“編織”便以符號的形式承載人們對自然界生物的托喻。

圖7 ICD-ITKE 創作的系列 “編織建筑”作品
“編織”作為人類活動的行為符號,同樣推動了藝術形式的創新。正如藝術家克里斯托(Christo,1935—2020) 與珍妮·克勞德(Jeanne-Claude,1935—2009)夫婦,雖然他們拒絕被定義,但是他們跨越藝術、建筑、工程等領域,暗合創新設計之意。他們利用織物來包裹建筑物、構筑物、植被甚至地貌,將織物符號和包裹行為進行極致放大(圖8)。然而在克里斯托夫婦看來,“包裹”不是他們作品的共同點,這些織物符號只為作者與受眾提供解讀信息。

圖8 克里斯托、珍妮-克勞德《包裹國會大廈》,1995年
五、結語
從上述“編織”行為的四大特征中,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已成為創新設計中“編織”的主要外顯要素。然而透過表象,促使其發展的原動力更應該被關注。
自古以來,對“編織”的闡釋往往集中于功能與形式兩方面。現代主義時期,物的簡潔實用符合大工業生產的要求,設計的功能性得以凸顯。隨后,由于經濟的發展與思想的解放,相對單一的形式已無法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功能性不再是設計的第一要務,“形式追隨功能”的理論也顯得不再應時了,“形式追隨理念”的觀點因而被提出來。所以,在保守與激進的歷史漩渦中,人類文明總是由創新理念推動的。進一步說,創新理念揭示了不同時期個人與社會的追求,并直接與設計作品相關聯。人們將創新理念和人文精神融入對社會、自然、物質的思考中,最終使“編織”在思辨中得以升維。紡織品藝術家安妮·阿爾伯斯(Anni Albers,1899—1994)曾提出編織線需在自我表現的同時形成自身風格的觀點,她將紡織技術與抽象藝術相結合,讓古老的工藝成為一種現代藝術的載體,沖破了“大藝術”和“小藝術”之間的嚴格邊界。而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數字技術與人文哲思的進步,使得“編織”突破技藝與時空的限制,阿爾伯斯的呼聲因此得以延續。由此可見,技術與理論在不斷更迭,形式與功能也瞬息萬變,唯有追求創新的理念永恒不變。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創新視域中的“編織”異構時,其已在實用與去實用、具象與抽象中的交替前行中留下了深刻印記,并向世人們宣示著自己的影響。具體來說,“編織”不僅在虛擬化、數字化的進程中跨越了學科與工藝的邊界,還在多維表征形式下擺脫以往具象化的束縛,進而成為一種邏輯與符號。可以說,“編織”的定義在物與行為的滲透中早已實現擴張,而科學、技術、人文、哲思等關鍵詞,也始終盤旋在“編織”周圍,推動著“編織”的創新。本文期望豐富“編織”在創新設計中的語義,為創新設計提供部分補充性樣本,進而提出創新理念是“編織”發展原動力的觀點。這或許可以改變從包豪斯時期至今,設計學科中人們一直視“編織”為邊緣門類的根深蒂固的認知,從而為創新視域中的“編織”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① 離卦,上下皆為離,離為目,也就是網眼。離卦的二三四爻為巽卦,三四五爻為兌卦(覆巽),巽為繩。兌伏卦為艮,艮為手。所以,整個離卦,就是用手編結繩網的“象”。
② ICD-ITKE 即德國斯圖加特大學計算機設計學院(ICD)、建筑結構與結構設計學院(ITKE)。